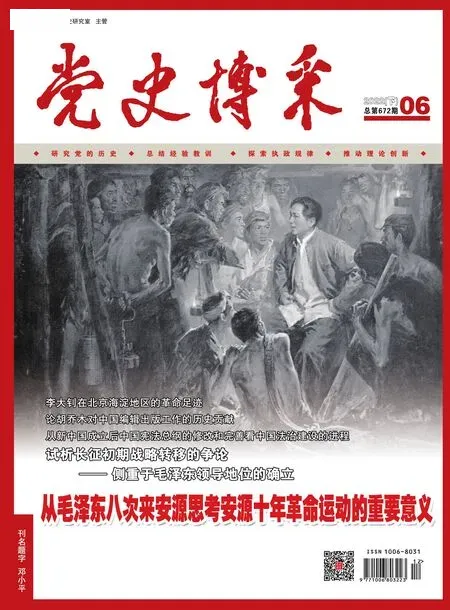试析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争论
——侧重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孙建猛
学术界目前对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研究成果颇丰。①本文立足于目前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分析了党中央在长征初期围绕战略转移所展开的三方面争论以及毛泽东在其复杂性中所秉持的正确立场,对长征初期的战略转移推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一、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与党内的不满
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接连遭到战役失利,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腹地暴露出来,这不得不使党中央开始考虑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不久后,共产国际就对中央的来电进行复电,表示“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②由此,战略转移的计划正式形成。
战略转移在当时是符合革命的客观形势的,然而中央对此的准备工作却存在很大的问题。问题表现在,一是战略转移的准备事宜完全被“三人团”所操纵,二是战略转移的下级传达工作不到位,三是战略转移人员去留问题存在宗派主义作风。“三人团”是指1934 年夏所成立的专门负责战略转移的机构,仅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位成员在其内。且在分工问题上,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并没有战略转移重大事宜的决定权,决定权完全被博古和李德所操纵。下级传达工作不到位是指在战略转移的整个准备时期乃至长征初期,战略转移只有“三人团”和少数几个人知晓,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和战士都不知道,即便是有些政治局委员也是如此。人员去留问题存在宗派主义作风是指在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情况下,一部分人员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打游击,而人员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博古手中,博古有权将自己认为一贯右倾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战略转移准备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充分揭露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领导问题上压制民主的作风,这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针对“三人团”把持准备事宜的情况,彭德怀曾回忆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③而在下级传达工作不到位问题上,杨尚昆也曾回忆说,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到瑞金才知道的”。在人员去留问题上,当时中央编队时流传的“六亲不认”的口号更是充分揭露了准备工作中所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伍修权更是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④
战略转移准备工作所引起的民主问题争论是巨大的,也因此成为了长征初期广大指战员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猴场会议上,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⑤的决定,正是中央针对此问题所作出的。而在遵义会议上,更是对李德在军委内部压制民主的情况进行了直接而严厉的批评。会议认为“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⑥,认为政治局“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并最终作出了取消“三人团”的决定。
纵观长征初期中央内部围绕战略转移准备工作所引起的民主问题的争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表态,但是他和其他党内领导人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必须纠正军委乃至党内所存在的压制民主问题。因此,这场争论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明确的政治支持,但是在客观上却推动了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成为了促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确立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战略转移的路线选择与毛泽东的力争
鉴于红6 军团已经西征,党中央在制定战略转移计划时的最初目的就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⑦,然后北上与红2、6 军团汇合。其原因,一是红2、6 军团在湘鄂西已经建立有稳定的根据地,可以容纳中央红军的大规模转移;二是红6 军团西征原本就是意图“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⑧,其西征已经为中央红军的转移探了路。
战略转移最初的路线选择并没有战略意义上的错误,中央红军在过湘江之前一直是力求与红2、6 军团会合的。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随着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战术调整,继续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显然已经不符合客观形势。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国民党方面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的意图,在湖南、贵州一带设置了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会师。
正因为上述情况,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部队翻越老山界以后,就向中央提议放弃北上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赞同,然而博古和李德没有同意。紧接着在通道举行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与会者针对红军行动方向进行了专门讨论。博古和李德坚持原有计划,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在会议表决中,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⑩,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占据了上风。会后,中革军委明确了“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⑪。
此后,中央又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博古在会上坚持此前的意见,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他在会前向周恩来表述了再次北上的意见,毛泽东同样如此,坚持此前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也最终决定予以采纳。会议决议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⑫之后,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获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支持。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主张,认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⑬
经过了以上三次会议关于战略转移路线选择的反复争论和毛泽东的力争,毛泽东改变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不利局面,获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政治支持,使自己的意见在政治局里占据了上风。这不仅使中央得以继续西进,而且推动了接下来遵义会议的召开,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初步获得了党内的政治支持,成为促使遵义会议上形成压倒性的局面,并推动毛泽东成功入选政治局常委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战略转移的战术错误与毛泽东的批评
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然而在战术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其错误主要是指,一是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二是消极避战,实行了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在第一点上,主要表现为部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记、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⑭而在第二点上,主要表现为“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像叫花子打狗似的,边打边走”。⑮这种战术错误给长征初期的红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直接导致了中央红军在湘江一带战斗了数日,人数也锐减为三万多人,成为了长征以来打得最激烈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
湘江战役的失败,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广大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错误指挥的不满。刘伯承曾回忆说,广大干部“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⑯杨尚昆也曾写道“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⑰聂荣臻也认为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⑱
如果说广大指战员只是产生了对错误战术的不满,那么毛泽东则是首先挺身而出对错误领导进行批评的人,而且其批评不仅包括对错误战术的批评,而且引申出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军事路线的批评。早在湘江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红军过湘南时提出“乘国民党各路军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⑲,以求改变被动局面,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通过。且毛泽东在进入湘南以后,就已经开始对王稼祥、张闻天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湘江战役之后,消极防御的战术错误被明显地纠正了过来,毛泽东所坚持的运动战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因而毛泽东开始将批评的重点从战术错误问题转向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进入苗族聚集区之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开始针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评,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之后的黎平会议上,会议针对此问题再一次发生了争论,但是鉴于中央内部存在巨大争论,目前战场形势又十分严峻,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再对此问题进行开会总结。
因此,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的观点认为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确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在失败问题上更多地强调客观原因。周恩来在副报告中则对此表示了反对,认为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张闻天在“反报告”中明确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则是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⑳,王稼祥在军事路线问题上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会上,只有博古、李德和凯丰表示反对,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至此,毛泽东在中央军事路线问题上和与会者大多数持有一致立场,都明确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获得了除博古、李德和凯丰之外的所有人的政治支持。这种广泛的政治支持,是政治局会议表决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推动大会决定毛泽东入选政治局常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也由此初步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结语
中共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的,因此获得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就成为毛泽东确立党内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恰为毛泽东获得政治支持提供了帮助。原因在于战略转移工作有三个层面的错误,而这三个层面的错误又直接引发了党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凭借着正确的立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且其他领导人也反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而毛泽东获得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也就成为了必然。
不仅如此,这三个层面的错误对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来说还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党内民主问题既是无形的,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在党内民主问题上获得过政治局与会者的明确政治支持,也是影响最小的,因为民主问题本就不是长征以来党内的主要矛盾。在路线选择问题上,毛泽东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了与会者的支持,然而支持却是有限的,仅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支持。而这既源于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规模过小,许多政治局委员因为战场形势不能如期到会,也源于路线选择的问题并没有暴露出党内最主要的矛盾。在战术选择问题上,战术错误是次要的,其背后引申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才是主要的,是党内彼时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因而构成了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也因此获得了政治局的最大政治支持。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研究多集中在是否确立了领导地位、确立领导地位的过程、确立领导地位的性质、确立领导地位的话语表述等方面,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影响因素的论述较少.其代表性成果有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J].北京:党的文献,2016.赵炜.红军长征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J].陕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李方祥.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实辩证[J].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56.
③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3.
④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4.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6.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9.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四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51.
⑧红军长征·文献(第一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12.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77.
⑩奥托·布莱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边刊社,1980:124.
⑪红军长征·文献(第四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171.
⑫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2.
⑬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5.
⑭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04.
⑮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5.
⑯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
⑰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4.
⑱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32-234.
⑲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6.
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