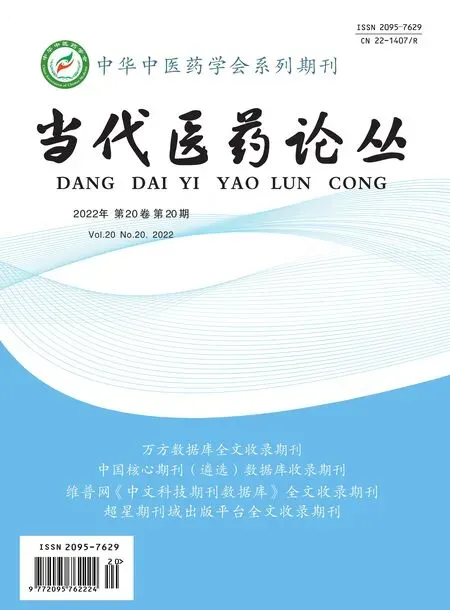基于升降学说从浊毒论治高尿酸血症
荣晓瑞,周 静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近20 年来我国高尿酸血症发病率升高了10%左右,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且逐渐出现向年轻化方向发展以及有家族遗传风险因素等流行特征[1]。高尿酸血症不仅是痛风相关疾病的直接病因,还与许多疾病,如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代谢综合征、脑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的发病以及病程进展密切相关[2],因此早期治疗本病尤为重要。高尿酸血症患者存在饮食不节,摄入大量高嘌呤饮食,或饮酒、久坐不动等不良生活方式而导致的体内尿酸生成增多或排泄障碍,从而导致血尿酸异常升高。此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多仅实验室检查可见血尿酸升高而无关节症状,现代医学针对此病早期多是通过控制饮食及生活方式干预,常不能引起患者足够的重视。中医无高尿酸血症相应病名的记载,根据其临床特点及症状,结合长期的临床诊治实践,大致将其归为“浊瘀痹”“血浊”“膏浊病”等范畴[3-5]。笔者导师周静主任在临床上基于升降学说从浊毒论治高尿酸血症,疗效尚佳,现介绍临证体悟如下。
1 高尿酸血症的病因病机
1.1 脾胃为升降之枢纽
气机升降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古人通过对自然界气机升降客观规律的总结,取象比类至人本身生命活动亦有赖于气机的升降出入,正所谓“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故气机升降失常为疾病发生及进展的重要原因。李东垣于《脾胃论》中言:“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机体气机升降的主要场所为脏腑,而诸脏腑中脾胃居于中焦,升清降浊,运化水谷精微至全身,亦下传糟粕至体外。脾气充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得以充养,脾胃内伤则枢机不利,清浊不分。
水谷进入人体, 若不能正化精微,或化为精微后不能正常地为体所用, 以及所化糟粕不能及时排出,则必瘀滞于内变生他邪。导师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现代医学所讲高尿酸血症的病理过程,人体内正常浓度的血尿酸即为体内水谷精微。高尿酸血症多因饮食不节,嗜食肥甘等不良生活习惯发病,可使脾胃虽未伤却运化不及,或伤及脾胃脏腑使升降失司枢机不利,均可致已摄入体内的水谷不得正化而痰湿瘀浊等邪内生,而后瘀滞体内,进一步阻碍气血之运行,最终发为高尿酸血症。
1.2 气、血、津液之升降
脾胃升降为一身枢机畅利之关键,气、血、津液亦有升降。《丹溪心法·六郁》言:“凡郁皆在中焦”,至于郁之原因,乃气机“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不升,当降者不降……”元代朱丹溪倡导治疗注重调畅气机之升降。气滞多与情志相关,现今人们生活压力远甚于古人,情志不舒多已为常态,气先为病首责于肝[6],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亦调节脾胃气机升降。肝气郁结,木不疏土,影响脾胃之升降,若再加摄入多肥甘厚味,则水谷精微失于运化输布化生痰浊瘀毒留滞体内为害,可发为高尿酸血症。在病变过程中病机常可发生转化,“气郁久则必见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气滞日久可致血瘀,痰湿内停日久,阻碍气血之运行,亦可导致气滞或血瘀;痰湿、血瘀又可加重气滞;气滞、痰湿、血瘀日久均可化热,而成郁热、痰热、湿热、瘀热。高尿酸血症病程的进展不定,气滞、痰湿、血瘀的程度及其相互转化情况也会不定。
1.3 高尿酸血症病理产物的特殊性
吴深涛教授在内分泌代谢性疾病领域提出“浊毒”致病的理论[7],认为“脾不散精”,水谷不得正化则浊邪内生,浊瘀于血分,则易生血浊等病理产物,浊质腻秽易壅滞于血,易“腐秽生毒”,进而由浊致毒以致浊毒内蕴。笔者导师基于此理论进一步认为,人体内正常浓度的血尿酸为体内水谷精微,变化有常则“变化而赤是为血”,如若体内代谢失常,脾胃升降失司,水谷则不化精微,而生壅滞黏腻之气,久则瘀积于血分而生浊邪,壅塞阻滞缠绵成毒为害,未能及时代谢而持续升高的血尿酸就是机体内生浊毒之邪的物质基础,体内长期存在的高血尿酸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浊毒内蕴发展的过程。因此,脾胃升降失司,浊邪内生,由浊酿毒的病机变化过程可以认为是高尿酸血症发生发展的关键病机,浊滞壅塞影响气、血、津液的升降运行亦可化生痰湿瘀毒,浊毒亦易与气滞、痰湿、瘀血等邪气相兼为患损害脏腑正气,进一步加速疾病进展,使病程更为缠绵易反复。
2 治法方药
2.1 化浊解毒法贯穿治疗始终
对高尿酸血症越早进行干预,越能有效延缓和阻止疾病后期进展为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此阶段没有特别明显的临床症状,仅以化验指标异常为主,西医没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中医可以根据舌脉遣方用药。导师认为,对有些辨证为脾虚气滞浊淤为主的患者,此时体内尚未酿毒,治宜以健脾化浊理气为主,并防由浊酿毒;而有些辨证属浊淤已化毒者,治宜尤重化浊解毒。浊瘀已化毒者,应以化浊解毒而治,而浊邪尚未致毒者,依据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亦应以化浊解毒治之。此两种辨证情况虽为高尿酸血症疾病进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但治疗时都应将化浊解毒法贯穿始终。不同的是,脾虚气滞浊淤尚未成毒者,除运用化浊解毒法未病先防外,还应注重调理脾胃升降;浊瘀已化毒者,化浊解毒的同时还应根据气滞、瘀血等相兼邪气的程度用药兼以理气活血。
2.2 化浊解毒方加减
吴深涛教授基于浊毒理论自拟化浊解毒方用于治疗浊毒内蕴证消渴病患者,疗效显著[8-9],本着高尿酸血症的病机特点及中医“异病同治”的原则,导师认为亦可使用此方化裁治疗高尿酸血症。化浊解毒方由升降散合大柴胡汤化裁而成,以黄连、佩兰为君药,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佩兰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共奏化浊解毒之基;升降散取自于《伤寒温疫条辨》,组方以大黄、蝉蜕、姜黄、僵蚕为主,善调脾胃之枢机,“一升一降……杂气流毒顿消矣”,用于高尿酸血症,疏利脾胃气机可绝浊毒化生之源;大柴胡汤是治疗少阳、阳明合病的专方,用于高尿酸血症,可通腑泄浊,排已成之浊湿瘀毒。故化浊解毒方可使脾胃升降相因,未成之浊毒无处生,已成之浊毒有处化。
对于脾虚气滞浊淤尚未成毒者,若兼脘腹痞满等脾胃升降失司之症,脾虚湿困症状重可加用党参、白术、茯苓、薏苡仁等健脾益气渗湿之品,湿浊重者可加用芳香之品如草果以醒脾和胃,芳香辟浊;若兼呕恶吞酸者,可加黄连、吴茱萸取左金丸泻火降逆之义;若兼嗳腐吞酸、大便臭秽等症状,提示食积于胃而见胃气不和,可加用山楂、神曲、莱菔子以消食导滞。对于浊瘀已化毒者,若兼口苦、口黏、大便黏滞不爽等湿热之象,可加用车前子、泽泻、龙胆以加大健脾清热燥湿之力;若兼心烦失眠者,可加栀子、淡豆豉以清心除烦;若痰湿郁滞日久,伴有血瘀表现如舌暗或有瘀斑的患者,可酌加当归、川芎、丹参等以活血行气。
3 医案举例
案1 李某君,男,30 岁,2020 年6 月12 日初诊。
患者半月前于本院体检结果示:血尿酸(SUA):469μmol/L(140 ~414μmol/L),甘油三酯(TG):2.98mmol/L,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LDL-C):3.87mmol/L,总胆固醇(TC):5.41mmol/L。现症:口干、口黏,晨起明显,平素懒动倦怠,大便2 ~3 日一行,黏滞不爽,有解不尽感。舌黯略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根浊腻微黄,脉弦。此为脾虚升降无力,浊毒凝聚稽留体内,兼肝郁气滞之象。以化浊解毒方化裁:柴胡15 g、黄芩15 g、党参15 g、茯苓20 g、姜黄20 g、白芍15 g、佩兰15 g、黄连10 g、枳实10 g、炒僵蚕10 g、蝉蜕6 g、川芎15 g、桃仁15 g、甘草10 g、熟大黄6 g。14 剂,水煎服,每日一剂早晚分服。
6 月26 日 二 诊: 患 者 昨 日 复 查SUA:418μmol/L,口干、口黏较前缓解,大便1 ~2 日一行,质黏滞不爽,解不尽感较前减轻,情绪急躁易怒较前减轻,仍倦怠懒动,舌黯略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腻,脉弦。予前方去黄连,加虎杖20 g、炒白术12 g。14 剂,服法同前。7 月10 日三诊:患者复查SUA :372μmol/L,TG :2.2mmol/L,LDL-C :3.02mmol/L,TC :4.57mmol/L。现症:大便1 ~2 日1 次,便质偏软,无解不尽感,无口干、口黏,倦怠懒动较前减轻,舌淡润,边有齿痕,脉濡。予前方去大黄、僵蚕、蝉蜕、川芎、桃仁,党参加量至30 g,加炒薏苡仁15 g。14 剂,服法同前。后患者继续复诊2 月余,中药随复诊症状变化情况加减,患者SUA 水平始终波动在330 ~360μmol/L 之间,血脂水平稳定。
按:本案患者首诊发现血尿酸、血脂均升高,导师以化验指标结合症状、舌脉辨证施治。患者口干、口黏为浊邪上溢于口,大便黏滞不爽为湿浊淤邪气下泄,平素倦怠懒动、舌黯略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可见有湿浊之邪困阻脾胃,脾胃之气已有虚损之象;舌脉亦示湿浊壅塞体内且有化热之征。其根源乃脾胃枢机不利,升清降浊失司,终致浊淤蕴结化热,故以理脾化浊解毒,酌加川芎、桃仁等化瘀之品。二诊时患者诸症缓解,SUA 下降51μmol/L,大便仍黏滞不爽,但排便频率增加,且解不尽感较前减轻,此为湿浊热瘀之邪从大便而出,予前方去黄连,加虎杖、炒白术以增强理脾利湿排浊之力。三诊时患者血尿酸检测值继续下降,诸多不适已缓解,此为湿浊显去之象,但仍倦怠懒动且舌象仍有虚感,故予前方去排浊化瘀之品,党参加量至30 g,加炒薏苡仁15 g,以增健脾之力。此病案理脾与化浊同用,健脾气,祛湿浊,解瘀毒,诸药合用效果满意。
案2 李某,男,27 岁,2020 年9 月4 日初诊。
患者3 月前于当地医院行阑尾炎切除手术住院治疗,其间发现SUA:484μmol/L(155 ~357μmol/L),诊断为高尿酸血症,予口服苯溴马隆片(具体不详)治疗,1 个月后患者复查SUA 示368μmol/L(155 ~357μmol/L), 患 者 自 行 停 药,2 天 前患 者 于 我 院 复 查SUA, 结 果 示:471μmol/L(140 ~414μmol/L)。现症:口干、口苦,平素情绪急躁,心烦易怒,偶有胸闷,无心慌、心悸,胸胁痞满,食后尤甚,面部及后背部反复新起痤疮,色红略暗,痒感明显,大便3 ~4 日一行,干结难解,偶需服助排便药物方能解,舌暗红,苔黄浊腻,脉弦。此为浊淤化热蕴毒,兼有肝郁气滞之象。以化浊解毒方化裁:柴胡12 g、枳壳12 g、熟大黄18 g、炒僵蚕10 g、蝉蜕6 g、黄连12 g、黄芩15 g、姜黄20 g、当归15 g、白芍15 g、川芎15 g、桃仁15 g、牛蒡子20 g、升麻10 g、茯苓15 g、甘草10 g。7 剂,水煎服,每日一剂早晚分服。
9 月11 日二诊:患者口干、口苦较前减轻,面部及后背部痤疮颜色变暗,病灶范围变小,近日无新起痤疮,情绪仍急躁易怒,大便2 ~3 日一行,质干难解,舌红略暗,苔黄浊腻,脉弦。予前方去僵蚕、蝉蜕,加龙胆15 g、土茯苓20 g、延胡索15 g。14 剂,服法同前。9 月25 日三诊:患者复查SUA :437μmol/L(140 ~414μmol/L),口干、口苦已缓解,面部及后背部痤疮局部颜色变暗,范围缩小,未有新起,情绪急躁、心烦易怒较前减轻,大便1 ~2日一行,质尚可,舌红略淡,苔腻微浊,脉弦。予前方去川芎、桃仁,加炒白术15 g。14 剂,服法同前。10 月9 日四诊:患者复查SUA :388μmol/L(140 ~414μmol/L),诸症均已缓解,痤疮渐消,未有新起,大便1 ~2 日一行,便质可。舌红略淡,苔薄腻,脉弦。予前方继服14 剂。后患者继续复诊2个月,中药随复诊症状变化情况加减,SUA 水平复查在340 ~380μmol/L 之间。
按:初诊时患者口干、口苦,以及大便情况均为浊淤郁滞体内化热伤津之象;平素情绪急躁,心烦易怒,提示兼有肝郁气滞;面部及后背部反复新起痤疮,色红略暗,痒感明显,为浊瘀之邪外溢于肌表之征;舌暗红,苔黄浊腻,脉弦,亦为浊淤化热蕴毒,兼有肝郁气滞之佐证。故治疗应以清热化浊解毒,疏肝理气行血为主。二诊时,患者口干、口苦及痤疮情况有减轻,仍有情绪急躁、心烦易怒,大便仍干结难解,故加龙胆以增强清肝泻火之力,加延胡索以助行气活血,加土茯苓解毒之品以阻浊淤化毒。三诊时,患者SUA 水平下降,诸症亦有减轻,此为浊淤热毒得减之象,另加白术以健运脾胃。四诊时,患者复查SUA继续下降,故效不更方以巩固疗效。
4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发展,高尿酸血症患者人数大幅增加,由于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受环境、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其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从而错过其关键治疗时期,因此尽早对高尿酸血症患者进行防治干预,能够有效延缓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高尿酸血症的形成,与中医所讲脾胃升降失司和浊成毒蕴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导师基于升降理论从浊毒论治本病,方用化浊解毒方化裁,调理脾胃,畅行气血,化浊解毒,为中医治疗本类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