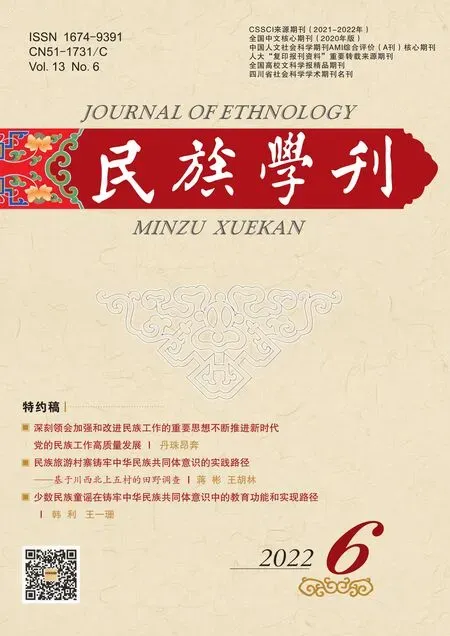从历史“方国”到神话“异国”的断裂与重构
——基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的考证
王 淼
近代以来,随着“神话”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学界常以神话和历史为两个对立的概念。神话常被视为想象虚构的故事,而历史则被视为对过去事实的记录。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疑古派”提出了将神话从历史中完全抽离的口号。之后学界对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展开了长期的讨论,钱穆、梁启超、茅盾、徐旭升、陈梦家、张光直等先生均参与了相关讨论,虽然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史与神话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实际上早在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即指出:“最初的神话故事都是历史。”[1]468同样,“一切古代世俗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故事。”[1]475回归到中国神话与历史本身,二者在早期发生与传播过程中往往是一个混合的整体,这便意味着神话本身包含着历史的素地,而这种包含关系也意味着历史存在“神话化”的机制。基于此,现代学者常对神话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进行追溯,如赵逵夫先生指出:“上古神话不是先民凭空编造出来的,只是在长期流传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事件加以集中或减化,也无形中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愿望体现在其中,使它同本来的事件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其内核仍然包含着历史的真实。”[2]4并据此对“夸父逐日”神话的历史内涵进行追溯。王宪昭先生则提出了“史性神话”这一概念,并对“蚩尤”神话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进行了辨析。[3]99-106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历史与神话之间相互转化原因和转化过程缺乏清晰而全面的认知,所以学界部分研究存在以“形而象之”便随意附会的特点,这在对《山海经》所载“海外异国”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学者麦克斯·缪勒在研究神话中非理性成分生成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语言疾病说”,认为其生成原因是语言与思维之间“裂隙”不断扩大的产物。虽然“语言疾病说”对神话中非理性成分产生原因的阐释有失偏颇,在19世纪后期的西方神话学界遭到了大量的非议。②但其研究思路提示我们,与语言、思维一样,历史与神话之间非理性成分的生成也可能与二者在传播接受过程中“裂隙”的不断扩大有关。故笔者不揣谫陋,以《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为例,探索其从历史“方国”到神话“异国”的断裂与重构过程及其生成原因,并求教于方家。
一、“贯匈”之义的争辩
《山海经》“海外经”部分记载了众多奇异的远方异国,而对于这些远方异国的原型追溯,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贯匈国”为例,《山海经·海外南经》载:“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一曰在臷国东。”下文又有“不死民……一曰在穿匈国东。”[4]181可知“贯匈国”即是“穿匈国”,其之所以以“贯匈”为名,是因其“为人匈有窍”。《淮南子·墬形训》亦有“穿胸民”,高诱注:“胸前穿孔达背。”[5]177然而“匈有窍”的原型谓何,历代多有歧说。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中具体引述了古人对此的两种主要阐释:第一,以《艺文类聚》引《括地图》、张华《博物志》以及周致中《异域志》为代表,皆沿“匈有窍”而比附神话传说,神异色彩颇重;第二,以郭璞注引杨孚《异物志》为代表,则强调“贯匈”实因东南少数部族特殊的服饰而得名。[4]181
近现代关于“贯匈国”的研究也多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去探索“贯匈”之义。第一类着重解答“胸有窍”,如周士琦先生认为“穿胸”乃是“穿鼻”之误,其来源于西南少数民族“穿鼻”习俗。[6]28耿立言先生认为,“穿胸”是后人对《山海经图》的误读,古图中穿胸而过的竹木其实是抬人行走于山路的滑竿,竹木穿胸取意为以杆抬人。[7]54第二类沿着杨孚《异物志》继续发挥,如吴永章先生认为“穿胸之民”当系因其服制而得名。[8]6这些研究各据所说,但往往忽略《山海经》内容产生的历史时代和地域背景,同时对于《山海经》成书时代和地域背景在文化上的继承性,以及相关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断裂与重构的特征也缺乏关注。只是在“形而象之”的基础上就加以阐释,乃至附会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民俗,产生了很多类似于“天方夜谭”式的歧说。虽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人类在原始思维下基于现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情境产生的信仰与神话传说具有共通性,但仍需考虑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地域环境、语言模式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不加限定随意附会,则不利于追寻问题的真相。
美国学者约瑟夫·马里指出:“一则神话无论多么富有传奇意味,它并不表示编造或纯粹的虚构,因为它通常包括共同体历史中所包含或涉及的关键问题,诸如共同体共同的祖先和边界的传奇。这些问题需要并能够催生关于历史的神话,因为它们不仅适于形而上学的神秘事物,诸如共同体的最初起源和命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真实的叙事是共同体成员所信赖并经历的事实,即便(或者正好因为)它们是神话的而非逻辑的或历史演绎的。”[9]4这也就表明像“贯匈国”这类远方异国的神话传说虽然有夸张虚构的成分,但是必然包含有历史的素地。从“贯匈国”所在的《海外经》的文本形式来看,《海外经》部分应是依据更古的图像而阐释,刘宗迪先生指出:“(《山海经》)这个图应该非常非常古老,在文字通行之前,经过漫长岁月到战国时代,这时候文字通行了,书写也方便了,这个图才被战国的学者复述为文字,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的祖本……图画是无法摆脱口头传统的,古图是依赖于口头传统而被人理解被人接受的。”[10]38实际上除了图像和口头传统外,文字的传承也是存在的,学界普遍认为《山海经》成书在战国时期,在秦汉间亦有补益。而以周原甲骨为例,商周文字明显存在传承关系。结合《管子·幼官图》以及发掘出土的战国秦汉间的帛书(画),则可以明确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着“图文结合”的“图书”模式。所以,主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所依据的“原始图文”必然会有相当体量的内容来自商代及西周时期,而这一时期记录这些内容的图像和甲骨文、金文字形以及相关口头内容的传承、断裂与重构的过程势必会对《山海经》成书时期的文本内容产生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观点,喻权中先生指出《海经》中的方国之名多数来源于对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所构成的古图中的方国名称、族徽等的再阐释。[11]10-12并指出“贯匈国”应即商代甲骨卜辞中出现的“毌方”。[11]86笔者认同此观点,但认为其说尚有瑕疵。
第二,对于“毌方”方位的认定,喻先生认为西周封置的“贯国”是商代“毌方”之后,在今山东曹县南,春秋属宋国。通览其书考证《海外南经》部分,喻先生有意将《海外南经》诸条均考定在豫东北鲁西北。但《海外南经》经文明有“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其考《海外南经》之首的“结匈国”即“葛”国,在今河南宁陵县北境。[11]29此地在商丘西北不远,作为“海外西南陬”似嫌不确。以近几十年考古发掘来看,殷商文明的辐射范围并不局限于中原,郭静云先生指出:“中原、西北、东北、鲁北、江浙、江南等前商文化皆参与‘殷商文明’的形成。”[12]11尹弘兵先生亦指出,南至江汉平原南部荆沙地区的“荆南寺类型所在地区虽与中原相距较远,但荆南寺类型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有较紧密的联系。”[13]69由此,则商代对于西南方疆域的认知应不止于今河南宁陵北境。
第三,喻先生在《海外南经》考中预设了前提,即以经文中“南山”为《诗·曹风·候人》之“南山”,即今山东曹县南山。[11]28关于先秦时期“南山”的地望,学界存在多种说法,③喻先生专取一说,似为不妥。而其上述观点的重要前提是《山海经笺疏》中郝懿行注“自此山以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时指出的“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也。”故喻先生以此山在山东。[11]28然而考北方方言称“蛇”为“虫”或者“长虫”者,基本覆盖了北方西起今甘肃陕西、东至今山东、北至今东北一部的广泛地区。郝懿行是山东栖霞人,故其言东齐人之方言,句中用“亦”字,就表明此并不具备特殊性,故以此为前提定“南山”在山东之地,于理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此处以“结匈国”“南山”在今河南东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的衔接地区。案《海外经》各经之间的关联,《海外西经》中在“结匈国”之北的“灭蒙鸟”亦应在这一区域内,故喻先生将“灭蒙鸟”考在春秋时期的蒙邑,即今商丘东北,在商王畿区域的东南方。但按照《海外西经》顺序,“灭蒙鸟”北即夏后启所舞之“大乐之野”,可喻先生考定“大乐之野”即今山西太原附近,在商王畿之西北。[11]155二者相距过远,几乎纵贯商王畿之地,似为不确。喻先生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便以《山海经》为依图说文而方向倒置加以解释。案《海外经》部分确是依古图图文阐释,古人看图之方位观多有不同,故有南北倒置,东西倒置的现象,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与《淮南子·墬形训》均言“自东北陬至西北陬”,但所述方国的顺序却正好颠倒。再则古人在解读古图图文过程中,因图像文字重叠等原因,也确有造成部分方国位置错讹的现象,如《海外南经》“贯匈国”在“不死国”之西,而《淮南子·墬形训》中则在“不死国”之东。但如喻先生所言《海外西经》整篇经文“南北东西方位整个颠倒了过来”[11]153,似太过牵强。
此外还需要注意,虽然目前学界普遍强调《五藏山经》《海经》“内经”部分、《大荒经》与《海外经》分属于不同系统。但仍必须注意各经之间出现的相同或相似意象及其存在的关联,特别是相同意象在各经中所表现出的“音训”(即音同或近而文字不同)特点,这与古代神话传说流传的另一传统,即“口头传统”密切相关,不能弃之不顾,单一地以“本经”证“本经”。
基于以上几点不足,可以认定“贯匈国”的研究还有可推进之处。故之后安京先生指出“(贯匈国)并非真的人胸长有‘窍’,也应为西方氏族名称的音译,或即‘犬戎’,‘犬’‘贯’‘穿’上古同韵部,声相近也。‘贯胸’放在‘南经’误,应为西、北方之国,似为错简所致。”[14]94此说即注意到了“贯胸(匈)”应为一个整体,故从“音转”的角度进行阐释,亦有可取之处。综合分析两家之说,则可以明确若要考定商代的“毌方”如何转化为《山海经》中的“贯匈国”,则“贯匈国”所在区域和“毌方”地理位置的对应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欲要解决“贯匈”之义,应首先明确其所活动之地域。
二、“贯匈国”地域考
第一,出土文献方面,武丁时期甲骨卜辞有:

毌其取方。(《殷虚卜辞》.606)
其次,“毌”与“方”亦发生过战争,关于“方”的地望,主要有两种观点,陈梦家先生考定商代“方”之地望应在“沁阳之北、太行山以北的山西南部……亦即《逸周书·王会篇》‘方人以孔鸟’之方人。”[20]270罗琨先生则认为:“武丁对于‘方’的征伐卜辞,却揭示出了一个活力极强、活动范围很广,带有草原民族特点的古族。”[21]217其应主要活动在殷西北或北方。综观二说,结合传世文献来看,《逸周书·王会篇》中方人与西申、氐羌、巴人、蜀人同列,皆在西方而东向,可见以周代地理方位认知“方人”应在成周之西。而甲骨卜辞中的“方”亦在商王畿的西方或北方,则方人主要活动在商王畿的西方应无问题。
再次,“毌”与“雀”亦发生过战争,陈梦家先生指出“雀”与“羌”“犬”“马羌”“基方”“亘”等都发生过战争,这些方国大部分集中在晋南,也就是商王畿的西方或西南方,故“雀之所在,当近今豫西。”[20]298郑杰祥先生则依从丁山先生《殷商氏族方国志》的观点,认为“雀”所在应是《穆天子传》中的“雀梁”,大致位置在今郑州市西北方。[22]222-223
综上,若以“毌国”在今山东曹县,则其向西确可与“雀方”发生战争,但从活动地域和接触条件上来看,“毌国”似不能穿越商王畿南部和其间诸多方国与远在“西土”的周氏族和“方方”发生战争。
第二,在涉及到“贯匈国”的传世文献方面,首先《逸周书·王会篇》载《伊尹四方令》有:“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23]915其中“贯胸”与“昆仑”“狗国”“鬼亲”等西方方国并列。汉代《易林·师之谦》有:“穿胸狗邦,僵离旁脊。”[24]71亦以“穿胸狗邦”并称。二书提到“贯胸”时均涉及到“狗邦”“狗国”。案《逸周书汇校集注》有:“王应麟云:‘狗国,犬戎也。’”[23]916再查《殷墟书契前编》有:
其次,郭璞注“贯匈国”引《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贯匈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常致之。”[4]181“深目者”应是《海外北经》《大荒北经》的“深目国(民)”,在《大荒北经》中靠近赤水、犬戎,其地望应在西北。“长肱者”应是《穆天子传》所载:“天子乃封长肱於黑水之西河。”郭璞注:“即长臂人也,见《山海经》。”[27]73“黑水之西河”学界普遍认为亦在西北方或者西南方,要之在西方无疑。但郭璞注引的“长臂人”在《山海经》中则出现在《海外南经》《大荒南经》,一作“长臂人”,一作“张弘国”,似有方位错讹。不过应注意,首先以上二者皆不作“长肱”;其次考《海外西经》“奇肱国”,《淮南子·墬形训》作“奇股民”,[5]177古代文献中常以“股肱”并称,而《海外南经》中的“交脛国”,《淮南子·墬形训》又作“交股民”。[5]176则《尸子》《穆天子传》中的“长肱”或应是《大荒西经》《海外西经》的“长脛(长股)之国”的讹误,而“长脛(长股)之国”在《大荒西经》中紧邻“姬姓西周之国”[4]331,可见其亦在西北。而“贯匈”与二者并称,其地望亦应在西方。
再次,《海外南经》本身记载方国位置是比较混乱的。按其经文顺序:“贯匈国”之前的“南山”,其文作“自此山以来,虫为蛇,蛇号为鱼。”[4]175与《大荒西经》的“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4]351应是前者为地域,后者为神物、神迹的同一条目的不同记载。“比翼鸟”“毕方鸟”皆同出现在《西次三经》,见于“蛮蛮”“章莪之山”条。[4]35-36、46-47“三苗国”情况比较复杂,参考《大荒北经》《大荒南经》以及其他传世文献,其地望有南北之分,诸家说法各异,但《山海经》经文中与“三苗国”相关的有“黑水”“赤水”,学界普遍认为出自西方,故其大的区域方位或属西北,或属西南。“三株树”亦与“三苗国”相邻,皆近出昆仑之“赤水”。[4]351
“贯匈国”之后的“三首国”,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认为即《海外西经》的“有三头人,伺琅玕树”之类。[28]241“周饶国”应即“焦侥国”,按郝懿行注引《淮南子·墬形训》《说文解字》的内容,其大致区域亦在西南。[28]242由此按照《海外南经》所记录“贯匈国”的顺序,其亦可能不在东南。

另外,从活动地域和接触条件上来看,《诗·绵》和《诗·皇矣》所载周氏族西迁岐山时期及之后与周氏族有过战争的古国有“崇国”“密国”“混夷”“串夷”,当时周氏族主要活动在关中渭河流域地区。首先,关于“崇国”所在地望有三种主要说法:一曰在秦晋之间,王夫之《春秋稗疏》有:“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33]59一曰在丰镐之间,皇甫谧主此说。[18]118一为河南嵩山说,杨宽先生等主此说。[19]83综上,则“崇国”地望最东不过今河南郑州。其次,关于文王所伐“密国”的地望,学界依据《汉书·地理志》《左传》杜注、《括地志》等文献记载,均言在泾州鹑觚县西,即今甘肃灵台西,几成学界共识。[34]59-60再次,“混夷”即“昆夷”,学界普遍认为亦属于“西戎”的一支。综上,“串夷”亦不太可能活动在今山东地区,因为周氏族几无可能直接跨越商王朝核心区域征伐地处东方的“串夷”(毌国),其主要活动地域应在商王畿的西方。
而“串夷”(毌国)之所以在西周后出现在今山东曹县地区,极有可能与西周武王、成王时期分封诸侯有关。案《礼记·明堂位》有:“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郑玄注:“崇、贯、封父皆国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国迁其器以分同姓。”[35]1491《世本》亦有:“贯氏,国名,其后氏焉。”[36]316按照《诗·皇矣》,周氏族自太王时期就与“串夷”(毌国)发生战争,结合《礼记》的记载,周氏族应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贯鼎”。再考“毌国”(串夷)与商王朝的关系,甲骨卜辞有:
丙子卜贞,毌亡不若,六月。(《龟甲兽骨文字》2.244.6)
己未□贞,毌尹归。(《龟甲兽骨文字》2.26.4)
……侯毌来。(《龟甲兽骨文字》2.3.16)
陈梦家先生认为卜辞的“侯串(毌)”应是某侯的私名,“串尹(毌)”则为串国之尹。[20]294赵诚先生则认为:“从卜辞来看,各方国的白(伯)基本上不属于商王朝,而侯则基本上属于商王朝。”[37]58喻权中先生基于此认为:“毌本即商族。”[11]87案商代“侯”系爵位,需商王室册封,并向商王室进贡,“(白)伯”亦类似,从甲骨卜辞中还未发现“侯”“伯”之间级别和远近关系存在差异的明确证据,此说稍嫌证据不足。但武丁时期甲骨卜辞显示出,商与周之间在这一时期常处在战争状态,“毌国”(串夷)称“侯”,又在此时期与周发生战争,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内,“毌国”(串夷)依附于商王朝是无可置疑的。结合《诗·皇矣》的记录,这种依附关系可能长期存在,“毌国”(串夷)极可能是商王朝长期以来用以制衡周氏族的方国。而在武王灭商之后,武王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其中即封同母弟曹叔振铎于曹,《汉书·地理志》载:“(济阴郡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38]1571此外,对从属于商王朝的商贵族势力则采取了笼络、分割并严加控制的政策,《史记·周本纪》有:“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18]126《礼记·乐记》则有武王“投殷之后于宋”之说,郑玄注:“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35]1542-1543其后周公在平管蔡、征淮夷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分割商王朝遗民的势力,按《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周公营建洛邑,迁殷遗民,作《多士》,征淮夷之后又作《多方》给予告诫。[18]133同时为了加强对东土的控制,成王时期又加封了鲁、卫、唐三个同姓诸侯,而且按《左传》定公四年载: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17]2134-2135

综上所述,商代甲骨卜辞中的“毌方”应即周代《诗·皇矣》中的“串夷”(贯夷),其早期活动地域主要在商王朝西部地区,可以与传世文献中“贯匈国”的活动地域相对应,二者应具有传承关系。
三、“贯匈”之义溯源
第一,传世文献方面,首先,关于“昆夷”,《诗·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郑玄笺:“文王为西伯,服事殷之时也。昆夷,西戎也。”孔疏:“正义曰:西方曰戎夷,是总名……故知昆夷,西戎也。”[29]412-413再结合《诗·绵》《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可以明确“昆夷”即西戎的一支。
第二,根据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东方部族亦称“戎”。首先,西周班簋铭文中有“东国戎”。唐兰先生认为:“字疑与偃通,戎即徐戎。”[46]346-351此说法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陈梦家、马承源等先生的观点与此类同。此外童书业先生认为“戎”即是“东国戎”。[47]514-522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戎当即奄人。”[48]21-22而白川静先生认同郭氏的观点,并指出:“戎是夷狄的总称,因此班簋中把东国的夷称为戎。”[49]839要之,虽然关于“戎”具体所指学界存在争议,但“戎”不在西方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则可以明确在西周时期,“戎”“夷”均可以用以指代周王朝周边方国的族属,二者可以混用,其运用方式即往往以“族属特征+族属”的形式命名,早期并无刻意方位地域上的区分。这种命名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商代被称为“某方”的方国,在周代即可被称为“某戎”。后世文献中亦有类似例子,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跂踵国”,《今本竹书纪年》言帝桀时则云:“跂踵戎来宾。”[53]212《吕氏春秋·当染》亦有:“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毕沅注:“歧踵戎,《墨子》及诸书多作‘推哆’,亦作‘推侈’。”梁玉绳注:“歧踵戎与推哆未必为一人。”[54]48-49二注皆以此处“歧踵戎”为人,但参以《山海经》《今本竹书纪年》,其应是“跂踵国”,至战国时期则被称为“跂踵戎”,又被《吕氏春秋》误作人名。故商代之“毌方”即周人口中的“串夷”(贯夷),而“串夷”(贯夷)亦可以是“串戎”(贯戎)。
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贯匈国”之“匈”,在战国时期亦被用于族属之名。以“匈奴”族名为例,以现存材料来看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任崇岳先生在《“匈奴”族名来源辨析》一文中总结了“匈奴”族名来源的五种说法,其中第四类提到匈奴之“匈”应为“猃狁”的拼音:
这种意见认为,匈牙利(Hungary)的“匈”(Hun)为种族名,“牙利”(gary)为地名,匈牙利即匈人之地。《诗经》中的“猃允”、《史记》中的“猃狁”均拼音作“匈”,那时还未出现“奴”音。《逸周书·王会篇》也只称为“匈戎”。“匈奴”之名出现于公元前3-前2世纪。民国时期,何震亚在《匈奴与匈牙利》一文(《中外文化》1937年第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称边疆民族及外人均有贱视之义在内,故于其名下多加‘戎夷蛮狄’等字样,《逸周书》之匈戎,戎字乃中原人所加……”[55]


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大荒北经》)[4]366
“天脊化肥专营店”是天脊集团市场深耕终端发力的“桥头堡”。天脊集团以基层网络建设为重要抓手,把“给政策”扭转到“教技能”上来,积极推进重点门店向天脊化肥专营店发展升级。今年验收通过200家,在三年内至少建成1000家以上天脊化肥专营店,让其成为农民丰收交流、科学种田案例示范、增产增效成果分享、农民致富亲身体验的“新时代天脊助力乡村振兴喜悦舞台”。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大荒西经》)[4]347
据比之尸,其为人折颈披发,无一手。(《海内北经》)[4]273
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4]196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海外南经》)[4]184
从这些记载的地理分布来看,大部分集中在西方、北方。从甲骨卜辞的记载来看,商代与西方、北方的少数部族方国频繁发生战争,所以“毌方”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战争中普遍擅长使用盾牌作战而被命名为“毌方”。这种以惯用器物而得名的情况,类似于《华阳国志·巴志》中的“板楯蛮”,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中指出:“板楯即木盾,是一种武器,又称彭排或彭旁,使用这种武器的民族,遂被称为板楯蛮或彭人。”[60]56另外相似的例子还有南北朝时期的“高车国”,《北史》载“高车国”得名原因是“唯车轮高大,幅数至多。”[61]3271《新唐书·回鹘传》亦有“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62]6111
除此之外,“毌”之义或还应是经常使用“类盾形”物品的少数部族。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今西北、西南地区的羌族,如四川省茂县较场羌族,其传统服饰中,胸前即悬挂有圆形的银牌,是其“民族的特有标志”[63]56,这种银牌即特殊的“类盾形”物品。此外,羌人祭祀所用之“羊皮鼓”,亦是特殊的类“盾形”物品。李祥林先生指出:“羊皮鼓严格说来也并非是常人跳舞所击之物,其最主要的功用在于此鼓非释比莫属,是羌民社会中释比在击鼓诵经跳舞以请神祈福、逐祟驱邪仪式中使用的具有神圣性的法器。”[64]13这种圆形的具有神圣性的羊皮鼓在羌族生活中被广泛的应用。而根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羌人曾经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与犬戎、毌国(串夷)在活动地域上存在关联,其在风俗上亦应多有相似之处。而羌人广泛使用“类盾形”的羊皮鼓,也极有可能是同处西部地区的“毌国”之“毌”得名的原因。

四、余论:“断裂”与“重构”之间
上文关于“贯匈国”的论证旨在说明《山海经》中“贯匈国”并非全源于古人异想天开的想象,其神话发生背后有其文化背景和历史素地。古人对于《山海经》性质的界定,有多种说法,自刘歆《上〈山海经〉表》中将其归为“地理类”,《隋书·经籍志》等多从之。《汉书·艺文志》则将其列为“刑法家”之首,同类还有《国朝》《宫宅地形》《相人》等,应是认为其在地理类书籍属性之外还有巫术占卜的性质。不过综合以上二说来看,汉代到唐宋时期学者还是部分承认其内容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到了明清时期,《山海经》则被看作了“语怪”“小说”之类的典籍。自近现代“神话”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基于神话学方面研究逐渐成为《山海经》研究的主流,这类研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基于神话本身所具有的“虚构性”特点,在相关研究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割裂文献内容与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忽视《山海经》本身成书的复杂性;不顾及神话传说本身所具有的“图文结合传统”和“口头传统”并存的特点等弊端。这些弊端带来的结果便是在《山海经》神话研究和阐释过程中的随意附会,而这种附会甚至导致了《山海经》本身的学术价值被降低。
基于以上问题,在《山海经》研究过程中,首先,应明确《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和过程,就目前的学界研究成果来看,主流观点认为其成书在战国时期,在秦汉间亦有附益。其次,就《山海经》所反映的神话传说内容来看,虽然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其中包含有商代以及更早的传说时期的内容,这说明《山海经》中的部分内容与商周时期存在文化传承关系,所以在《山海经》研究过程中不能够割裂文本内容与时代、疆域、方国地理以及区域文化交流程度等文化因素而随意附会。再次,除了文化传承性之外,还需注意《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图文结合传统”与“口头传统”并存的特点。这两种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都表现出了“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共存的特点。就其“不稳定性”而言,《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内容与其他文献中的相同或相似内容,往往表现出“音同(近)字不同”的特点,这类异文产生的原因即是“口头传统”在传播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导致的,而异文本身即会导致误读和再阐释现象的出现。同样还有部分内容是以“图文结合”形式传播的,而“图文结合”形式在传播过程中,文字形式由于传播区域、人为因素和时代更迭容易产生改变;图像形式虽不易发生改变但容易让人产生意义上的误读。一旦这二者中的任意一方在口头或者书面传播过程中缺失或发生异变,人们只能基于图像或文字本身进行再阐释,这种再阐释的过程包含着不同材料的叠加和书写者个人化的理解和再创造。以“贯匈国”为例,经文中的“其为人匈有窍”极可能是战国至汉代时人在《山海经》成书过程中对原始内涵失据的“贯匈国”的个人理解或注释而误入经文。这种情况在先秦典籍的流传过程中比较常见,在《山海经》中尤为明显。按照郭璞注《五藏山经》结尾记载:“《五藏山经》五篇,大凡15503字。”而至清代郝懿行统计其所本《五藏山经》的字数则达21265字,[4]170其间的流变可见一斑。而在被重新阐释的过程中,“贯匈国”在《海外经》中,对于古人来说“海外”的概念不仅指代的是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同时也包括叙述者由于文化差异而对空间距离的主观夸大和界定。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人们不无理由地说,原始社会把他们的部落集团的界限当成是人类的边界,而把他们之外的一切人都看成是外人,即肮脏、粗鄙的低等人,甚至是非人,危险的野兽或鬼怪。”[65]188而西汉末年刘歆《上山海经表》言:“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4]398-399依然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映。所以对“贯匈”之义,自以“为人匈有窍”为“怪”且“妙”,对于当时人来说无须多加考证。而后人去古更远,其研究又基于西汉末《山海经》流传下来的写本,如果相关研究忽略上述影响因素,只在“形而象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那么只会使以“贯匈国”为代表的《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的原始意义更加晦暗不明。
注释:
① 案:中国学界对于“历史”与“神话”的关系的研究在早期主要分为“疑古派”和“信古派”,之后又有“中间派”如徐旭升先生,其观点突出“传说”概念,认为“传说”介乎于“神话”与“历史”之间,以“传说”这一中间概念,来回避神话“虚构性”的特质,实际上这依然是对“神话”本身特点认识的不足。而钱穆、陈梦家、张光直等先生则更加强调“神话”与“历史”存在密切的关系。叶舒宪先生等则进一步提出了“神话历史”的概念,强调二者不可分割。相关研究史梳理和评述,可参于玉蓉《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第90-98页。
② 案:麦克斯·缪勒的相关理论及学界对其的争论和评述,详参陈刚、刘丽丽《语言疾病与太阳学说遮蔽下的缪勒神话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77-183页。
③同出《诗经》的“南山”即有多说,如《小雅·天保》为赞美周王之诗,其文有“南山之寿”的“南山”,应指西方关中南部的终南山;《齐风·南山》有“南山崔崔”,又有“鲁道有荡”,应是指东部齐国南境的丘陵山地。毛传有:“南山,齐南山也。”此外,《召南·草虫》亦有“南山”。《小雅·南山有台》则“南山”与“北山”相对,应为泛指南边之山的通名。
④如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结合考古发现的先周时期斗鸡台瓦鬲墓类型遗址和周原遗址,认为周氏族在克商之前就已长期居于今陕西境内。详参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65页。
⑤对于《上博简》的真伪问题,学界存在争议,但至今尚无明确证据证明其伪,故本文本着“疑阙从无”的态度,引其文作为旁证。
⑥案:关于“串咎”,还有学者释为“玄宫”,见张富海《上博简〈子羔〉篇“后稷之母”节考释》,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或释为“玄丘”,见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70页。或释为“高禖”,见罗新慧《从上博简〈子羔〉和〈容成氏〉看古史传说中的后稷》,《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