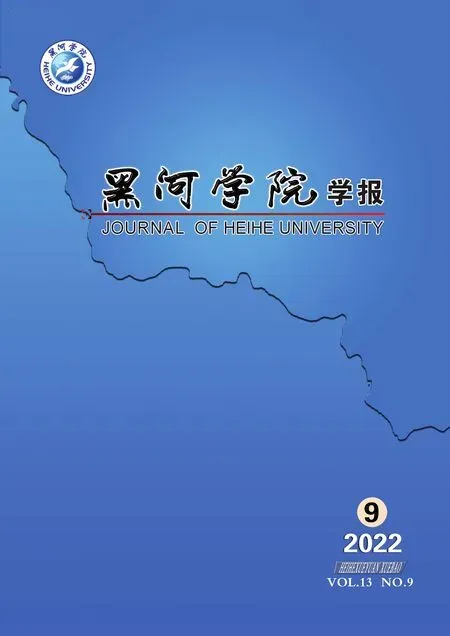“同源异道”和“兼而用之”:先秦时期的儒墨音乐功用思想
杜仲赢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一、“圣人之所乐也”:《礼记·乐记》中的音乐教化
《礼记·乐记》和《墨子·非乐》中都记录着关于乐或礼的评述,抛开礼制不谈,乐在二者那里也有所偏倚。《礼记·乐记》中的乐有泛化倾向,即相当于今天的“艺术”。从乐本篇章节开端便可窥得,起于人心的“声”通过规律性表达呈现为“音”,“音”又通过乐器的演奏、舞蹈的编排而形成“乐”。由此可见,乐不仅仅是从属于听觉的艺术表现形式,还融合了舞蹈等要素。事实上,这里关于“乐”的形式表述也未能充分展开。先秦时期的音乐表现形式还有歌唱的参与。中国原始音乐的表现形式常常是“歌、乐、舞”一体化。例如,《九歌》:“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九招》《九辩》《九歌》与巫术有关,是巫用来召神、帝和招魂的乐歌。后来的《大招》《招魂》都属于这个系统[1]。
《礼记·乐记》中对音乐功用的界定是从属于国家管理者的,意在强调社会秩序,又常与自然物相联系以谋求治理权力的合法性。在具体维护社会秩序的治理过程中,音乐又常常起到评价、奖罚的作用。具体如下:
其一,音乐作为巩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音乐在赋予先秦时期政治统治集团合法性时,主要通过与自然物建立联系而实现。例如,“乐着大始,而礼居成物。着不息者天也,着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日礼乐云。”便将“乐”与蕴生万物的“天”相联系,进而为“圣人曰‘礼乐’”增添了神秘性。又如,“乐者天地之和也”,即用乐来展现“地气”“天气”“阴阳”“天地”“雷霆”“风雨”等一系列自然变化。再如,“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即将乐的实行与所谓天道紧密相连,成为一种增加民众理解的可行工具。事实上,这也是先秦音乐阐释的一般表现特点。《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中的古乐篇言:“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2]也是为五弦瑟赋予了调和天气风雨的巫术功能,以此表现音乐的效用。
其二,音乐作为表现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系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3]715又有“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礼记·乐记》不仅仅认为乐是当时施政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也将这样的评价系统看作从古及今的通用法则。例如,《大章》《咸池》《韶》《厦》等古乐引证音乐与文治武功的联系。这种举证可以说不无道理。《咸池》是陶唐氏时期的舞乐,主要是祭拜天神的乐舞。《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4]在这里,乐舞便与神圣美好的事物产生了想象联结。《韶》是帝舜时期的舞乐,在此时期,便已应用于祭祀活动中,并与政治教化直接相关。《尚书·益稷》有言:“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5]通过乐师在打击乐中的具象表现而呈现出音乐的感召力量。《厦》是大禹时期的乐舞,其歌颂内容已逐渐从恩泽万物的神转向了治水有功的禹,表现了乐舞与世俗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加深。由此可见,在先秦一段时期内,乐与施政的联系逐渐加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记·乐记》中关于音乐反映社会治理水平的功用及特征已然比较清晰。
其三,音乐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荣誉奖赏系统。《礼记·乐记》先行指出帝舜时期的古乐即有奖赏之功用,以乐官夔为例,揭示了奖赏机制运行得当的良好治理格局。对此,《风俗通义》有如下记载:“昔者舜以夔为乐正,始治六律,和均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服。”[6]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以夔为代表的乐官便已较为注重音乐的评价功能。其后,《礼记·乐记》进一步指出音乐可以差异化的形式对诸侯形成奖赏反馈机制。根据乐施篇记录,诸侯治理下如若百姓安居乐业,获得天子赏赐的舞队就规模大,舞者多,已彰显其功勋卓著;反之则规模小,舞者分散,以劝诫其加强德治。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立足于荣辱感的奖赏机制,在礼崩乐坏、诸国纷争之前,有效引导着地方势力的正确施政,维护以天子为中心的统治权威与秩序。
二、“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中的音乐批判
墨子云:“为乐,非也。”与儒家“倡乐”思想不同,墨家学说强调“非乐”思想。作为墨家学说十个主要主张之一,“非乐”思想主要集中呈现在《非乐上》篇中,《三辩》《非儒》《节用上》《公孟》等篇章也有少量论述。墨子非乐思想主要与其实用美学和代表中下层平民阶层的政治理想相关联。但未能获得先秦时期奴隶主阶层的推广。虽为“显学”而流行一时,却也最终复归于百家学说中。相比于儒家学说,墨家崇尚理性思辨,兼具科学思维,其中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合称世界三大逻辑源流。因此,墨家“非乐”观音乐思想呈现出不同于儒家的致思理路。
首先,墨子的“非乐”理论是自洽的,是墨子逻辑方法论“三表法”的具体阐释。三表法就是本、原、用,本是圣人之事、原是百姓耳目之实(也即大众评判)、用是对百姓之利(也就是社会民生)。在我们看来,本实际上也是为原、用服务的。因为能被墨子学说引证为圣人的,通常都是要求符合百姓民生福祉。在非乐篇中也是如此。例如,对“本”的应用:
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与宫,是谓巫风。”[7]281
常在宫中跳舞,就称为巫风,要接受刑罚,君子交出两束丝,小人加倍,加两匹帛。这里是用先王的法制律令来告诫人们音乐的危害。又如对“原”的应用:
“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万民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7]275
这里就是引用古代先王利用社会财富修造工程而未遭到百姓的怨恨的事例,揭示其中本质原因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先王未尝有损于百姓的利益。再如对“用”的应用:
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是故叔粟听之,郎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璐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曰,孰为大人之鶸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7]280。
这里是说农夫和妇女如果耽于音乐,会耽误粮食种植与衣物纺织。《墨子·非乐》在这里总结道,是谁使得农民和妇女荒废了本业有损了收益呢,是音乐。
其次,墨子的非乐理论贴合当时社会结构特点。墨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以天下为重,但是这种天下是墨子进行理论塑形的“天下”,其主要排除了统治阶层,转而关注民众疾苦。考虑到当时的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条件,百姓通过社会分工协作获得的利益要少于自给自足式劳动,也少于免于被统治者盘剥的状态。这主要有几点原因:其一是在农业社会要农业生产优先,墨子强调统治阶层要减少劳民伤财。例如,谈及齐康功喜欢一种乐万的音乐,演奏者锦衣华服膳食精美,批评他们“不掌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7]278即不常从事衣服食品生产,而经常靠别人供给衣食。其二是在封建社会士人阶层是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宜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君子士人如果喜欢欣赏音乐就无法竭尽四肢力量、头脑智力来治理官府和征收税利,粮仓库房就不能充盈。
就社会治理层面来说,既要重视道德教化,又要避免影响社会生产的运行;就民众参与的层面来说,作为政治功用批判工具的“非乐”学说主要指责音乐的三种社会危害。首先是花费社会税收财富。“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7]274其次是耽误社会农业生产。这里墨子关注了演奏音乐的人力占用问题。“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织纫之事。”[7]277最后是影响行政运行效率。“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7]278
三、“推之以礼,化之以兼”:以墨家“兼用”哲学统筹儒家音乐经验
2020年11月21至22日,山东大学与墨子学会、地方政府举办了“儒墨会通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四川师范大学秦彦士、中国人民大学杨武金等学者立足于儒墨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趋向,将儒墨会通与当代国家治理思路相结合,创新强调了同源异流的儒墨两家学说在融合互补下呈现出的创新优势。这次研讨会的交流成果主要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8]。
《礼记·乐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3]739礼乐制度在儒家音乐思想中作为一种维护秩序的工具,强调区分尊卑贵贱与统筹人心。因此,音乐在传统儒家看来,“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3]730《墨子》云:“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竿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7]275墨家学说在政治主张上强调兼爱、非攻,反对征伐,这便与维护贵族统治的礼乐制度相斥;在社会民生方面则同样强调节用、节葬。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音乐自然成了一种非必需品。加之贵族礼乐的音乐往往铺张华丽,费用出自民膏民脂,墨家“非乐”理论便从其政治立场阐发,所谓“为乐非也”。
儒墨两家在先秦时期是不同的理论主张,而在多元视角的今天,对二者的辩证审读有机会重新统筹两家相异的观点。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阐读:
其一,儒墨两家的相异不在本质论上,而在乎方法论。我们以儒墨两家关于“爱”的核心观点来分析。儒家的仁爱是“爱有差等”的爱,墨家的兼爱是“兼以易别”的爱,儒家仁爱强调“爱有差等”,而墨家兼爱授意“兼以易别”。儒家的爱出于“孝悌”讲究亲疏,墨家的爱出于“相利”而强调交互。也就是说,儒墨两家关于爱的情感并无实质区别,更多是在于方式的差异。儒家基于家庭血缘而衍生来的爱较之墨家互惠互利之爱在普适性和可推广性上有所差距。关于“何故为乐”的讨论亦是如此。孟子作为儒家代表反对墨子“以乐害政”的主张,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即音乐能够作为一种载体深入人心。而《墨子》中的非乐思想则从财政视角出发为“王与民同乐”而倡导,但这种反对声音本身也承认了音乐可以对社会施加影响。
其二,墨家的方法论对统筹儒家的经验具有借鉴价值和可行性。“非乐”作为一种主张,没有善恶之分,如果要加以评价,就要进一步明确“非乐”作为一种学说在探讨还是作为工具在批判。如果作为理论探讨,显然是针对性较强的论辩,主要反对的是儒家对礼乐制度的追求。这与墨子及其代表集团是劳作者不无关系。将“非乐”说视为先秦音乐哲学一种,探讨音乐的本质、功用,“非乐”说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墨子强调乐的运行有诸多负面影响,而这种看法大多与墨家社会功用(尤其是政治功用)思想密切相关。将儒墨音乐功用思想并置在一起,可以挖掘出一种崭新的音乐功用构型——儒墨会通实践下差异性的同归路径。
四、结语
儒墨学说同出于鲁国,同源而异道。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礼记·乐记》的儒家礼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看,这是统治阶层的风雅娱乐、政治治理,只是国家管理集团的生活断面。但在西学东渐的当下,启蒙精神、辩证方法潜移默化影响政治塑造与社会参与,一味强调礼仪制度和试图完全掌握音乐的施用显得困难重重。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应允《墨子·非乐》的反乐号召,因为音乐作为情感的触发机制,常常能很好地记录心路历程,与文学一道挑动人的情绪,施加有益的道德影响。因此,我们无妨采用墨子学说中“兼”的方法,整合儒家学说对音乐功用的认识,将音乐教化有效性和音乐可能影响社会运作的警示兼而用之,把握社会道德建构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世界秩序衰微、国际话语冗杂、强权介入消弭异己的特殊时期,而当下我们同样面临新的话语困局。面对差异和争端,中国话语汲取古典智慧推之以礼,化之以兼,以墨学中的平等、法治、理性、科学兼化儒学中的秩序、典雅、诗性、同一。在儒墨会通的现代阐读下,儒墨音乐思想应脱胎于对立的旧统,促进世界文明的求同交流与审美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