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吸引力戏剧”与“元蒙太奇”
赵 武
受未来主义美学思潮影响,苏俄初期新戏剧人一反传统戏剧观念,探索现代戏剧表现手段。他们不仅借鉴了未来主义诗歌的创作观念,也吸收了欧陆马戏等民间艺术技法,并引入戏剧,产生了吸引力戏剧(即杂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跳跃”逻辑与“意象”生成,由此催生了“蒙太奇”概念。作为横跨戏剧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当下理论界对其理论意义的探讨仅限于电影角度,而对其源头的戏剧性本质少有关注。由此,本文提出“元蒙太奇”概念,旨在探索蒙太奇之戏剧原生性及其对电影的内在驱动。
一、“吸引力戏剧”实践与“蒙太奇”辨析
吸引力(attraction),早先翻译成“杂耍”,后来逐渐统称为“吸引力”。从对未来派戏剧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可以了解到,“吸引力”是特指那些主要来自欧陆马戏技艺并融入戏剧场面中各类超高难度的、极吸引眼球的表演技巧(杂耍),而“吸引力戏剧”则是指由此形成的戏剧场面,所以,“吸引力戏剧”也可以称作“吸引力场面”。
“吸引力”一词的概念是由爱森斯坦首次提出的。据罗伯特·里奇的说法,爱森斯坦在梅耶荷德1922年《塔雷金之死》剧组中担任副导演,从中见习了梅耶荷德如何在这部作品中将未来主义(1)未来主义是发端于20世纪的艺术流派,最早出现于1908年的意大利,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俄罗斯尤甚。未来主义的理论与创作涵盖了所有艺术样式,包括绘画、雕塑、诗歌、戏剧、音乐。限于篇幅,本文所论特指俄罗斯未来主义及其诗歌与戏剧部分。、马戏技艺和喜剧艺术融合为独特的舞台呈现,随后就在1922年夏天,爱森斯坦与尤特克维奇合作导演了《哥伦布的吊带》(由特列季亚科夫编剧)一剧。就是在这次创作之后,爱森斯坦撰写了《吸引力蒙太奇》,首次阐述了“吸引力”(或杂耍)的概念。(2)Robert Leach,Russian Futurist Theatre: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8),133.对于“蒙太奇”,一般也都默认为爱森斯坦的“专利”,他自己在文章第一句也这么提道:“这个术语是第一次使用。它需要解释。”(3)Sergei Eisenstein,“The Montage of Film Attractions (1923),”Richard Drain(ed.),Twentieth-Century Theat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88.然而,我们在罗伯特·里奇所著的《俄国未来主义戏剧:理论与实践》中看到一段记载,提到梅耶荷德曾邀请无产阶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在作家工作室任教的特列季亚科夫加入梅耶荷德剧院,他们共同开设了“文本-运动”课程。特列季亚科夫在与梅耶荷德合作的首部作品《世界颠倒》首演当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文本与话语蒙太奇》(4)爱森斯坦在1923年《左翼文艺战线》第3期上发表《吸引力蒙太奇》,于1923年3月4日《世界颠倒》首演当日发表《文本与话语蒙太奇》,从时间上推算,在启用“蒙太奇”一词上特列季亚科夫可能比爱森斯坦略早。,提出“话语蒙太奇”,强调节奏、旋律和发音都可以给角色带来怪诞的暗示。(5)Robert Leach,Russian Futurist Theatre: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8),134-135.
“吸引力戏剧”是特列季亚科夫在1923年《思想的十月》第1期中发表的同名文章《吸引力戏剧》里提出的。(6)姜训禄:《视觉艺术家谢·爱森斯坦的吸引力戏剧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文艺》,2022年第1期。同年的《左翼文艺战线》第3期刊载了爱森斯坦的《吸引力蒙太奇》。(7)据姜训禄文载,爱森斯坦原文名也是《吸引力戏剧》,后因与特列季亚科夫文章重名,遂改为《吸引力蒙太奇》。这就使问题变得有趣了。先阐发“吸引力”的是爱森斯坦,先使用“蒙太奇”的是特列季亚科夫。不过,率先把“吸引力”与“戏剧”嫁接的是特列季亚科夫,而把“吸引力”与“蒙太奇”组合成词的却是爱森斯坦,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合成状态。正因为发现了这种彼此相融的状态,这才引起关于“吸引力戏剧/蒙太奇”与“元蒙太奇”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它们既然可以“重名”或改名,那么,其中必有共同的内涵。这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蒙太奇”取自法语,其基本含义为“组合、装配、构成”,原为建筑学术语。由于法语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所以很多罗曼语族国家都有“蒙太奇”的近似词汇,如法语“montage”、西班牙语“montaje”、葡萄牙语“Montagem”。而属于日耳曼语族的国家以“编辑”“剪裁”指代,如英美语的“editing”和“cut”,德语的“schnitt”,这三个词汇都较偏重技术性。
或许是语言概念的关系,年轻的库里肖夫在苏维埃成立后不久建立的VGIK(8)莫斯科电影学院,1919年由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加丁创建,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学院。的鼓励下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经过格里菲斯《党同伐异》的数千镜头的影像剪辑实验,获知格里菲斯的剪辑主要是以连续剪辑(也称无缝剪辑)达到叙事的目的,而他们的实验是以不同画面在逻辑或经验上的组合所形成的某种意象表达或象征为目的,这就使得蒙太奇的组合/剪辑过程对导演和观众来说都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9)David A.Cook,A History of Narrative Film,5th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Company,2016),98.也就是说,库里肖夫的实验始于格里菲斯连续剪辑的蒙太奇,源于法文“构成或装配”的蒙太奇。然而,实验初期的蒙太奇理论与实践尚不能以今天的成熟理论来对应,距离“敖德萨阶梯”的剪辑观念还存在四五年空隙。也正因此,在罗伯特·里奇的撰述里,他对“蒙太奇”一词的解释既非剪辑(“edit”或“cut”)也非特指苏联蒙太奇学派的“montage”,而是指“parataxis”(并列,意合)。(10)Robert Leach,Russian Futurist Theatre: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8),13.在里奇看来,爱森斯坦在戏剧阶段所发表的蒙太奇思考尚未与后来他在电影创作阶段发展出来的蒙太奇理论联系起来。而之所以改“吸引力戏剧”为“吸引力蒙太奇”,一是避免与特列季亚科夫的文章重名,二是道出了“吸引力戏剧”潜在的规律,即罗伯特·里奇的“parataxis”(并列,意合)之意,这就为笔者探讨“吸引力戏剧”的“元蒙太奇”性提供了逻辑起点。另一个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大卫·库克的《叙事电影史》中的一段话:“如果认为蒙太奇的想法仅仅来自库里肖夫工作室,或者是《党同伐异》的影响,或者是由于缺乏赛璐珞而强加给苏联制片人的经济措施,那就错了。事实上,这种想法在1910年到1918年的前卫艺术中非常活跃。”(11)David A.Cook,A History of Narrative Film,5th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Company,2016),98.随后,库克还引证了大卫·波德维尔的研究。后者认为,蒙太奇的想法是在未来主义和形式主义实验的伟大时期,作为艺术构建手段的碎片化和重组的概念。(12)Ibid.
在“剪辑”一词的用法上,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各有侧重,前者重“装配”和“组合”,后者偏“连续”和“衔接”。这两类词汇在电影叙事上也是异同互现,同者都是“连接”,异者是一个重叙事,一个重“意象”(爱森斯坦),即“表现”。“表现”需要遵循一种特有的语法规则和叙述方式,如并列或对立,甚或冲突。这就与波德维尔所说的未来主义在艺术构建手段上的“碎片化和重组”相关了。由此看来,蒙太奇的观念并非电影叙事所独有,与之相关的具有诗意叙事性质的艺术门类都可能具备和运用这一语言手段,而笔者特别提出“元蒙太奇”的概念亦基于此意义:它是先存在于电影蒙太奇里,潜行在诗词、戏剧之中,显学于电影之上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尤其是经过对俄罗斯未来主义各派美学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存在着太多的“并列与意合”的“元蒙太奇”思维。
二、“吸引力戏剧/蒙太奇”的美学溯源
短暂而辉煌的俄罗斯未来派戏剧,自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仅仅持续了二十多年,从小型的、嘈杂的、破坏性的、在剧院内外的表演开始,到戏剧-马戏“两化”的疯狂实验以及对跨理性语言和构成主义的探索,逐步形成以“吸引力戏剧”为主打特色的俄罗斯未来派戏剧风格。“俄罗斯未来派戏剧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挑战性和最具深远意义的戏剧和作品的起源。”(13)Robert Leach,Russian Futurist Theatre:Theory and Practic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8),10.以马雅可夫斯基、克鲁切尼赫、赫列布尼科夫、特列季亚科夫、卡门斯基、兹达涅维奇等文学剧作家为核心推动,加上波波娃、斯捷潘诺娃、罗琴科等舞台设计家(他们之前都是画家),以导演梅耶荷德为旗手的戏剧导演群(如拉德洛夫、福雷格、爱森斯坦、捷伦提耶夫(14)捷伦提耶夫(Igor Terentiev),俄罗斯诗人、艺术家、舞台导演,早年加入41度诗派,1923创建了新闻之家剧院,追随梅耶荷德排演《钦差大臣》等剧,1937年5月不幸离世。等),他们通过一大批未来派戏剧作品,在诸多方面对戏剧进行了大胆革新。在表导演的呈现上,他们将演员从一个复杂的台词背诵者变成了一个结合了杂技演员和小丑素质的表演者,取消了生活片段式的布景,倾向于用裸露的舞台重新展示表演的机械性;剧作上消除了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引入了怪异的特质和系列结构;剧场性方面则突破第四堵墙,要求观众参与到戏剧中来。所有这些相应的戏剧探索,几乎无不受到俄罗斯未来主义的美学理念影响。尽管这些美学观主要是以诗歌创作为探索对象,但由于戏剧与诗歌的天然血缘关系,很多诗人纷纷“以诗入剧”,将其美学理念由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之浪漫情怀而嫁接到俄罗斯轰轰烈烈的革命戏剧上来。
1910年马雅可夫斯基等立体未来主义者联名发表《对公众口味的一记耳光》,给俄罗斯未来主义奠定了一个总的基调。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扬言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性的船上扔下去”。(15)Anna Lawton and Herbert Eagle (eds.),Russian Futurism through its Manifestos,1912-1928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51.随后,由坚守这一宣言精神的理论家和诗人克鲁切尼赫在题为《文字的新形式》中深入阐述了他的“跨理性”的语言概念,提出“词比思想更广”的理念。“词(以及它的组成部分,声音)不是简单的截断的思想,不是简单的逻辑,它首先是跨理性的”,“句子的不规则结构(在逻辑和组词方面)产生了运动和对世界的新认识,反之,运动和心理变化产生了单词和字母的奇怪的‘无意义的’组合”。(16)Ibid,70,71,73.虽然这说的是诗学原理,但与“吸引力戏剧”的观念和方法在学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否定了单个字词在思想逻辑中的作用,而是视其为“无意义的”组合,这就像马戏团的单个杂耍(吸引力)相对于戏剧情节是超越理性的、非必然逻辑关联的个体部分,但通过戏剧组合,使得“无意义的”组合变得很不规则,并以不规则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由“句子的不规则结构”而“产生了运动和对世界的新认识”。可以说,这是未来派戏剧人有意无意间所追求并遵循的基本创作法则,他们的戏剧几乎充满了马戏团的各种杂耍技巧,包括面具与小丑等各种手段和表演技巧,以此实现《对公众口味的一记耳光》的宣言中所说的创立新的戏剧语言的理想。
自我未来主义“诗歌夹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西扬斯基在其所写的《向立体未来主义发出的战书》一文中对于词语及其组合的解释,把重点落在了“组合”观上:“在语言组合(可能没有情节)中显现出来的抒情力量,把它的光芒投射在这些组合所涉及的对象、思想和感情上。”这里涉及单个词语在叙事语境下的组合所释放出的“抒情力量”,其中所谓“装饰性的创作方法对绝对事物的揭示”更是论及形式对内容的反向叙事创作的观念。这些阐述对于激发后来的戏剧“吸引力”创作意义深远。该诗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舍申耶维奇继续将罗西扬斯基的理论扩展为“词-形象”。他在一封致罗西扬斯基的公开信中首次提到“词-形象”,认为词语最初是凭直觉产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动重复,这个形象变成了一个陈词滥调,一个传统的“内容”,不再由直觉暗示,而是由逻辑支配。因此,只有“词-形象”才构成真正的诗歌材料。他举了一个例子:“每一种表达方式在其诞生的那一刻都不是‘词的内容’的组合,而是‘词的形象’的融合。我发现现在很难说是谁首先使用了这个表达:‘滋养希望’。但很明显,这是一种图像组合……它对我们的理解说了很多,但对我们的想象力来说却是空洞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抛弃过时的 ‘滋养’一词,而用更现代的 ‘喂养’来代替,那么 ‘我喂养希望’听起来会很奇怪,不仅是因为一个词被另一个词取代了,而且还因为这个新词让人直观地理解其表达的生动性。”(17)选集原注:《致米-米-罗西扬斯基的公开信》被刊登在《诗坛年鉴》的第三本(莫斯科,1913年11—12月)。See Anna Lawton and Herbert Eagle (eds.),Russian Futurism through its Manifestos,1912-1928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145.“词-形象”一说算不上新鲜理论,但是“滋养”与“喂养”的“奇怪”之说,对后来的戏剧-马戏“两化”的“吸引力(杂耍)戏剧”来说具有重要影响,他实际上说出了一个以怪异的“新词”构成形象达到“吸引力戏剧”场面组合的审美效果,而这种手法,亦即前文特列季亚科夫所论述的“文本蒙太奇”或爱森斯坦后来深入总结的“吸引力蒙太奇”的思维来源之一。
由自我未来主义转入“41度诗派”的克鲁切尼赫(A.Kruchenykh)先后写了好几篇文章。(18)克鲁切尼赫的文章中,辑入《未来主义宣言》一书的就占了三篇:《超理性语言宣言》、《俄罗斯诗歌的词转移学》(节选)、《文字的新形式》。《未来主义宣言》还辑入了别人论他的《克鲁切尼赫的〈大地之光〉》。在《超理性语言宣言》(DeclarationofTransrationalLanguage)中,克鲁切尼赫指出,当“思想和语言无法跟上处于灵感状态的人的情绪”时,或者“没有明确意义的语言”时,就可以使用“跨理性语言来自由表达自己”了。它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当艺术家表达不完全确定的形象时;二是当他不想命名对象而只是暗示它时;三是当一个人失去理性而嫉妒、仇恨、愤怒等时。“(理性)思想导致文字收缩、蠕动,变成石头,跨理性时狂野、燃烧、爆炸等”,而跨理性的语言具有随机性,如“不合逻辑的、偶然的、创造性的突破、机械的词语组合:口误、错别字、失误”。(19)See Anna Lawton and Herbert Eagle (eds.),Russian Futurism through its Manifestos,1912-1928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182.这篇宣言的意义主要在于他把所论内容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将传统的理性语言与跨理性语言做出比较,推进了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他所列举的对跨理性语言的创作需求条件和可能的语言现象预示了“吸引力戏剧”,如在马雅可夫斯基《澡堂》《臭虫》和特列季亚科夫《我想要个孩子》等剧作里,其喜剧讽刺张力不能不说与此美学观念关联密切。尤其在《俄罗斯诗歌的词转移学》里,克鲁切尼赫提出“转变”或“错位”一说:“当两个背对背的单词在语音上发生拼接时,就会发生转移。音节由节奏的重新分配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即第一个词的结尾和第二个词的开头产生一个完全不协调的新词。”这就是所谓“语义移位”:“跨理性语言总是一种转变的语言,它包含了断裂的碎片,转移渗透到整个诗句中……它修改了单词、句子、声音。转移传达了运动和空间。转移传达了意义和形象的多重性。”(20)Ibid,179.如果我们不把这段论述看作诗歌的美学而是作为吸引力戏剧或蒙太奇组合学理来研究,会发现,其基本美学原则,即通过各种泛指的“词语”(可以是各独立的杂耍吸引力,也可以是单个镜头画面)错位搭配与并列组合而使词义有了创新的观念,这既是未来派戏剧的核心美学理念,也直接引发了本论文的思考:俄罗斯未来主义美学背景下的吸引力戏剧或许催生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蒙太奇语言,而在蒙太奇没有完全被电影同化之前,它以元蒙太奇形态存在于俄罗斯未来派戏剧中。
三、“元蒙太奇”的生成及其戏剧DNA
毫无疑问,由“并列或意合”所形成的“吸引力戏剧/蒙太奇”是促成元蒙太奇思考的前提条件,但仅限于此,尚不足以阐发其内在成因。笔者以为,在未来主义美学风潮引领下,带动的是一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关于“元”意味的实践探求。
“元”,作为一个前缀“meta-”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组词法,大致意为“之后”“之外”“之上”“之间”,并延伸为“有变化的”“超出一般限制的”意思。从元戏剧的首倡者莱翁内·阿贝尔在其《元戏剧——一种戏剧形式的新观点》一书中对《哈姆雷特》的元戏剧分析——结构和角色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意识,可以大致了解,在叙事类体裁中的“元”,具有以体裁本身的形式作为表意工具的特征:“几乎每一个主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都像剧作家一样行动,用一个剧作家的戏剧意识将一种确定的态度和看法施加于另一个角色。”(21)Lionel Abel,Metatheatre: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 (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46.它不满足于传统的表述,如莎翁之不满足于古希腊悲剧的原则,让哈姆雷特以“戏中戏”反身自指,同理,俄罗斯未来派诗歌或未来派戏剧人同样不能接受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原则,他们在诗歌观念上标新立异,百家争鸣,在戏剧表现上,更是以传统戏剧为主要突破对象(即“壁垒突围”),目的是“给大众口味一记耳光”。
早在1913年7月,马雅可夫斯基就发表了《电影、剧院、未来主义》一文,批评“在当代戏剧中,演员的艺术被 ‘死的装饰背景’,即事无巨细的自然主义背景所 ‘奴役’,从而被扼杀”,提出演员的艺术在本质上是动态的,体现在声音的音调上(即使所说的话没有具体的含义),或者体现在“身体的运动”上。(22)V.Mayakovsky,“Cinema,Theatre,Futurism,”David Elliott (ed.),Mayakovsky:Twenty Years of Work (Oxford:Museum of Modern Art,1982),22.马雅可夫斯基以一出《神秘的布夫》,联手“反传统”先锋梅耶荷德率先展开了他们的“元”戏剧探索。《神秘的布夫》的基本形式是“戏剧马戏化”,因为马戏在道德和思想上比歌舞表演来得纯粹,又能够展示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表演技能,它集惊险、惊叹、奔放于一剧。它所呈现的可以不完全是戏剧,也不完全是现实。因此,马戏在意识形态上是健康的,也是官方认可的。
相对于契诃夫、高尔基的“天真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梅耶荷德联手的戏剧在形式上开创了“寓言”式自我指涉,如以两个演员撕下象征旧剧院的幕布而开场,将全剧分成参差不齐的片段;被资本家贬称为“不洁者”的工人们从甲板下走出来时被绳索捆住,像合唱团一样齐声说话或唱歌;“沙皇”被扔到了海里;美国人骑着摩托车在舞台上咆哮,而商人则像小丑一样掉下舞台……场面相当于马戏的场段,也包括一系列小丑特技和自成一体的转场。“戏剧马戏化”的形式语言完全颠覆了传统戏剧的舞台幻觉,使戏剧形式超越了传统约定或限制,具有了在“之外”“之上”“之间”的元戏剧自我指涉的形式特征。如果将这出首创的戏剧马戏化视为阿贝尔元戏剧之说的“戏剧形式的新观点”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拉开了未来派元蒙太奇的序幕。阿贝尔在分析元戏剧特征时指出:“现代西方的剧作家难以相信缺乏自我意识的角色。安提戈涅、俄狄浦斯、俄瑞斯特亚这些角色缺乏自我意识,就像自我意识是哈姆雷特这个西方元戏剧标志的特征一样。”(23)Lionel Abel,Metatheatre: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 (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77.虽然《神秘的布夫》在剧作上未必具有如哈姆雷特那样的自我指涉,但梅耶荷德在舞台导演语汇上的形式自喻却无意中既赋予了元戏剧的色彩,又为以吸引力戏剧为特色的元蒙太奇思维和手段铺垫了基础。因为作为一种创作观念和手法,自我意识和反身指涉是有目的地去打破舞台幻觉,是一种“持久和弥漫的内在转变,当追踪到极致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形式变为内容”。(24)June Schlueter,Metafictional Characters in Modern Dram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3.正是基于以“形式变为内容”的“元”意味,才能使本属于元戏剧的创作方法蕴含了元蒙太奇的延展空间。
按照理查德·霍恩比在《戏剧,元戏剧和感知》中的说法,“简而言之,元戏剧可以被定义为关于戏剧的戏剧;只要戏剧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戏剧本身,它就会发生”。(25)Richard Hornby,Drama,Metadrama,and Perception (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6),19.接着,霍恩比对有意识或显性元戏剧的可能形态做了描述:戏中戏、戏剧中的仪式、角色中的角色扮演、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观照以及反身指涉或自我观照。(26)Ibid,20.照此推演,我们发现,吸引力戏剧在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并列、意合”的未来主义美学思想,又与元戏剧的显性形态有所吻合,这不仅使吸引力戏剧具有了自觉的现代戏剧属性,且在其中蕴含了“关于蒙太奇的蒙太奇”的元蒙太奇属性。爱森斯坦在1926年有个总结:“吸引力与特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特技,或者更准确地说,‘把戏’是一种特殊的精湛技艺(大部分是杂技)的成品,它只是一种适合于展示的吸引力。就技巧本身的绝对性和完整性而言,它意味着与吸引力的直接相反,后者完全基于相对的东西,即观众的反应。”(27)Sergei Eisenstein,“The Montage of Film Attractions (1923),”Richard Drain(ed.),Twentieth-Century Theat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89.这里所指“观众的反应”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剧场效果,而是特指吸引力戏剧场面组合所引发的“意象”审美。在戏剧导演阶段,爱森斯坦在其师梅耶荷德的引领下,协同马雅可夫斯基、特列季亚科夫、拉德洛夫等未来派戏剧家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戏剧性”(28)Lionel Abel,Metatheatre: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 (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60.,其戏剧仪式和舞台形式的自我观照“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他们自身的戏剧化中”。(29)Ibid,78.他们已不满足于改写“外在的现实”(30)June Schlueter,Metafictional Characters in Modern Dram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4.(恰如莎士比亚不会屈尊为情节剧作者那样),而是超越戏剧传统人物叙事,使戏剧在写实与幻觉之间游移,成为真实与虚构二元同在的“自治的实体”(31)Ibid,4.,逐步形成了在戏剧与马戏的“互化”实践中的“吸引力戏剧”风格,以“并列、意合”的舞台手段将“马戏—戏剧”由纯技巧转化为戏剧内容本身,“形式即内容”,呈现出一种霍恩比所说的“戏剧-文化复合体”的形态:“一部戏剧在戏剧整体系统里运转。文化,以这种方式集中于戏剧,我简洁地将之定义为戏剧/文化复合体。”(32)Richard Hornby,Drama,Metadrama,and Perception (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6),22.这个形态中,既有元戏剧本身的属性,又有作为将来电影蒙太奇的元素,所以,元戏剧和元蒙太奇就像一个镜头分切两段再以“叠化”的剪辑技巧使之既连续又分立,最终催生了以“吸引力戏剧/蒙太奇”命名的元蒙太奇创作原则与方法。
在以特列季亚科夫为编剧、由梅耶荷德和爱森斯坦分别导演的两部戏剧《世界颠倒》和《智者》中,吸引力戏剧的元戏剧和元蒙太奇的“双元”特性有所体现。1923年初,特列季亚科夫为梅耶荷德剧院贡献了一部重要的史诗剧《世界颠倒》。(33)《世界颠倒》(The World Upside Down),因原剧名“Zemlya Dybom”(含有“使地球变得狂暴、混乱、跃动”等意思)几乎无法转译,故而英文作者大多译作如此,该剧也被译为《大地横行》《大地奔腾》等各种剧名。See Sergei Tretyakov,trans.Robert Leach and Stephen Holland,I Want a Baby and Other Plays (London:Glagoslav Publications,2019),7.在剧中,老妇人因儿子被卷入战争而悲痛。剧本重点放在“黑色国际”和农民之间的冲突上,含蓄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即这种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工人阶级的支持。编导对人物进行了“去心理化”,采用“海报口号”投屏的手法,并以其所谓的“信号语”的“文本-话语蒙太奇”,使戏剧集中在“语言手势”上。原剧的五幕被改成八幕,把讽刺、小丑和悲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组合——梅耶荷德充分借助了这一特点。当时的观众描述了开场的情况:一些汽车从连接观众席和舞台的桥上直接开过,后面还跟着一些穿制服的自行车手。当“沙皇”得知起义的消息时,管弦乐队响起“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一个勤务兵端来了御用锅。“沙皇”用膳后,勤务兵抱着锅穿过观众席。其中一个著名场景是,“沙皇”的厨师拿着一只活公鸡来准备“沙皇”的晚餐,它拍打着,叫着,接着厨师跌倒了,公鸡飞走了……公鸡很快被再次抓住。有一次,公鸡飞进了观众席,梅耶荷德自己从座位上跳了下来抓住它,并把它还给了舞台上。(34)See Rene Fulop-Miller &Joseph Gregor,The Russian Theatre,Its Character & History,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1st edition(London:George G.Harrap&Co.),67-68.可以想见,戏剧在这一系列吸引力戏剧场面中呈现出一种自我指涉的元戏剧/元蒙太奇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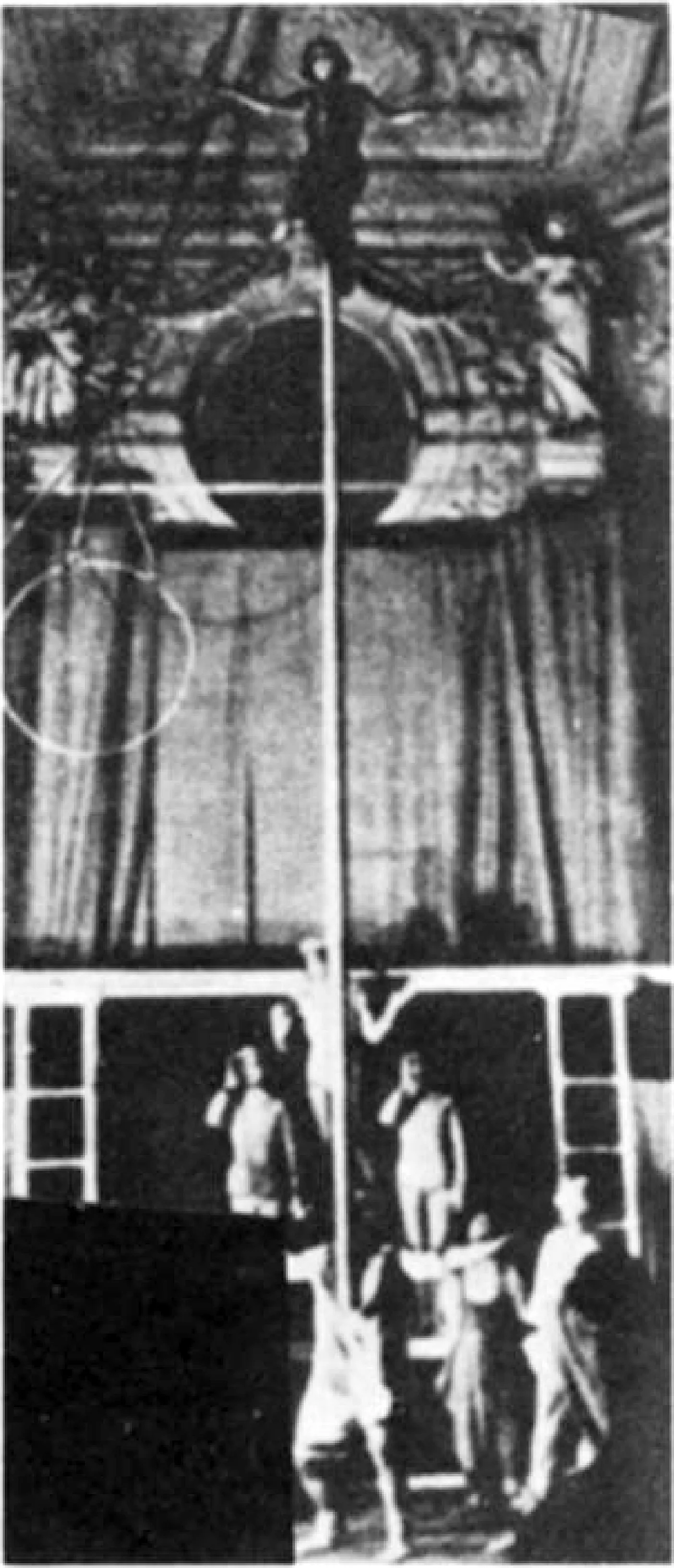
图1 《智者》的高杆
在《智者》的改编中,编导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聪明误》进行了一次全面解构。特列季亚科夫秉持其一贯的剧作风格,将剧作切成一个个小片段,使各片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彼此毗邻,结构上具有“意合”逻辑的戏剧序列,为导演爱森斯坦的吸引力导表演设计储备了舞台空间。《智者》在导演处理上将安年科夫、拉德洛夫、弗雷格(35)弗雷格:苏联早期戏剧导演,他的“弗雷格工作室”专注于演员的身体工作,因其“古怪”或“机械”的舞蹈而著名。和怪异演员工厂(36)怪异演员工厂(FEKS:Factory of the Eccentric Actor)由科津采夫和特劳博格于1921年在彼得格勒成立,将演员培训与戏剧和电影的集体艺术创作相结合。FEKS团体被认为是怪异前卫艺术(Eccentrism)的一个新方向,它试图在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之间找到一个位置。的做法引入剧中,集合了空中表演、地板体操、飞身空筋斗、翻滚、平衡、讽刺性歌曲和小丑表演等。也正是由于这部戏的导演实践(《智者》是爱森斯坦在继《墨西哥人》后正式执导的第二部戏,也是与特列季亚科夫合作的第一部戏),爱森斯坦继特列季亚科夫的《吸引力戏剧》之后发表了《吸引力蒙太奇》一文。
爱森斯坦在三年后总结道:“我所说的吸引力是指在表演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和主要的元素,一个戏剧有效性的分子(也就是组件)单位……任意选出的独立(也是在给定的构图和人物的情节联系之外的)效果(吸引力)的自由蒙太奇,但目的是建立某种最终的主题效果——吸引力蒙太奇……将戏剧从‘虚幻的模仿性’和‘表象性’的重压中完全解放出来的方法,是通过向‘可操作的假象’的蒙太奇过渡,这允许将整个‘表现性片段’和行动的相关情节线交织到蒙太奇中,不再是自成一体和完全决定的东西,而是为特定目的有意识地选择的当即有效的吸引力。这种表演的唯一基础不在于‘发现剧作家的意图’‘对作者的正确解释’‘对那个时期的真实反映’等,而只在于吸引力和吸引力的系统。”(37)Brooks McNamara,“The Scenography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The Drama Review,TDR Vol.18,No.1(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爱森斯坦关于吸引力的表述,明确了吸引力是独立的结构元素,它们可以在某种主题内自由组合(元蒙太奇)后形成“吸引力蒙太奇”(即以相对独立的“吸引力”场面构成戏剧自我指涉的“元蒙太奇”);它的目的并非图解剧本,而是让形式(元蒙太奇)成为内容。试看剧中一例。剧中玛玛耶娃面对着好色的士兵乔弗尔,她感叹道:“救命啊!他要占有我!这下我可倒霉了!”接着,舞台工作人员拿来一根平衡杆,把它固定在乔弗尔的身上,然后这位女演员灵巧地爬到顶端(杂技),大声说:“现在我正站在杆子上。”乔弗尔答道:“现在你就像莫斯科,不可能够到你。”“是的”,她回答说,“现在我和俄罗斯一样高不可攀,一样无所畏惧”。在这里,演员伫立杂技高杆的顶端之造型被转喻为高不可攀的、无所畏惧的、充满革命性的俄罗斯精神,使我们直接看到爱森斯坦的“吸引力蒙太奇”意象,更发现其中的“双元”(元戏剧/元蒙太奇)意味:它是一种舞台语言的“转喻”,是克鲁切尼赫的在1921年发表的《跨理性语言宣言》所提出的“转变”(sdvig)美学观点的呈现。也正如霍恩比所言,它“关于 ‘现实’,不是在仅仅反映现实的被动意义上,而是在提供描述现实的‘词汇’或测量现实的‘几何’的主动意义上”。(38)Richard Hornby,Drama,Metadrama,and Perception (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6),22.(参见图1)
以上论述可能会引发一个疑问:既然特列季亚科夫的“吸引力戏剧”或爱森斯坦的“吸引力蒙太奇”都几近相类地具有元戏剧特质,那么本文为什么又提出“元蒙太奇”一说呢?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爱森斯坦的电影影响力,其“吸引力蒙太奇”一说占据了学术话语高地,而“蒙太奇”也仿佛可以与电影画等号(民间大多如此),再加上“吸引力戏剧/蒙太奇”概念本身在理解与阐述上的艰涩,既难与未来派戏剧联系起来,又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鉴于此,笔者才著文追本溯源并审慎提出“元蒙太奇”一说,借此希冀矫正一下对“吸引力戏剧/蒙太奇”的误解,确立其戏剧DNA身份。
其二,“元蒙太奇”的提出不仅是为未来主义美学或未来派戏剧“正名”,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作为第一篇未来主义宣言《给公众品味一记耳光》的主撰者马雅可夫斯基,其由天才诗人转而投入戏剧创作,与梅耶荷德联手创作了一系列经典之作,但人们对他的戏剧仅以“讽刺喜剧”命名,其颠覆性戏剧美学观并未被深入解读;而国人对梅耶荷德的理解也大多停留于“有机造型术”(或“生物力学”),对其深具“吸引力戏剧”方法的“元蒙太奇”思维却鲜有理论探索。理论或影像资料缺乏固然是一个原因(39)笔者因教学之故,由筹备排演特列季亚科夫《怒吼吧中国》一剧开始接触未来派戏剧以及未来主义美学,方始得窥未来派戏剧之一斑。,但如前文所言,即被爱森斯坦的电影权威话语虚化了戏剧焦点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潜在原因。
其三,爱森斯坦从承接梅耶荷德的戏剧衣钵、参与库里肖夫电影实验室的蒙太奇实践,再到接拍苏维埃国庆十周年庆典片《十月》,其所积淀的戏剧与电影素养在“吸引力”和“蒙太奇”的重叠部分——元戏剧和元蒙太奇“双元叠化”——中彰显出来。相对于戏剧来说,这是元戏剧,相对于《十月》以及后来的《战舰波将金号》等电影作品,这是元蒙太奇。由于“双元叠化”横跨了戏剧阶段的“并列、意合”探索和电影阶段的蒙太奇发展,形成一个有趣的“未来的过去”和“过去的未来”时间序列,元戏剧/元蒙太奇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来主义美学化身和“元”精灵栖息在“戏剧-电影”的双峰之间。它既开创了现代戏剧思维和语言,又开辟了有别于格里菲斯的以叙事为主的连续剪辑以外的、以意象表现为追求的理性蒙太奇电影之路。
其四,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未来派的戏剧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被迫中断——革命后的未来派经过重组,最终以左翼文艺阵线(即“列夫”)的名义开展活动。“列夫”的目标是把所有艺术的代表都包括在内,他们希望打消人们把跨理性诗歌当作是个人主义标志的印象,但遗憾的是,由于“时不我与”,“列夫”被改组,“新列夫”随后转向于“事实的文学”,这就等于把他们最初对传统的“壁垒突围”打回“被突围”原点,跨理性语言从“新列夫”的页面上消失。在当时的环境下,未来派戏剧精英除了爱森斯坦“转移”到受待见的电影行业外,马雅可夫斯基、特列季亚科夫、梅耶荷德等以各自的不幸而告别始终属于“未来”的戏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