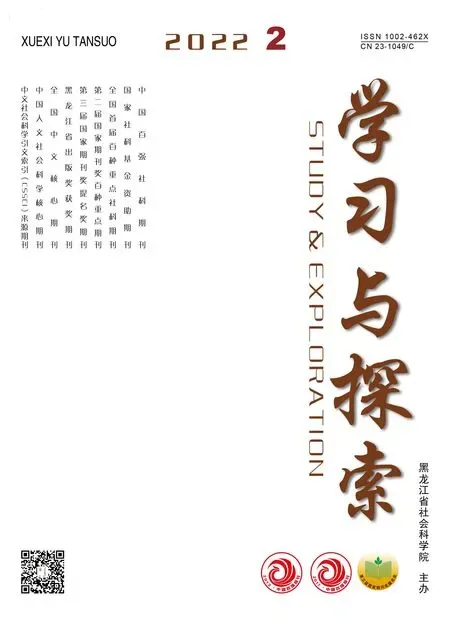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
何 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80年代起,中文学术界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韦伯热”,即马克斯·韦伯(1864—1920)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乃至更广泛的公共阅读领域的一个焦点,韦伯著作受到社会学及相邻学科的广泛关注,并不时引发公共话题。苏国勋先生很早就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韦伯热”现象,指出这一学术发展潮流首先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的“韦伯复兴”,此后,西方学界的韦伯热潮开始东渐,引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苏联、东欧诸国亦有其韦伯研究成果[1]。这样看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韦伯热”并非孤例,进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学术背景不尽一致,发展阶段亦有参差,为什么均产生了韦伯研究的热潮?
E.汉克提出了一个“深刻或激进的变革”命题,她观察到,世界范围内韦伯研究形成风潮,往往是在科学范式的变化、社会经济变迁和政治秩序产生合法性危机之时,文章甚至试图证明,在各国发生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过程中,韦伯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2]。具体到韦伯在中国的继受情况,蔡博方将韦伯文献的多样性列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详尽梳理了中文的韦伯研究文献,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手文献的集中译介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韦伯的接受[3]。
基于以上两个研究的立场,可以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即韦伯作品及相关文献呼应了变迁社会中的思想需求,从而引发关注的热潮。当代中国的情况与此基本相符:在改革开放40余年间,韦伯热的出现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其发生与发展既有赖于有利的制度环境,又回应了变革时代人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
不过,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诸经典都重新回到学术领域,为什么韦伯研究如此突出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且,从时机和环境两个方面来看,与其他理论大家相比,韦伯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具有优势,“韦伯热”的出现多少有些意外。一方面,韦伯著作进入中国相对较晚,并不占据有利的传播机会。韦伯作品最初进入中国学界是在1936年,即商务印书馆著名译者郑太朴所译《社会经济史》,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分工论》在1929年和1935年就已相继被译为中文了,影响很大;(1)1948年,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开篇即指出,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五十年间,“脍炙人口的重要作品”计14本,孔德、斯宾塞自不必说,涂尔干著作有三本在列,德语社会学列举的是滕尼斯、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舍夫勒(Schaflle)的著作,马克斯·韦伯及其作品未计入。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页。中国社会学从建立时期就深受英美或“西方社会学”(2)所谓“西方社会学”,在此指与“德国社会学”相对的英、美、法等国的社会学,参见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吴文藻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5-121页。实际上,德国思想与社会中长期有与英法等“西方”相对的自我认知,韦伯时期的“西方”仍然是与德国相对而言的,这一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发生变化。在韦伯文献的接受与翻译中可以看到“西方”概念逐步的演变,参见何蓉:《何处是西方?——韦伯文化通史的概念基础与流变》,《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传统的影响,德语社会学的影响本来就相对较弱,而且韦伯在19世纪90年代末罹患疾病之后,长时间疏离于学术圈,影响有限。换言之,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韦伯作品并未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学者的垂青。
因此,“韦伯热”在中国的出现,汉克的解释尚有不足。汉克注重学术工作的外在条件,但忽略了韦伯研究者的自主性。这种忽视会带来一种倾向,即韦伯作品在全世界不同时期的流行,会被看作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种“布道”。由此就可以理解,同样观察到了韦伯研究的热潮,在苏国勋先生看来,“韦伯热”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相继出现的一种类似的现象;而在汉克的文本中,韦伯作品在不同国家是“流行”(popularity)、“传播”(distribution),而在中国就是一种“发烧”(fever),其背后所预设的、非西方社会的被动接受和非理性膜拜是需要警惕并加以质疑的。
实际上,中文世界的韦伯继受史必须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前者使得社会科学新学术建立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中,后者是此一文明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巨大历史挑战与转折,而两者的叠加与交汇点,便是近代以来具有中国文化自觉和世界意识的知识人,他们所承受与呈现着的,是中国与世界、学术理想与现实境况等多方面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来到中国的百年历程,既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建立、发展的学术史,又是在时代大潮中探索新路径的思想史,更是在传统的溃颓和外部力量的冲击中实现知识人的人格重建的心灵史。
本文关注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韦伯研究的状况,与不同世代的韦伯学人(Weberians)的努力密不可分,应以核心文本与关键学者来理解韦伯在中国的继受情况;另一方面,韦伯被介绍到中国,实际上比“韦伯热”出现要早半个多世纪,应有更长期的学术史考察,或可有助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文学界韦伯热潮的性质与发生机制。
为此,下文将梳理相关学术史资料,将韦伯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步划分为初来(1920—1950年)、离散(1951—1979年)、复苏(1980—2020年)三个阶段。本文将进一步揭示,中文学界的韦伯继受过程涉及多种作用机制,有开眼看世界的“学习”过程,有韦伯作品与变迁时代、多样性的主题“呼应”,更有基于学术人能动性的“选择”。笔者认为,数代中国学者对韦伯作品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即并非被动的、简单的接受,而是基于自身文化认同与学术使命感的主动抉择。
一、韦伯“来而未到”(1920—1950年):基于学术自主性的选择
之所以说韦伯作品进入中国有“先天”的不利因素,首先有韦伯本人的原因,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韦伯都不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出现。他在学术训练上是法学家,获得了经济学的教职,以关注社会问题的农业经济学家出道,很晚才逐步获得社会学家的某种认同。而且,出于健康的原因,也出于思想情感的原因,他与德国学界的主流保持着某种距离,罗特梳理了韦伯家族史和思想史,表明韦伯具有某种“准英国人”的情感,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更为亲近[4]。因此,即便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家试图介绍德奥传统,由于韦伯并非德语社会学的主流而较少被涉及。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学的奠基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英美社会学的主导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清末,社会学经由严复、梁启超等学者的译介为中国学人所知;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程度逐步提高,第一批职业社会学家的学术取向主要源自英美社会学传统,知名的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均留学英美[5],甚或可以说,美国社会学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榜样[6]。因而,基于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专业化和建制化过程中,英美社会学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相应地,德语社会学对中国学人的影响并不突出。(3)据孙本文在1947年12月的调查,全国125位中国籍的社会学教授中,大部分具有留美经历,另有部分留英、法、日,仅有邱长康、冯汉骥、刘子明属于留德人员,另有陈序经兼有留美和留德经历,实际上,冯汉骥并非留德生,而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同时,社会学也不是当时留德中国学生青睐的科目,据研究者统计,截至1945年,留德的中国学生共计完成了47篇经济类、12篇交通、10篇农业与水利、9篇法律、7篇地理学、6篇中国政治、14篇自然科学其他领域、10篇人文类的博士论文。参见托马斯·哈尼师(Thomas Harnisch):《汉学的疏误?——1945年以前中国留学生对汉学的贡献和推动》,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刘梅译,廖天琪校:《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63页。
就笔者目力所及,1924年俞颂华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是最早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成果作介绍的中文文章。俞文指出,国人对德奥社会学的新动向缺乏了解,实际上,德语社会学界特色鲜明,既有注重科学法则的“经验派”,又有注重哲学研究的“直觉”派,两派之下又可进一步细分,其中,“德国知名之社会学家韦伯氏(Max Weber)”可归入经验派中的比较历史派。俞颂华进一步指出,韦伯社会学具有“物”“心”并重的特征,研究主题包括有关“资本主义源起与宗教之意义”“以历史与系统条理融合一贯”[7],点明了韦伯思想中统合精神与物质的驱动力、历史事件与演化机制的特色。不过,虽然俞颂华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语社会学已有一定整体认识,对韦伯的简短点评颇能把握要点,但他并不具有专业社会学者的身份,其影响并未能深入到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之中。(4)俞颂华(1893—1947)对德国社会学的了解得自其在欧洲的旅行与游学。1921—1924年旅德期间,他一方面作为驻德特派员,为《时事新报》等写作《柏林通讯》;另一方面研读马恩著作,学习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常到柏林大学旁听。1924年归国之后,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沪江夜校、东吴大学上海分校等担任兼职教授,讲授社会学、逻辑学等科目。不过,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在《东方杂志》任编辑,后以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学者闻名。
涉及韦伯的第二篇文献写于1934年,系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专门引介德国社会学的系统社会学派或形式社会学派的一篇文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文化类型学和比较宗教学等信息仅出现在文后的注解里。不过,由文中论述看,吴文藻知晓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此外,他在美读书期间曾经学过德语,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帕森斯英译本也已在1930年出版,也就是说,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吴文藻有充分的时间,亦有可能阅读到这本书的德文或英文本。更重要的是,吴文藻敏锐地看到了韦伯与德语社会学主流之间的差异,他指出,按照形式社会学的立场,韦伯有关宗教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甚至算不上是社会学,而只是宗教史与经济史的混合[8]。在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论文化表格》中,他将韦伯设定为“马克思派后期”的思想家,认为韦伯树立了新教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以文化事实间的功能关系代替了因果关系[9]。
由此可见,初入中国,韦伯所受关注并不多,而且有种种定位的游移,对中国学界没有过多影响。不过,这是一种无意间的擦肩错过还是有意的选择?本文倾向于认为,这种“忽视”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即具有自主的学术判断,在潜在的可能性之中进行鉴别与抉择。(5)本文所使用的“选择”一词,是建立在韦伯社会行动诸分类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概念。“选择”本身设定了一个理性和自主的学术行动者,在既定的外在约束之下衡量可能目标及其后果,基于目的—手段的计算而在潜在的可能性中抉择。基于此,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对韦伯的“忽视”亦是一种选择。
对此,吴文藻的上述两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家已建立关于德国乃至欧洲学术的清晰的知识框架,对于国际学界的动向非常敏锐,对不同学派之间的区别也有洞察力,(6)1935年,吴景超在《清华学报》发表一篇书评,其中指出,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兄弟二人以历史材料来解决社会理论问题的路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是有启发性的,即以应用社会学的眼光去整理历史材料。参见吴景超:《哈特曼〈社会学〉书评》,《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应当看到,这是较早从韦伯理论入手、从方法或进路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探讨,提出了具建设性意义的学术路径。因而对韦伯的惊鸿一瞥而未加深入,更有可能是出于研究立场的取舍。
支持“选择”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者是费孝通。在费孝通学术生涯早期,除了1940—1941年间写作发表的《禄村农田》《消遣经济》等篇简短提及韦伯之外,并未发表相关的专门研究,亦无理论应用的例子。但他有关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轶稿近年来被发现,对轶稿的深入分析表明,他不仅了解韦伯的名著,且对英国社会经济史等相关学术脉络有充分的知识[10][11][12]。不过,轶文将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放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思想脉络之中,进入了一个以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凡勃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研究的问题体系[13],其思路包含着欧洲思想史和社会学史的诸多线索。换言之,费孝通的阅读以韦伯著作为平台,延伸到了更大范围的学术主题,因而,虽然曾经对新教伦理的相关文本着力甚多,但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与韦伯的关联并不显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既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又有紧迫的发展要求。例如,中国并未有类似西方的教会宗教传统,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状态既出不了加尔文这样的人物,且加尔文那一套也行不通;从时代背景来看,韦伯讲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发生学问题,费孝通面临的则是现实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强势地位。费孝通及他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关注的是,在被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世界所包围的条件之下,中国自身作为一个复杂的、高度发展的独特文明体系,无法简单移植其他道路,而应致力于本土社会实践,实现强国富民。或许因为如此,他无意从学理上追觅宗教与经济的历史关联,而投身于理解中国社会、正视乡土特色、寻求中国发展之途。
费孝通的选择与不选择体现着中国知识人在重大转折时期的困顿与自我拯救。对于这一代知识人而言,中华文明自身是根本前提与约束、是思想与价值的资源、是自身认同的来源。知识人的重建,亦是护持并重新安放文明之脉的过程。
费孝通与韦伯的未尽之缘表明,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肢体与心灵亦随时代而动荡,产生某种身、心之分立,立足于中华之文明与社会系统之“身”,无法专一其“心”而仅致力于纯粹的理知探索。观照其中华文明之身而非仅满足个人理知的追求,成了知识人的自我建设之途。
这篇文稿未能更早刊出,终究是一种遗憾,韦伯及其作品对费孝通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力不那么显著,更未通过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产生影响,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道路既是被选择所决定、也是被未选择所决定的。从学科史的发展而言,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们具有内在的文化自觉、从而对西学有取有舍。从韦伯学说传播的角度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韦伯学说便传入中国了,却终究未能真正立足,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开端。
二、离散时期(1951—1979年)的遥远呼应:通过韦伯回望中国
以上对韦伯初入中国的学术史梳理的一个背景是,彼时韦伯的国际影响仍相当有限,他在世界社会学学说史的地位,有赖于20世纪中期开始帕森斯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力、美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学界的地位上升等时代背景。这样,在中国早期社会学(7)陆远的研究梳理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相关限定[5]6-7,本文采纳其界定,即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的30年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韦伯被放置于时代的思想脉络、问题意识的整体之中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了。在20世纪中期国际韦伯学界掀起热潮的同时,社会学在中国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家的学术命运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简言之,一部分人失去了社会学家的身份,一部分人则失去了中国本土的生命滋养,韦伯理论构成了后者成长中的学术背景的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旅居美国的一些中国学者处于韦伯理论的强势冲击之下,即塔尔科特·帕森斯、爱德华·希尔斯、格斯与米尔斯、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等几代学者竞相翻译韦伯作品、推进韦伯理论和韦伯式路径的经验研究,其中,1951年H.H.格斯的《儒教与道教》英译本出版,主题的相关性使得旅美中国学者有机会表达对韦伯学术的理解,李树青、杨庆堃是二战后前往美国的一代中国学人,作为中国人而具有的文化传承与认同,使得他们对韦伯作品中有关中国、有关世界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有特殊的关注。
例如,李树青在1952年1月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一篇书评,高度评价了韦伯的这本著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他指出,简单地批评韦伯的资料不充分、数据不准确等是容易的,但是瑕不掩瑜,韦伯的成就仍然极为突出,因为相对于传统中国学者对悠久文化的沉迷、眼界的局限,相对于西方汉学家身陷种种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迷雾,韦伯表现出了驾驭广博资料、应用比较视角的出色能力。通过简单勾勒韦伯书中有关儒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国民经济等内容,李树青试图表明,韦伯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解读,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14]。
对《儒教与道教》更全面的解读来自费孝通的同学杨庆堃,1964年,他为英译本写作了一篇重要的导言。由于此前(1961)他有关中国宗教的著作已经出版,杨庆堃对韦伯的理解更深入,对其理论之繁复、内容之丰富和洞见之深刻有较为全面的解说,在主题梳理、材料评析、论证逻辑等评述基础上,强调韦伯著作的比较研究、行为研究的科学性质,以及身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却能够系统地勾勒出古老中国的特色、提炼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命题[15]。这篇导言附在格斯的译文之前,构成了重要的导读文献,其影响至今不堕。
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意外地使韦伯著作影响了一个离散的学术群体,即20世纪50年代以后跻身美国学术界的中国学者,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西方学术与东方认同之激荡,反射出那一时期学术的曲折之光。他们恰逢其时,受到了当时极盛的韦伯理论的影响,荦荦大者,除李树青、杨庆堃、瞿同祖外,(8)瞿同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其间曾听过帕森斯的《宗教社会学》课程,当为其受韦伯影响的渠道之一;不仅如此,他在美期间写作的《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一文被认为具有“最好的韦伯传统(best tradition of Max Weber)”。参见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还包括杨联陞、黄仁宇、(9)黄仁宇受韦伯著作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也有自主的思考与创见,此不赘述。参见陈占江:《现代性的他者:“传统”与“中国”——以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为讨论对象》,《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4期。余英时、许倬云等文史学者。这一批学者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而且,随着近年来社会学对历史维度和中华传统的重视,他们的研究路径将对社会学有更具体的影响。仅从本文的论述而言,尽管他们并不以专业的韦伯研究者知名,但其作品中蕴含着中国知识人接受、发展韦伯理论的不同路径,有的取径中学、有的立足西学,但殊途同归,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华文明。
例如,在立足中国、交汇中西方面,杨联陞的努力尤为卓著。20世纪50年代韦伯理论在美国学术界流行之时,杨联陞已任教哈佛大学,享誉国际汉学界,其后多篇著作都有对韦伯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尤其善于提炼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本土概念。例如,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中,杨联陞陈述了交互性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原则,对帕森斯所传达的韦伯的中国文化论述,杨文并非简单接受,而试图进行对话,表现出文化的自觉与学术的自主。(10)参见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9-202页。此外,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直接回应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国宗教研究,是在西方学术框架下、基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提问,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享有盛誉,2021年该书由田浩(H. Tillman)编译为英文出版,进入了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渠道。
在突破区域研究的框架、对社会科学理论命题进行推进方面,何柄棣的工作尤为显著,他的治学有以西学为知识框架、以中学为立足点的抱负,其学术理想系以西人史学的最高水平为尺度,以国史研究的心得,突破汉学局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例如,何炳棣以历史材料与数据质疑了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的发生学的努力。在1954年发表的在对两淮盐商的研究中,他梳理了食盐生产、销售的规模、组织、财富与成本等数据,指出盐商群体中的炫耀性消费、家族成员入仕比例高等现象,尽管财力雄厚,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因而主张中国近世并无“商人精神”,对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不以为然。这种以普遍理论为框架和追求的学术理想,使得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出汉学或史学的藩篱,与美国社会学家产生互动,并曾在1964年参加了加州大学“家庭制度的危机”多学科研讨会,宣读了《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家族制度》一文,与韦伯理论的权威帕森斯有问答往还[16]。
韦伯理论对较年轻一代学人的影响更为显著。许倬云1957年赴美,自述适逢韦伯理论在芝加哥大学兴盛的时期,对其宗教、城市经济、理想型的方法等都有所钻研。(11)参见:http://www.cssm.org.cn/newsite/view.php?id=26359。因而,在许倬云的作品中,无论是《西周史》这样较系统的研究,还是《历史分光镜》之类的研究心得或笔记,以中国上古以来的国家、华夏文化的形成、文化动能与文化比较等问题为关注点,着力在中国,着眼却在世界,其间不难发现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乃至直接的引用。
当然,旅美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主流学术界影响有限,但是,即便存在种种困难与挫折,他们的工作还是在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12)参见吴原元:《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繁荣,藉由他们筚路蓝缕的学术工作回流到中国学术圈,韦伯的影响洒播到中文学界,构成了一个分散的、曲折的作用链,显著地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韦伯阅读风潮。
从韦伯继受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批学者的研究主题、方法等不尽一致,例如,余英时试图在中国社会中梳理资本主义精神之对应物,开启了一条讨论中国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路径,其后十余年间有关东亚经济腾飞的文化解释大多在此路径上;何炳棣则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工具切入中国制度与文化研究,以更具普遍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验。虽然在侧重点、方向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试图通过韦伯思想来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体现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学重建,这一批学者的成就传播甚广,藉此韦伯在中国人文与社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的“韦伯热”(1980—2020年):中文韦伯研究的启封与行进
如前所述,韦伯学说进入中国的前半个世纪中,并未真正落地,不过,国际学界韦伯研究的发力基本上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1]13-20。甚至二战后西德尚需法国人雷蒙·阿隆为其讲授韦伯学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韦伯有关方法论、世界宗教的比较历史研究、经济与社会诸领域等大部分著作相继有了英译,新一代韦伯学者不断出现和成长。特别显著的是德国学者的进场推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沃尔夫冈·蒙森、沃尔夫冈·施路赫特、弗里德里克·滕布鲁克、迪尔克·克斯勒等德国学者的韦伯研究广受关注,立足于韦伯著述史及其德国学术传统,从文本脉络、思想背景、视角与范式等角度,大大加深了国际学界对韦伯的理解与阐释[17],由此,当中文学界关注儒家伦理等主题时,与国际学界对《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经济通史》等作品的关注不期而遇,并可汇入后者、成为其组成部分。
与此基本同时,中文韦伯研究获得了一个重要发展契机,即中国社会学的重建。1978年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界隔绝、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状况开始改善,自此,社会学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学界积蓄已久,汇聚民国学术与海外华人学者之力,开始恢复社会学学科,前述初来、离散时期培育的韦伯影响力,复又挹注、浇灌新时代的学术根芽。
因此,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韦伯研究热潮与国际学界的韦伯复兴基本同时。差异在于,由于学术传承的断层,中国的韦伯研究之热,呈现出学习、选择与呼应的继受机制同时发生的叠加状态。例如,一个典型的年份是1987年,这一年,丁学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韦伯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一文,介绍韦伯比较历史研究、新教伦理、中国宗教研究,于晓、陈维纲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苏国勋先生完成了中国第一篇以韦伯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这一年的三篇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的韦伯著作的引介、汉译和韦伯研究均已开始发力。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适逢国际韦伯研究界云蒸霞蔚的新气象,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韦伯研究起点很高,享受到了中华文化圈的学术“红利”,韦伯作品和重要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多、质量提高显著。韦伯的重要著作,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方法论著作、学术与政治的演讲等,在各个时期,均有多个中译本问世。自2010年以来,以往在国际韦伯研究界亦较受忽视的一些韦伯作品,如中世纪合伙制、古罗马土地法、音乐社会学研究等都有了中译本,韦伯方法论著作有了选编全面、译文流畅准确的张旺山译本,与同期出版的英文编选本相比,各擅胜场,这些都推动着中文韦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3)数十年间的韦伯作品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译者群体,诞生了一些社会理论的出版物。例如苏国勋先生主编的《国外社会学》,前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创建初期的参考资料汇编,1986年以后改为内部刊物,专事译介国外社会学的理论思潮,其中包括了不少韦伯研究的经典文献。还有韦伯研究的同人出版物,以北京大学李猛主编的《韦伯:法律与价值》(2001)、《韦伯“科学作为天职”100周年纪念文集》(2018)等为代表,集合了相关主题的经典文献和国内学界的新锐研究,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韦伯研究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随着东亚“四小龙”在二战后经济腾飞,学者们希望从儒家传统去解释东亚现代化,因此,对韦伯的探究集中在其新教伦理研究、中国研究之上,尤其侧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在今日形势下谋求儒家思想实现自我转折与自我充实,以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现代化中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1]17。基于此种理论与现实的呼应,1983年、1985年、1988年在中国香港召开的三次“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华人学者对中国传统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关系进行探讨,对韦伯有关中国的论断提出质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思考。在此热烈的研究氛围中,1985年,《读书》杂志召开了“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标志着中国韦伯研究的热潮之开端。
然而,中国社会理论领域的韦伯研究者并没有局限于风头正盛的儒家伦理命题,而是关注韦伯自身更为丰富和深入的文本脉络。自1983年起,苏国勋先生以哲学为依托、以社会思想史为研究方法,以宗教、政治、方法论为主线,梳理了相关韦伯作品,提炼、阐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他完成于1987年的博士论文《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不仅是中国社会学韦伯研究的启封之作,而且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首部介绍西方社会理论的专门论著。其学术锐度在于,看到了西方学界流行的韦伯诠释背后是某种单一的现代化路径,忽视了韦伯学说本身有关理性化过程的局限与张力。经由对韦伯著作的深入探寻,立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处境,苏先生指出,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道路既非独一、亦非主导性。此探索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为刚刚恢复的社会学学科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扎实的理论基础,成为引领新世代社会理论学者的典范之作。
此外,社会理论学者对韦伯文本的深耕,一个持续深入的工作是韦伯作品的汉译,这不仅是使经典得以表达的过程,更是力图将现代汉语打造成学术语言的事业。翻译使韦伯作品进入中文学术研究,翻译史本身亦体现着韦伯学术的成长,尤其是韦伯研究的视野逐步开阔、见解逐步深入。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为例,1986年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应是最早的中译本,但存在着未将该书非常重要的注释部分收入等重大缺失。随后,三联书店在1987年出版了于晓、陈维纲等翻译的版本,将原书的注、帕森斯添加的注等悉数译出,形成了一个实用的译本,其后将近20年间,这一译本是学界阅读韦伯的基本选择,影响深远。另一个译本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从2004年起引入的台北远流版,由康乐、简惠美译出,译文格式等以德文原样为基础,添加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部分,并有不少相关背景知识的注释,流布广泛,受惠者众。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等的新译本,反映了国际韦伯研究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动态。可以说,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著作的三个中译本各有特色,为不同时代的学者阅读韦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从韦伯继受史的角度来看,则分别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学习西方社会理论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以后专门的韦伯研究更深入、更强调贴近德文原文,以及新世纪以来与国际学界逐渐同步发展的三个阶段。(14)这一划分与肖瑛、郭琦的研究基本一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理论研究队伍可以划分为三代人;第一代在社会学恢复之初从哲学等学科转入社会理论领域,对社会理论研究有开启之功;第二代在世纪之交崭露头角,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了框架、研究规范、培育研究梯队;第三代在2010年左右开始活跃在社会理论诸领域,并形成了有实质交流、共进的学术共同体。参见肖瑛、郭琦:《从引介到重建: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国进程》,《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韦伯研究领域的学术传承亦具有类似的代际特征。另,按照所属机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机构在韦伯研究的学术积累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卓著。其间的问题意识亦有转变:早期阶段,学者虽然缺乏对国际学界动态的了解,但有将韦伯作品置于西方学术与文化背景之下的眼光,有鉴古知今、无问东西的胸怀,韦伯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是整个思想界参与的、具有整体学术史意义的事件;到了新世纪之初,经过社会理论界的长期努力,韦伯研究的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文本,树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和研究框架;近10年来,韦伯研究领域增多、问题更深入,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看世界,与国际学界之间建立对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社会学研究》(15)在2005年《社会》改版、2013年《社会学评论》创刊之前,《社会学研究》(1986年创刊)是中国唯一的社会学专业学术刊物,因此,透过《社会学研究》即可直观地看到中国社会学的高水平研究。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办的《社会理论学报》、南京大学《社会理论论丛》等,亦成为社会理论和韦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的刊物。自1986年创刊至2020年,共刊发30篇以韦伯为主题或主要依托韦伯文献的文章,从主题上来看,方法论文章的数量最多(5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问题的关注,涉及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次之(4篇),这与学术资源积累和思想导向有关;从写作方式来看,得以在较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展开研究,其内容一方面深入“新教伦理”等经典命题,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社会与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反思,涉及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国家社会学等专门领域。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近四十年来,中文学界韦伯研究本身的发展成就卓著,积蓄着新生研究力量;韦伯研究的成长过程,亦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发展、学术话语积累、学术人才培养的历程,反映了社会学各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拓展,并有结合中国社会、中国经验的深入思考。而且,中国当代的韦伯热具有跨学科的特色,对韦伯的热忱有不少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之外,且都有相当出色的成果,因此,“韦伯热”是当代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韦伯 “继受”不是无批判的接受,而是韦伯研究者基于学术视野、内心情怀的主动选择。作为对前述汉克相关论述的回应,笔者认为,中国的韦伯研究热潮,不是后来者对前先者的跟随,不是无批判地接受普遍对特殊的统摄,而是共同经验的挖掘与辨析,其立足点在本土,其眼光则在全球,有充分的潜力、以新的视野将经典范式推向新的解释边界,推动社会学范式的建设与创新。
四、结语:基于韦伯研究的世界学术的可能性
通过学术史梳理,笔者认为,韦伯来到中国,有一个并未完成的“序章”(1924—1950年),还有一个意外成就的“别传”(1951—1979年),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才真正落地生根,自此,学界的韦伯热潮从未消减,其中,既包括专门的韦伯研究,也包含着依托韦伯理论的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对不同主题的探讨,既有基础的翻译、文本梳理,也有对理论的应用、反思与进一步的发展,如同一部结构复杂、律动丰富的“交响曲”(1980—2020年)。
本文将韦伯继受史向前大大推进,这有助于摆脱中国学者仅仅是被动“学习”的刻板印象,并有可能发掘出韦伯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隐含的关联,即源自知识资源、问题意识的某些重合。例如,韦伯在写作《儒教与道教》时,使用了传教士明恩溥的著作来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与民间社会,而潘光旦亦应用了同一作者的著作来发展其优生学[18],其间的关联与两者的差异应是颇值深入探讨的话题。再如,《儒教与道教》所引用的一个社会史的资料,就是社会学家陶孟和在英国留学期间与梁宇皋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乡村与市镇的生活》(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19]。这表明,韦伯著作与早期中国社会学之间,时间的、主题的、资料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甚至有可能存在某种平行发展的、潜在的对照关系,或者说是某种近乎同时代者的关联或某种天然的呼应。
可以说,韦伯研究在中国之真正开启与发展、韦伯热潮背后的驱动力,是中国的韦伯学人的学术素养与文化自觉。在此意义上,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未引介韦伯,与苏国勋在20世纪80年代从哲学进入韦伯研究,其背后的动力是一致的,即将韦伯作品置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长河之中,置于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根本关注上,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费孝通回到乡土中国、寻求富民之途,苏国勋则深入韦伯作品更基础的理论脉络当中。
回溯苏国勋先生的学术路径,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转折。首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从公认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学科,转向尚在恢复中、学术积累尤为薄弱的学科。这一转向有源自哲学尤其是社会学哲学的积累,也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因而不仅是个人的学术道路的选择,更有梳理学科脉络、建立专业领域的使命感,又有不受学科畛域局限的视野。1996年,他在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哲学》卷所写的“导论”中梳理了社会哲学、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不同,表明了这一转向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诉求[20]。简言之,经由社会理论,可以从人的活动、互动、群体生活及其秩序等方面研究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哲学思考的延伸,体现着对现实内容的关照,建立可检验的因果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导论”明确了社会理论的科学属性和学科特征。
第二个转折发生在21世纪之初,苏国勋先生从紧扣西学脉络,转而悠游中国文化之思,基于深厚的中西学术积累,以中国经验为立足点,对韦伯的中国研究进行了批判分析,检视其研究立场、分析方法,认为韦伯在有关中国的知识上有偏见与不足,并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21]。苏先生的立场在于,既应看到韦伯思想中弥合行动与结构的冲突、多元因果分析和超越唯物与唯心对立等教益与启迪,又要在立足文化自觉的立场上,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展开与韦伯的对话。正是中国的韦伯学人的眼光与胸怀,使得中国的韦伯研究具有突出的主体意识,在本土性中实现其超越性。
作为中国最早的韦伯研究者,苏国勋先生的这一转折是自身研究方向的调整、是对个人既有成果的突破,但并非对韦伯文本的疏离,而是更深刻理解、更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创见。因此,苏国勋先生对于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将儒家传统与东亚诸国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的关系等做法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认为韦伯被诠释为一位文化论者的同时,实际上忽视了对其作品的制度论面向的解读,苏先生倡导“利益驱动的因果性说明与结构制约的意义性理解”的“双向诠释”[22],为韦伯研究指出了一条方法论路径,并将关注点放在韦伯文本自身的丰富内涵上。
实际上,从苏国勋先生的教育背景、成长氛围而言,他很早就有机会了解一个线索多样、多传统的“西方”,体验多宗教并存共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因此,看上去只是学术生涯中与西的重心转换,实则是基于生命体验的学术新开拓,并在此转折中,将中国社会嵌入社会理论,完成了近代以来知识人重建的关键环节。由是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使当代中国韦伯学人得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成长,融汇中西,在学术问题的牵引之下,不断突破自我、向着未知之域进发,以社会理论梳理古老的、尚少社会科学分析的中华文化传统,将学术融入生命、以己身济渡来者。
回顾近百年中国韦伯研究的学术史,既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又是几代学人的“心史”。中国的韦伯学人不仅努力深入学术的文本脉络与理论范式之中,还力求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工作之中。前述韦伯继受的三个阶段的社会环境不同,与之相应,韦伯学人的学术抉择亦有不同。
在第一个阶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在学科初创的同时,就要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换言之,既要让社会学讲中文,又要让中文成为一门学术语言;兼以在风雨如晦的时节,中国知识分子更面临着强国富民的迫切现实要求、为中国寻出路等任务,因而,在种种内外条件的约束之下,对韦伯作品的引介有限,仅具有理论史的参考意义。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中期,韦伯的中国研究、世界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等作品获得了海外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发展为学者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契机,通过韦伯研究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与道路,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提供思路。第三个阶段的学术繁荣,得益于前辈学者的中西学术积淀和将中国学术置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胸襟,中国近四十余年间的韦伯研究得以启动,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理解韦伯及其时代问题,另一方面,以韦伯研究为契机,以完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为使命,进而推进中华文明的自我省思。进入新世纪,韦伯研究界立足世界学术、立足自身文化传统,深入到各个专门研究领域加以推进,韦伯学人所关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家庭与社会政治制度、农业社会学理论、宗教与世界文明等问题,回应了经典的理论主题,为社会学及相邻学科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多样的研究主题。
中文韦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以来,与国际学界的重要转向基本同步,中国韦伯学人的成就使得基于韦伯研究的“世界学术”成为可能,即以韦伯文本为平台,以其中包含的学术命题与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以并立而多样的世界文明体系为对象的学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四十年的韦伯学术有自身的脉络,但与欧洲、美国、东亚等地区的韦伯研究同属于整体的世界学术的一部分。
因此,当代中国的韦伯研究者对于世界的韦伯学术亦有其独特贡献,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从韦伯继受史的“学习”机制的角度,汉语的韦伯研究已具有较完善的文本基础,但研究型翻译及文本梳理仍需努力,将韦伯置于他的时代背景、学术传承和交流网络之中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推进;从“呼应”机制而言,中国的韦伯研究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现实关照,韦伯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解的工具、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中有关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经济组织、家庭与社会团体、教育、政治制度与技术等内容,对于当下的中国研究仍有所启发;本文所主要关注的“选择”机制则体现出中国韦伯学人的学术自主性,即在自身价值理念烛照之下的深耕与创造,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对韦伯理论进行反思、修正与推进,透过普遍理论和中国经验的互动与创新,中国学术受惠于世界学术、亦可为其活力的来源。
正如克斯勒观察到的那样,韦伯在世时从未成为主流,但却在身后成为经典大家,除却其作品本身的因素,其声望得以形成的动力,源自韦伯作品的研究者,例如,以韦伯夫人为代表的负有特殊使命的人(trustee)、温克尔曼为代表的鼓与呼者(promoter)、帕森斯为代表的理论诠释者和国际传播者(interpreter and international propagandist)。有意思的是,不少为传播韦伯著作与思想努力的人,往往亦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甚至并非社会学家,更非划地为牢的学派,在韦伯学说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国际韦伯学者的“看不见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s” of international Weber-scholars),他们当中,有人关心韦伯作品的历史语境化,有人关注韦伯作品的理论延续性,经由这些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韦伯研究者,马克斯·韦伯成为“活着的经典”[23]。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韦伯著作所受到的格外关注,源自其作品的格局、主题等,内在地呼应了中国四十余年来的种种巨变,具有文化自觉的中国学人在其作品中发现了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因此,一个认可韦伯开放学术精神的韦伯学人,会秉承着科学的原则,向着韦伯力不能及的领域拓展;一个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韦伯学人,会以学术的精神,肩起中国文化的反思、创新与存续的任务。此或为热烈与冷静、继承与发展的共同汇聚,从而有可能构成一个以韦伯为对象、韦伯作品为平台、以真实与真理为共同目标的“世界学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构成了雷蒙·阿隆意义上的我们的同时代人;韦伯又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或那个国家,而属于科学世界的一个部分,在每一代人的最高价值之光之下不断映射出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