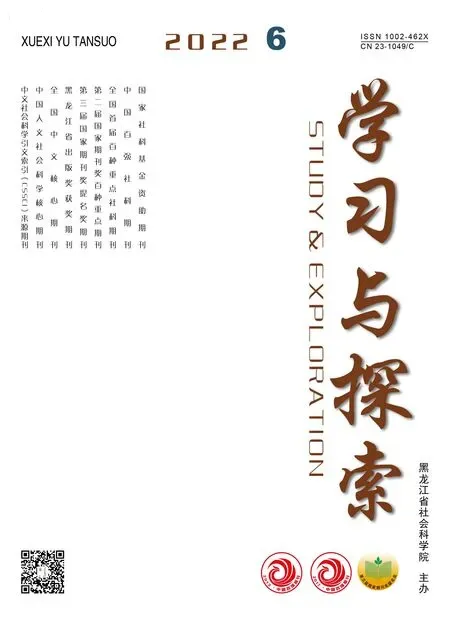当代西方左翼共同体之思的不同面相及其文论价值
王 琦,梁 海
(1.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081;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早在1920年代超现实主义时期,巴塔耶就开始思考个体如何通过相互关系而形成整体了。1930年代其更是致力于“反攻”“无头者”和“社会学学院”等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的组织和实践,1940年代在“无神学大全”里重提迷狂体验的交流问题,最后总结出“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1]3的思想。巴塔耶毕其半生精力,对共同体进行的先行思考与运作实践,或隐晦、或明朗地奠基了法国知识者对共同体的基本态度——反思和重构。正是在巴塔耶的光芒与阴影下,面对着共同体失落的历史命运及其引发的怀旧情绪,面对着共同体的迫切要求正不断遭到遗忘和离弃的现实处境,以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2021)、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8—2003)、吉奥乔·阿甘本(Giogio Agamben,1942—)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左翼思想家展开了一场“共同体之辩”,接续了这一反思和重构的基本态度。他们的共同体之思,既是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思想基础上的自为生长,又是彼此共同体思想的相互应和,形成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同体之思的不同面相。在传统共同体遭遇现代化浪潮洗礼和后现代解构思潮冲击而濒于瓦解之后,清理这些不同面相,对于我们理解和反思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南希:从存在的独一多样到共同体的非功效
南希继承了巴塔耶“失落的共同体”和“否定的共通体”开辟的反思和重构态度,首先区分了共同体的两个层面,继而在传统和现代的冲突结构中反思“封闭的共同体”并重构“非功效的共通体”。南希把“存在—于—共通”(l’être-en-commun)的逻辑嵌入存在的理解之中,在德里达“有限性共显”的基础上提出了“独一多样存在”的概念。存在既是独一性、个性化的存在,又是多样性、共通性的存在。共同体是保障存在的这种“独一多样”性的组织,在其中,一与多的张力关系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存在论意义。不过,在南希的理解中,处于共同体之中的“独一多样存在”其实是“非体”之体——非逻辑主体、非呈现的物体、非言说的语体,共同体因此也成了“非功效的共通体”,是无体之体。
(一)反思:“封闭的共同体”的失落
南希首先区分了communauté一词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指涉着同一性、有机性和中心化的“共同体”;二是指涉着无目的性、非本质化、共通性和分享性的“共通体”。南希用“共同体”来指称建立在亲缘、地缘、血缘等基础上的、实体化的、有机生成的社群生活形式,这是其所反思的“封闭的共同体”;用“共通体”来表达自己应对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寻求对策的理想社会生活愿景,这是其所建构的“非功效的共通体”。南希共同体之思的基本要点在于“共同体分裂、错位或动荡的危机是现代社会最痛苦的见证;传统理解中的共同体是以人为中心、以个体为基础、以自杀逻辑运作的封闭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应该是建立在独一性共在基础上的,以绽出、外展、分享作为本质特征的共同体,它总是拒绝任何实体化、中心化、同一化、内在化的或显或隐的倾向,而总是面向非实在性场域、外在性、差异性、他异性等保持开放”[2]。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南希的共同体愿景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
南希将传统的、封闭的共同体的失落理解为神话和共同体的打断(interruption)。这里的“打断”含有失效、封存、保留、重启、再生成等意味,喻示传统的、封闭的共同体已经成为一去难返的“乡愁式”存在,也暗示出要开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必须重启共同体的建构、重建共同体话语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希的共同体之思在解构传统共同体观念的同时,并没有陷入共同体失落或消失的虚无主义之中,故而具有极大的建构意义。南希通过改造和深化海德格尔的“共在”和“共同此在”概念,发展出“存在—于—共通(l’être-en-commun)”的基本理念。根据这个理念,所有存在都是在共通中的存在,所有共通都是存在的共通,“存在于共通”或“共通中存在”的基本状态规定了“于”(en)作为存在最基本的结构或方式。“于”即“在之间”,属于存在的关系范畴,分享、沟通、向着彼此外展、打开间隔空间、创造非实在性场域等,都必须以这个“在之间”关系范畴为前提。这决定了南希愿景中的共同体是“存在—于—共通”的共同体,其功能在于“在承认独一性的界限时又分享彼此共在的间隔空间,以此打破极权主义的‘内在性’的总体政治神话”[3]381。对南希来说,共同体被抹除或取消,不仅仅是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幸,更是本体论上的不幸,因此存在在本质上是存在于共通的。
因为为了存在的私有的存在,在本质上,或者说不仅仅在本质上,是存在于(/通过:en)共通的。存在于共通意味着独一的存在只是存在着,表现自身,显现在一定范围中,在这个范围中彼此共—显,外展,表现和供奉出自身。这个共显不是添加于存在之外的某种东西,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在这个共显中——成为存在[4]146。
存在本身是独一性的存在,是在而且只在共显中才成为存在的,共显、外展、绽出、分享、于共通之中是存在作为独一存在的基本特征,独一存在于自己的内在性中始终保留着一个敞开的间隔。正因为这样,独一存在始终抵制着无限内在性的主体化和封闭化。需要注意的是,共显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对于主体间性而言,它首先预设了一个先在主体,之后才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才有主体间性,所以有论者指出主体间性的局限:“虽然讨论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仍旧以隐含的方式被保留着。”[5]
南希所指的共显属于更加本原的层次,它取消了存在的主体性及其特权,拒绝存在被整合或融会成同一性,它强调的是存在的独一性,是剔除同一性又见出区分性的相互分享和彼此外展,这也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有限性共显:有限性共显“并不自我创立,并不自我安置,它并不出现于已经被给予的主体(对象)中间”[6]355-356。作为共显的独一存在始终保持着警醒,既不在与外部的彻底连接中失去自我,也与妄图融合彼此的内在性、同一性、亲密性保持距离。
共显、外展和“共/与”的本质,使共同体成为一个内在性被撕裂了的“共同的织体”——严格说来,没有“体”,没有织体,没有肉体,没有主体,没有实体;有的只是共同,只是共显,只是共享,只是共/与本身。这也就是共同体的“不可能性”。被撕裂的内在性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巴塔耶意义上的“裂口”(déchirure),它不是虚无,不是伤口,在裂口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一个向外部不断展露和绽出的开口,正如言词从人的口里说出来一样,外展出的是在我自身之外如同在我之内的存在本身。所以,共同体的存在只是作为诸独一性的外展和外展的分享,这也就是共同体不能作为某种作品(work)存在的“非作品性”。这样,以人(生产者)、国族、精神、灵魂、话语、制度、象征等他者作为共同体之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解,就被从基底里彻底地解构了,共同体终于处于“非功效”(désœuvrement)状态之中了。
(二)建构:“非功效的共通体”
所谓非功效,指的就是某种打断、取消、悬搁、中止的东西,它使作品处于未完成状态,取消了作品的功效性、完成性和自足性。用南希自己的话来说,“非功效指的是,在作品的这边或那边,那种离开作品的东西,那种不再同生产或完成打交道,而是遭受到中断、破碎和悬搁的东西”[4]78,“非功效是共同的面孔和亲密性的失效”[4]98。
显然,在南希的理论世界中,共同体的非功效是指悬搁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共同体之后产生的那种东西,是对内在性的抵抗和超越,是作为作品的共同体的不运转和不起作用,是共同体的非作品性和永不完成性,也就是同一性被打断之后的永不完结的分享、沟通、共显、共同、共与、共通。
不存在共通体的实体,也不存在共通体的神圣基体(hypostase):而是存在有“激情的释放”,独一存在的分享,以及有限性的沟通。在其通向它的界限的时候,有限性“从”一个通“到”另一个:这个通道构成了分享[4]87。
这样,南希的共同体之思就与他的共在本体论哲学取得了理论上的呼应。概括而言,南希的共同体是建基于他将存在理解为“居间存在”(être-entre-deux)和“共通中存在”的。正是“居间”和“共通”,决定了存在永不会让自己被吸入什么共同的实体,决定了共同体永不会拥有或留居于任何形式或任何地方,决定了共同体只是诸独一性存在共同分享和共同显现的非实在性场域。所以,真正的共同体并非被建构、生产或加工的产品,也不生产/再生产任何形式的实体化作品,因为任何成形的产品和作品都必然令共同体失去“居间”和“共通”之意,也会失去“一起”(together)和“共/与”(with)之意,正是“非功效”(/非操作/非作品性)才是共同体形成的缘由。
在上述理路中,南希充分发挥了解构作为方法的力量,解构了传统的封闭的共同体那种潜在的极权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色彩,以“存在于共通”作为基本理念从根本上重构了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剔除了以个体作为共同体组成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体现出极为深厚的思想底蕴。他建构的“非功效的共通体”,其实正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同体之思形形色色、不同面相的共同体形式之一,“非功效”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后现代语境中共同体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显示了南希应对社会转型引发的普遍焦虑而勇敢探索的努力。
二、布朗肖:从他者和言语的共通性到共同体的不可言明
南希的“非功效的共通体”理论对布朗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布朗肖认为南希偏离了巴塔耶开辟的道路,指责南希所建构的共同体仍然是传统的共同体。布朗肖借助于巴塔耶的“否定的共同体”提出了共同体的不完满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发展出“不可言明的共同体”思想。
(一)共同体的不完满原则
在《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Communautéina-vouable)中,南希的共同体之思成了布朗肖的评论对象。在这本小册子里,布朗肖对南希关于共同体的主张颇以为然:传统的、封闭的共同体主义作为人之绝对内在性的目的论预设;共同体并非从属于某个群体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共同体不是社会形式也不倾向于共通的融合;共同体不生产任何形式的作品;外展、分享和非功效才是共同体的本质……然而,布朗肖又绝不仅仅是重申共同体的“非功效”。他所要论证的,是“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7]。他在巴塔耶那里所发掘的也不仅仅是共同体的“否定的”特征,还有“不充分性(insuffisance)的原则”[1]10(不完满原则)。在布朗肖共同体之思的思想泉眼里,也绝不仅仅只有巴塔耶的“否定的共通体”,还有列维纳斯自我与他者的不对称性、杜拉斯情人共同体中的“死亡的疾病”;除了书写的、文学的共同体之外,还有友谊、阅读、献祭、离弃……可以说,布朗肖对南希的评论,与其说是对南希的回应,不如说是共同体之思的延异和播撒。因此,敞开这个回应的内里,打通南希与布朗肖之间的通道,并不仅仅是在参照中镜像思考南希的共同体之思,更是共同体之思本身的绽出、沟通、外展和分享。
南希毫不讳言地指出,人的内在性要求构成了共同体的“绊脚石”。把共同体的目标理解为实现人的本质,实际上是将共同体作为某种待完成的作品去进行生产,是对共同体之沟通和分享本质的“粉碎和封锁”[3]13-14。被称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3]21的共同体的思想传统,是必须被清理和被超越的。在布朗肖的理解中,这个清理和超越的必要性,来自于“一个大大超出了毁灭的灾异(désastre)”[1]4的背景,以及将个体设定为纯粹现实的思想倾向。前者使共同体陷入一种难以逃避的、不可能的可能性之中,后者声言个体自身的绝对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拒绝任何不同于自身的他者。正是这种预设,使人们相信,只要全人类的需要平等地得到满足,这个不完满的社会就可以被克服,一种建立在透明人性准则基础上、以实现人的内在性本质为目的的共同体就可以实现。在这个观念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理解为同类的关系,是“同者”与“同者”的关系,是绝对对称并可以无碍通约的关系。真正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它是一个待实现的、处于未来之中的、缺席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性存在与他者的“存在—于—共通”。承认共同体成员的差异性、他异性及其相互沟通与分享,走向并生产这种开放的共同体,是超越孤独和漠然的当然选择。
和南希一样,布朗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同一化、本质化和绝对内在化的共同体,认为这些强加给人们的共同体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决定的自由:它是现状的社会性,或对土地、对血统、甚至对种族的赞颂。”[1]75也正是在这种批评中,布朗肖发现了共同体的“不完满原则”。所谓不完满原则,巴塔耶的解释是:“每一个存在的根基上,有着不充分性的原则……”[1]10存在之所以不充分,是因为它的实现始终依赖于一个他者或他物的存在。如果存在只是单独孤立的存在,它就必然封闭自身,拒绝与其他存在发生联系,也就无从产生一个以交流、沟通、外展和分享为特征的共同体。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源于存在本身的质疑:“每一个存在的实体都毫不懈怠地被其他存在所质疑,甚至一道表达爱意和崇拜的目光也把它自身依附于我,如同怀疑触及了现实。”[1]11在这个意义上,不完满原则实际上是在共同体各独一多样存在的关系中产生的。
为了理解这个不完满原则,有必要提及列维纳斯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对称的交互关系”的思想。在列维纳斯那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都有一个先天的不足,那就是并不真正关注他者。列维纳斯说:“现象学停留在光的世界中,这个自我独居的世界没有作为他人的他者。对于自我来说,他人只是另一个自我,一个他我。认识它的惟一途径是同情,也就是向自身的回归。”[8]104即使是涉及他者的主体间性,也只是“先验自我内部的间性”,是与另一个自我的间性,消弥了他者的异质性,从而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设定为“可以相互转换的项之间的不偏不倚、对等互惠的交换关系”[8]117。这实际上取消了他者本身的独立性和他者之于自我的首要性,因为存在只有在面向他者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身,才能实现自身,才能持存为自身,而他者则不断地质疑和否定自身。存在发现,只有把自身经验为一种先行的外在性,才能在他者面容的注视下避免自我分裂,才能整合自身。所以,按照列维纳斯的理解,真正的主体间性,应该是以他者的绝对异质性和相互外在性为前提的“不对称的交互关系”,应该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本身作为纯粹存在者的关系”[9],是面向他人的面对面的关系[10]。因此,必须把他者本身还原到存在论的意义上,才可以认识存在本身。
布朗肖写道:“无疑,不充分性需要受到质疑,但即使是我独自一人的质疑,也总是对其他人(或他者)的外露——因为只有他者能够凭其位置将我带入游戏。”[1]15言下之意,不完满原则并不必然意味着共同体必须让其成员融入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那会付出成员的内在性和共同体的外在性的双重代价,会导致共同体成为单纯的群体共存,从个体化趋向均一化。不完满原则意味着,共同体只有在“一种复多之存在的共享意志”[1]15中才能实现。它向着他人、向着外在而存在,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向外部和他人的敞开,它所激发的并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同一,而是一种强烈的不对称关系,即分裂和交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应该相信,只有打破个人内在性的绝对边界,含纳排斥它的存在的外在性,才能保持共同体本身的位置。不过,这个位置并非传统的、封闭的共同体所要求的那种同质化的、神圣性、至尊性、同一化的实位,而是一个像“无”[rein]一样的虚位。分享本身及其在共同体中的外展,才是共同体本身的真理。“其中,没有什么要持有的东西,它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它只在无作(按:非功效désœuvrement)之中工作(œuvrer)……不存在一个由限度(finitude)所支配的终点(目的:fin)。”[1]15所以,布朗肖准确地总结了南希共同体之思的两个结论,并进行了最为决然的肯定:“(1)共同体不是一种受到限制的社会形式,它同样不倾向于共通的融合;(2)它不同于一个社会细胞,它不允许自己生产作品且不以任何的生产价值为目的。”[1]14-15
(二)共同体的不可言明
除了南希所发掘的书写、书文等共同体思想之外,布朗肖还在巴塔耶的“否定的共通体”中发展出关于阅读和友谊共同体的思想。布朗肖发现,在巴塔耶那里,友谊(友爱:amitié)是《有罪者》的副标题,属于“至尊的操作”,是从不连续性出发的对连续性的肯定,是“献给没有朋友的求知者的友谊”[11],它通过书写和阅读召唤着共同体。书写,意味着向他者展露自身、绽出本己,意味着“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阅读,则意味着把未知暴露给已知,把有限性外展给外在性;在书写和阅读中,没有任何思想的界限,准确地说,是界限的打开、交流、分享,这是“为一个人自身一直趋向消解的友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友谊,作为通道,作为一种从必要的不连续性出发的连续性的肯定”[1]38。这恰恰是南希和布朗肖要求我们反思和重构的“非功效的共通体”的形式。
然而,对这种形式,如何交流与沟通?使用什么工具来外展和分享?对此,布朗肖发掘了言语和沉默之于共同体之分享的意义。在他看来,言语并不能保证自己被他者所接受,因为言语总是出离自身活动的。它总是在存在“自身之外”的,它并不是存在自身的绝对内在性,所以只能作为“纯粹‘丧失’的礼物”给出自身。它总是意味着打断和纯粹性的丧失,而在它给出自身的同时,它就已经瓦解共同体的持存了。言语本身不可分享、不可言说。那么,沉默呢?就像维特根斯坦的格言“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2]一样,对共同体保持沉默,就可以吗?布朗肖指出,当维特根斯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无法把沉默强加于自己了,他已经开始他的言说了:“一个人归根结底必须为保持沉默而说话。”[1]90因此,沉默也无法作为分享和交流的基础,共同体只能成为不可言明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inavouable)。“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的存在的东西。”[1]90
那要如何面对这个“不可言明”呢?言语和沉默的“非功效”,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卸下言说的责任。就像列维纳斯的自我必须“面对面”地为他者负责一样,我们也必须承担起这个敞开未知自由空间的责任。用布朗肖的话说,就是“让我们对新的关系负有责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劳作(œuvre:作品)和我们所谓的无作(désœuvrement:非功效)之间的,总被威胁,总被渴望的关系”[1]91。这种伦理责任,颇有中国儒家传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和情怀,这也与南希“共在本体论”的伦理结构遥相呼应。
南希曾说:“一旦对‘共通体’(它的形而上学术语、人类神学术语、政治术语、甚至感发的术语、美学术语)的所有哲学用语的解构成为必然,就必须对这个in(非)(即我所谓的‘非—功效’)进行重新思考,于是困难从此而生。我们必须从语言的下层(infra)语义、下层句法和下层概念中重新建构一种语言。这就是这项工作之所以艰难的原因。”[3]229-230这并非南希的自我标榜,因为为这项工作做出努力的,还有格拉内尔(Gerard Granel)、迪骥(Michel Deguy)、巴利巴尔(E. Balibar)和阿甘本。尤其是阿甘本,以其对“无论什么(whatever)”的共同体的思考,在还原如其本然(as such)的存在、存在的独一性与共通本质、共同体的分享与通道、外展与触及界限等思想方面,与南希产生了强烈共鸣。
三、阿甘本:从存在如其本然到共同体的正在来临
如果说,布朗肖是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思想的基础上,对南希的共同体之思作出了延异和播撒,那么,阿甘本对南希的“回应”则立足于“神学传统”,他再次敞开并深化了南希对存在之独一性和共同体之“非功效”的理解,将共同体的解构之思导向一种“正在到来的共通体”。
(一)共同体的独一性
在阿甘本那里,“正在到来的存在就是无论什么的(whatever)存在”[13]107。这里的“无论什么”,在通常的意义上意味着“无所谓是哪一个存在”。但在阿甘本的理解中,它是指“如此存在以致它总是很重要”[13]1。所谓“如此存在”(being as such),就是拒绝一切先在预设或者终极目的的存在,是如其本然、是其所是的存在,是存在自身性(ipseity)的本己(proper)状态。阿甘本用这个“如此存在”概念,既遥遥接续了现象学“悬搁”与“还原”的基本方法,又与南希将存在理解为源初意义上“如其本然”(as such)的共在观念两相应和。只是在南希那里,如其本然的存在是“存在—于—共通”中的存在,是共同生存着的共同显现的独一多样存在,特别突出它的“共/与尺度”。而在阿甘本这里,“无论什么”更多地与独一性相关,但这里的独一性指的不是与某种共通属性无关的独一性,而是从“个体的不可言明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之间的两难选择中解放了出来的独一性[13]1。换句话说,阿甘本的“如此存在”也像南希的“共在/与在”一样,回收了那些足以将存在同一化为各种集体的属性,而真正回归到本己归属。
那么,这种取消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如此存在”,为什么又是独一的?其独一性来自何处呢?对此,阿甘本从圣托马斯关于地狱边缘的思想中获得了启示。圣托马斯认为,那些未经洗礼、死去时除原罪之外并无其他罪愆的孩童,就是地狱边缘的居民,它们所受的惩罚是“永远见不到上帝”,既不像受诅咒者那样感到痛苦,也不像受福者那样获享天堂的愉悦。它们保持着一种对于救赎的中立,在上帝的遗弃和遗忘上帝中无痛苦地持存。这种状态,就是“无论什么/如此存在”的本己状态,准确地说,就是摆脱了同一性和总体化的限制,从与概念相关的各种决断中解放了出来,处于纯粹未定位置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世界本身的秘密,也就是南希所说的“界限”和“门槛”。这里的“如”(as)并不指涉某个先行的本质目的或意指对象,“此”(such)也不服务于给出某个“如”以意义的指示,“此”没有“如”之外的存在,而“如”也没有“此”之外的实质,“如”与“此”两者相互规定、彼此暴露,所呈露的就是如此实存的绝对的“如此品性”。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预设或前置[13]96。
这种基本规定性实际上瓦解或悬置了个体与普遍之间的二律背反。例如,我们往往用普遍意义上的“树”的概念无差别地意指了所有的树,实际上每棵树都是有其独一性的(这棵树、那棵树、一棵树……)。这就意味着我们常常把独一性收编为普遍性的某个成员,以一种共同/共通(common)的种类属性定义了或者说取消了独一性自身。这还仅仅是发生在语言中的一个简单实例。因为作为一个表意系统,语言的存在是一个集合,具有无可质疑的共通性。但语言同时又是以言语的形式存在的,在每一次言语活动又是独一不可复现的。这个悖论,界定了语言存在的边界。为了超越或者回避这种“个体的不可言明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之间的两难绝境,阿甘本将“范例”作为哲学的致思范畴。范例既不完全是个体的又非全然是普遍的,既有个体性又有某种类属的共通特性。这决定了既不能以个体性又无法用共通性来呈露它的存在,而只能把它作为一种独一的存在,如其本然地呈现自身、揭示其独一性。“这些纯粹的独一性只在范例的空无空间中发生交流,它们不与任何共通的属性和任何同一性绑定。这些独一性被剥夺了所有的同一性。这样,它们才能归属自身。”[13]10
“如此存在”每一次都是作为“范例”存在的,它拒绝同一性的暴力收编。那么,它又是如何进入共同体并维持其独一性的呢?这里涉及个体化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曾力主从物质中寻求个体化之所在,邓·司各特主张将个体化设想为作为先在现实的本质或共通形式的附加,斯宾诺莎则力主共通性是非本质的。正是在斯宾诺莎这里,阿甘本获得了启发。斯宾诺莎指出,“所有的身体,在表达神的广延属性上都是共通的”,“共通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构成单一实例的本质”[14]。这实际上拒绝了将共通性视为诸独一性本质的集结的理解。
阿甘本指出,“诸独一性在广延属性中的交流,并没有在本质上统一它们,而是在存在上使之分散”,“一个独一存在的个体化,并不是一个点状的事实,而是一种生成和缓解、占有和挪用,在一切方向上持续的渐变”[13]20。这就打开了独一性与共通性之间的通道,取消了在个体化形式中搜寻先在同一性的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置入一种永恒运动的结构,使它们彼此渗透、交替穿梭、相互指涉。“无论什么/如此存在”只有把自身的独一性生成为某种无同一性的、共通的、绝对外展的独一性,它才能“第一次进入一个无预设、无主体的共同体,进入一个无不可交流之物的共同体”[13]65。
换句话说,“无论什么/如此存在”只有绽出自身,在自身之外的一个独特的空间中,才能持存自己的内在性即独一性。这个空间并非某个确定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确定空间,而是一个通道,一个给出自身的开口,一道门槛,一个无所预设的共同体。这样,它就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外在性、一种纯粹的外展,它就自我生成为某个“外在的事件”,获得一种非本己的绝对无物的经验——从无生成。阿甘本的这个观点,与南希的“间隔”“绽出”和“非实在场域”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共同体的正在来临
与南希一样,阿甘本也对德波尔所描述的“景观社会”进行批评。在他看来,景观主要的还并不是图像或图景,而是语言,“即交流活动,或人类的语言的存在”;景观社会的发展,“不止被导向对生产活动的剥夺,还被导向语言本身、人类的语言和交流天性、以及作为共通者的逻各斯的疏离和异化”[13]80。阿甘本不是要缅怀逻各斯共同体的失落,也不是要重树语言中心的逻各斯主义,而是发掘出景观社会对存在展露为“如此存在”的事实,并予以社会学式的确立。因为景观社会抽离了建立在逻各斯基础之上的可交流性本身,打断了同一性本身的自我连贯性,将存在还原为原子化的极度虚无化的分散状态,人们被从他们所寓居的语言王国中拔根。所以,景观时代是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13]83时代。那么,如何从这种虚无主义中解脱出来?阿甘本赋予“如此存在”以重大使命:“如此存在”的独一性和平地展示它们共通的存在,进入那无所预设的、拒斥一切同一性条件的共同体,无所掩盖地展露自身,把语言本身带给语言。
这个共同体就是“正在到来的共通体”。“正在到来”意味着:第一,我们已经处在共同体的进程之中,而且永远处在存在之中,它就在当下,既不是德里达“尚待来临”的弥赛亚主义,也不是一种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如此存在”的是其所是、如其本然、此时此刻的实存所在。第二,共同体内的个体不再寻求同一化的本质实现,也不被还原为阿甘本的所谓“牲人”(神圣人);他们拒绝神圣及其与污浊的专横区分,共同本质与个体性的区隔及其二元结构也被无效化,他们以其“潜能”永恒地出离自身,在独一性与共同体之间交替穿梭。第三,它祛除了任何先在的预设,打破任何线性的时间观和累积的进步观念,呼吁通过切断与当下现状的联系而让共同体到来。阿甘本的共同体思想,再次敞开并深化了南希对存在之独一性和共同体之“非功效”的理解。在还原如其本然的存在、存在的独一性与共通本质、共同体的分享与通道、外展与触及界限等方面,与南希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他对“如此存在”的共同体的思考,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四、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同体之思的价值
南希“非功效的共通体”、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阿甘本“正在来临的共通体”等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同体之思的不同面相。南希在解构传统共同体理论的同时,在“存在—于—共通”的基点上重构了以分享、沟通、外展、绽出为本质特征的共同体,通过对“居间”和“共通”的强调将传统共同体发展为“非功效的共通体”。布朗肖在肯定南希共同体之思的基础上,赋予共同体以“不完满原则”,挖掘了死亡共同体和情人共同体的哲理内涵,将共同体定性为“不可言明的共通体”。阿甘本则通过对存在的自身性、本己性以及“如其本然”状态的强调,充分敞开了处于个体的不可言明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之间的独一性的内涵,乐观地肯定了共同体“正在来临”的基本特征。他们的共同体之思,既是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思想基础上的自为生长,又是彼此共同体思想的相互应和,建构了后现代语境中共同体的不同面相。
一方面,以南希、布朗肖和阿甘本为代表的当代共同体之思对人类中心主义、同一化、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共在、独一性、外展、分享等概念中蕴藏的他者维度,可以启发中国文论传统中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推动生态美学、生态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南希等人的共同体之思启发我们思考,在西方相对连贯的共同体思想传统之外,作为他者的中国文论传统中的共同体观念以及形形色色、内蕴丰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话语。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观念立场,充分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和他异性,在“共通”之中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分享自身”“走向域外”“向外展露”,向世界文论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共同体文论话语体系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吸收南希等人共同体思想的合理内核,承认作为独一多样存在的各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与汉民族文学在外展、对话、分享和沟通中彼此生成和共同发展的,克服以西方文论话语诠释中国文学的概念化弊端,将中国文论传统中的共同体话语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共同体之思进行有效对接,那么我们将重构出一种“更真实而博大地表述中国文学的现实和历史”的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将重新发现并揭示出“每个独一体之内都藏有秘密的他者性”,进而将建立起更立体、多元、开放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另一方面,南希、布朗肖、阿甘本等共同体之思对于“共在”“独一性”“共通性”等的强调,有助于我们在共通、共在等观念指导下形成符合中国文学现实的批评观念和话语系统。南希的“共在”虽然建立在海德格尔共在概念的基础上,却突破了海德格尔将共在局囿为此在之日常生活方式的限制,将它还原为富含他者维度的更基本的“共/与”状态;此在与此在不仅是共同存在的关系,更是与其他非此在“共/与”存在于世界之中、始终处于对话和分享状态之中的关系。阿甘本的“独一性”概念取消了“个体”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克服了“个体”概念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从而排斥共同体的潜在危险,将多样性规定为与独一性同时存在的人的基本存在论特征。这些思想家们强调通道的打开、永恒的分享以及整体的运作,这本身也是对封闭式结构的打破和对中心化独语体的排除,提供的是一种与社会学批评、政治批评乃至意识形态批评等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时候,虽然并不排斥结构分层、分类处理、标准齐一的操作方式,但在对待具体的文本对象时,应该将它们理解为多样存在的独一性以共在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文化场域之中,主流与非主流、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之间有着极具宽容度的共通性,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批评结果或话语秩序就会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希利斯·米勒以南希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底色的文学批评实践,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正确的示范。
值得补充的是,南希等人的共同体之思仍在不断发展之中。2014年,在得到布朗肖和阿甘本的先后回应之后,南希出版了《异议的共同体》(LaCommunautédéwavouée)一书进行再回应。其中涉及两性关系、身体的本体论、情人共同体、文学和写作的实践、政治空间与共同体的关系等等,解决布朗肖的“不可言明”与他自己的“非功效”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开启了我们对存在的“共在/与在”特征、共同—显现的必要性,以及共同体的“自身之外”和“绽出”等问题的更为全面的关注。但是总体来看,《异议的共同体》仍然没有离开南希以“独一多样存在”为基石的“共在本体论”,仍然可以看作其“存在—于—共通”哲学理念的具体演绎和“非功效的共通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里不作详细展开。
可以看到,“非功效”“不可言明”“正在来临”甚至后来的“异议”等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内核还是解构。只是这里的解构,不应该被理解为拆散、打破、摧毁、否定、消解、批判等消极的含义,而应该回到德里达最初赋予这个词的肯定性的原初内涵那里去。德里达曾一再申说:“解构不是一种以否定性、甚至本质上以批评……为标志的过程或计划。解构首先是对原始的‘是’的再确认”[15],“我常强调解构不是‘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6]16。也就是说,解构最初的意味在于建构,只是这种建构并不致力于恢复传统形而上学中心结构、本原或本质的中心地位,而是致力于解构之后的重组和重建,它意味的是肯定、承诺、建设、责任和承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南希、布朗肖和阿甘本的共同体之思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但却为敞开共同体的未来之思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