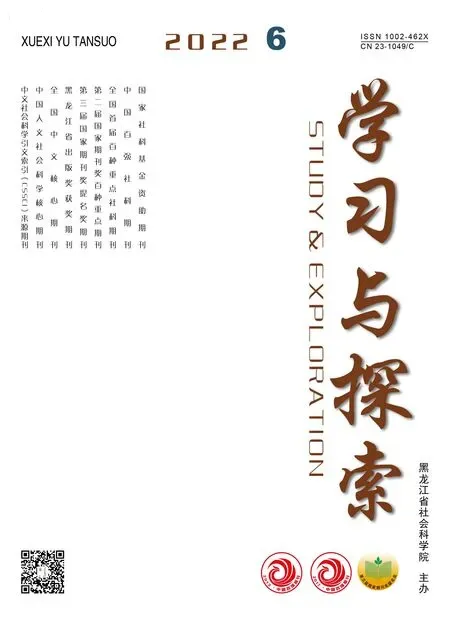免疫的哲学话语:德里达的自身免疫困境与健康共同体
夏可君,李 杰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2.西华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自身免疫( l’auto-immunisation/auto-immunity)或自体免疫,按其字面含义理解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自身的问题与免疫的问题。一方面,自身性的问题即自我、自身性(Selbstheit、ipseity)、自身的同一性、自身的成己(ereignen)、自我的保护等,这是指来自于自我又回到自我的自身感发状态过程中产生的系列问题。不过,问题还在于,自我也可能处于越是要回到自我便越是自我摧毁的悖论之中。比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自恋行为,或者整个西方具有悲剧感的自我认知行为等。另一方面,就免疫的医学定义而言,免疫反应是一种人体天生的自我保护机制。遭受外界侵犯时,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自发启动,免疫细胞会聚集在某一局部而释放出一种霉干扰素的蛋白,阻止病毒的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免疫来自于自然机体对自身抗体发生的作用和排斥外来物的触发作用。病毒入侵引发的免疫反应可能形成免疫系统的敏感性,但也可能导致自然机体的一再反应,乃至于过度反应,甚至反过来攻击机体自身,引发所谓的免疫疾病。
通过上述的对比,可以看出自身与免疫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即两者都在要求自身保护的同时导致了自身的破坏,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产生了自我威胁,由此形成了生命本身的悖论(vital paradox)。深入思考会发现不仅仅是生命本身,甚至是思考本身、哲学的逻辑本身,也都出现了内在的悖论:一方面,对于自身性的哲学化思考包含着西方哲学特有的自身认知的悖论,无论是那喀索斯自恋神话——看到自己却失去自身而成为水仙花这个他者,还是希腊悲剧智慧——俄狄浦斯越是自我认识越是自我摧毁而刺瞎双眼,都体现出海德格尔所言的“成己—去己”(er-eignen/ent-eignen)的相关性。在这个悖论中,越是要形成自身性的成己事件,便越是要在去除自我,越是面对着去己是否还可以重回自身的难题。另一方面,就免疫反应而言,本来起着自身保护作用的免疫反应,因为过度反应或者过度自身保护,而导致了自身机体的破坏。自然机体的保护机制或“自然的技术”,在激发自身保护的免疫反应时却导致机体的自身破坏。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可怕的自身毒化(horror autotoxicus)。“疫苗技术”带来的后天保护也可能导致免疫逃逸,从而削弱机体的天然免疫保护性;同时,个体的免疫保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借助于群体的共同免疫。因此,免疫技术所体现的技术功能,也与此前自身认知的悖论处境有着相通之处。
在成己与去己之间,在免疫与保护之间,并没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而是在“成己”中“去己”,“同时”运作这个不可化约的“张力”,但又不能摧毁自我,还要接纳他者。既要去己,也要成己;既要成己,也要去己;既不能没有了自我,也不能不去除自我。这个悖论的张力,就是德里达所言的“双重约束”(doublebind):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互为条件,体现出一种“绝境”(aporia)的逻辑,既要成为自身和保护自身,但同时也要去除自身和抹去自身,这不也是摧毁(destruction)自身与解构(deconstruction)自身?我们由此看到了这种双重约束与免疫反应有着相通之处。
既要自身免疫,也要接触他者。所谓接触他者,也就是向他者敞开,对他者友善,其间有爱意与接触的必要性,自身免疫的问题也随之在与他者的接触中,变得复杂而富有张力。而一旦指向最为复杂的健康共同体的层面,就更具有了一般的普遍性,从而导致一般免疫学的出现。
一、走向一般免疫学的必要性
走向一般免疫学是德里达要把自身性与免疫性两者结合起来思考的根源。自然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躯体反应与哲学认知与逻辑学表达的自身认知无疑是同构的。自身免疫,曾经作为生理化的自我意识,现在则体现为免疫反应的具体身体感知方式或是自身的认知悖论。这种感知方式,在传统是通过神话、悲剧与辩证法,乃至于事件哲学体现出来,现在则通过病理传染与病毒传播事件体现出来。那么,以免疫学范式来再次思考自身性,与之前的思考方式到底有什么差别与重要性呢?如果传统已经很好地思考了自身性的悖论,为何还需要用免疫学来思考?
这是因为人性成了“免疫的人性”(Homo immunologicus)。只有从免疫学来思考人性,现代性的危机才可以被更准确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具有相关性的三重危机:人性的生命存活危机、人性的无保护状态,以及哲学自身的非现实性危机。
哲学因为丧失了现实性,而显得几乎无用。“9·11”这一巨大的恐怖主义事件,迫使哲学家们来到了现实的旋风之中,开始思考历史的脱节。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又使缺乏现实性的哲学变得更为手足无措。面对疫情,哲学的思考变得更为急迫,并开始转向,从之前的语言哲学与技术化的科学哲学转向与生物性相关的一般免疫学。其实,无论是德里达在1990年代思考信仰与知识的关系,还是斯洛特戴克在思考“资本的内在化”过程危机,都已经触及当代危机。而随着新冠病毒的出现使这个危机更鲜明地凸显出来,一般免疫学变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起来。
这种紧迫感与现代的人性丧失了保护性内在相关。如同诗人里尔克在1920年代所彻底认识的,如同海德格尔在1946年的《诗人何为》中所作的分析[1],人性已经进入了深渊,丧失了安全感。所谓的安全保护,既是生理学上,也是心灵上的,而现代性的外在化与技术加速,形成了斯洛特戴克在《资本的内在化》中所言的“水晶宫式”的球体学[2],也形成了一种针对里尔克“世界内在空间”的另一种内在化——不过是把全球化与人性置于一种透明的“外在”保护状态。这种水晶宫的球体本来已经成为虚幻的泡沫,但随着病毒的全球化,这种外在化的保护方式失效了,人性处于彻底的无保护状态。这种呼吁产生一种新的思考范式,一种保护人性的免疫学。
斯洛特戴克接续之前对于免疫学保护的思考,在本次疫情期间再次强调,要形成一种全球免疫(Global immunitary)的方式和一种新的共同体免疫(co-immunism),要思考建立一种理性的一般免疫学(immunitary reason)的可能性[3]。
我们有必要一一展开德里达对于自身免疫的丰富思考,考察他思想的基本逻辑,以及他如何在时代的根本困境中寻求可能的出路,以打开哲学的未来。这个未来,是隐含在德里达思想中尚待展开的:尽管德里达从1960年代在《柏拉图的药》中就开始了对毒药的双重性、替罪羊的保护机制以及过敏反应的免疫性进行思考,但直到《信仰与知识》(Foietsavoir,1996)、“9·11”事件之后不久的对话《自身免疫:真实的和象征的自杀》,以及在其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无赖》(Voyous,2003)中,德里达才深入展开对自身免疫问题的研究。
我们之所以认为一般免疫学是德里达思想遗产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有待于被展开的珍贵财富,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这个思想还处于尝试性的准备阶段,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主题化写作文本,还有待于细化;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病毒全球化肆虐的危机状态之中,免疫问题无疑成为最为核心也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自身免疫的各种悖论
第一,自身免疫来自于自我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自我伤害。任何的自我保护冲动,无论是生物性的还是意识活动的,都可能在自我保护的同时导致自我伤害,或者说,并没有纯粹的自身性。德里达曾经在专论南希的著作《论触感》中,专门分析了自身感发(auto-affection)与它异感发(hetero-affection)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任何自身感发的回归或者激发,其实都受到它异感发的刺激与浸染。在反思9·11恐怖事件与自身免疫的关系时,德里达曾经思考了三种美国式政治化的自身免疫方式,其中“第一种症候:攻击方式”[4],就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遭受到袭击,袭击不是来自外部,反而是来自内部,攻击者没有从外部携带任何武器,或者这些武器都可以直接从本土获得。这个攻击方式就与自身免疫的方式相关。
人体免疫系统和病毒本有着微妙的平衡,但一旦周围生态环境被破坏,病毒就会通过中间宿主被带到人类社会。尽管病毒会激活人体的免疫保护机制,但人体本身不足以面对这个自然的巨大力量,因为自然本身也在施行某种自我保护。对于自然的自身免疫,这是德里达尚未思考的,为此,南希在《一种太人性的病毒》中提出病毒过于人性化的观点。新冠病毒本身体现的恰好就是“自然的神圣性”。病毒不断在人性中复制、存活、击倒人类,寄生在人身,似乎不可能离开。这种寄生性,并非德里达早期所思考的外在技术的假肢寄生性,也不是技术嫁接的传染,而是来自于自然的自身免疫反应。这种自然生命的自身保护,德里达在其晚期开始有所关注,提出“生命问题处于存在问题、在场与在者问题的中心”[5]的问题,展开对“还没有学会生活”等话题的思考。德里达的哲学,尤其是对免疫的思考,基本上还是以“死亡”及其“余存”为主的。
第二,自身免疫的运作还体现为这样的悖论:越是自我保护,反而越是导致自我损害。德里达在分析美国式免疫反应的“第二种症候:过度反应或强制遗忘”时指出,尽管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包括核弹在内的各种高科技武器的威胁不再来自某个确定的国家,而是来自一些匿名的、无法预见也无法计算的力量,这导致了创伤的时间化效应。由于恐怖的源头飘忽不定,创伤逐渐也成为众多创伤中的一个,慢慢被遗忘、被压抑、被驱逐。但实际上这个绝对的“创伤”已经存在于某一个地方了,而其威胁与幻影一直在扩展。
病毒的萦绕性特征,与此相似,也具有某种幽灵式的特点。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病毒的发生学机制。作为介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病毒,似乎具有了德里达所说的幽灵的特点——既非生命,也非非生命,一直存在着,比人类更为早先。但似乎并没有对于人性有着直接作用。当代记忆的生理学基本上认为人类的记忆离不开大脑中“朊病毒”的作用,那么人类确实要通过重建与病毒的关系来思考自身的根本存在方式了。
第三,德里达还提出,机器化或者电子技术的机器在保护与重复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解体与无能。德里达作为“外在技术改变人性”观点的最早提出者,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记号纹码学的方式,发现了外在铭记技术对于人性感知与历史演化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在斯蒂格勒那里被扩展为“器官学”与“药物学”,得到了彻底的发挥。但是,不同于斯蒂格勒对于技术转录的肯定,德里达是要回到技术与灵魂的可能关系上去展开思考。德里达认为,电子技术已经成为同一欲望的反拜物教,成为恶的机器和根本恶的机器。他指出,电子—技术科学机器的发展形成了新时代的金刚不坏的免疫信仰:“不断制造的解体,剥夺所有权,迁徙,拔根,取消习语和剥夺(在所有的领域,特别是在性领域——崇拜男性生殖器)中。仇恨的反应通过分解而把这种运动与其自身对立起来。这种反应就这样在同时免疫和金刚不坏的运动中自我避免损伤。对机器的反应和生命本身一样是机械的(或因此说是下意识的)。”[6]60、75显然,这是一种新的“机器泛灵论”,它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非人化或后人类化。
第四,德里达还分析了生命本身的自动性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性之间的悖论。如同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和回到寂静状态的自我毁灭冲动,生命本身具有某种自动性。其实,可以认为,整个精神分析都来自于某种生命的防疫机制。无论是无意识的梦想,还是艺术家的创作升华,都是对来自于生命本身的原创创伤记忆及其强制重复的反应。
精神分析中的这些带有病态或者迷狂的反应,也具有某种自身免疫的特点,即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在自我伤害。自恋情节就是如此。从弗洛伊德对于《哀伤与忧郁》的卓越分析,到德勒兹对于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分析,都是在强调,无论针对世界还是自我的哀怨,其实都是在自我保护的同时在自我伤害。而如何避免强制重复的自我保护与自我舔舐伤口之间的悖论,依然是精神分析的亮点与内在困惑。如同德勒兹要“反—俄狄浦斯”,利奥塔要让“力比多”的能量开始漂移,德里达要用“生死”和“死生”的同时性解构死本能的威胁,都是面对生命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与过度的危险。德里达在自己大量关于哀悼纪念的文本中展开的工作(比如2003年最后的著作之一《每一次,唯一的,都是世界的终结》)中,还提出一种被允许的“好的自恋”,并认为“自恋”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方式。
与病毒相关的是,人性对于病毒的恐惧乃至于创伤记忆,是否会导致一种对于病毒的恶性崇拜,即一种病态的恐惧所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自身免疫的力量不足以面对自身的危机时,会出现自我破坏来自我强化的虚假幻象,尤其是以权力的管制来代替疾病的治理,似乎权力本身才是在自然与技术之外最为有力的保护方式,乃至于出现某种病态的管理,把病毒当做敌人,甚至当做致命的敌人来看待。这些现象需要深入思考。
第五,德里达在《无赖》一书中,除了讨论政治的免疫危机之外,还深入分析了理性的拯救、恢复以及自身疾病的治疗要求。这是他再次回到了自己思想的开始,面对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的最终要求,面对胡塞尔对于理性与西方精神危机的思考,希望分离精神的仇恨而形成战胜自然主义的理性精神。
在德里达看来,这种胡塞尔的理性精神和欧洲的几何学精神,确实具有一种哲学的严格性,但理性要自我保护,要拯救自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困境:即理性之为可计算性的要求与生命本身的不可计算性的矛盾。在可以计算与不可计算性之间,思想是可以调和还是不可调和的呢?德里达认为这个和解就处于自身免疫的困境之中。这也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面对的挑战,面对技术“集置”的不可回避和一切都要被程序化的危险,思想试图从更为自然的自然化方式,以泰然处之的态度,让自然和“宽忍”的伦理来转化技术的危险。这是德里达已经注意到的方向,但因为海德格尔的《黑皮本》最近几年才出版,德里达对于这个泰然处之与宽忍的伦理,只是在生前少数几个文本中有所触及,并没有深入展开。德里达只是提及了相关的原初伦理态度:“谨慎,尊重,克制(Verhaltenheit),羞愧(Scheu,shame),泰然处之,等等。”德里达尚未看到的海德格尔《黑皮本》中的细微思考:节省、保护、守护、爱护、珍惜、允让、宽让等等的生命保护伦理,这是思想未来要展开的工作。
这还涉及试图根除根本恶的危险,即必须肯定威胁的风险与机遇风险的并存,注意这是两次,不是一次,“担保”根本恶也是保存好的行为的条件。德里达认为,那些以为可以彻底根除根本恶的想法也是危险的。这就涉及德里达所指出的美国式自身免疫的“第三种症候:恶的循环”。德里达认为,对那些受害者阵营而言,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有理有据的报复或真正意义上的反恐,两个阵营的立场完全一样,都是要保卫自己,都是与恐怖主义战斗,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永无宁日,两者都是要去根除那根本恶,彻底净化世界,却导致了更大的恐怖主义。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就触及了与自身免疫相关的伦理态度,面对病毒的自身免疫,是去继续强化自己的免疫力,还是去容忍病毒,与之共在?或者是学会以理性的方式,耐心、反复地与病毒周旋,寻找与其共在的“游击方式”?自身免疫不仅仅是加强自身、保护自身,而是要阅读病毒,勇敢担负起面对病毒的伦理学责任,以健康共同体的视野来对待病毒,不因对新冠病毒对健康年轻人的危害较小而致年老、体弱者于不顾。对病毒的正义态度和积极的防御措施本身就是与病毒协调。
第六,是基因剪辑的生命保护所导致的偏靶危险。这种危险一旦被传递开来,其后果难以预估。尽管德里达试图区分开治疗性克隆技术与生殖性克隆,但克隆过程中排斥反应一直都会起作用,如同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南希,免疫排斥反应一直都在。如何与另一颗心共在,一直是人类生命技术的难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共同体的问题,也是生命余存的经验。
2022年5月的研究显示,Omicron 感染有效增强了疫苗引发的免疫力,在接种疫苗的个体中引发了广泛的交叉变异保护。未来Omicron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结束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但与之同时,疫苗技术对于生命免疫加强保护的同时,疫苗本身的副作用或者危险并没有被充分实验与评估,而且面对大量“免疫逃逸”的风险,技术保护是否一直有其自身的限度?或者说,技术免疫是否要如干细胞技术所提供的启发,要与自然免疫结合起来?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尚未展开的维度。如何回到生命本身,这是德里达之后哲学的根本工作,随着本次疫情的爆发,生命与自然、生命与技术、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再次展开思考。
三、共同体的免疫
自身免疫必然走向免疫共同体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体的免疫保护,还依赖于群体免疫,仅仅依靠个体并不足够抵抗病毒的传播,而一旦依赖于群体,就会有人要做出牺牲。这也是德里达反复强调的悖论:让一部分活,另一部分就得死,面对生死根本就没有评估的标准可言。就此而言,许多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面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在防控措施失效的基础上,刺激南希提出了“太人性化的病毒”的观点,发现了新冠病毒自然化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新冠病毒毒株的不断生成中虽然强化了其传染性,但也降低了病毒的致命性和对身体的危害性。这是疫情失控导致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给中国的疫情防控情势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随着病毒自我保护机制的强化,诸如毒性的下降等,也会为我们的防疫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如果群体免疫是最终的方法,是结合了自然免疫与疫苗技术这双重保护后形成的共同体免疫方式,但如何保护这两种人:既没有自然免疫力——比如老年人,也没有疫苗注射的人群——比如,有基础病的人不适合注射,依靠什么来保护这些人群?这就进入了政治干预的权力领域,需要权力来保护这两类人群,但一旦从权力的保护出发,势必会伤害那些已经获得了免疫保护的人群,并且导致次生灾难。这不又回到了解构的绝境?为什么走向群体免疫的最大保护,却要以牺牲一部分为代价和条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权和其他权利比较起来,在哲学上更有本质性的地位,生命权是人的第一重权利,如果生命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其他的一切权利都会成为没有本质依据的空中楼阁。德里达在思考自身免疫时,还是过于关注技术的力量了。从生命技术来看,一旦Omicron出现,这来自于病毒自身提供的所谓“自然免疫”,反而比疫苗更为保护生命,可能是终结病毒的病毒、弱化了的病毒,这不就是自然反转的辩证法吗?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自然与技术合作的辩证法,而德里达对此的思考并不充分。
德里达对于免疫共同体的思考,主要还是集中于思考死亡的维度。
生者的生命只有注重生命之外的东西才绝对有价值,对于生者的超越,概括来说就是打开死者空间,人们把死者与自动(规范讲是“男性生殖器”),与技术、机器、假器、潜在性等联系在一起,一言以蔽之,与自我—免疫和自我牺牲的各种补充维度联系在一起,死亡的这种冲动默默地作用于所有共同体、所有自动—共同体,并且实际上在其重复性、遗产和幽灵传统中原原本本地构建这种共同体。作为共同自我免疫性的共同体:没有不保持自身自我免疫性的共同体,一种摧毁自我保护机制的自我解构原则,这是基于某种不可见的和幽灵的死后的生命。这种在生命中坚持自我—免疫的共同体,更多地向着他物开放,而不是面向自身:他者,将来,死亡,自由,他者的到来或他者的爱,所有救世主降临之外的幽灵化的降临性的时—空。这就是宗教可能性之所在,是在生命价值及其绝对“尊严”和神学机器、“制造诸神的机器”之间的宗教关联(谨慎的、恭敬的、畏惧的、节制的、冷静的)之所在[6]69-70。
对于德里达思想的双重“再解构”在于:一方面,自身免疫的生命中有着一种自然化的生命保护机制。德里达并没有充分思考这个自然的保护性,他的自身性还是过于人性化的自我了,而不是自然自身,不是自然化的生命。实际上,起着根本免疫作用的恰恰是这种自然化的免疫力。尽管会因为过度反应而自我摧毁,但人性必须再次发现自身的自然性,使之有着更为具有可塑性与可再生性的技术,比如干细胞技术。另一方面,自身免疫的反应中,确实有着不可避免的自我破坏机制,但是在免疫的共同体行为中,恰好需要接纳他者,尽管其中有着接触传染与隔离距离的悖论,但彼此的接纳,不仅强化了各自的保护性,还打开一个内在的保护性。
因此,自身免疫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也是关涉宗教和神学的危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德里达最初在意大利讨论宗教的会议上提交《信仰与知识》这一长篇文本的原因。德里达在其中直接讨论了何谓免疫:
“immune”(immunis),就是免除负担、服务、赋税、义务(munus,是communauté中commun的词根)。这种免除随后被转到制宪或国际法律(议会或外交豁免)。但是,这种免除也属于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和教会法。寺院(这里指的是古时巴黎由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豁免权,也是某些人可能在其中得到庇护的豁免(伏尔泰因为这种“教堂豁免”是“蔑视法律”和“教会野心”的“不公正的例证”,因而对之气愤不已)。……Immunite这个词尤其在生物学领域中发挥了其权力。免疫反应通过制造抵抗外来“抗原”来保护身体不受伤害。我们知道,对于活的有机体来说,根本在于通过破坏其免疫防护而自我保护。由于病理学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求助于免疫—抑制的积极功效。这种功效在于限制排斥机制,以便促进移植器官的融合。我们赞同这种扩展,并且将讨论一种自我—免疫的普遍逻辑。在我们看来,这种逻辑对于今天思考信仰和知识及宗教和科学的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对把其当作两种普遍的根源来思考是必不可少的[6]58-59。
德里达还指出,免疫一直与宗教有着内在的深度关联:
拯救,被救,自救。第一个问题的借口:人们能否把有关宗教的话语和有关拯救的话语,也就是关于健康、圣徒、神圣、安全、不受损害、免疫的话语(在很多语言中都有它们的对应词,如sacer,sanctus,heilig,holy 等)区分开来?而拯救是否必然是在恶、过错或原罪之前或之后的拯救呢?现在:恶——今天明显的罪恶——在哪里[6]4?
对于我们而言,思想要摆脱抽象思考的最好方式,就是面对病毒这个来自于自然的神圣之物。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宗教的本质将要在它要成为的不受损害的经验中的不受损害。金刚不坏(不受损害,indemn),是否这就是宗教事情本身呢?”德里达还在随后的脚注中说明了何谓“金刚不坏”,提出Indemnis或者绝对免疫保护在于“不受损害或没有损失”。这种无害化,是指回报和恢复的过程有时是祭礼的,重建不变的纯洁性、健康和平安的完整性,以及一种未被损伤的纯洁属性。德里达总结“金刚不坏”这个词的概括意义:在任何亵渎、伤害、违犯、损伤之前的纯粹、未损、圣物、圣人。德里达也联系了海德格尔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将其翻译为“heilig”(神圣、平安、健康、未被触动)。他主要是把“indemne”“indemnit锓indemnisation”和“immune”“immunit锓immunization”,尤其是和“auto-immunité”联系起来思考,从而走向了最为一般的免疫学。因此,一般的免疫学与理性的免疫学,其实已经是带有神学思考的免疫学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绝不仅仅是哲学、理性的危机,也是技术本身、生命本身,即世界本身与宗教本身的危机。
德里达因此也深入思考了走向“金刚不坏”之彻底免疫的幻象,来自于宗教的神圣与圣洁,平安健康、不受损害、不被触动与传染,都是对于绝对免疫的期待。而这种神圣的区分,越是保持区分的神圣,即保持所谓宗教信仰的金刚不坏的幻象,就越容易导致虚假的满足,也越是可能导致自我的郁闷甚至自杀。
那么,有打开内在性区分的可能性吗?中国文化的道教文化中内丹与外丹的生命保护与健康安福的方式是否会有所启发?一方面,道教的外丹术有着德里达所解构的药物的双重性,本来是要让长生不死的丹药,却导致很多吃药者中毒死亡(越是期待长生,越是导致加速死亡)。另一方面,中国宋元道教的内丹化,则是继续汉代的吐纳与导引修炼。这种走向内丹的自我保护,是否具有某种自身免疫的启发性?这种依靠意念引导呼吸的《周易参同契》的调节方式,是否具有某种自身免疫的彻底性?它并没有触及外物,但又打开了某种神圣的宇宙通感通道;它并不损害身体,也不损害外物,而是彻底打开内在的内在性,如同里尔克要通过诗意想象打开的“世界内在空间”。在一个越来越水晶宫式与元宇宙虚拟的透明时代,这是否是另一种真正的生命保护与免疫方式?由此呼吸调节形成的共同体免疫模式,将会是什么样的理性免疫?这是未来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的问题。
对我们当下而言,病毒总是以多种形式向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深度的嵌入,形成了“三体”的纠缠。这里所谓的“三体”,一是自我免疫机制的身体,二是病毒作为总体的魔幻化的“第一自然体”,三则是作为人类整体的健康共同体。在德里达笔下,身体、病毒和健康共同体之间似乎只有通过神学的“金刚不坏”才能达成某种和谐和平衡,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德里达强调生命技术的重要性,似乎仅仅将健康共同体的追求视为一种自然化的政治。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新形态的人类实践智慧,是有能力、有责任扛起抗疫使命的治理共同体,旨在捍卫人的基础性权利,即生命健康权。德里达的一般免疫学在当今的语境下,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特殊免疫学,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也就有了对病毒不同的态度,也生成了“非均等非同质的共通体”[7]。面对太人性化的病毒,是让其在自己身上自然演化、自我保护,还是将其视为一种警醒机制,以时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保卫人民健康,也会生成身体的内在免疫学和共同体的外在免疫学。在当今时代,好像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些国家面对失控的疫情只能放任自流,而中国的健康共同体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防御机制。这绝非德里达的自然化的政治,而是政治的自然化,勇敢扛起抗疫的政治责任,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打造外在免疫学的铜墙铁壁,更胜过宗教化的、理想化的“金刚不坏”之身。
———记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研究所副教授侯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