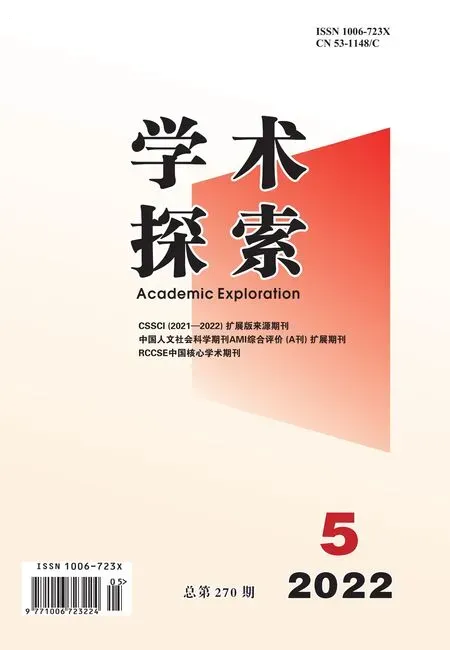西南边地形象的想象建构
——以罗常培、费孝通、曾昭抡的考察记为中心的讨论
杨绍军,张婷婷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出于巩固边疆、建设西南的需要,国民政府和众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先后对西南地区开展了多种边疆、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调查活动。(1)据不完全统计,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先后有1931年凉山彝族曲木藏尧受国民政府委派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宣化夷族”,搜集彝族生活、风俗、文化和社会等资料,1933年12月出版《西南夷族考察记》;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陶云逵、技术员赵至诚和勇士衡到云南河口、麻栗坡、金平和腾冲、泸水等地对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和社会情形考察;1934年5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雷马峨边考察团,对大小凉山地区进行以生物地质为主的调查,形成《四川省雷马峨边调查记》等;1935年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考察,形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1938年,任乃强曾经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等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进行调查,撰写《泸定导游》等;1939年大夏大学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到贵州的安顺、定番和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地进行民族调查;1939年,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的费孝通和同事在云南禄丰、路南(今云南石林)和玉溪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形成《云南三村》出版;1942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邢公畹等到云南新平、元江等地进行语言、宗教、巫术和地理环境的调查;1943年,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林耀华参加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形成《凉山夷家》等。具体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在实地调查活动中,考察者除提交考察报告外,还产生了一批生动活泼的考察记或旅行记,如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滇康道上》《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等,“但是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写作与写作目的的不同使得这些表现西南边区各族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旅行记与传统的游记有着很大的差别”。[1]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写作者的学者身份确定的,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他们写出了反映西南边地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事象,对传统游记文学进行了新的开拓和发掘,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重要存在,也使得西南边地的形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视野。
在传统中华帝国版图中,作为边陲的西南始终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化外之邦”,正如白之瀚在《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里提到时说的:“在昔滇以僻远,中土人士之至者绝罕。故自来言滇事者,非臆说武断,即影附之离。阮元、檀萃之伦,牵于职事,用志多纷。杨慎谪居虽久,偏擅惟词章。皆于滇事鲜所发明。”[2](P101)也就是说,在中心/边缘的视角下,古代文人学者对西南边地的描写带有“异域”视见,某些叙述甚至呈现动物化、色情化的虚构与想象。但是由于抗战前后不断有学者深入西南边地进行实地调查,在科学、理性的观照下,西南边地“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2](P101)本文拟以罗常培、费孝通和曾昭抡等学者的考察记和旅行记为中心,对他们在作品里对西南边地形象的想象建构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语言学家罗常培(1899~1958)就是对西南边地进行书写的重要作者,他在1941年5月到8月,与梅贻琦、郑天挺等由昆明到重庆、泸州、成都等地,归来创作《蜀道难》,于1944年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1946年在上海再版;1942年1月和1943年2月,他两次到云南大理等地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讲学,创作《苍洱之间》,于1947年由南京独立出版社出版。1996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将《蜀道难》与《苍洱之间》合编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学生周定一评价认为:“在《蜀道难》和《苍洱之间》,也不乏形象生动、情趣盎然的大段描写,比读《徐霞客游记》,有趣得多。”[3]周定一对老师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是描写生动活泼的文学作品。
首先,作品对西南边地的真实再现。中国古代文人对西南边地的描写,大多叙述边地蛮夷擅长放蛊、男女两性关系混乱、存在致人死亡的瘴气……,甚至到1930年代,艾芜在写到西南边民时还说:
女的短衣齐腹,长裙及踝,通作黑色。说话时,露出漆黑的牙齿,但面容却是美好的。头部用黑绸缠着,堆高至尺许,仿佛顶了一只小桶似的。我一看见,便禁不住联想起故乡城隍庙里的地方鬼来了……如果把这一夜的经历,作为到了幽冥世界一样,也许更要恰当些吧。[4]
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还是将边地的少数民族视作“他者”和“异类”,将其与“地方鬼”相提并论,将边民生存的环境与“幽冥世界”进行比拟,这与传统文人对西南边地的叙述没有本质的区别,依然充满着“妖异”的“视见”。对此,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苍洱之间》的序里对罗常培的写作进行评述时说,无论是唐宋以来古文家的短篇游记,还是陆游的《入蜀记》和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失诸支离破碎,或质胜于文”“失诸空疏无物,或文胜于质”,能够做到文质彬彬的叙述实在难求。但是在罗常培的考察记里,对西南边地的描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这不同之中显而易见可以看出几分进步”。[5](P99)也就是说,《苍洱之间》对自然山水和世间诸象的描绘,既不同于柳宗元、欧阳修笔下的自然,也不同于袁枚、徐霞客叙写的山水,而是在描摹山水的同时,再现了真实的社会,做到在描摹山水中展示历史文化,在历史文化的发掘中观照现实。因此,在《从滇池到洱海》中,他写到1942年2月2日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经楚雄、云南驿,2月4日到达大理,在对沿途见闻进行描写的同时,对大理的历史地理、“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进行了描述,还对与大理有关的蒙氏南诏、段氏大理等历史进行叙说,内容丰富、文字优美。如在写到洱海边上的才村时,他说:
才村在县城东八里的海边上,村多杨姓。在明清两代的功名很发达,村口的题名坊便是一个好证据。民族文化书院的校舍是新建筑的楼房,原系杜文秀水师营故址。院内有亭可以看崇圣寺的三塔倒影,可惜时较早,风太大,我们并没看见一点影儿。[5](P107)
作者对才村的历史进行溯源,说明在明清时期这里文化较为发达,证据就是立在村口的题名坊;才村的教育较为昌盛,这里有新建的民族文化书院;环境优美,可以看到苍山脚下的崇圣寺。可以说,这些都是罗常培在大理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时的亲见亲闻亲感。在作品里,他结合地方史志和实地考证,将西南边地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出来,不再人云亦云,也不带任何偏见,而是客观真实地将西南边地呈现出来,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因而具有多重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次,作品对联大学术活动的叙说。1940年5月,罗常培一行到重庆,目的是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谈西南联大校务;“到叙永视察分校,到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且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个学生的论文”;[5](P8)此行他们顺路到四川乐山、峨眉、成都等地参观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大学。在记录此次旅程见闻的《蜀道难》中,由“从昆明到重庆”“叙永的一周间”“闷热的板栗坳”“观光川大”“走上了艰难的蜀道”“尝尝成都跑警报的滋味”“赶上了‘疲劳的轰炸’”等17章组成,对旅途的艰难险峻、人情世态和自然景观作了优美细腻的描述。但是,这次旅途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作品着墨最多的地方,是到暂住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的3位研究生(2)1939年5月,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此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昆明。同年6月,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研究生招生,导师分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科目有中国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人类学5部,名额10人。经过两次考试,招收的研究生有中国文学部逯钦立、阴法鲁,语言学部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史学部有汪篯、阎文儒、杨志玖、王明,哲学部有任继愈。1940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研究生随导师到李庄学习。具体参见杨绍军:《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第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论文进行审定。因此,他在作品里写道:
二日上午,约刘君念和来,评订他所作的史记汉书文选旧音辑证……因此我认为刘君的研究结果还是成功的,只批示十点意见让他依旧修改。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语语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于研究藏汉系的语言颇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
四日上午,约任继愈来评订他所作的理学探源……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之下,两年的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究源竞委的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5](P23~28)
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依托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的师资和图书资料,让部分研究生随导师到李庄学习,但在四川李庄,这些研究生并没有因为远离西南联大校区而放松对学业的追求,而是在导师的严格指导下,“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积极进行自由、独立的探索,也为他们的学术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后这些研究生都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如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李孝定等。可以说,《蜀道难》细致地记述了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活动,成为了珍贵而生动的教学见证。对此,陈远认为:“我最喜欢其中的《蜀道难》,罗先生以大量丰盈的细节,让我们看到缓缓流动的西南联大历史,而其中关于学人之间的交往,又是研究现代学术史的绝佳一手材料。”[5](封底)
二
作为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R.David.Arkush)在《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中译本名为《费孝通传》)中认为:“他是一位很感人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善他所同情的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苦难生活,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改革农村经济的建议。”[6](P1)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杂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1942年5月,日寇经缅甸侵入中国,占领怒江以西地区,云南畹町、陇川、龙陵、腾冲等地沦陷。国民政府在怒江东岸驻防的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获悉在缅甸境内和江左各县有大量的华侨和青年学生无处安置,于同年8月在大理成立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培训流亡华侨和青年学生支持中国军队作战。1943年2月,宋希濂邀请西南联大的曾昭抡、罗常培、潘光旦、孙福熙、费孝通为滇西干部训练团讲学。在此期间,联大的5位教授游览了滇西佛教名山——鸡足山,费孝通写下了长文《鸡足朝山记》,由“洱海船底的黄昏”“‘入山迷路’”“金顶香火”“灵鹫花底”“舍身前的一餐”“长命鸡”“桃源小劫”7章构成,详细描述了游览大理洱海、鸡足山的见闻,被认为“费孝通的游记《鸡足朝山记》是与罗莘田同游苍洱山水的产物,然而带有更多的主体情思,似乎更有艺术感染力”。[7]
首先,作品对云南山水的描摹。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书写,或表现为山水诗,或表现为游记,前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王维《过香积寺》、苏轼《西湖绝句》等;后者如柳宗元《小石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袁枚《西湖游记》等,他们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大多纯粹写景或是寄景抒情,以从容的心态游刃于自然山水之中。但在1940年代费孝通的云南山水描摹中,人们看不到古代文人轻松的游观,而是充满了对自然的景仰和向往:
三年前有一位前辈好几次要我去大理,他说他在海边盖了一所房子,不妨叫作“文化旅店”。凡有读书人从此经过,一定可以留宿三宵,对饮两杯。而且据说他还有好几匹马——夕阳西下,苍山的白雪衬着五色的彩霞;芳草满堤,蹄声嘚嘚;沙鸥傍飞,悠然入胜——我已经做了好几回这样的美梦。[8](P19)
作为社会学家,丰富的田野实践为他提供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为他从严谨的学术思考中审视周边世界提供了别样的艺术经验。从语言表达上来说,《鸡足朝山记》明确印证了评论者认为“似乎更有艺术感染力”的说法,如他写到的“白雪衬着五色的彩霞”“芳草满堤”“沙鸥傍飞”,不仅再现了苍山洱海间的美丽景致,而且表现出湖光山色的意境,堪称优美的现代散文。如果说这段文字是作者对苍山洱海美景进行“臆想”的话,那么对鸡足山的写实则同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如在写到鸡足山上的金顶时:“一忽醒来,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寒风没有了踪迹,红日当窗,白雪春梅,但觉融融可爱,再也找不着昨夜那样冷酷的私威。”[8](P27)在经历寒夜登顶的劳累疲乏和迷途恐慌后,作者面对鸡足山的自然美景,内心油然生发激情般的想象,觉得金顶“红日当窗,白雪春梅”,周边的世界“融融可爱”。可以说,这种对自然山水的艺术表现,与传统文人明显不同,在他的笔下,自然拥有赤子般的情怀,也拥有诗意性的品格,作者将生命的色彩与自然的美景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学者书写自然山水的生动例证,也是对西南边地的真实再现。
其次,作品对世事人生的体悟。在《鸡足朝山记》中,费孝通将宗教、民俗和历史、文化融合起来,对世事人生作出了深刻的体悟。英国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曾说过:“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事实上,反过来看……它们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9](P58)确实,在特定空间的文学描述中,空间景观作为传达某种意图的象征或是作为作品中的构成物,参与了文学作品的想象建构,同时也表现、标识着作者对特定空间的理解认知。在作品里,作为空间景观的佛教名山鸡足山,成为作者表达所见所闻所感的特定空间,与鸡足山有关的宗教、民俗和历史、文化成为表述的内容,也承载着对世事人生的洞见。因此,他在作品里说:
佛教圣地的鸡山有的是和尚,可是会过了肯和我们会面的之后,我却很安心地做个凡夫俗子了。人总是人,不论他穿着什么式样的衣服,头发是曲的,还是直的,甚至剃光的。世界也总是这样的世界,不论在几千尺高山上,在多少寺院名胜所拥托的深处,或是在霓虹灯照耀的市街。我可以回家了,幻想只是幻想。[8](P32~33)
由于童年与佛教的因缘,作者在“鸡山圣地,灵鹫花底”突然生发出想做和尚的念头,但是,在与大庙的江苏老乡老和尚攀谈后,得知老和尚以抗战的名义开矿牟利,使作者不得不感叹,“不论在几千尺高山上,在多少寺院名胜所拥托的深处,或是在霓虹灯照耀的市街”,都充满了世间常见的“庸俗”和“势利”,他毅然放弃突发的出家幻想。如果说作者的感悟到此为止,显然作者的灵魂和读者的期待都难以得到提升和满足,这样的写作也和古代隐士的凌空高蹈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在“舍身前的一餐”中,他又写道:
美和真似乎不是孪生的,现实多少带着一些丑相,于是人创造了神话。神话是美的传说,并不一定是真的历史。我追慕希腊,因为它是个充满着神话的民族,我虽则也喜欢英国……我们中国呢,也许是太老了……连仅存的一些孟姜女寻夫,大禹治水等不太荒诞的故事也都历史化了。礼失求于野,除了边地,我们哪里还有动人的神话?[8](P33)
在这段关于神话与历史的叙述中,费孝通将希腊神话、英国的实用主义和中国的历史进行揭示,“三个形象跃然纸上,而费孝通在此处显露出平时不怎么流露出来的对神话的热爱。也正是因其对神话的热爱,在鸡足山上,他对自身此前的社会科学生涯展开了反思”。[10]这种反思的见解,就是在特定的宗教空间里,他对历史与神话进行理性强调:“神话是美的传说,并不一定是真的历史。”但是,这种理性思考的真实目的,是他想唤醒失去的“礼”,这个“礼”并非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繁复的宗教仪式,而是再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他发出“除了边地,我们哪里还有动人的神话”的追问,在这样意义上,他对西南边地或者说“华夏边缘”进行了“正名”,边地不再是瘴气、巫蛊、野人和蛮俗的世界,而是充满民族文化的“野性”,唯有继承这种“野性”,才有生命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范卫东认为费孝通的“这种觉悟还有更高一层的文化象征,即这些学者在精神上挣脱了书斋的专业拘囿,他们的思考因而具有一种生命元气浑厚的现实质感,首先使他们自己在思考中成为一个对现代社会敏锐感应的‘人’”。[11](P174~175)
此外,费孝通还于1942年11月在滇池边的呈贡创作了《西山在滇池东岸》,将神话传说与西山、滇池的美景融合在一起,对山水的形态和生命的形态进行了阐释,语言朴实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三
1984年1月,费孝通在回忆他的同事和朋友曾昭抡(1899~1967)时说:“曾公对化学的爱好和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把他看成是个封锁在小天地里的专家,那就贬低了曾公的胸襟了……从一九四二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西部鸡足山旅行后,我开始注意到他兴趣之广和修养之博。”[12]不难看出,费孝通对曾昭抡的评价切合实情,也非常中肯,可谓知人善论。在抗战期间,作为中国现代化学的奠基者——曾昭抡对西南边地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这些考察不仅是对祖国的山河进行认识与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传播现代知识与文化的过程。在1939年3月11日至25日,他就乘坐汽车,沿着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考察记《缅边日记》,对沿途的自然环境、风景名胜、珍稀植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作了实录。《缅边日记》1941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1年6月,他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团长,组织了西南联大政治、社会、地质和生物等系的10名学生,(3)除团长曾昭抡外,其他的学生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柯化龙,地质地理气象系的黎国彬、马杏垣,化学系的李士谔、戴广茂、陈泽汉,算学系的裘立权,物理系的周光地,生物系的钟品仁,政治学系的康晋侯等。于7月2日从昆明出发,经云南禄劝、西康会理到达西昌,对大凉山夷区的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等进行实地考察。正是根据这次考察,他完成《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对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到西昌,再从西昌经昭觉、美姑等地到大凉山的过程进行了叙述。其中的《滇康道上》于1943年10月,在桂林文友书店出版;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于1945年4月在重庆求真社出版,1947年8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再版,“《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采用的是传统游记体裁的方式进行书写,全书共7编、112节……每节的字数各不相同,少的有二三百字,多的有六七千字,形式灵活,文字优美,内容或为社会生活的描述,或为文化事象的分析,或为旅途风景的叙写,都是对大凉山夷区的地理环境、交通情形、历史源流、组织制度和现实社会等进行的描述,向读者充分展示大凉山夷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当地社会的历史状况与现实生活图景”。[13]
首先,作品对西南边地民族的描写。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时,对“民族”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充满想象的人类学范畴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4](P5)在他的这个定义中,安德森对民族的“客观特征”——诸如语言、地域、经济、共同心理等——问题作了聪明的回避,为其划定了主观主义的界域: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虚构”或任意“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依靠集体记忆无法实现,必须被叙述出来。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传》到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不同的写作者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西南边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了叙述,其间充满了误读和虚构,甚至捏造。到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到西南边地,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较为客观准确的叙述,如曾昭抡在《缅边日记》中就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滇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在写到“‘摆夷’‘崩龙’和‘山头’”时说:
在芒市、遮放、畹町的“夷族”,分为“崩龙”“摆夷”“山头”“栗粟”四大族。在滇东一代常看见的猡猡,却自保山以西,就很少看见。这四族底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族;比方在“山头”的统名底下,实在有许多支的“山头”。[15](P74)
在曾昭抡的叙述中,存在于滇缅边境的少数民族不再被视为一个需要进行教化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充满奇风异俗的“不忠实的神奇故事”而被记载,而是成为读者了解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和习俗的重要文献。此外,作者还对有关滇缅边境的土司制度、土司衙门、民族服饰、民族家庭和婚恋习俗等进行了科学性的考察和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贡献。同时,在《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中,他对被西方人称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4)最早说该地区是“独立倮倮”的是1877年进入越西海棠等地进行考察和探险的英国人巴伯(Baber),他曾在1882年和1883年出版的《在华西的旅行和研究》和《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概况》中首次提到凉山夷人为“独立倮倮”。其后,在戴维斯(H.R. Davies)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条》(剑桥大学出版社1909年版)、哈里·弗兰克(Harry. Franck)的《华南漫游记》(伦敦菲希尔欧文有限公司1926年版)和亨利·考迪(Henrie Cordier)、布鲁豪尔(A.L. Broomhall)、吕真达(A.F. Legendre)等的著作中都提到。所谓的“独立”,指的是由于大凉山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治理,其独特性在于,西方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庇佑下曾肆无忌惮地出入新疆、蒙古、青海、四川、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唯独对西南腹地的大凉山“望洋兴叹”“裹足不前”,零星的几次尝试也无疾而终。区域的民族——夷族的历史、地理、景观、矿产、习俗、语言等进行客观、真实、详尽的描述,在调查和写作中,他是抱着“了解之同情”进入大凉山腹地的,因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区别于其他考察记之处:将旅途生活化,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流露其深深的人文关怀”。[16](P9)
其次,作品对西南边地的地理实录。根据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边地既是实际的地理区域,也是抽象的文化空间,“是一个由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17](P4)基于这种认识,西南边地具体指向的是西南地区与邻国相毗连的边疆,同时还包括滇川、滇黔、滇康等交界地域。在曾昭抡的考察记中,除《缅边日记》是搭乘汽车进行考察外,《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都以步行为主。因此,他的考察记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地理景观的实录,也在考察记里形塑了这些地理景观。在《缅边日记》中,他写到从昆明出发,经安宁、禄丰、楚雄、镇南、凤仪、漾濞、永平、保山、龙陵、芒市、遮放,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畹町;作品对距离昆明的里程、海拔的高度和自然物产等,都有准确的记载。如在“由功果桥到保山”中,他对沿途的植物进行描写:
在沿着澜沧江行的一段路中最后一小段,路旁开始看见滇西的一种特殊的植物。那种植物,名叫“蜂桐”,是一种相当高大的树。我们这次去,正巧碰着它开花的时候。花是很大朵的大红色花,一棵树上结许多朵;可是树上连一片叶子也没有看见。据说这树的木头自行腐烂成洞以后,蜜蜂喜欢跑到里面去做蜂窠,所以叫做“蜂桐”。[15](P74)
由于作者是自然科学家,因此《缅边日记》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如在对珍稀植物“蜂桐”的介绍中,他对树木的高度、花的颜色和外形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树木的具体用途作了说明。可以说,他的叙述是对“蜂桐”的如实记录,没有虚构和想象,让人如亲眼所见,文字朴实,优美流畅,使得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科学性,还有较高的艺术性,将科学与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在《滇康道上》,作者对旅行的路径和地理环境进行了近乎偏执的描述。作品里屡次出现的“约行两里”“陡向下趋”“由此前行”“势颇平坦”“左旋山边行”“沿途所见地质”等重复、单调的字眼,俨然有幅定位精准的地图摆在读者面前,如果按照他的描述,重走这条线路依然不会有较大的差错。此外,作品还对具体位置的地理景观进行了描述,如在“鲁车渡”中:
金沙江上游,乃是目前云南、西康两省的天然界限。在这一段,两岸陡峭异常。逼窄陡峭的河谷里,夏天怒流着那条橘黄色的,水面满作漩涡的狂水。虽则纬度并不十分靠近南边,海拔也有相当地高,就是因为河谷逼窄,终年无风的关系,在此金江两岸,逼近水面的处所,一年四节,天气炎热,和次热带一般。[18](P67)
曾昭抡这里写到的“鲁车渡”,位于云南和西康两省间,北岸是西康省,南岸是云南省,由于是典型的干热河谷地区,这里气候炎热,盛产热带水果。因此,他对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和地质地貌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让读者领略到边地的风情和真实面貌。在写到金沙江水时,他用了“怒”和“狂”来形容,一改路径叙述的沉闷,显得活泼而生动。可以说,这些真实、可信的叙述都是对地理景观的叙述,也是在场的、鲜活的场景描写。
再次,作品对西南地区边政的思考。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们在政治上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日益丰富。因此,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不仅普通民众希望他们承担起拯存救亡的重任,他们也希望以“学术报国”或“文化抗战”的方式对民族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边地,面对日益突出的边疆问题,投身边政研究成为川、滇一带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这其中,对于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边政思想的曾昭抡来说,1939年3月对滇缅公路的实地考察,其实有着明显的现实目的:
滇缅公路成功以后,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来因为滇缅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尤其很少踏进。我们平常听见关于那地方的,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实的神奇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感缺少。[15](P1)
正因为如此,他想用自己的实地调查,以“亲身的经历”破除外人对边地的误解,以彰显缅边之真相。两年后,他对大凉山夷区进行考察,当时西南边地大兴田野调查之风,众多社会考察团体和个人共同的指向——就是地理、生活环境相对偏僻、封闭的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的目的亦如康区刊物《康导月刊》所说:
我们藉此在边疆工作的机会,就所见、所闻、所行,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法律的,生活的,习俗的,气候的,地理的,生物的,矿藏的实际情况、现象,在我们理解的范围内,尽量介绍,提供素材,以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引起国人开发的兴趣,纠正过去一般人对边疆的唯蛮论和唯冷论。[19]
在这样的意义上,曾昭抡对滇缅边境和大凉山夷区的考察及其著述,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严正关切。此前,他就曾多次表示,希望他们的考察对边政事务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有所帮助。至于他的作品,则希望被更多的读者阅读,以引人入胜的内容引起广大民众的兴趣,最终引起最高行政当局的重视。因此,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有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以及对凉山“夷务”的处置办法。如在“宁属宝贵的资源”里提出:“宁属各县,因地近边陲,迄今一般人对之,仍属隔阂,每以为此处乃是蛮荒地带,没有多大开发的价值与可能性,其实大大不然。”[18](P29)在“凉山倮夷家庭与社会制度”里,对于凉山夷区普遍存在的“打冤家”提出建议:“将来如能开发凉山对于夷民的教育,似应针对这方面,多下工夫,教以将胸襟放宽,勿轻结怨,而要勇于解怨。”[18](P117)可以说,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情怀,使他不仅促进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而且致力于“帮助国家巩固边陲,捍御外侮”。
四
西南边地作为中华帝国的边缘,长期以来远离中原地区和中央政权,如果以中原地区作为本位,西南边地则处于政治、文化和地理的边缘,因此在“华夏”的叙述体系里,西南边地是对应的“蛮夷”区域,到近现代以前,对西南边地的书写始终带有“动物化、妖魔化和色情化的书写”。[20](P13~17)但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南渡,以罗常培、费孝通、曾昭抡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流亡西南,在西南边地的生活、考察和旅途中的见闻,将此前被外来者“蛮夷化”或者认为“无名”的边地,实现由“想象的真实”到“事实的真实”的转变,于是西南边地“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在对西南边地进行书写的过程中,他们赋予了西南边地以新的形象建构,这就是将西南边地客观地表现出来,而不是延续古代文人的以讹传讹、道听途说,对西南边地形象进行真实的叙说和再现。
在一定程度上,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对西南边地的考察和实录,再现了西南边地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也印证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民族志、旅游读物……的边界其实很模糊,看似客观公正的民族志写作借鉴文学作品的叙述手法,或者在虚构性文本中强调叙述者亲历现场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20](P38)他们关于西南边地的考察记写作,一方面促成了战时西南考察记和旅行记的兴起,如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等的出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描述,感知各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现实,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呈现了客观真实的边地场景,如罗常培的《苍洱之间》是作者两次到云南大理讲学和进行语言学调查的记录,书中除《五华楼》一节为书评外,其余都是实地考察的见闻。这些作者在战乱频仍时进行田野考察,在避难边地中传播文化,在颠沛流离中寄情山水,对西南边地的自然风物进行描摹,不仅再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而且有着深沉的历史意识。同时,罗常培、费孝通、曾昭抡等对西南边地自然山水、民俗风情、现实问题的展示,以及对边地形象的建构,再现了流亡、战争和理想、使命的生存图景,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中,饱含着他们的家国意识和学术报国的情怀,他们对西南边地形象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展现,催生了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