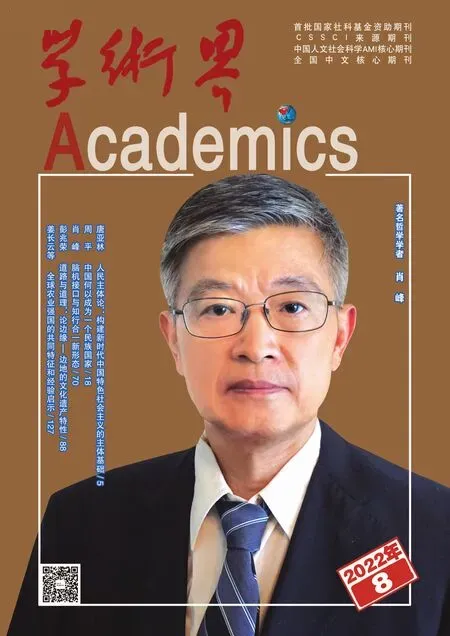论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及学术史意义〔*〕
王 杰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1920年,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在投身成立公学社、承办上海中国公学、组织讲学社之余,以半个月的时间撰写了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尔后直至逝世前,又先后撰著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多部史学论著。这些史学论著中多次提及年谱编撰的重要性,如:“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1〕“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2〕“年谱在人的专史中,位置极为重要”;〔3〕“倘使做成了年谱,以后做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4〕在此期间,梁启超还撰著了《陶渊明》《先秦学术年表》《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与年谱、传记相关的论著,尤其是《辛稼轩先生年谱》成为梁启超倾注大量心血的绝笔之作。梁启超晚年对年谱这一文体形式的偏爱体现了他的史学观导向,他关于年谱编撰的意义及方法的言论,也成为百年来编撰作家年谱时所遵循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是如何做到搜罗材料之宏博、爬梳史实之丰富、考辨真伪之精严?如何通过一人之史管窥时代之变,使年谱兼具史料贡献与研究价值?如何通过对谱主材料的编撰复原文坛风貌,呈现更多丰富的文学史细节?这是编撰作家年谱时亟待思考的问题。学界常引述梁启超年谱观的个别言辞,却未进行系统探讨,或存在误读。系统梳理梁启超的年谱观,进而探讨其学术史意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这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理论体系
自宋代吕大防编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栎编撰《杜工部年谱》开始,年谱作为记述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宋代的年谱谱主多为政治家、学者或其他知名人士,年谱的关注焦点多为谱主的生平事迹及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功业成就、学术之路、品德行踪等方面。到了年谱编撰极为流行的明清两代,达到“附庸蔚为大国”的盛况。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始将“年谱”作为人的专史的五种类别(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之一,认为年谱不同于列传叙述人物事迹,可不遵循时间先后的自由排列,而是“叙述一生事迹,完全依照发生前后,一年一年的写下去,不可有丝毫改动”。〔5〕年谱的编撰动机是为了便于更好地阅读、理解诗文,呈现与诗文相关的人物生平、时事背景、社会关系。梁启超首创性地阐述了年谱的种类、年谱的体系、年谱的格式、做年谱的益处等一系列概念,并分门别类地针对年谱编撰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具体方法论,构建了一整套关于文学家、学者年谱编撰的理论体系。
其一,年谱的种类。梁启超认为,年谱从编撰者角度可分为自传和他传,自传年谱能省却考据功夫,他传年谱后出的常胜过先出的;从谱主的现有材料基础来看,可分为创作的和改作的,创作的年谱须构筑完整的年谱框架,改作者仅须对已有年谱进行增订删改;从年谱与文集的关系切入,可分为附见的和独立的,列传与附见的年谱须简切,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从谱主事迹材料真伪的视角,则包括平叙和考订两种方式,平叙年谱的工作在于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考订的年谱则要从各处钩稽谱主事迹,订讹现有记载的故意污蔑或观察错误。
其二,年谱的记载体例及具体做法。梁启超认为,年谱的编撰格式通常包括直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的最简单的平叙体,以及对所述谱主事迹的具体情形、意义进一步记述的稍严格的纲目体;记载时事要根据谱主的发展趋向详简得当,交代谱主的时代背景;记载谱主生活中所交往的人,既要聚焦谱主的家族,又要注意师友生徒亲故;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视年谱体裁独立成书则载重要文章,而附见文集的年谱则不载文章的标准灵活掌握;考证方面则为谱主距离编撰者年代愈远,考证工夫愈加重要,但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构即可。
梁启超在论述构建自己的年谱理论体系时,还通过引入冯辰《李恕谷年谱》、李贽《王阳明年谱》、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王文诰《苏东坡年谱》,顾栋高、蔡上翔分别编的《王荆公年谱》等,以及梁启超自己编撰的《陶渊明年谱》《朱舜水年谱》为例,剖析各自年谱的优点、不足及改进的方向,尤其是针对编撰文学家年谱应如何处理文学家与时势的关系,概述道:“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6〕也即是说在编撰文学家年谱的过程中,要尤为重视文学家与时代的关系互动,不能把文学家作为孤立于时代重大事件的局外人,重要的时事变迁无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打下一定的烙印,这些重大的事件理应纳入文学家的年谱编撰体系中。这种根据文学家与时势浓淡的关系来决定记述时事详略的年谱编撰方式,可以说是梁启超的首创,这与梁启超本人作为文人气息很浓的学者,同时兼政治家的多重身份密不可分。
在构建年谱编撰理论体系时,梁启超无疑最为关注文学家年谱的编撰特色。在处理如何辑录文学家的作品、如何做到详略得当等方面的问题时,梁启超列举了编撰文学家年谱时可供参考的范例:“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谱后”。〔7〕而在择取文学家的作品时,要充分地考虑到文学家作品体裁的丰富性,强调“替文学家做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品……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不能详录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若录多了,就变成集子,不是年谱的体裁了”。〔8〕显然,梁启超对于年谱编撰的章法、体例极为讲究,文学家年谱编撰的求真求全与梁启超的史学理念是一以贯之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是梁启超所致力于追求的史学研究目的。〔9〕尽管后人常批评梁启超的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从梁启超的年谱观来看,其对年谱编撰作为一种典型的历史研究所具备的通过钩沉法、正误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等方法来保证历史事实之真实是深信不疑的,只是由于梁启超学术兴趣极为广泛、著书立说的速度极快,造成了其史学著作的疏漏之处,我们不能由此否定梁启超年谱观中对爬梳材料之丰富、考辨材料之真伪的高度重视。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驰骋在多个学术领域内,创作了洋洒千万言的大作,“尤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10〕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认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1〕有研究者对此曾敏锐地指出:“梁氏对新史学所应发挥的‘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社会作用的体认,也是对其所从事的传记写作的内容与宗旨的基本定位”。〔12〕
于梁启超而言,这种以史学承担社会教化功用的理念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提出,其在尔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地强化、扩展、延伸,创作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并开创了中国现代新体评传体式。年谱与传记相比较而言,虽同属于人的专史的类别,但年谱比传记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一目了然的特色。谱主的选择以及与谱主相关的历史事件、文人交游、文学作品等一系列材料虽有“求得真事实”的旗号,但为达到“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也就必不可少地打上当下语境与编撰者自身诉求的烙印,这种内在的旨归与传记作品并无二致。此种意义上来看,梁启超晚年所构建的年谱理论体系仍然受到了其早年所倡导的“史界革命”的光辉烛照,并且“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作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13〕这种理念既表现在包括年谱理论体系在内的史学著作本身的研究方式,又体现在梁启超年谱观的构建中。
二、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书法”与白话写作方式
梁启超逝世后,其及门弟子谢国桢在谈到其文章风格时指出:“按先生少年之文,以豪迈胜;及夫壮年治学,以系统条理见长,故恒亦有疏忽之愆;及夫晚年,则由提要钩玄,一变而为精湛纤密之作,而文则情韵不匮,真迫东汉”。〔14〕年谱编撰作为梁启超晚年史学论著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其倡导通过“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保证年谱提要钩玄的史料价值,那么对于年谱的“书法”问题,如何做到叙述的翔实,如何使得客观平叙的年谱兼具“情韵不匮”?梁启超显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尝试。
在当下大力推进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史料建设的进程中,年谱编撰以其资料的丰富性、史料的可靠性备受推崇,但一些学者在论述年谱这种研究范式的长处之时,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年谱研究”是一种“述而不作”的体例,采用的是“春秋笔法”。〔15〕这显然是对梁启超年谱观述学“书法”的一种误读。梁启超认为年谱体裁的好处在于“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16〕虽然只是“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但“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别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梁启超进一步表明观点:“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17〕在论述年谱编撰的书写章法时,梁启超只是强调相对客观地呈现,并非年谱家完全“失语”,可以通过材料的择取“引而不评”,或者加以适当的评述。这种倡导显然不是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梁启超年谱观中“述而不作”的“春秋笔法”,当然也不同于梁启超早年提倡“史界革命”时师法欧西的新体评传方式。
梁启超在1902年著述《新史学》时曾谈到“书法”问题,他显然并不赞同中国传统史著的“春秋笔法”,认为“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龈龈于总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推崇西方那些“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的《英雄传》《罗马史》的笔法。〔18〕梁启超在后来创作《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等传记作品时很明显地摒弃了传统的纪传体式,而效仿西式评传体。这种自主添加议论成分的“专传”写作方式体现在梁启超创作于20世纪头十年的大量传记作品中。正如胡全章所评述的,“作为一个有强烈政治情怀的学问家和文学家,梁启超的传记文写作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其传记作品的创作旨趣可总括为‘明朝局’、‘振民气’、‘厉国耻’、‘新吾民’。这一创作主旨,鲜明地体现在梁启超对传主的选择上”。〔19〕而晚年的梁启超专心治史,编撰文学家年谱之时,无论是其史学论著,抑或是谱主的选择上,都更多地倾向于由学术风气或自我境况的感慨而著书立说,已与青年时期的壮志凌云有所不同,但那种文笔的锐气并未完全泯灭。
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同样谈到了“史家的文章技术”,认为文采方面要兼顾“简洁”与“飞动”,即使是史著文章,“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让读者百读不厌,功力在于笔法的飞动。〔20〕尔后1927年8月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在探讨年谱观的理论体系时,认为年谱的编撰同样有一定的规则和章法,“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随后进一步表明年谱与传不同,“即使作家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21〕从梁启超对史学述学的“书法”技巧来看,其对文章情感的诉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地减弱,但文章所应具备的通顺畅达等要求却并未因年谱的史料性之客观排列而降低。
在表述谱主的个人行迹和著述时,如何在年谱编撰体例上做到既“详尽细致”又“选精择粹”?如何征引遴选谱主与同时代作家批评家关系的材料?如何呈现重大政治、历史、文化事件尤其是文学事件对谱主的影响?这些正是年谱家编撰年谱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知人论世”的概念时认为:“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22〕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论述时代之“人”时,不能妄下结论,要充分铺排时代背景的历史史实。这与青年时期的梁启超所倡导的以“悲壮淋漓之笔”全面评述传主时代之历史,显然已有所不同。同样在1922年,由胡适编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问世了。胡适在编撰年谱时,其年谱观与梁启超有一定的类似处,认为“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23〕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阐释“谱牒学”时认为:“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随后褒奖了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其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24〕
然而,梁启超的年谱观与胡适也不尽相同,关于年谱编排时如何处理批评家的评述文章,以及年谱家是否融入评述话语的问题,梁启超就曾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为例,认为“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25〕而胡适本人在年谱编撰的“书法”上则改变了以往年谱“单记行事”和专事谀颂的“正则”,注重发掘学者谱主的学术思想,批评学者思想上的不足之处,同时引述了关于谱主的种种议论并加以评述,表明自己的观点。〔26〕如此看来,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书法”与胡适相比,看似相对较为保守,但梁启超并非对年谱编撰中的年谱家观点的流露完全持反对意见,而是认为年谱家“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可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27〕也即是说,梁启超与胡适相比,更讲究年谱编撰时须遵循严格的章法,其所推崇的是述学“书法”的规范化,但在构建年谱观的理论体系时也选择性地汲取了胡适的观点。
与此同时,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形式倡导白话写作方式。梁启超早在世纪之交提倡“文界革命”时,就认为德富苏峰的著作“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28〕尔后,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9〕这段话中,梁启超对自己报章文字的特点及其影响作了简要的概括与说明,即他所倡导的“新文体”。仅就“文界革命”所追求的新文体而言,内容及所指并非单一的,既可以理解为针对桐城派古文的报章体,又可以像梁启超本人那样理解为“新文学”,即“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梁启超在其史学著作中,也将这种新语体贯通始终,报人徐凌霄曾评述梁启超:“世人所认为真正之梁文,大抵皆以《新民丛报》所作为标准也。其用语体文于学术之演讲,及整理旧艺之著作,亦出于自然。以新语体自有显白条理之特长。此系实用问题,贵得其便”。〔30〕
于梁启超而言,这种运用新语体、白话写作的方式已融于其写作方式之中,因此即便是在编撰年谱之时,面对的是古人之生平材料、古人之文章评论,梁启超在辑录叙述之时,语言表述上力倡“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31〕对于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作附录,使得读者阅读明白,以了解谱主的真性情,力求平实中有震撼、有感动。正如陈平原所认为的,借助“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互补、政论文章与历史著述的钩连,发现史家风范与文人习气并非势不两立,梁启超所积极实践的“史界革命”,其“论学文字”仍然是“极宜着意修饰”。〔32〕
三、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4年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已对年谱编撰进行了一些思考,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1926年9月—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续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通过讲义的形式探讨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及写作方法,一部分刊登在《清华周刊》第26卷上,其余部分后来才编辑成书。而在1923—1928年期间,梁启超也撰写了有关陶渊明、朱舜水、辛稼轩的传记或年谱。可以说,梁启超在构建年谱观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编撰实践,不断地调整、补充,这样就使得其年谱观更具实践操作性。这种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一在于创制了年谱的新体例。在梁启超之前,学术界虽不断地有年谱问世,却从未有系统的年谱理论,只能在一些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有关年谱观的只言片语,梁启超通过溯源式分析了年谱自诞生以来在各个时期的状况,并对学界知名度较高的几十种年谱的优缺点进行了系统评述,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年谱的种类、体例、格式、益处等层面的理论体系,对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又结合实例进行了剖析式解读,向读者表明不同年谱种类所适合的谱主情形,尤其对文学家年谱的编撰进行了详尽介绍。当中所提到的“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述的翔实”也成为后来年谱编撰时所借鉴的方法。
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二在于由文学家年谱沟通了文学史研究。年谱不仅是对谱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文学整体风貌的窗口,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与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整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复原当时文坛复杂的网络结构。梁启超在《陶渊明》自序中指出:“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征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吾夙有志于是。所从鹜者众。病未能也。”〔33〕由此看来,梁启超所编撰的年谱与撰写的人物传记在具体写作手法上虽有所不同,但同属于其晚年的史学成果,学术思想的根基是一致的。无论编撰年谱,抑或写作人物传记,梁启超在学术意义上所致力的最终是文学史研究。梁启超在总结年谱编撰经验时指出:“替一人做年谱,先须细查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人”。〔34〕于作家而言,不同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时代潮流的濡染、重大文学事件的波及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流淌在其笔端的文字也被打上了一定的烙印。这种以一人之史管窥一时代之变迁,进而切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在当下大力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适用。这种由作家年谱入手的研究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进程。
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三在于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并为20世纪以来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如果说前半生的梁启超以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名声大噪,那么后半生的梁启超则因其文学及学术成就而在文史学界流芳百世。自梁启超编撰《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辛稼轩先生年谱》,胡适之编撰《章实斋先生年谱》年谱之后,其他的作家、学者年谱也在不断地编撰中,如李俨编撰的《梅文鼎年谱》《李善兰年谱》、朱自清编撰的《李贺年谱》、吴晗编撰的《胡应麟年谱》、刘盼遂编撰的《段玉裁先生年谱》等。尔后,鲁迅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种的消息”;〔35〕王瑶提出:“由年谱入手,钩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36〕夏承焘认为:“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37〕
乃至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现代文学学科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史料辑轶整理队伍,如丁景唐、马良春、朱金顺、陈子善、刘增杰、陈梦熊、解志熙、张桂兴等在史料建设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他们群策群力,使得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老舍、冰心、胡风、冯雪峰、丁玲、废名、朱自清、沈从文、穆旦、冯至等作家都有了自己的年谱。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程光炜多次呼吁“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38〕林建法主编的“《东吴学术》年谱丛书”、武新军策划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39〕陆续推出了莫言、铁凝、苏童、阿来、阎连科、范小青、余华、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的文学年谱著作,柳青、路遥、陈忠实、高晓声等作家的文学年谱也已问世。而纵观这些作家年谱,能惊奇地发现当中的编撰理论皆来自于百年前梁启超所构建的年谱观。作家年谱编撰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材料梳理本身,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却又带着生命温度与积存的纵向个人文学史,拖着其长长的历史背影与文坛编年史相结合,或许能够呈现文学史的另一副面貌”。〔40〕
综合分析来看,通过对梁启超发表的有关年谱方面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结合梁启超的学术发展脉络得知,梁启超的年谱观在理论上既承继了其早年倡导“史界革命”发挥新史学的社会功用,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理念,编撰“书法”上与新体传记文同具通顺畅达的特征,语言上则以白话见长,并把这种年谱观付诸编撰实践。这种年谱观承续的正是梁启超“史界革命”“文界革命”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并汲取了胡适等人的观点,开创性地构建了年谱的理论体系。梁启超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清末民初的年谱编撰风气,也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年谱的编撰是一项极其辛苦却难免出现错漏的工作,然而这种工作对于浩大的史料工程建设,对于文学史研究无疑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注释:
〔1〕〔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84、393-394页。
〔2〕〔3〕〔4〕〔5〕〔6〕〔7〕〔8〕〔9〕〔20〕〔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刘梦溪主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7、397、449、397、434-435、438、438-439、363-368、386、334-335页。
〔10〕〔13〕夏晓虹:《梁启超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4页。
〔11〕〔18〕梁启超:《新史学》,刘梦溪主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5、440-441页。
〔12〕〔19〕胡全章:《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14〕谢国桢:《〈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原载1929年3月5日天津《益世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426页。
〔15〕闫海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有益尝试——论〈东吴学术〉“年谱研究”的意义》,《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16〕〔17〕〔21〕〔25〕〔27〕〔31〕〔3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刘梦溪主编、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7、440-441、448-449、441、441、449、432页。
〔23〕〔26〕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32、24-58页。
〔28〕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86页。
〔30〕彬彬(徐凌霄):《梁启超》,原载1929年1月26-28日《时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32〕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33〕梁启超:《陶渊明·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07页。
〔35〕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6〕王瑶:《郁达夫生平的发展线索——温儒敏著〈郁达夫年谱〉序》,《王瑶文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37〕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
〔38〕程光炜:《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
〔39〕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文艺研究》2020年第3期。
〔40〕王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学术启示及编撰规范问题——基于当代作家年谱著作(二〇一六-二〇一八)的考察》,《东吴学术》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