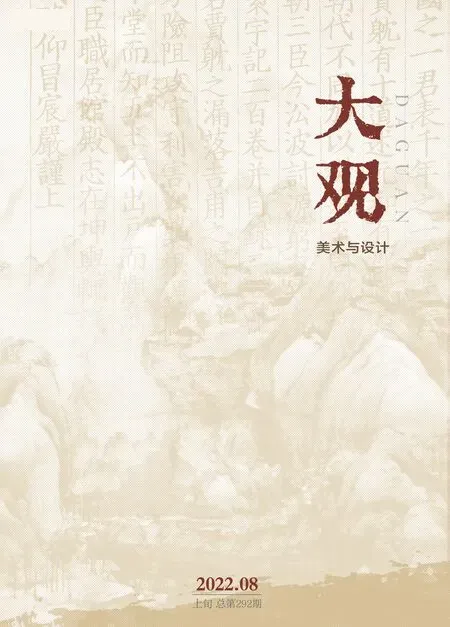传统工笔人物画的人物表情刻画研究
◇王琳昭
一、表情是传统工笔人物画的语言要素
(一)表情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将“表情”解释为:“表现在面部或姿态上的思想感情。”可见表情是用来传递思想情感的,它具有语言的属性,甚至在传递特定信息时会超过语言传递的效率。文字叙述是给被传递者提供经验性的想象画面,而面部表情是直接将画面作用于人脑,让观者以最直接的方式接受信息,这就是表情传达信息的力量。
(二)表情与符号象征
艺术文明的创造者需要表情,中华民族的祖先善用表情。新石器时代仰韶半坡彩陶的人面鱼纹和商代三星堆青铜人面像,都是对人脸和表情的模拟,一为平面一为立体,一为质朴一为狰狞,用相异的刻画方式体现着时代思想精神和社会审美。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品类,尤为注重表情刻画,由此表情语言成为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重要的语言要素。如隐去画面人物面部表情,画面将会失去很多艺术魅力,也将导致人物形象精神表现的缺失。由于工笔这种技法以工整精细为特点,相对于写意画法而言,更善于表现人物面部表情的微小动作,包括人物面部的色彩、毛发、皱纹等细节都能精微刻画,精准、精彩地传递出画面人物的性格和状态,使观者感受到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
(三)面部表情与传统工笔人物画人物形象塑造
“形象”可以拆开来分析。“形”字意为事物表露出来的形体、形状,是客观存在事物的外表形状。对于绘画创作者来说,客观存在的“形”是艺术创作的依据和出发点。绘画形象的“象”是自然之象与内在精神的结合,“象”可真可假、可有形可无形。造型的过程是将观察到的客观事物外形、表象根据创作者自身的审美和经历,将心中的思想与情感寄托于艺术形象。经过艺术创造后的造型是“形”与“象”的平衡与对应。例如,郑燮在创作中领悟到创作的三个阶段,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这三个阶段可以看作绘画艺术创作的完整过程,经过见形、立意、造象三个阶段完成了艺术形象的塑造。
二、影响传统工笔人物画表情呈现的主要媒介
(一)以线为核心的表情塑造方式
线是中国绘画艺术传递精神的主要媒介,造型过程中强调用线条表现和创造形象。不同的线有不同的情感,直曲回转间体现着创作者的经营。画中的线条看似自然随意,实则需要经过多年的锤炼,所以线也是画家功力的体现。偶然(客观创作条件)和必然(用笔)相结合,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工笔人物画注重线条,人物画的神态表现集中体现于面部,线条的张弛形成表情。线的宽窄、断续、曲折都结合着笔墨的运用,根据所画形象选择用线达到传递精神、情感的目的。
(二)传统工笔人物画作品中的线与表情
如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在刻画面部时已经会将线条区别运用,以体现画面人物的性别、性格特点。《人物龙凤图》中人物面部线条符合女性形象特征,眼神的舒悦平静和眉毛前端的弧度体现人物的善良,眼角、眉毛绘成上挑的形态,增强了女性形象特征和艺术表现力。《人物御龙图》中对男子面部胡须的描写细致程度,超过对其唇部轮廓线条的精细程度,以突出男性特征。画面线条流畅,飘带随风而起,线条简括。男子眼神坚定,体现了人物潇洒从容的状态。
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描绘了文人隐士的形象,画中人物线条以书入画,人物面部线条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嵇康眺望远方,神态孤傲,体现出他任性率真、刚正不阿的个性。阮籍只露侧颜眼神似醉,体现他清高、不羁,不为世俗规矩、明教法理屈服的处世态度。作为竹林七贤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山涛在竹林七贤中有重要地位,最为年长,辈分最高。所绘山涛正直上身,目视前方,表情泰然自若,似欲题诗以助兴,突出了其内心淳厚、独高其志的性格和圆融不失方正的思想取向。王戎年龄最小,所以面部未有过多纹理修饰,头部倾斜角度最大,表情惬意,体现出他诙谐幽默的性格和从容自得的生活状态。阮咸的表情与其他人的闲适状态形成差异,皱眉低眼,露出认真弹琴之态,上扬的嘴角使人感觉他哼着曲调悠然自得,暗示了他音乐的高深造诣,胡须线条随风而起,豪放旷达、博学多才的阮咸形象立于画中。刘伶低头专心品嗅酒的香气,眼部线条表现出他自然沉浸、闭眼回味的超脱境界,恣意酣畅、放意肆志,好似尘世的喧嚣与他无关。向秀为人沉静平和,可以说他在竹林七贤中性格最不鲜明。整幅画中他是唯一正面面向观者的人物,依靠着树,流露出孤独的气息,体现他儒、道兼容的玄学思想,从面部线条勾勒的眉宇间透出一丝愁苦哀伤,暗示了他为好友的故去伤怀最终含恨死去的结局。画像砖中的荣启期面容慈祥,怡然自得,表现出其知足而乐的精神状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作者运用线条刻画表情,传达出人物性格和其精神世界,尽显当时名士之风采。
(三)表情与色彩
色彩作为表情传达的辅助因素,经常被应用于传统工笔人物画。传统工笔人物画的人物形象塑造具有主观性,画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和人物的身份等诸多因素,对生活中事物的固有色进行艺术化处理。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的用色是一种“心理色彩”,谢赫的“六法”中“随类赋彩”理论说明了中国画色彩运用的基本原则。自然界客观事物都有其形象,艺术造型离不开客观存在,在色彩的运用上亦是如此,塑造形象不是对自然进行单纯的模仿。为了强调形象特征和画面主题精神,画家在客观事物固有色的基础上主观地删减和施加色彩,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物面部罩染了白色,突出皮肤的质感和洛神的仙姿,符合造型特征和梦中意境,尽显晋代画家的浪漫主义创作情怀。唐代《步辇图》中作者阎立本用色彩将唐太宗、侍女、吐蕃使者的形象和身份区别开,唐太宗的形象面部线条饱满,没有多加罩染白色,体现了皇帝的敦厚谦和。为了突出性别特征,侍女面部罩染了明显的白色,描绘了宫廷中女性的面部质感,侧面体现出由于唐朝国力强盛,宫中人生活条件优越的时代背景。吐蕃使者面部主要以线条描绘,突出了沧桑的特征,把地域性差异充分表现了出来。这种施彩方法,不仅将性别和身份区别开来,而且使画面增添了层次感。多种施彩方法的运用,使线条与色彩更加和谐。
三、美学思想及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的引导
在中国画发展进程中,人物画起源最早,魏晋时期走向独立与成熟。工笔人物画的面部塑造过程是从自然表情向审美道德表情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造型时,人与自然相融合。人自然的表情是生物的客观特征,在刻画时经过儒家、道家等社会美学思想充盈,形成了程式化、规范化,具有艺术性的平面图示,且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创作者会根据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的需要,将人物表情赋予教化意义。从传统工笔人物画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美学思想、礼仪道德作用的痕迹。美学思想的进步促使造型方式的进步,社会礼仪道德规范形成了造型的范围和框架,这种创作体系的形成,为工笔人物画人物造型的向前发展提供了养分和动力。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得到巩固,社会各方面得到稳定发展,这为哲学观念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绘画被当作传播哲学思想的媒介,随着哲学思想和绘画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基础也应运而生。
(一)儒家思想的引导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儒家崇尚中庸思想,根据这一基本观念产生了“中和”之美的审美理念。“中和”就是“中正、平和”,包含人与自然、政治与人伦之间的关系顺达、和谐。工笔人物画中的表情符合“中和”之美的理念,画中人物表情喜怒哀乐均点到为止,没有过多夸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和入世之路,表现在绘画上就是多描绘男子独立、雄健、宽厚的形象。这种美学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工笔人物画作品帝王画像中的表情刻画,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帝王表情。从刻画的方式上能看出,画者精心突出了帝王的性格特征。如人物面部统一采用线条圆润饱满、留有须发的程式化绘画语言,以突出明君帝王的威严、庄重之态,气势雄浑、沉稳庄重的帝王形象符合儒家思想中对男子的基本形象要求。而那些庸碌无为的帝王,从面部线条表现方面就失去了气势,多数用文弱绵软的线条,突出懦弱、无为的表情状态。
(二)道家思想的引导
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如果说儒家的精神状态是“坚守”,那么道家的精神状态则是非放纵性质的,非人为作用的“放松”。庄子将这种“放松”比喻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美学思想是崇尚自然之道的“大美”。老子《道德经》中也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的道家理论。工笔人物画中的“无表情”是人生活中的常态,也是最自然的状态。含蓄的人物表情暗示观者看“无”还“有”、“大象无形”的意象境界。
(三)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的引导
在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的引导下,既反映社会现实又有教化作用的工笔人物画层出不穷。它们多采用审美和道德情操相结合的造型方法,体现出社会礼仪道德规范阶级性的特点。如阎立本的《锁谏图》绘制了身为臣子的陈元达勇敢向皇帝进谏的场景,图中的臣子行为符合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陈元达匍匐进谏的举止,印证了儒家礼仪道德中对文官而言,臣子尊敬君王、勇敢进谏的行为准则。图中的臣子意见虽然与君主有不同,但是依然遵守臣子礼仪道德规范,可见社会礼仪道德规范对工笔人物画造型的影响。
又如南宋时期的《女孝经图》,图中描绘了古代女性在生活中要遵守的道德礼仪原则。全卷九幅以图文并叙的形式,告诫了不同阶级身份的女子应遵循尊敬长者、以夫为天、善待亲邻等规范。再如明代陈洪绶的《童子礼佛图》,绘制了孩童模仿成人拜佛的场景。拜佛中的人物表情凝重虔诚,画面兼具造型美和精神美。
中国的道德评价标准在不同时期有一定变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推崇儒家道德体系标准。儒家的道德体系主要是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生命哲学,孟子在此基础上将“仁”扩充为“仁义礼智”,补充了儒家道德体系。随着儒家道德体系的完善,封建统治的社会道德评价标准也逐渐确立。儒家社会道德体系发展到汉代,有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兴起,道家的老庄道德观逐渐发展。加之佛教的输入,形成了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道德原则。宋代时理学兴起,为封建统治的主权性提供了依据,随着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渗透,进一步约束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明清时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批判理学的不足,但“仁义礼智”依然是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会根据描绘对象的社会身份、性别、道德要求、状态等因素对线条和色彩进行调整。在保证造型线条严谨的同时,平涂杂染间进,体现了社会的礼仪道德规范的引导作用。
四、结语
人物的情绪传达可以通过肢体动作,但都不如表情直观。因此,研究传统工笔人物画中人物表情的表现方式,可以为当代画家奠定探索的基础。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线条和色彩将中国画人物形象丰富起来,线与色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人物形象与表情塑造的基本方式。
传统美学思想影响着工笔人物画的造型方式,不断创新的造型手法符合民族文化主体的心理审美结构,表现着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从中国宇宙观和人生哲学中产生的美学思想和社会礼仪道德规范,引导着工笔人物画的形象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而绘画作品利用其具有的同化属性,成为诸多传承方式中直观、高效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