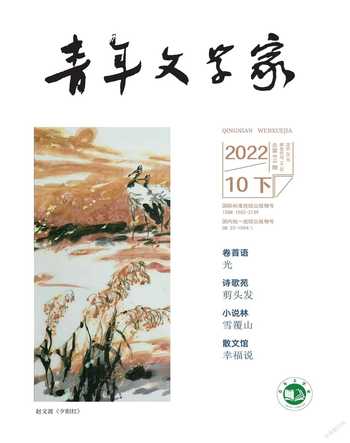浅析《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人物形象
陈玮冉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小说形式革新的先锋人物。她强调现代小说重心的转移,即从“物质主义”转向注重心理活动的“精神主义”。伍尔夫通过创新写作手法来表达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开创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的人物形象,探讨其主题意蕴,使读者充分理解这部小说的价值。
《达洛维夫人》以一日为框架,记录了达洛维夫人的一日生活,其中包括晚会前的筹備以及晚会的顺利举办。就在她筹备晚宴的一天里,自印度归来的她的昔日情人彼得·沃尔什,她少女时代仰慕的好友萨莉·塞顿,和她极其相似的赛普蒂默斯·史密斯,以及伦敦社交圈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相继穿梭在她的思绪里,引发了她对过往青春岁月的无限怀恋和对老年将至的种种恐慌。表面上的华丽舒适的生活与内心的空虚交织在一起,使克拉丽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绝望。在这一天中,克拉丽莎一方面过着现实的生活,另一方面则不断在回忆当中游走。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通过两条平行发展的叙事线索使主人公克拉丽莎的思维穿梭于回忆与现实之间,通过两条线索的延伸与发展,从多个层次、多个侧面反映了克拉丽莎这个人物矛盾的内心世界。即使小说的钟表时间只局限在短短的一天,伍尔夫通过使用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使人物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中穿梭,突破传统钟表时间的局限,深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来书写人物的一生。为了把握人物的真实心理,从而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她将创意的写作技巧融入了人物的悲剧意识和绝望心情,可以使读者充分认识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包括伍尔夫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
一、对自我的统一追求
书中的每个人物对克拉丽莎的外表印象的看法都不同:邻居波维斯先生觉得她是一位美丽的夫人;花店老板皮姆小姐觉得她慷慨大度,但看上去稍微衰老;女仆露西是夫人的崇拜者,认为她是最美丽可爱的;理查德觉得她是需要支持和帮助的娇妻;女儿伊丽莎白认为她古板虚荣。
克拉丽莎是一个生活无趣、内心深处拷问自己人生意义的人物。当露西告诉克拉丽莎,布鲁顿夫人没有邀请她和丈夫理查德一起去参加她的午宴时,她有何感受呢?“她怕光阴似箭,从布鲁顿夫人脸上她就看到生命逐渐萎缩,好似刻在冰冷石块上的日晷;年复一年,她的生命一点儿一点儿被切除;余下的时光不能再像青春时期那样延伸,去吸取生存的色彩、风味和音调。”可是,在想到彼得从印度回来后是否会觉得自己衰老时,克拉丽莎觉得“她尚未衰老,五十二岁刚开头嘛,还有好多个月份要过:六月、七月、八月!每个月几乎都完整无缺”。从以上两个片段,我们可以看出,克拉丽莎想要抓住时间,怀念青春时光和梦想,同时又觉得自己的人生还长,自己依然没有衰老。
克拉丽莎早上外出采买,看到周围美丽的景象,她不由自主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有史以来第一次,她考虑真正认真对待生活。过去的记忆在她脑海中涌现,她想起了她的老伙伴,萨莉和彼得,她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最美丽、最快乐的时光,但她无法回到过去。她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失去的青春、无法实现的梦想和不尽如人意的当前生活。在那个早晨之前,克拉丽莎并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的危机,或者说故意忽略了危机。但从那时,她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开始追求真正的自己。她知道,她极力向世界展示的东西并不符合她的真实面貌,她与两个不同的自我共存。她开始追求自我统一,审视自己在伦敦的生活。结婚后,她从乡下的布鲁顿搬到了大城市。伦敦的生活忙碌、繁忙,人们很少关心彼此。而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年。这是她第一次承认她对在伦敦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满意。“因为只有天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它,如何看待它,把它编造出来,把它建在自己身边,把它翻滚起来,它围绕着一个人,翻滚着。”她第一次认识到,伦敦的喧嚣和繁忙的生活根本不属于她,她对这里没有任何情感依恋。她在伦敦生活了二十多年,外在展示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显然存在偏差:一个是达洛维夫人,她优雅、体贴、温柔、和蔼,喜欢伦敦这个大城市里的一切;一个是克拉丽莎,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乐天知命的女孩儿,她强烈地渴望着乡村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当克拉丽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她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在她的内心危机和她的现实生活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克拉丽莎和现在的达洛维夫人,通过正视自己来追求自我的统一,开始思考去面对自己并不快乐的事实。她在伦敦的生活是一场灾难,她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危机和问题,这就是达洛维夫人这个身份让她窒息的地方。她无法感受到生活中的任何安慰和幸福感,她从心底里憎恨这个达洛维夫人。
阅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意味着在她内心深处,她仍然保留着童年梦想的艺术追求。克拉丽莎仍然对艺术抱有期待,但她仍然要履行她作为达洛维夫人的职责,买花、献茶、宴会,穿梭于各种人之中谈笑风生。整本小说以围绕晚会的核心而准备,晚会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是维系社交关系的手段。达洛维夫人对于办晚会的意义只回答了一次,但是她的回答被多次重复叙述。“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啊,是啊,可是你的那些晚会—你的那些晚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她只能说(她不期望任何人明白):它们是一种奉献。”然而,达洛维夫人看到晚会中被联系起来的人,她又感觉到这种生活是无意义的。文中出现了三次关于晚会的意义,比如这里“也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吧。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天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达洛维夫人反复寻找晚会意义,以及最终思索无果的妥协。她时常感到叹息和不满,对生命中无休止的宴会感到厌烦和疲倦,表面热闹的场面也无法掩盖她内心深处的哀愁和怅惘。虽然,她不可能再回去变成那个无忧无虑的克拉丽莎,但她仍然不遗余力地追求她的自我完整和自我统一。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到克拉丽莎开始关心内心需求,而不仅仅是达洛维夫人的欲望。克拉丽莎一直在读《回忆录》,说明她想回到过去,她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和厌恶,只有回忆能给她一种安全感和温暖感。
二、对爱情婚姻的理智抉择
尽管与议员丈夫婚后生活优越、相敬如宾,但克拉丽莎内心深处并不满足。在整部作品中,彼得·沃尔什的名字远远比克拉丽莎的丈夫理查德·达洛维的名字出现得更频繁。彼得是克拉丽莎年轻时深爱的人,但是两个人经常因为性格差异太大而吵架。克拉丽莎热爱生活,陶醉于大自然之美。而彼得只对世界的状况感兴趣,他喜欢瓦格纳的音乐、蒲伯的诗歌和自己灵魂中的缺点。小说叙述的这一天时间中,有十一个小时是关于克拉丽莎,十个小时涉及彼得。彼得与克拉丽莎的青春是联系在一起的,克拉丽莎的青春消失,这三十年的空白也对应了主人公对时间流逝的怅惘。
克拉丽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爱情和婚姻的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清醒和果断。她年轻时住在布尔顿,和彼得曾有过一段真挚热烈的感情。但她最终没有选择浪漫多情、具有叛逆精神的彼得,而是嫁给了更有安全感、看上去循规蹈矩的理查德,尽管后者不如彼得聪明,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以同样刻板的理智去处理,没有半分想象力,甚至认为正经人就不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们当然可以把此举解读为一个普通女子的谨慎选择:克拉丽莎最终放弃了理想而嫁给了现实,性格温和的正人君子显然比漂泊不定的浪子更适合步入婚姻,但这份世俗里又透出一份罕见的早熟和明智。大部分女子在这个年纪,看不清婚姻的本质,也很难抵制爱情的诱惑,往往不切实际,沉溺于幻想,容易将爱扩展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而失去自我。
三、对生存与死亡的深入思考
小说开头,她早上去买花,感叹“多好的早晨啊—空气那么清新,仿佛为了让海滩上孩子们享受似的”。在对生活享受和热爱的同时,她也思考生命的意义并对生活有着深深的焦虑。在这部小说里,克拉丽莎曾好几次想到死亡,她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台词时表明了她对死亡的强烈渴望。“不再惧怕太阳的热度,也不再惧怕愤怒的冬天肆虐。”她似乎从莎士比亚的台词中得到一种生的力量,这使她能够继续前进,以勇气和胆量面对生活。这些摘自莎士比亚《辛白林》的台词显示了克拉丽莎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考验和磨难的决心。诗中所说的“太阳的热度”和“愤怒的冬天”充满了艰难和悲惨的时刻。这些诗句也暗指死亡,无论一个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死亡都会成为一切的结局。因此,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是同时勇敢地面对死亡和生活。在她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和不愉快的时刻,她几乎被强大的力量紧紧包裹而感到窒息。然而,克拉丽莎决心不再惧怕她枯燥乏味的常规生活,就像达洛维夫人一样,她试图勇敢地拥抱真实的自我。她承认自己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女主人,她极其渴望消灭她生活中的一切。她认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克拉丽莎而不是达洛维夫人。莎士比亚的诗给了克拉丽莎勇气和胆量。
在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经过其双生体赛普蒂默斯死亡的洗礼肯定了生命的意义,从而鼓起活下去的勇气。伍尔夫通过克拉丽莎“向死而生”的積极态度,最终揭示了生命的意义。赛普蒂默斯死亡的消息给克拉丽莎审视自己生命的机会,明白了赛普蒂默斯选择死亡的意义,让自己获得了新生,主动作出自我抵抗,完成了内心的自我超越,重获完整独立存在的自我。
在小说中,克拉丽莎和赛普蒂默斯不存在直接的交流,唯一的联系便是在伦敦街道一起看到天空中的飞机。这种移情作用使得两人对死亡这一主题的理解和感知得到了统一和升华,并且这种移情作用也在哲学层面上暗示赛普蒂默斯与克拉丽莎两人的共生—这恰恰是从侧面展现了伍尔夫意识流叙事手法的高妙之处。在结尾,两条线索又得以汇聚。达洛维夫人从前来参加晚宴的客人口中听说了赛普蒂默斯自杀一事,达洛维突然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生出了一丝敬意,甚至开始相信“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但是,克拉丽莎并没有选择死亡,她领悟到了生命的价值,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积极态度。对于赛普蒂默斯而言,他历经战争创伤,在荒诞冷漠的外部世界里,他不愿面临被隔离的危机,于是选择死亡作为一种抵抗,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本质。生存与死亡的主题,在赛普蒂默斯的“虽生犹死”和克拉丽莎的“向死而生”中实现了统一。
死亡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无奈。最后被逼自杀的赛普蒂默斯死前还抱着最后的生的希望:但他要等到最后一刻。他不想死,生命是美好的。和多次经历生死离别之苦的伍尔夫一样,热爱生命的克拉丽莎对于死亡,既被它深深吸引,又感到无比恐怖。克拉丽莎甚至想过:“如果现在就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但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快乐有着敏锐感受的她又不愿接受死亡。伍尔夫在小说故事中弱化了故事情节,重点从人物的意识世界中探索人物的内心感受。在小说结尾,读者才明白两条线索的意义,才明白赛普蒂默斯的想法与克拉丽莎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饱受精神痛苦,迷惘于生命的意义,找不到脱离精神泥沼的办法。
《达洛维夫人》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风格成熟的标志,是现代叙事艺术的精品。小说的视角能十分流畅地转换,将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完美地融合,同时也揭示了伍尔夫对人生的思考。通过分析克拉丽莎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她努力追求自我的统一,对爱情、婚姻的理智抉择,以及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
——解析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艺术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