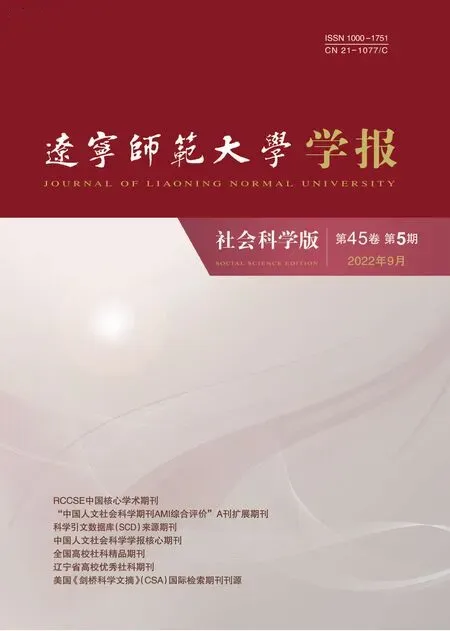科幻叙事中的后人类身体与生命政治
李 缙 英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在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科幻漫画等艺术中,从感知、意识与身体等维度来构想赛博格逐渐成为重要的创作趋势。而这些科幻叙事中的离身性与具身性的想象,也为探讨新的后人类主体以及新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维度。
一、“赛博朋克”电影的科幻叙事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等科幻小说,引领了关于后人类的科幻小说、科幻漫画和科幻电影等“赛博朋克”(Cyberpunk)艺术的潮流。这些文艺作品并非被动地应和观念的转变和技术的革新,而是在文化语境中塑造关于技术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探讨与科学理论相关的假设或假说。而实现科学文本与艺术文本互动的核心就在于叙事[1]。改编自科幻小说、漫画的《黑客帝国》《阿丽塔:战斗天使》《攻壳机动队》等科幻电影因其所杂糅的文学性与创新性,更成为科幻叙事的重要形式。
而齐泽克、维利里奥和奈格里等当代西方左翼理论家,也从诸多领域、多重维度来探讨关于赛博格的科幻构想。这些理论家为何探讨科幻叙事中的赛博格呢?其实,在当代左翼理论的视域中,赛博格是涉及哲学、美学、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后人类主体,是人类主体理论谱系的一部分,而科幻叙事的前瞻性构想使其在后人类的探讨中显现出重要的寓言性/预言性作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与历史小说是来自过去的信息相似,科幻小说是一种来自未来的信息,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一种新的再现,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机制[2]。科幻艺术中的后人类想象是用比喻的手法来表现全新社会的可能性,而新的感官现象并非在创新层面被具体化,而是在象征以及审美层面展开。具体来说,由于一种新的特性需要一种新的感知,而新的感知需要新的感知器官,因而也就要求一种新的身体。对科幻艺术来说,这就涉及象征意义上的生产性,即想象出新的感觉器官和迥异的身体[3]。而从人类与机器、人类与后人类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只有当机器人挑战人类的主体界线并威胁到其主体地位时,才会出现后人类观念及其在艺术中的体现[1];另一方面,以人机嵌合为特征的“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既是虚构的,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赛博格在20世纪末成为人类的本体论,人类也成为被理论化、被制造的机器有机体的耦合体、嵌合体[4]205-206。换句话说,科幻叙事关于赛博格的感知与身体的想象,是探讨构筑新的(后)人类主体以及新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切口。
更重要的是,科幻叙事的想象虽侧重对视觉表象的建构,但这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化投射,而是试图借助技术以意识的自由性来克服身体的局限性,构建出人类的新的认知模式、世界结构与社会机构[5]。而且,赛博格绝不仅是一种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的形式创新提供语境的现象,赛博空间也并非现实世界的投射,而是一种共识性的幻觉,一个新的公共空间。那么,科幻叙事如何想象、理解与推衍新的赛博格呢?
在科幻电影中,关于赛博格的想象主要从“离身性”与“具身性”维度及其与后人类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展开。在科幻叙事的意象方面,以人类大脑、脊髓等神经系统为人机结合的媒介,即“脑机接口”(mind-computer interface jack)、“神经链”(neuralink)、“连线神经”(wired nerves)或“连线大脑”(wired brain)等,不仅成为想象离身性的生命形态以及生成后人类主体的关键性意象,还为科幻叙事带来多重维度的叙事空间。
首先,这种意象不仅可以实现后人类“脱离肉体”的形态,即在赛博空间中摆脱肉身而作为电子数据或经由媒介上传的意识而存在的状态,还可以实现人类意识与赛博空间的联结,创造出“离身性”的赛博格形象。在《黑客帝国》中,人类的大脑、脊椎和四肢被配置了安插线路的接口,以确保人工智能可以控制人类意识,并将意识生成的影像投射到赛博空间。这种神经网络昭示了一种人类末日的景象,而如果将其推衍至极致,也就开启了所谓“奇点”(singularity)的前景[6]以及全球空间的共享意识。其次,通过这种媒介的意象,人类可以借助机器来实现身体界线的扩张和能力的增强,由此生成人机嵌合的后人类。在《阿丽塔》《攻壳机动队》等科幻电影中,后人类可以通过这些神经系统来驱动机械躯体和装备、改变身体形态,还能够实现“脑潜入”“脑清除”和给药等功能。再次,这种意象改变了传统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机伦理,创造出涉及新的后人类的自我认同等伦理问题的新语境,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机器、肉体与灵魂、人类与赛博格、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的多重伦理关系以及权力关系。可以说,这种意象不仅为生成去身体化和再身体化的后人类创造了可能性,还为探讨人性与物性、动物性之间的抉择,以及有机体与机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转换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然而,如何以关于赛博格的构想来探讨后人类及其对构建新的人类主体性和社会结构的启示性意义,又能够避免相关的解析沉醉于绮丽诡谲的想象或沉溺于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呢?应该说,西方左翼理论能够为解析赛博格想象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范式。
二、从离身性的赛博格到后人类的意识
在科幻叙事中,关于赛博格的“离身性”构想是指一种关于在身心二元化剥离、沉浸式的赛博空间中的离身性体验的幻想,也就是一种脱离肉体的想象。赛博空间通过提供虚拟经验和虚拟环境,推动了对离身性体验的模拟的实现,使赛博格摆脱肉体的局限,突破空间的界限,作为纯粹的数据或经由网络上传的意识而存在,而肉身则成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对象、功能的承载物。在维利里奥的“视觉机器”与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视域中,这种想象为探讨后人类主体的构建问题提供了一种去身体的维度。
(一)离身性赛博格的影像
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人类生命形态的艺术表征呈现出抽象化、去身体化,或者说,非身体的趋势。在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关于在机器装置中流动、游荡的工人的幻想式演绎,成为一种对劳动者的“生产机器”本质的揭示:工人成为配合资本的“无器官身体”的机器。而在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中,关于生产机器的幻想式演绎转变为一种科幻式的表达:人工智能将人类置于营养仓中控制人类的肉体以充当为矩阵提供能量的活电池,并通过“脑机接口”监视人类的意识。而人类根据残留的意识对自己形象进行心理投射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则成为人工智能在电脑生成的“矩阵”即虚拟世界中生成虚拟影像的基础。然而,如果虚拟影像在虚拟世界中死亡也会导致人类意识的死亡,而营养仓中的肉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被当作废物处理掉。在实质上,虚拟世界成为监控意识的监狱,而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下逐渐成为一种功能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机器,一种被控制、被剥削的对象。
除了作为生产机器的赛博格,《黑客帝国》中的“特工”即虚拟世界内部的某种杀毒程序,就是一种作为杀戮机器、战争机器而存在的赛博格。特工不仅是自创生(autopoietic)的不死之身,还能够识别并杀死尼奥等人,使虚拟世界中失衡的状态恢复平衡。与这种去身体化的杀戮机器、战争机器相关的就是虚拟战争。然而,吊诡的是,虚拟战争意味着一些身体被另一些使用武器技术的身体所摧毁。譬如在《星际迷航》《星际特工》等科幻电影所描绘的关于“星球大战”“星际大战”的场景中,常常出现在装备上占据优势的一方远程操控飞船、战舰和武器,攻击远在数光年之外的敌人,甚至出现将部分肢体投射到另一维度的空间中与敌人展开搏斗的情节;而在虚拟战争的武器攻击之下,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位置的士兵,其意识和肉体却会真的死去。可以说,这些战争机器代表了社会劳动的高度积累,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而技术化、冷漠化的战争逐渐变得“去身体化”。换句话说,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争变成无身体的;从技术角度来看,战争由此变成了虚拟的[7]。在这种虚拟战争中,敌对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博弈造成了一种非对称格局,而这绝不仅仅是刺激的游戏设置或疯狂的科幻想象。
那么,作为一种赛博格的虚拟影像如何形成?首先,从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来看,关于去身体化的赛博格的想象与实践源自一种“脱离肉身”的观念,其本质为一种身心二元论。在《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海尔斯以控制论的自反性、自组织、创生性的三次进化来概括后人类理论的推衍过程,而推动控制论发展的关键是信息论中的“去物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推衍为一种看似荒诞的“机器中的幽灵说”,但这种假说却逐渐成为事实。人类的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被转化为处于重塑、重构以及变形过程中的虚拟身体[8]。这种去身体化的赛博格也就是人类生命本质的信息化,消解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并将二者融为一体。
其次,从艺术表征的方式来看,去身体化的赛博格是对处于“脱域”状态的赛博空间之主体的想象,而这源自现代社会时空机制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与实践中时间与空间逐渐相互抽离,形成了迥异于前现代社会的时空分离状态。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关系从高度局限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而成为“脱域”(disembeding)状态,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常规形态[9]。而科幻叙事中的赛博空间正是对这种常态的想象性飞跃,即时空重组、身心二元分化的状况,这是依据人类意识的自由性而重新理解、组合、创造的时间、空间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正是“脱离具身的意识”投入到网络所构筑的感官沉浸式的、时空重组的世界。在此,人们不仅可以重新定义关于时空的理解,展开一种更深广的时空探索,还可以克服身体的局限,使感官世界进入到更自由的境界中。而在构想赛博空间时,对视觉表象的展示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人们总是通过视觉来感知和认识世界,而在一种所有感官被占据的全沉浸式的情况下,视觉更成为一种绘制赛博空间的线索[5]。
功能性饮料中大多富含电解质,可以适当补充人体在出汗时丢失的钙、钠、钾、维生素B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但由于婴幼儿的身体发育还不完善,代谢和排泄功能不健全,过多的电解质会加重宝宝的肝、肾、心脏负担,增加宝宝患高血压、心律不齐的几率,甚至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害。
那么,视觉表象所主导的、感官沉浸式的赛博空间是何种形态?赛博空间是在将人类的所有信息和体验进行数据存储的基础之上,以信息景观来构筑的超级表象结构。更重要的是,将其诉诸视觉表象,也就是重新想象人的自身形态的外化表征的问题[5]。可以说,赛博空间试图在新世界中提炼出一种新秩序,而这代表了一种去身体的模式、一种视觉化认知的模式。
在法国左翼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看来,虚拟影像是对人工的“视觉机器”替代人类的视觉和知觉的符号性表征。在本质上,虚拟影像或作为一种赛博格的虚拟人,存在于以电磁场为特征的虚拟空间中,是由代码构成的特殊符号集,既可能由现实人转化而来,也可能由程序生成,但这并非一种代偿性或模拟性影像而是虚拟现实的影像。而这种虚拟现实的影像与“视觉机器”有关。维利里奥指出,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数字图像和数字合成视觉等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人工智能等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视觉学”,即不用目光而使用机器分析来获得的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这种视觉机器并非远离反而回归了虚拟图像的本质,即一种没有表面载体的图像业,而事实性/操作性和虚拟性也就融合在一起[10]117-119。从图像发展的历史谱系来看,全息摄影、视频通信、计算机成像的时代就是图像的反常逻辑的时代,而所谓逻辑的反常是指控制再现物的实时图像的反常,是再现图像的真实时间压倒真实空间的反常。这种机器图像有利于展示一种反常的在场:在现时现地,物体或生灵的“远程在场”替代了自己的存在;在图像的辩证逻辑时代中存在于底板、胶片、交卷中的物体的“错时在场”,衍变为反常逻辑时代中的物体的“实时在场”[10]123-125。从关于虚拟影像的视觉机器来看,机器的解译与人类的视觉没有任何关系,数字化的图像对计算机来说也只是一系列编码,而感知器则是逻辑的结果。因此,赛博格的机器图像的反常逻辑具有控制时事的潜能,扰乱了真实与虚拟概念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身性的赛博格是一种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谓的“生成动物”“生成机器”,也是“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11]的后人类主体。
(二)后人类的意识
除了赛博格的影像,赛博格是否具有意识,或者说赛博格的“意识”是否与人类意识相同?在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后人类主体的自我认知。在科幻叙事方面,电影《攻壳机动队》(GhostintheShell)探讨了赛博格的自我认知危机。在未来日本,“蜜拉”是阪华机械根据少女的大脑制造的第一个成功的全身机械化的军用赛博格,后来成为国防部的特工部队“攻壳机动队”的少佐,是人类灵魂与机械躯体相结合的完美产物,不仅拥有由先进技术改造的全身机械化的躯体,更因人类大脑和电子脑(cyberbrain)而拥有指挥能力、想象力、同情心和直觉等“灵魂”,并在“攻壳机动队”队友的帮助下消灭了幕后的资本家,实现了对自己后人类的身份定位、情感归属和使命确认。然而,后人类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体认,不是在人与机器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二元对立的中间位置,一种内在性的、奇异性的位置。
从拉康精神分析来看,在后人类主义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操演性悖论”(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齐泽克指出,在拉康精神分析中,人类婴儿的“镜像阶段”是通过对镜子图像中身体的一部分进行认同化以确认完整的自己的。换言之,主体性认同的基础是在其所不在的反转场域中看到自己,这本身就是误认。人最初就是通过这种镜像操作而进入“现实”,即碎片化的器官被统合成单个实体,进而用“我”来认定社会-符号性的角色。然而,在后人类的自我认同过程中,一个被操控的人类能否将自己的行动“体验”为某种自发的行为?他能否意识到自己被操纵,或者说,意识到某种“外力”以某种方式体现为某种内在冲动,抑或只是一种简单的外部强制?在齐泽克看来,当人类意识面对机器的直接物化,即与神经网络直接整合时,人们不再能够保持独立的个人性的幻想了。这种机器的增补并不只是我们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一个外在装置,而是组成了我们作为有机生命的自我经验的一部分,也因此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离心作用。倘若将外在化的智能作为人类身份所内在的一部分,而不考虑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主张从“意识的社会”到“社会的意识”,也就是人们必须在由社会关系和能将智能客观化的人造机械增补物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中发挥意识的作用[12]52-55。那么,如何在网络结构中发挥意识的作用?从积极的视角来看,这些引发颠覆既有秩序的新伦理语境,将为构建新的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提供一个契机。
那么,后人类的“虚拟的性”或“电脑中的欲望”这种颇具争议的意识,仍是一种意识吗?这是基本的乱伦、普通的性颠倒和代替,还是虚拟的、异化的欲望?对齐泽克而言,意识形态和欲望都是一种规范着有形与无形、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关系及其诸种变化的“生成矩阵”(generative matrix),是一种对社会起规范作用的虚幻结构和隐藏机制。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或欲望的对立中,对立物的某一极在平衡其对立面的过度力量时,也内在于它的对立面中。从拉康“不存在性关系”的命题来看,真实性行为也是以“真实的他者”的身体为虚幻投射的支持的。换句话说,“虚拟的性”并非对真实性欲的扭曲或异化,而是对意识形态幻象的结构的明晰化、显性化[13]。
其实,虚拟世界的其他意识也是对“真实”意识形态及其结构的揭示。在《黑客帝国》中,从虚拟世界呈现的带有绿色的影像,到接线员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生成虚拟世界的绿色代码,再到尼奥被特工所伤的眼睛所看到的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机器帝国,都是数字所构筑的网络结构。从虚拟现实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虚拟现实标志着我们的感性经验被根本地还原为数字体系、电子符号,人们也通过机器的中介直接共享心理过程或心理经验,生成一种沉浸于集体意识空间的主观体验与自我意识;另一方面,虚拟现实由视觉机器来保障,能够生成视觉幻觉而导致视觉和知觉的感知混乱,而且作为虚拟的象征秩序的赛博空间也为我们建构现实的网络,这意味着巨大的机器网络嵌入到社会支配关系中。换言之,虚拟现实的潜能开始瓦解并支配“真实”,不仅参与后人类主体生成的装置中,而且构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言,重要的不是虚拟的真实(virtual reality)而是潜存的真实性(the reality of virtual)。虚拟的真实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在媒介中复制的真实,而潜存虽然是象征性的,却具有真实的作用和影响,并始终保持着一种未完全实现的、作为永恒威胁而存在的状态[12]27-28。因此,与其将这种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看作一种悖论,不如将其看作一种讽喻性的寓言,而赛博空间也就是构想新的认知方式、人类生存形态以及世界结构的乌托邦。
三、从赛博格的身体到后人类的生命政治
除了离身性想象,关于赛博格的具身性想象也成为科幻叙事的重要灵感。在许多科幻电影中,随着形貌整容、芯片植入与基因改造等成为常规技术,人类的肢体和器官被移植、改造,成为机器的假肢,或者复杂机械、数字设备的内在性元素,换言之,逐渐被赛博格化。
(一)赛博格的身体美学
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科幻漫画《铳梦》的《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BattleAngel),是关于赛博格的具身性想象的典范之作。漫画《铳梦》不仅沿袭了20世纪80年代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赛博朋克”风格,而且弥漫着日本社会思潮尤其是漫画文化中“技术乌托邦”与“末世废土”的双重想象的时代氛围。而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编剧和监制詹姆斯·卡梅隆的技术至上主义,使电影《阿丽塔》强化了人与机器共同进化的主题,以及“战斗天使”阿丽塔的身体形象、格斗技术和战斗场景等。可以说,“赛博朋克”风格和技术至上主义理念的糅合,使关于赛博格的身体想象显现出强烈的美学意味。
而从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美国文学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生命政治理论来看,这种想象也将关于后人类身体的探讨漫延至身体政治乃至生命政治层面。
从身体政治以及生命政治来看,《阿丽塔》通过权力控制与资本剥削的方式揭示出后人类身体所处的境况。在赛博空间中不仅存在着暴力和犯罪,超越肉身的想象更使身体遭受残酷的剥削与戕害:一方面,“天空之城”撒冷的社会生产已转变为一种非物质性、协作性、合作性的生命政治生产,即将身体、情感、欲望等作为原材料和商品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撒冷索取钢铁城的原料、商品而抛下废物,是一种取消资本内外界限的实质吸纳方式。而实质吸纳就是资本凌驾资本市场的内外边界,过度剥削情感、身体、交往方式和普遍智能等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商品的方式,因而“实质吸纳=生命权力”[14]74。更重要的是,赛博空间成为一种全景监狱式的、公共的社会文化空间,不仅为人类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定位、定性还重塑主体性,而且形成一种虚拟现实世界的控制机制[15]。而这种机制也就是一种依赖数字化管理、智能分析与智能控制的治理术,也就是数字化的生命政治。
可以说,赛博空间是后人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赛博朋克”式的、生命政治化的反乌托邦。
(二)后人类的生命政治
那么,抵抗权力控制、资本剥削并构建新的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谁?从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来看,蕴涵着解放潜能的主体正是后人类。后人类的主体性生产具有混合性、杂交性和调节性的特质,这并非传统的中心化主体,而是一种重组的杂合体,一种涉及人类与机器的本体论关系的赛博格/机器主体[14]107-111。在《阿丽塔》中,阿丽塔的心脏是由反物质微型反应堆所驱动,拥有驱动钢铁城运转几十年的能量,而她的躯体能根据潜意识的自我认识来重塑形象。她不仅拥有大马士革钢刀、等离子火焰等高科技战斗装备,拥有记忆陀螺仪、中枢能量连接等数字化装置,还能够熟练运用咏春、太极等功夫,在“天坠之战”、机动球比赛、挑战赏金猎人、地下大战等战斗场景中展现出综合格斗的技能。可以发现,阿丽塔的身体构造和装备都是以战斗为目的而设置的,既表现出“战争机器”的本质,又蕴含着反抗的巨大潜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丽塔就是奈格里所谓的“生命政治士兵”,也就是他通过反思在后现代军事变革中被去身体化的战争机器而构建的再身体化的生命政治主体,一种后人类主义的主体在革命或军事领域的变体,也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蕴涵着抵抗控制与剥削的自我增值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对后现代主体的寓言式演绎,或对其重建自身的乌托邦想象,也就是一种奇异性的乌托邦,一种作为乌托邦的奇异性形象[16]。可以发现,正是这种解放潜能才是吸引奈格里等西方左翼理论家探讨后人类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探讨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时,后人类主体将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其实,赛博格不仅是对人成为机器的隐喻性表达,也揭示出后人类的主体性的发展潜能。或许,机器智能取代人类智能正是智能演化的趋势,而机器所拓展和增强的也可能是人类机体之中的力量。也许人类向机器进化或曰“爆裂式突破”并非人类的毁灭,而是自我提升[8]。对奈格里而言,这种杂交主体性的生成,蕴含着消除身份差异、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方面的政治潜能,具有一种颠覆等级制度的革命性力量。从“尼采学派”的身体理论来看,赛博格是对后人类主体之身体进行最大限度的智能化、科技化、信息化,在人机关系本体论基础上生成的杂交主体性,是一种游牧式或赛博格式的主体[14]116-123。这种混合物、镶嵌物、嵌合体,不仅消弭身体与非身体的界限,其复制也超脱有性繁殖的制约而成为一种自我繁殖或“自创生”的生成装置。这种生成也就是生命政治化的后人类本体论,而后人类也就具有一种超越种族差异、性别差异、身份差异的身份政治的潜能。
从更为抽象的装置层面来看,后人类蕴含着反抗二元论的解放潜能。在哈拉维、海尔斯等学者看来,赛博格挑战了自我/他者、身体/心智、现实/表象、男性/女性、整体/部分等二元论,进而推翻了维系现代性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4]247。然而,这种观点对二元论持有双重标准,其观点在反抗二元论的同时又沦为另一个二元论的傀儡。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在通过推翻既有的二元结构并生成新的后人类主体之后,又构建出一个潜在的“后人类主体/世界客体”的二元结构。与被推翻的二元结构相比,在新的二元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类主体被后人类主体所置换,而其结构及其主客对立的模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17]。而在西方左翼理论视域中,后人类蕴涵着更加激进的潜能。从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来看,后人类是一种蕴涵“生命政治理性”的主体,也就是以主体的另类生产范式,从非物质的生产延伸至主体性的生产,并向共同性的构成开放。这种生产范式能以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超越“现代/反现代”的二元结构及其二元对立逻辑[18]。更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这种以情感、欲望和感受为基础的共同性行动,具有构建共同体的潜能。在《阿丽塔》中,以阿丽塔为代表的“火星共和国联盟”正是以爱和正义为基础的共同体乌托邦。
综上所述,在维利里奥和齐泽克的理论视域中,离身性的想象是从非身体维度来探讨后人类的主体性生成的;在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论中,具身性构想是从身体美学与身体政治维度来探讨后人类的主体性生产的。而通过西方左翼理论分析科幻叙事中的赛博格,可以揭示出后人类主体所蕴含的反抗资本主义并通往共同体的潜能,为探讨后人类乃至未来人类的主体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域与研究范式。然而,西方左翼理论视域中的后人类,将通往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导向一种以审美乌托邦为基础的共同体乌托邦呢?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