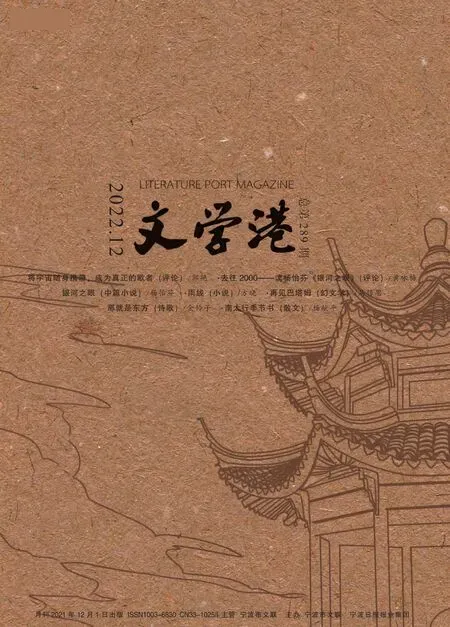创作谈:在后视镜中虚构
□杨怡芬
年岁渐长,初老已至,不免时时回望来路。作为一个已经写了二十年的写作者,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清晰,是用来固定当下的,以今日之踏实努力,去成就未来;模糊的是,随着写作岁月中虚构形象的增多,他们占据了我的真实记忆:因为曾着力塑造的缘故,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比我真正的邻居面目清晰,到底谁更真实?模糊难辨。
小葵也是,我熟知她的一切,但她并没有真的存在过。在这篇小说里,她从1984年的16岁一直生活到2000年的32岁,对亲情和爱情,她有刻骨体会;对城乡差别和阶层变化,她有微妙体悟。我努力在小说里呈现往日真实芜杂的生活质感,我努力让读者以为我和小葵之间有非常接近的关系;具体而微的编年,氛围十足的季节,也都在强调事情曾“真实发生”,借以逃脱小说“虚构”的牢笼。如果读者真的有了共鸣,把作者和人物混为一谈,我想,那就是我这个作者的成功。
这里说个趣事。近年,我写了一个二战中舟山海域沉船的故事,用了男性英国战俘的视角,我也努力呈现那艘日军战俘运输船的日常,努力贴近那个男性角色。这个题材关乎战争和俘虏,通常,这是男性作家的领域,因此,有个女评论家笑说我“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胆敢去碰触。答案真的很简单,大概就单纯地想 “怼”一下谁。因为,在写作的前十年,我写了一系列的以女性为对象的小说,有读者(甚至是同行)认为我在写“我自己”的生活。 “你写的都是你自己的生活吧,否则细节怎么这么逼真呢?”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是一个写作者的风险,读者会以为你是在以自己的隐私为燃料,对女性写作者,风险尤其大。小说本就是虚构之物,这是基本概念,毋庸多言。对此,我的“回答”还是写作。在《海上繁花》 (将出版)里写二战中的男性战俘,在《离觞》 (已出版)中写内战中的小城男女,我的人物和“我”很远,但我依然有能力去走近他们,依然有“逼真的细节”,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样的回击,往深里想,是很可笑的,但却是我近十年里的偏执,这份偏执,成就了我上述两部长篇小说——是的,都是在久远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我和书中的人物,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可是,说到底,这样的“回击”,也不过是我自己在乎罢了。写作,也许就是自己在角落里和自己各种过不去吧。
今年三月底,我完成了那个二战沉船的长篇小说,为终稿而挣扎,交出稿后,几乎虚脱。缓了一阵子,我天真地想,我来写个短篇小说庆祝我的新长篇完工吧。
事实证明,冒出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佐证我真的只是个“长篇新手”。短篇小说的叙述似乎得匹配充沛的体力,而我此刻正在亢奋后的疲惫里。盘桓三四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叙述的力量了,最后成稿的是这个中篇, 《银河之眼》——这个题目是在写作中途来的,它挤走了原来的题目,并强势覆盖,到现在,我已经忘记原题是什么了。
小说写作一直以它“玄妙”的一面吸引着我,比如,我刚才再三说,小葵不是我,是我虚构的,但是,在我努力让她“逼真”之后,怎么向普通读者解释她是怎么从我的脑海里升起来的呢?这个故事的小宇宙,是怎么从某个奇点爆炸的呢?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一名记者,能很清晰地解释一篇稿子的由来;一个写小说的,却很难说清楚——不是不愿,实是不能。
还是得逼问自己。可能,缘于对“20世纪八十年代”的探摸?这是我下一个长篇的时代背景。近期,我做的功课,就是逐年细看中外大事记,打量具体民生细节。我想在心里构筑一个改革开放之初的舞台,我的主人公们在其间走动,我就能与他们一起生活。
1984年,以它的魔力叩击我个人的记忆之门,那时候,我也已经记事了,只是当时年少,如身在庐山之中,一切都面目不清;而现在已隔关山万重,凝视它的眼光里又借助了集体记忆,似乎,我能 “看见”了。那一年,“人民公社”在变成“乡”;那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枚金牌;那一年,一个叫“幸子”的日本姑娘让国人唏嘘……这些共同记忆和我的个人记忆混杂在一起,在某个黄昏,面对落日,一个叫小葵的姑娘,从我的脑海(记忆)中升起。那么,就是她了,她是我的叙述者。开头,只是一个她面对落日的背影,接着,是她在夏夜的南边天空搜寻银河的双眸,那么,她在1984年会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在那个夏天,她会遭遇什么?艾丽丝·门罗在《加拿大论坛》杂志上发表的名为《什么是真的》一文中说过,她的小说会用一部分真实的经历作为发面的引子,还可以把想象出来的东西作为酵母巧妙地加在引子里。那,我的引子和酵母何在?
也还是得亏艾丽丝·门罗的引导,在读她的短篇《谢谢你让我搭车》的时候,我自己的一段陈年往事破壳而来。对啊,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些大变革即将发生的年代,我也好奇地看过外来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我们这样的岛民是什么?这个时刻,“引子”来了。萨特说过:“阅读就是写作。”这样的论断,看着真是武断,但我把那个短篇读了两遍之后, “新”小说的场景开始呈现,这个时刻,“酵母”也来了。类似阅读和写作之间关系的判语,不独萨特,很多很多人说过,无论如何,说成“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总是没错的。
于是,故事以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进行着了,这些场景,来自“后视镜”中的观望。我的小说,对于季节的感觉和空间的感觉,总是相对敏感,这两者,常常是我将琐屑而混乱无序的日常细节组织起来的工具,它们也汇聚在场景里。那些场景,就是“后视镜”里闪现的画面。单向度的人生通过 “后视镜”,好好打量一下“过去”,这是我希望这个小说能生成的意义。
但是,能吗?我和小葵面面相觑。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是第三人称的小葵。我一向觉得,即便是动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也应受限——至少,不是完全打开的上帝视角,那么,我得找到适合小葵的腔调和视角。在小说的开篇,她是个16岁的少女,调试再三,我定下了偏文艺腔的叙述。这也是我想做到的,叙述者和叙述腔调,要有形式上的某种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落实在对话里,更得融化在叙述里。叙述是无声的对话。
当全篇完成,以我自己的标准,从头至尾复盘,修改再三,如释重负交出稿子之后,次日醒来的刹那,惊觉还是少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声音:蝉声。于是,赶紧又和雷默说,收回重改。
现在,和交稿又隔了一段日子,于是,心生贪求:如果这小说能再放松点,可能会更好。当然,我又马上宽慰自己: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记得我第一次在《文学港》杂志发小说,是2004年,杂志社还请了吴义勤老师写了评论推介。虽然当时并没有“甬舟一体”的概念,但《文学港》实打实地助推了我这个舟山作家一把。据我观察,这些年来,不独是我,我们舟山很多作家,也得益于《文学港》杂志——甬舟两地的情义,恒久且真实无虚。感谢,是必须的。时隔多年,我很想写个“好小说”作为谢礼,心意虽诚,但笔力迟滞。小说,永远是有缺憾和瑕疵的,犹如我们的人生,但惟其如此,才是真实的吧。
人生的时序在渐渐入秋,在严冬来临之前,我仍将继续努力,我能以小说,去生成此生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