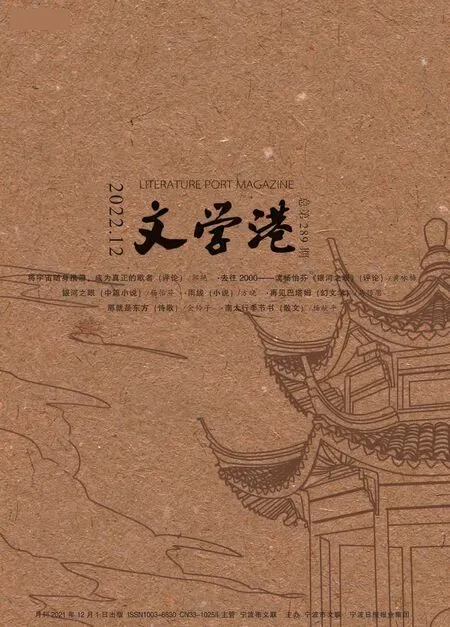送信
□杨 枥
1
那个初夏的早晨,我爸让我替他去大娘家送一封信。我问什么信,我爸嚅动着干燥的嘴唇说,别管这么多,送去就好。
那时,天还没大亮,我妈已经下地了。她一早起床,就是为了搜捕那些躲过数次围剿的老虫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菜青虫也懂,尤其那些历经风雨的老虫子。年轻虫子,因为气盛,做事高调,不懂得收敛。一棵菜,菜心固然鲜嫩,却是战场的核心地带。
菜叶正面,阳光充足,叶绿素丰富,但危机四伏。年轻虫子脑子一热,才不考虑这些兵家大忌,往往仗着腰杆子硬,冲上去就啃。它们吃饱喝足了,在甜美的“虫生”里摇头晃脑,也完全暴露在了靶子上。
有人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大概说的是森林中的鸟吧。飞进菜地的鸟,只会啄食西红柿和偷盗土里的种子。早起的虫儿有菜吃才是真的。刚包心的包菜,被露水滋润了一夜,肥美多汁,咬起来咔吱咔吱的。春蚕咀嚼桑叶算什么,青虫啃包菜才叫一个痛快。
小虫子啃食菜叶,就像蚂蚁啃骨头,小嘴一扁一扁,叶面很快被啃出许多小米粒样的凹斑。老虫子铁嘴钢牙,好好的菜叶,不大工夫就大窟窿小眼睛了。如果治理稍有延迟,整片菜地变为废墟就在弹指之间。
为了保卫自己的果实,菜农会增加农药剂量和喷洒频率,可日渐升高的农药残留指数,反而锻炼了菜青虫的生存能力。有时候科技手段还真不如土办法好用,我们决定人工捉虫,既安全,又能一了百了。一个称职的菜农,要肯下力气,要有技术,眼睛要亮,还要掌握天敌们的生存规律。
老虫子命长,是有道理的。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它们先其他虫子一步, “进化”成了穴居动物——当我发现这一现象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惊讶。
它们建造在土里的洞穴,通常在菜根附近。虫子精心计算过,按照它们的脚力,远了费时,近了容易被人发现。它们每天两点一线,和上班族一样勤劳。
对虫子而言,啃菜既是生活所需,也是工作内容。下雨天,它们照样上班,就伏在叶子阴面、雨水洒不到的地方。有时候雨大,冒雨也要出来。毕竟, “虫是铁,菜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虫子上班,不是朝九晚五,更不会整个白天都上班,它们昼出夜伏。吃饱了在菜叶上躺平,好是好,但有暴露的危险。居安要思危,老虫子也这么想——千万别小看造物主的任何心思。因此,老虫子吃饱就闪,它们和工作时间久的老油子一样滑头。只不过,老虫子躲人,怕被捉;老油子躲工作,怕出力。
老虫子伺机而动,就像阴谋家,逼得菜农也成了战略家。
看着一团团湿漉漉的粪便,却不见虫子的身影,任谁都会恨得牙痒痒。眼看一棵菜快被翻腾熟了,还找不到它们——千万别急躁,虫子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跳槽,老虫子更念旧。大约从虫卵孵化为虫的那一刻,老虫子就把咬了第一口的那棵菜当成了第一口母乳和唯一的故乡。
别不信,我实践了很多次,且每次都不落空——要么它借着菜叶的掩护在泥块下休憩,要么它回到了自己的洞穴里闭关。
其实,所谓老虫子,仍是菜青虫的幼虫期,可每天不定次数从洞穴里爬进爬出、爬上爬下,通身磨出一层老茧,青虫变成了黑虫或褐虫,拥有老农民样的肤色——换个角度看,虫子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
至于醉酒的我爸,后半夜回来的,还是前半夜回来的,那天早上我妈并没有深究,也没有生气——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其实我妈就算生气,也不会停下劳作的态势。岁月渐深,我妈的心胸也随着宽广——都是被生活的棱角撑圆磨润的。因为她明白,地球不会因为她生气了就停止转动;日头也不会只把光芒洒向庄稼,不洒向野草;野草更不会从而刹住与庄稼争天夺地的野心。
一只菜青虫的卵,也酝酿着飞翔的理想,我妈——这个有着两个未成年孩子,两头半桩子猪,六亩庄稼地,三亩菜地,一个病丈夫的农村妇女,才不舍得把时间浪费在生气上,她要把作为母亲的责任化作汗水,撒入生活的汪洋,哪怕流着眼泪。
2
等我走出屋门,天快亮了。破天荒,我爸已在院里,还煮了早饭,而不是在睡回笼觉。我爸经常说,天明睡个回笼觉,年下吃个卤猪头,好酒招待好朋友,是他人生的三大快事——看似很俗套,却是有原因的。
凌晨一两点,黄金睡眠时段,我爸却像被谁下蛊,准时咔咔咳嗽一阵子。一声接一声,一阵紧一阵,打破黑夜的静谧,也震荡着脆弱的神经。墙也拦不住,咳嗽声总是令人恼火。睡得越熟,恼火的火苗越高——白天,我会感到悔恨:他是我爸呀,他也不想生病。可到了晚上,火苗照样燃烧。
我爸蹲在花池边,好像盯着一株月季冒出的新芽。花池一米见方,是我坚持用废砖头垒砌的。木本有月季,草本是指甲草和烧汤花。开始,都嫌它挡道碍事,还好它不是一条狗。不知何时,我的神经里滋生了斗士的基因。饭桌铺桌布,喝茶用杯子,上地戴个遮阳帽,现在看来顺理成章,在当时的农村,却会惹人厌烦、见笑。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爸那天的目光,格外闪烁;他高大的身躯,仿佛也变得矮小——我内心一阵慌乱,我见不得我爸这样,虽然有时我会恨他,恨他喝酒,恨他只当甩手掌柜,恨他时不时病歪歪的。可那一刻,我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谁让他是我爸呢。
平心而论,我爸对我极好,没弹过我一指头。我没出生前,有个算命的说,我爸没有闺女的命。我爸扬言,如果我还是儿子,就换个闺女去。当接生婆说我是女娃,我爸先是难以置信,再到欣喜若狂。立马买了两斤糖和一条烟,逢人就说他有闺女了。
月子中,我爸做饭洗尿片,大包大揽,不像其他月子,油瓶倒了也不扶。晚上,也要揽着我睡,怕我妈压坏我了。他似乎忘了,我妈是生了三个儿子的母亲——因为这个,我妈无数次对我说,我可以不孝顺她,但一定要孝顺我爸,就算我爸去世后,每逢提到我爸伺候月子的情分,她满脸富足,仿佛那短暂的幸福时光,轻轻松松就抵消了她一生的辛苦。
3
这个大娘,不是我亲大娘,已经出了五服。她能说会道,性子温柔,在村里属于巧女人的行列。因为她的针线茶饭、院里屋外的本事,都不逊色于人,甚至还高上半头。她会绣花,我们这里叫扎花,长短针法的花朵枝叶,跟活的一样。人也不邋遢,衣着得体——但我依然不喜欢她。因为她讲话只讲半截,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谜面专家。眼神呢,看人也要遮遮掩掩,让我想起地上缓缓爬行的蚯蚓——如果单这些,我也不会那么生厌,毕竟人与世界是多样性的。
可作为大娘的儿媳妇,腊梅就悲催了。在大娘心里,腊梅无知无觉,是木头是泥坯,干脆就是一头猪吧。当家婆这样看待腊梅,丈夫嵩岳也这么认为……渐渐地,腊梅就真成木头了。
晌午,沟边的老皂角树下是人们吃饭的集合点。沟里有风,树下阴凉,多惬意的时刻啊。大娘却端着瓷碗,两根筷子三挑两挑,长吁短叹的,碗里似乎放了毒药般难以下咽。又叹道:唉,带颜色的菜都长到你们家地里了,俺家地里光长韭菜啊。
谁说呢,你家西红柿西瓜大呢?珍珠婶子撇撇嘴。
大嫂会舍得吃?啥东西不跟金豆一样,还要卖钱呢。我妈笑着说。
大娘拾着笑了几声。接着又举着碗说:瞧瞧,瞧瞧,那女人切的韭菜,这是喂骆驼呢。
珍珠婶子和众人对下眼神说:大嫂,你就知足吧。不动手就能吃上现成饭,还抱怨个啥。换做我,嘴都能笑歪。附和声顿起。
珍珠婶子想了想,又说:大嫂,你家嵩岳官席都会做,让他教教腊梅。或者,你做。
大娘做出苦笑的样子:俺儿可不像你家大伟有耐性……恐怕教都不会,你们是不知道,那女人猪脑子呢。我做?你看咱村哪个当婆子的还做饭?唉,白瞎两丈灯芯绒咯。她丧气的模样,好像亏了一大桩买卖。
腊梅做饭不精细,刷个锅大娘也照样嫌弃。
有一次,我妈正在刷锅,大娘来了,盯着我妈捉刷子的手左看右看。
看你,刷子头尖尖的。看够了,大娘冷不忒这样说。
我妈停下刷锅,盯着手中司空见惯的高粱毛刷子,一时不明所以,如我审读着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一般。
唉,我是说,那女人刷个锅像是在犁地,每把刷子都被她戳成秃子头了。
大嫂,一个人一个做法,不算啥毛病。我妈解劝道。可接着,大娘的话,让我差点惊掉大牙,否则三十年过去,我也不会记得这么清楚。她说,一把刷子的形状,都能看出来我妈生男孩多,腊梅只会生女孩。
我妈吃惊了,沉默了。伶牙利齿的我妈,也被大娘这个荒谬的观点砸蒙了。我放下笤帚,忍不住多看这个邪恶的老女人两眼,想弄懂她究竟是哪个星球来客。
她继续挤着邪恶的眼睛说,你家的刷子毛都用散架了,还是尖头。看看,像不像那个东西?说完,还嘿嘿干笑两声。
我妈忙压低嗓子,大嫂,闺女还在这儿,看你说的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生理卫生课,老师讲过生殖系统,但不屑、气愤和羞赧,还是一齐涌进我的胸腔。于是,我满含怨恨地瞪了我妈一眼后,咣当一下摔门走了。
4
无时无刻挑腊梅的不是,成了大娘打发岁月的习惯。如果只是这样,腊梅还不算悲惨。但大娘对腊梅的恶,远远不止这些。
家暴,现在是法律所禁止的侵权行为。可在当时,在大娘这种人眼里,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正常行为。嵩岳家暴腊梅,不管是在门里,还是门外,只要他老娘解气,他伸手就扇,抬腿就踹。
面对穷凶极恶的男人,腊梅像猪狗一样在地上翻滚,哑巴一样哭号。看到有人来,大娘忙拦住嵩岳,说:看看,打成这都不会服个软,挨死打的东西啊。你都不会起来跑?换谁谁不气,不打你打谁?可私下里,大家都知道大娘的秉性,她经常教育儿子说:打,狠狠打!媳妇就是墙上泥皮手上垢甲,该搓搓,该揉揉。
在嵩岳母子的揉搓下,腊梅越发木头。走路像木头,干活像木头,连眼神也像木头。
除了拉架和背地里同情腊梅,作为外人,明面上没人会深管这种事情。出于生存等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多数人只会拂去自家门前雪,而旁人的瓦上霜,则有心无力,或者有力无心。从这个层面讲,人类的世界是悲哀的,人性也是残忍的。
如果,腊梅的人生还有人温暖,那人就是小静,腊梅的小女儿。小静属虎,比我大一岁,她的两个姐姐,受奶奶的教唆,从小就疏离腊梅,也管腊梅叫那女人,从不叫一声妈。
我去小静家串门,腊梅总在干活,动作迟缓,一声不吭。老巫婆倚在门槛上,或者坐在当院,监工似的。我去过腊梅的卧室——西院的一孔窑洞。窑洞幽深,半截打着一道土坯隔断。腊梅和小静睡在外间一张床上,里面没去过,太黑了,一股泥土的腥潮气。
床铺很简单,一张素色大布单子,平整得像张铁皮。床头是张黑漆(也许是枣红色)的桌子,上面一把木梳,一个红塑料边的圆镜和一瓶花。不,不是花瓶,准确说是豁鼻儿的粗瓷罐,每家每户都有的粗瓷盐罐,花是满沟渠的淡蓝色的马兰花。它的存在,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它们就像一幅画,一束阳光,让我原本感到压抑的心情倏地轻松了很多。小静说,这是她妈放的。
5
我妈教导我,做事认真,做人不要太认真;与人相处,多看长处——这些话是对的。可当时,她是在劝我不要和大娘撕破脸,我内心是抵触的。
客观说,大娘也有长处。我家男孩子多,衣帽鞋袜都费。我妈忙不过来,大娘也会帮忙上个鞋帮子,纳个鞋底什么的。
再个我爸身体不好,常年卧床,饮食上需要将养,鸡蛋奶粉的离不了。隔三差五的,我家的三斗桌上会放着半盆白鸡蛋,一看都不是我家母鸡生的,我家母鸡品种是骆驼红,生的是红皮鸡蛋。
鸡蛋是大娘送来的,我心里隐约感觉不妥,她都不能趁我妈在家时再来送吗?那阵子,我爸犯病,一直卧床不起,地里的活计全靠我妈早出晚归地收拾。特别第一次看见大娘坐在我家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和我爸说话,我头皮突地震了一下,大娘的神情看似寻常,我却感觉多少有些不自在的成分在里面。我妈却说,小孩子家别那么多心眼,大娘是咱一家子的骨肉。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于是便笃定我妈是被大娘这些恩惠收买了。

当嵩岳的大女婿想在我们村落户遇到阻力时,大娘对我家越发亲厚,不,对我爸。她不管我妈在不在家,要么拎着半斤鸡蛋糕,要么八两芝麻酥饼就来了,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虽然她也明白,这件事非常棘手,因为它看似合法,却不符我们村的民情。
我们村紧挨着市区和公路,粮食地菜地都是水浇地,属于“好地区”。耕地三十年不动的政策没出来前,村里每年添丁进口的家庭,就指望着谁家闺女嫁出去,好接盘腾出来的土地。独生女的家庭,上门女婿落户进村,旁人无可厚非。嵩岳三个闺女呢,一旦开了这个头,势必搅乱了村子的秩序。
按理,我爸一不是村长,二不是乡长,可在他的诸多朋友里,虽然白丁居多,却也不乏“鸿儒”——指的是端着铁饭碗的人。我爸念过初中,算得上农村文化人。那时,没有手机和网络,可神奇的是,尤其在大雪纷飞时候,总有朋友来和我爸温酒叙话。就好像,落雪就是他们的秘密暗号一样。有时候,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朋友的朋友,都是朋友。一碗咸菜,一碗腌萝卜丝,一瓶白酒也能从早喝到晚——尽管很痛恨我爸喝酒,但我现在非常怀念那些日子。
大娘家和我家一墙之隔,一点动静她都能听见。她貌似做着针线,耳朵却也支棱着,听着上房屋男人们爽朗的谈笑声,她会说,瞧,俺兄弟多有本事,认识这么多有本事的朋友——口气满是羡慕。我妈微笑着,并不接话。
唉,俺那人如果在世,朋友也多哩——大娘继续叹息。那人,是大娘的丈夫,死得很早。生前是大商号的掌柜,常年走南闯北。我爸评价他,精明不失豁达,豁达不失儒雅,若不是命短,一定是个大生意家。
娶了大娘后,大伯依然常年在外——其实,我爸只比嵩岳大四岁,有关大伯的事情,多数也是听族人说的。可我爸说,他见过大伯,很体面,很有风度,待人也亲。大伯死在天津客栈的时候,三十还不到。商行来信说,他晚上肚子疼,天明就死了。
那时,大娘刚满十九,儿子嵩岳也才一岁,满打满算,她和丈夫就没见过几回面。大伯的后事,是本家一个兄弟去天津料理的。嵩岳十六岁时,大娘让他和本家叔叔把大伯的遗骨背了回来。她说,活着孤着也就罢了,死后再不能孤零零了……可惜,大娘的不幸离我太过遥远,并不能够抵消我对她的厌恶。
6
虽然不清楚我爸遇到了什么难处,可一听去大娘家,心里还是有点犹豫。
我最后一次去大娘家,是个后半晌,小静喊我去看《哑巴新娘》。床沿还没暖热,电视屏幕翻个白眼,咯嗒一声,灭了。不晌不夜,怎么停电了?我发着牢骚。小静努努嘴,指指窗外,一个黑影猫样溜了过去。
我脸庞发热,嗓子眼堵了一团棉花,还感觉心被什么东西扎了几下。黑衣黑裤的大娘正在院中央摘花椒。她一副不怕鬼敲门的模样,居然还能笑眯眯地说,没事常来啊——好像电闸是我拉的。哪个兔崽子吃饱了才来你家——我对着那扇黑漆木门说。
终于,我走出家门,去给父亲送信。此时的日头,还红着脸躲在树梢后面。树木枝青叶绿的,散发着清新的草木气息。鸡鸣,狗叫,鸟啼,绞水的辘轳声,都和往日早晨无二。远处洼地里,人影晃动;近处,花婶迎面走来。我一阵心跳,好像她洞察我的去向,耳根紧随着也发烫了。她看我一眼,干啥去?目光带着问号,似乎还长了刺。我……去地里找我妈——多机智的搭话啊。然而,花婶挑着担子早已走远。
大娘家的大门,仍然紧闭。门板上的春联残破不堪,看不出一点红气。
透过门缝的目光,被花椒树繁盛的枝叶阻挡住了。大门到后窑有二十几米,花椒树就像一堵迎门墙。推门、进去,看似简单,手脚却被什么东西黏着。煮猪食的味道越发浓厚,咣当咣当像是擀面的声响沉闷不堪。
当我硬着头皮推开门,西墙角那窝鸡狗样狂吠,震得头皮发麻。后窑门西边大锅台旁,腊梅在烧猪食。火膛塞满柴火,她仍在见缝插针。腊梅瞟我一眼,没说话。
整个院子,笼罩在聚拢又散开的烟雾里。窑洞里也灌进去不少,像一条幽蓝神秘的隧道。咳嗽的人是大娘,是她在擀面。她套着灰色大布衫的身子,一前一后,一前一后,随着擀面杖的远近忽闪着。看不清她的脸色。反而是腊梅,脸庞和眼睛许是被烟熏火燎的,带了颜色。乍看腊梅,与昨日无二,但整个人的气场显然不是昨天的腊梅,周身散发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意味。那种气息,我能捕捉到,却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晰。我正为难,嵩岳哥从偏院出来了,我迎着他的目光,可他只是张张嘴,却没吐出一个字,扛着屋檐下的锄头,咚咚出了门。
那个清早,我见识到了自己的厚脸皮,大娘家没有一个人待见我,可我感觉使命没有完成,不能走!见我磨蹭着,大娘叹口气说,回去吧,啥事没有,昨儿你爸就是喝多了,来家里喝了一碗水。哦,我松了一口气,可耳边却传来腊梅一声刺耳的冷笑声。我的心脏被腊梅的冷笑刺激得猛然一缩,仿佛一块石头,缓缓落入了冰冷的河中。
我在腊梅身边蹲下身子,捡起一根干柴投入灶膛。腊梅慢悠悠对我说,回去告诉俺叔,觉也睡过了,抓紧办事……这人,我爸睡觉不睡觉,关她啥事。
7
那天回来,我爸依旧蹲在花池边上。地上好几个烟头,和他一起在等我。
听完我在大娘家的“侦查”结果,我爸乌黑紧锁的眉头越发拧作一团,他低头不语,攥着一个烟头,在地上来回划动。乌黑的划痕,像是一堆谁也解不开的密码,更像是他懊恼不堪的心情。
爸,你是不是搞错了?纸条上一个字也没有,我谁也没给——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果然是我爸搞错了,我爸说的。
大约十点来钟,我妈捉虫归来,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嵩岳的小叔,一个是大娘的娘家兄弟,他们关着门,像是在开一个秘密会议。我在院子里,先是听见我妈压低嗓子,不紧不慢说了好半天话。最后才听见嵩岳小叔说,婶子,我清楚了,从此以后,咱还是一家人……
送走众人后,我爸神情落寞,我妈不悲不喜,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但我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没两天,嵩岳大女婿落户的事情最终尘埃落定——这是我爸的功劳。
也许,有了女婿撑腰,腊梅的家庭地位陡然提高了不少,敢人前人后说大娘的不是,敢公开喊丈夫的名字。
而大娘,开始变得唯唯诺诺,不再人前人后数落腊梅的不是,就连她想摸摸重孙子的脸蛋也不行——腊梅不让,冷着脸说她的手不干净。嵩岳就在一旁,看到老娘受了委屈,居然也不再吭气,而是催促大娘回家去吧。渐渐地,除了佝偻着身子、拎着猪食桶出来喂猪,大娘便不常出门了,活成了一只老孤鹰。
从此,大娘家和我家的关系,像是隔了一道无形的篱笆。小静偶然来找我一次,也跟做贼似的……直到现在,我爸让我送“信”的事,我一字没向母亲提起,好多次我想张嘴,可迎着我妈浑浊但仿佛能够看透一切世俗的目光,又觉得一切尽在不言中,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