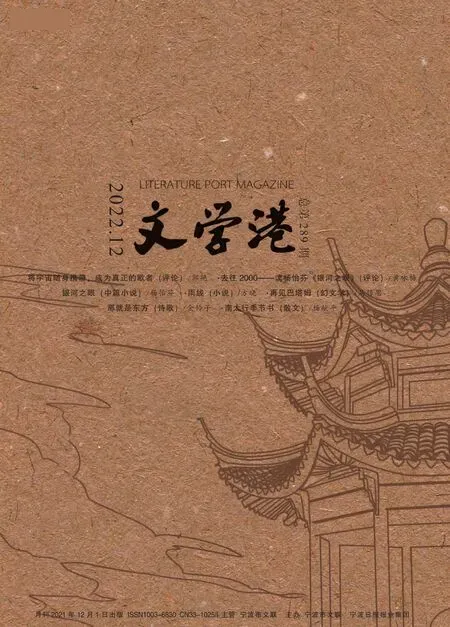抲蛇佬(外二题)
□老 筒
我们那一带的人都说:好人不在世。村里的抲蛇佬死的时候,他们也如是说。
我并不知道抲蛇佬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那时我刚初中毕业,不大谙世事,有点懵懂。只是当我挑大粪上坡的时候,有一次碰到抲蛇佬,他见我吃力难上,二话没说,帮我挑到了岭头。当时我确是从心底里感激他。据村上的人说,这样的事,抲蛇佬是常在那里做着的。
抲蛇佬其实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诗文。这似乎和他的农民身份有点沾不上边,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因为他根本不懂这名字的本质含义,斗大的字他还认不得一箩呢。当他还在娘肚子里寄生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名字是谁取的,周围的人当然更无从得知了。诗文从小到大活得很苦,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好不容易混上个媳妇,接下来的三年给他生下了三个蝌蚪似的男孩,使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生活更加艰难。妻子在家烧烧饭、带带孩子。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人的衣裤尚勉强可以遮体,孩子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光腚的日子占其大半。冬天到时才从邻居家要一点破衣烂裤,稍微缝补一下,给孩子挡一挡严寒。所幸的是他家还有一间祖上留下来的破屋,为一家人遮风挡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我们村那满地爬着的大蛇变得值钱了,蛇毒和蛇胆均可入药,尤其那能致人死命的蛇毒,更是名贵无比,和黄金一般值钱。只是乡亲们对这被称之为长虫的大蛇的惧怕与生俱来,提起它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相遇于道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将其打死。没有人会想到去抓它来换取谋生的票子,也不敢去抓。只有诗文是穷极无怕,认准这是一条能够改变家庭境况,使全家人有饭吃的捷径。于是,他在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之余(当时的生产队是不允许擅自缺工的),拿着编织袋,出没于荒坟野地之间,干起了抲蛇的行当。这抲蛇的活是冒险的,社员们戏称之“拿生命开玩笑”。一次,诗文在抲一条蕲蛇时,不慎大拇指被咬,他深知这种蛇的厉害,毫不犹豫地用刀削去了大拇指。诗文虽然失去了大拇指,但迫于生计,他仍然乐此不疲,只是抲蛇时比以前更加小心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被大蛇咬过。他的家境渐见好转,由村里的赤贫户变为中等,老婆孩子的衣着也一天比一天光鲜,只是诗文的衣着依然如旧,披一件缀满补丁的上衣,终日在山野间晃荡,为生计而奔波。
久而久之,诗文的大名在乡亲中没见人叫了,取而代之的是“抲蛇佬”的称呼。这倒也名符其实,诗文的家里摆满铁丝做的笼子,里面关满了大蛇,等待蛇贩子上门收购。
岁月悠悠,世事实难预料。当我真诚地为诗文祝福时,他却意外地死了。而且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死。那是一个夏天,夏至过后的第二天中午,我利用午休时间去自留地为番薯锄草。路过一个蓄水库,见诗文和他生产队上的二十来个社员坐在水库前的柏树荫下乘凉闲谈,我便也参与其中。这天出奇地闷热,没有一丝风,树上知了的声声鸣叫,更衬出这夏日的难熬。社员们在天南海北、鸡毛蒜皮地神聊后,话题便扯到了眼前的水库上。这是一个不大的水库,严格地说,是蓄水池,因为没有地下水或山水纳入它的怀抱,它全部的积水是靠抽水机从一公里外的溪塘里抽水送入水池,以备天旱时灌田。因此,池水不是很深,最深处也只有五米左右。在水库的南边角上,从西岸到东岸,各有一株小柏树,相距约有三米。话题便是从此开始的,悲剧也由此发端。不知谁开的头,说是两株小柏树间有多少距离,不会游泳的人能不能由水上从这株柏树到达那株柏树。议论者自然分成两派,一方的人说,这一点点距离准行,另一方的人则说,不会游泳的人肯定不行。诗文不会游泳,但他坚信凭着自己一米八的个头,结实的身体,当然能够横渡这不起眼的三米。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于是,有人提议打赌。立即,争论双方各跳出一人。响应的一方当然是诗文。赌注是一包新安江香烟。当时的一包新安江香烟,只要二角四分钱,差一点的大红鹰只要一角三分钱,好一点的上游是三角六分钱。最好的要数牡丹烟了,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工资三十三,香烟吃牡丹。”诗文是没福气抽牡丹烟的,连新安江他也只抽过一支,还是人家送给他,他不舍得一次抽完,抽了三次,烟蒂也没有丢掉,放在旱烟锅上再抽。他一般只抽旱烟叶,有时嘴馋又遇兜里有几角钱,便买包大红鹰香烟来过过瘾。这次见有一包新安江可得,加上诗文又天生胆大,他便义无反顾地应战了。当他扑向水库时,便走向了死亡。没有人阻止,包括诗文自己在内,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将会是一个悲剧。很多人相信诗文自己的话:我人这么长,一扑就过去了大半,再划几下就可以拽住对面的小柏树。一包新安江香烟笃定赢得了。就没有人会想到过不去将会怎样。
悲剧就此发生。诗文下水后只扑腾了一下就不见了。没有人敢下去救诗文,他长得五大三粗,像座铁塔,都说即使用榔头敲也很难敲死诗文。而生产队里几个特别会水的人当时都不在现场,二十几号人眼巴巴地看着诗文不再浮上来。当附近的做瓦老师拿着长竹竿准备搭救诗文,机会已不再出现。
诗文就这样去了,仅仅一包新安江香烟,二角四分钱。愚昧?无知?看着他的尸体,我的心里酸酸的,悲凉感顷刻袭满全身。
三年后我考上中专,离开了家乡。在我求学的日子里,大哥来信时顺便告诉我,诗文的妻子改嫁到他乡去了,带着三个男孩。我想这是必然的结果,那种酸酸的感觉仍然浮上来,只是淡了些。
学校毕业后,我天南地北地闯荡,领略了太多的世态炎凉,然后是娶妻生子,平庸地一直活到了现在。渐渐地已将诗文淡忘。今年清明,在回家祭扫了父母的坟墓之后,我忽然想起了诗文。大哥将我领到诗文的埋葬地,他的坟只是一个土包,没有墓碑,茅草高高地长着,荒荒的,很久没有人上坟的样子。他的妻儿不知身在何方?村里又有几人能记得有一个叫诗文的抲蛇人呢?人生大抵便是如此了!
剃头老师
“自己的头由别人来剃”,这已是常识,这句话也已流传久远。然而,偏偏有这样一位剃头老师,自己给自己系了个解不开的死结,出了个令他自己及世人都难以解决的难题。
这个剃头老师剃了多年的头,手艺娴熟,生意奇好,门庭若市。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在店门口做了这样一则广告:我给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而且只给这些人理发。一个来剃头的看了广告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那你自己的头发谁来给你剃呢?剃头老师给问住了。因为,从广告的内容来看,这位剃头老师的头发既不能由他自己来理,也不能被其他任何人来理了。而头发是终归要剃的,这就难住了。这则广告也成了逻辑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悖论。
当然,我家乡的剃头老师们还没有聪明到或者愚蠢到写这样的一则广告来为难自己,同时也为难别人。他们只知一门心思地剃头,赚钱来养家糊口。计划经济时代,小镇上的剃头老师单独开店的不多,大都集合在一起,共同开店,类似合作商店。一溜剃头椅排在那里,等待顾客的到来。至于顾客找谁给他剃头,那是顾客的事,以至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些手艺好一些的剃头老师身边常常围满了人,门庭若市,有些顾客情愿等上一两个小时也不愿意叫那些他们认为手艺不大好的剃头老师剃自己的头。而那些技不如人的剃头老师,座椅前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他们也只有坐在那里清嬉了。可见,大家对自己的头还是挺看重的。难怪人们常说,剃头老师的行当是“顶上”功夫。生意如此悬殊,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分红的。
顾客可以自由选择剃头老师,而剃头老师也很会看人下菜,当他对你看不顺眼,或者你不是小镇的重要人物,便不会很认真很仔细地给你剃,草草了事。那么,你的头便不会被修理得光洁,在剃好的头上,常常这里那里地突兀出一撮撮毛来,弄得你很尴尬。
痊愈为NIHSS评分减少≥90%,脑电图正常;显效为90%>NIHSS评分减少≥50%,脑电图显著改善;有效为49%>NIHSS分恢复≥15%,脑电图有所好转;无效为以上指标均未满足。
在我懂事的时候,我们乡下就不大看得到担着剃头挑子上门剃头的剃头老师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距小镇不远的山村里的一个剃头老师。乡人们称他为“王大寿”,他的真名则无人知晓,我想,这样一个充满贬意的称呼,总不会是他的真名吧。此人有点有趣,在我们乡下是个名人,提起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他有间发性神经病(我们乡下称精神病为神经病)。不发病的时候,他可以把你的头剃得好好的,而且手艺也不赖。发病时,那你就惨了。往往剃到一半或三分之二时,他会突然收拾剃头工具,说是今天有事,先剃到这里,下次再来给你剃完。说走就走,弄得你哭笑不得,最后只好戴上一顶帽子或包上一块手巾,到剃头店央求别的师傅把头剃完。求剃这半拉子头,还得看人脸色。
起先,还有人请王大寿剃头,因为他的收费比剃头店便宜,一般剃一个头不会超过一角钱,而且是上门服务,又方便。乡人们贪便宜,图方便,王大寿的生意也好过一阵子。但随着尴尬事的不断发生,上下三村便再也没有人请王大寿剃头了。王大寿却总是担着剃头挑子,终年走街串巷,也不管有没有生意。真不知他是用什么来谋生的。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却很难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仪表是越来越注重了,以至于理发行业空前发达。现在,不管是城镇还是乡下,理发店、美容美发店,如雨后的春笋,遍地是。只是,面对如此众多的店铺,我们无所适从了,不敢轻易地走进一个剃头店。多数的剃头店,名曰美容美发,实则连一个完整的头也剃不下来,又何谈美发。
走笔至此,倒怀念起挂着“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对联的剃头店来。胆敢挂出这样对联的剃头老师,其手艺一定了得。因为,剃头毕竟是“顶上”功夫呵。
盐菜花
不知盐菜花还在不在人世?我已好久没有回故乡了,物是人非,沧海桑田,老乡故人在不断地故去,偶尔回去,熟面孔越来越少,陌生面孔在蓬勃地多起来,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天真的青少年竟将我这个“反认它乡作故乡”的本地人当作了他乡客,让我“近乡情更怯”啊。
和所有人一样,我的故乡情结始终不解。故乡的人人物物,是是非非,山山水水,始终萦回在我的脑中。我的情感小船始终泊于故乡这处港湾,那里有我前行的航道。在这个前行的征途中,故乡人始终陪伴着我。当我静下心来,会常常想起他们。一切好好坏坏,恩恩怨怨,都灰飞烟灭,化作一泓清澈的春水。
侄儿从老家来,告知我盐菜花尚在人世,虽然老态龙钟,却很能吃饭,她的丈夫也活得很滋润,只是实在太老了,已不再操扛棺材的生计。对于一生扛棺材的老棒来说,能割舍这一营生,肯定是力不从心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国人普遍生计艰难,我的老乡也不例外,一年总有几个月吃不饱饭。因此,盐菜花的老公老棒扛棺材的营生,就很让人眼红。但眼红归眼红,没有人会去抢老棒的饭碗,毕竟和死人打交道,不但不干净,还不吉利。因此,尽管扛棺材可以吃到猪头肉,喝喝老酒,用乡人的话说是“吃香的喝辣的”,但不到万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扛棺材的。扛棺材就这样成了老棒等少数几个人的专利。
盐菜花家的境况不好,按当时的标准看,也算得上是赤贫。她家人口众多,上有老,下有少,儿子女儿一大堆,光填满一家十来人的嘴巴,就很难。再加上盐菜花是一个不会算计不会持家的女人,不知道过日子也是要有计划的,要搞综合平衡,不晓得忙时吃干的,闲时喝稀的,粮不够瓜菜代。她是有钱即花,有饭就吃,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日难不难。兜里有钱,她不会留到明天,原本不多的粮食,她也不会匀着吃,而是狠吃猛吃,半年便将全年的粮食吃光。她家的日子就过得一塌糊涂,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饿肚子的日子有的是,只好东借西挪,凑合着过。好在乡邻们善良,看她家过得不像样,劝说无效之后,也只好由她去了。不忍心的时候,就送一点吃的,拿几件破衣服给她,聊作救济。全赖乡邻们的好心,盐菜花一家人才不至饿死。而盐菜花则依然我行我素,一点教训也不吸取。
沾老公的光,盐菜花一家人也经常吃香的喝辣的,尤其是死人多的日子,她家的生活就像过年了。老家的习俗,扛棺材佬自己在丧宴上吃饱喝足后,可以用塑料袋装一些吃剩的猪头肉之类的菜带回家。除这一点外快,丧家通常还要给些劳务费。当然,这为数不多的劳务费,老棒是不能装入自己的口袋,要全数上交生产队,再由队里折算成工分给老棒。而老棒也会耍一点小聪明,千方百计地留点钱给自己买老酒喝,以不辜负带回来的猪头肉。
在这样的时候,盐菜花一家人的嘴巴便会油光光的,脸上也不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愁眉苦脸的颜色。
乡邻们为老棒可惜。按理说,扛棺材的营生,老棒一家人的生活会过得比一般人滋润,由于讨了盐菜花这样不会过日子的老婆,一家人的日子便过得难以为继。而老棒是不管家事的,他是只管喝酒,偶尔遇有死人,就配上点猪头肉。若是无菜可配,便淡酒也喝。除非兜里无钱。而他经常是无钱的日子居多。可惜归可惜,又有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扛棺材的?哪怕子弟再优秀,毕竟名声不好听啊。况且优秀的子弟是不会去扛棺材的。得出的结论是,老棒只能讨到盐菜花这样的老婆。这样说来,老棒还是幸运的,和老棒一道扛棺材的还都是光棍呢。
尽管盐菜花不会过日子,还邋里邋遢,但她吉人自有天相,身体是出奇的健康,生儿育女的本领不错,为老棒接二连三地生养了一大堆的儿女,使得老棒家人丁十分兴旺,也使老棒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儿女总是父母亲的希望之光。
自从盐菜花嫁到了我们村以后,乡邻们时常会拿盐菜花家和那些原本家境并不好,讨了贤惠能干的媳妇后日子逐渐红火起来的人家比,深感媳妇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选择儿媳时便分外挑剔,将能不能持家过日子作为第一标准,由此也打散好多对忠贞不渝的恋人,悲剧也发生过。但乡邻们不管,乡邻们是务实的,他们把居家过日子作为第一要务。不会过日子的媳妇只是花瓶,中看不中用。
也许人的福分是天定的。尽管乡邻们有些鄙视盐菜花,但盐菜花老来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可以。据说,盐菜花的几个儿女都比较争气,通过自己的努力,发了点小财,小日子过得很红火。可能是小时候的苦日子给他们的烙印太深了,使得他们从小懂得人生是必须靠自己谋划的,得过且过便没有好日子过,天上若掉馅饼,还要起早去接呢。
儿女日子好过了,当然不会忘记生养他们的父母。盐菜花和她的老公老棒过着吃用不愁的日子,纵使她再不会筹划,也有儿女们供着,用不着她来愁心。
只是,人们见到她时,她总是一如既往,一副老样子,邋里邋遢的,没有干净的时候。也许她已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