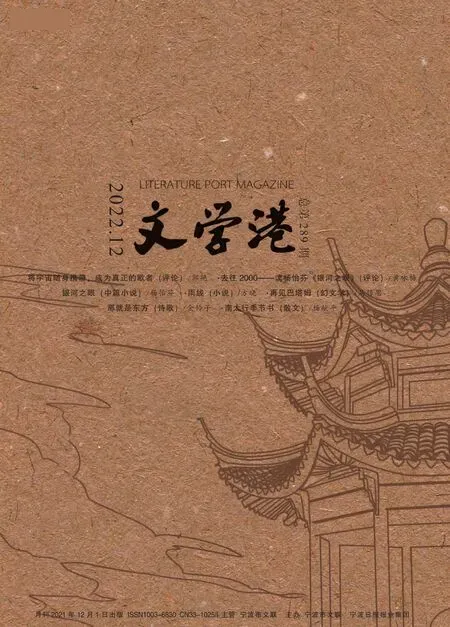梦见鸟(组诗)
□姚辉
蚂蚁
骤雨前 整条大路
都在关注蚂蚁基金会的
系列活动
黑蚁聚集在大风
南侧 它们分享过
黑夜亘古不变的深度
在历史淤积地带
它们曾找到各类涉及恨
与承诺的汛期
它们不只代表一种群体性
祝愿或救赎 再没有比
救赎更为深刻的
祝愿了……一只试图
展翅的白蚁 又将抖落谁
梦境之外的习俗?
还有许多事项被捆扎在
基金会边缘 成为
一种栅栏式业务
蓝色蚂蚁仍在梳理这类
业务 它们想返回到
风与道路交织的
光芒中 它们正在构建
抵御骤雨的程序
大量黄色蚂蚁仍滞留在
雨滴弧形的魂魄中
说到系列活动 你不该
忽略由一万零三只
蚂蚁嵌成的宏大
缄默仪式
一只赤蚁缓缓退开
它将带走基金会
仍在限制的某种
钙化功能
海
如何保持海的单调性?
三个饮酒的人数着
晕眩的礁石
他们以为自己还留在
多年前的教室中 提问
等待回答 老师在黑板上
写字 大海吱吱嘎嘎
别擦拭那些潦草的字迹
风也在点数礁石
礁石 礁石 礁石
一个破碎的酒杯改变了
海的弧度……
三个很难沉醉的人
想瓜分千古潮汐 你
从教鞭横斜的浅影中涌出
你旁边流着热泪歌唱的
人即将属于海
不倦的承诺
海在渴望什么?酒
是日月的平方还是某个
错字旖旎的偏旁?
海 蜷入杯盏底部
它试得出所有
让人不安而又乐于
期待的坎坷
海想用你和另外
两片晃动的身影抟制
千种繁复的醉意
梦见鸟
一只红鸟 占据
梦境的左下角
它不鸣叫 它一下又
一下啄多余的
太阳
树是丝绸的
在上个时刻它们是
铁质的 旋舞的树上
聚着一群黑鸟
它们在坚持鸣叫
一只白鸟传递
山与时间不变的使命
它飞得较慢 它
努力保持着与太阳
较劲的距离——
某些喜鹊的位置比较固定
它只能成为你苦乐
最切实的证词
那只蓝色鸟披挂着我
颤抖的影子 它也可能是
第五种时辰之后的
我 它把我三年
之前的追缅交给天空
它代表了我最为
怯懦的诚意
而鹰是石刻的 它
即将成为大地坚固的
铭文 它想用
一己之痛 替换梦想者
随风起伏的缄默
鹤与桥墩
鹤仍在嘲笑大家建桥的念头
“开工多少年了?这桥墩
依旧像一种半成品式预感
——你看那流水上
遍布的钢铁网格
坚硬又凌乱。”
“岸与岸是一种对比
流水已被毛羽界定过多次
这绝不仅是我的毛羽
燕雀与鹰 也试图
搭建出此岸成为彼岸的
各种可能性。”
鹤在浮荡的木板上
眺望 它啄开桥墩之暗
将大量晨光
倾倒在我与你们
战栗的灵肉间
“钢铁发芽 我肯定钢铁
会发芽 泛绿的钢铁
让河忘记了喘息”
一个沉默的人误将赞美
抛在旭日拍打的桥墩
夹缝中
鹤还将说出什么?鹤从
天穹掰下一片彤云
它退回到黎明命定的
阴影内侧 桥墩
开始微微颤栗
故地
你肯定认不出那个临河
栽种还魂草的人
他黝黑。四十年前的
黎明有没有此刻重要?
风从河底翻出你
淤积的脚印 他将
一部分脚印掺进土层中
他继续着看似与你
毫不相干的种植
河还是那条河 想过改道
想过用颂辞抬高墨绿的
波澜 但河只能
这样流淌 它的流量
维系着四十年前
甚至四百多年前那片
晨光既定的深度
我不敢询问栽种者的
姓名 他从土块与
骤雨的耦合中
获取夙愿 我怕他与我
可能存在的三十种
身影重合——
遗忘为何变得严肃?
我还能遗忘什么?刻在
砖墙上的星已然泛黑
那以还魂草的梦境
修饰堤岸的人默默抬起头来
他 突然认出了
逐风而来的你
洗马滩
觅虹的人站在滩头
好像那虹仍
游离于他的想法
而流水中的虹影曾在
上个黄昏化为石片
虹 有些胆怯
它怕错过觅虹者
哽咽的手势
熟悉的河滩 一百年前
是一句滚动的谚语
有人在删减水浪
有人将某个家族的痛
写成天穹虬曲之蓝
有人抵达虹预设的多重
警示 一匹赤红的马
融入河的爱憎 虹
被架设在史书与
马的肩胛上 觅虹者于
彼时此地老去
洗马磨剑的人将
逐渐替换旌旗上的霜痕
水试图归还一部分
刻骨的期盼
请为觅虹者铺展出
另外的坦途 字丛中
闪耀的虹 业已习惯了马
与波涛蜿蜒的追忆
河
喧闹之城 河是
一种自愿弯曲的背景
河 在适当控制
自己的辽阔
我遇到的波浪即将
成为往事
河让一座城市活着
并不断拂拭描金的
各类污垢
河记得大量星辰对
未来的臆想
星辰试图超越
什么?这么多星辰已
进入大河的履历
泅渡的人变成一个
值得摹写的符号
他 那么苍老
他半裸的灵魂让孩子
躲开了追忆
此刻的河又将大把
黄昏搁在船舷上
而我不追忆
我让河的光芒再次
变得灰暗
鸟儿问答
在夏天的蓝底板上
出题——
问:翅膀为什么疼痛?
先别忙着回答
先试试你是否还有值得
疼痛的翅翼
有人会抽暇替你回答
鸟 尖喙剥啄黎明
鸟给予黎明以
最大的质询
——天穹为何弯曲?
大概还是因为靠近王位与
各类钙化信仰
丰腴的躯体中部有一种
瑟缩的欲望么?
——有的那肯定是有的
那就让它完美地毁灭
史册或许不止
容纳过三种覆巢
它 还将容纳什么?
它容纳骨头
持续延展的奇迹
噙着树枝飞翔又能象征
什么?象征是
一种策略 所有象征
都是大鸟从腿部筛落的
皮屑与痛——
把一种飞翔完善到极致
又该怎样颠覆红妆
女人满溢的幻想?
——为什么要去颠覆?
为什么不可以否定这样的
颠覆?颠覆的时辰
已然逝去
尾翎上有大捆
粗壮的盛夏 A鸟的
欲望 仍然会
漫无边际么?
B鸟猝然代替A鸟
我不对你黑色和其他
华丽的欲望负责
良药
所幸目前能接触到的
均为良药
压低疼痛的势头
让魑魅从自身正反面
抽离光焰 而且也
肯定有一粒药丸会携你
跃出梦境嘶哑的
隔绝层底部
当黄连成就的荣耀曳动
某种浅黄色花序
谁必须凭借大量药片
区分痛苦的真伪?
在耻骨和风的
痛苦之间 可能仍
存在着各类脱敏式警示
而一部灰色仪器
该怎样不断强化这些
苦痛的合理性?黄昏的
处方黎明同样适用
多少庄严的盲目者掌握着
救赎的全部隐秘
如果唯一的药效仍然
来自你沉睡的父亲
请迅速调换
龙与黑鸦近似的呓语
请以父亲的指纹为参照
甄别灵与肉各自
坚守的主义
那种柱状药性必将
触及云的许诺
及早期善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