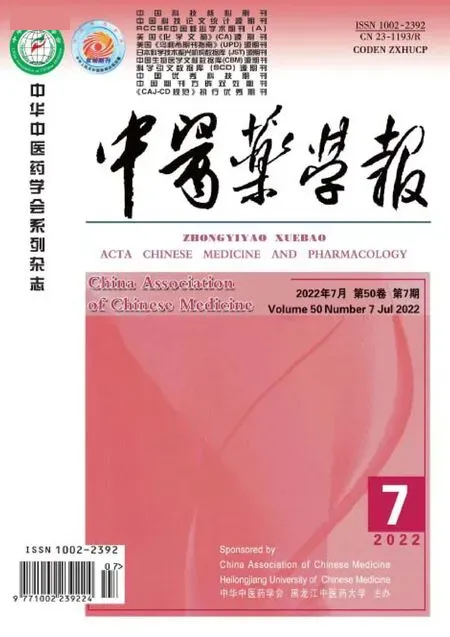从“五脏相通”理论试论高血压治疗
许力文,焦华琛
(1.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高血压在中医学中被归属为“眩晕病”范畴。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眩晕病的记载,认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因而在现代中医学研究中,多数医家将高血压的发病与肝脏相联系,通过肝脏的生理功能论治高血压疾病。然而单纯通过辨肝的阴阳偏实偏虚,选用平肝或补肝的治法治疗高血压,疗效差强人意。近年来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提出新的诊疗思路,即“五脏相通”理论,认为五脏为相通的整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均可犯及五脏,该思想被用于高血压病的治疗,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本文试从“五脏相通”理论论述高血压的治疗。
1 五脏相通理论的源流
1.1 《内经》从五行论五脏相通
五脏相通理论起源于《内经》,主要从五行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五脏归属五行,又通过解释五行的生克乘侮来对五脏相通理论进行说明。
五行相生是五脏相通理论的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论述:“东方生风,风生木……肝生津,筋生心,肝主目……肾生骨髓,髓生肝。”即从五行角度来看,五脏之气相互输送,相互交通,组成循环的整体,五脏气机调畅,脏气流转不息,则五脏功能调达,于人体各司其职,互不相犯。明代医家吴昆提出:“五脏之气相通,其脏气输移,皆有次序”[1],亦说明了五脏之气循环相通的理论。
五脏相克是五脏相通的病理基础。《素问·五脏生成论》云:“心之和、脉也……其主肾也……肾之合、骨也……其主脾也”,此处之“主”,张仲景解释为制约之意,说明五脏间存在相互克制的关系,亦可解释为五行中“所胜”与“所不胜”的关系。《素问·玉机真脏论》:“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则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则死。”明代马莳注为:“受气者,受病气也”。认为五脏相互克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病理条件下,五脏所受病理邪气,有所受,有所传,有所舍,有所死,始于我所生,终于克我也。究其本质,在病理上,五脏之气的相通理论也根基于五行理论。
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五脏之间生克制化的关系均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任一脏均不为独立的个体,高血压病的病位主在肝肾,同时与肺、脾、心均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理论也是基于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提出的。
1.2 张仲景“五脏病”理论阐释了五脏的疾病传变规律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创立“五脏病”理论,用以解释病理情况下脏气相通的理论,同时说明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各脏腑之间存在的传变演化规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五脏病各有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论证了疾病发生时脏气的输移传变,邪气不单只犯一脏,各脏腑相通,有所喜恶,故疾病病程中表现为不同的脏腑证候,同时,张仲景根据五脏之气相通的特点,基于五行生克的规律,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即“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为后世治未病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疾病发生之初,病程进展之时,根据五脏之气的相通、相生、相克来施治,是现代“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理论的核心。陈伯坛解释为:“五脏各有所失者病,各有所得者愈。”究其本质,无论是“五脏病”还是“治未病”,这二者均为“五脏相通”理论的延伸,是根据《素问·玉机真脏论》中“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的理论提炼出来的。
1.3 刘完素“五运主病”理论
金元时期,刘完素提出“五运主病”学说,是通过五运来概括分析五脏的疾病[2]。其理论来源为《内经》的病机十九条,在此基础之上,又加入各脏相对应的五运,即木、火、土、金、水,如“五运主病,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寒收引,皆属肾水”[2],这一学说弥补了原病机十九条归类简单且疾病不全的弊端,并从“五运”的角度阐述五脏之间的联系。
刘完素认为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心火所致,故肝风掉眩之证,非肝独病,与肺、心二脏亦关系密切;至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刘完素认为依据五行之理,心为火脏,微热则痒,热甚乃痛,五行相克,一行过极则胜己者反来制之,故火热过极,则反兼水化。强调了五行之间相克的相互关系,在五脏中多表现为心火与肾水的相互关系。至于风胜湿,湿自土生,脾盛治之以燥则体现了脾脏与肝肺的关系。
1.4 “五脏旁通说”与“五脏穿凿论”
“五脏旁通说”首见于孙思邈的《五脏旁通明鉴图》。根据《中国医籍考》记载,早在唐宋年间,就有关于“五脏旁通说”理论的记载,但均已亡佚,所以后代医家研究“五脏旁通说”,多从《素问·调经论》中“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遂,以行气血”这一句进行拓展,认为此应为“五脏旁通说”的理论来源,旁通说应是对此理论的进一步阐述,为强调脏与腑的对应关系的一种理论。
明代医家李梴总结前人思想,并加入自己新的见解,在《医学入门·卷一脏腑》中提出五脏穿凿论曰:“心与胆相通……肾与命门相通,此合一之妙也。”后代医家对此进行研读,认为这是对“五脏旁通说”的另一种解释,但文献典籍中并没有关于该理论的详细叙述,故现代医家多将“五脏旁通说”与“五脏穿凿论”并论,用来解释脏腑相应关系。两种理论在人体经络所属中应用较为广泛,提出从脏腑生理功能的相通性来解释各脏腑的表里关系,如心与胆相通,解释为心主神明,为君火,胆主中清,为相火,二者相须为用,共同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
1.5 近代:五脏相关理论正式提出
1988年,邓铁涛教授正式提出“五脏相关”理论[3],解释了五脏相关的科学内涵:“包括五脏系统内部的关系,即五脏的功能系统观,系统之间的关联,即五脏之间的联系观;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4]系统说明五脏相关理论应落在人体的大系统中,即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组织器官,共同组成一个大系统,如舌为心之苗窍,肾主骨生髓,脾之华在唇,肺外合皮毛等,将人体按五脏系统分为肝、心、脾、肺、肾五个功能子系统,这样,五脏之间就呈现多层次的功能结构,构成了多维的、立体联系的网络。如此对于五脏中任一脏腑体系的研究都可认为是属于五脏相关研究的范畴。各脏之间的联系可为两脏相关、三脏相关、四脏相关等多种关系,邓铁涛教授重点研究两两相关模式,如心脾相关等,以疾病为载体,对患者进行信息收集和观察归纳,证明了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五脏相关存在的客观性相关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则表明五脏相关不仅是指脏腑系统的“小五行”,还包括“大五行”的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应用“小五行”“大五行”的概念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小五行”承认人体的独立性,认为人体内存在独立的五行系统,五脏各有所生各有所胜,脏气相通。“大五行”则强调了自然界对于人体的影响,为古代“天人相应”理论的延续,在临床治疗时,不仅要辨证辨病,还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并认为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均可从这五大系统及内外环境相互关系入手研究。
2 从五脏相通理论论治高血压的理论依据
2.1 肝:风眩之主脏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这说明肝在高血压病的发病中具有重要的地位[5]。现代医家多认为高血压的病变脏腑主要在肝。因肝五行属木,为风木之脏,其性主动主升,肝又为藏血之脏,相火内寄,体阴而用阳,主疏泄,性喜条达,恶抑郁。《内经》有言:“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肝为藏血之脏,性主升动,若肝阴不足,无法涵敛肝阳,肝气升发太过致使肝阳有上亢之势。
刘燕池教授[6]认为肝阳上亢为临床上高血压发病最常见的病因,肝阳上亢患者多素体阳盛,因一时恼怒过度,情志失调,致使阳升上扰清窍而发为眩晕,亦可见于平素忧思过度者,此类患者大多肝气不疏,郁久化火,伤及阴血,阴不敛阳,亢阳上扰清窍而导致眩晕。肝主疏泄,在人体气的运行中占有重要的作用,气机运行具有推动血行的作用,正所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杨士赢《仁斋直指方》中谓:“瘀滞不行,皆能眩晕。”[8]王绍隆亦在《医灯续焰》言:“眩晕,有因于死血者。诸阳上行于头,诸脉上注于目。血死,则脉凝泣……薄则上虚而眩晕生。”这说明了肝气不疏可以导致血行不畅,从而引发血瘀致眩。所以高血压的发病与肝脏的功能密切相关,这也是由肝脏的生理特点和生理功能所决定的。
2.2 肾:母病及子,精亏为本
肾为先天之本,内藏精,肝为藏血之脏,精血同源,相互化生;同时肾主封藏,肝主疏泄,二者一疏一藏,关系十分密切,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记载:“北方生寒……肾生骨髓,髓生肝”。从五行来看,肝五行属木,肾五行属水,水生木,二者为母子相生的关系,故肝气久郁化热,可由子及母,伤及肾精。而肾阴为一身之阴的根本,肾阴不足进一步会影响肝阴,肝阴失其所养,则会导致阴不敛阳,肝阳上亢,引起眩晕,此类眩晕大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虚证,因其本为肾虚,故临床发现此类患者多有视力减退,少寐健忘,腰膝酸软等肾精不藏,髓海不充的症状[9],故临床上对于此类高血压患者,医家秉持标本同治的治则,在平潜肝阳的同时加入滋补肾阴之品。
高血压的发病亦可与肾脏直接相关,如《灵枢·海论》有“脑为髓之海”和“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10]之言。肾虚血瘀为老年高血压病的主要病因,人至老年,肾精不足,髓海不充,脑失所养则多致眩晕,根据证候表现,可分为肾阴虚型、肾阳虚型、肾阴阳两虚型,宜用补肾活血的治疗方法。同时肾为水脏,主津液,肾脏调节一身水液代谢的功能对于维持血压至关重要。若肾脏功能失司,水液代谢失常,水气上泛,湿浊中阻,可引起心肺脾等他脏的功能失司,出现心悸、喘促、水肿等严重的高血压变证。
沈依功[11]擅长从肝肾论治高血压,把高血压分为急性期和缓解期,提出急性期责之肝,宜平肝潜阳、清火熄风为主;缓解期则多为肾虚,则补益肝肾、填精益髓为要。
2.3 脾:相侮为病,痰饮之宗
脾病所致眩晕,古今医家多从痰论证,如《丹溪心法·头眩》云:“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无痰不作眩”。可见痰的生成与眩晕的病机十分密切,中医认为痰的生成主要在脾,自古有“脾为生痰之源”的说法,脾胃位居中焦,五行属土,主要功能为运化水谷,输送所化精微,有后天之本的称谓,其位居中焦,在一身气机运行中起着枢纽的作用,脾以升为健,胃以降为顺。故患者因饮食失节、情志失调、劳力过度等影响脾胃的功能时,不仅会发生运化失司、蕴生痰湿、中阻气机的病理状态,从而出现痰蒙清窍的眩晕症,亦可导致气血化生乏源,气血俱虚,脉道失充,无力鼓动血行,出现气虚血瘀的征象,同时气虚无力升举清阳,出现头窍失养导致眩晕的高血压虚证。在此基础上,如在治疗过程中,忽视调理脾胃的功能,可导致痰湿郁久化热,出现湿热夹杂上蒙清窍的变证。
从脾论治高血压,亦可从脾与他脏五行生克关系的角度考虑,脾五行属土,肝五行属木,木克土,二者为五行相克的关系。土壅则木郁,肝失疏泄,气机不畅,郁久则化火,肝火上扰清窍,出现眩晕症候,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由脾失运化而致高血压病的患者临床多表现不同程度的痰湿症状,如眩晕耳鸣伴见纳呆腹胀、肠鸣泄泻等,临床问诊应注意患者的平素饮食起居情况,在治疗时加用健脾渗湿之品,疗效甚佳。
蒙定水教授[12]擅长从脾论治高血压,根据患者症状表现的差异,分别治以化湿、祛浊、化痰等法,多选用半夏泻心汤、温胆汤、四君子汤等作为基本方,适用于脾失健运、中湿不化、痰浊内生型高血压患者。王清海[13]认为多数高血压患者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脾气虚弱、痰浊壅盛症状,强调在从脾论治高血压病时要注意结合“三因制宜”,不同高血压患者在治疗上要有所侧重。
2.4 心:子病及母,阳亢为根
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主藏神,刘燕池教授[6]认为论治高血压病除应注意肝的生理功能外,亦不能忽视肝与心的相生关系,心肝同病亦为高血压发病的重要病因,此类高血压病根据表现可分虚实两端,治疗上需应用“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治疗法则,虚证多为心肝血虚证,因心血久亏,累及肝血,致子母皆虚,临床除头晕外,多兼有心悸、失眠多梦等心神失养的症状;实证则多因心火亢盛,引动肝火,子病犯母,终致心肝火旺,此类患者大多性情急躁,询问病史大多有一时情志失调的诱因;同时心火亢盛,可损伤肝阴,子盗母气,临床上亦可表现为母虚子实的虚实夹杂之证。如《素问·邪客》所言:“心者……精神之所舍。”肝为藏魂之所,心神不安,魂不居所,相火易动,亢阳挟痰火上扰清窍,治疗上主要以泄心火为要。
郭维琴教授则认为[14]高血压疾病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血瘀”的病理因素,主张将高血压分为三期,早期多为情志因素所致的气滞血瘀证,病情进展到后期,热邪伤阴,阴虚血阻,晚期多为气血两虚,气虚不运而致瘀,郭教授在治疗高血压时常在各期高血压中加入活血化瘀的药物,疗效显著。
2.5 肺:宣降失常,气机失调
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中提出:“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晕者,由风木旺,必是金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从五行关系阐述了头目眩晕的理论[12],同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云:“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胃气又复上逆”,二者均强调了肺在“肝风内动”病机中的重要作用。
从肺的生理功能来看,肺主通调水道,朝百脉,可助心行血。所以肺脏与心的关系密切,在血瘀型高血压病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若肺受邪致生理功能失司,通调水道失调,人体水液失于代谢,导致体内水湿泛溢,气行不畅,从而引起血压升高,亦可出现水肿等高血压变证。刘燕池教授认为肺为五脏六腑之华盖,其气以清肃下行为顺,肺气有防止肝气升发太过的作用,所以临床治疗高血压时加入潜降肺气的药物,有助于降肝气。
亦有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肺不仅是一个呼吸器官,也是一个复杂的代谢器官[17],可以参与防御、液体交换、排泄等复杂的代谢活动,这也与中医“五脏相通”的理论相合。更有现代西医学研究表明,肺与前列腺素的合成、释放和灭活关系密切,还是血管紧张素转化的主要场所。所以,肺的功能直接影响血压的高低。
3 从五脏相通的理论治疗高血压
高血压发病病因病机复杂,病程缠绵难愈,其病变脏腑涉及甚广,不同的医家对于治疗高血压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综合各大医家治疗高血压病的医案文章,不难看出,均为立足五脏论治高血压,通过对肝、心、脾、肺、肾各脏进行辨证分析,对主要病变脏腑进行治疗,同时兼顾他脏防止传变,本文通过总结各大名家的治疗思路和临床经验来论证五脏相通理论在高血压治疗中的重要性。
3.1 五脏同治,不令偏颇
邓铁涛教授在五脏之气相通理论的基础上创制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在论治高血压病时亦围绕五脏相关理论展开,或从肝论治,或从肝脾论治,或从心脾论治,或从肝肾论治。
早期高血压以调肝为主。早期多因恼怒等情志不遂引起[18],情志失调,郁怒伤肝,导致肝脏或失于疏泄,郁结化火,火性炎上,扰动清窍而致血压升高,或疏泄太过而阳亢上逆引起血压升高。需要注意的是,肝主疏泄的功能除与情绪关系密切外,与肝藏血的生理功能亦不可分割。肝所藏之血可化生和涵养肝气,使肝气畅达。正如叶天士所言:“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升主动,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则刚劲之质,得柔和之体……何病之有?”这也是邓老强调调肝为治疗高血压病重要一环的原因所在[18]。邓老临床治疗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疾病,常用平肝潜阳之法,选用自拟方石决牡蛎汤或天麻钩藤饮为主方加减[18]。
中期高血压宜肝脾同治。此期高血压,邓教授多从肝脾论治,正如《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高血压发展到中期,肝气横犯脾胃,损伤脾气,影响脾胃运化水谷的功能,导致脾气的推动与调控、温煦与凉润二项生理功能衰退,从而引起津液的生成、运行输布失常而痰浊泛生[19]。故高血压发展到中期多表现为“气虚痰浊”的本虚标实证,临床也应根据证候辨证分析。在治疗此型高血压患者,邓老多用健脾益气平肝之治法。虽然五脏相通,高血压病发展到中期影响的脏腑也不单肝脾两脏,但在临床治疗时当分清主次、权衡轻重,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故临床治疗时首抓肝脾。根据邓老以往的医案记载,常用半夏白术天麻汤作为基础方来加减,半夏白术天麻汤出自程钟龄的《医学心悟》,方中半夏、天麻为君药,半夏燥湿化痰、天麻化痰熄风,二者共用治疗风痰眩晕效果显著。白术祛湿化痰,增强君药的止眩之功;茯苓合白术尤能治痰之本;橘红理气化痰;甘草和中;姜枣调和脾胃。诸药合用,祛风消痰,眩晕头痛自愈[19]。邓老认为气虚生痰,除痰必先理脾,健脾必用补气,故方中选用白术也有健脾益气之意。
高血压病中期多见肝脾同病,亦可见心脾两虚型。此类病人平素多忧多思,忧思劳倦耗心伤脾,故在起病之初多为阴血耗伤,肝血不足,失于濡养导致肝气上逆引起高血压。此类高血压发展到中期,阴血耗伤加重,影响心血的生成运行,同时肝气横逆影响脾胃的运化,血液化生乏源,最终导致心脾两虚证。此证型的高血压患者在治疗上,邓老多选用归脾汤作为基础方加减[19],治法为调脾护心。归脾汤中参、术、芪、草之甘温补心,使血归于脾而不妄行;茯神、远志、枣仁、龙眼之甘温酸苦以补心;当归滋阴养血;木香行气舒脾,既行血中之滞,又助参、芪而补气。
晚期高血压宜滋肾养肝、五脏兼顾。肝藏血,肾藏精,肝血化生有赖于肾精的充盛,肾精的充盛亦赖于肝血的滋养,年老、久病多易伤肾精肾气。若肝肾阴俱亏,阴亏不能涵养肝阳,肝风内动更甚,血压上升。此时临床上除眩晕、头痛等肝风内动症状外,多可见耳鸣、腰膝无力、或盗汗、遗精等一派肾阴虚之症。治疗上以滋肾养肝为法,方用镇肝息风汤为主方加减。
3.2 五脏皆重,不可忽视
高血压这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在病程发展过程中可表现为多个脏腑的功能失调,这要求我们在临床诊疗中不应忽视整体,必须立足五脏同调。当然,五脏同调不代表五脏并重,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学会从复杂的症候群中抓住病变的主要脏腑亦为重要的一环,方有君臣佐使,病变脏腑亦有轻重缓急之分。再者要注意观察五脏的功能关系,并考虑它们之间的五行生克制化关系,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注意防止传变,截断疾病的发展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高血压病发病过程中,还会有风、火、痰湿、瘀等多种病理因素的存在,亦为相应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
3.3 以肝肾为中心,五脏同治
董桂英[19]提出以肝脏为中心、五脏相关论治高血压的理论,认为高血压危象病位在脑,肝肾为病变的核心脏。肝肾密切相关,相互滋生、相互影响,肝血亏虚则肝阳上亢,肝阳妄动,损伤肾阴,肾阴亏虚,肝木失养,肝阳上亢加剧,如此形成肝肾密切相关的恶性循环。提出高血压危象虽以肝肾为中心,但与五脏相关,五脏之间相互影响,临床上不可脱离整体。临床治疗以平肝潜阳、补益肾精为主,平肝以恢复肝脏调畅气机的正常生理功能,益肾以恢复肾精、肾气为目标,同时还应该注意改善高血压对肺、脾、心的不利影响,减少眩晕的诱发因素和并发症状。
3.4 “调五脏,祛邪实”,虚实兼顾
何立人[20]认为,高血压和其他多种心系疾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病机也有相似之处,均与五脏功能失调相关,具有久病多虚、久病及肾、久病入络、久病致郁、久郁生痰的特点。何师强调,中医治疗高血压病应注重“调五脏,祛邪实”的整体观念,标本同治。
所谓“调五脏”,即调肝、益肾、理肺、健脾、宁心。调肝包括平肝、泻肝、疏肝、柔肝等多种含义,从脏腑而言,高血压病的发病未必一定为肝阳上亢的实证,也可能为阴虚导致阳亢的本虚标实证,故临床应辨证施治,以肝气舒畅、肝木平和为目标,临床常配伍理气之品以调肝。补肾则多针对水不涵木导致的高血压病证,因肝肾同源,故临床治疗此病不单纯补肾,常常肝肾同补,肝肾为母子相生关系,二者同补疗效更佳,临证时酌情选用培补肝肾之品。理肺,因肺为华盖,居上焦,为水之上源,故其气以降为顺,且肺主一身之气,若肺气敛降失司,可使人体气机升降失序;肺金功能下降,不能制约肝木,是高血压发病的一个原因,故临床辨证时应注意观察肺气宣降功能。健脾多与调肝之法同时应用,因肝脾为五行相克的关系,故健脾化湿时也应注意调肝为用。宁心强调临证时注意重视心的功能,“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主司人的精神情志活动,高血压的发病和情志关系密切。
经过对各医家治疗高血压的病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各大名家论治高血压多从五脏出发,在治疗过程中也注意观察各脏腑的联系及功能变化,选方用药更是五脏兼顾。然而因病人体质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或者职业的性质差异,导致临床疗效也各不相同,但是灵活运用五脏相通理论治疗高血压亦已成为现代治疗高血压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以后高血压的治疗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作为近现代新兴的临床理论,从五脏相关论治高血压病仍处于临床试探阶段,各项理论仍存在不成熟之处,仍然存在未解决的疑问和尚需补充的理论,需要更多的临床实践来验证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