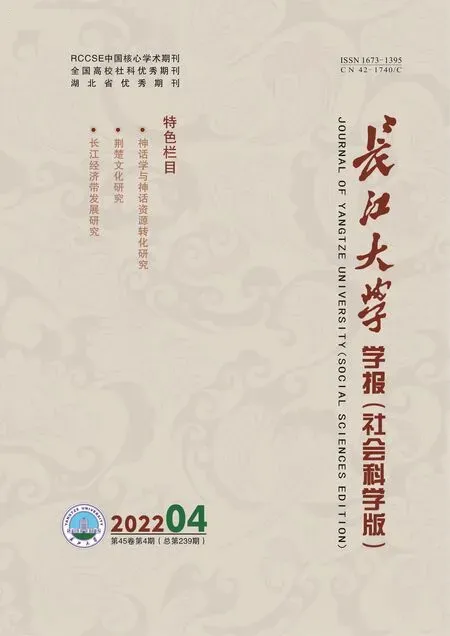游戏、意象与遗产:竹马文化的多维透视
任正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学界关于竹马的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艺术学、民俗学领域学者从非遗的视角着眼,对各地特有的地方性非遗项目的个案观照。如张士闪对山东昌邑小章竹马活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社会变迁中村落艺术传统的形成与保持[1];子仁介绍了浙江富阳的龙门竹马在正月的表演[2];郑尚宪、林聪辉对闽南竹马戏进行了阐释[3];张胜环对福建漳州南靖竹马戏开展了调研,认为“它的表演形式丰富,道具制作复杂,具有鲜明的音乐舞蹈特征和重要的传承价值”[4];温和探析了粤东竹马戏的历史渊源[5]。其二,关于竹马嬗变历史的简要介绍,如杨秀清以敦煌壁画为中心,将竹马作为一种古代儿童游戏进行了分析[6];刘毅探究了唐代竹马发展演变历史[7];郭小刚则基于图像学理论,对竹马舞的流变作了细致考察[8]。其三,从文学角度对文学作品中的竹马意象进行分析,如李晖对唐诗中的竹马意象进行了梳理[9],熊明从民俗意象的宏观角度探讨了唐代小说、诗歌中的竹马意象[10]。总的来看,关于竹马的非遗研究占主导,但以微观的个案研究为主,其他领域还比较薄弱,从宏观角度着眼对竹马进行多维阐释、综合分析的文章尚少。本文从文娱游戏、文学意象、文化遗产三大视域出发,对竹马的历史演变、文化意涵及当代发展进行探讨,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的视角。
一、作为文娱游戏的竹马:从儿童玩具到民间仪式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竹马的传播与传承地域从北方扩展到南方[8],制作工艺由简到繁,活动场所由不拘时空到特定时空,使用主体由儿童扩展到成人,文化功能也实现了由娱己的儿童玩具到娱人的民间表演再到娱神的民间仪式的转变,最初的世俗性也演化为世俗性与神圣性并存,但其作为文娱游戏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
(一)汉唐时期:娱己的儿童玩具
竹马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关于竹马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
(并州牧郭伋)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11]
这里数百儿童所骑即为竹马,竹马迎接能臣循吏的传统自此开始。东汉时期的竹马十分简易,就是将一根竹竿当马骑的儿童游戏。宋代王应麟在《玉海》卷七九“汉鸠车”条引《杜氏幽求子》云:“儿年五岁有鸠车之乐,七岁有竹马之欢”[12],表明竹马是汉代七岁左右男童常玩的玩具,也是一些无子夫妇求子的重要信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延续了东汉以来的竹马游戏。裴松之注《三国志·陶谦传》时引《吴书》云:“谦父,故余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13]
《世说新语》中也有两则关于竹马的记载。《方正第五》第10条载: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14]
《品藻第九》第38条载: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14]
这两处记载说明,竹马是贵族儿童与小伙伴们童年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好童年的承载物。
唐代的竹马比汉晋时期更受欢迎,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爱。王永平对唐代儿童游戏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他把竹马游戏归类为与植物有关的游戏,“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6]。《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龟兹传》载:“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15]这一时期,竹马开始进入文学作品当中,开启了竹马入诗、入小说的新纪元,众多唐诗、唐传奇中丰富的竹马记录,为唐代以降的竹马戏、竹马灯、竹马舞等民间表演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在汉唐时期的发展历程中,竹马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儿童玩具,其他功能尚在孕育之中。这一时期,竹马的流传范围逐渐从北方扩展到了南方,这与气候的演变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密切相关。
(二)两宋时期:娱人的民间表演
两宋时期的竹马活动沿袭汉唐,依旧在民间十分流行,竹马内涵不断丰富,逐渐由儿童游戏向民间表演嬗变,制作工艺也由简向繁发展,使用的时空活动场所由不拘时空到特定时空。这是竹马作为文娱游戏的第二阶段。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极度丰富,竹马也从没有时空限制的儿童自娱游戏转变为在特定节日、城市空间展示的民间娱人表演。如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载:
国忌日,分有无乐社会。恃田乐、乔谢神、乔做亲、乔迎酒、乔教学、乔捉蛇、乔焦锤、乔卖药、乔像生、乔教象、习待诏、青果社、乔宅眷、穿心国进奉、波斯国进奉。禁中大宴,亲王试灯,庆赏元宵,每须有数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场傀儡、阴山七骑、小儿竹马、蛮牌狮豹、胡女番婆、踏跷竹马、交衮鲍老、快活三郎、神鬼听刀。[16]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云:
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17]
这一时期的竹马成为娱人的民间表演,使用主体仍为儿童,但已经不仅是儿童的游戏,成为节庆盛典上娱人的游戏舞蹈。竹马制作也由抽象简易向具象繁复转化。汉唐时期的竹马仅有一根竹竿,两宋时期的竹马更像一匹马。该阶段的竹马拥有先用竹篾制作轮廓,再用纸糊成的简易马头,这种马头拥有马耳、马鬃、马眼、马鼻、马嘴,还装饰有辔头、缰绳和铃铛,十分形象。除了马头外,两宋时期的竹马也有简单的马身和马腿,儿童跨在竹竿上,手中挥舞着竹枝或树枝做的马鞭,颇似真马。作为民间表演的竹马,已经由简单的儿童游戏演变成多人参与的竹马舞、竹马戏、竹马灯,成为元宵节等节日上的必备演出。此外,宋代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舞队》中提到,“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男女竹马……其品甚伙,不可悉数。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眩耀华丽,如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18]可见,玩竹马的人群由原先的多为男童扩展到女童,不仅队伍庞大,且颇有“男女平等”的感觉。
(三)元明清时期:娱神的民间仪式
元明清时期,竹马在延续两宋时期形态与功能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特征,竹马的形态与内涵进一步丰富,开始由世俗性较强的民间表演向神圣性与世俗性兼具的民间仪式转变,竹马的形制也更加灵活,其原本的世俗性也具备了神圣性的特点。这是竹马作为文娱游戏的第三阶段。
这一时期的竹马同时兼具儿童玩具、民间表演与民间仪式三大功能,但作为民间仪式的娱神功能颇为突出。元明清时期是我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戏曲成为民间娱神的主要方式。有寺庙、道观在纪念祖师诞辰、成道、升仙时请戏班子唱戏酬神的,有善男信女因祈祷灵验许下承诺而请戏班子还愿娱神的,在这些特定的时空语境下,竹马戏往往成为许多庙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僧道和民众用来娱神的民间仪式。
明清时期的民间戏台上经常有“执鞭代马”的表演形式,这种表演程式虽然尚未定型,但已经可以看出后代戏剧中相关表演的端倪,这是竹马戏曲舞台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属于竹马的一种变形。此外,竹马的形态也有了变化。明代,竹马末端添加了小轮,儿童骑起来更加方便省力,明青花瓷上有很多这样的儿童玩竹马游戏图。[8]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习俗变迁与儿童玩具的日益丰富,竹马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作为文学意象的竹马:文人书写与符号象征
(一)儿童玩具:童趣记录与天伦之乐
“到了唐代,竹马之戏也成为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在诗歌中,竹马意象常成为人生中欢乐无忧、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的象征。”[10]唐代以降的历代文人延续了唐人的竹马书写,其中作为童趣记录与天伦之乐的象征最为普遍。这些竹马意象有文人所见外姓儿童的童趣白描,有文人对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之乐的记录,还有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时光流逝的感伤。如李贺《唐儿歌》云:“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睒光踏半臂。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19]白居易在《赠楚州郭使君》中高歌“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20]。两宋时期,竹马不仅是宋诗中的常客,也成为宋词中的“宠儿”。陆放翁喜欢看村童玩耍,其《观村童戏溪上》云:“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谢晚晴。竹马踉蹡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21]
竹马意象还是文人享受天伦之乐的见证。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归婺州》云:“春风秋月携歌酒,八十年来玩物华。已见曾孙骑竹马,犹听侍女唱梅花”[20],描绘了好友婺州滕庶子退休后与曾孙同乐的美好生活。关注日常、热爱生活的宋人特别喜欢竹马意象,尤其在一些高寿文人笔下,与孙子、曾孙玩耍,尽享天伦之乐的场景比比皆是。如陆游《岁暮》载:“浅色染成官柳丝,水沉熏透野梅枝。客来莫怪逢迎嬾,正伴曾孙竹马嬉。”[21]文人笔下的竹马意象除了对童趣的记录和天伦之乐的享受,还有对逝去光阴的惋惜,竹马承载着他们的文化记忆。晚唐颜萱《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载:“忆昔为儿逐我兄,曾抛竹马拜先生。书斋已换当时主,诗壁空题故友名。”[22]范成大年过花甲之时,作《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感叹“童心仍竹马,暮境忽蒲轮。镜里全成老,尊前略似春”[23]。
(二)爱情信物:青梅竹马与纯美爱情
除了拥有最常见的童趣与天伦之乐的意涵外,竹马作为纯美爱情的象征自唐以来便影响深远。在李白《长干行》一诗中,诗人首次把“竹马”与“青梅”联系起来,“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24]。
清人程颂万《踏莎行》云:“小阁妆才,回郎立遍。中门映处侬初见。青梅竹马一年年,而今不是当时面。刬袜描鸳,搔头隔燕。千金不换华年转。紫薇花顶日低横,簸钱声是谁家院”,词人将与美人初见时的欣喜到“华年转”的感慨书写得委婉动人。清代樊曾祥《鹊桥仙·其二·代夫人答》言:“青梅竹马,玉台纱障,成就神仙夫妇。两情如蜜透中边,浑不识、梨酸杏酢。莲花莲子,凭君采撷,那用仓庚疗妒。若将侬比玉观音,问卿可能持长素”,作者将自己与夫人琴瑟和谐的甜蜜爱情娓娓道来。清末民初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红豆》诗道:“青梅竹马系相思,耳鬓撕磨忆少时。托体茑萝欢乐共,含香豆蔻笑颦宜。玉珰缄札频贻我,宝箧妆奁欲付谁?忍唱懊侬啰唝曲,曲栏干外折柔枝。”红豆是相思的信物,青梅竹马则寄托着诗人对少年时期纯美爱情的真情回忆,佳人的一颦一笑都刻骨铭心。“青梅竹马”意象甚至流传到国外,成为日韩等国文学创作中的意象,如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代表作《青梅竹马》。
(三)交通工具:神奇法器与玄怪故事
在唐人的传奇小说中,竹马不再是儿童的玩具,而是幻化成一种神奇的交通工具,拥有快速移动的神力。唐人崇尚道教,认为道士可以成仙、通天,故而很多玄幻故事中往往有道士的身影。《太平广记》中收录有《逸史·李林甫》一文,文中的李林甫形象与历史上的奸相形象不同。李林甫的魂魄被一道士从居所带到了一处神秘的帐榻华侈的“府署”,李林甫往返均以竹马为交通工具:
唐右丞相李林甫……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25]
唐代牛僧孺在其《玄怪录·古元之》中描写了一段情节:
(古弼)即令(古元之)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26]
元之因酒醉不幸离世,古弼是其远祖。当时古弼想要前往和神国,却苦于没有随从为其担囊,故而召唤古元之与其同往。而竹马正是他们去和神国的交通工具,这种竹马“飞举甚速,常在半天”,成为真正日行千里的神奇的交通工具。
除上述两处可见竹马的神奇作用外,《续定命录·李行修》一文中亦有类似情节,描述了李行修进入幽冥之境与其亡妻相见的场景:
故谏议大夫李行修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行修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人。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修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修折一竹枝,亦令行修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25]
这些唐人小说中的竹马长短不一,或“数节”,或“长二丈余”,但均为竹制法器,往往都能腾空而起,以飞快的速度翻山越岭,带着主人公去往神界或冥界等凡人难以到达的神秘之处,但主人公获取竹马时都需要有“古弼”“道士”“王老”等高人指点。后世《三洞群仙录》《西游记》《平妖传》等神魔小说中各种神奇的交通工具或受其影响。
(四)迎宾使者:竹马小儿与能臣廉吏
用竹马表达民众对地方官员的爱戴,始于《后汉书·郭伋传》,后来这一意涵渐入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文学意象。诗文作品中的竹马意象不仅是儿童玩具、爱情信物和奇幻的交通工具,还是古代出任或巡视地方的廉吏能臣的象征。“竹马迎宾仪式常被用于表现中央王朝的权威与儒家文化的道德优越感”[27],巡视地方者嘉言懿行声播地方,出任地方者爱民如子,甘棠遗爱,而天真无邪的儿童仰慕其名,为表爱戴,骑着竹马夹道欢迎他们,这不仅是其教化百姓、治理有方的证明,也是其深孚众望的体现,故而竹马意象在唐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是好官的象征,成为送别诗中的经典意象。如李白在其《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载:“君从九卿来,水国有丰年……竹马数小儿,拜迎白鹿前。含笑问使君,日晚可回旋”[24],盛赞宇文太守出任地方后,这里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老者称颂,儿童笑迎。岑参《凤翔府行军送程使君赴成州》云:“程侯新出守,好日发行军。拜命时人羡,能官圣主闻。江楼黑塞雨,山郭冷秋云。竹马诸童子,朝朝待使君”[28],期待程使君造福一方,成为成州儿童欢迎的“能官”。白居易《送唐州崔使君侍亲赴任》载:“发时止许沙鸥送,到日方乘竹马迎”[20],寄托着对好友崔使君就任地方的祝福。刘商《送庐州贾使君拜命》云:“人咏甘棠茂,童谣竹马群。”[22]
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传统,也留下了诸多具有此类象征的竹马诗词。宋代杨炎正《水调歌头·一笛起城角》言:“一笛起城角,吹破小梅愁。东风犹未,谁遣春信到吾州。闻得东来千骑,鼓舞儿童竹马,和气与空浮。”[29]宋代晁端礼《永遇乐·雪霁千岩》云:“雪霁千岩,春回万壑,和气如许……儿童竹马,欢迎夹道,争为使君歌舞。”[29]苏东坡在数首诗中也有此类书写。如《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云:“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30]《次前韵再送周正孺》道:“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耸。竹马迎细侯,大钱送刘宠。”[30]此外,竹马不只是诗词曲、小说中的意象,还发展成了竹马子、竹马儿等词牌名。
三、作为文化遗产的竹马:民俗活动与国家在场
近十余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我国的广泛开展,竹马(竹马戏、竹马舞、竹马灯、高跷竹马等)被列入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属于“传统舞蹈”门类。
(一)保护现状
1.分布状况
目前,竹马作为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分布于汉族地区,是元宵社火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与旱船等一起表演,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舞蹈表演形式。近年来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诸多地方的竹马以“某地+竹马”的命名方式被列入县、市、省、国家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中,其中,江苏高淳竹马(东坝大马灯)、江苏邳州竹马(邳州跑竹马)、江苏溧阳竹马(蒋塘马灯舞)及浙江淳安竹马4项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见表1),入选省级非遗的有44项,入选县、市级非遗的则更多。

表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竹马项目
以44项省级非遗竹马为例,它们广泛分布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即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天津市、北京市、安徽省、山东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陕西省、青海省的50个县域。(1)省级竹马非遗的相关数据来自于各省公布的不同批次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空间分布看,作为非遗的竹马在地理上集中分布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汉族地区,零星散布于西南的瑶族、畲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东北、西北等地区几乎没有。从展示时间来看,竹马作为一种民俗活动与岁时节日联系紧密,其展演时间主要集中在从春节到元宵节的这段时间,但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地区的竹马表演成为民间婚丧嫁娶、一般节庆盛典及一些景区日常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俗性在资本运作下走向异化。
2.表演情况
全国各地的竹马别名颇多,有跑竹马、竹马舞、竹马灯、高跷竹马等叫法,往往前面冠以村、县等地名,如香河大河各庄竹马会、三家村竹马舞、平遥竹马、淳安竹马,等等。这些竹马制作过程大同小异,主要步骤如下:首先,用竹篾将竹马框架扎好;其次,用彩纸或彩布包裹框架;最后,把辔头、缰绳、铃铛等小配件搭好,一匹逼真的竹马就完成了。竹马表演人数不固定,可为单人,可为双人,也可为多人,但以多人为常。竹马表演的演员往往扮相简单、色彩鲜艳,由单人套上竹马,然后多人再共同组成竹马阵,演唱节奏感强,队形整齐喜庆,场面壮观威武,贴近民众日常生活,深受百姓喜爱。竹马表演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唢呐、锣、鼓、铙钹等传统乐器。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有些地方的竹马表演有文场和武场之分。元宵节前后,竹马与旱船、秧歌、舞龙、舞狮、威风锣鼓等民俗表演一同成为民俗活动的节日呈现。
3.传承机制
古代的竹马表演传承往往是子承父业或者师徒相传,是一种民间传承的自发行为;当代的竹马表演保护则是一种国家参与的自觉行为,国家在场使得民间仪式得以更好地传承。(2)关于“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二者的关系,详见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随着我国一系列非遗保护政策的落地,作为非遗的竹马实现了在国家在场下的家族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方式双轮驱动,为竹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家族传承最核心的还是传承人的代际传承。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保障下,竹马非遗传承人不仅可以获得一定补助,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获得可观的演出收入,竹马在生产性保护的道路上走向繁荣。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事业单位与传统文化研究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等民间团体则是社会传承的重要力量,作为官方或半官方组织,这些机构在竹马人才培养、竹马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竹马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公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竹马,喜欢竹马。
(二)存在问题
1.文化生态:支离破碎
竹马是农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在步入工业时代后,作为非遗的竹马,其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其内在结构、特征与功能的剧烈变化。竹马这一原本在农业社会十分普遍的文化形态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土壤,成为一种剥离了其原生的农耕文化语境的被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创新发展的文化资源,其原有的文化生态支离破碎。比如,很多地方的竹马表演原为佳节酬谢神灵保佑的娱神活动,民众通过一系列表演来表达对神灵的感谢与来年再获丰收的期待;有的表演则是为了通过竹马活动体现尚武精神和对祖先的怀念。无论是哪种功用,都是农业文明下的民间文化呈现。竹马表演也成为农民对传统生活的一种追忆性表达,更具象征性而非实用性。
2.文化空间:严重扭曲
竹马文化生态的剧烈变化也使得其文化空间遭到了严重扭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就自然属性而言,包括在自然空间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场域性,以及在时间形态基础上形成的延续性、周期性与时点性等特性;就社会属性而言,包括在社会组织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情感性和综合性,以及在文化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性、共享性、多样性等特性。”[31]竹马文化空间的扭曲变化主要体现在自然空间与时间形态两方面。其一,自然空间逐渐萎缩。原本流传于广大汉族地区的竹马表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逐渐残留于偏远的山村,城市基本限于博物馆中的展览品,乡村也仅仅局限在一些交通不便的传统文化浓厚的村落之中。其二,时间形态发生变异。竹马表演往往在农历元宵节前后,带有浓厚的节庆色彩,随着非遗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开展,原本在特定时间段展示的民间表演,其展演时间越来越长,不仅由元宵节扩展到其他传统节日,还成为一些民间婚丧嫁娶、开业典礼等活动的助演活动,在一些旅游景区,更成为日常表演的一部分。
3.文化生产:资本异化
作为非遗的竹马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得以传承发展。在政策的鼓励下,资本开始进入非遗保护与开发领域,通过生产性保护让竹马适应现代生产、生活。资本的介入对竹马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竹马在资源化开发过程中获得新生,另一方面也使得资本在竹马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无序扩张,资本异化比较明显。其一,资本的运作加剧了竹马表演的同质化。各地的竹马虽有地域性,但在资本的参与下,竹马表演成为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地方开始学习行业成功案例的有效经验,对自身在地文化反而缺乏深度挖掘,最终导致这些竹马在表演场地、表演内容、运营模式等方面日益趋同,失去特色。其二,资本运作扰乱了竹马表演的民俗性。竹马表演本身是一种民俗活动,但资本介入后,追逐利益与效率成为导向,竹马由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民俗景观逐渐转变为徒有其表的舞蹈表演,其原有的浓厚乡土气息与独特民俗样态逐渐褪去。
(三)发展路径
1.国家在场
竹马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离不开国家在场。其一,整体性保护竹马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与文化空间。各级政府应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继续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落实有关地方政府主体责任”[32],让现存的竹马文化生态得以改善,文化空间得以保护。其二,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相关法律、制度。当前,以竹马为代表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较大,而市级、县级的相关制度还需完善,保护力度还需加大。其三,合理利用资本,推动竹马与旅游的融合发展。鼓励建设竹马特色景区,充分利用VR、AR等技术,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形成“竹马+”乡村旅游新型业态。合理利用竹马文化资源进行文艺创作和文创设计,支持并监督相关企业发展,提升竹马知名度与美誉度。加强竹马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发挥资源组合优势。
2.民间发力
竹马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离不开民间保护,如果说国家在场为竹马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那么,民间发力则为竹马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其一,民间应该积极对接国家的相关政策。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等民间组织,还是非遗传承人,都需要及时关注并积极响应国家出台的关于非遗的相关政策,提高思想觉悟,主动抓住政策红利与发展机遇。其二,民间应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竹马非遗人才。可以通过举办竹马进校园、竹马培训班、竹马文创比赛等活动扩大竹马受众,吸引相关人才参与竹马保护与发展。这些人才不仅包括竹马非遗传承人,也包括竹马文创设计者与营销人员等。其三,民间还应创新宣传手段,扩大竹马的知名度。不仅要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推送竹马相关的文章、视频,更要跟上时代步伐,借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将竹马制作、竹马表演、竹马文创等过程用短视频与直播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培养一批竹马表演网红,让竹马活起来,火起来。
四、结语
在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竹马从汉唐时期娱己的儿童玩具到两宋时期娱人的民间表演再到元明清时期娱神的民间仪式,内涵日益丰富,工艺越发繁复,流传地域越来越广,但无论是作为儿童玩具,还是作为文学意象,二者都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是特定时空下的文化记忆。随着社会转型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竹马为代表的农耕时代的产物存在的文化土壤逐渐消失,原有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竹马逐渐被具有类似功能的新事物取代,玩具汽车、弹珠、积木等成为儿童的玩具,作家甚至普通人关于童年的记忆也必将出现新的意象,竹马则成为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一种文化符号,了解历史的一把文化钥匙。作为遗产的竹马在传统文化碎片中裂变重生,成为人们对过去的一种文化记忆。
当然,我们应更加关注朝向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建设非遗博物馆、非遗生态环境保护实验区,对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将非遗保护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把点状非遗项目、线性文化遗产、面状文化生态区结合起来,进行生产性保护,让生态性保护与生产性保护双轮驱动,让非遗“活”起来,成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意源泉,不断增强民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增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后劲,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文化自信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