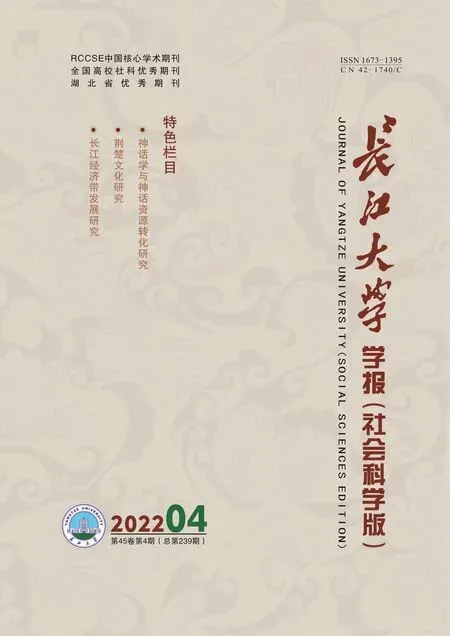近代词学批评方法及其内涵
程诚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词学批评是词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批评理论与词学理论相互交融,正因如此,当前学界对于词学批评的研究,往往与词学理论交叉在一起,而不刻意加以区分;然而,词学批评还是存在着如具体性、针对性等一些自身特点,故而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有助于更好地观照词学理论。本文将在总结近代词学批评方法的基础上,探讨近代各个时期的词学批评。
一、近代词学批评方法
近代词学批评方法是近代词学家在研究词学时所采取的一些学术手段。今人对于批评方法的研究,多是从现当代学术体系出发予以归纳,虽然比较完整,但未必还原了近代词学批评的原生态面貌;亦或从近代批评文献的形态及批评思想出发,将方法与方式予以统合,虽然较为全面,但对特定时期而言,未免有失确切。就近代词学批评而言,其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法、喻象法、溯源法、例举法及归纳法等。
其一,比较法,即运用对比、比拟的手段辨析所论对象的批评方法。其目的在于突出强调所论对象的特征,使其更加鲜明,其使用范围广涉词人词作、词风、词境、词史、词之声律等。如周济比较苏辛词,认为二者虽并称,然实有别,辛氏或许偶然能得“苏之自在处”,然而苏氏却无法得到“辛之当行处”。[1](P1633)谢章铤比较温庭筠词与梦窗词,认为二者之异在于“风骨”与“神韵”,温词“生香活色”,而梦窗词犹如“七宝楼台”般不可拆碎。[1](P3420)张祥龄以词人与诗人对比的方式来论定其地位,认为周邦彦犹如“诗家之李东川也”,姜夔犹如“杜少陵也”,吴文英犹如“李玉溪也”,张炎犹如“白香山也”。[1](P4211)刘熙载亦以与张氏相同的理路从词品出发论断词人地位,认为苏辛犹如“李杜也”,柳永犹如“香山也”,吴文英犹如“义山也”,姜、张则犹如“大历十子也”,而张先“似韦苏州”。[1](P3697)周太玄亦云:“两宋诗之三唐,清真诗之老杜,稼轩诗之太白,而石帚诗之退之也。”[2]况周颐比较女性词人,认为朱淑真词“清空婉约”,而易安词则“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1](P4497)又如陈廷焯比较词人成就,认为后主词虽“不及飞卿之厚”,但“自胜牛松卿辈”。[1](P3779)他还通过诗词对比的方式来评判词史发展,认为唐词犹如汉魏之诗,五代词犹如“两晋六朝”之诗,两宋词犹如“三唐”之诗,元明词犹如“两宋”之诗,而“国朝词”犹如“国朝之诗也”。[1](P3903)他还认为诗境与词境同理,可以通过比照诗境,进而揭示犹如“渊明之诗”与“杜陵之诗”[1](P3966)两种未得见的词境。江顺诒也以诗词对比方式分析词史流变原因,认为五代词犹如初唐诗,面对“陈、隋之绮靡”,所以“变为各体之宏大”,而“晚唐之纤薄”导致了“小令之秾厚”。[1](P3222)还有如陈锐《词比》专门通过对比方式来辨析声律中的相类字句、韵协及律调等。值得一提的是其《袌碧斋词话》,创新性地将词体与戏曲、小说对比,突破了以往多用诗词对比的批评范式。他认为柳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在小说中如《金瓶梅》”;而清真词在院本中“如《会真记》”,在小说中“如《红楼梦》”。[1](P4198)
其二,喻象法,即运用比喻的手段评说所论对象的批评方法。其目的在于生动形象地描绘一些较为深奥抽象的概念,使其变得浅显活泼,易于理解。如谢章铤论及“雅趣”的重要性,将“雅”喻为“美人之貌”,“趣”喻为“美人之态”。他认为如果词只有“雅”而无“趣”,就像美人“有貌无态”,没有情趣;反过来,如果词只有“趣”而无“雅”,就会像美人“有态无貌”,仿若东施效颦。[1](P3461)沈祥龙论及词尚“清旷空灵”,将之喻为“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此惟在妙悟而已”[1](P4048)。陈廷焯论及白石词喻其“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1](P3723),论及贺铸词喻其“如云烟缥缈,不可方物”[1](P3722)。周济将温庭筠词喻为“严妆”,将韦庄词喻为“淡妆”,将后主词喻为“粗服乱头”。[1](P1633)值得注意的是闻宥的《恤簃词话》,其多数篇幅皆以喻象法行文论述。这与其为刊物型词话关系密切,因报刊具有普及性,故对其理论上通俗易懂的要求更甚。闻氏主要论及历代词人、作词法及词境等问题。如其论宋代词人云:“苏东坡如深山剑客,不娴俗礼。秦少游如花间丽色,却扇一笑,百媚横生。”[3]其论清代词人云:“清诸家词,龚芝麓如初日芙蓉,姱容秀发。王阮亭如青春少妇,媌娙多致。”[4]其论近代词人云:“谭仲修如宦家闺秀,步履矜持。王骛翁如海国珊瑚,不假磨琢。”[5]其论作词法云:“词有三要,略同于诗。其一命意。百尺之楼,基于壤土,繁英之发,荣于一芽,故其意须具。不则辞胜于情,失之也虚。辞情俱短,失之也俗。其二立局……其三选辞。”[6]其论词境云:“词境有四。其一,如新桐始叶,嫩翠若滴,柳梢月上,娟娟欲波。天机灵活,生意澹宕,且无丝毫迹象可寻。东坡所谓‘空山无人,水统花开’者也。此境唯飞卿、正中、小山诸公具之。”[7]喻象法特别受到批评者的喜爱,为其常用之法。如冯煦《论词绝句·其五》将简单模仿苏词的后世之人喻为“后起铜琶兼铁拨”[8]。高旭《十大家词题词》评白石词,将白石清劲之风喻为战国法家的“申韩之气”[9]。朱祖谋的论词组词《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12首将周济《词辨》之功喻为“一灯乐苑此长明”[10](P351)。
其三,溯源法,即追溯本源历时性考察所论对象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整体把握与清楚认知其由来及发展流变。如周济认为“清真词多从耆卿脱胎”[11](P231)。陈廷焯认为欧阳修词乃“飞卿之流亚也”[1](P3723)。谢章铤认为“晏、秦之妙丽”源自李白和温庭筠,“姜、史之清真”源自张志和与白居易,只有苏辛独辟蹊径。[1](P3444)沈祥龙认为唐词分两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胜在“气格”;“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胜在“才华”。[1](P4049)又如沈祥龙认为词体在思想内容上源于风骚,须得“离骚之旨”[1](P4047)。谢章铤认为“词体源于三百篇及古乐府”[1](P3430)。陶骏保认为词体“实由铙歌军乐所变迁也”[12]。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知人论世之法,其本质实为溯源之法。如陈廷焯认为苏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源于其“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1](P3925)的性情。他又认为杜诗悲壮,源于其“沉雄博大之才”,加之当时唐朝正值中兴;而碧山词之所以哀思,乃因其“以和平中正之音”[1](P3813),却无奈处于宋朝衰败时期。二者风格的不同,在追本溯源中得到了解释。
其四,例举法,即通过举例来具体论述研究对象。其目的与喻象法相类,即使得抽象概念生动形象起来,易于理解。如张祥龄提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1](P4213),随后便例举了“稼轩《摸鱼儿》、酒边《阮郎归》、鹿虔扆《金锁重门》、谢克家《依依宫柳》”予以说明。严既澄《月耑阁词话》论及“词之疎快淋漓者,苏辛而外尚有张于湖”,但恐《于湖词》流传不广,未必有人识,故其随后例举云:“‘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一阕,语语脱口而出,飞拜旷放,直如天马脱羁。”[13]张庆霖《固红谈词》论及“金章宗喜文学,善书画”[14],随后即例举其题扇词《蝶恋花·几股江龙骨瘦》,并借机继续论述其词源于二主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例举法还有摘句法这个变体,即摘引他人语句为己例证。如沈祥龙摘引“雨打梨花深闭门”和“落红万点愁如海”两句为例来说明何为“情景双绘”“趣味无穷”之佳句。[1](P4056)又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广泛摘引前人诗词,以例证其境界说之理论内涵。
其五,归纳法,即总结各种词学问题,使其理论得到升华,并得出自己的词学观点。如刘熙载在《艺概》中以“词品”说为理论基础将词总结为“三品”。张德瀛总结清词发展有三变[1](P4184),即“国初朱、陈角立”,去除明词积弊;“樊榭崛起,约情敛体”;张惠言创立常州词派。陈廷焯前期在《词坛丛话》中将历代词人的代表总结为“五圣”与“三绝”,“五圣”即北宋贺铸、周邦彦,南宋姜夔,清代朱彝尊、陈维崧;“三绝”即清代朱彝尊、陈维崧和厉鹗。后期他又在《白雨斋词话》中重新总结,修正为“三绝”与“四圣”,“三绝”即周邦彦、姜夔与王沂孙,“四圣”在“三绝”基础上又增加了秦观。
二、近代对唐宋词的批评
近代对唐宋词的批评基本可归纳为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两部分。宏观批评主要围绕唐宋词的发展流变、流派分类等热点问题予以探讨,微观批评则聚焦于具体的词人词作。
(一)对唐宋词的宏观批评
唐宋是词发展的鼎盛期,近人多通过总结唐宋词的发展流变,来为自己的词学主张寻求立论依据。其主要围绕唐宋词的发展流变、流派分类等热点问题展开。
其一,就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而言,近人主要是描述其演进轨迹,总结其风格特征。如张惠言将唐宋词的演进划分为唐词、五代词和两宋词三个阶段,认为唐词以“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词乃“词之杂流”;宋词号称极盛,“渊渊乎文有其质焉”,但也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1](P1617)陈廷焯论及词史发展,认为唐词声律渐开,五代词如同六朝诗,而北宋词乃“诗中之风”,南宋词是“诗中之雅”。[1](P3720)江顺诒认为词史划分不应简单以时代为依据,而应按照词史自身的发展阶段来重新划分。他将五代词、宋词划分为四个时期:初期以二主词为代表;极盛期以南宋姜、张为代表,“为词家之正轨”[1](P3227);中期以碧山词、梦窗词为代表,“各臻其极”;晚期以北宋词为代表,只有易安词勉强值得一提。张祥龄创新性地以四季变迁来喻五代词、宋词嬗变,生动而形象。他认为五代词以二主和冯延巳为宗,但尚处于萌芽阶段;发展至晏词、柳词,犹如春天来临;清真词和白石词,代表夏天的到来;梦窗词和碧山词则代表秋已至,“至白云,万宝告成,无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1](P4212)。
其二,就唐宋词的流派分类来看,近人主要是以词风来划分流派。如谢章铤认为“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纯雅”[1](P3443),即以秦、柳、清真、易安等为代表的“婉丽”派,以苏、辛等为代表的“豪宕”派,以姜、张、梦窗等为代表的“纯雅”派。此流派划分法较为合理,并非简单以雅俗相论,而是相对完整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趋向,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宋词发展的原貌。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发展阶段在时间上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所重叠,如“婉丽”派的清真词实早已为“纯雅”派的兴起埋下伏笔,开其词风之先河。又如沈祥龙认为词有“婉约”与“豪放”,而二派之风不可过于偏废,如若是“房中之奏”却重“豪放”,就会缺少缠绵的情致;如若是“塞下之曲”却要“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1](P4049)所以,沈氏认为苏辛与秦柳实贵在集其长,无有偏废。
(二)对唐宋词的微观批评
唐宋词代表着词的最高成就,故历代都热衷于品评唐宋词人词作的风格及地位,近代亦不例外。由于此类批评数量很多,为避免杂乱,笔者特从批评流派视角切入,对其予以归纳概述。
其一,从浙西派的词学批评来看,其主要以“雅正”“清空”为标准,多以姜、张为批评核心而兼及其他词人。如陈廷焯前期提出了“五圣”说,其中属于两宋的有贺铸、周邦彦和姜夔。他还在唐五代词中最为推崇温庭筠和冯延巳,认为温词“风流秀曼,实为五代两宋导其先路”[1](P3719),而冯词则为“巨擘”。钱裴仲也推崇姜、张,认为其词最为清空;与此同时,他对柳词多有批评,认为其“无非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毫清气”[1](P3012)。江顺诒在《词学集成》中推崇姜、张,贬周邦彦,认为清真词未能达到“浑成”之境。张祥龄宗尚姜夔,批评黄、柳、梦窗,认为“山谷之村野,屯田之脱放,则伤雅矣”,而“密丽”如梦窗,则“失于雕凿”。[1](P4213)李佳虽崇浙派“清空”,但对不同风格词人亦有公允评价,如认为东坡《水龙吟》“淋漓悲壮,击碎唾壶,洵为千古绝唱”[1](P3106~3107)。
其二,从常州派的词学批评来看,其主要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等为标准,多推崇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辛弃疾、王沂孙等而兼及其他词人。如张惠言认为词中“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P1617)。周济推崇宋四家,所谓“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1](P1643)。邓廷桢评词虽亦主寄托,但多有折衷之论,如其亦同样推崇姜、张,认为“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1](P2530),又赞玉田词“堪与白石老仙相鼓吹”[1](P2532)。此外,他认为柳词有其高明之处,不可一味抹杀。蒋敦复宗尚“有厚入无间”,认为初学词虽应从玉田着手,但易“流于空滑”,所以还需要“以梦窗救其弊”。[1](P3671)陈廷焯后期于唐五代词推崇温庭筠、冯延巳、韦庄,认为温词乃“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1](P3777);于两宋词推崇“三绝”与“四圣”,“三绝”即周邦彦、姜夔与王沂孙,“四圣”在“三绝”基础上又增加了秦观。他认为周、秦胜在“理法”,姜、张胜在“骨韵”,碧山胜在“意境”,碧山词“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1](P3808)冯煦宗尚“婉约”,对于柳永、秦观、姜夔评价最高,尤其是他重新评价柳词云:“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1](P3585)这对于近代重新认识柳词及提高其地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陈锐认可“词贵清空,尤贵质实”[1](P4206),评词推崇周、柳、姜、吴,尤其是将姜夔与吴文英并举,体现出融合浙常的意味。陈氏对于词作批评往往独抒己见,如他认为姜夔《齐天乐·咏蟋蟀》“捏造故典”,张炎《南浦·咏春水》“了不知其佳处”。
其三,从融合浙常或自成一家的词学批评来看,近人主要以“词品”“雅趣”等为标准,多以苏辛、秦观、姜夔等为批评核心而兼及其他词人。如刘熙载以“词品”说为批评标准,推崇苏辛、秦观和姜夔,而对周邦彦和史达祖多有批评,认为二者虽有优势,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1](P3692)。谢章铤以欧阳、晏、秦、姜、高、史为词之正宗,亦崇苏辛,认为晏秦“妙丽”,姜史“清真”,苏辛独辟蹊径。谢氏对柳、黄、梦窗、竹山多有批评,认为他们分别因为“滥”“伧”“涩”“流”[1](P3470)而有所失。
三、近代对元明清词的批评
近代对元明清词的批评以清代为核心,其批评力度更强,涉及层面更广,尤其是侧重宏观批评与理论建构,彰显出学术总结的自觉意识。
(一)对元明词的批评
元明两代是词的衰落期,名家甚少,词学不兴。故近代对于元明词的批评宏观上主要集中于反思词学衰落之因,微观上关注的词人词作则屈指可数。如陈廷焯认为“词至元则衰,至明则亡,唯张翥一人堪称作者”[15](P809),“然明词之失,谁作之佣?论古者,不得不归咎于元代”[16]。谭献认为“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17](P54)。况周颐于元词推崇刘文靖,认为金元词“清劲能树骨”[1](P4456),能自成格调。张庆霖论及金章宗题扇词《蝶恋花·几股江龙骨瘦》,认为其词源于二主词。[14]又如丁绍仪认为明词衰落是因为“格调之舛”[1](P2575)。谢章铤认为明人“专奉《花间》”,不知宗尚“辛、刘、姜、史诸法门”[1](P3470),是导致明词衰落之因;但与此同时,谢氏也对刘基、高启、杨慎、王士祯、陈子龙等人评价较高,认为他们知词之法门,而其他明人则误以作曲为填词。陆蓥则认为“明以时文取士”[1](P2544),所以文人不关注诗词创作,遂导致其衰落。
(二)对清词的批评
清代与元明两代不同,清词号称中兴,故近代对于清词的批评,力度更强,层面更广,且更多是从词学研究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创作角度着手。这首先是对清词的宏观批评。
近人对清词的宏观批评主要围绕清词的发展流变、流派分类等热点问题展开。
其一,就清词的发展流变来看,近人主要有“三段”说、“三变”说、“三期”说和“三类”说等代表性的批评理论。谢章铤提出“三段”说,认为清词发展有“三段”[1](P3530),即“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此为第一阶段;“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此为第二阶段;“迨其后,樊榭之说盛行,又得大力者负之以趋,宗风大畅,诸派尽微”,此为第三阶段。张德瀛提出“三变”说,认为清词发展有“三变”[1](P4184),即“朱、陈角立”,去除明词积弊;“樊榭崛起,约情敛体”;张惠言创立常州词派。胡薇元提出“三期”说,认为清词发展有“三期”[1](P4038),即清初时期,以陈、朱等人为代表,“词采精善,美不胜收”;中期,以吴锡麒、洪亮吉等人为代表,“均称后劲”;嘉道以后,以龚自珍、张惠言等人为代表,“足继雅音”。谭献提出“三类”说,认为清词可分为以王士祯、钱芳标为代表的“才人之词”,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学人之词”,还有以纳兰性德、项莲生、蒋春霖为代表的“词人之词”,“与朱、厉同工异曲”。[18](P255)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杜文澜,他从创作成就、声律、词选、词谱等多个角度对清词发展进行了总结,如他认为创作方面“如朱竹垞、陈迦陵、厉樊榭诸先生,均卓然大雅,自成一家”[1](P2852);声律方面,万树《词律》“实为词家正轨”;词选、词谱方面,则以康熙时期的《历代诗余》《词谱》为代表。
其二,就流派分类来看,近代词学批评主要围绕浙常二派的总体得失展开。如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批评浙派后期的词坛有“三蔽”泛滥,即“淫词”“鄙词”“游词”充斥其间。谢章铤批评浙派填词好堆砌典故,滥用俗语,不得词之真义:“岂词独可以配黄俪白,摹风捉月了之乎。”[1](P3387)与此同时,谢氏又赞扬常州派功绩,认为“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1](P3485~3486)。又如谭献赞扬张惠言修正词坛风气之功,云:“茗柯《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1](P4005)蒋敦复也高度评价常州派,云:“独常州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窥唐人微旨。”[1](P3633~3634)
其次,是对清词的微观批评。清词创作极为繁荣,近代对于清代词人词作的品评亦是词学批评的热点。由于此类批评数量极多,且不少为零散状态,为避免杂乱,笔者特从历史时期视角切入,选择各个时期词人词作批评的几个焦点予以归纳概述。
其一,从清前期来看,近代词学批评主要以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三大家为批评核心,论及其风格、地位等。如胡薇元认为朱彝尊词“严密精审,超诣高秀”[1](P4038)。丁绍仪认为朱氏“于南北两宋词兼收并采,蔚为一代词宗”[1](P2590)。陈廷焯前期誉朱氏可“与白石并峙千古”[1](P3730),后期则对其略有批评,云其“微少沉厚之意”[1](P3834)。钱裴仲批评朱彝尊词用典过多,认为其词“故实多而旨趣少”,提出用典“须运化无迹,而以虚字呼唤之,方为妙手”。[1](P3013)又如谢章铤云:“大抵文字无才情,便无兴会……吾读迦陵长调,庶几绰有余勇哉。”[1](P3379)蒋敦复却批评道:“第如迦陵之叫嚣,反觉无味。”[1](P3640)陈廷焯则誉迦陵为“国初词家”之“巨擎”[1](P3837)。还有如胡薇元认为“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词坛”[1](P4038)。谢章铤云:“容若以情胜。”[1](P3472)李佳认为纳兰词风“清微淡远”[1](P3114)。谭献将纳兰性德与项莲生、蒋春霖归为“词人之词”,认为三家“与朱、厉同工异曲”[18](P255),又认为纳兰词风的形成源于其“别有怀抱”,但“容若长调多不协律”[18](P255)。李慈铭也批评“容若词长调不如中令,中令不如小令”[19](P234)。
其二,从清中期来看,近代词学批评主要以厉鹗、张惠言为批评核心,除了论及其风格、地位外,还批评其词学观。如钱裴仲极为推崇厉鹗,誉其“清高精炼,自是能手”[1](P3014)。谢章铤认为雍乾时期“词学奉樊榭为赤帜”[1](P3460)。谭献则批评其“苦为玉田所累”[18](P255),以致无法达到清真之浑化境界,并进一步批评道:学习朱、厉会“流为寒乞”[18](P255)。蒋敦复也批评朱、厉固步自封,“不肯进入北宋人一步,况唐人乎?”[1](P3636)又如谭献评张惠言词具有胸襟与学问,“开倚声家未有之境”[18](P255)。沈曾植也认为张词“疏节阔调”[1](P3607)。文廷式则批评张词“才思未逮”[20](P610)。陈廷焯极为推崇张惠言《词选》,云其“精于竹垞《词综》十倍……轮扶大雅,卓乎不可磨灭。古今选本,以此为最”[1](P3877)。丁绍仪则批评其《词选》“矜严已甚”[1](P2824)。
其三,从清后期来看,近代词学批评主要以蒋春霖为批评核心。如谭献誉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将之与纳兰性德、项莲生归为“词人之词”,认为三家“与朱、厉同工异曲”。[18](P255)谭献还誉《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17](P37)。又如李佳认为蒋氏作词“炼字炼意,极词家能事”[1](P3699)。杜文澜云蒋氏“性好长短句”,其词“专主清空,摹神两宋”[1](P2922)。
综合上述,近代词学批评方法多样而成熟,词学批评所涉层面广泛,批评力度强烈,理论性、学术性与系统性都得到了增强。近代词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近代的词学理论,对近代词学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