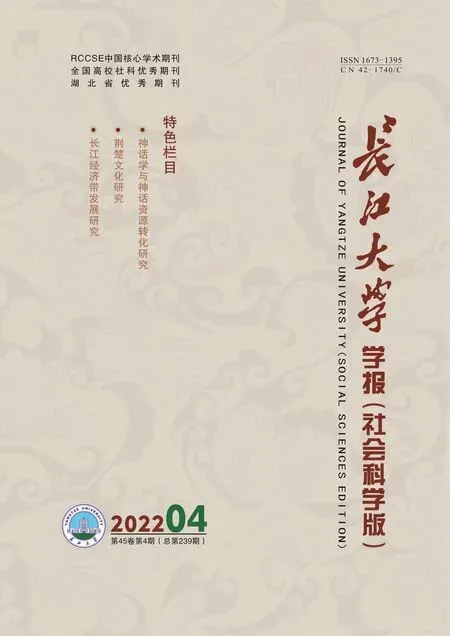语境视角下民间艺术形式的播布与重塑
——以聊城木版年画为个案
张兆林
(聊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聊城大学 黄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研究民间艺术形式不应停留在艺术形式本体,而应该观照与之相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将该艺术形式视为在某个特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活态传承的文化复合体。民间艺术形式的产生、发展、承继,并不限于一时一地,甚至其产生都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点,而只能用一个大致的时间段来圈定。民间艺术形式在我国各个地区的流传播布,与人群的迁徙、风俗的融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密切相关,在国家大势与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得以发展与承继,且随着不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呈现不同的时代样态或地域文化特色,学术界对此已有所关注,如杨帆围绕菏泽面塑开展的相关研究(1)杨帆的文章《乡土文化的传承、延续、断裂与再造——以山东菏泽面塑手艺发展变迁为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地域社会中手艺文化的塑造——以菏泽面塑手艺与地域社会的关联互动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流动的手艺:民间面塑与鲁西南地域社会的关系》(《文化学刊》2012年第5期)等,对菏泽面塑与鲁西南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研究。。
民间艺术形式的播布是随着人群迁徙而实现的,多是由一个中心点发展到多个地域点,经过一定的发展,多个地域点逐渐成为不同区域范围内各自的中心点,再由若干个区域中心点辐射到更大的地域范围。聊城木版年画就是符合该播布规律的典型民间艺术形式。现有研究资料表明,聊城木版年画是由迁至原东昌府(今山东省聊城市)一带定居的山西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移民凭借雕刻技艺创造的,其在鲁西地区广泛传播,聊城成为木版年画的生产中心,后又逐渐扩散至今泰安、潍坊、菏泽、滨州一带。此外,当地大量刻印艺人以家族、邻里、师徒、亲友等为纽带,集体外出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从事相关行业,聊城木版年画及木版书的刻印技艺被传播到更大范围。与此同时,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群,与之相伴而来的还有众多的其他艺术形式,这些也影响着区域内已有的社会风俗及艺术形式,地域社会在经济发展与人群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由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原本相对封闭的年画村落被动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本区域内逐渐出现了既具有民族普遍性,又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民间艺术形式,丰富了区域内原有民间艺术形式的题材,营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时性语境。因此,以聊城木版年画为个案,进行不同语境下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探析该民间艺术形式及有关技艺与地域社会的关联互动,勾勒其文化传统,深描该民间艺术形式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流传播布,有助于强化当地民众对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增强地域文化吸引力。
一、民间艺术形式的纵横向播布
民间艺术形式随着其所处历史时期与地域社会的变迁,被动地经历了自身艺术形态与命运的流变。笔者围绕聊城木版年画,对艺术本体、艺人、地域进行社会不同层面的剖析与描述,以期更好地展现民间艺术形式的本体及相关技艺的纵横向播布轨迹。
(一)聊城木版年画的纵向播布
木版年画的纵向播布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承继与变化。民间艺术形式本是区域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多是在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等特定时间点被广泛使用的娱乐形式或民俗用品,并因承载辟邪祈福、装饰审美、伦理教化等特定功能而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民间艺术形式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多是用来娱神娱己的物质载体与装点生活的符号饰物,更是部分民众赖以谋生的手段或产品,并可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艺人群体,甚至促成以生产该艺术形式为重要生计的村落或村落群,进而成为某一个地域内民众手工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处区域内的社会传统相关,故任何社会的变革或发展都会对其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初,山西平阳木版刻印技艺进入鲁西时,木版年画是部分移民谋生的一种技能,满足了迁入民众的精神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年画售卖增加了民众的农事收入。至清康乾年间,聊城木版年画业发展到鼎盛阶段,与当地刻书业、毛笔制作业等一起成为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康乾之际,聊城境内有木版年画店60余家、刻书作坊50余家、笔庄30余家,当地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一说。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运河聊城段频受黄河泥沙的影响,河道逐渐淤积乃至断流,当地因运河而具有的区位优势顿失,大量外来商人陆续迁往别处,百业日益萧条,木版年画业也不例外。直至建国前,聊城木版年画作为民间艺术形式,满足着区域内民众的部分精神需求,尽管年画店数量大减,且生产规模缩小,但是人们依然能够维持该类艺术形式的传承。1946年10月,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聊城开展了木版年画的改造工作,开办了进步年画店,将改造后的年画作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发动群众的新载体,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建国后,当地的年画生产一直停留在乡村作坊的层面,而且这种乡村作坊只有在秋收或入冬之后才会开工,印制的年画题材较之以往也少了许多,尤其是一些神像类的题材更是大幅减少。随着国民教育的推广,当地民众对除了门神、财神、天地神、灶神之外题材的兴趣减弱,但是戏出年画依然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生产队将本队的年画艺人集中起来,开办年画合作社,以此作为生产队的副业。据东阿县的民间年画艺人迟庆河回忆,“大队里成立了年画合作社。那时候用的版多数是老版,也组织人新刻了几套,当时干活是论产量,也就是计件给算工分。大小是个技术活,比干庄稼活挣得多。那时候印出来的年画,都是卖给茌平、平阴、东平、东阿。”(2)被访谈人:迟庆河(1944年生,农民);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5月11日;访谈地点:迟庆河家。在同一时期,聊城市的阳谷、冠县、临清、莘县、高唐等地也存在着类似的生产方式,销售范围大多是周边乡镇。
但是,这种生产场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合作社式的年画作坊被迫停业,市场上也不再允许木版年画买卖,年画艺人被迫转行,大量的年画木版作为“破四旧”的对象之一,被有计划地毁弃。“‘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十年动乱,以极‘左’的形式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无情的摧残,许多优秀作品都被诬为毒草加以批判和铲除,年画被列为四旧,民间的木版年画更遭到几乎是彻底覆灭的破坏,富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雕版被砸劈焚毁,老艺人被批斗,一批年画专业作者被迫改行,一些侥幸残存下来的画版也因长期无人管理而损失严重。年画遭到灭顶之灾,年画园地百花凋残,成为一片荒芜的沙漠。”[1](P200)
笔者在梳理资料及与文化部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文化工作者普遍认为,聊城木版年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处于断层期,既没有出现一些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木版年画,也没有人组织木版年画的刻印活动。但是,笔者在田野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如聊城、东阿多个村落的年画艺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然偷偷从事一些传统年画的刻印工作,原因就是当地乡村民众中还存在一定的年画需求,民众在私下还是努力找寻一些原本熟知的木版年画题材来表达自己朴素的精神欲求。据堂邑、迟庄等地的年画艺人回忆,每到年底,还是有一些民众私下里来家请灶王,请财神,“上岁数的老人总觉得过年不请财神,不请灶王,就没有年味”(3)被访谈人:栾喜魁(1939年生,农民);访谈人:张兆林;访谈时间:2016年1月24日;访谈地点:栾占海家。。
从表面上看,当地的传统木版年画基本销声匿迹,但这并不代表当地没有年画,当地民众仍然可以通过新华书店购买到一些表现劳动生产等场景的年画,以样板戏为内容的戏出年画数量较多。笔者认为,该类型的年画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木版年画,不再是通过木版刻印形式生产,不再反映民众传统的精神欲求,也不能满足民众在春节时特殊的心理期待,而是一种具有独特宣传功能的机器印刷品。为了更有效地表现一定的宣传内容,将年画的工具性发挥到更大,设计者甚至不惜改变传统木版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这些特定的宣传内容与民众所期待的春节喜庆气氛并无密切关系,其社会功用等与传统木版年画已经不可相提并论,但并不影响我们将其视为聊城木版年画的衍生品,因为其本身就是新年画改造的成品。随着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诸多民间技艺逐渐走进了当代人的现实生活,聊城木版年画由原来的年节装饰品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收藏品,并在国家、地方、民众的多方共同运作下,被人为地附加或释读了一些特定的“无形文化”的价值与蕴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体认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逻辑和象征意义。
聊城木版年画作为区域民众在年节等特定时间段内所需的特定艺术形式,曾广泛地被应用到地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随着区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蜕变,但依然被承继于区域村落的部分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承载着一定的民俗功能。虽然区域内的木版年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命运多舛,但相关技艺依然在一定范围的艺人群体内部承继,并未中断。新世纪以来,聊城木版年画被重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被文化部门或专家学者凝练或释读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元素,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与文化价值。因而沿着历史纵向的时间轴来梳理木版年画的播布,我们可以探索源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木版年画是如何在纵向播布中经历不断的发展变迁,又如何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受着来自民众、专家学者、地方社会、国家大势等力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播布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流动变迁的过程。
(二)聊城木版年画的横向播布
木版年画的横向播布主要体现为更大承继与销售空间的扩展和多地域文化的蕴积。任何民间艺术形式的产生总是可以追溯到一个相对明确的区域范围,且该艺术形式多因原生区域人员的流动或文化的交融,从原生区域向更大区域范围传播发展甚至海外播布,从而形成了该民间艺术形式所能影响的巨大地域性空间。民间艺术形式的播布也是双向的,即向外在区域播布的同时,也将外在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选择地融入到该民间艺术形式本身及其从业者的认知中,促成了该艺术形式在不同区域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民间艺术形式的地方类型或题材,使得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个地域文化特质的蕴积,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与地方文化特质。民间艺术形式的横向播布不只限于一国之域,也会穿越国界进入异族的文化体系,并对异族文化体系中的多种艺术形式产生影响,从而使得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同类或相近艺术形式有着某种类同的特质。
我国传统木版年画自在中原地区出现以来,逐渐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共享的民间艺术形式,其因朝代的更替、经年的战乱、人口的迁徙、物质的交流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多地扎根发展,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多个地方型民间艺术形式。至清中期时,我国除了东北、新疆、内蒙、青海外,其他地区都有年画生产的作坊及一定规模的年画艺人群体,并形成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山东东昌府、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台湾台南等十余个年画生产中心,也促成了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朱仙镇年画、东昌府年画等多个地方型年画艺术形式的形成。明朝时期,大量的苏州桃花坞年画被商船运到日本长崎售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爱与追捧,也促成了日本画匠用木版印制风俗画的尝试,于是,“一种新的方法出现了,它在十七世纪初已经充分研究成功,并且很适合于表达普通市民的生活与娱乐”[2](P157),浮世绘也就由原来的笔墨绘制发展为成熟的木版印制,其生产周期缩短,生产成本下降。
山西平阳移民携年画刻印技艺入住东昌府,民众分散居住在该区域众多的州县乡村,但是,木版年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出现,或者说,聊城木版年画的发展,肇始于今阳谷县张秋镇,学界将此处出现的木版年画称为张秋木版年画。到了清初,东昌府区域木版年画生产的重心转移到聊城县,并在其辖属莘县、堂邑、冠县、临清、高唐及周边的东阿等地形成了数个生产中心,促成了东昌府木版年画、张秋木版年画、莘县木版年画、堂邑木版年画、冠县木版年画、临清木版年画、高唐木版年画、东阿木版年画等同生并长的盛况,并在清康乾年间达到鼎盛。(4)关于今聊城区域内木版年画的发展轨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详见《从碎片到完整:聊城木版年画研究的转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此外,该地木版年画还传到菏泽鄄城等地,形成了菏泽木版年画。[3](P76)
由上可知,虽然民间艺术形式有纵向和横向两种类型的播布,但是其播布的核心要素依然是该民间艺术形式的技艺及艺人。艺人的流动,扩大了民间艺术形式的播布范围;而民间艺术形式播布范围的扩大,促进了该艺术形式及相关技艺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承继,又在其播布区域范围内培养了一批以此为业的艺人。民间艺术形式及掌握相关技艺的艺人在不断播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有视农业生产为国家之本,其他均被视为副业的传统,故在广袤的乡村,一直少有职业艺人或全职手工业者,其相关技艺与艺人身份多是在农闲之时才更为明显,是一种“农忙而隐,农闲而作”的间断性显现,这在我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承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聊城木版年画虽然在当地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但也只是作为民众农业生活的补充或帮衬,这也就决定了木版年画刻印艺人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只不过是农闲时多了一个年画艺人的身份标签而已,而且这种身份标签及社会对该身份的认可在地方史志中少有出现。聊城木版年画艺人虽多在本乡本土从业,但是也有部分艺人在农闲时外出从事刻印工作,如刻年画木版、木版书或葫芦画等,而农忙时则留在家务农。[4]这种错时制的人员流动及其带来的技艺流动,既有人为选择的原因,更有民众顺循自然天成的原因,且最终形成了该技艺播布的独特时空图景。
二、民间艺术形式播布与社会文化语境
无论是民间艺术形式有关技艺的播布,还是艺人群体传承区域的分布,都与该民间艺术形式所表达或迎合的地方文化或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也是该民间艺术形式在不同区域内承继的根本动力与现实制约。对具体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可以从其所在的区域社会文化图景入手,从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入手,将其理解为生活型的艺术或区域型的艺术,更具有可感性,也更便于理解民间艺术形式于广大民众的现实意义。
民间艺术形式对于民众而言是一种多功能的资源,既是一种娱神娱己的精神资源,又是一种谋生利己的物质资源。而民间艺术形式作为资源的不同解读,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图景及生活在该图景中的人群。分析作为资源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国家大势、地域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中如何被利用及重塑,对于构建及解读其与地域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特有文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通过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播布、有关技艺的承继、艺人群体的迁徙以及该艺术形式在不同时代的重塑等开展研究,有利于探寻该民间艺术形式嬗变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也有利于展现其所处区域社会的多彩历史文化图景。
区域社会文化是民间艺术形式在一定区域内播布的内在驱动力,其变迁也使得同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得以不断重塑。木版年画本是民众在某些时间节点上的实用品,其承载着在岁时节日和民间信仰中的某些民俗功能,而该功能也因国家大势和区域社会的变动而不断得以增益或消解。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木版年画对于没有年画生产作坊的区域而言,是广大民众娱神娱己的精神资源,在该区域的社会文化图景中扮演着某种类型的文化载体或者文化形式。然而,在有着年画艺人群体存在,尤其是在某些年画生产中心的区域社会中,木版年画虽然也是民众娱神娱己的精神资源,但对于该区域内部分民众而言,更是一种重要生计,木版年画的物质性生产优于精神性享受。
新世纪以来,我国传统木版年画逐渐淡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中多是被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品或旅游纪念品予以出售,其原有的民俗功能也被简化为某种民俗标识。尤其是在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传统木版年画被各级文化部门重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使得原本具有丰富民俗内涵的实用品又被动地附加了诸多无形文化的价值,使其自身承载的文化内蕴得以增益,并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解读。木版年画在其承继的过程中,由年节祭祀所需的民俗用品发展为新时期携有某些传统文化特质的文化象征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和部分民众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怀旧心理,而推动其发展进程的恰恰是现实的国家大势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民间艺术形式与乡土语境
笔者尝试将本研究中的民间艺术形式界定为,由民间艺人参与创造,反映乡间民众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满足乡间民众的某些精神诉求,并承继于乡间民众日常生活多层面的艺术形式。故,本文涉及的聊城木版年画就是在民间社会产生,并且深深融入乡间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或者说,其本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民众的现实生活,又是民众生活中的实用艺术。
语境概念的引入推进了民俗学者的相关研究工作,而且他们认为“就具体的民俗事象来看,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景、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共同构成了民俗传承的语境”[5]。在一个提前界定且相对明确的语境中,围绕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展研究,使得相关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民俗事象,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5)刘晓春曾对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该类成果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完成,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的成果。这类成果主要包括该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如黄涛的博士学位论文《民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以河北省景县黄庄语言现象的几个方面为例》(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岳永逸的博士学位论文《庙会的生产——当代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张士闪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社会与乡民的艺术表演——以山东昌邑地区小章竹马为核心个案》(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刁统菊的博士学位论文《姻亲关系的秩序与意义——以山东枣庄红山峪村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等。此外,还有张士闪的《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文史哲》2007年第3期)、《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等。,这对我们在新文化语境下开展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颇具借鉴意义。任何民间艺术形式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周围的人及物等构成了其所在的乡土语境,乡土语境是其存在及发展的背景。回首过往的相关研究,我们很遗憾地发现,一些研究者多把民间艺术形式“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无视具体时空坐落中的语言与制度体系、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人们对制度和行为的看法,更不考虑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5],研究的结果多是呈现一些脱离具体时空的无生命力的僵硬文化物象,其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与生命韧性反而被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就变得枯燥。
语境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因参与其中的时间流转、空间大小、人员多少甚至自然条件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语境的范围既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还可以是纵横向结合的,其范围的大小及取向取决于研究者的选择需要。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村落、乡镇甚至区域的语境范围,也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类型或人类族群的语境范围,还可以看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语境范围,更为复杂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内涉及不同人、物、社会、自然等纵横向错综复杂的语境,而同一个研究对象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迥异的面貌。任何一个可被选作研究对象的民间艺术形式,既存在于当前的文化语境之中,也存在于其生成之后的不同时间点的阶段性语境之中,还存在于其所播布的不同区域的多样化语境之中,在不同语境下的研究工作呈现不同的文化特质及多个侧面的特征。故,如要围绕具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展开研究,就必须要对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呈现形式及文化寓意加以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呈现一个真实而具体的民间艺术形式。
聊城木版年画虽是一项随移民而来的民间技艺,但是在鲁西一带广受黄河流域农作文化与运河流域商业文化的影响。聊城木版年画最初是由移民相携而来的刻印技艺以满足区域民众特定精神欲求的民俗用品,后来因掌握技艺人群的扩大而成为区域内部分民众群体生计的产品,又因时代变迁而成为新文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一嬗变过程虽然只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发展轨迹,但是其背后是政府移民、以技谋生、群体生产、文化认同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明初随移民而来的年画刻版技艺成为部分民众生活的帮衬,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民俗生活。对于迁居此地的山西移民而言,聊城木版年画不亚于其故土生活的一部分,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逐渐地方化并拥有了一些区域性的艺术题材。清康乾年间,聊城木版年画发展至鼎盛,成为区域内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群体性生计,周边也出现了一批年画村落,当地成为中原地区的年画生产中心之一。解放战争期间,聊城木版年画被选作冀鲁豫边区政府宣传新思想和动员群众的有效工具,并为边区政府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1949年以后,当地的木版年画生产维持在乡村作坊的层面。21世纪以来,聊城木版年画重新进入当地民众的视野,并在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保护工作中被给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身份标签,成为各级文化部门着力保护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时的聊城木版年画已从区域部分民众的群体生计发展为少数民众感兴趣的文化遗产,成为研究人员与收藏者所倾心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其民俗寓意与民俗功能已经被弱化。对于多数民众而言,聊城木版年画不过是一种怀旧符号或精神寄托的民俗遗产,“这样的‘非遗’在文化的领域之中也不过是一种标签化的摆设”[6],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
四、结语
通过上文,我们不难看到处于不同语境中的聊城木版年画,经历着由重物质表现到重精神象征的嬗变,由重经济收益到重文化蕴含的发展,嬗变与发展的背后是多种力量围绕民间艺术形式资源的多方争夺,聊城木版年画不过是被动地做出了适应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多方力量参与争夺与重塑的焦点是聊城木版年画刻印技艺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显性与隐性收益,尤其是民间艺人及相关力量对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争夺。此外,随着世界各国对本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和社会大众认知水平的提高,聊城木版年画在新语境下的文化附加值不断被强化,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对其可能带来的政绩的考量。当然,这种文化附加值对多数民众而言可能是隐性的,而对于民间年画艺人而言却是显性和可感知的,结果就是文化附加值对他们从事该类民间艺术形式所获得的收益及社会评价的变化。
将语境引入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或者在一个相对明确的语境中研究民间艺术形式,能够让观者看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宏大社会现实,更能看到一个与社会密切相关的活态艺术形式。在特定语境中存在的民间艺术形式,是对其历史沿革、题材、特征、功能等诸方面的活态展现,也将使得相关研究工作及研究成果更具有质感。
当然,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在一定语境中研究民俗事象或民间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正如有学者所担心的,“当一种研究范式为大多数学者所掌握,成为一种学术操作模式的时候,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沦为学匠式的重复劳动”。在一定语境中研究民间艺术形式,尽管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颇有帮助,但是也有将其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拿来套用的嫌疑。如何为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寻找一个更好的视角或工具,或者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是笔者今后思考与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山西木版年画展在山西美术馆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