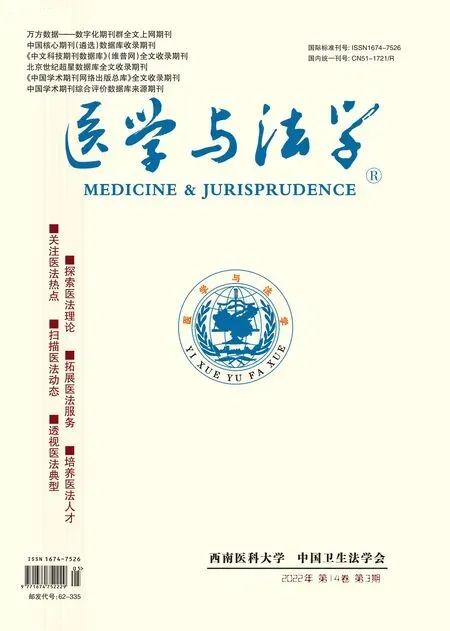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的法哲学基础
吴叶乾
患者的医疗决定权与其人格利益密切相关,根据人格利益的专属性原则,医疗决定当然由其自主行使。“一个意识清醒、精神正常、有表达能力的成年人当然可以对个人医疗独立地作出决定”,这是自二战以后由《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里斯本权利宣言》等一系列国际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的基本精神。虽然人是自身权利的最高主权者[1],但患者在医疗过程中随时存在丧失意思能力的可能,此时由于其难以对医疗行为有足够的认识以及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往往无法自己作出医疗决定,其相关医疗事务之决定往往会以家属、监护人、代理人等替代决定的方式呈现。这在实践中似乎成了不证自明的标准答案,也受到了传统“家庭中心”观念和医疗家长主义理念的有力支撑。
但“巴金晚年求死不得”“深圳拔管杀妻案”“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案”“榆林产妇坠楼事件”等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事件警示我们: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家属替代决定这一辅助行为,常常以家属等代理人之意志僭越患者本人之意思自由,患者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信仰偏好等人格利益受到侵害。因此,仅因成年患者丧失意思能力就否认其在自身医疗中的主体地位,并不具有法哲学上的正当性。虽可通过预先医疗指示之方式,先行确定医疗决定代理的大致方向与范围,以最大程度保障患者意思能力缺损时的意思自治,但仍需进一步阐明其理论基础。
本文拟据人的尊严不容折损、知情同意原则、先前自主权理论、主体同一性原理等,来对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的法哲学基础作出疏释。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取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一方面,人的尊严不容折损和知情同意原则是医事法一直以来的基础理论,且两者在内涵上具有高度的相合性,从这两方面论证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是基于对既有理论的重申与细化。另一方面,先前自主权理论和主体同一性原理是学界为了支持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而在法哲学上的积极探索,两者在内涵上是相互补充的,从这两方面进行论证,是基于对新理论的理解和阐释。笔者从以上四个角度展开对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之法哲学基础的探讨,以期能为患者医疗自决及其具体实现途径——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此外还当注意,所谓“意思能力缺损”是指相较于这一“意思能力健全”所指的正常状态而言的异常状态;本文所称“意思能力缺损患者”,仅指意思能力受损的成年患者;由于未成年人的意思能力本身就并不健全,故其不存在“缺损”这一异常状态,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内。
一、人的尊严不容折损
尊严是人的独有价值,它在人类认识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的过程中产生、在个体意识到与其他个体的独特差异中深化;它是哲学、法学、神学、医学乃至生物基因学等多领域都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现代尊严观将其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即是指“人之为人的天然属性”,诚如康德曾言“不能把你自己仅仅视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对他们来说,你自己同样也是一个目的”[2]。尤其是经过二战的洗礼,重新确认并保障人的尊严的规范和实践层面的行动愈加频繁,如今保障人的尊严成为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和几乎所有国家宪法的必备内容。人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抹杀,它是“人权”内涵的核心本质,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尺度,也是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实现医疗自决的逻辑出发点。
尊严之享有仅以人的客观存在为唯一条件,不以意思能力之有无为转移。因此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理应享有与一般人同等的人格尊严。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患者的尊严常因其意思能力缺损而被忽视。康德的尊严哲学赋予了人的尊严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不被当做“物”或者客体来对待;二是人应当自主决定自身事务。[3]然而,家属等在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的医疗中的绝对替代地位,却使得患者尊严的这两个方面都被或多或少地折损。一方面,当患者陷入持续性、不可逆的意思能力缺损状态时,如绝症终末期患者、“植物人”等,在其医疗过程中,常为挽救其生命而将其当做“物”或者客体而不是主体来对待;诊疗方案等则通常在其家属的控制之下,使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常饱受侵入性维生医疗措施所带来的的强烈痛苦,而被迫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存困境,使得其死亡时间可能就是医疗器械关机或停电时间[4]。在这种情况下,无意思能力末期疾病患者的生命质量极大下降,其隐私利益、信仰偏好、情感利益等“作为人的证据”也被完全忽视了。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也同样面临被“物化”的问题。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不受侵犯”,但现实中不乏借“保护”“救治”之名,将其作为“工具或者手段而非目的”而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利益的事例。例如南通市某福利院在1980至2005年年间,以“为免除患者痛经的痛苦及可能在不经意间怀孕等不良后果”,至少将9名患有精神障碍的女性送到医院做子宫次全切除。[5]因此,重新确立并保障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在其医疗过程中以及在医疗服务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是医事立法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对涉己医疗行为的决定权因其不具备直接行使的客观条件而被直接忽略。但以家属的决定直接替代患者本人的决定是否当然具有正当性?答案是否定的。医疗决定权作为人格利益,以权利人本人行使为原则,以代理人行使为例外。医疗行为是一种高风险、不确定的行为,大多具有侵袭性,对人类的生理机能、身体健康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损害[6],其后果仅能由患者本人承担且多是不可逆的,因此医疗决定应当由患者本人亲自作出。但患者丧失意思能力在医疗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若其在无法自我决定之时仍一味坚持患者自主决定,反而将患者置于不利境地;因此,为了不耽误医疗,医疗决定的代理也就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医疗决定代理的例外中,必须贯彻医疗决定不得代理原则的核心本质——应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意愿,代理人的选定和行动均得以患者的意愿而展开,此时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对自身医疗的决定方可通过意定代理人的行为得以延续,并且意定代理人应当抱持最大程度地尊重患者真实意愿、在必要范围内最低干预患者医疗、围绕患者本身寻求患者的最佳利益等原则,审慎且规范地行使医疗决定代理权。
这一设想可以通过认可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的医疗自决以及其实践层面的预先医疗指示制度来实现。为了保障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的尊严不受折损,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作用能够持续发挥,应当允许其在有意思能力的情况下作出预先医疗指示,对其丧失意思能力后的自身医疗作出安排。可以将指令型预先医疗指示和代理型预先医疗指示两种制度并举、相互补充,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患者意愿得以贯彻。所谓“指令型医疗指示”是指直接指向医师行为的特别的、具体的医疗偏好和期待;“代理型医疗指示”则是指通过指定医疗代理人来延续、贯彻自身医疗意愿的安排。
二、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作为普通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在反对医疗父权主义①的基础上,经二战后的反思和对患者中心地位的倡导,逐步确立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医事法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应当遵循以下要求:首先,患者本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医疗事务的最后决定者;其二,“同意”必须基于“知情”,即患者或其家属作出决定应当基于对当时所有必要的信息全部知悉并了解;其三,当患者神志清醒时,其同意、拒绝治疗的原因概不影响其行为之效力[7]。综上,医疗事务的展开原则上应当让患者充分知情并自主同意,且其所谓“同意”是为“决定”之意——患者对于个人医疗既有同意的自由,还有拒绝以及选择的权利;否则医疗行为就会因患者本人承诺(即知情并同意)这一豁免理由的消失而失去其正当性,回归其原始属性——一种与殴打、袭击无异的侵害行为。
知情同意原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知情”与“同意”。“知情”又包含着医师的说明和患者的知晓;“同意”不仅是指患者的接受,还意味着有权拒绝和选择。知情是同意的基础,同意是知情的延续,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8]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医生就医疗内容应该积极主动地向患者进行充分的说明,确保患者完全知晓和理解所说明的内容;而患者可以基于自主意愿,不受他人非法干涉地对医疗事务作出同意、拒绝或者选择。医师或者家属等对于患者而言都是促进其医疗开展的辅助者,应以最低干预、最大尊重患者个人意愿为基本准则,切实以患者为中心,不得“僭越”。
但知情同意原则需以患者具有意思能力为必要形成条件,当患者意思能力出现缺损时,与其相关的医疗活动是否就不受这一原则的约束?当然不是,否认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在其个人医疗中的中心地位,明显是对知情同意原则之核心要义的违背,是对野蛮的医疗父权主义的回归。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对其个人医疗知情同意的空间。本文认为,认可成年患者在尚且具备意思能力时对其意思能力缺损时的医疗事务进行知情同意的预先安排,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这种安排展开后续的行动,是知情同意原则在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活动中的应然体现。这就是“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的基本内涵,其在实践中则催生了预先医疗指示等制度。
三、先前自主权理论
认可成年患者在有意思能力时预先所作出的医疗安排可以延伸到其意思能力出现缺损的特殊阶段,德沃金的“完整自主权”和“先前自主权”理论为其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依据其在《生命自主权:堕胎、安乐死与个人自由的论辩》一书中的论述,人们通过两种权益——体验权益和关键权益,选择自主的生活方式,达成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体验权益,就是人们想要拥有做某些事的体验,这些体验是基于个人喜爱或偏好,所以因人而异;关键权益,则是人们以此来实现人生的圆满和正确,包括体验式偏好和关键性判断[9],“完整性”是其重要特征。在德沃金看来,关键权益在实现人生价值上更具重要地位,但对其的理解无法借助客观的描述,而需要从“从这类权益的内在本身来理解它们”[10]。他还指出:在经历了一系列经验、成就和种种艰难选择的磨砺之后,人们会逐渐形成基本确定、一贯的人格,构建起稳定、连贯的“整体性人生”的架构。此即“完整自主权”理论:人们所作出的决定“其实是和他想过的人生的整体形式有关”[11],可以辐射到作出决定的前后,乃至整个人生阶段。当一个成年患者意思能力出现缺损、丧失了继续作出医疗决定的能力时,其自主权并非就毫无挽救的可能。德沃金以“先前自主权”理论对此作了回应。要是一个成人在其具有意思能力时为他万一丧失意思能力后所需的治疗事先作出了决定,根据完整的自主权理论,这一决定蕴含了“完整、一贯的自主”之线索,应当获得最要的尊重。通过对过去所作决定的尊重,成年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可以延伸到无意思能力的阶段。这实际上与人们通过设定遗嘱预先安排自己死后的财产分配应当得到尊重有着相似的逻辑。美国1979年“马莱特诉舒曼案”(又称“耶和华见证人案”)中主治医师马莱特败诉,就是对此的有力佐证。其审理法官罗宾斯认为:基于自作决定原则和个人自主原则,该患者在此事件中就输血所作出的“不接受”决定,在她失去知觉后仍然有效,而该医师动手为她输血便会是未经授权的行为。②在本案中,法官认可了患者在丧失意思能力前对自身医疗作出的先前决定在无意思能力时仍有效,因为她的这一先前决定所体现的是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贯性的“关键权益”,如果对其加以否认,则会妨碍到其美好人生的圆满。[12]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无意思能力成年患者的医疗自主权以及预先医疗指示制度,并不一定指向死亡的选择;尽管它们在涉及死亡选择的领域更具突出作用,但我们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在这些领域。德沃金的“先前自主权理论”所强调的是尊重患者在先前所作出的决定,并在其丧失意思能力时继续贯彻,而不论其是怎么样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是消极的,如拒绝维生医疗、拒绝输血;也可能是积极的,如接受试验性治疗、接受必要的剖腹产等。
四、主体同一性原理
具有完整意思能力时的预先安排可以涵盖到意思能力产生缺损时的医疗,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前后的主体是同一的。这本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但在反对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自决和预先医疗指示制度的意见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成年患者的人格会因意思能力的丧失而失去同一性,即以意思能力丧失为界,之前和之后的成年患者实际上分立为两个主体——“自我(意思能力健全时)”与“非我(意思能力有缺损时)”。换言之,假设一个成年人因为疾病等原因导致意思能力不健全,此时的他根本无法意识到过去的自己是何属性,包括性格、偏好和价值观等等,实际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而该意见反对“自我”作出的预先医疗指示可以应用于“非我”时期,认为预先医疗指示因“自我”与“非我”的断裂而不复存在,成为废纸一张。该意见还主张“自我”与“非我”的关系较之其他人并非更亲近,反而因为其他人能从“非我”的一举一动中“理解”他,由这些人确认他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合理性。[13]这种意见虽然犀利,实则并不能站稳脚跟。
个人同一性,或称为“主体同一性”,起初由洛克提出,已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经典论题。它所追问的是:一个经历了诸多变化的人如何可能还是同一个人?一个此时之人在彼时如何可能还是同一个人?[14]笔者认为,德沃金的“完全自主权”的理论事实上已经可以回答这一追问,其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将经验内容与经验主体相混同,主体是由经验构成的,但经验无法取代主体;某些经验事件形塑了这一时期的主体特性,但这并不代表不同的经验事件就塑造出多个主体。我们需要诉诸经验变化背后的某种统一性,以这种统一性寻求将现在的自我与过去之我、未来之我视为同一。[15]否认成年患者在意思能力缺损前后的同一性的不合理性,这一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若将成年患者依据意思能力的健全与否划分为两个主体,在处理其相关法律关系时存在巨大漏洞:如果成年患者竟然能够成为两个法律主体,那么发生在前的诸多法律关系该何去何从?难道能认为成年患者因为意思能力的缺损而导致先前存在的亲缘、婚姻、债权等关系上发生了变化?这明显过于荒谬。人自出生以降即恒为同一人,我们并不会因为意思能力的变化而导致主体属性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否认主体同一性者还认为:意思能力健全的成年患者较之其他人,也并非能更好地理解丧失了意思能力后的自我,不如将此时的医疗事务交由家属、医师等其他人。这一说法亦不稳固,因为任何医疗行为都与患者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对此都应持审慎的态度,所以成年患者在意思能力健全时所作出的预先医疗指示应当被认为是理性的、合理的,其内容必定是基于对自己美好人生之“关键利益”的理解和安排。我们选择接受患者的预先医疗指示,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最完美的方案,而是因为它们是患者自己作出的,仅此而已。[16]并且,犹如上述家属、医师等在替代决定的过程中仍存在侵害患者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信仰偏好等利益的可能,既然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的预先医疗指示和其他人的替代决定都可能是不完美的,那为何不选择更具自主色彩的前者呢?
五、意思能力缺损成年患者医疗决定的完整程序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知道,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实行医疗自决在法哲学上是具有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的。一直以来,我国的意思能力缺损患者的医疗决定是由家属、监护人等代理人行使;其程序,除特殊情形下的医疗机构的紧急救治③外,一般是代理人通常基于自身判断或偏好而直接作出医疗决定。这即是从代理人到医师的两级程序;而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两级程序具有严重弊端。
因此,应在我国现有的意思能力缺损患者医疗决定的两级程序中加入预先医疗指示制度,以形成动态的三级程序:患者在意思能力健全时行使自主决定权而有作出预先医疗指示的,则代理人在代行医疗决定时应依此得出最终的医疗决定;患者在意思能力健全时没有作出预先医疗指示的,才由代理人直接作出医疗决定;并且,为了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医疗理念,即使是代理行使医疗决定,也应以保护患者最佳利益为目标,尽可能探寻患者的真实意愿和主观利益偏好,以体现其主体地位。
注释
①父权主义,又称家长主义、父爱主义,是指“一个人故意地控制另一个人的已知偏好或行为,而这种控制行为是以有益于或免于伤害受控制的人为目的来证明其正当性”。父权主义的行为方式具有强制性、主动性和善意性,常见于法律和政治领域。当父权主义表现在医疗领域时就形成了医疗父权主义。
②1979年美国曾发生过一起极具争议的“马莱特诉舒曼案”:马莱特女士因车祸重伤而失血过多,已经陷入休克,值班医师认为必须立即对其进行输血。但护士发现了马莱特身上有一张警示卡,表明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在任何情况之下均不得为她输血。但医师认为,如果不输血,马莱特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亲自为其进行了输血,马莱特最后得以康复出院。但半年以后,医师被马莱特诉诸公堂。经过近十年的漫长诉讼,上诉法院法官罗宾斯最终判定医师败诉。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