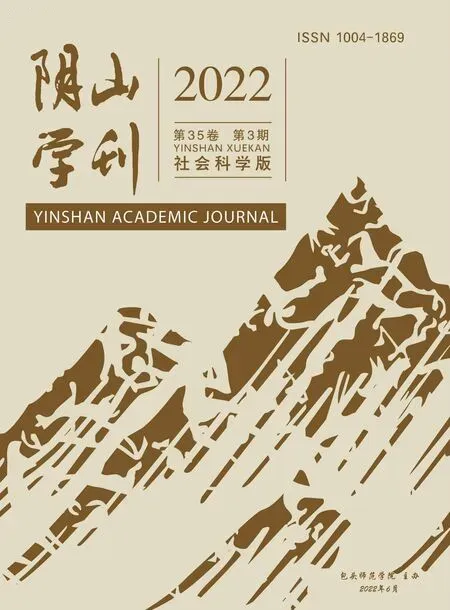唐代河西玉女信仰再探
濮 仲 远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各民族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河西亦曾出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局面。多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必然存在文化上的改造过程,从而使得该过程中民族性发生某些变化,使之显得更具有适应性。这种变化在唐代汉人的乐器、舞蹈、饮食甚至生活习俗上均有体现。然而,学界对异域文化如何具体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还需深入研究。本文以唐代河西玉女信仰为个案展开相关研究,这对于理解祆教(1)祆教,又名拜火教,波斯人琐罗斯德所创,流行于波斯及中亚诸国。祆教认为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火是光明的象征,代表善神。祆教也拜日月星辰及天,西晋末叶开始传入中国。唐朝祆教进一步发展,信徒渐多,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都建立了祆祠,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研究考证,仅长安内就有五所,分别在布政、醴泉、普宁、崇化、靖恭坊。在华夏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河西玉女信仰的渊源
唐代河西有较为兴盛的玉女信仰。如《旧唐书·李轨传》云:“有胡巫惑之曰:‘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李轨)遂征兵筑台以候玉女,多所靡费。”李轨失败后,“轨叹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台,置酒为别”[1]2250-2252。文中所言玉女,乃是一女神。李轨筑台而迎,可见希望玉女神保佑他的统治。但是,史书称:“崇信妖巫,众叛亲离,其亡也宜哉。”[1]2261可见崇信玉女成为大凉政权败亡的一个祸因。
玉女信仰除凉州外,敦煌也有其表现,S.5448《敦煌录》记载:
(敦煌)城西八十五里有玉女泉,人传颇有虚(灵),每岁此群(郡)率童男女各一人,充祭湫神,年则顺成,不尔损苗。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求郡人告之,太守大怒曰:“岂有川源妖怪害我生灵?”遂设坛备牲泉侧曰,愿见本身,欲亲享。[2]
川源指玉女泉水神。敦煌民众还信奉都河玉女娘子神,S.343《都河玉女娘子文》载:“天沐高(膏)雨,地涌甘泉。”文中表达了人们对雨水的祈盼,可见玉女神是当地的水神。玉女神不但司职雨水,还可庇护城郭,S.3914《结坛发愿文》:“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尚书先奉为金山圣迹,以定遐蕃;玉女渥洼,保清社稷。”[3]594敦煌有专门供奉玉女娘子的道观,P.4075背《某寺丁丑年破历》:“四月八日官取黄麻五硕,又粟肆斗,太宝(保)就玉女娘子观来着酒用。”[4]以上文献中的玉女神乃何方神祇?
玉女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渊源有自。据高启安先生研究,敦煌玉女神形象不仅与司霜雪的“天神青腰玉女”有关,而且融合了华山玉女的事迹,还与早期昆仑神话有一定的联系[5]。此外,余欣先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带有自然崇拜和上古神话色彩的“青女”后又称为“玉女”,成为道经中习见之神,应该是汉魏以降道教影响日深,被道教所吸收的结果[6]67。以上结论大致可从,本文略做补充。
玉女在《礼记·祭统》等文献中指容貌光泽之美女。汉时,玉女作为神祇名称而使用。如《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时,“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7]1250。又《汉书·地理志》:“陈仓,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育冢祠。”[7]1547王先谦《汉书补注》:“《真诰》‘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说文》引《甘氏星经》云:‘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祀之,曰明星。先谦曰:‘《地理志》……扶风陈仓有明星祠,即玉女祠矣。’”[8]可见,汉代有神祇玉女或明星玉女,其信仰跟女媊星有密切关系。汉时,华山始置明星玉女庙祀,东汉张衡《思玄赋》曰:“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9]此后,华山明星玉女名播渐广,从魏晋而下,降及唐宋,大量的诗文都只写华山的明星玉女,使华山玉女成为一个稳态化的合成词[10]40。李白诗云:“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11]唐玄宗李隆基御制的西岳华山祭文,也有“明星玉女、仙草琼浆”之词[12]。《太平广记》引〔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记载:“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13]其中“雨不加溢,旱不减耗”,表明华山玉女已有控制水的神力。同时期明星玉女还演化出仙人玉女和六丁玉女,二者均和道教有密切关系[10]40-41。
东汉末年,河西就有祭祀六丁玉女的活动,如董卓部将李榷“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刻厌胜之术,无所不为”[14]。《六壬大全》中指出,干支有奇偶之别,因而分阴阳。丁属阴干,有“丁为玉女”的说法[15]。《上清黄庭内景经》务成子注云:“六丁者,谓六丁阴神玉女也”[16]。因此“祠祭六丁”指对六丁玉女的祭祀。
综上所述,青女和华山明星玉女等信仰在不断传播的同时,又被道教所吸收。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玉女信仰亦传至河西,遂与民间信仰相融合,逐渐演化成了河西本土神祇。
二、河西玉女祆教化之表现
从上述研究结论判断,尽管河西玉女来历较为复杂,但至少是具有华夏文化背景的本土神祇。但是,本文认为唐代河西玉女还有另外一面,即受到祆教文化的影响。
1.凉州玉女
隋末凉州李轨建立大凉政权时,粟特人起到了关键作用。李轨举兵,不仅六位首谋中有曹珍和安修仁两位粟特人,而且具体的军事行动也有粟特人参与,“轨令修仁夜率诸胡人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1]2249。大凉政权建立之后,安氏家族“职典枢密者数十人”[1]2251。由于粟特人在李轨政权内部的强势,他们也成了被其他政治力量排挤和联合的对象,史载:
初,轨之起也,硕为谋主,甚有智略,众咸惮之。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1]2249
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因其大馁,欲离其众。[1]2250
无论是梁硕与安修仁发生矛盾,还是谢统师联合粟特人排除李轨旧人,始终与粟特人密切相关。正如吴玉贵先生所言:“隋末唐初,以安氏家族为代表的粟特胡人在凉州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直接左右着河西的局面,李轨政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向背。”[17]既然李轨政权中粟特人是其重要力量,那么前文所引《旧唐书》中鼓惑李轨迎接玉女的那位胡巫就可能为粟特人。因为一般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简称“胡”。又“巫”在《说文解字》解释为“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18]入华祆庙祆主一般都能行幻法、表演歌舞。如《朝野佥载》记载凉州祆庙祆主“铁钉从额上钉之,……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19]65综合以上,上文的胡巫即粟特祆主。既然胡巫与祆教有关,那么迎接的这位玉女也就带有祆教因素,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李轨为迎接玉女,特地建立了玉女台。中国古代通常祭祀神、仙、灵、祖的地方一般被称作庙、寺、殿、阁、观等,台式建筑并不多见。一般祆教会选择高台建庙。如阿富汗苏尔科·科塔尔有一座贵霜时代火祆教神庙,这座火祆教神殿建立在五层台基上,最顶层台基上有一个宽阔的台基,一直通向神殿,神殿主室包括中心内殿(11×11米),内殿中心还有一个方形平台,平台每一侧都带有三层台阶和一个柱基[20]66。粟特地区撒马尔罕附近的库尔岗达坂,也发现一座火祆庙,特征是,在升高六米的有台阶的月台上,有方形的生土砖建筑[21]245。根据李轨“征兵筑台以候玉女”“多所靡费”判断,玉女台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台基建筑。
其二,李轨失败后,选择携妻子上玉女台,置酒为别。这一举动令人匪夷所思,即李轨为什么会选择玉女台和置酒这样的地点与形式来告别故土?从后来他被安修仁俘获等史事可推知他并不想逃离。之所以有以上选择,可能与祆教豪摩祭有关。因为酒在祆教仪式中不可或缺,敦煌文献P.2569有“夏季赛祆用酒肆瓮”的记录[22]。《隋书·曹国传》称用“金破罗”酒器祭祀祆神。相关研究认为祆教仪式中,用豪摩酒(haoma)来祭神,供拜神者饮用。波斯《火教经》的haoma即是梵文《吠陀》的Soma。Soma是从植物中榨取的汁,饮之令人精神旺盛,是一种兴奋剂,可以长生不死[23]。可见李轨携家人登玉女台是一场具有祆教意味的祈福活动。
总之,李轨在建立政权中,利用玉女神团结凉州民众。由于政权多倚重粟特人,他们在塑造玉女神的过程中,不免受到祆教因素影响。
2.敦煌玉女
如果凉州玉女之祆教化还表现得不够充分,那么敦煌文献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变化。S.343《都河玉女娘子文》:
天威神勇,地泰龙兴;逐三光而应节,随四序而骋神;凌高山如(而)掣电,闪霹雳如(而)岩崩;吐沧海,泛洪津,贺(驾)云辇,衣霓裙;纤纤之玉面,赫赫之红唇,喷骊珠而永(水)涨,引金带如(而)飞鳞;与牛头如(而)粗(而角)圣,跨白马而称尊。邦君伏愿小娘子炎光扫殄,春色霞鳞;都河石堰,一修永全;平磨水道,提坊(堤防)峻坚。俾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膏)雨,地涌甘泉;黄金白玉,报赛神前。十方诸[佛],为资胜缘;龙神八部,报愿福田。[3]22
这是唐代敦煌民众在祈雨时的赛文。唐宋时期人们赛神一般有作赛文之习,如张说《赛江文》、杜牧《赛木瓜神文》等。引文祈赛的对象是玉女,人们把这位女神亲切地称为“娘子”,这种对女眷的称呼在敦煌文献和壁画题记中多有反映,可见这位女神已人格化。余欣先生曾从社祭变迁的角度解读了该文,认为唐宋时期敦煌社神职能被玉女娘子等诸多新神祇取代,出现了神祇碎化的现象[6]68。本文主要从祆教化的角度,对玉女神和得悉神进行比对,并探讨二者的关联。
(1)得悉神
有关得悉神的源头,有祆教说和突厥说两种观点[24]39。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2号古信札中有“得悉”一词。该信札的发信人曾提到他的儿子txs’yc-βntk。1965年,亨宁将古信札中txs’yc比附为唐代文献中的得悉神,并否定了将其比附为突厥部落Tuxsī的观点。因此,txs’yc-βntk一般汉译作“得悉槃陀”,意为“得悉神之仆”[25]。关于粟特文古信札年代,学界一般倾向于公元4世纪初。西突厥在中亚建立统治地位则始于隋唐易代之际的统叶护可汗时期。因而公元4世纪就已出现的得悉神源于突厥部落似难成立[24]40。
1900年,新疆焉耆七星乡出土一件银碗,碗沿上刻粟特铭文。经西姆斯·威廉姆斯释读,有“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之句,并指出该神名带阴性词尾,表明是女神[26]。据蔡鸿生先生考证,得悉神很可能是祆教的“星辰雨水之神”,即tištrya,粟特城邦盛行女神崇拜,于此又添一证[27]。
这位祆神在中亚地区流传甚广,《隋书·曹国传》记载:
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28]
曹国乃昭武九姓国之一,“金破罗”则是“丈余阔的酒器”。从祭祀所用驼、马、羊及酒数量而言,得悉神在曹国地位崇高。不仅如此,“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信仰在古代中亚地区具有普遍性。总之,得悉神至迟出现于4世纪的粟特本土,学者们将其比附为琐罗亚斯德教的雨神tištrya。
(2)赛文中得悉神的特征
鉴于中亚粟特地区的祆教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存在密切联系,可利用琐罗亚斯德教文献中tištrya内容和考古发现与赛文玉女形象进行比对。
第一,玉女“吐沧海,泛洪津”,“俾五稼时稔,百姓丰年;天沐高(膏)雨,地涌甘泉”,显然是位司雨之神。据《阿维斯塔》专门赞颂雨神的《蒂尔·亚什特》云:“我们向光明与光荣的星辰献祭!人们仰望这一星辰,暴风雨洒向山岭,雨水洒向平原。人们仰望着她,在坏年景或好年景来到国土,(他们自己想)怎么使Aryan乡土成为丰饶的土地?”[29]160此处“星辰”即tištrya,其掌管雨水的职能与玉女相同。
第二,玉女有“纤纤之玉面,赫赫之红唇”等脸部特征。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4—1905年),在高昌古城以北20里火焰山胜金口发现一批高昌火祆教彩色泥塑神像,其中C号女性天神的头部细节是脸为白色,双颊、下颏、嘴以及额头靠近鼻子处为朱红色,眼眉为黑线条,眼皮周边描以黑线[20]62。虽然我们不能判断其塑像是否为得悉神,但其形象颇符合玉女“玉面红唇”的特点。
第三,赛文有“与牛头如(而)粗(而角)圣,跨白马而称尊”等描述,牛、马等元素在中国古代祈雨场景中并不多见,却是祆教祈雨中的重要内容。牛灵在祆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山西介休祆神楼中即有牛灵头像。1982年,天水发现了由数方画像石和素面石条组成的石棺床,其中编号为9的石屏风画像,就有从神牛口中不绝地淌出酒的图像,反映的是在祆教仪式中用酒祭祀雨神的场面,也是敦煌文献《安城祆咏》中“朝夕酒如绳”一句的形象说明[29]158-159。中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重要神学著作《班达希申》记载:奥哈尔玛兹德向提什塔尔(tištrya)“赋予十匹良马、十峰骆驼、十头牡牛、十座山、十条河之力。”[30]
马作为得悉神的化身常出现在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和考古资料中。tištrya专司降雨,但是反对派旱魃阿普什却尽力阻挠,由此引出“雨神和旱魃之战”的神话故事。《蒂尔·亚什特》记载:威严的提什塔尔化作金耳朵的白骏马,戴着镶金辔头飞落法拉赫·卡尔特河边,与变成黑秃马的旱魃阿普什大战[31]235。《蒂尔·亚什特》还记载了tištrya每月的三次变形,每月凡十日一变,最初为“健美威武的十五岁青年”,其次变为“金犄角的公牛”,最后变为“金耳朵的白骏马”[31]234。这三次变形与赛文中玉面青年、带角牛头和白马等要素完全相符。另外,唐代《酉阳杂俎》也记载了阿姆河岸边祆庙中的铜马,对此荣新江先生认为可能是得悉神的化身[32]349。撒马尔干阿弗拉西亚卜的一幅7世纪的大壁画上,有一支队伍正奔赴帝王陵墓,队伍中的两个人之间有一匹戴鞍鞯的马,马前面的人将它牵向一位祭司。马尔沙克接受葛乐耐的意见,认为此马是用来表示粟特雨神tištrya[32]347。基于此点,学者们判断日本美秀美术馆所藏中国北朝时期一组石棺上马崇拜画像与tištrya有关[24]47。
通过以上分析,赛文中白马、公牛和祈雨等内容与得悉神特征相符。
3.玉女祆教化的原因
中国传统神祇玉女受到得悉神的影响,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与祆教在河西传播关系密切。众所周知,由于古代河西走廊曾是粟特人兴贩的必经之路,故而其所信仰的祆教传至河西。早在晋代,有刘弘等在凉州天梯山“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33],王素先生认为从燃灯鼓吹光明的宗教形式来看,其为火祆教[34]。唐代河西有不少祆庙,如P.2005《沙州图经》记载:“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35]13这座位于敦煌城东的祆庙,有二十个神龛,其祭祀的祆神不在少数。又如唐人张鷟撰《朝野佥载》卷三云:“凉州祆神祠,……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19]65该文不仅记载凉州祆庙,而且透漏出离凉州数百里的西祆神可能是甘州祆寺[36]。9世纪中叶,敦煌赛祆活动较为频繁,每年要举行数次活动,期间一般支出酒、粮食、油、灌肠等神食[21]254-255。随着祆教不断传播,祆教习风也自然融入当地民风。
第二,二者相同的神格。敦煌玉女的原型之一即青腰玉女,是一位主霜雪的女神。《淮南子·天文篇》记载:“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诱注曰:“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37]据前文所述,得悉神被比附为琐罗亚斯德教的雨神tištrya。相同的神格是彼此能够融合的先决条件。
此外,得悉神之所以受到粟特人的重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属严重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其耕地和牧场对雨水的依赖很强,所以祈祀得悉神就成为他们的重要话题。与粟特地区具有相似气候环境的河西,对水祈盼的问题同样突出,如唐宋时期敦煌祈赛的水神就有张女郎、雨师、风伯等。因此具有施雨神职的得悉神容易被河西民众所接受。
第三,和祆教本身特点有关系。林悟殊先生研究指出,传入中国的祆教虽包含了早期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但它们自己并没有完整的宗教体系,其性质盖可界定为粟特人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因为民间信仰并不像很多体系化的宗教那样,具有强烈的宗教排他性,其兼容性使其教徒较为容易地接受其他宗教。因此火祆教是粟特人的民俗,似乎更能以感性的模式为汉人所接受[38]。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受到祆教影响,不止玉女其例。P.2569《儿郎伟》:“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大祆,但次三危圣者。”[3]945安城大祆已融入当时岁末的驱傩活动中,成为部领之神。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把祆神归入杂神类,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风伯、雨师、土地并列[35]13。池田温教授指出:“敦煌的祆神尽管还保留着祆神的名称,但是其实际机能已完全同中国的礼仪以及民间信仰相融合,与汉人的信仰合为一体。”[39]
基于以上三点原因,一个穿霓裳,驾云辇,保留有汉文化特点和汉名的神祇,变成一个有白马、牛头等祆教因素的新神祇,满足了唐代河西各族民众的信仰需求。
四、结 语
唐代西北民族大量涌入河西地区,各民族在这一地区共同生存,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过程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要在另外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就要适应该地的文化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玉女祆教化的同时,得悉神亦在汉化。具有汉文化背景的玉女和祆教得悉神的结合就反映这一过程。玉女源自华夏传统的星辰信仰,后来又演化成华山玉女、青腰玉女、六丁玉女等,被道教所吸收。随着玉女信仰的不断传播,又和地方的民间信仰合流。魏晋间,随着粟特人的东渐,河西的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成了他们的聚点。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习惯,在聚落建立祆祠。在祭祀祆神时,所表现的幻术、燃灯、舞蹈等祆教仪式被汉民众逐渐接受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得悉神借助于同样具有施雨能力的玉女的形象而传播,逐渐二者合为一,成了混合多元文化特征的新神祇。总之,祆教在华夏的传播,会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但同时也是本土化的过程,最终被华夏文明所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