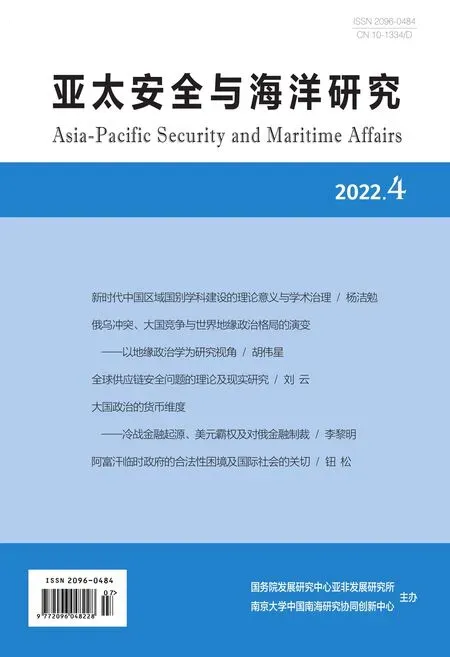论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
卜凌嘉
内容提要: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现有的一些主张——“平台决定法律地位说”“军舰说”“船舶说”“军事装置说”,均有其依据及其问题。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其安全和权益,而且适用范围有限。“军舰说”不符合《海洋法公约》对军舰定义的文义解释和缔约国的意图。现阶段,海上无人系统不满足《海洋法公约》第94条对船舶的航行安全和第98条对海难救助的实质性要求,将其作为船舶存在安全隐患。“军事装置说”有利于保护沿海国安全,但可能会遭到海洋军事强国的反对。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的利益冲突,不仅会影响其对无人系统的定性,还会阻碍相关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曾多次发现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潜入我国海域搜集海洋军事信息。2016年12月,中国海军救生船在南海相关海域对一水下潜航器进行查证识别,美国国防部称该潜航器正在执行军事海洋测量任务。(1)参见《美称中国海军在南海捕获美军无人水下潜航器》,环球网,2016年12月17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duP [2022-05-01]。2020年至今,江苏渔民在我国领海发现十个他国制造的可疑装置,具有水下调查、识别、窃密等特殊功能,给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参见《江苏渔民捞获10个境外水下窃密装置》,新浪网,2022年1月17日,http://k.sina.com.cn/article_1301904252_m4d997b7c03300xri9.html[2022-05-01]。由于域外国家介入东海和南海的军事行为越发频繁,预计美国等国家将在我国管辖海域内使用更多更先进海上军用无人系统。
一、从海洋和平与安全角度研究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法律地位
海上无人系统(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指非载人且有自主推进能力的海上系统或装置,主要包括无人水面航行器(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无人潜航器(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和海上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s)。(3)我国海洋工程科学者把“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翻译成水下机器人,参见李硕等:《我国深海自主水下机器人的研究现状》,《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8年第9期,第1152页。海上无人系统既可用于民用用途,如海洋科研、海洋矿藏资源勘探和海底电缆管道埋设及维护等,也可用于军事领域。由于具有在极端情况下长时间工作、低成本、精确度高和人员伤亡零概率等优势,海上无人系统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优势不容忽视,无人系统与有人战舰混合作战,可能会改变未来海战的模式。(4)参见马存瑞、刘瑞瑞、文曦、吴伟伟:《美国海军无人作战系统分析》,《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21年第11期,第20—21页。
为应对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对我国海洋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必要研究该系统的法律地位及其相关权利义务。中美南海无人潜航器事件曾引发国内学者对水下潜航器法律地位的研究。(5)参见郭中元、邹立刚:《南海无人潜航器事件的国际法评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8页;王淑敏、唐晓聪:《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法律地位研究——“中美无人潜航器事件”引发的思考》,《时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3—8页;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1—27页。有学者指出应根据无人潜航器的控制平台判断其法律地位, 有的学者则认为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6)参见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5页;刘丹:《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规制——法律地位、现实挑战与我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7页;王淑敏、唐晓聪:《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法律地位研究——“中美无人潜航器事件”引发的思考》,《时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7页。
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其规模、性能和作用还在不断演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娜塔莉·克莱因(Natalie Klein)认为,对海上无人系统的法律定性需要结合该无人系统的性能特征及其开展的具体活动情况,遵照各与之相关条约规定的目的和宗旨进行个案分析。(7)Natalie Klein, “Maritime Autonomous Vehicl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to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 95, 2019, p. 251.换言之,探讨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仅要根据特定系统的特性和功能,更需要结合特定条约的目的。具体而言,每一条约有其特定的目的,不同条约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定性可能不一样,而不同的国家对同一条约存在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国家之间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定性也可能不一样。
现有研究很少从海洋和平与安全角度探讨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同于民用无人系统尤其是无人商船用于货物运输,所涉法律问题主要是海事安全问题(8)从海事法角度对无人商船法律问题的探讨,参见李瑞:《无人船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华海洋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第149—164页;孙誉清:《商用无人船法律地位的界定》,《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7—138页;初北平、邢厚群:《海事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创新——以无人潜航器法律适用困境为例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76—81页。, 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因为有情报搜集和军事打击等功能,本身具有威胁性,对海洋和平与安全有重要影响。维护海洋和平是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宗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序言指出,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与加强各国之间和平和安全是该公约的重要目的。本文将从海洋和平与安全的角度研究和平时期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问题。(9)由于海上无人机主要属于航空法规范的内容,本文从国际海洋法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以海上无人水面航行器和无人潜航器为研究对象。
二、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法律地位的理论争辩及分析
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属于军舰、船舶还是设备或装置,将影响其在国际法层面的权利义务。国际社会对海上无人系统还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国家实践和学术界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观点,主要包括“平台决定法律地位说” “军舰说” “(政府非商业服务)船舶说” “军事装置说”。以下将简要介绍各种观点,对其进行分析评论。
(一)根据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控制平台决定其法律地位
国内外一些学者主张根据无人系统控制平台判断海上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具体指根据发射控制平台的地位决定海上无人系统法律地位。(10)国内一些学者按照操作方式把无人潜航器分为五类:具有自主规划、自主航行、自主环境感知能力的全自主型;由预先内置的程序进行控制、按照内置程序航行并执行任务的程控型;非自主航行的通过岸上人员进行远程操作的岸基遥控型;从工作母船释放的、通过工作母船上的人员进行操控的船基遥控型;用于攻击等作战、杀伤目的的武器型。参见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1页。美国海军把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分为三类:一是有人控制型(需要有人循环不断或者几乎不间断的控制);二是半自主型:无人系统的有些功能是完全自主的,例如往返行动和激活传感器,有些功能由操作者控制如武器开火;三是全自主型:自主行为并自主作出决定的无人系统。参见:US Navy, The Navy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 Master Plan, 23 July 2007, http://www.navy.mil/navydata/technology/usvmppr.pdf[2022-05-01]。国外相关观点如下:如果海上无人系统通过遥控方式航行,尤其是由军舰所控制的无人系统,它们就可以被认为是控制平台的一部分,因此也分享此平台的法律地位;如果海上无人系统为自主航行,那么它们不能分享发射平台的法律地位。(11)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Warship,” in Frauke Lachenmann and Rüdiger Wolfrum eds.,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ra. 15.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罗布·麦克劳林(Rob McLaughlin)认为,由船舶或潜水艇发射并由其母船控制的海上无人系统构成该船舶的一个系统,实际上是该船舶的延伸,因此具有母船部分的地位,而没有独立的地位。(12)Rob McLaughlin, “Unmanned Naval Vehicles at Sea: USVs, UUVs, and the Adequacy of the Law,”Journal of Law, Information and Science, Vol. 21, No. 2, 2011, pp. 108-109.德国海军的《指挥官手册:海军军事行动法律基础》指出,如果海上无人系统由军舰控制,则该系统享有与军舰同样的法律地位和豁免。(13)German Navy, Commander’s Handbook: Legal Bases for the Operations of Naval Forces, 2002, S. 2.11.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控制平台是影响海上无人系统法律地位的关键。宋淑华、赵劲松认为,船基遥控型无人潜航器,为实现其母船或军舰作业的目的,被释放在水中进行作业,不具备独立的船舶法律地位,而是构成其母船或军舰的工具。刘丹也赞同这一观点。(14)参见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5页;刘丹:《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规制——法律地位、现实挑战与我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7页。
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根据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发射控制平台决定其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海洋安全与权益。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在沿海国管辖海域内的行动,容易引起所属国和沿海国的纠纷。例如,对于出现在沿海国领海内的不遵守领海无害通过法律的无人潜航器,沿海国需要首先判断该潜航器的法律地位,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按照发射平台决定论,如果无人潜航器是由军舰发射和控制的,其享有军舰的法律地位。根据《海洋法公约》第30条,沿海国对于不遵守其关于领海通过的法律和规章,且不顾沿海国向其提出遵守法律和规章要求的军舰,仅可要求该军舰立即离开领海。这意味着沿海国只能要求该无人潜航器离开领海。而如果无人潜航器是由军舰以外的平台发射和控制的,其不享有军舰的法律地位。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5条,沿海国可对该无人潜航器系统采取包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必要措施防止非无害通过。然而,对于不搭载无线通信设备的小型无人潜航器,沿海国无法与其建立通讯联系,也缺乏合适的手段去查验核实无人潜航器的控制平台,无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难以对该无人系统采取相应措施。因此,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其海洋安全和权益。有研究者就指出,平台决定论与沿海国的利益直接冲突。(15)Oliver Daum,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Unmanned Naval Craft,”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 49, No. 1, 2018, p. 87.
其次,根据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发射控制平台决定其法律地位的主张适用范围有限。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可能在军舰上发射,也可能在军用飞机、陆地平台或者由其他海上无人系统发射和控制。平台决定论无法确定在船舶以外平台控制的海上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对此,一些国内学者主张,全自主型、程控型和岸基遥控型无人潜航器具有独立的船舶地位。(16)参见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5页;刘丹:《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规制——法律地位、现实挑战与我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7页。然而,无人水面航行器的主流结构可能是遥控和自主型混合操作,因为混合型模式可以兼具遥控型和自主型两种模式的优点。(17)Paul W. Pritchett, “Ghost Ship: Why the Law Should Embrace Unmanned Vessel Technology,” Tulane Maritime Law Journal, Vol. 40, No. 1, 2015, p. 200.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海军无人水面航行器总体规划》,半自主型无人系统属于遥控和自主型混合型,其有些功能是完全自主的(例如往返行动和激活传感器),有些功能如发射武器由操作者控制。(18)US Navy, The Navy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 Master Plan (Executive summary), 23 July 2007, p. xi. http://www.navy.mil/navydata/technology/usvmppr.pdf[2022-05-01].对于同一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所属国可根据其实际需要,同时适用不同的操作模式,或者在不同的操作模式之间进行切换,例如无人水下滑翔机在下潜海底时无法接收卫星信号,需要进入自主型模式,而当其上浮水面时则由控制平台遥控,而控制平台可能根据需要在陆地平台和军舰平台之间切换。因此,根据发射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有限,难以适应所有类型的海上无人系统。
最后,有的国家反对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美国的《海上军事行动法律指挥官手册》指出,水面无人系统和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地位不取决于其发射平台的地位。(19)US Navy, US Marine Corps and US Coast Guard, 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Naval Operations, 2007, para.2.3.6.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卡斯卡(James Kraska)认为,美国海军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必然取决于发射无人系统的船只、潜水艇或飞机。(20)James Kraska, “The Law of Unmanned Naval Systems in War and Peace,” The Journal of Ocean Technology, Vol. 5, No. 3, 2010, p. 56.美国的国家实践不代表国际法规则,但作为拥有众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海洋大国,其主张对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和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其海洋安全和权益,适用范围有限,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存疑。
(二)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军舰的观点
有的国家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视为军舰,例如丹麦国防部编制的《国际军事行动国际法军事手册》认为,军舰和其他海军船只,既包括常规船舶,也包括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航行器。(21)Danish Ministry of Defense, Military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Relevant to Danish Armed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eptember 2016, p. 597.少数外国学者如德国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教授沃尔夫·海因切尔·冯·黑因格(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认为,海上无人系统可构成军舰。(22)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Warship,” in Frauke Lachenmann and Rüdiger Wolfrum eds.,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ra. 15.
《海洋法公约》第29条,将军舰定义为“属于一国武装部队、具有辨别军舰国籍的外部标志、由该国政府正式委任并名列相应的现役名册或类似名册的军官指挥和配备有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的船员的船舶”。
一些研究者认为,由军官“指挥”可以包含位于岸上的军官遥控行为,“配备”船员可以指岸上或不亲身位于无人系统上的军事人员对该系统航行、工程、传感和武器系统的监控行为。他们认为,“指挥”和“配备船员”更多是指实施行动的责任和能力,或确保采取某种行为,而不仅仅是亲自现身。(23)Natalie Klein, Douglas Guilfoflye, Md Saiful Karim and Rob McLaughlin, “Maritime Autonomous Vehicles: New Frontiers in the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20, p. 724.黑因格指出,军舰须由军官指挥和配备服从部队纪律船员这一要求的重点不是要求军官和船员在船上控制船舶,而是操作船舶人员的身份必须是船旗国正规部队成员。军舰的定义源自19世纪国际法禁止私掠船只参与海上武装冲突的实践。根据习惯国际法,只有冲突国家的军事船舶才能开展交战行为,因此有必要区别军舰和私掠船。1907年《关于商船改装为军舰公约》第3和第4条最早规定“由战舰舰队军官指挥和由服从军事纪律的人作为船员”,是军舰区别其他船舶的标准。对军舰的这一要求被写入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第8条。《海洋法公约》对军舰的定义受到这两个公约的影响。(24)Simon McKenzie, “When is a Ship a Ship? Use by State Armed Forces of Un-crewed Maritime Vehic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2, 2020, p. 398.黑因格认为,《海洋法公约》这一定义并不一定意味所有军舰须载人操作,该要求的目的是规定只有对船旗国负责的正规部队才拥有交战权。因此,如果遥控或控制无人海上船只的人员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无人船只可构成军舰。(25)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supra note 2, para. 16.
这种观点有几个问题:一是不符合条约解释规则中的文义解释。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国际条约的解释通则,其第1款指出“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其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根据这一规定,解释条约应首先考虑文义解释,即文字通常含义。《海洋法公约》第29条中“配备”的英语表述为“manned by”,《牛津英语辞典》对“man”这个动词的最常用解释是提供人力(to provide with a man or men),该词来源军事和海事领域,指向(堡垒或船舶)提供一个人或一群人作为船员或防卫军队。(26)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https://www.oed.com/[2022-05-01].根据对“配备”一词的通常解释,军舰应当指载人航行的船只。如果把“manned by” 解释为无需登船的遥控行为,这将与无人系统的关键词“unmanned”(无人操纵)产生语义重复,逻辑上不合理。因此,把遥控和控制行为解释为 “配备”违反条约法解释的基本要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斯米特和英国皇家海军的大律师戈达德(Schmitt and Goddard)合作的研究就指出:“海上无人系统是不载人的(至多是由人遥控),根据对配备服从军事纪律的船员的字面解释,海上无人系统不符合军舰的要求。”(27)Michael N. Schmitt and David S.Goddar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Military Use of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8, No. 2, 2016, p. 579.二是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情况,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解释为军舰超出缔约国意图。公约在1973—1982年起草,由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海上无人系统还未进入公众认知范围,因此缔约国对军舰的理解显然是指载人航行的军事船舶,将不载人的海上军用系统纳入“军舰”的解释,超出公约起草时缔约国的意图。由于《海洋法公约》的这一定义得到广泛承认,并且普遍认为其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上述对军舰的扩张性解释能否获得缔约国的接受存在疑问。三是全自主型海上无人系统,不符合由军官指挥的要求。对于具有自主感知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的全自主型海上无人系统,其执行任务过程无需人工干预,不符合《海洋法公约》军舰须由军官指挥的要求。如果把这类预先编程的自主操作也解释为“配备”,那么对军舰明确措辞的解释就太过牵强。(28)Robert Veal, Michael Tsimplis and Andrew Serdy, “The Legal Status and Operation of Unmanned Maritime Vehicle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50, No. 1, 2019, p.31.
总而言之,根据《海洋法公约》对军舰定义的文义解释和缔约国的意图,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军舰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政府非商业服务)船舶的观点与国家实践
不少学者主张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船舶。例如,服务于美国海军的汉德森(Henderson)根据美国国内法提出军用无人潜航器属于船舶。(29)Andrew. H. Henderson, “Murky Waters: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s,” Naval Law Review, Vol. 53, 2006, p.7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员麦肯兹(McKenzie)主张,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30)Simon McKenzie, “When is a Ship a Ship? Use by State Armed Forces of Un-crewed Maritime Vehic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2, 2020, pp.383-386.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全自主型、程控型和岸基遥控型无人潜航器具有独立的船舶地位。还有研究者认为,无人潜航器为海军辅助船。(31)参见宋淑华、赵劲松:《无人潜航器的法律地位》,《南海学刊》2017年第3期,第25页;刘丹:《无人潜航器的国际法规制——法律地位、现实挑战与我国的应对》,《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7页;初北平、邢厚群:《海事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创新——以无人潜航器法律适用困境为例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77页。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卡斯卡、佩德罗佐(Pedrozo)和澳大利亚的麦克劳林在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船舶的基础之上,主张无人系统为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船舶。(32)James Kraska, “The Law of Unmanned Naval Systems in War and Peace,” The Journal of Ocean Technology, Vol. 5, No. 3, 2010, p.56; Rob McLaughlin, “Unmanned Naval Vehicles at Sea: USVs, UUVs, and the Adequacy of the Law,” Journal of Law, Information and Science, Vol. 21, No. 2, 2011, p.110; James Kraska, Raul (Pete) Pedrozo, “China’s Capture of U.S. Underwater Drone Violates Law of the Seam,” 16 December 2016, https://www.lawfareblog.com/chinas-capture-us-underwater-drone-violates-law-sea[2022-05-01].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大国,把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船舶。美国《海上军事行动法律指挥官手册》规定,专门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无人水面航行器和无人潜航器是主权豁免船只。(33)US Navy, US Marine Corps and US Coast Guard, 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Naval Operations, 2007, para.2.3.6.根据英国议会国际关系与防务委员会报告,英国国防部已把23个海上自主系统注册为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船舶(以下简称“政府公务船舶”)。(34)UK House of Lords, UNCLO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1 March 2022, p.63, para. 247.
《海洋法公约》没有对“船舶”一词作出解释。有的学者如麦肯兹根据演化解释的方法,主张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35)参见:Simon McKenzie, supra note 1;张书凝:《海上无人系统法律地位的认定》,《上海法学研究》第14卷,2021年,第45—47页。这一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为船舶,可能超过《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意图。如前所述,由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公约起草者对军舰或者船舶的理解都是指载人航行的船舶。演化解释是解释者根据时代变化作出与时俱进但仍符合缔约目的的解释,这种解释方法的性质和依据具有一定的争议。(36)参见张乃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3页。鉴于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内在威胁性,将其解释为船舶可能不符合缔约国的共同目的。
二是在现阶段,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尚不满足《海洋法公约》对船舶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等的实质性要求。尽管公约没有明确船舶的定义,但规定船舶拥有航行权利且需实施与船舶有关的规定。《海洋法公约》对船舶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的要求,有可能把海上无人系统“排除”出船舶范围。例如,《海洋法公约》第94条第4款项规定,每艘船舶都由具备适当资格的船长和高级船员负责,而且船员的资格和人数与船舶种类、大小、机械和装备是相称的。第98条规定,每个船旗国应责成船长,在不严重危及其船舶、船员或乘客的情况下实施海难救助义务。第94条和第98条表明,公约中的船舶是指载人操作的船只,因为有关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的规定需要由船长和船员实施。《海洋法公约》没有就航行安全义务和海难救助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已通过相关条款将相关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纳入公约。例如,第39条规定过境通行的船舶应遵守包括《避碰规则》在内的海上安全国际规章。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海上无人系统所属国在实质上履行航行安全义务就符合相关要求,而无需载人实施。例如,麦肯兹认为,只要海上无人系统在设计和编程中能做到确保海上安全,并且有船长和船员负责该系统的航行和通讯,无论是否有人在船上作出决定,船旗国都符合该款的义务。(37)Simon McKenzie, “When is a Ship a Ship? Use by State Armed Forces of Un-crewed Maritime Vehic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2, 2020, p.388.卡斯卡指出,美国海军正在努力确保其水面无人系统尽可能满足《避碰规则》,海军已经把相关规则要求纳入其无人系统之中。(38)James Kraska, “The Law of Unmanned Naval Systems in War and Peace,” The Journal of Ocean Technology, Vol. 5, No. 3, 2010, pp.52-53.英国报告指出,皇家海军采用“等效原则”适用《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条约的规定。(39)UK House of Lords, UNCLO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1 March 2022, p.62, para. 242.
然而,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如何实施《海洋法公约》对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规定,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法律责任的界定与承担等制度层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克雷格·艾伦(Craig H. Allen)认为,用一系列“等效”规则来改变《避碰规则》这些条约的规定在知识层面上是不诚实的,更不是明智的。(40)Craig H. Allen, “Determi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nned Maritime Vehicles: Formalism vs Functionalism,”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 49, No. 4, 2018, p.505.我国学者也指出,《避碰规则》以有人操纵作为规则的预设起点,海上无人系统直接适用相关规则存在困难。(41)参见初北平、邢厚群:《海事法律规则的适用与创新——以无人潜航器法律适用困境为例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78页。
现阶段,有关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航行安全、海难救助和环境保护等重要规则还处于空白状态,主张军用无人系统构成船舶会产生许多现实问题。(42)对海上无人系统适用《海洋法公约》及其他国际海事公约的问题的讨论,参见刘丹、李瑞:《无人海洋系统与国际法》,北京:海洋出版社,2020年,第100—110页。例如,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在航行中出现碰撞事故,应由谁来承担船长或相关船员的责任?(43)有专家指由于无人舰艇自主避障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不成熟,大吨位的无人舰艇距离实战还有较远的距离。参见马俊、刘煊尊、晨阳:《无人化海军时代还有多远》,《环球时报》2022年6月14日,第8版。对于遥控型的无人系统来说,在岸上控制中心实施监控或操作的工作人员可能构成“船长”或“船员”。但这些“船长”或“船员”应当具备什么适当的资格才符合《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规定?对于自主型无人系统,其自主感知外界环境、自主决策,谁来承担船长和船员的责任?是程序员还是某种算法?又如,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在A国注册,其操作人员在B国的陆上控制中心实施监控,无人系统航行中发生碰撞或污染事故,应当由哪一国实施管辖?还有,自主型海上无人系统应如何实施海难救助?不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实践中就会出现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局面。换言之,对于有人船舶,国际上对于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有相应的规则和制度,而无人航行器的航行安全和海难救助问题还没有国际规则,如果现在把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为《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其航行权利与法律责任的不平衡将构成国际海事安全的隐患。
(四)军事装置说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丹尼尔·瓦列霍(Daniel A.G. Vallejo)认为,海上无人系统属于军事装置。《美国法典》第18编第845节对“军事设备”的定义为,“子弹、炸药、发射物、地雷、水雷、导弹、火箭、锥孔装药、手榴弹、穿孔弹以及类似专用于军事或警察目的的设备”。他认为,根据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物理特性和其功能,对于现阶段海上无人系统的使用和发展而言,这一定义是合理的。(44)Daniel A. G. Vallejo, “Electric Currents: Programming Legal Status into Autonomous Unmanned Maritime Vehicles,”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7, No. 1,2015, pp. 414-416.
《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b项指出,外国船舶在领海内以任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和f项中外国船舶在领海内在船上发射、降落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应视为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的活动。第19条没有解释军事装置的含义,但该条在不同款项分别规定武器和军事装置的使用问题,表明军事装置不等同于武器。巴恩斯(Barnes)教授指出,应根据该装置所要实现的功能对“军事装置”的含义进行理解。军事装置包括所有武器系统的军需品、水雷、陷阱、侦察系统、监视系统、通讯系统、无人机、无人潜艇以及携带武器例如水上摩托艇或汽艇的部队。(45)Richar A Barnes: “Article 19,” in Alexander Proeless et al.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C.H. Beck München/Hart Oxford/Nomos Baden-Baden, 2017, p.194, para.20.《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f项中的军事装置,似乎指武器以外的各种用于军事目的的设备。现阶段,水下无人潜航器主要运用于军事侦察和情报搜集,军事科学研究者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军事装备进行研究。(46)参见史小锋等:《水下攻防武器能源动力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水下无人系统学报》2021年第6期,第634页。广义的军事装置,可以理解为用于军事目的一切设施或装备,包括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及其他军事设备。军事装置说可以涵盖各种类型的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包括用于侦察的小型无人系统以及用于运输或军事打击的中大型海上无人系统。这种主张操作性强,较为符合现实。未来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可能往多功能方向发展,即研发具有航行、侦察、通讯和打击能力的综合性无人系统。
军事装置说,可平衡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所属国和沿海国之间的利益。一方面,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为军事装置,其不具有船舶的航行权利,尤其是不存在领海无害通过权,未经沿海国明确许可,不得进入其领海,可以避免“军舰说”和“(政府非商业服务)船舶说”对沿海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军事装置,不是完全禁止其活动。根据《海洋法公约》第87条,所有国家均享有公海自由。除了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等明确列举的公海自由,公海自由还包括对公海的军事使用,包括操作军事装备、武器试验和军事测量。缔约国可以在公海部署使用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但同时要符合第87条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即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有关权利。(47)Oliver Daum,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Unmanned Naval Craft,”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 49, No. 1, pp.89-91.同时,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使用,还需要符合《海洋法公约》第88条对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之规定。《〈海洋法公约〉评注》指出,第88条并非禁止在公海开展军事活动。结合第301条,第88条不排除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公海军事利用活动。(48)M. H. Nordquist et al.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Sea 1982: A Commentary, Vol.2, Nijhoff Dordrecht, 1995, p.91.换言之,一国不得使用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对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行使武力或武力威胁。
军事装置说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国际法上对于军事装置没有定义;更重要的是,海洋军事强国可能反对这种主张。美国和英国等海洋大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科研力量发展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一种海洋军事装置,没有航行自由,这意味战略价值会被缩小,这可能是拥有大量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国家所无法接受的。因此,此种主张能否得到认可有待国家实践检验。
综上所述,“平台决定法律地位说” “军舰说” “(政府非商业服务)船舶说” “军事装置说”均有其依据及其问题。学术界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存在分歧,其法律地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在实践中,各个国家则根据自身利益和需要选择不同的学说。
三、影响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法律定性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
一方面,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是一个起点式的法律问题,因为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决定其权利义务和相关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与军舰是否享有领海无害通过权问题类似,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利益的现实问题。应当注意到,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有可能影响其定性。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存在不同的利益,它们会根据自身利益对无人系统作出不同定性。以下将以航行权利、豁免权和交战权为例,说明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所关涉国家利益的判断是影响其对无人系统定性的重要因素。
(一)海上无人系统的航行权利问题
《海洋法公约》只对船舶的航行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第17条规定所有国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其他不属于船舶的设施或结构,比如科学研究设施或设备以及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是否有航行权利,《海洋法公约》无明确规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否船舶,与无人系统是否享有受公约保护的航行权利这一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密切联系。
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船舶,这意味着无人系统可以在外国领海行使无害通过权、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行使过境通行权、群岛水域行使群岛海道通过权以及在公海拥有航行自由。自由来往穿梭全球重要海域,不仅可以提升所属国投射海洋军事力量的行动能力和维持军事存在,还可以依据航行自由开展军事情报搜集活动。作为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先进国家,美国和英国拥有大部分海上无人系统,两国都主张无人系统是政府公务船舶,因为这明显提升无人系统的海洋行动能力和战略价值。
然而,大部分沿海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鲜有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而且缺乏监控和拦截外国无人系统的能力。如果无人系统享有船舶的航行权利,许多沿海国将面临无人系统对其海洋安全的威胁。现阶段,以无人潜航器为代表的海洋军事情报搜集和侦察是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重要实践。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享有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将对沿海国领海的安全构成威胁。《海洋法公约》第19条规定,如果外国船舶在领海内从事搜集情报损害沿海国防务和安全的行为,属于非无害通过。考虑到潜艇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公约第20条规定在沿海国领海内的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须在海面上航行并展示其旗帜。尽管有这些规定,潜艇非法潜入他国领海甚至内水搜集军事情报的事件仍时有发生。(49)Ingrid Delupis, “Warship and Immunity for Espionag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8, No. 1,1984, pp.53-75; Said Mahmoudi, “Use of Armed Force against Suspected Foreign Submarine in the Swedish Internal Waters and Territorial Se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stal Law, Vol. 33, No. 3, 2018, pp.585-599; James Kraska, “Putting Your Head in the Tiger’s Mouth: Submarine Espionage in Territorial Waters,” Co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4, No. 1, 2015, pp.164-247.比起潜艇,无人潜航器的隐蔽性更好,对沿海国的威胁也更严重。无人潜航器活动范围大、体积小,下潜之后,运行噪音小,隐蔽性很强。(50)参见徐会希等:《自主水下机器人》,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第3页。如果其利用船舶无害通过权进入沿海国领海,搜集军事海洋信息,沿海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手段进行探测,难以觉察其行踪。尽管无人潜航器所属国可能会承诺无人系统在沿海国领海内停止情报搜集活动,上浮水面并展示其旗帜,但沿海国无能力核实其是否遵守承诺。而且,无人潜航器还具有数量优势。军用无人潜航器成本低,可由多种平台布放与回收,方便灵活,易于伪装,海洋军事强国可以大量制造和投放,集群作业用于搜集军事情报或实施监控。沿海国难以对其进行拦截和驱离,这对沿海国的国防安全形成巨大压力。
如果海上无人系统中的武器型海上无人系统构成船舶,会对沿海国领海产生更严重的问题。鱼雷和水雷具有航行能力,但没有航行权利,未经沿海国同意在其领海布设这类武器是对沿海国主权的侵犯,甚至构成非法使用武力。与鱼雷相似,海上无人武器系统兼具航行能力和打击能力。基于海上无人武器系统自动实施攻击的能力,沿海国可能会认为其通过领海本质上构成损害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的行为。(51)Hitoshi Nasu and David Letts,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Lethal Autonomous Maritime Systems: Warships, Torpedo or Naval Mine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96,2020, p.93.如果海上无人武器系统构成船舶,海上军事强国甚至会利用无害通过制度向沿海国领海内派遣无人武器系统,形成事实上的武力威胁。
除了对领海主权和安全构成威胁之外,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会加剧所属国与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争议。相比起潜入他国领海从事情报搜集活动这种典型的违反《海洋法公约》的行为,公约对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未作明确规定,因此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军事活动的合法性存在争议。一些沿海国认为,为保障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如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科学研究和保护海洋环境的权利,未经沿海国同意其他国家无权在专属经济区内开展军事活动,而美英等海洋强国则认为在专属经济区内开展军事活动属于《海洋法公约》第58条的航行自由,无需获得沿海国授权。(52)参见金永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问题与国家实践》,《法学》2008年第3期,第122—124页;管健强:《美国无权擅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测量”——评 “中美南海摩擦事件”》,《法学》2009年第4期,第54—55页; Raul (Pete) Pedrozo, “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 No.1, 2010, p.29。一方面,海上无人系统低成本和集群作业优势将大大提升所属国开展军事测量和情报搜集能力;另一方面,大量海上无人系统长期航行或停留在专属经济区会对海洋环境和航行安全造成更大的风险,而海洋强国和沿海国就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争端可能随着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尖锐。
由此可见,由于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未来,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可能将导致海洋强国开展海上军事活动与沿海国保护海洋安全与权益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频繁和尖锐。海洋强国会强调《海洋法公约》中的航行自由以保障其开展海上军事活动的自由,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船舶,以提升其战略价值,而大部分沿海国则强调《海洋法公约》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的宗旨,可能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装置或设备,减小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对其海洋安全的威胁。
(二)海上无人系统的豁免权问题
豁免权,指国家履行其职能的财产或行为不受其他国家管辖的国际法规则或制度。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军舰或政府公务船舶,那么其享有军舰豁免权或政府公务船舶豁免权。军舰豁免权或政府公务船舶豁免权,指这类船舶仅受到船旗国的管辖,其他国家不得对船舶采取强制措施或司法管辖。《海洋法公约》编纂和发展了军舰豁免权和政府公务船舶豁免权。《海洋法公约》第32和第95条分别规定军舰在领海和公海的豁免权。《海洋法公约》对政府公务船舶规定了类似于军舰的豁免权。例如,第32条规定,除特别规定情形之外,公约不影响政府公务船舶的豁免权;第96条规定,政府公务船舶在公海上享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第236条规定,有关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规定,不适用于政府公务船舶。
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拥有军舰豁免权或政府公务船舶的豁免权,将扩大所属国的战略优势,对沿海国的安全和权益构成更严峻的挑战。其结果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沿海国无法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采取强制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如前所述,一些海上军用无人系统隐蔽性强,沿海国对于潜入其领海搜集军事情报的无人潜航器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其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如果无人潜航器拥有豁免权,沿海国即使发现无人潜航器在领海内从事非无害通过行为,也只能要求其离开领海,而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保护其安全和国家利益。豁免权可以保护军用无人系统免于扣押等强制措施,相当于拥有“护身符”,而这无疑将对沿海国安全形成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二,沿海国难以通过国际途径要求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所属国承担相关违法责任。如果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拥有军舰豁免权或政府公务船舶的豁免权,沿海国无法对其实施司法管辖。从理论上说,沿海国有权通过国际途径要求无人系统所属国承担违法责任。例如,《海洋法公约》第31条规定,对于军舰或政府公务船舶不遵守沿海国有关领海通过的法律规章或公约的规定或其他国际法规则,而使沿海国遭受损失或损害,船旗国应负国际责任。沿海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所属国承担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违法责任。然而,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有赖于相关国家的政治意愿,而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也存在障碍。例如,《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规定了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争端的强制解决机制,但缔约国理论上可根据第298条第1(b)声明有关军事活动,包括从事非商业服务的政府船只和飞机的军事活动的争端不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换言之,海上无人系统所属国可能试图通过第298条第1(b)将有关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军事活动的争端排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管辖。由此可见,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拥有军舰豁免权或政府公务船舶豁免权,意味它除军事优势之外还拥有法律特权,这将使少数海洋军事强国的战略优势更加明显。
美国一些学者就坦承,豁免权是影响一个国家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法律定性的重要因素。美国军方的汉德森和卡斯卡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的论证分为两步:第一步,通过论证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船舶,主张系统享有船舶的航行权利;第二步,论证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政府公务船舶,不仅可以规避《海洋法公约》对军舰的明确约束,又可以享受类似军舰豁免权的待遇,可谓一举两得。汉德森指出了豁免权与赋予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船舶地位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如果无人潜航器是船舶,它们就可以作为海军辅助船享有主权豁免。因为辅助船是国家所有或经营并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船舶,其享有主权豁免。建立无人潜航器的豁免权可以保护其免于外国捕获,这符合美国利益。(53)Andrew. H. Henderson, “Murky Waters: The Legal Status of 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s,” Naval Law Review, Vol.53, 2006, pp.67-72.这解释了为何美国和英国均把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政府公务船舶。对豁免权的追求,是促使美国和英国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政府公务船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美英的立场相对,沿海国则可能否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有豁免权。在南海无人潜航器事件中,中国否认潜航器拥有豁免权。中国国防部不认同美方的无人潜航器为“享有主权豁免的船舶”观点,而是称其为不明装置并对其进行识别查证。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属于一种用于军事目的的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财产,军舰享有的绝对豁免权来自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为《海洋法公约》所编纂和发展。然而,除军舰之外的其他用于军事目的财产豁免问题,则缺乏明确统一的惯例和规则。(54)参见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当代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共同课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未生效)承认用于军事目的财产享有绝对豁免,第21条第1项(b)款规定“属于军事性质,或用于或意图用于军事目的的财产”在法院诉讼中免于强制执行措施。但要注意,该公约主要是处理国家与自然人或法人之间交易的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争议,而非针对海上无人系统这种新型军事财产的豁免权问题。德国基尔大学的道姆(Daum)认为,由于不存在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豁免权予以规定的国际条约,有关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豁免权的国家实践很少,并且缺乏相关法律确信,相关习惯国际法尚未形成。因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没有豁免权。(55)Oliver Daum, “Th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Unmanned Naval Craft,”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 49, No.1, 2018, pp.96-98.不过,黑因格则认为,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国家用于非商业目的的财产,拥有豁免权。(56)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Does the Increasing Use of Naval Weapon Systems Present a Challenge for IHL?”, in Wolff Heinstchel von Heinegg, Robert Frau and Tassilo Singer eds., Dehumanization of Warfare: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w Weapon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18, p.122.基于不载人的特性,沿海国可能对潜入领海的海上军用无人系统采取比军舰和政府公务船舶更加严厉的措施。实践中,沿海国可能会捕获未经许可进入领海内武器型海上无人系统作为侵犯其领土主权的反措施,甚至会摧毁这类无人系统。(57)Hitoshi Nasu and David Letts,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Lethal Autonomous Maritime Systems: Warships, Torpedo or Naval Mine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96, 2020, p.93.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捕获或损毁不存在人员伤亡或被扣押的问题,所属国对此可能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要求归还或营救。因此,相关国家实践可能倾向于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没有豁免权。
综上,海洋强国和沿海国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应否享有豁免权存在利益冲突,这也影响了有关国家对其定性。为保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免于沿海国的强制措施和管辖,美国和英国均论证其为享有豁免权的政府公务船舶,而为维护国家安全,沿海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否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享有豁免权,倾向赋予其较低的法律地位,比如定性为设施或装备。
(三)海上无人系统的交战权问题
现阶段,海上无人系统主要是用于执行军事侦察、监视和情报搜集任务,用于攻击的海上无人武器系统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大量投入实用。因此,美国和英国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政府公务船舶,主张其享有航行权利和豁免权,完全可以满足其现阶段的军事需求和国家利益。未来,如果武器型海上无人系统进入规模化运用阶段,并存在实际战斗需求。(58)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无人艇技术日渐成熟,环太平洋国际军事演习即派出四艘无人艇参加。参见张一帆、刘扬:《环太军演释放三大危险信号》,《环球时报》2022年6月7日,第5版。美英等海洋军事强国很可能会改变其立场,主张海上无人系统构成军舰。根据海战法,在武装冲突中只有军舰才享有交战权,海军辅助船等政府公务船舶不能主动使用武力打击军事目标,只能在自卫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因此,具有攻击能力的海上无人系统如果是政府公务船舶而非军舰,缺乏独立交战权,其将丧失其大部分的战略价值和战术价值。(59)Hitoshi Nasu and David Letts,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Lethal Autonomous Maritime Systems: Warships, Torpedo or Naval Mine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Vol.96, 2020, p.86.服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大律师查瑞克(Chadwick)因此指出,在海上无人系统与有人军舰共同作战的情况下,对军舰采取严格解释是无益的。(60)Kara Chadwick,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Naval Operations: Is International Law Ready?”, in Malcolm D.Evans and Sofia Galani eds.,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Help or Hindrance?, Edward Elgar, 2020, p.144.这预示着,美英国家未来可能根据实际需要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出新的定性,即主张其构成军舰。
但是,一些沿海国则可能否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军舰,因为如果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属于军舰,将使军舰无害通过权问题更加复杂。外国军舰是否拥有领海无害通过权问题是国际海洋法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海洋大国与沿海国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一些沿海国担忧外国军舰通过其领海对国家安全和权益构成威胁。(61)参见陈致中:《领海“无害通过权”在实践中的几个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25—26页;李红云:《也谈外国军舰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第88—91页;高健军:《中国与国际海洋法——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10周年》,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年,第46—57页;金永明:《论领海无害通过制度》,《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2期,第67—68页。现在,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尚且存在巨大争议,很难想象沿海国会接受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军舰。对于海洋大国而言,主张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军舰可能会引发沿海国的抵制和反对,得不偿失。有研究指出,美国不将无人船认定为军舰,是为了避免在他国领海中的美国无人船受到沿海国国内法规制,进而被要求离开。(62)参见刘丹、李瑞:《无人海洋系统与国际法》,北京:海洋出版社,2020年,第112—113页。海洋大国单方面拓展军舰概念并赋予海上致命性自动武器系统军舰地位,将会引发更多的沿海国采取保护性反应。(63)Hitoshi Nasu and David Letts,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Lethal Autonomous Maritime Systems: Warships, Torpedo or Naval Mines?”,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Series, US Naval War College, Vol.96, 2020, p.93.
(四)国家利益对海上无人系统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影响
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于无人系统的国家利益冲突可能会长期存在,并阻碍相关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需要广泛、反复和一致的国家实践以及相关的法律确信。美英国家可能会向其他海洋大国推广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公务船舶的实践,进而引导和塑造相关习惯国际法规则。例如,英国报告明确指出,国内立法和皇家海军的实践,对于形成有关海上自主系统使用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具有重要意义。(64)UK House of Lords, UNCLOS: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21st Century, 1 March 2022, p.67, para. 264.美国称“将承认其他国家海上无人系统的对等性完全豁免权”,试图引导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家实践。(65)US Navy, US Marine Corps and US Coast Guard,The Commander’s Handbook on the law of the Naval Operations, 2017, para.2.1.1.一些西方学者也呼吁其他国家采纳美英国家实践,例如黑因格建议有关政府可以通过联合声明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为船舶,麦肯兹号召其他国家跟随美国实践,公开承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拥有航行权利的船舶。(66)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Unmanned Maritime Systems: Does the Increasing Use of Naval Weapon Systems Present a Challenge for IHL?”, in 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Robert Frau and Tassilo Singer eds.,Dehumanization of Warfare: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w Weapon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18, p.121;Simon McKenzie, “When is a Ship a Ship? Use by State Armed Forces of Un-crewed Maritime Vehic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1, No.2, 2020, p.402.
然而,发展中国家沿海国则可能会拒绝美英国家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定性。2016年中国和美国对南海无人潜航器的争议,就反映了单方面定性的做法不可行。美国称无人潜航器为主权豁免船舶,中国则称其为不明装置。显然,中国不接受美方对无人潜航器的单方面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正在就无人商船的国内立法进行咨询,试图通过其国内法引导国际海事组织对海上无人商船规则的制定。(67)UK House of Lords, supra note 1, pp.66-67, paras. 259-266.
四、无人商船国际海事规则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法律地位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通过现有国际公约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进行的各种解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相关国家实践尚不足以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国际海事组织相关规则的制定将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习惯国际法产生影响。2018年5月,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就海上无人船(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的航行安全、海难救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开展“规制内容筛选调查”(regulatory scoping exercise),评估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如何适用于不同自主程度的无人船,这些规定是否排除无人船的运营,分析解决无人船运营问题的最合适方式。(68)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Takes First Steps to Address Autonomous Ships,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08-MSC-99-MASS-scoping.aspx[2022-06-11].2021年5月,海上安全委员已完成对无人船规则内容的筛选,其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对无人船的“船长”“船员”“责任人”的解释,是对其规制的重点,而遥控中心的运作要求以及是否将遥控操作员作为海员也是关键问题。(69)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Autonomous Ships: Regulatory Scoping Exercise Completed,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MASSRSE2021.aspx[2022-06-11].这意味着,国际海事组织作为国际航运的全球性规范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无人船的规则。有专家指出,制定智能化船舶国际规则的进程或许是缓慢的,双边安排或区域性多边安排或许会很快出现。(70)参见童凯、肖桐:《“海洋法的发展、挑战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华海洋法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151页。
虽然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无人船规则是针对商用无人船,但其对海军船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按照惯例,军舰一般自愿遵守《避碰规则》中的规定。因此,为实现保障海事安全的目的,一些符合对无人商船国际海事安全规则的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比如用于后勤补给的大型水面无人系统未来可能构成船舶。然而,即便一些海上无人军用系统符合无人商船国际规则中的“船舶”要求,该系统不一定构成《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更不一定能拥有船舶的各种航行权利。因为国际海事组织所制定的无人商船国际规则很可能属于“软法”规则,即便其获得成员国的认可和执行,本身并不能修改《海洋法公约》对船舶的相关规定。不过,无人商船国际规则将影响国家对海上无人系统的国家实践,进而影响对《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根据《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乙),对条约进行上下文解释时,应将“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纳入考虑。由于许多国家既是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也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对海上无人系统的国家实践如区域性安排可作为解释《海洋法公约》的嗣后协定与惯例,影响缔约国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解释。另一方面,有关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国家实践如果符合一般性、反复性和一贯性要求,并存在相应的法律确信,可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总而言之,未来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否《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以及其是否享有公约赋予有人船舶的航行权利,取决于相关国家实践及其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五、结 语
对于海上军用无人系统这一新事物,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国家实践和学术界对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观点,主要包括“平台决定法律地位说”“军舰说”“(政府非商业服务)船舶说”“军事装置说”。研究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仅要根据特定系统的特性和功能,更需要结合定性所要实现目的。基于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内在威胁性,对该系统的定性应当把维护海上和平和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本文认为,根据控制平台决定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不利于沿海国保障其安全和权益,而且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海洋法公约》对军舰定义的文义解释和缔约国的意图,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构成军舰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现阶段,由于海上无人系统不满足公约第94条对船舶的航行安全和第98条对船舶海难救助的实质性要求,将其作为《海洋法公约》中的船舶,将对国际海事安全构成安全隐患。把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作为军事装置,有利于保护沿海国的安全,但可能会遭到海洋军事强国的反对。
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存在利益冲突,它们会根据自身利益对其法律地位作出不同定性。美国和英国拥有大量海上军用无人系统,为使无人系统获取航行权利以提升其海洋行动能力和战略价值,两国均主张无人系统构成船舶。同时,为了保护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免受沿海国的强制措施和管辖,美国和英国都论证其为享有豁免权政府公务船舶。沿海国由于缺乏监控和拦截外国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能力,为保护自身海洋安全和利益,可能会将海上军用无人系统定性为地位较低的设施或装备,并否认其享有豁免权。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于无人系统的利益冲突可能会长期存在,阻碍相关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总而言之,海上军用无人系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其法律地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现有的各种主张,均有其依据及其问题。海洋军事强国和沿海国对无人系统的利益冲突,不仅会影响其对无人系统的定性,而且会阻碍相关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研究海上军用无人系统的法律地位,需要密切注意未来相关国家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