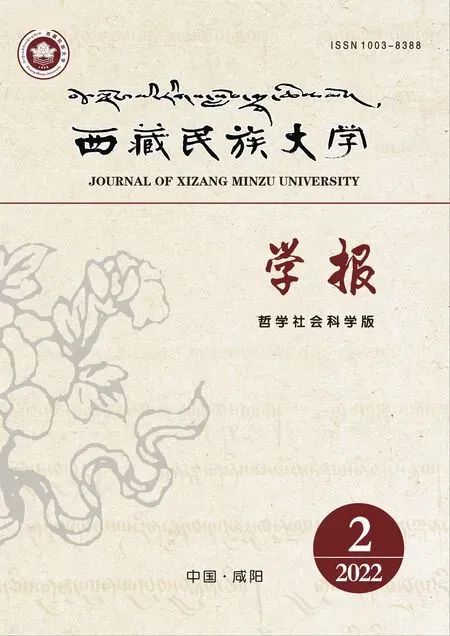印度议会语言地位规划提案(1952-2021)探析
任 娟
(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印度毗邻,近年来,由于中印在洞朗、班公湖等地区军事对峙和冲突频发,印度涉藏政策和西藏边境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别与区域学者研究的主要议题。2020年12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1]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2]的通知,为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制度基础。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旨在规范和加强陆地国界工作,保障陆地国界及边境的安全稳定[3]。该法规的出台为处理边境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也进一步凸显了边境治理和边境安全的重要性。而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国家的显性特征和文化符号,不仅体现着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而且作为信息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军事、文化、政治等诸多安全领域密切相关,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工具。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强调:“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4]边疆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而语言安全是维护边疆安全的必要基础。基于此,深刻剖析印度议会,特别是中印边境地区语言地位规划相关提案,不仅有助于拓展印度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为我国西藏边境地区“语言安全规划”的制定和“治边稳藏”战略的实施提供基础研究支持。
一、语言规划及研究方法
Haugen在1959年 将“语 言 规 划(Language Planning)”正式引入社会语言学领域,相关学者(Rubin 1977[5];Cooper 1989[6];Hornberger 2006[7];Tollefson 2015[8])对语言规划的定义、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和修订。早期的研究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系统的对语言结构,语言行为,语言资源等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在Ru⁃bin(1977)将语言规划区分为“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基础上,Cooper(1989)提出了“习得规划”,这一新的维度拓展了语言规划理论的广度和深度。Hornberger(2006)在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三个维度细分为语言政策规划和培育规划两个范式,建立了语言政策与目标综合框架,成为本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理论框架。
21世纪以来,语言规划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规划国别研究、语言规划与语言安全、对外传播规划和跨境语言规划等维度。何宁,廖波(2017)[9],戴曼纯(2015)[10]和文秋芳(2014)[11]通过对印度、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语言安全问题进行梳理,论证了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开展中国关键语言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和培养“关键语种”人才的迫切性。张日培(2018)[12]和沈骑(2020)[13]尝试构建基于我国语言规划和政策的语言安全理论框架。戴庆厦(2016)[14]和张军(2018)[15]等学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跨境语言规划进行了观测和分析,并深入探讨了语言关系、语言认同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学者们通过援引不同国家的史实,论证了语言规划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政治工具和手段,通过构建语言安全规划模型和评估体系,为我国语言安全规划的制定、实施和完善提供了标准参照。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重点关注印度国家官方语言和官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问题。数据来源主要为印度议会官方语言提案(38个)及相关语言地位规划提案。语言地位规划是指通过政府官方的承认,确立某种语言在社会或者其他语言环境中的使用地位[16],是国家语言安全的主要变量。因此本文主要从语言地位规划维度对文本数据进行阐释和分析。
二、印度议会语言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包括语言官方化、语言国家化、语言地位标准化、语言复兴、语言保持、语言传播等类型[7]。
(一)国语、官方语言的确立
国语是指能够体现国家身份、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语言,是国家政府机构在外交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官方语言是在政府公务中,如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各种功能性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17]。
1917年,甘地在古吉拉特邦(Gujrat)教育大会上提出印地语是唯一具备“国语”资格的语言,是潜在的经济、宗教和政治交流的纽带。1946年,印度制宪会议关于“国语”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印地语地区提出了大量支持印地语作为唯一国语的提案,但遭到了南方非印地语地区各邦的强烈反对,经过三年的辩论,双方于1949年底达成妥协。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第343条 第1款规定印地语(天城体)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并未明确规定印地语为国语;第343条第2款规定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15年后(至1965年)是否废止由联邦议会决定。1963年5月10日,印度议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案(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1963)》,鉴于印地语取代英语的过渡期并不平稳,决定自1965年1月26日起,英语继续作为联邦、议会、最高法院的官方语言,联邦政府和未将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方邦政府的交际语言,以及印地语邦和非印地语邦的邦际交际语言。1976年印度议会成立了官方语言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ar⁃liament on Official Languages),主要职责为监管处理和官方语言相关的各项事宜,并定期向总统提交印地语使用情况报告。1976年出台的《官方语言条例(The Official Languages Rules,1976)》在1987、2007和2011年经过了3次修订,但印地语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都没有明显变化。2000年,印度议会议员Laxminarayan Pandey提出了《官方语言撤销提案(The Official Languages Repeal Bill,2000)》,认为《官方语言法案(1963)》规定的无限期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违背了上述宪法第343条规定,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应设置国语,这不仅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也关乎国家团结和稳定,因此建议废止该法并确立印地语为国语,以确保国家统一和完整,但此项议案至今悬而未决。2012年,议员Tiruchi Siva Shri提出《官方语言提案(The Official Languages Bill,2012)》,鉴于印地语主要使用人口只集中在6个邦,其他地方邦居民在处理公务时因使用当地语言而受到歧视,因此所有地方邦语言都应被赋予官方语言地位,但此议案并未通过。截至2021年8月18日,印度议会再未有关于国语地位规划的提案提出,印地语和英语继续保持着官方语言的地位。
(二)地方邦、联邦属地官方语言的确立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认为按照语言建邦将会导致地区间的领土争夺和分裂主义的增长,妨碍国家整合的进程[18],划分地方邦时应同时考虑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19],但这一决定违反了国大党1920年既定的独立后按照语言建邦的施政纲领,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拖延的战略遭到了南方泰米尔语系各邦的强烈不满。1949年,马德拉斯邦的泰卢固语地区要求单独建立一个讲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导致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和动乱,随着抗议活动的不断升级,尼赫鲁政府不得不妥协,1953年8月27日印度人民院通过了建立第一个语言邦的法案《安德拉邦法案(The Andhra State Act,1953)》。1956年8月31日印度议会人民院通过了《邦改组法 案(The States Reorganization Act,1956)》,全国按主要语言分布重新划分为14个邦,6个联邦属地。这一法案以语言为界限确定了各个地方邦的轮廓,但同时也诱发了更多的族群因为语言问题要求独立建邦的诉求。例如,自1950年起,锡克人要求建立以旁遮普语为官方语言的旁遮普邦,但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在印度教极端分子的煽动下,坚决反对建立旁遮普语言邦,导致矛盾不断持续激化,1981年9月至1983年4月,总共发生约100次袭击和暗杀事件[18]。此后,语言建邦运动此起彼伏,印度的地方邦结构又经历了多次调整和重组,形成了表1所示的行政区划和官方语言版图。
如表1所示,印度语言生态复杂,语种多样。根据2020年3月印度议会通过的《第三语言法案(The Third Language Act,2020)》统计,印度目前使用语言780种,语系构成为:印度-雅利安语系78.05%,达罗毗荼语系19.64%,和其他(南亚、汉藏等语系)2.31%。中印边境地区主要语言地位规划和分布如下:
2020年9月22日,《查谟和克什米尔官方语言提案(The Jammu and Kashmir Official Language Bill,2020)》在印度联邦院通过,主要内容为:1.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官方语言为克什米尔语、多格拉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和英语;2.促进地区语言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戈杰里语、帕哈里语和旁遮普语的发展。
1975年《喜马偕尔邦官方语言法案(The Him⁃achal Pradesh Official Languages Act,1975)》规定本地区官方语言为印地语,主要语言还包括尼泊尔语和藏语。
2014年《北阿坎德邦梵语教育法案(Uttara⁃khand Sanskrit Education Act,2014)》规定政府工作语言为梵语或者印地语;设立梵语研究与培训、教育管理与规划、梵语文化等管理规划机构。2019年《北阿坎德邦官方语言法(The Uttarakhand Offi⁃cial Languages Act,2019)》规定印地语为官方语言,同时考虑到梵语使用群体的利益,设置梵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1977年《锡金官方语言法案(The Sikkim Offi⁃cial languages Act,1977)》规定尼泊尔语、菩提亚语、雷布查语、林布语为本地区官方语言。尼泊尔语是锡金的主要语言,与印地语相似,使用天城体。菩提亚语和雷布查语使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北部。此外,藏语、巴尔蒂语、英语和林布语都有分布。
1986年,印度议会通过了伪《“阿鲁纳恰尔邦”法案(The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Act,1986)》,并于1987年2月20日宣布成立伪“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此地区部落种族数量众多,语言生态复杂,有50多种语言和方言,大部分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官方语言为英语,主要语言还包括印地语、孟加拉语、阿萨姆语、尼泊尔语、藏语等,但由于诸多部族语言不通,因此印地语、阿萨姆语和英语是该地区的通用语。
三、印度语言地位规划的特点及动因
印度语言地位规划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6]印度政府不断推动印地语成为“国语”,促进国族整合和语言意识形态统一的进程从未止步;地方邦促进地区性语言地位的标准化和实现特定政治意图的进程也从未停止;而在边境地区,以语言为手段进行文化同化历来是印度政府边疆政策的一部分。
(一)语言国家化和官方化与语言意识形态的统一
1947年印度独立之初,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文化的影响,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加快国家整合是统治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民族共同语是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国大党普遍支持印地语成为“国语”,但由于南方非印地语邦的强烈反对,宪法仅规定印地语为官方语言,但相关法律条款充分反映了印度政府实施的是过渡性的语言地位规划和权宜性的语言政策。《印度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第351条:联邦政府有责任推广印地语,使之成为印度文化的传播媒介。
第344条:建立专门的委员会向总统汇报在联邦公务中推广印地语和限制英语使用的进展情况,并就促进印地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和逐步淘汰英语提出建议。
《官方语言法案(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1963)》(As Amended,1967)第5条:印度议会两院拟提出的所有法案或其修正案的英文权威文本,应附有印地语译本。
《官方语言条例(The Official Languages Rules,1976)》(As Amended 1987,2007,2011):从中央政府办公室到位于“A”区(比哈尔邦等9个地方邦和德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2个联邦属地)的通讯须使用印地语,特殊情况下使用英语须附有印地语译本。
《圣雄甘地国际印地语大学法案(Mahatma Gandhi Antarrashtriya Hindi Vishwavidyalaya Act,1996)》:建立一所教学型大学,通过教学研究发展印地语语言文学,促进印地语发挥更大作用,推广印地语成为国际通用语。
上述法案不仅循序渐进的为印地语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也充分反映了印度政府欲确立印地语为“国语”的政治意图。在印度国家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语言问题导致的冲突屡见不鲜,但语言地位规划的演进史揭示了有意识地促进语言意识形态统一是印度国家语言地位规划的一部分。印度历届政府都在积极推动印地语地位的提升,试图以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来加强国家认同。国语作为一个国家的符号和象征,是传播该国政治意识形态和巩固文化认同的主要工具。根据印度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1961年到2011年,印地语使用人口比例从30.37%增长到57.10%,“特别是莫迪政府上台后采取印地语优先的策略,确立印地语为国语的意图相当明显。”[20]印度政府强势推广印地语的各项措施已经在政府部门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印度议会事务部(Ministry of Parliamen⁃tary Affairs)2019-2020年度报告:为确保政府公文以英印双语或仅以印地语印发,该部总务处设立了检查点并成立了官方语言执行委员会,对《官方语言法(1963)》和《官方语言条例(1976)》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印度议会的12个部门中有6个部门(包括联邦院、人民院)100%的工作都使用印地语完成,其余6个部门50%的工作用印地语完成。随着印地语在印度语言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有可能成为莫迪政府进行国家意识整合的有力工具。
(二)语言认同与语言地位标准化
语言认同是语言地位标准化的基础,和其它联邦制的国家政体相比,印度的行政区划主要以语言为界限,因而语言问题也往往和党派、教派、政治联盟斗争等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冲突、民族分裂主义的联系更为密切,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印度,无论是1946年制宪会议上,议员Dhulekar认为“制定印度宪法的人,如果不了解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就没有资格成为议员,最好离开,”[21]还是北方印地语集团和南方泰米尔语系各邦多年来因官方语言问题冲突不断,抑或是1966年信德语(Sindhi)族群坚持要求将信德语纳入宪法表列语言,“阿萨姆山区和边境地区有的部族不仅要求建立独立的语言邦,有的甚至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18]此类显性的语言问题背后是隐性的身份、资源和权力的认同问题。在一个多语种、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语言问题不仅体现着国族身份认同,也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和宗教等多个领域权力和利益的认同。
如果印度政府真正希望整个国家团结和强盛,包括喜马拉雅地区爱好和平的弱势群体,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将“菩提语(Bhoti)”列入印度宪法表列语言,使喜马拉雅地区人民也能以自己的语言为荣,使我们的议员也能在议会以更有效的方式代表我们,用母语表达我们的问题和愿望[22]。
在印度,征选士兵入伍的语言不是印地语就是英语,这显然使那些来自“印地语带”的应征者比南方应征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印地语或英语知识薄弱的农村地区的应征者更具优势[23]。
因此,语言地位标准化不仅要体现在宏观法律文本层面的认同和制度保证,更要体现在语言规划实施过程中对语言相关权力和利益的认同和实现,否则就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不和谐因素。在印度一些语言群体看来,不承认一种语言的地位,就等同于否定了其群体的民族身份、所属党派或者宗教团体等,这就会给一些地方势力(如部族、党派、宗教领袖等)提供契机,让他们有机会有理由去动员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例如,1955年邦改组委员会否定了锡克人要求单独建立旁遮普邦的要求后,阿卡利党谴责国大党和邦改组委员会对锡克人抱有偏见和歧视,并愤怒的质问道:
宪法列出了14种主要语言,其中包括旁遮普语,为什么别的地区语言都能建立相应的语言邦,唯独旁遮普语不能?是不是中央怀疑锡克人对国家的忠诚?否定锡克人的要求是灭亡锡克的判决书,表示要誓死抗争[18]。
在阿卡利党的大规模政治鼓动下,锡克人的单独建邦运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英迪拉·甘地执政后才得以初步解决:旁遮普邦一分为三,以旁遮普语为官方语言的新旁遮普邦,以印地语为官方语言的哈里亚纳邦,东北部印地语人口并入临近喜马偕尔邦。但长期以来寻求印度宪法、联邦及地方邦法律法规语言地位认可的运动此起彼伏。一方面,地区性语言未被纳入宪法表列语言的地方邦一直在积极的推动联邦政府和宪法的承认,提升其语言地位和使用范围。印度1950年宪法承认的表列语言有阿萨姆语、印地语、梵语和乌尔都语等14种语言,1967年印度宪法修正案加入信德语,1992年增加尼泊尔语、曼尼普尔语和孔卡尼语,总数达到18个。2003年博多语、桑塔利语、迈西里语和多格里语加入表列语言,使印度宪法表列语言的数量增加至22种。而另一方面,印度一些地方邦少数语言族群也不能容忍集体认同的弱化和边缘化,一直寻求地方邦法律法规的认同。例如,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官方语言法(2020)》颁布后,锡克和古杰尔族群强烈抗议将旁遮普语和戈杰里语排除在法案规定的克什米尔语,乌尔都语等5种官方语言之外。正如一位印度总理曾经所说:“如果承认一种语言,那么就得承认其他200种语言。”[24]由于印度宪法、联邦和地方邦语言法案既未真正赋予各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地位和认同,也未给予未规划语言群体在教育、就业等领域充分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削弱了他们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这是印度社会一直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三)印地语的强势传播与梵语的复兴
在中印边境地区,宏观层面《官方语言法(1963)》和《官方语言条例(1976)》不仅为印地语地位的不断提升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印度政府对尼赫鲁政府边境地区语言政策的沿袭:“印地语是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应当将其视为在边境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工具”;“尼赫鲁政府在占领区积极创办印地语学校,通过利用印地语作为语言工具扩展中央对占领区乃至锡金、不丹的影响力。”[25]此后,印度历届政府都将语言作为边境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利用隐性的语言教育规划加速对边境地区的同化和事实占领。印度在非法占领中国藏南地区后,亦妄图利用隐性的语言文化政策影响、同化当地居民,以达到其非法占有中国领土的目的。印度议会先后通过伪《“阿鲁纳恰尔”大学法案》(The Arunachal University Act,1984)、《“阿鲁纳恰尔”教育 法案》(The Arunachal Pradesh Education Act,2010)和《北阿坎德邦语言教育机构法案(Uttara⁃khand Language Institutions Act,2018)》等法案建立了大量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机构和专门的语言教育机构,加速了印度传统文化和印地语的传播、弱化了本土语言的保持和传播,这无疑在印度的边疆同化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从1994至2020年,印度议会共通过《中央梵语大学法案(The Central Sanskrit Universities Act,2020)》和《北阿坎德邦梵语教育法案(Uttara⁃khand Sanskrit Education Act,2014)》等16项法案促进梵语的复兴,这些议案主要目标包括:组建梵语教学研究型大学,推动梵语复兴;促进梵语、日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梵语文学研究、佛教学和印度学研究;传播梵语语言文学蕴含的普世价值观,促进古印度智慧和现代科学体系的融合;设立专门委员会,统一规范和监督北阿坎德邦中小学梵语教育、教师教育和课程设置等梵语复兴和教育规划。梵语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的吠陀梵语,梵语文本主要包括诗歌、传统戏剧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文本。作为一种仪式语言,梵语在印度教和佛教实践中广泛使用,是佛教学的主要语言(梵语、巴利语、藏语和汉语)之一。梵语哲学宗教典籍在佛教领域具有权威性,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会潜移默化地提升中印边境地区佛教群体对印度文化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有可能成为莫迪政府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扩大宗教文化辐射圈进行隐性文化同化的另一有力工具。
四、印度语言地位规划对西藏边境地区语言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印度的语言地位规划始终以满足其国家政治需要为目的,尤其在与中国相邻的边境地区,其语言地位规划的针对性、目的性更强。例如,印度在强占中国藏南地区后,不仅将中国藏南地区进行法理上的行政区划,命名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而且通过大量教育机构强势推广印地语,妄图以语言为工具同化藏南中国人民。此外,近年来,印度政府亦意图在梵语等佛教语言的复兴和传播规划的基础上构建从拉达克到达旺的跨喜马拉雅地区佛教文化缓冲区,提升其在南亚佛教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加强对中印边境地区藏传佛教群体的文化同化,对我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一)开展针对中印边境地区“关键语种”印地语、梵语和菩提亚语等语言规划的储备性研究。全面系统梳理和动态追踪印度政府近年来针对上述语种的语言地位规划、教育规划和本体规划,进一步理清其对西藏边境地区语言文化安全具体的、潜在的影响。加强对中印争议地区、边贸口岸、山口通道等重点方向的语言生态的观察和科学记录,建立语言监测和预警机制,更精准有效地为西藏边境地区语言安全规划提供学术支撑。
(二)推动国防语言能力建设和非通用语语言资源的开发。开设非通用语专业的外语类院校和西藏自治区各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南亚语种优势和地缘文化优势,在西藏边境地区开设语言培训机构,编写相关读本和教材,对戍边人员进行“关键语种”的语言培训,提升驻边部队官兵和边民的语言能力、区域文化知识和语言安全意识。
(三)加强“语言学”和“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建设,培养同时具有中印边境地区“关键语种”语言能力和“国家安全学”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宗教学和民族学等专业背景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便在复杂变幻的周边安全环境下,为“治边稳藏”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复合型专业人才储备。
“语言规划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和保障国家语言安全”[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等中央和地方性法律法规的颁布和修订为有效开展边境地区语言规划提供了法律和政策支撑,但目前从事印度及南亚研究的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印度国别研究和中印边疆研究,聚焦中印边境地区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需要国内学者对该地区的语言生态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为西藏边境地区“语言安全规划”的制定提供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为“治边稳藏”等国家战略提供具有前瞻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的咨政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