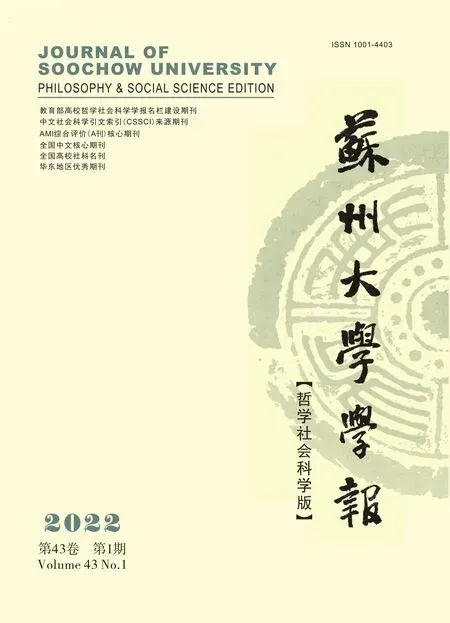预防刑法:辩证、依据与限度
魏 超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问题的提出:预防刑法之理论争议
科技的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的出现,社会生活复杂化程度明显升高,不同文化的碰撞日趋激烈,使得重大法益(包括超个人和个人)的安全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威胁。为了更为周全地保护法益,立法者不得不将刑法的阵线不断前移,“在修改完善的内容、频率上都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以注重刑法保护社会、积极预防犯罪功能的发挥”①(1)①郎胜:《我国刑法的新发展》,《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35页。。但此种立法模式正如一柄双刃剑,在回应社会安全需求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由。与之相对,学界对此种积极创立预防刑法的模式也存在不同甚至对立观点,持消极刑法观的学者认为,此种立法模式会造成法益保护过早化、抽象危险犯入刑化等问题,弱化了刑法的科学性,侵蚀了刑法的独立性,也损害了刑事法治建设。②(2)②参见刘艳红:《刑法的根基与信仰》,《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第152-153页。持积极刑法观的学者则指出:此种立法模式是社会治理与控制的客观需要,与谦抑性之间并无矛盾,也不会带来刑法过度干预的系统风险。③(3)③参见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31页。还有学者持一种“积极谨慎刑法发展观”,认为需要兼顾两种刑法观,在刑法迭代变革与发展中,对其过度扩张保持足够的警惕。①(4)①参见孙国祥:《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9-10页。由此可见,虽然积极预防刑法观与刑事立法的长期亲和使之大有成为主流刑法观之势,但在此过程中,理论上对其的反思与批判不仅从未停止,反而愈发激烈和深刻②(5)②参见《政治与法律》编辑部:“编者按”,《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第18页。。预防刑法是否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其正当化依据为何,应当如何对其进行限制,都仍然存在巨大争议。而此种争议的背后,其实更涉及刑法的社会根基、价值取向与功能设定等基本理论,一旦处置不当,便会侵蚀整个刑法体系的教义理念,造成不可预知的法治风险。而且,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与民众的一言一行息息相关,若用之不当,更会使国家与民众深受其害。有感于此,本文拟对既有的预防刑法条款进行分析,探寻其正当化依据及边界,以求对刑法理论及未来立法有所裨益。
二、既有预防刑法批判之反思
虽然学界对于预防刑法的批判在形式上各有千秋,但其内核却几乎完全相同,均集中于司法适用率偏低、工具主义化或者因过早介入而有违“最后手段性”原则等方面。故在本部分,笔者拟对上述批判进行辩驳,以求让其受到公正的评价。
(一)适用量低不等于缺乏规制效果
针对预防刑法的第一种批判在于,部分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较多的适用,“空置化”“僵尸化”现象严重,缺乏实际规制效果,因而属于“象征性立法”,应当予以废止。③(6)③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6页;魏昌东:《新刑法工具主义批判与矫正》,《法学》2016年第2期,第87页。
本文并不否认条文缺乏规制效果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量低”,但同时认为,仅仅凭借“适用量低”并不能够直接推导出条文缺乏规制效果,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数量只是判断其是否为象征性立法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此种做法过于片面。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某一罪名的适用量低,可能存在两种原因,其一是此类犯罪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较为少见;其二是因为刑法的颁布施行产生了一般预防效果,让行为人不敢再去实施相应犯罪。因此,某一罪名的适用量低下,正可能是因为刑事立法起到了行为指引之作用,但这显然不能够被称为是“象征性立法”。而且,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操作来看,影响某一罪名适用数量可能存在诸如犯罪黑数、未达证明标准、选择性执法等诸多原因,故立法的实际效果难以从司法实践中的案发数量直接推导而来,需要根据精确的犯罪学统计方能得出妥当结论。另一方面,即便部分立法规定在当下实践中很少用到,我们也不能将之直接认定为象征性立法,因为此类“备而不用”的罪名虽然在平时发案率极低,但在特殊时期却能够发挥重要作用。④(7)④参见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50页。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2019年前,在各大裁判文书网仅能够搜索到58份裁判文书,若依照前述论者的逻辑,本罪应当属于典型的“象征性立法”。但是,在疫情大量暴发,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特殊时期,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本罪在此期间维护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秩序的重要作用,故单纯以条文的适用量来批判其是否属于象征性立法,仅重视了其“裁判功能”而忽略了其“行为指引”功能,有以偏概全之嫌疑。
综上所述,判断某刑法条款是否缺乏实效或者沦为政策宣示的工具,不能只看案件发生的数量,“适用量低”确实是象征性立法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仅凭此现象并不能够当然推导出某一条款属于“象征性立法”,唯有某一预防刑法的条款完全沦为形式立法,从而同时损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人权保障与实用主义三项实质功能时,其才属于应当遭受批判的象征性立法。①(8)①参见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45-48页;陈金林:《象征性刑事立法:概念、范围及其应对》,《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3-115页。既然以使用率低为由对象征性立法的批判不成立,那么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对于预防刑法之批判当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二)限度内刑法并未将人“工具化”
还有观点认为,当前刑事立法出现了犯罪化与处罚前置化的趋势,抽象危险犯这一犯罪类型大量增加,使得刑法演变为一套“全面且具有弹性的危险防御工具”。②(9)②参见程红:《象征性刑法及其规避》,《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第24页。此类批判的核心在于,其认为处罚前置的预防刑法过于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从而将刑法作为特定目的的工具,如满足公众情绪、预防损害发生,因而忽略了刑法的核心价值。③(10)③参见吴亚可:《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问题、根源与理性回归》,《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110-112页。
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首先,法律本身就是“目的为导向”(zweckgerichtet)的产物,立法者之所以制定新法或修法本身便是着眼于实现特定目标④(11)④Vgl.Kindermann,Symbolische Gesetzgebung,in:Grimm/Maihofer(Hrsg.),Gesetzgebungstheorie und Rechtspolitik(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13),1988,S.230.,故只要我们承认刑法具有目的或者任务,便无法否认其工具属性。正如李斯特所言:在人类文化史的初始阶段,人们只能认为刑罚是国家对社会成员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的盲目的、本能的、原始的、不受目的思想决定的一种反应。但是,刑罚特征随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经验启发了人们对于刑法目的的理解,对犯罪的盲目反应转变为符合目的之法益保护。⑤(12)⑤Vgl.Liszt,Der Zweckgedanke im Strafrecht,in:Strafrechtliche Aufsätze und Vorträge(Erster Band,1875 bis 1891),S.23.是以,无论学者认为刑法的目的何在,只要国家创制、施行刑法是为了有效保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公民的个人利益,就意味着刑法必然或者应当追求功利目的,这便同时意味着,刑法是国家追求目的之工具。因此,刑法天生便带有工具的色彩。
其次,即便承认刑法带有工具色彩,也难以认为其不具有正当性。部分学者之所以反对刑法的工具属性,是因为其认为此种做法没有将人作为刑法关系的组成部分,而是仅将其作为客体,因而侵犯其人性尊严。⑥(13)⑥Vgl.Michael Köhl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1997.S.45.但必须指出的是,刑法工具化并不一定侵犯人性尊严。德国通说认为,根据康德哲学⑦(14)⑦康德认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不仅仅作为这个或者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手段而实存”。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推导而来的客体公式,当具体的个人被贬低为客体、纯粹的工具或者可替代的数字,以至于其主体资格或者法律主体地位陷入疑问的对待时,其人性尊严便遭到了侵犯。⑧(15)⑧BVerfGE 27,1(6);30,1(25f.);Duerig,Der Grundrechtssatz der Menschenwürde,in:AöR 81(1956),S.127.但此种情况在满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时并不存在。因为康德也从未反对刑罚,只是认为不能为了达到特定的效用性目的而判处刑罚。在康德眼中,刑罚是犯罪的镜面反射,针对他人实施的犯罪,通过刑法这面镜子原封不动地反射到了罪犯自己身上。由于国家刑罚是一种“恶”,为了防止这种“恶”被滥用,就必须为其确立明确的界限。⑨(16)⑨参见陈金林:《从等价报应到积极的一般预防——黑格尔刑罚理论的新解读及其启示》,《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第149页。故“适当的刑罚反而会使得正义成为原则和准绳”⑩(17)⑩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而根据如今的量刑理论,我们只能在确定了行为人责任刑的点以后,再在其之下考虑预防刑(18)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是以行为人最终被判处的刑罚,绝不会大于其法益侵害性所招致的报应刑,其宣告刑的刑期必然会在报应刑的刑期以内,仍然是其侵害法益行为所应得的惩罚;相对地,个人也就并没有被贬低为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而是仍然被当作独立的理性的主体加以对待,因而并不存在侵犯人性尊严之嫌疑。
事实上,从上述学者的批判来看,其所担心的并非是刑法被工具化,而是担心刑法被工具化后所造成的后果,即预防刑法被设立以后,会造成刑法范围的过度扩张,以至于出现因过度强调一般预防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等“将人工具化”之现象。但是刑法的工具化并不等于刑法将人工具化,刑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天然地具备工具属性,这是由刑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若因为其在使用中会被当作工具便弃之不用,无异于因噎废食,而且如前所述,唯有超出必要限度的刑法才会将他人当作一般预防的工具,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刑法是否被当作工具使用,而在于我们对刑法的使用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以工具主义对所有预防刑法进行批判的观点,混淆了刑法工具化与刑法将人工具化这对概念,忽略了刑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一面,与前述“空置率高”的批判一样,存在以偏概全之嫌疑。而且,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法益具有抽象的危险,其便已经因为存在法益侵害性而具有相应的违法性,在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刑限度内科处刑罚是刑法的应有之义,此时的刑法(当然必须满足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其实是“协助”其实现个人自律的工具,即为了满足个人在民主体系中的自我决定权的实现,如通过法律的形式解决社会冲突①(19)①Vgl.Maihofer,Gesetzgebungstheorie und Rechtspolitik,in:Grimm/Maihofer(Hrsg.),Gesetzgebungstheorie und Rechtspolitik(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13) 1988,S.409.,具有合理性;超出此种限度的刑法,方才沦为如满足公众情绪、预防损害发生或者纯粹一般预防的“过度”工具化的刑法,为笔者所不采。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止刑法工具主义化,而在于如何防止刑法过分工具主义化,以确保刑法价值与功能的均衡,合理排除刑法的自带危险,并将之控制在法治的“底线”范围内。
(三)有违最后手段性原则之反思
除了上述质疑外,学界对于预防刑法最多的批判莫过于其过早地介入了社会治理之中,因而有违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因为作为国家最严厉的手段,刑法应当最后被使用,只有其他所有的方法都难以起效时,才能够动用刑法。②(20)②Vgl.Baumann/Weber/Mitsch/Eisele,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12.Aufl.,2016,§ 2,Rn.8.但是由于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加,刑法的立法定位与性质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立法者不但没有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反而在部分情况下将其作为首要甚至唯一手段加以运用。③(21)③Vgl.W.Hassemer,Produktverantwortung im modernen Strafrecht,1994,2.Aufl.1996,S.8.虽然德国学者对于谦抑性与最后手段性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但均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因此没有必要将二者进行强行区分。Vgl.Rudolf Rengi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12.Aufl.,2020,§ 3,Rn.5ff;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1,5.Aufl.,2020,§ 2,Rn.97.显然,学界的批判是建立在刑法“最后手段性”必须被无条件遵守的前提下,而依照本文的观点,此前提并非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该原则本身也存在诸多疑问。
首先,从逻辑上分析,在刑法前没有其他法律加以制裁,原因并不一定在于刑法的管辖范围过广,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法律设置的并不周全。如我国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即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虽然彼时并没有前置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却罕有学者认为该条款有违刑法“最后手段性”。④(22)④参见刘艳红:《民刑共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法学论坛》2021年第5期,第42页。因此,只要某一行为严重侵犯了法益,我们便能够且应当运用刑法对其进行惩处,而毋须等到设立其他前置法后再用刑法进行“二次调整”,此时刑法违反所谓“最后手段性”的原因不是其处罚范围过广,而是其他法律的规制范围过于狭窄。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如今多将最后手段性理解为合比例性的普遍宪法原则在刑法相关内容上的体现⑤(23)⑤Vgl.Jahn/Brodowski,Das Ultima Ratio-Prinzip als Strafverfassungsrechtliche Vorgabe zur Frage der Entbehrlichkeit von Straftatbeständen,ZStW 2017,S.371.,即只要某一侵害法益的行为满足比例原则,且能够归责于行为人,就能够被作为犯罪行为予以处罚①(24)①Vgl.Wolfgang Frisch,Voraussetzungen und Grenzen staatlichen Strafens,NStZ 2016,S.24.,并不要求具有相对应的前置法。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所有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可以且必须在宪法中找到具体依据,并对其提供直接保护或者保障,因此,与其说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毋宁说刑法是宪法的保障法,且是最全面、最彻底保障宪法有效实施的法律部门。②(25)②参见高铭暄、曹波:《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第5页。既然刑法是宪法而非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在逻辑上,其就不应当“只有在其他部门法调整无效时才被动用”,也无须在其他法律无效的时候才“替补出场”,而是在必要的时刻,如某一行为其他部门法并未规定却已经侵害宪法所保护的利益时,也可以冲锋在前,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③(26)③参见付立庆:《积极主义刑法观及其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而且,刑法天然具有谴责的意味,对于部分严重侵害法益之行为(如故意杀人)必须且只能交由刑法来加以管控,就此而言,刑法是对其进行制裁的唯一手段,而不是最后手段。
其次,在最后手段性的发源地德国,此概念也具备两重含义:第一,必须在所有可用的社会控制措施中考察、比较刑法与其他可能的替代措施;第二,由于刑法在适用过程中作为手段的刑罚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错误适用该措施会给公民个体和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此,刑法不能被作为纯粹的社会治理工具,对刑法的适用必须有法治控制机制的保障。④(27)④Vgl.Lüderssen/Nestler-Tremel/Weigend(Hrsg.),Modernes Strafrecht und ultima-ratio-Prinzip,1990,S.11.是以,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并不是指唯有穷尽其他法律手段无效后,才能够使用刑法进行规制,而是指司法者必须依据明确的限定标准来适用刑罚。因为只有明确了刑法适用的限定标准,才能够明确其处罚范围,进而将之与其他制裁措施的处罚范围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功能边界,从而确定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制裁措施。所谓“最后”,是指基于刑罚的严厉性,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相比,刑法的适用应最为谨慎、限定标准应最为明确及具体。⑤(28)⑤参见敬力嘉:《信息网络犯罪规制的预防转向与限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9-60页。
最后,就谦抑性而言,其本身也并非一种强制性规定,仅仅是一种刑事政策上的要求⑥(29)⑥Vgl.Roxin & 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1,5.Aufl.,2020,§ 2,Rn.101.关于Roxin教授刑法理论在各种预防性刑事政策冲击下的变动,参见陈尔彦:《德国刑法总论的当代图景与变迁——以罗克辛〈刑法总论教科书〉第五版修订为线索的展开》,《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4期,第112-123页。,而刑事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之物,其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故对刑法谦抑性的理解与适用应在合理的限制内,并与犯罪形势、社会形态等因素保持一致。从词源上探究,“谦抑”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主观主义刑法学家宫本英脩的著作之中,氏受当时大审院的著名判例“一厘事件”之影响,结合其特殊预防主义和征表主义的立场,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无法根绝,刑罚不能任意发动,刑法必须自我谦抑,只能处罚那些征表出适合用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⑦(30)⑦参见宫本英脩:《宮本英脩著作集(第1巻):刑法學綱要》,成文堂1986年版,第79-80页。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刑法的谦抑性就并非一味地强调限定处罚范围,而是更倾向于“具体地、实质地探求为保全国民利益所必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刑罚”⑧(31)⑧参见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5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5页。。单纯或片面基于谦抑精神主张慎重处罚,使刑法无法作为、不能作为或完全消极应对,本质上是与刑法作为社会制度的功能本性背道而驰的。一如我国学者所言,从刑法谦抑精神的起源、发展、理论基础、基本主张、实现方式等内容看,其核心旨趣是克制刑罚权的滥用;或强调刑罚的有效性,刑罚权的配置与启用应当遵循慎用性。⑨(32)⑨参见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83页。综上,既有对于预防刑法的批判,或存在逻辑上的谬误,或存在对相应概念之误解,因而并不可取。
三、预防刑法的正当化依据及其界限
从立法模式分析,预防刑法其实是将既有部分犯罪的预备犯正犯化,具有提前干预的特点,而且为了追求有效的风险控制,其构成要件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然事与愿违,此种做法不但无法为刑法的预防目的提供内在规范限度,更容易导致集体法益保护范围乃至刑法处罚范围的恣意扩张①(33)①参见刘艳红:《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第74-75页。,因此才招致了前述的诸多批判。但在批判之余,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古典自由主义刑法是否足以应对目前纷繁复杂的犯罪手段?Schünemann教授在抽象危险犯被法兰克福学派大肆抨击时便指出:根本地诋毁抽象危险犯其实意味着刑法学无法将抽象危险犯作结构性的严谨的合理化,也无法在抽象危险犯这个领域促成理性的立法,因是一种失策与倒退。为了使刑法在目前的环境下也能履行它保护法益的任务,必须在实用的方向上进行研究。②(34)②Vgl.Schünemann,Kritische Anmerkungen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GA 1995,S.213.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如今的预防刑法③(35)③而且从学界指出的条款分析,预防刑法所涉及的罪名也均为抽象危险犯,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若传统的立法模式完全能够有效预防犯罪,我们自然无须采取侵犯更多人权,更加限制公民自由的预防刑法;若既有的立法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如今的社会风险,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以牺牲部分自由为代价,选择更能保护法益的预防刑法,再从其他方面对其进行改良。④(36)④相同观点,参见付立庆:《积极主义刑法观》,《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第103页。而根据本文的观点,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刑法理论上,预防刑法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只要对其进行相应限制,完全能够同时符合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原理。
(一)预防刑法的现实需求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刑法已经无力应对各类新型犯罪。例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连接网络的每台计算机终端均可相互访问,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反馈都是即时交互完成的,计算机犯罪的预备阶段、实行阶段与结果发生阶段之间几乎不存在时间间隔。对于这种犯罪,传统刑法即使在出现法益侵害危险时就提前介入,也阻止不了犯罪结果的发生。⑤(37)⑤参见王良顺:《预防刑法的合理性及限度》,《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第55页。事实上,传统刑法之所以会对预防刑法做出上述批评,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诞生之际,法治思想薄弱、国家侵犯公民人权严重,因此刑法以抵抗政府为基本价值取向,要求严格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以免国家过多地干预民众自由⑥(38)⑥Vgl.Thomas Vormbaum,Einführung in die modern Strafrechtsgeschichte,4.Aufl.,2019.S.26.,而且彼时的社会工业化水平较低,危害结果也较容易控制,故只需要处罚结果犯和少量的抽象或者具体危险犯就足以实现保护法益的刑法目的。然而,此种社会现状已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传统犯罪已经呈现出全新面貌,新时期犯罪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预防与应对早已无法交由个人来单独完成,恐怖犯罪和网络犯罪等其他犯罪的频繁发生也充分能够说明,传统刑法无法有效控制此类可能对重大超个人法益造成严重威胁或者损害的犯罪。一如德国学者Calliess所言:相较于启蒙哲学时代的讨论,当代风险社会的规范议题不再是强调限制国家统治权力、自由应如何分配等问题,而是聚焦在社会持续处于一种高度仰赖社会控制机制的氛围,亦即要求国家积极采取行动排除或降低风险(恐惧),或是实现安全保证之需求。换言之,如今的讨论中心在于国家任务如何防止生存基础的毁败。⑦(39)⑦Vgl.Rolf-Peter Calliess,Strafzwecke und Strafrecht,NJW 1989,S.1340.而且,无论学者是否愿意承认,如今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心都已经由事后惩罚向事前预防偏移⑧(40)⑧参见孙国祥:《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3页。,且该倾向已经日渐明显,在此种社会背景下,一味呼吁返回(并未被精确重构的)传统刑法,不但完全无法提供什么未来的愿景,难以指导立法,而且只会让理论与实践的分歧愈演愈烈,反而成为法律发展的绊脚石,更无法为如今占主导地位的立法趋势提供必要的批判。⑨(41)⑨Vgl.Schünemann,Kritische Anmerkungen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GA 1995,S.217.是以,刑法不能固步自封,应当重新审视自我定位,正视自身的不足,在概念工具和方法论上更新,才能在新的刑法变革时代找到自身价值。①(42)①Vgl.Michael Kubiciel,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wissenschaft,JZ 2018,S.176ff.
其次,预防刑法的设立并不违背教义学基本原理。从逻辑上分析,若预防刑法有违教义学基本原理,则所有的预防刑法条款均应当遭受批判,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最为重视刑法合宪性、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德国,其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法益已经面临威胁这一事实就是刑法规范合法化的理由。刑法理论中被广泛接受的一点是,刑法所遵循的目标不只是压制,而且也是预防,同时阻止未来的犯罪行为也是其正当的目的。②(43)②Vgl.NJW 1993,S.1911,NVwZ 2006,S.583f.该院在近期的判例中更是明确指出:在没有出现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将刑法提前到对法益损害的预备阶段,这并非与基本法不协调。在攻击行为预备阶段就已经确定了其刑罚可处罚性的规定与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的宪法规范命令是一致的……即便这涉及特殊的、与刑法典第89a条的调控范围无法直接比较的情况,但从该规定中仍可以推断出: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根据反对处罚损害法益的预备行为。③(44)③Vgl.BGH HRRS 2014 Nr.929,Rn.27.由此可见,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刑法从来没有存在过,“预防刑法”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刑法当中,只是因为其保护了极为重要的法益,具有相对明确的构成要件,满足罪刑法定原则故并未招致批判而已,学界对于预防刑法的批判也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做出了一定的价值衡量后“因条文而异”。既然如此,我们在评价预防刑法时,就不应轻率地陷入一种片面批判的立场,并认为所有的预防刑法都有违“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而是应当对各个条款进行个别判断,衡量其侵犯的自由与保护的法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最后,从国家功能的角度,也应当认为如今法治国勿须再恪守消极的古典自由主义,而应当积极主动承担起社会国的保护义务。现今的法治国理念认为,社会国不能够仅停留在形式的法治国即“守夜人国家”之上,而是应当为社会正义服务,肩负起社会安全与平衡社会差距的任务,以有效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自由。④(45)④Vgl.Zippelius/Würtenberger,Deutsches Staatsrecht,33.Aufl.,2020,§ 13,Rn.4ff.根据社会契约论,民众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⑤(46)⑤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页。,但即便建立国家后,民众仍然有可能遭受其他公民或国家的不法侵害,因此,现代法治国家负担有“通过保障内部与外部安宁而对公民加以保护”之义务。⑥(47)⑥Vgl.Calliess,Die grundrechtliche Schutzpflicht im mehrpoliegen Verfassungsrechtsverhältniss,JZ 2006,S.321.我国《宪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并在第33条提纲挈领地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这些条款中的“保障”“保护”或“不受侵犯”等字眼完全可以解读出,国家对于民众背负有保护义务。⑦(48)⑦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保护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6页。是以,在既有的刑法无法充分保护法益时,我们完全可以设立更多、更为完备的条款,以充分履行国家的保护义务。而且在如今的风险社会中,个人自由与基本秩序的保障较以往更加仰赖国家所提供的保护,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到来,国家的角色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何防范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潜在风险,有效应对危机,为公民提供安全的生活条件,已然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因此国家需要积极地承担起风险预防的任务。刑法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一种,也理应做出相应改变。⑧(49)⑧参见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4页。就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风险刑法的强烈批判者Prittwitz教授都不得不承认:在如今的风险社会,国家不只是提供自由的法治国,同时也是限制自由的保护国,这里没有提供自由的刑法,而是必须被规定、被控制、被镇压。安全在此时优先于自由!⑨(50)⑨Vgl.Prittwitz,Das Strafrecht:Ultima ratio,propria ratio oder schlicht strafrechtliche Prohibition?,ZStW 2017,S.397.
(二)预防刑法的法理依据
不言而喻,预防刑法在提前保护法益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众的自由,虽然有赞成者指出:“保障人权与保卫社会并非绝对的互斥关系,限制自由无非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价值。刑法适度侧重安全价值,并非剥夺或限制自由,而是保障更多人的自由和安全。”①(51)①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82页。“维护自由和国内和平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这些国家活动也必须得到社会认可。如果法律证明是有效的,那么这也必须被适用于社会,因为只有在保障公民自由的角度,国家强制力满足其安全职能的要求上,它才能宣称具有合法性。”②(52)②Vgl.Bernd Heinrich,Zum heutigen Zustand der Kriminalpolitik in Deutschland,KriPoZ 2017,S.13.但这样的论述显然值得商榷,一方面,刑法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法律,故事实上所有人的自由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由于预防刑法“打早打小”的策略,往往将犯罪扼杀于萌芽之中,因此“预防性刑法措施预防犯罪的效果并不明确,但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却是现实的和明显的”③(53)③参见王强军:《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隐忧》,《当代法学》2019年第2期,第8页。。更何况,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的位阶关系,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④(54)④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1 页。,在此种情况下,刑法是否真的限制了少量自由而保障了更多的法益,在理论与经验上难以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不难看出,此类说辞均是站在国家层面,论证预防刑法的妥当性,即只要刑法保障了更多人的法益,便能够自动获得合法性,而现今的法治国原则以尊重自我决定权、维护自由不受侵犯为核心价值,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只能来自公民自身的同意。⑤(55)⑤Vgl.Kristian Kühl,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8.Aufl.,2017,§ 8,Rn.9;Neumann,in:Nomos Kommentar Strafgesetzbuch,5.Aufl.,2017,§ 34,Rn.9.是以,从国家利益衡量层面难以论证预防刑法的合理性,我们只能从公民个人同意的角度去寻找预防刑法的正当化依据,而依笔者之见,这样的论证思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我国的社会观念中,预防刑法较传统刑法更能够得到民众的赞同。
根据社会契约的思想理念,以人权为导向的刑法根据和刑罚根据,主要是由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推导而来的⑥(56)⑥Vgl.Hassemer,Darf es Straftaten geben,in:Hefendehl(Hrsg.),Die Rechtsgutstheorie,2003,S.58.,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公民只是为了达到自由与和平的共同生活且这种生活在程度上不能通过其他更轻的手段达到时,才把如此之多的刑法干预权转让给了立法者。⑦(57)⑦Vgl.Roxin,Rechtsgüterschutz als Aufgabe des Strafrechts?,in:Hefendehl(Hrsg.),Empirische Erkenntnisse,dogmatische Fundamente und kriminalpolitischer Impetus:Symposium für Bernd Schünemann zum 60.Geburtstag,2005,S.138.虽然我国传统的罪观念以儒家的天道、礼制、伦理为先验性基础,最终形成了公私两元对立、国家法益>家族法益>个人法益的基本结构,但随着近代政治理念的转型,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主权在民的理念塑造了新的政治关系,国家不再是教化人民、统御宇内的至上者,而是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载体。⑧(58)⑧参见李勤通:《中国法律中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当代刑法实践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132页。是以,只要能够论证民众在面对巨大的风险时,会愿意让渡更多的自由和处罚权给国家,预防刑法便能够拥有正当性。笔者并不否认,在当今所谓的风险社会,我们最需要防范的是不断扩张的国家刑罚权,因为以风险之名行扩张刑罚之实,不断地侵犯人权与自由,对我国的刑事法治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刑法对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并非亘古不变的,而是应当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不断地做出调整。在法益遭受严重的侵害而需要强化保护时,就应当适当地扩张刑罚权,增设新的犯罪或者加重某些犯罪的刑事责任,公民的自由度也就会有所抑制;反之,在法益不再存在严重的侵害危险时,就应当对刑罚权加以限制,适当降低刑法对法益的保护力度,公民的自由度也会得到适度的扩张。⑨(59)⑨参见王良顺:《预防刑法的合理性及限度》,《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第57页。诚然,极度的法益保护会压缩国民的自由,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刑法规范还远远没有达到此种程度,因为此时民众让渡出的自由,并非是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长达数年的刑期⑩(60)⑩参见房慧颖:《预防刑法的天然偏差与公共法益还原考察的化解方式》,《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第106页。,而是国家为了查处此类预备行为规定的一些侵犯自由的检查措施,如现在随处可见的抽查身份证件、地铁安检、上火车喝开封液体以及疫情期间的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等,这些情况对民众自由的侵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根据既有的条文判断,我国预防刑法之条款均为可能给民众重大法益造成损害的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因而也能通过宪法比例原则的检测并得到绝大部分理性民众之认可。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所做之修改为例,本罪保护的法益为抽象的公共安全,因而属于典型的预防刑法,虽然立法者将本罪的对象由“甲类传染病”扩张至“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扩大了处罚范围,较既有的条款侵犯了民众更多的自由,但这样的做法显然能够得到民众的赞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够理解并且会遵守国家规定,闭门不出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可见,与域外倡导“不自由,毋宁死”的极端个人自由思想有别,我国民众更为重视生命的存续与生活的质量,愿意为了自己日后更长久、更幸福的生活放弃眼前短暂的人身自由,而此种思想正与预防刑法的主旨不谋而合。综上,从理性人的视角分析,在如今的风险社会,为了避免自身重大法益遭受损害,民众更可能仰赖而非抵抗国家,其更可能希望拥有一个积极预防风险、维护安全的国家,而不只是一个消极保护个人自由的“夜警国”,仅仅侵犯了轻微法益,却保护了重大法益的预防刑法完全能够得到我国民众的赞同。
(三)预防刑法的合理限度
部分学者可能认为,若将预防刑法的正当性建立于民众的同意和支持之上,纯粹依照民众的喜好或者同意来确定刑法的范围,将会导致刑罚民粹主义。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有此担忧。诚然,本文是以“自由主义”为立足点,将理性人最大限度维护个人法益之目的作为刑法的正当化依据,但是这并不代表某一侵害法益的行为只要民众的同意即可入刑,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必须满足宪法及刑法的基本原则,故唯有在满足如下条件时,才能够设立“预防刑法”条款。
1.不得过度干涉公民基本权利。在当今法治理念之下,任何新增的刑法罪名都必须具有宪法依据,故若某一罪名限制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则只有此种限制能够通过合宪性审查,该罪名才能在法秩序中合法化。①(61)①参见王钢:《刑法新增罪名的合宪性审查——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为例》,《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第83-84页。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添了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作为120条之六,以制裁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之行为,而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此,公民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便与刑法规范发生了冲突,而且,由于我国宪法并未对该条款做法律保留,故在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应当更为审慎。诚然,恐怖活动一旦开始实施,不但会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更可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损害,而社会秩序及民众的生命安全都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价值,故对于可能直接甚至间接导致恐怖主义发生的行为进行规制,虽然可能会遭受不符合明确性的诟病,却也能够通过均衡性原则的审查。但问题在于,在本罪中,行为人仅仅是持有恐怖主义物品,并未实施任何宣传或传播行为,并不会给民众安全造成任何危险,故行为人其实只是侵犯了“恐怖主义物品的管理制度”,虽然《宪法》第28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确立了国家具有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职责和义务,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与无法律保留之基本权利相冲突并对其予以限制的宪法利益,但此种为了保护抽象的秩序而限制公民不受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能否通过均衡性的审查,却着实值得怀疑。是以,立法者在日后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当“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与宪法之间”,注意“刑法的合宪性调控”,使得所保护的法益与所限制的国民基本权利满足均衡性之要求,以免刑法条款因不符合宪法比例原则而违宪。②(62)②参见何荣功:《“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第154页。
2.当某一犯罪行为具有侵害极为重大的个人法益或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时,才能够设立预防刑法。①(63)①参见姜敏:《刑法预防性立法:罪刑国谱和法治危机消解》,《政法论坛》2021年第6期,第184页。因为预防刑法会侵犯每个人的自由,故其保护的也必须是每个人均能够享有的极为重大的法益,唯有如此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赞同。我国有学者指出,刑法干预前置化适用的集体法益类型必须具备以保护个人法益为目的、与个人法益存在紧密的关联、能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以及不能对个人自由造成伤害,不能压缩公民的自由空间三个条件,才能够具有正当性。②(64)②参见王强军:《刑法干预前置化的理性反思》,《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239-240页。本文赞成学者对预防刑法限制解释之思路,但认为其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不论何种集体法益,其最终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发展而服务的,因此,侵犯集体法益的行为必然间接损害了所有人的法益,只是紧密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论者的第一个条件并不能够起到有效的限缩作用。另一方面,预防刑法的设立,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压缩民众的自由,故认为预防刑法不得给公民自由造成损害的要求,也有些不切实际。与之相对,本文将预防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限制在“重大的个人法益或公共安全”范围内,显然更有利于限制预防刑法的设立。就此而言,《刑法》第287条之一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将销售淫秽物品甚至部分违法行为的预备行为设定为犯罪难以得到本文的赞同。③(65)③同旨参见闫二鹏:《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法教义学审视与重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思考〉》,《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第60页。虽然有学者指出:此类违法行为会因为计算机、互联网应用的技术优势,使在短时间内以近零成本大量反复实施,倍增行为的危害量,使累积危害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而有提前处罚之必要。④(66)④参见皮勇:《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35-136页。但是此种理由也只能够解释为何可以将盗窃、诈骗等犯罪的预备行为入罪,却始终难以回答,为何在线下散布违法活动信息或实施违法行为,无论数量多大、次数多少都不成立犯罪,而在线上只要发布违法信息达致一定数量就能够成立犯罪之疑问。
3.与前条相对应,立法者不得将轻微的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虽然我国刑法处罚范围较外国为窄,但这并不意味我们的处罚范围也必须向域外看齐,因为在我国社会观念中,对于受刑人具有相当大的偏见,不论罪行大小轻重,个人一旦被认定为罪犯,都会给其自身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刑罚本身的严厉程度,而我国又缺乏域外刑事追诉体系漏斗形的强大的过滤功能,若立法者如域外一般,将许多较为轻微的违法行为都认定为犯罪,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堪重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罪刑不相适应”之体现。⑤(67)⑤参见姜涛:《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24-125页。作为理性人的国民当然会知晓,其终生都不可能实施重大犯罪行为,故其考虑的也并不是国家会为了预防何种犯罪而制定新的条款,其所关心的只是法律将侵害重大法益的犯罪处罚前置后,自己的行为会受到何种限制,以及自身法益能够获得多大的保护;但同时他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绝对理性地行事,也有可能成为不法侵害人,可能因为一时激愤或各种原因实施一些轻微的侵害法益之行为。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即便决意遵循法秩序、恪守内心的规范障碍,也仍然可能因受诱惑或者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以恶小而为之”,侵犯他人的微小权益。⑥(68)⑥参见王钢:《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610页。而一旦其赞同将任何程度的违法行为都认定为犯罪,必然会让自己身陷囹圄。因此,他们在赞同不会过分干涉自身自由来保护自身重大法益之预防刑法的同时,也会反对刑法处罚过于轻微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以免刑法强大的附随效应祸及自身。
4.必须具有更为具体的构成要件。如前所述,预防刑法的正当性来源于理性人为了保护法益而让渡出的部分自由,若某一条文不具有明确性,则意味着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会被无限扩张,从而使得民众实际让渡出的自由超过原先预设让渡的自由,有违其设立预防刑法之初衷。因此,“明确性”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从理性人个人意愿中推导而来的预防刑法的必然结论。然而在我国近期的立法例中,却出现了些许有违“明确性”原则的立法。例如,为了预防恐怖主义的蔓延,《刑法修正案(九)》增添了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并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和社会管理等制度。但一方面,对于究竟何谓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立法者却始终语焉不详①(69)①参见刘艳红:《二十年来恐怖犯罪刑事立法价值之评价与反思》,《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43-45页。;另一方面,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和社会管理概念本身也非常模糊,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概念本身非常模糊、内涵和外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还对本罪的对象作如此宽泛的列举,本条款几乎可以实现对基层日常社会治理的全面覆盖②(70)②参见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59-60页。,必然大大限制民众的自由。又如,为了预防危害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立法者规定了妨害安全驾驶罪,但对于条文中“暴力”范围以及“干扰”之程度却并未作出任何规定,两大核心构成要件要素的不明确就导致本罪的认定标准不明,进而导致了各地争相判处“首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奇异景象,这些构成要件要素的不明确不但会给相应犯罪的治理实践带来难题,而且也难以实现良好的对公众行为的规范指引作用。诚然,此类问题是属于预防刑法设立后的司法认定问题,但这恰恰说明立法者在预防刑法设立之初并没有对其前置行为的危害性以及严重程度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以往修正案中预防刑法设立后“考虑不周造成司法困难”的教训并没有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得到避免和遏制③(71)③参见王强军:《刑法干预前置化的理性反思》,《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242页。,希冀在日后的立法模式中应当予以避免。
5.必须满足其他罪刑法定原则及法益保护原则。因为无论如何扩张,预防刑法都不过是刑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必然无法脱离刑法的本质,因此,预防刑法也必然受到其他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如罪刑相适原则、责任主义等。
此外,因为危险预防的实现有赖于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加强合作,若以刑法为工具来实现社会风险的预防与控制,则势必增加公民的刑法义务④(72)④参见何荣功:《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47页。,故在法律适用阶段,我们应当将作为行为规范的刑法条文中可能存在的过度干涉公民自由的危险予以排除或者修正⑤(73)⑤参见黎宏:《预防刑法观的问题及其克服》,《南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20-21页。,主要体现在:1.时刻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防止预防刑法在实践中的扩张过度而赋予民众更多的义务。例如,《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本条属于典型的不作为犯,以具有作为可能性为成立条件,故虽然从法条的用语上看,只要“拒不改正”即可成立本罪,但若行为人一旦实施改正行为,必将极大影响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破产,也应认为其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具有作为可能性⑥(74)⑥虽然期待可能性与作为可能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德国通说认为,在不作为犯中,二者在法律上具有同样的意义。Vgl.Bosch,in:Schönke/Schröder,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30.Aufl.,2019,Vorb.§§ 13ff,Rn.155.,并不成立本罪。因此,在实际运用该条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在责令改正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完全可以暂停相关业务、关闭网站等以防止侵害进一步扩大。所谓没有改正能力而不改正,不过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愿意割舍经济利益的托词”⑦(75)⑦参见邱陵:《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探析》,《法学杂志》2020年第4期,第71页。,进而将没有改正的提供者一律认定为犯罪,而应当具体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事实上的行为可能性以及规范上的期待可能性。⑧(76)⑧参见梁根林:《传统犯罪网络化:归责障碍、刑法应对与教义限缩》,《法学》2017年第2期,第13页。2.正确认识到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故唯有在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对法益造成抽象危险时才将之认定为犯罪,以免让刑法沦为“行政处罚法”。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后,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诸多判例,但在部分判例中,行为人却并未危及本罪保护的法益。如我国有判例指出:
被告人因刷卡问题与驾驶员刘某发生争执,遂用手掌拍打正在驾车的刘某头顶部,致公交车急刹车停在道路上。法院认为被告人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①(77)①参见北京市密云区法院(2021)京0118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书。
本文不赞成此项判决。因为本罪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即可,而是必须达致“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该条第2款也规定“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故按照体系解释,唯有在行为人的暴力或抢夺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达到足以让交通工具处于“类似无人驾驶”的状态时,才能够成立本罪。但在本案中,行为人并未实施如此严重的暴力行为。因为被告人是用手掌拍打驾驶员的头顶部位,而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拍打行为并不会具有很大力道,事后的伤情鉴定也指出,刘某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未见明显损伤,可见其的拍打力道并不大。故本文认为,被告人的拍打行为并未达到干扰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程度,不会导致车辆出现失控的风险,因而没有侵害到社会公共安全,法院的判决仅仅对其行为进行了形式判断,而没有结合该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进行考虑,因而有所不当。
综上所述,合理限度的预防刑法只是对严重侵害重大超个人法益的高度危险犯罪的特殊措施,它是对传统刑法的必要补充,并不违背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也不会改变刑法作为“犯罪人大宪章”之本质;相反,它合理地平衡了公民的自由保障与安全需求,有助于社会秩序的长期安定并符合公民的根本利益。
四、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代社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时代。相应地,刑法作为控制社会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也需要观察过去,预测未来,并借此构建具有融贯性的刑法理论。因此,罔顾时代背景,一味批评预防刑法有违古典自由主义刑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毕竟与之对应的“古典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一如Hilgendorf教授所言:我们不能因为实体刑法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扩张具有“惩罚性”就武断地谴责其不合法。相反,当新型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和平的共同生活构成威胁的时候,存在许多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理由,而最终做法是在议会制民主的政体下通过民主制度制定有效的法律。而且,刑法的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责任原则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立法者,但无法确切定义国家刑罚权的界限。②(78)②Vgl.Hilgendorf,Punitivität und Rechtsgutslehre:Skeptische Anmerkungen zu einigen Leitbegriffen der heutigen Strafrechtstheorie,In:Neue Kriminalpolitik,Bd.22(2010),S.131.对于面向未来与走向世界的中国刑法学而言,也应当与时俱进,扬弃传统刑法的精华与糟粕,借鉴域外有益成果,以国情与本土需要为问题意识,促进刑法教义学的创造性转换。③(79)③参见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89页。具体至预防刑法中,在应然层面,只要某一立法满足比例原则及刑法的基本原则时,其便是符合法律的实质要求的,而是否符合前述的法律基本原则,又是一个纯粹的价值判断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结论,故除非出现了“显著不成比例”“明显失衡”以至于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之情况,我们便不应当以自身的价值理念去贸然否定立法者或者其他学者的价值理念;在实然层面,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理应与它所处的特定时代相对应。在恐怖主义犯罪、环境污染、重大传染疾病等各种风险迎面而来,且一旦现实化便会造成巨大且不可控制之法益损害的情况下,个人自由与基本秩序的保障日益地仰赖国家所提供的保护,国家也需要积极地提前介入,承担起风险预防的任务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与自由。④(80)④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第33页。我国《刑法修正案》中绝大部分条款均能够满足前述预防刑法的立法要求,只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将之正确运用,在当今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相较固步自封的“古典自由主义刑法”其实更能够满足保护法益之需求,因而更能够体现刑法的机能,也更能获得我国民众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