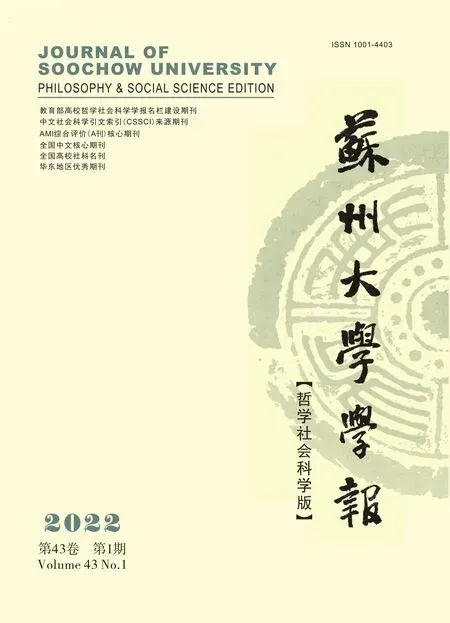永嘉之乱后汉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变化
——从后宫、前朝的联动到内朝、外朝的对立
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汉国于光兴二年(311)、建元二年(316)接连攻破洛阳、长安,俘获晋怀帝、晋愍帝,即将实现刘渊即位诏书中“绍修三祖之业”的政治目标①(1)①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8、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4-2685页。,然而却在两年后遭受灭顶之灾。“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②(2)②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8、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4-2685页。,平阳之众奔于关中,平阳宫室亦被焚。③(3)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8、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4-2685页。虽然史家将刘曜的长安政权视作汉国的后继,但刘曜追尊高祖以降四代为四帝,“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④(4)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2650、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8、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4-2685页。,事实上构建了新的王朝。汉国虽国祚短促,未能接续西晋建立大一统或北方统一的王朝,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前、后赵的对峙,华北的长期混乱,未尝不以之为源头。对于汉国在覆灭西晋后转瞬速亡的原因,学界或从胡汉矛盾予以解释,或从五部屠各与氐人联盟的关系进行立论,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而且符合史实的①(5)①唐长孺先生认为汉国以降的五胡政权,按照部落贵族军人们的利益建立起来,各族间形成区隔;同时他们还须取得高门大族、堡坞豪帅、各族酋豪的合作。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7-192页。在汉国胡汉关系问题上的研究,参见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方诗铭:《“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史林》1996年第3期;邓乐群:《刘渊宗汉立国的历史评价》,《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在汉国内部胡胡关系的研究,参见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陈勇:《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对汉国政治整体变迁的系统研究,参见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日本对汉国的相关研究,参见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版,第49-72页;内田吟風:《南匈奴に関する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版,第201-356页;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南匈奴的自立及其国家》,第22-50页;片桐功:《屠各考——劉淵挙兵前史》,《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988年总第13号,第1-30页;田中一輝:《西晉時代の都城と政治》,朋友书店2017年版,第七章《永嘉の乱の実像》,第229-256页。。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汉国内部的权力架构及其变迁,以期从内政的角度对永嘉之乱后汉国未能重建一统的原因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一、嘉平二年至四年间(312—314)后宫与前朝的联动
光兴二年(311)四月,汉军俘获晋怀帝,达成了自河瑞元年(309)出兵以来攻占洛阳的目标。东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已用“永嘉之乱”来表述洛阳倾覆后全国的混乱局面。②(6)②沈约:《宋书》卷十七《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2页。如果从胜利者汉国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同样影响深远,平阳政权在倾覆洛阳七年后便告终结,未尝不与此相关。《晋书》史臣评价刘聪“信不由中,自乖弘远,貌之为美,处事难终;纵武穷兵,残忠害謇,佞人方辔,并后载驰,阉竖类于回天,凝科踰于炮烙”③(7)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702、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58-2660、2660页。。史臣批评的这些行为大多出现在倾覆洛阳之后,可以说汉国政治以嘉平二年(312)为转折,此前主要致力于倾覆洛阳的西晋朝廷,此后转为建构具有专制性的皇权。
《晋书·刘聪载记》载:“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④(8)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702、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58-2660、2660页。对于汉国决策方式的这一重要转变,《资治通鉴》将之系年于嘉平二年(312)正月。⑤(9)⑤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左贵嫔为太保刘殷之女刘英(丽芳)。⑥(10)⑥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694页。嘉平二年正月,刘英与妹刘娥(丽华)一同被拜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除刘英、刘娥外,刘聪“又纳(刘)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⑦(11)⑦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702、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58-2660、2660页。,《资治通鉴》载贵人“位次贵妃”⑧(12)⑧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三十国春秋·前赵录》云“自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⑨(13)⑨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694页。。同在正月,刘聪改革后宫制度,除了贵嫔、贵人,还设有昭仪、贵妃与夫人,后三者“皆金印紫绶”⑩(14)⑩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
刘聪之所以增设后宫嫔妃,是为了扩大外戚阵营。其意与孙皓、晋武帝相同。(15)李磊:《刘渊的顾命大臣与河瑞、嘉平之际汉国的皇权重构》,《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第177-186页。正因如此,后宫嫔妃的秩位差序须与前朝的权力格局相对应。刘殷为侍中、太保、录尚书,实居宰相之位。《资治通鉴》云:“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直接以“相”来称呼刘殷,又载刘聪“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乘舆入殿”(1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呼延后死于嘉平二年(312)正月,继任者张后在十二月方才登位(17)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故而嘉平二年(312)正月至六月刘英去世这半年间的后宫以左贵嫔刘英为尊。司空王育、尚书令任顗、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右仆射朱纪的位望低于刘殷,他们女儿在后宫中任昭仪(司空王育、尚书令任顗女)、夫人(中军大将军王彰、中书监范隆、左仆射马景女)、贵妃(右仆射朱纪女)(18)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5-2776、2775-2776、2775、2780、2786、2775页。,秩位低于刘英、刘娥的贵嫔之位。
后宫与前朝在政治上声息相通,成为汉国的第二个政治场域。嘉平二年四月,中军大将军王彰进谏惹怒了刘聪,“上夫人王氏叩头乞哀,乃囚之诏狱”①(19)①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1、2661页、卷八十八《孝友传》第2288-2289页。。。同时在前朝,“其太宰刘延年及诸公卿列侯百有余人,皆免冠涕泣固谏”②(20)②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1、2661页、卷八十八《孝友传》第2288-2289页。。。迫于后宫、前朝的舆论压力,刘聪以“朕昨大醉,非其本心”为借口进王彰为骠骑大将军、定襄郡公,并劝慰道:“先帝赖君如左右手,君著勋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过,希君荡然。君能尽怀忧国,朕所望也。”③(21)③《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79页。陈勇认为原文中的“骠骑将军”当为“骠骑大将军”,参见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从这段话可知刘聪赦免王彰的缘由是“先帝赖君如左右手”。刘聪明白其朝臣多为刘渊旧臣,能否善用他们事关汉国的政治稳定。刘聪与朝臣联姻、扩大后宫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嘉平二年汉国的决策机制是:“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由于后宫与前朝间保持着政治上的联动,左贵嫔刘英的决策,与刘殷关联甚大。《资治通鉴》载:“汉主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④(22)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左贵嫔决之”,其实是将“群臣出,(刘)殷独留”的决策地点由前朝迁至后宫。这种决策方式建立在刘聪对刘殷的信任上。这一决策模式在嘉平二年(312)六月时遇到挑战。《资治通鉴》载:
六月,汉主聪欲立贵嫔刘英为皇后;张太后欲立贵人张徽光,聪不得已,许之。英寻卒。⑤(23)⑤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
关于刘聪立皇后,《三十国春秋·前赵录》载“刘聪皇后刘氏,殷长女也,字丽芳,以左贵嫔立为皇后”⑥(24)⑥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694页。。陈勇先生认为仅有刘英(丽芳)妹刘娥(丽华)一人被立为皇后,司马光对史料的裁断正确,刘英(丽芳)并未被立为皇后。⑦(25)⑦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99页。六月立后引发了后宫矛盾:一方是刘殷父女,另一方则是张太后及其外甥女。张徽光、丽光姐妹入宫时间是嘉平二年四月,《资治通鉴》言“太后张氏之意也”⑧(26)⑧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或许是受到正月里刘聪扩大后宫的刺激,张太后意识到嫔妃之位的政治价值,故而力主外甥女入宫。张徽光、丽光为贵人,“位次贵嫔”,在后位之争中本难以越次,张太后之所以得逞,与刘殷死于六月有关。刘殷之死让刘英失去了外朝的支持,刘聪“不得已”屈从太后。刘英亦在角逐后位的背景下死亡,于是“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的决策方式便难以为继。
张后立于嘉平二年十二月,嘉平三年正月乙亥张太后卒,两日后(丁丑)张后亦卒。尽管《资治通鉴》将张后的死因记述为“张后不胜哀”⑨(27)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但如此相近的死期很难让人不起疑。尤其是张后死的当天(丁丑),刘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怀帝着青衣行酒”⑩(28)⑩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酒宴之设既不合张太后丧礼,又不合张后将死的氛围。从嘉平三年三月刘聪立刘英妹刘娥(丽华)为皇后的情况来看,张氏争夺后位是刘聪建构新权力体系中的一段插曲。
刘娥死于嘉平四年正月己丑,《资治通鉴》载“刘氏贤明,聪所为不道,刘氏每规正之”(29)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所谓“贤明”,《三十国春秋·前赵录》云“(刘娥)与诸兄争论经义,理旨超然,诸兄常深叹谢”(30)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694页。刘殷“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31)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1、2661页、卷八十八《孝友传》第2288-2289页。。。刘娥“贤明”,乃是继承父兄的“博通经史”之学与“济世之志”。刘娥身处后位的十个月,在政治上可以看作是刘殷辅政的延续。
《资治通鉴》云“自是(刘娥死)嬖宠竞进,后宫无序矣”(3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0、2778、2791、2791页、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08、2809页。。将刘娥之死看作是汉国“后宫无序”的开端。在嘉平二年体制中,后宫为前朝的延续,刘娥之死实为转折点,标志着嘉平二年正月至四年正月(312—314)这两年间借助与外朝大臣的广泛联姻来巩固皇权这一政治路线的终结。
二、嘉平四年的改制与掌“万机之事”新相权的成立
嘉平二年体制是以刘渊的顾命大臣为皇权的权力基础,刘聪通过联姻的方式保障他们的政治地位与统治权力。①(33)①李磊:《刘渊的顾命大臣与河瑞、嘉平之际汉国的皇权重构》,《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第177-186页。因而,嘉平二年体制具有从刘渊时代向刘聪时代过渡的性质,指向于维系政权的稳定。然而这一体制未能解决汉国的核心问题:一是汉国与新附晋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五部屠各与六夷的关系;三是汉国与石勒、曹嶷等附从势力之间的关系。为此,刘聪于嘉平四年(314)正月改革了官制。《晋书·刘聪载记》:
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绿綟绶,远游冠。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以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②(34)②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5、2665页、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6、2671页。
嘉平四年的官制改革将五部屠各、六夷、汉人分别纳入不同的职官系统中予以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刘聪用以维系这一体制运行的人事安排:
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食五都。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顗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朱纪为大司空,刘曜为大司马。③(35)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5、2665页、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6、2671页。
七公之中,外戚占据四公。尚书令朱纪上升为大司空后,不再负责尚书政务。加上嘉平二年十月任顗卸任尚书令、马景卸任左仆射、王彰卸任中军大将军,至此外戚全部丧失实权。这标志着刘聪政治路线的调整。刘聪不再依靠与刘渊顾命大臣的联姻来巩固个人的权势。在嘉平四年的体制中,除了刘渊之兄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外,刘粲录尚书事、十六将军“皆以诸子为之”。这一安排是将屠各刘氏的宗室权力集中到刘聪家庭成员身上。
刘粲“进封晋王,食五都”,超越了刘渊所建立的封爵制度规定。汉国封爵制度是“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④(36)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5、2665页、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6、2671页。。所谓“五都”,《晋书》校勘记引《通志》一八六,认为当为“五郡”。然而“五都”为晋人习称,如晋安帝策刘裕文中有“永嘉不竞,四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之句。⑤(37)⑤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二《武帝纪中》,第39页。北魏时崔鸿上表言编撰《十六国春秋》之缘起:“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⑥(38)⑥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六十七《崔光传》,第1503页。崔鸿亦将“五都”与“三帝”“二皇”对举。刘粲“进封晋王,食五都”,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笼络攻破洛阳后新附的晋人。西晋洛阳朝廷虽然覆灭于永嘉之乱,但仍是人心所向。刘聪在覆灭洛阳朝廷后,他以刘粲为晋王,目的在于取代西晋皇帝在人心观念中的位置。
刘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仅位居七公之首,而且掌握了军权与行政权。嘉平四年十一月,“省丞相以并相国”⑦(39)⑦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5、2665页、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6、2671页。,“汉主聪以晋王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⑧(40)⑧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17页。。晋人、五部屠各、六夷均归于刘粲一人管辖。《晋书·刘聪载记》云“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杀生除授”⑨(41)⑨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5、2665页、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第265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6、2671页。。“去冬”正指嘉平四年十一月。可以说,刘聪在嘉平四年建立了汉国新的权力结构,“军国之事”归于相国,“杀生除授”则归于皇帝。这实际上创造了新的皇权与新的相权,汉国的权力结构是主、相二元体制。对于刘聪创设嘉平四年体制的目的,东宫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判断:
(刘聪)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已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踰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①(42)①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7、2667、2667页、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4页、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29页。
汉国东宫设太师、太傅、太保,乃是延续西晋东宫官制,而非两汉旧制。②(43)②刘雅君:《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第76-80页;刘雅君:《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5-82页。东宫三太认为相国“非复于人臣之官”,判断嘉平四年(314)改制让刘粲“威尊踰于东宫”。如所周知,汉国的政权稳定建立在五部屠各与氐人的联盟基础之上③(44)③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71-174页;陈勇:《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16页。,刘乂为氐人领袖单徵外孙、刘渊皇后单氏之子。河瑞二年(310)刘聪夺位后立刘乂为皇太弟旨在维系这一联盟,即东宫师傅们所言“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④(45)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7、2667、2667页、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4页、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29页。。在嘉平四年的改制中,刘聪以刘粲为大单于,掌管统治六夷的“单于左右辅—都尉”机构,的确动摇了刘乂的政治根基。
在东宫三太的研判中,“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的设置是为了羽翼刘粲。太宰是刘聪子河间王刘易⑤(46)⑤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载于《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27-4031页。,刘易在嘉平二年六月与彭城王翼“并典兵宿卫”⑥(47)⑥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80-2781页。。大将军是刘聪子刘敷,刘粲任职在嘉平四年十一月刘粲转为相国之后。唐长孺先生认为刘聪诸子所分配的营兵源自胡汉分治的体系。⑦(48)⑦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7-192页。陈勇先生发现了胡胡分治的体制,即“司隶—内史”体系管理五部屠各,“单于左右辅—都尉”体系掌管六夷。⑧(49)⑧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86-97页;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7页。在东宫三太的理解中,屠各诸营的设置是为了监视“单于左右辅—都尉”体系下的六夷。
卢志、崔玮、许遐被东宫舍人荀裕告发⑨(50)⑨在西晋东宫制度中,太子舍人、庶子、中庶子参预东宫机密。参见刘雅君:《汉晋南朝太子舍人的演变分化与东宫中书、门下机构的形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第9期,第9-17页;刘雅君:《两晋南朝太子洗马之“清选”与东宫秘书机构之发育》,《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06-116页;刘雅君:《权力继承的制度保障——汉晋东宫侍从官体系考述》,《史林》2015年第6期,第32-40页;刘雅君:《汉晋南朝太子中庶子的演化与东宫门下机构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66-72页。,刘聪“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以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⑩(51)⑩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7、2667、2667页、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4页、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29页。东宫三太对时局的判断揭示了刘聪的政治目标,直接引发了刘聪削弱刘乂势力的政治行动。嘉平四年的改制并不仅仅针对刘乂。在汉国权力体系中,幽、冀的石勒、青州的曹嶷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之中。无论是七公、十六将军的人选,还是“司隶—内史”“单于左右辅—都尉”的管理体制,都在事实上排斥了石勒、曹嶷的势力。虽然刘聪遣使署石勒为大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东夷校尉、幽冀二州牧、上党郡公(52)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7、2667、2667页、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4页、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29页。,但多为地方军、政的赋权或遥领与虚封,与汉国主体部分无关。按《晋书·地理志上》,汉国“幽州刺史镇离石”。在汉国幽州刺史存在的情况下,除授石勒为幽、冀二州牧,实待之以外臣。(53)谷川道雄:《東アジ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構造——冊封体制を中心として》,载于唐代史研究会:《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汲古书院1979年版,第98-103页。
刘聪在设置司隶、内史、单于左右辅的同时,“又置殷、卫、东梁、西河阳、北兖五州,以怀安新附”(54)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7、2667、2667页、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24页、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29页。。新置的五州为汉国直辖领土,石勒活动的幽、冀二州并不包括在内。嘉平三年(313)陈元达在谏言中说:“陛下承荒乱之余,所有之地,不过太宗之二郡。”胡注云:“时聪所有之地,汉河东、西河二郡耳。”①(55)①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92页。可见时任廷尉的陈元达并未将石勒领地算在刘聪“所有之地”的范围内。嘉平四年之制规范了汉国的行政体系,同时也清晰了汉国主体与附从势力之间的界限。汉国对石勒的拒斥,成为几年后二赵(前赵与后赵)对峙的滥觞。②(56)②李磊:《石勒的政治名号与政权建构——兼论十六国法统之汉晋复归》,《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第246-253页。
三、建元、麟嘉年间(315—318)的内朝佞幸及其与外朝的结构性对抗
《晋书·刘聪载记》言“佞人方辔”“阉竖类于回天”,主要发生在嘉平四年主、相二元体制建立后。
时聪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宴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率以其意爱憎而决之,故或有勋旧功臣而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而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踰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③(57)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1、2669-2670页。
佞幸指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中护军靳准,即由宦官与掌宿卫禁兵的中护军构成。嘉平四年十一月后,“军国之事一决于(刘)粲”,刘聪“唯发中旨杀生除授”。刘聪深居后宫,依靠中常侍、中宫仆射、中黄门等内朝宦官与外朝大臣发生联系,这成为佞幸弄权的制度基础。
佞幸弄权主要在“叙录”方面,即刘聪保留的发中旨除授之权。王沈的子弟、中表布衣有三十余人成为内史、令长。内史为司隶下属,每一内史管理屠各万户。内史总数四十三名,其中不少为王沈宗族。但这未必是王沈弄权,而是刘聪借助于王沈等佞幸家属,掌握屠各的基层控制权。所谓“奸佞小人数日而便至二千石者”,也是刘聪有意提拔新人到“二千石”这个层级上。“二千石”指九卿、太守等,为汉国诸卿、各郡主官。“二千石”这样高层级的官吏除授,佞幸很难在蒙蔽刘聪的情况下擅自委任。佞幸在“叙录”问题上的弄权,其实是刘聪重新委任了二千石、内史、令长。委任的“小人”,即资历不足者。这一人事上的新政恰恰是为了改变“勋旧功臣”垄断各级官位的情况。刘聪的皇权与刘粲的相权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由刘聪控制人事、刘粲负责行政。佞幸则是刘聪皇权的执行者。
《晋书·刘聪载记附刘粲传》评价刘粲“自为宰相,威福任情,疏远忠贤,昵近奸佞”④(58)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1、2669-2670页。。刘粲昵近的奸佞与刘聪宠信的奸佞皆是王沈等人。陈元达、王延在上表中抨击王沈等“内谄陛下,外佞相国”⑤(59)⑤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1、2669-2670页。。王沈等人对刘粲的“佞”主要表现在构陷皇太弟刘乂一事上。刘聪即位之初,虽顾及屠各与氐人的联盟,不得不以刘乂为皇太弟,但从皇权延续的角度考虑,刘聪是希望由自己的儿子来继位的。《三十国春秋·前赵录》载呼延后以“父终子绍”的理由劝刘聪废皇太弟,“聪亦信之”,并承诺“吾当为计”。⑥(60)⑥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页。在夺取储君之位的问题上,刘聪、刘粲的目标相同。关于佞幸参与刘乂案的缘由,《晋书·刘聪载记》云“郭猗有憾于刘乂”,“靳准从妹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惭恚”。⑦(61)⑦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1、2669-2670页。私人恩怨固然会影响佞幸的好恶,但政治利益才是根本。王沈等构陷刘乂,既是帮助相国刘粲夺位,也是帮助皇帝刘聪实现其不便彰显的政治愿望。归根结底,王沈等佞幸是将刘粲视作皇权继承人,所佞的仍然是皇权。
陈勇先生考察了刘乂案的内情、过程与影响。从时间来看,该案发端于建元元年(315)三月东宫舍人荀裕的告密,激化于麟嘉二年(317)三四月间,历时两年之久。先是郭猗、靳准说服刘粲并为之谋划争夺储君之位,再由靳准、王沈说服刘聪并领兵诛杀东宫官属及亲附刘乂的大臣。陈勇先生认为刘乂案的曲折反复缘于刘聪对刘乂的“爱信”,以及在卢志等东宫师傅被杀后大将军刘敷(刘聪子)的居中沟通。①(62)①陈勇:《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16页。建元二年十一月,晋愍帝君臣被俘至平阳,刘聪大赦并改元麟嘉。晋愍帝朝廷的覆灭,是汉国在俘获晋怀帝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与氐人的联盟在汉国政局中的重要性也便相对下降了,这为刘聪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刘乂案后,刘粲被立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②(63)②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汉国的相权成为皇权的依附。
正因建元、麟嘉年间(315—318)刘聪的政治运作依靠“奸佞小人”,其联姻对象也便转为了佞幸集团。建元元年三月,“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皆国色也”。数月后,“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为右皇后”③(64)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靳准在佞幸集团乃至汉国政坛中地位的上升,主要取决于这次联姻。麟嘉元年(316)刘聪立张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④(65)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麟嘉三年,刘聪立王沈养女为左皇后,立宣怀养女为中皇后。⑤(66)⑤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佞幸在建元、麟嘉年间(315—318)大多成为外戚。刘聪以这种方式使佞幸与皇权捆绑在一起。
建元元年(315)上、左、右三后并立史无前例,亦无礼制依据。左司隶陈元达以“非礼”为理由“极谏”。在遭到刘聪拒绝后,陈元达转而揭发上皇后靳氏的淫秽之行。“靳有殊宠,聪迫于元达之势,故废之。”⑥(67)⑥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所谓“元达之势”是指支持陈元达的势力,包括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在刘聪“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贤,内实夺其权”之时,范隆等人“皆抗表逊位,以让元达”。刘聪不得不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使之名正言顺地“举劾案章”。呼延晏、范隆为外戚,尤其是范隆是嘉平二年(312)的联姻者。此外,嘉平三年陈元达也曾为后宫之事惹怒刘聪,为之辩护者为任顗、朱纪、范隆、河间王刘易。⑦(68)⑦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八《晋纪十》,第2792-2793页。其中任顗、朱纪、范隆在嘉平二年与刘聪联姻,且为刘渊的顾命大臣。陈元达反对三后并立,具有维护刘渊顾命大臣政治利益的意味,故而得到他们的支持。
刘聪所立的左皇后刘氏为刘殷女孙⑧(69)⑧陈勇:《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 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在刘英、刘娥相继去世的情况下,她是嘉平二年入宫者的代表。但刘氏不仅早死于建元年间(315—316),而且被污名化。《三十国春秋·前赵录》载:
建元中,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肉傍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见陨肉之旁。刘氏卒,……乃失此肉,哭声亦止。⑨(70)⑨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百四十二《皇亲部八》,第694页。
《太平御览》卷一四二《皇亲部八》将这一记载系于“刘聪小刘后”条下。刘娥死于嘉平四年,卒于建元中的刘皇后当是原为贵妃的刘殷女孙。《晋书·五行志中》在采用《三十国春秋》记载的同时,还记述:“是时,刘聪纳刘殷三女,并为其后。天戒若曰,聪既自称刘姓,三后又俱刘氏,逆骨肉之纲,乱人伦之则。陨肉诸妖,其眚亦大。”⑩(71)⑩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按《晋书·刘聪载记》,刘聪纳刘殷女及女孙时,“子弟辈”以同姓不婚为理由予以反对。但随后刘延年(刘渊兄)、刘景等屠各宗老对二刘的祖源差异进行阐释,同姓不婚已经不再成为刘殷女孙入宫的礼制障碍。(72)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5、2667-2668、2676-2677、2676-2677、2668页、卷二十八《五行志中》第866-867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刘皇后所产子嗣被当作“害人而走”的蛇、虎,又与流星陨石联系起来,被视作“陨肉诸妖”,是“逆骨肉之纲,乱人伦之则”的报应。结合建元中三后并立、陈元达劝谏、靳皇后之死等事件来推测,这一谣言当出自靳准一系的佞幸之手。
刘皇后之死标志着嘉平二年联姻者在后宫的失势,也标志着刘渊顾命大臣退出汉国的政治舞台。在力撑陈元达反对三后并立之举后,他们虽仍居高位,但在建元、麟嘉之间(315—318)的政局中再未发出政治声音。可以说,随着嘉平四年体制的建立,刘聪的皇权运行依赖佞幸。在刘聪死后靳准举兵夺权之际,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纪、太尉范隆既无力也无意参与平阳政局,他们投奔刘曜并“上尊号”,成为前赵的开国功臣。
佞幸的政治对手还包括外朝的尚书、九卿。刘聪信用佞幸,中断了与外朝的制度性联系。麟嘉三年(318)四月,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上表反对刘聪纳王沈养女为左皇后:
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弟女,刑余小丑犹不可尘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①(73)①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6-2677、2677、2677、267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页。
王鉴等人的批评针对麟嘉元年(316)以来的情况,认为“刑余小丑”和“家婢”没有资格与“公子公孙”同列于六宫,更没有资格居于皇后之位。表面看来这场抗议是站在嘉平二年联姻者的立场上,是建元元年陈元达极谏“非礼”的延续,但正如王沈所骂“乃公何与汝事”②(74)②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6-2677、2677、2677、267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页。,王沈与刘聪的联姻既与尚书、中书等机构无关,也与王鉴等个人无关。这场抗议其实是尚书、中书官僚的借题发挥,目的在于削弱佞幸的权势,结果却被刘聪冠以“慢侮国家”“无复君臣上下之礼”的罪名而遭杀害。③(75)③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6-2677、2677、2677、267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页。
在诛杀尚书、中书长官之前,刘聪曾一次性诛杀七卿。麟嘉元年二月,“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皆群阉所忌也”④(76)④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6-2677、2677、2677、267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页。。被杀的七卿中,少府、大司农属于九卿体系,尚书属于尚书机构,均是汉国政治运行中某一系统的负责人。《资治通鉴》记载少府陈休、左卫卜崇“为人清直,素恶沈等,虽在公座,未尝与语”,还曾自述心迹:“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阉竖乎!”⑤(77)⑤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八十九《晋纪十一》,第2828页。刘聪诛杀七卿当然不完全出于对佞幸的偏袒,而是以暴力的方式清除权力行使方式中的障碍。七卿对佞幸的抵制,影响的是刘聪的皇权行使。由于左卫领宿卫禁兵,卜崇的不满在刘聪看来会带来宫禁安全上的问题。刘聪诛杀七卿并未解决内朝与外朝在权力结构中的矛盾,尚书、中书、九卿的不配合仍在延续,这才有了麟嘉三年(318)诛杀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的事件。
刘聪死于麟嘉三年七月。刘粲即位一个月后,靳准发动政变。⑥(78)⑥李磊:《屠各汉国多族群政治体的瓦解及其原因探析——十六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首次尝试及其结果》,《东岳论丛》2021年第5期,第134-142页。刘粲被杀,“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发掘元海、聪墓,焚烧其宗庙”⑦(79)⑦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第2676-2677、2677、2677、2671页、卷一百二《刘聪载记附刘粲传》第2678-2679页。。这未尝不是佞幸势力尾大不掉,而外朝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力量,皇权遭反噬的缘故。
四、结论
光兴二年(311)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后,刘聪的施政重心转移到汉国权力结构的调整上来。先后构建了嘉平二年(312)、嘉平四年(314)两种政治模式。嘉平二年的模式是,通过与刘渊顾命大臣的广泛联姻,使后宫成为与前朝声息相通的第二个政治场域。后宫嫔妃的秩位差序与前朝的权力格局相对应,“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左贵嫔为宰相刘殷之女刘英。这一体制终结于嘉平四年正月皇后刘娥之死。
嘉平四年的政治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五部屠各、六夷、汉人分别纳入州郡、“司隶—内史”“单于左右辅—都尉”等不同系统予以管理。二是创造新的主、相二元体制,“军国之事”归于相国,“杀生除授”归于皇帝。三是依赖内朝佞幸行使皇权,并使佞幸成为新的外戚。内朝佞幸与嘉平二年联姻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外朝尚书、中书、九卿间的斗争,成为建元、麟嘉年间(315—318)的政治主轴。刘聪在皇权行使过程中对内朝佞幸的袒护与对外朝机构的压制,使内朝势力独大。刘聪死后,靳准之变的发生实是内朝佞幸势力对皇权的反噬。嘉平二年、嘉平四年两种政治模式的出现,均是刘聪巩固皇权的结果。后者对前者的接替,其实是重构权力,将权力从刘渊的顾命大臣集中至刘聪本人。公允地说,嘉平四年的政治模式并不必然导致汉国的政治崩坏,但刘聪的权力重构在削弱“勋旧功臣”势力的同时,并未寻找到新的社会支持力量,而且在政治运行中过度申张皇权,破坏了内、外朝间的权力平衡,这是汉国覆灭的根本原因。刘聪的政治改革使汉国衰败于内耗,也使汉国难以成为取代西晋的政治力量,北中国不可避免地继续处于分裂与战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