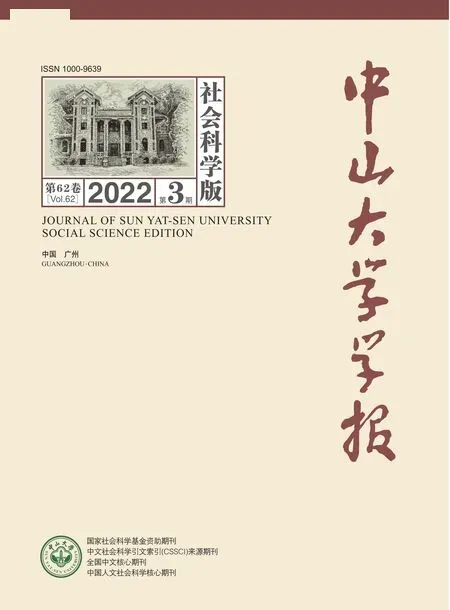以整全性视野探究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
谭安奎
在当前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是最响亮的政治表达和促进政治凝聚的强心剂。在学理上,我们不能只是重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史,也不能停留于对“强起来”的未来愿景作进一步畅想。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或许应该是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提出的两个相当简约但却极有分量的判断之中: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二,这个百年历程中探索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理解这两个论断的政治学意涵,不仅关乎政治学研究的知识构造,而且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
一
《决议》的上述两个判断一个指向社会过程,一个指向社会状态;一个强调历史路径上的中国特色,一个昭示文明形态上的普遍意义。我们知道,“现代化”是一个着眼于过程、路径并强调动态性的概念,相对而言,“现代性”则是对现代社会总体状况和特征的质性刻画。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判断其实表明,我们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一种新的、对人类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政治现代性。鉴于民族复兴的事业仍在推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上述文明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现代性仍然“在路上”,它还是一种有待最终完成的事物。我们如何对这种发展中的政治现代性进行学理上的构造和反思,确实是政治学理论上的一项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工作。当然,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代性构想(虽然它已经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项研究工作就必须在与西方政治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对话中才能展开。
西方政治现代性的显著成就,同时也是诸多社会病灶的根源,大概在于其标签式的个人主义。在智识资源上,除了基于个体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观念的政治哲学奠基,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为之提供了简明、深刻却又日益显现其偏狭性的治理思路。
这种现代性,首先在西方内部制造了智识上的古今对立,以及社会道德和政治实践上的冲突与撕裂。在西方,从基于人性目的论的自然正当秩序向基于个体意志的自然权利的转变,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哲学前提。自然权利因其建立在个人意志的基础上,因此是主体性的或主观的权利。同时,既然个体的意志是第一位的,尊重个体意志和自然权利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在个体同意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其内部固然有诸多重要的差别)的基本逻辑。西方宪政民主政治的政治正当性想象,正是从这个基本起点出发的。相对于西方古典传统对自然正当秩序以及相应的共同体价值的强调,基于主体性权利的现代社会,基本的假定前提是人类从宇宙整体秩序、个体从种种共同体及其传统中的“大脱嵌”。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内在价值,以及它们对于权力约束、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价值,无疑已经被西方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成就给予了充分证明,它也是其它替代性的现代性想象无法予以彻底否定的重要维度。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与上述政治正当性理念相关联或相匹配,成形于18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为西方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基本框架。其中包括逐步被视为万世不易之准绳的效用最大化与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而是以商品、市场逻辑对社会关系、政治过程的全面重塑。政治学界通常认为,西方的这种治理模式,在法治与民主问责方面体现了优越性,但在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方面却暴露了严重短板。事实上,问题可能较此要更加深刻得多。市场化逻辑的不断扩展,不但让社会公平的价值一再成为显性问题却又总是难以克服,而且,它使得社会关系趋于崩溃、共同体本身趋于瓦解——而共同体的统一认同,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支持力量。共同体的良善生活或共同福祉,在实质上难以见容于这种政治模式。如果说西方现代政治建立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上,我们由此可见商业社会本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体现了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政府观念、政策主张,包括它对人性、人的行为动机的基本假定,对于我们建立良好的现代秩序的不足。
二
当然,在西方社会内部也有自我反思、自我疗救的重要尝试。例如强有力的福利国家实践与社群(共同体)主义想象,以及从道义(德)经济学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传统的批判。道义经济学对市场逻辑的无限扩展深以为忧,认为它意味着让经济从社会中“脱嵌”,进而让市场反噬了社会。但这些反思似乎没能提出替代性方案。福利国家或其它人为推进社会公平的实践,又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制造了价值上的张力。这些张力的存在和不断强化,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社会的“极化”——相对而言,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乃是显性的、物化的和可以量化的,而观念上的极化,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的渐行渐远以致互不相容,才是政治共同体存续的根本危机。毕竟,任何一种政治,终究要解决的是“我们”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问题。
此时,我们难免要回想起,西方现代政治本来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人民”之维。既然西方的现代性以个体化与平等化为开端,人格化的君主国难以为继,在权力尤其是主权的归属问题上,“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君主的替代者而出场的。人民主权,因此也是西方的政治现代性一开始就倡导的重要理念。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整体性的甚至是抽象的,因而也应该是具有历时稳定性的,但现实中可见的人民只能是具体的、流变的杂多之众(the multitude)。由于西方现代政治中强大的个人主义前提,整体性的“人民”往往合乎情理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它常常被还原为个体化的人,这就导致了“人民”实质上被虚化。与此同时,在政治现实中,人民的无定形特征则使之充满含混性,因此又总是被各取所需地加以滥用,民粹主义尤其擅长此道。结果,西方现代政治中的人民理念,在伦理、制度上难免陷入不得落实的边缘化境地。
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及其治国理政的探索,从一开始就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一理念,可谓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灵魂。所谓“初心”,就是对这一理念的隐喻式表达。作为唯一执政党的政治自觉,使得强化和落实这一意识形态理念具有常态化的紧迫感。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相对而言便具有鲜明的共同体和整体性取向。相应地,国家能力与治理绩效成了我们显著的比较优势。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彰显了这一理念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巨大潜力,而共同富裕政治目标的提出与实现,也有赖于这一理念的道德能量及其制度化的前景。与此同时,个体的维度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展开和丰富起来: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的洗礼,我们在理论上日益确信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意味着我们对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承诺,它们业已进入我们日趋丰富和完善的人权话语和法制体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雄心与现实探索,有望为个体的政治参与提供多层次的机会和渠道。
正因为人民理念不仅关乎个人的主体性权利和自由,而且关系到政治参与、国家能力、社会公平、共同体建设与维系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抱持且愈发自觉地突出系统性思维。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开始“点题”,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专门以此作为《决议》的核心主题,被认为是正式“破题”。所谓“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的正是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思维,它是“弹钢琴”隐喻的具体化,也是一种升华。
三
如果说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正在实践中逐步显现和展开,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则尚未走出懵懂状态。但上述中西对比,也意在提供一点方向性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极为艰难的,便是基于整全性的视野,探究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治理之学。所谓整全性视野,一方面体现为要素结构的全面性,另一方面体现为人性观念的健全性。前者意味着,国家治理之学要同时观照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参与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让它们成为政治共同体建设的构成性内容,而且能够相互协调。而在习焉已久的理论光谱中,对这些要素的处理往往对人性持有不同的假定,或者说对人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市场机制往往基于理性人对于私人利益和私人事务的关注,这与政治参与的要素就不尽相同,而社会公平乃至共同富裕则要诉诸更厚重的伦理观念。与此相应,整全性视野的第二个方面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之学要以对人性的一种整体性理解作为前提,它要求我们在人性论上实现一种新的综合,首先是要探究一种统一的实践理性观念,以避免人性内部的相互交战。正如有哲学家所说,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在根本的方面最终仍然是柏拉图式的,即政治秩序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人性内部的和谐之上。
整全性被认为是古典政治(哲)学本来的、却被后世淡忘了的特性。这样的政治哲学着眼于人的复杂性,探究关乎共同体整体福祉的整全性知识。它会强调治国才能(statecraft)的重要性,而不是依随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偏狭假定,让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完全接受理性行动者自发行动的后果,从而使政治哲学让位于经济学,以及受经济学范式所支配的政治科学。事实上,直到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也只是立法者科学的一部分。当熊彼特批评斯密,说他把经济学只是当作政治家的“处方本”的时候,这种批评或许反倒表明了斯密对经济学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审慎认知。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今天强调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不是要完全回到古典模式。那种模式试图基于人性内部的纵向秩序为等级化的外部政治秩序提供论证,而任何一种可接受的现代国家治理之学,都必须吸收平等、个体性等根本性的现代元素,同时又要克服现代学术中的知识分割与人性分裂。因此,整全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之学,既不是对古典政治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西方既有现代性的全盘接纳,而是呼应着一种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面对通常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究这样的国家治理之学,就不能是一项封闭的为国立说的事业,而是一项开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论创新工作。事实上,一旦具备了这种整全性视野,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
当然,如前所述,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仍然在展开之中,本文所说的基于整全性视野的政治学,也不可能源于对现有国家治理实践的直接总结。政治现代性的新形态要得以完善,还有待我们克服一些重要的内在挑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与西方多中心的治理理念不同,强大的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塑造了独特的动力机制,因此也需要处理一些悖论性的后果。例如,这种动力机制当然会突出集体、美德,但它同时也是个体化、市场化的推动力量。由于“社会”的薄弱或缺位,国家力量推进的市场化、个体化反而导致了过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而这又对政治参与和共同体意识具有消解作用,并危及社会公平的伦理基础。因此,整全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如何对“社会”进行“建设”,从而生成真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便是挑战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