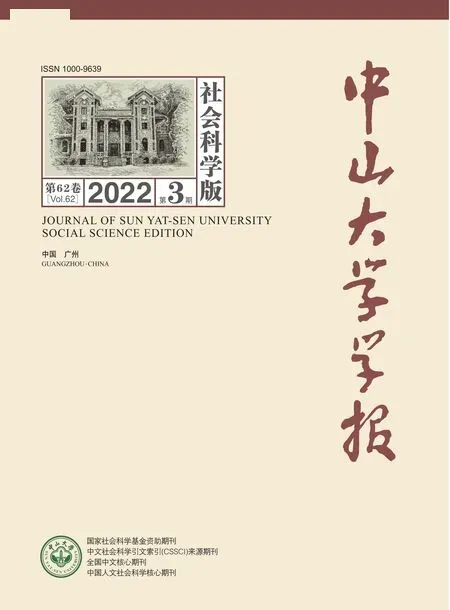从“杀身成仁”说重探孔子“许人以仁”的智慧*
龙涌霖
经典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留下了一些长久令人着迷和玩味的谜题。有时候,问题的推进不一定来自后世思想方法的更新,一条文本线索的钩沉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经典中的立体世界,从而获得实质性理解。本文即希望借助这样一种切入方式,来重新探讨《论语》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孔子许人以仁(以下简称“许仁”)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孔子几乎从未许过弟子以仁,可他又将此殊荣给了他讥讽过的管仲。如果这不是思想上的矛盾①津田左右吉认为这是孔子言论相矛盾的情形之一。其背后学理在于判定《论语》文本是由不同思想倾向的后世儒家学派编纂而成,不全是原初孔子思想。这似乎也是解决许仁问题的一种方案。然而这种原典批评主义往往从一些存在争议而不自知的思想史预设出发,其多大程度能呈现原义,则很成问题,故本文不取。见[日]津田左右吉撰,曹景惠译:《论语与孔子思想》,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223页。,那么孔子究竟是怎么考量的?对此,宋儒认为管仲只有仁的外在事功而无内在仁德,故孔子并未真许其为仁,晚近学者则会强调仁本身具有事功性来解决这一公案②参冯浩菲:《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文史哲》2006年第2期。。事功性的解释固然有其理据,然而像伯夷、叔齐、微子、比干等被孔子许为仁的古人以及死得早却得到孔子近乎仁的评价的颜回,都能从事功上解释吗?显然未必。人们不禁追问,孔子是否有一贯的原则?当然,预设孔子有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来支撑其评仁活动,极可能破坏经典世界的多元层次。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把背后的道理讲出来、讲明白。同时,能否合理解释孔门的许仁活动,也真正考验着我们对孔子“仁”观念的理解③以研究“仁”的名家为例,徐复观从“仁者人也”出发,解释“仁”为人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人的自觉和向上之心;芬格莱特根据“仁者不忧”和“克己复礼为仁”的内在关联,指出“仁”是依礼而立身行事的客观的和谐状态。这都很有见地,问题是其解释能否验证到孔子许管仲、箕子、微子等人为仁的评价上?他们均未直面此问题,则说明其解释仍大有商榷余地。见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第404 页;[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48页。。职此,下文将重新检讨历来被用以表明气节的《论语》“杀身成仁”说,揭示其所包含的少为人知的许仁逻辑,进而以此为线索,结合孔子仁学其他方面,力求展示孔子许仁的各种考量及其背后更为丰富的古典智慧。
一、“杀身成仁”说的许仁逻辑
首先来重审管仲被许仁的公案。《论语·宪问》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①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90页。
这两则问答的结构基本一致,孔子与学生的争论焦点都在管仲能否称得上仁。由于孔子曾讥管仲“器小”“不知礼”(《论语·八佾》,下引该书仅注篇名),历来学者多聚讼于他是否真许管仲以仁的问题上。然而一直以来,问题的更基础的层面被忽视了:子路和子贡为何会这样提问?照常理,管仲不死公子纠,至多落个不忠不义的罪名,何必上升到“非仁”?值得揣摩的是,孔子对弟子们提的问题本身并未感到一丝怪异。这可说明,师徒间存在着某种默会的共识,而孔子应曾事先许过管仲以仁,与上述共识有所冲突,否则就不会出现师徒之间的这场争论了。按这一共识即“杀身成仁”说。依此,假使管仲能像召忽一样死节,那也称得上仁。这并非本文首先提出的解读,郑玄就明确指出,管仲、召忽皆得为仁,只不过有大小之别:“九合诸侯,功齐天下,此仁为大,死节,仁小者也。”②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7页。据此,孔子说“如其仁”其实是认为管仲如同召忽,均为仁。但既然孔子认为召忽是杀身成仁,那么要追问,召忽杀身的行为哪一点符合仁?考虑到仁者爱人之义,或许你会认为召忽杀身是表其仁心于公子纠。但对主子的忠爱是仁么?恐怕孔子不会同意。召忽选择杀身,与其说是出于爱君,不如说是在为君难死节,尽份臣子之义罢了。问题就似乎无解。
在另一则案例中,也存在类似疑惑。孔子曾称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述而》),其实也是基于“杀身成仁”的语境,就其饿死首阳山的行为而言的,即邢疏云:“君子杀身以成仁,夷、齐虽终于饿死,得成于仁,岂有怨乎!”③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90页。问题还是在于,夷、齐杀身的行为中又有哪一点符合仁?或以为在于二人让国所体现的兄弟之爱。其实不是。据《史记·伯夷列传》看,作为孤竹君二子,伯夷继位的合法性来自其嫡长子身份,叔齐继位则出于君父之命,那么二人让国是要避开两种合法性冲突导致的不义,而非出于手足之爱;而且,二人饿死首阳山,是出于反对武王出兵无效而“义不食周粟”,怎能与让国的事件相混淆?可见,伯夷、叔齐整个故事没有一点与爱人之仁直接相关,若揪住“仁—爱”的关联不放,二人以及召忽何以称仁的问题都要陷入无解。
不妨暂搁问题,先来反思、归纳并厘清以上牵涉到的“杀身成仁”说的自身逻辑。首先可见,它并非如后世那般,只是用以表明气节;毋宁说,其功能是评价性的,即许仁。并且,它并不要求必须在某种直接关涉爱人的情境中作评价④例如为救溺水者、为保护弱者免以屠戮而牺牲生命,即情景式理解。但《论语》并无记载此类情景。,杀身者的行为只需符合宽泛的德义即可。这不很奇怪么?何以说是仁呢?这恰恰是孔子思想的复杂性所在,需要我们耐心去逐步揭开。为此,首先应看到,大凡某一道德主张,大致能区分出理论内涵与行动方式两个层面。仁的最基本的理论内涵固然是爱人,但怎样践行仁?仁者应如何行动?则属于行动方式的层面。“杀身成仁”说的独特就在于,它主要着眼于行动方式的层面许仁。也就是说,作为许仁的一条依据,它只规定当你为了坚持善道而杀身,这一行为足以令你称仁;却没有特别限定这里的善道只限于爱人之仁,而是内涵十分宽泛的义。以下宰我与孔子的一则对话,可进一步印证这条依据的上述独特性。《雍也》载: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①邢昺:《论语注疏》,第81页。
解读此则对话的关键在“井有仁”。过去注家多读为“井有人”②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15页。。若此,宰我是在问:仁者是否会舍己救人?可是这样的问题并无大错,孔子为何显得不悦?再者,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话?历来的解释,总不免迂曲之嫌。实际上,“杀身成仁”说正是理解此章的一把钥匙③俞樾已经用“杀身成仁”说解读此章了,但未引起重视,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说。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3页。。这里不宜将“井有仁”之“仁”读作“人”。宰我其实要说的是:假设井底有个“仁”(且不管它具体是什么东西),若跳井而死便可得“仁”,仁者会跳吗?我们知道,宰我既是孔门言语科的高材生,也是最惹争议的弟子,比如他曾质疑“三年之丧”的合理性,就弄得夫子大为光火(《阳货》)。而这里,宰我是在巧用言语构造一个两难悖论,所要挑战的正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说:跳井而死便满足“杀身成仁”,却白白死去,无疑也是愚蠢的,仁者会做吗?这种提问当然又会挨老师的训了。而孔子训宰我的话,同样需顺着“杀身成仁”说来理解,即君子确实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死(“可逝”),但不可使他困惑于如此两难(“不可陷”);甚至你可以骗他去义无反顾地死(“可欺”),也不要使他夹在两难中迷失自己(“不可罔”)。孔子所强调的是仁者的坚定不疑的行动姿态,而宰我正是顺此方向,抓住了“杀身成仁”说从行动方式上去许仁的逻辑,企图从更纯粹的行动形式的层面向孔子发起挑战,以至于剔除了“杀身成仁”所要坚守的善道价值——在跳井得“仁”的思想实验里,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道德内涵,更别说什么爱人之义了。正是这一悖谬,把孔子惹火了。
召忽、夷、齐以及“井有仁”的案例都能明显揭示孔门“杀身成仁”说的独特之处:当你为了正确的义举而牺牲,就能被许为仁,它并不限于爱人之举。这里的关键在于杀身者见义而勇为的行动本身,它才是孔子许仁的真正核心,否则,宰我就不会发起“井有仁”的挑战了。问题是“杀身”与“仁”究竟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④朱熹也注意到此问题,他认定杀身者的行为必然合“理”,合“理”则“心安”,“心安”则“德全”,全德者即仁,以此试图弥合“杀身”与“仁”的鸿沟。这一解释理学色彩过多,不宜直接作定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页。?“爱人”固然是“仁”的最基本之义,但如果只抓住这个单薄的义涵,那么无论如何,问题只会陷在死胡同里。孔子仁学蕴涵极为丰厚,但这并不排斥如下可能性:其中存在着一个核心面向,它决定了孔子立足于行动方式上许仁的独特逻辑。这个核心面向是什么呢?
二、仁者的天下责任感及“死而后已”
现在来看“杀身成仁”说的原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请留意“志士仁人”这个表述。结合孔孟常言的“志于仁”(《里仁》《孟子·离娄上》)来看,“志士”实即“志于仁”的人;“志士仁人”不是指“志士”“仁人”两类人,而只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的更准确表述。则“志”关乎对“仁”的理解。一般来说,心志的对象只能是在遥远的未来、需付诸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事物,故志士仁人追求的仁也应是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事情;它不是现成的,不是说你有爱心就是仁。那么,仁在何种意义上是遥远的呢?管仲的事例已表明,仁关乎整个华夏秩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且应当是普惠于天下民众的(“民到于今受其赐”)。故“志于仁”其实也即“志于道”(《里仁》《述而》),因为孔子理想之道所通向的,乃是“天下有道”(《季氏》《微子》)的秩序。仁最终指向天下的福祉。这可证诸以下对话,《阳货》载: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
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①邢昺:《论语注疏》,第235,83,103页。
按恭、宽、信、敏、惠五德明显是从《尧曰》宽、信、敏、公四德扩充而来的,而后者是三代圣王赖以治天下的主德。尤其从“得众”“使人”“人任”等政治效应来看,施行此五德者,显然有造福民众的实际事功。那么由此五德所表述的“仁”,就显示出了其与三代王道理想的连续性,从而面向天下人的福祉。这里更关键的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表述,它更凸显仁的天下面向。换言之,只能行此五德于家、于乡、于国都不算仁,必须能行之于天下方可为仁。那么,此章透露出的仁的天下面向,就与孔子许管仲“一匡天下”之仁的精神相通。就是说,能否利及天下,至少是孔子许仁的一个要素。
然而我们也知道,倘若真能“行五者于天下”而造益黎民,就不仅是仁人,更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了。《雍也》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②邢昺:《论语注疏》,第235,83,103页。
此章向来被认为是孔子论仁的核心文本,其理解的关键在于辨明“圣”“仁”关系。从语意不难看出,“仁”不一定是“圣”,但做到“圣”则必定是“仁”,否则孔子就不会许管仲以仁了,因为一匡天下、惠及后世的管仲确实有博施济众的事功。换言之,“仁”的外延要大于且包含“圣”。因为仁者立人、达人,推得最远就是立天下之人、达天下之人,即同于“圣”,但显然,并非要做到如此才是“仁”。这里要看到“仁”“圣”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仁”是在我的、可掌控的,而“圣”是外在的、不可必得的。进而,“仁”是主体由近及远的不断立人、达人的动态过程,而“圣”则是客观的高高在上的静态目标。能成圣者凤毛麟角,要看是否幸运;成仁的道路却开放给所有人,它取决于你主观的行动和努力。不过,虽说不必真做到博施济众,但仁者的心志必然指向天下。因为若没有“圣”的目标悬着,求“仁”者就不会被牵引着不息进取,一步步去修齐治平。正因“圣”“仁”不可割裂,孔子才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把两者捆在一起作为终生不倦追求的目标。只不过,两者虽然都指向博施济众,但相比于“圣”,“仁”是更内在的东西。它是一种存乎志士胸中的天下责任感,简而言之,即仁志。
若依上述,只要你心怀天下责任感,就是仁者了。如孔子所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关乎立志,故曰不远③芬格莱特也认为此处“仁”关乎立志,亦即熟习礼的君子决定遵从礼的那一刻的“决定”。笔者的不同在于,立志的内容不仅是遵从礼,更在于推广礼,并付出终身行动,由此仁又是至难的。见[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第51页。。可问题是,孔子为何仍极少许人以仁?尤其我们会注意到,他从未许过包括当时弟子在内的任何在世者以仁。其实,从理论上讲孔子并不否认在世的人当中就有仁者,比如他曾叮嘱子贡要“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但具体到对现实中某个人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要怎么证明某个人有志于仁?如前论,志的对象是遥远的未来事物,其实现有赖于长期的努力和行动。人们往往相信,要判断一个人能否持志,不是凭他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即“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更何况对于“圣”“仁”这样至大至难的志向来说,所要求行动绝非泛泛用功。《泰伯》载: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④邢昺:《论语注疏》,第235,83,103页。
此言深契孔子之旨。曾子视仁为“己任”,即本文所谓天下责任感。只有以博施济众为导向,仁才会有任重道远之感,才显得是“任”。这样的仁就必然要求志士在行动上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弘毅”),尤其能投入整个生命于仁的事业中,即“死而后已”。因此可以推论,既然就行仁而言,仁者须“死而后已”,那么就许仁而言,也必须是盖棺后才能下定论。仁的评定就像谥号一样庄重肃穆。因此,尽管仁志是在自己心中的,你固然可说欲仁则得仁,但志关乎行动,不在巧言,要向世人证明你心中有仁,虽不必真达到博施济众,但至少必须朝着这个方向用尽一生力气去追求。仁道必然是至难的。仁志的实现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它要求你行动到死前最后一刻,才能表明你对仁的沉重的承诺。
至此,“仁”与“杀身”的关系问题,似乎有些眉目了。然细思之,仍未一目了然。“死而后已”与“杀身成仁”这两种死亡方式其实未必相同。前者大多是自然死亡的情况,后者则出于主动的抉择,两者与仁的关联会是一样的吗?再者,“死而后已”的仁者是朝着博施济众的方向前进的,这很好理解;而“杀身成仁”的仁者往往只出于殉义,如何与博施济众有关呢?要深究于此,需进一步考察仁者的行动方式。
三、“中行”及其两种许仁情况
虽说仁道的至大至难决定了君子须“死而后已”,但绝不意味着君子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儒家要求君子之行必须受礼的规范。这不单是出于个体修养,而有来自更高的仁道理想的内在要求。前面已指出,仁者博施济众是一个不断立人、达人的过程。所谓立人、达人,不仅是满足民众生存需求,更是要用礼乐教化实现人格的充分发展,即“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博施济众的仁道理想是有具体蓝图的,即周代礼乐秩序,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但这似乎并不必然意味着君子本身必须守礼。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即君子努力推行周礼以化天下,自己却没有也没必要遵守周礼。这种做法,必会遭到孔子批判,所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如果用一种区分公共善与私人善的现代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很容易觉得一个人即便品行不正,并不妨碍他可以成为博施济众的伟大政治家。但问题在于,儒家的博施济众依赖于古典礼乐教化,其政教体系的全部基点在于施教者自身必须发挥道德榜样的力量,如果施教者不先以礼正己,何以取信于民?作为礼乐教化的奔走呼吁者,儒家又何以取信于当权者?也就是说,君子通过修身正己取得世人信服,是仁道教化得以推行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己而后正人乃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如“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礼记·大学》)、“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等。是故正己以正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是孔子心目中君子的最佳行动方式,即“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此处“中行”语焉不详,但可以借狂狷来把握。《孟子·尽心下》谓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据此,狂者志在复兴古礼,而自己却不能遵行古礼,亦即欲正人而不能先正己者;相反,“有所不为”的狷者即只正己而不愿正人者。据此,中行者无狂狷之偏颇,就是能正己而后正人的最佳行动典范。
依“中行”的行动要求,君子在踏入正人之途、实际出仕并努力复兴周礼之前,就必须对于冠、昏、丧、祭、乡、射、燕、聘乃至一整套周代封建礼乐有足够的学习和熟稔,同时对周礼蕴含的忠、信、孝、勇、义、智、敬、让等德目乃至各种行为规范,也必须有长期的熏习和践行,才有资格出师去进一步弘道正人。此即“学而优则仕”(《子张》)。话虽出于子夏之口,但无疑也是孔子所强调的。当子路让尚未学成出师的子羔去当费宰,并辩解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当即加以痛斥(《先进》);当孔子示意漆雕开可以出仕时,后者推辞说“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反而大悦(《公冶长》)。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这类信念应放在仁者正己以正人的“中行”语脉中理解,你才能明白当弟子不遵师诲而仓促出仕时,孔子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
现在,紧扣“中行”这一结构,就可以逐步揭开博施济众与杀身成仁的深层关联了。如前述,仁者志在复兴周礼以博施济众,故需“死而后已”。那么根据“中行”的行动要求,志士仁人自身对周礼及相关德义的恪守,也必然要终身不懈亦即与博施济众同步的。此即孔子“守死善道”的要求:“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由此话还能看出,所谓“杀身成仁”其实只是“守死善道”的仁者在极端情况下的一种生死抉择而已。换言之,“杀身成仁”不能甩开“守死善道”的脉络作独立理解,否则会流为一种轻视生命、沽名钓誉的行为。为何这么说呢?试想,假如有人故意找准一个机会,为了某个正义的理由而牺牲生命,是否就是杀身成仁了呢?若真如此,杀身成仁对于徒好虚名者来说,就是比博施济众更快捷的成仁之道了。这种想法绝非孔子本意。因为他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如果可以通过主动的舍身取义的行为来成就仁名,那么只要前往充斥不义的危邦乱邦出仕,随时都可以成仁。这说明,杀身成仁不是无条件的,或者说,不能抱着揠苗助长的心态去刻意追求。当被不可掌控的命运投入于义命不能两全的极端境遇时,杀身成仁的条件才会成熟。由此才有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的说法。遇到要杀身成仁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在义命可以兼顾的多数情况下,君子应当做的是推行礼义之道,不立岩墙之下,避开危乱之地,直至老死,即“守死善道”,亦即“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我们会看到,先秦儒家对于自己临死前的举止是否符合礼义的问题会格外慎重,比如孔子病重时严斥子路“使门人为臣”的僭礼之举(《子罕》)、曾子临终易箦以求“吾得正而毙焉”(《礼记·檀弓上》)等,正有出于“守死善道”的执念。
因此,如果没有遇到义命不得两全的情况,那么君子正己以正人,死而后已,即便未达到博施济众的事功,也足以被许仁了。因为如前所述,仁是存乎志士胸中的天下责任感,它需要通过终身的行动来证明。这种终身行动,一方面固然在于积极的入世和弘道,另一方面更需要君子对礼的终身恪守,作为教化世人的底气。孔子曾对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不是说你践行一两天的礼,就可称仁了。马融云:“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①邢昺:《论语注疏》,第157页。据此,“一日”是夸张之辞,它最终要强调的是成仁需要对礼的终身恪守。当然对于志士仁人来说,仅仅自己守礼是不够的,因为这很可能会变成狷者之流;而是要在此基础上一步步修齐治平,才能真正达致天下归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礼即行仁。孔子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也应放在此脉络下方可恰当理解。他不是说君子要时刻保持爱心,而是强调要时刻无违于礼。此乃仁者基本功。总之,君子推行周礼,守死善道,死而后已,从而被许仁——这是义命兼得情况下的许仁之道,不难理解。
难点在于志士仁人遇到无法逃避的义命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的抉择。也许你会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妨选择保命,日后仍有望实现博施济众。但孔子会认为这是“求生以害仁”。因为一旦你选择求生而违背礼义,那么一来你不能正己,便没有底气去正人;二来你的违背礼义的行为直接就与你复兴周礼以匡天下的仁志相抵触,这便是降志辱身了。除非你是天生圣人,或者是管仲那种能负重前行的罕世奇才,否则更大的可能,便是你在多次求生害仁的选择中逐步降低了对仁道的极高要求,最终沦为孔孟深恶痛绝的“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的乡愿了。那么与其沦为乡愿,不如杀身明志,用短暂而绚烂的一生向世人表明你胸中的仁志,从而被许为仁者。这里就能看到,杀身者所要坚守的某一个具体的礼数、节义或德目,虽然与爱人没有直接关联,但都属于寄托孔子仁道理想的周礼秩序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或缺;更关键的是杀身取义这一行为本身能够强烈表露出仁者对周礼的死守态度,从而展露出其内心的天下责任感(“仁”)。在这个意义上,杀身取义者便符合孔子心目中“中行”的仁者而被许仁,“杀身”与“成仁”的内在关联即在于此。
然而,问题仍未结束:如果杀身取义者所要成就的仁正是孔子所冀求的,即克复周礼以博施济众,那么伯夷、叔齐、召忽被许仁,是否意味着他们也有与孔子相同的抱负?很难说是。后文还将指出,当时世人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不是仁,而是另有其他。那么孔子许彼为仁,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评价规则,抑或有规则之外的深意?以下就需要全面考察《论语》中的许仁活动了。
四、孔门施教中的许仁智慧
首先应看到,“杀身成仁”当然不是孔子许人以仁的唯一依据,比如管仲虽未能像召忽一样死节,却因其博施济众之事功而被许仁。不过,尽管前文已指出博施济众与杀身成仁在孔子仁学中的内在关联,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许仁问题上,你必须因此而同时做到博施济众和终身行道(乃至舍身守道),才能被孔子许为仁人。因此可见,孔子至少有两条相互独立的许仁依据。可初步总结为:
依据①:从效果上许仁,即能博施济众者为仁。
依据②:从行动上许仁,即能终身推行礼义之道者为仁。
依据②又细分两种情况看:
情况A:在义命兼得的多数情况下,君子正己而后正人,死而后已,则为仁。情况B:在义命不可得兼的极端情况下,君子能舍身守道,则为仁。
由此可看到,子路、子贡执泥于依据②的情况B,遂有关于管仲是否为仁的疑问;现代学者更多关注依据①意义上的博施济众之仁,而鲜有看到行动层面的许仁之道,更对孔子许仁感到费解。现在,若能综合这两个层面来看,又能否对孔子的许仁之谜,给出一种更合理的解读呢?这无疑值得一试。
综观《论语》所有涉及许仁的案例(包括被问及而未许的),会发现里面讨论的对象不外乎两类人:一是门人弟子,有颜回、仲弓、子路、冉求、公西华;二是历史人物,有管仲、召忽、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令尹子文、陈文子。那么,面对这两类不同的对象,孔子在许仁时是如何考虑的?出于何种依据?又有何深意?为探究于此,以下分别作细化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一些看法。
先看门人弟子。
孔子从未真正许过任何一个弟子以仁,但对于颜回有点例外。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肯定他为仁,但有这么说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意谓只有颜回的内心能长期不违仁,其他弟子也就能坚持个十天半月而已。问题是,内心长期不违仁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程朱认为是“无纤毫私欲”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6页。,是用天理—人欲的理学框架作解,不能作为定诂。回到《论语》会看到,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更多是推许他有一种前进不息的精神,如“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语之而不惰”(同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等行为所表现出的巨大行动力。这一点,才触及其许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的核心考量,背后是来自“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引子曰)的观念。为何说刚毅力行者近乎仁呢?前谓仁道至难,仁者应终其一生推行礼义,死而后已,之后才能论定为仁。即依据②。那么可推论,若其人在世时能够力行不息,虽未可直接定为仁,却也接近于仁了。前提是你对于评价对象有足够的熟悉和信任,即相信他能够力行至死而非半途作废,才能给出这样的评价。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师徒间又有亲如父子般的信任,孔子美其前进不已,才说“其心三月不违仁”。这里“心”主要指心志的操持而言。心志关乎行动,颜回的行动具体表现在好学不倦、敏于改过、执礼不违等。而这些,都是仁者欲博施济众所当下苦功的环节。故“其心三月不违仁”,即是“力行近乎仁”。皇侃注解此条时说“仁是行盛”②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1页。,也保留了这一古意。
颜回的案例进一步提示,孔子对于是否许门人弟子为仁,其主要考虑不在于弟子是否有博施济众之功(依据①),而在于其行仁的行动能否坚持到死而后已(依据②)。那么严格来说,孔子不会许弟子以仁,因为他们都是处于未完成时态且充满无限可能的生命,既有可能守死善道乃至博施济众,也有可能中道而废甚至贼仁害义。那么,对于弟子,孔子经常说“不知其仁”,这种“不知”就不是直接的否定,也非故意装作不知,而是真不知道,因为仁的评定是要纵观一生才能下定论的③李巍也指出,《论语》“仁”指向个体认同礼义的心理状态,故他人不可直接获知,但仁者身上有一种长期持守的理性态度,又具有明显的理论特征。见氏著《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5—124页。。而孔子的未许,很多时候还会多出几分期待。当别人问他,仲弓、子路、冉求、公西华是否为仁时,孔子虽然说“不知其仁”,但也表扬了这些弟子的过人之处。(《公冶长》)可以看出,这里的“不知其仁”其实包含了对于弟子们的期待,即期待他们能发挥长处、投身仁道、进取不息、死而后已。总之,在是否许门人弟子为仁的问题上,孔子的考虑点主要在于依据②,这实际上就等于悬而不评。这种悬而不评,更多带有一种期待意味。
接着看历史人物。
直观上看,管仲、召忽、伯夷、叔齐之所以被许仁,可以很快在依据①②中对号入座。麻烦的是另外三位,即《微子》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除了比干是杀身成仁,微子、箕子又当归于何种依据?是否孔子还另有许仁的依据而未被发现?笔者很愿意听到学界后续有高见创发,但同时也会认为,在本文现有结论的基础上,未必不能作出有理据的解释。
问题首先出在我们对于博施济众的理解容易过于狭窄。博施济众必然是通过事功吗?未必。在儒家看来,除了事功,还有名声。孔子重名,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在先秦古人的观念世界里,“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项好名声可以承载、传播“德”,而这个“德”乃“国家之基”,意味着它具有影响现实政治的效力。只不过,名声往往不像事功那样对当时的现实世界产生即时影响,而是在身后世界慢慢传开,有时候甚至比事功更加深远。因此,立功和立名,是先秦儒家追求博施济众的同等重要的方式,而且往往是立功不成后,便转向立名。如此,“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上》)、“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荀子·君道》)等,构成了先秦儒家共同的出处之道。由此就能看到,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被许仁,不在于他们对殷末乱局有多少实际的匡正之功,而在于他们留下的深远名声惠及后世天下,成为万世楷模。皇侃指出三人“各尽其所宜,俱为臣法,于教有益,故称仁也”①皇侃:《论语义疏》,第475页。,这一评论十分到位。进而可见,伯夷、叔齐与比干一样,表面上是因舍身取义而被许仁,实际上更深的原因在于其名声能振作百代、博施济众。正如孟子称赞伯夷道:“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召忽被许仁也有同样道理,《说苑·善说》指出:“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
那么,多大程度的名声才能达到博施济众之仁的标准?孔子自有其衡量线:“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这句话是孔子褒贬历史人物的原则性论述。“斯民”应如包慎言所言,乃“三代之民”②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109,1109页。,而非孔子的同时代人;否则,如果孔子臧否时人都要“有所试”,那么如何“试”时人,解释起来都是相当迂远的事情。这里,“斯民”亦即三代贤人,他们对于三代是否有道(“直道而行”),是有积极作用的。那么,孔子如何“有所试”而知“斯民”对于三代之治是有积极贡献的呢?《汉书·艺文志》引孔子此言,补充道:“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已试之效”可发明“有所试”。据此,“有所试”不仅涉及名声,同样涉及功业的评判;它是指过去三代圣王贤人的功业、名声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真切的效果,即包慎言所谓“往古之成效可睹”③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109,1109页。。但如何才称得上“成效可睹”呢?答案是见诸“民心”。孔子称伯夷、叔齐,谓之“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称管仲亦云“民到于今受其赐”。这种“民到于今……”的表述,正是“有所试”的真实体现,其背后乃源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的基于“民之好恶”的深厚的民本传统。“民之好恶”不仅具有共时性,更具历时性;只有民众百代惦记的名声功业才具有恒久的品质,才能激起后世,从而博施济众。可见,“有所试”是孔子是否许历史人物为仁的一条筛选基线。因为不难想见,三代以来能守死善道、舍身取义抑或功及天下的人必定不在少数,但其名声能传唱至今者、其功业能造益今人者,则寥若晨星。因而就能明白,孔子为何未许令尹子文、陈文子为仁了(《公冶长》)。这两人只是比孔子稍早的人物,虽一忠一清,但论影响效应,哪能媲美比干的忠和伯夷的清?何况在后来,这两人的品行就被曝有瑕疵,远远够不上“有所试”的基准了。
进一步问题是,虽说留下一项长久激励民心的令名也有博施济众之仁效,但那是历史人物死后的客观效应,这与其生前的主观欲求,是否有出入?比如,我们说伯夷、叔齐杀身成仁,且不说所成之仁是否与孔子一样,就连他们内心所欲求的是不是仁,都是个问题。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伯夷、叔齐之所以逃离故国、逃离周政权,其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全无半点非议的清名,即“廉”。这才是时人的普遍评价,如“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孟子·尽心下》)、“廉如伯夷”(《战国策·燕策》)、“伯夷以廉饥”(《盐铁论·褒贤》),等等。可见,“仁”是孔子追授的。《说苑·立节》就直言二人是“杀身以成其廉”。只不过,单看客观行为而不考虑主观意愿,则二人舍身取义的行为又可对应到许仁依据②,只不过从“廉”到“仁”,其名声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滑转①《史记·伯夷列传》的评论也能透露这一现象:“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司马迁:《史记》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7页。。从这一角度看,其实不只伯夷和叔齐,管仲、召忽、微子、箕子、比干的仁名,都蕴藏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些人与孔子处于不同时代,因而在志趣方面与孔子克复周礼的仁志自然不同。但管仲的事功维系了华夏文明生活方式不坠于夷狄,殷三仁、召忽为后世人臣的出处去留之道树立了典范,这些又是有志扭转周文疲敝的志士仁人所当效法的先贤,其功业声名振作百代,故值得许仁。
这种富含深意的许仁,自然就不是一种定向于求真的史学求知活动,其意义只有放在孔门施教的古典经验中才能彰显。换句话说,这些被孔子许仁的历史榜样,始终面向孔门弟子。评仁的实质在教学。《论语》的许仁活动只涉及历史名人与门人弟子两类,这一现象恐非任意。孔子只对历史上能“有所试”者许仁,而与孔子同时代的其他人也不在其论列。这反映出,依据①②并非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则,即古往今来任何人,只要其客观行为符合其中任何一条规则即可许仁,就像司法判案中依据法律条文、客观证据来核定罪名一样。毋宁说,从依据①②出发的许仁,只是孔子一种灵活的解释活动。其解释力有特定范围。对于孔门之外不认同孔子仁道理想的时人,根本没有评仁的必要;孔子对弟子们的悬而不许,其实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期望,即期望他们能为仁道理想献身;没有这一共同信念,则许仁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对于未达到“有所试”的历史人物来说,许仁也意义不大;这些几近湮没的古人对今人来说太过遥远,没有像伯夷使后世“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的感染力。对历史人物的推许与对门人弟子的期许,两方面构成完整的孔门施教活动。那么许历史人物为仁,就富含着面向孔门弟子的施教价值:伯夷、叔齐、殷三仁、召忽等,是给弟子们献身仁道的行动提供可效法的榜样;而管仲的意义在于提醒弟子,你们的行动不能忘记博施济众的初心,否则即便守死善道,不过是成就“自经于沟渎”的“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如此,这几位历史上的仁者就被孔子注入微言大义。正是在孔子的阐述与施教中,三代历史才得以升华,它不是先王的已陈刍狗,而是能照进当下的鲜活资源②有关《论语》中孔子的施教如何活化历史,参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许仁说到底是一种活化历史、关照当下、激励未来的孔门施教活动。
以上,本文就基于考察孔子仁学所得出的两条许仁依据——能否博施济众(以事功或名声)、能否终身行道(乃至杀身守道),对《论语》中涉及许仁的所有案例给出了力求合理的解读。这种解读并不致力于提出一个逻辑严密的架构来归档所有案例,而是放在孔门施教的古典情境中,理解孔子为何这般许仁。孔子推举出历史上几位仁者,并非通过某种逻辑规则来评定的。被许仁者与许仁依据之间并非严格的逻辑对应,更多是出于教学所需而灵活解释出来的。否则严格说来,至少像管仲、伯夷、叔齐,恐怕也还未能达到孔子“志士仁人”的标准。但这些人被许为仁,相信你都会觉得要比尧舜禹等圣王(无疑也是仁者)更具真实可爱的感染力,从而具有出人意料的教学效果。这种智慧,也只有放在孔门施教的古典伦理形态中,才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