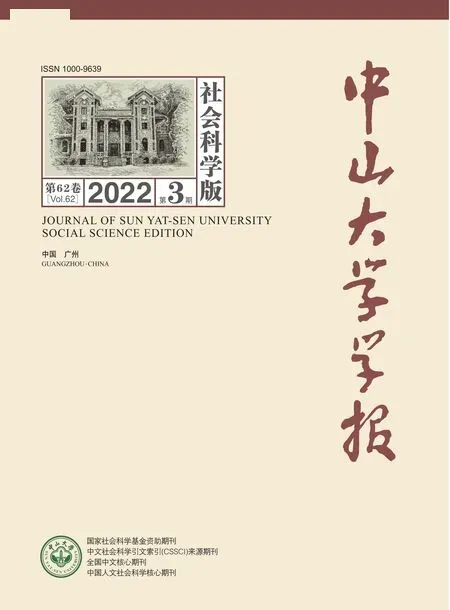国际难民的整合认同:越南归难侨多重身份研究*
黎相宜
引 言
学界有关多重身份认同的共存共融已经有了诸多探讨,包括“双重认同”(dual identities)①周少青:《加拿大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国家认同问题》,《民族研究》2017 年第2 期;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叠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②[美]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有限认同”(limited identities)③J. M. S. Careless,“Limited Identities”in Canada,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Vol. 50,No.1,1969. P. A. Buckner,Limited Identities Revisited: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Canadian History,Acadiensis,Vol. 30,No. 1,2000.等。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更多聚焦于多重身份认同共存共生的静态层面,却忽略了群体作为认同主体对其不同身份进行整合的具体实现机制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事实上,多重身份认同在不同政策机会结构与社会情境规范中的呈现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对于一些资本匮乏的边缘跨境群体,尤其是一些因国际格局及民族国家政策变化引发的国际难民来说,他们面临生产生活系统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④李明欢:《国际移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善治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4期。,难以通过单一群体身份实现文化调适与参与社会竞争。当单一身份无法完全满足个体需求时,个体便会借助其他更具竞争力的身份框架(如国家认同)进行自我归类以获得情感或利益上的满足⑤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97,No.5,2018.。
为此笔者重新梳理与思考了相关身份认同理论,借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有关“整合”“有机团结”“子系统”等概念,提出“整合认同”的分析性框架,用于描述某一群体的多种身份认同类型相互构成及共同演变的结构与功能状态①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73—92 页。[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张明德等译:《社会行动的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61 页。[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92 页。[美]塔尔克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著,刘进、林午、李新、吴予译:《经济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页。[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5页。。这里的整合认同指群体身份框架中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作为子系统相互支撑、高度胶着、深度粘合、共生共演,彼此处在非零和博弈但又没有完全融合的有机团结状态。对于“整合认同”,需要做一些限定:首先,整合认同不是双重/多重认同、叠合认同。双重/多重认同仅简单描述群体的多重身份认同的共存状态。叠合认同则指群体根据情境变化从身份工具箱中选择某一认同进行实践。而整合认同的形成与实践是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借助彼此叙事框架相互支撑与深化演绎的观念与实践过程。其次,整合认同并不用于解释认同主体因情境变化而采取凸显某一身份的情况(如有限认同、情境认同等)。群体的整合认同并非一成不变,也会受到国家政策变迁、社会经济转型及群体位置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调整与演变,但其多重身份认同的整合状态(相互支撑、高度胶着、深度粘合、共生共演)是随系统结构性、整体功能性发生变化的。
广泛分布在全国华侨农场的越南归难侨,为探究“整合认同”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提供了极佳案例②姚俊英:《越界:广州H 华侨农场越南归侨跨国流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3期;甘开鹏,牟军:《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越南归难侨”作为国际难民有着多重跨境与迁徙的生命历程,且历经国家政策变动,其多重身份认同在观念与实践层面不断整合,并随着情境变化而被调整。然而,相比国家层面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所开展的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性治理与归难侨群体层面丰富多元的身份实践而言,目前研究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基于此,本文将根据G 省南涌华侨农场的越南归难侨的文本资料③本研究的文本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13—2020年对G省南涌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所使用资料包括深度访谈、座谈、非参与观察与政府政策文本。其中,笔者对138位关键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28位市、区层面的政府及侨务部门干部、92位归难侨以及18位社区其他居民。,具体分析这些国际难民的整合认同是如何形成、实践、调整与演变的。
一、整合认同的形成与实践
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中国陆续安置了受越南排华、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波及的越南归难侨。国家对这些“回到祖国怀抱”的归难侨进行特殊化安置,在赋予这些归难侨群体以普通国民身份的同时,还对其实行倾斜照顾政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下面将分析越南归难侨群体是如何在观念层面生成其整合认同并进行实践的。
(一)整合认同的形成
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中越边境日趋紧张。1978 年6 月,南涌华侨农场首批接待安置越南难民五百多人,至1986年底止共安置4,497人④参见《1949年至2008年农场(管理区)大事记》,内部资料。。拥有特殊历史记忆与迁徙经验的越南归难侨,在与国家力量、本地社会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发展出整合认同。
整合认同的形成首先与越南归难侨回国前的华人性、在越南的社会境遇及其流徙经历有关。越南归难侨的祖父辈大多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边境尚未清晰之前,出于经济、政治原因流动到越南北部山区定居耕种的“边民”。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很大程度保有“华人性”的成分:“我们在越北都是中国人,因为我受到我爷爷、父亲的思想,不管我们居住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民族的文字,我们的名字。不管流落到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是中国人。”华人性为越南归难侨实现多重身份认同的顺利整合提供了前提。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大部分的归难侨对他们从流徙到安置的过程赋予了“回到祖国怀抱”的意涵:“本来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到祖国怀抱里来。”“肯定是中华民族,在越南也是中华民族,不然为什么回到中国。我们在越南就相当于寄宿在别人家里,不是我自己家。我回到中国就好像回到自己家里。”而且在此过程中,被威胁驱逐的屈辱与流离失所的逃难经历凝聚而成的历史记忆使越南归难侨有着极度不安全感。越南归难侨欧阳先生谈到:“你以前在越南它不把你当主人哦,因为你寄人篱下,它要赶你就赶你,要杀你就杀你。所以说没有国就没有家。”而国家认同则具有帮助建构惯常例行的生活情境,保证个体“本体性安全”的功能性力量①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因此,当他们回到中国时,他们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为其顺利接受归属性国家认同并以此发展赞同性国家认同②归属性国家认同指的是公民对国家/民族领土、历史、文化以及对祖国同胞的认同等基本元素组成的国家认同。赞同性国家认同则包括了公民对公民—民族的认同、对国家制度(宪政民主福利制度)的认同和宪法爱国主义三个维度。参见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提供了初始基础。
同时,越南归难侨的整合认同还受到了国家力量的深刻形塑。适时中国面临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转型,做好越南归难侨的安置工作,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印支难民安置办公室主任徐留根在回顾难民安置工作时说道:“20年来,我们积极工作,保障安置在我国的印支难民的基本权益,充分说明中国作为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是认真履行义务,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③韩松:《阳光家园——人道安置在广东》,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3—14,26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动用行政资源,通过华侨农场这种集中安置的方式,为归难侨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保障,并满足其安全感及归属感的需求④黎相宜:《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 年第1期。。国家这种优待安置政策强化了越南归难侨的“华人性”,使他们加深其归属性国家认同与赞同性国家认同:“他都列入我们是国家公民啦,承认了……不过说真一句,生活在哪里住都好,有一个自尊,有一个尊严不受损。你住得安乐就好……不受人侵犯就好。”同时,集中安置制度及相应政策也使这一群体产生了“难民”认同。一是官方表述为难民身份的确立提供了权威性依据。中国在安置工作的文件和对外宣传中都统一使用“难民”一词:“加强宣传报道工作。明确一律统称难民。”⑤韩松:《阳光家园——人道安置在广东》,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3—14,26页。官方的标签话语逐渐被越南归难侨内化:“如果按照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国际难民。”二是集中安置制度强化了难民意识。在相对隔离的空间内,越南归难侨作为个体所遭遇的苦难与逃难经历被反复表述、共享与传播,并逐渐凝聚为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由此而产生的群体归属感进而形塑了其群体身份。
此外,安置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境以及与本地群体的族际互动,对越南归难侨多重身份认同之间的最终整合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越南归难侨在与本地人的交往互动中,由于自身的异质性和匮乏的社会经济资本而受到一定排斥。本地人陈先生说:“当时他们是作为难民回来的,身份很低的,文化素质教育也不好,当时在整个社区是非常瞧不起这群人的。”在上述情况下,一方面,越南归难侨通过“我群”与“他群”的二元编码机制⑥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通过强化群体认同实现自我的心理防御:“以前都是说我们是越南佬嘛,肯定有歧视的意思了……读书的时候那些本地的对我们华侨有歧视的成分。一打架我们华侨子弟全部聚在一起打。”另一方面,他们借助国家认同来确立自身在当地生存的合法性,以避免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是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当时是不能过来的。”“我们的心态呀,就是中国人啊。回到祖国都是中国人的嘛。”来自本地社会的排斥使归难侨进而整合其群体与国民身份:国家认同经此得到强化与延伸,不仅帮助归难侨应对本地人排斥、缓解身份危机,而且为他们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而群体认同不只是承载他们根基性情感的意象,更是他们寻求归属感的重要途径。归难侨的多重身份认同在观念层面相互嵌套与整合,由此形成的整合认同不仅是越南归难侨为抵御本地社群排斥、寻求情感支持而形成的心理机制,更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表达利益诉求的凭借,为归难侨的适应与融入提供支撑。
(二)整合认同的实践
归难侨的整合认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实践的过程。整合认同的实践,首先体现于享有优势政策性地位的越南归难侨对于特殊国民身份的内化与强调上。在国家特殊化治理逻辑的影响下,越南归难侨除了享有归难侨待遇外,他们同时还是联合国难民署认定的国际印支难民。享有双重优势政策性地位①黎相宜:《政策性地位、区别化治理与区别化应责——基于一个移民安置聚集区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3期。的越南归难侨积极接受国家的政治整合,形成优于本地人的特殊国民身份。这种整合认同实践的一个表现是在越南归难侨能获得比本地人与其他归难侨(如马来亚归难侨)更多资源上。1978 年农场为了更好地安置越南归难侨,投入了136.87 万元建造砖瓦房。1979 年,整个农场砖瓦房面积达107,035 平方米,比1978 年增加了将近43,526 平方米;职工人均面积达到6.26 平方米,是1978 年的1.65 倍②《南涌华侨农场志(1950—1988)》,内部资料,第68,71页。。这其中增添的砖瓦房主要用于安置刚回国的越南归难侨。越南归难侨叶先生说:“以前我们过来,他们(笔者注:指本地人及马来亚归难侨)还住茅房,我们住红砖的嘛。”考虑到越南归难侨回国时间短,给予其种植责任田的亩数比当地职工低了25%③《南涌华侨农场志(1950—1988)》,内部资料,第68,71页。。另一个表现则在观念层面。相对优势资源的获得增强了越南归难侨的相对优越感。越南归难侨欧阳先生在回顾安置初期的情形时谈到:“我们直接就是中国公民了……总的来讲,归侨回来比在国外要好多了。经济生活有保障,起码一条,我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人……反正都有政策的,都有优惠和倾斜。”在这种整合认同的实践过程中,越南归难侨不断内化其公民身份及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整合认同得到发展与深化。
整合认同实践还表现为归难侨与国际难民身份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观念体系下被持续实践。在制度层面,归难侨以“政策性群体”的身份嵌入于国家制度体系,促进了群体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的深度粘合。陈先生回忆刚回国时的情境:“我们刚刚回来祖国的时候,我感觉是我们归难侨比其他人生活好一点……如果按照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国际难民。”郑先生说:“以前侨办的干部还是与我们交流挺多的……侨办会经常过年过节下来送点东西,走走看看。”归难侨的国民身份是其享受特殊政策性地位的凭借,归难侨与国际难民的身份是被放置在国家安置制度的框架下实践的。在观念层面,归难侨在当时国家与社会的特殊照顾理念支持下深化了其群体身份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的整合。归难侨的优势政策性地位得到当时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的接纳与认可。本地人与街道干部提及越南归难侨所受到的政策照顾时基本是持合理化态度的:“1978 年的时候,很多越南难侨过来,因为他是中国人,他们要回来,国家是要有责任安置他们的。”在这种观念因素支持下,越南归难侨的整合认同暗含了对国家的认同与对自身所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我们都是普通难民咯,我们都是华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属于中华人民。”
由上可知,回国后的越南归难侨群体在调适过程中发展出整合认同。这种身份实践得到了当时华侨农场、各级政府及侨务部门的积极肯定。首先,惠侨组织的设立与积极正面的宣传为整合认同不断生成提供了有利条件。1982年,农场“召开首届归侨、侨眷、港澳同胞亲属代表大会,成立南涌华侨农场归国华侨联合委员会”①参见《1949年至2008年农场(管理区)大事记》,内部资料。。随后,南涌华侨农场归国华侨联合会申请筹办了“综合服务社”。这个具有惠侨性质的组织在担负接待归国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任务的同时,还具有协助农场解决部分归侨、侨眷子女就业问题的特殊职能②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广东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此外,华侨农场积极宣传越南归难侨重建家园的活动。《广东侨报》先后以“苦涩的汗水变成了甜蜜的蔗汁——记南涌农场女难民刘源珍(1986 年11 月26 日)”、“志在农场建家园——记南涌农场难民女青年刘贤珍(1987年9月22日)”为题报道了归难侨的农场生活③韩松:《阳光家园——人道安置在广东》,第44页。。其次,各方的考察与监督使整合认同得以被持续实践。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各级政府与侨务部门会定时派人员下来视察南涌华侨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越南归难侨的生活情况。1985年,联合国难民署官员黎明·贺尔、李德华来场,并前往南涌中学等地视察④参见《1949年至2008年农场(管理区)大事记》,内部资料。。曾任侨办主任的杨先生说:“省难民办每年都要组织各个华侨农场来我南涌开会取经参观。”越南归难侨的整合认同实践,构成政府展示侨务工作成效以及凸显制度优势的“窗口”,进而得到认可和强化。
然而,受国家治理逻辑与政策变迁、农场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归难侨群体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动,其整合认同随之发生调整与演变。
二、整合认同的调整与演变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家对国有华侨农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均等化的改革措施。华侨农场及农场内的归难侨群体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政策性地位。在此背景下,越南归难侨试图重新调整其整合认同。
(一)整合认同的调整
南涌华侨农场的改革始于1988年。一方面,华侨农场的政治功能被下放,“由中央和省的侨务部门主管(以省为主)的领导体制,改为由地方人民政府领导”⑤《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85〕6号)。;另一方面,农场的经济功能也被剥离,“统包分配”的生产模式被取消。在上述宏观制度转型的影响下,归难侨群体的多重身份认同随之发生系统结构性、整体功能性变化,其整合认同也面临再调整。
首先,归难侨身份以及围绕此身份而能获取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越南归难侨尤其是第二代难凭借“侨”身份获取额外资源:“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没有,老爸老妈比我们好。我们现在生病都没钱看病,医疗什么都没有,真是病不起。”越南归难侨的相对失落感逐渐产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逻辑下,归难侨对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及对农场单位的生存依赖渐渐被赋予了一些负面含义。南涌街道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归难侨子女)是在农场长大的,在家里也没有很好的氛围,文化素质比较差,也没读什么书,也比较懒,总是觉得自己是归侨,有特殊身份,国家应该要照顾他们。”
其次,普通国民身份难以完全满足归难侨参与社会竞争的需要。长期形成的依赖性与优越感使归难侨很难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大潮。一些归难侨流向次级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些则向往高收入的工作,但却因自身匮乏的人力资本而陷入失业或无业状态。2006 年G 省华侨农场内归难侨的年人均收入为6,631.39 元,低于农场所在市县的农民人均总收入8,339 元⑥《G省华侨农场各指标总表(2006)》,内部资料。。此外,归难侨群体自身的跨国特性也加剧了其相对失落感。他们的参照群体并非本地人,而是安置在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亲戚朋友。对于归难侨群体来说,国民身份曾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安全感的需求,但在注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人力与社会资本匮乏的归难侨难以仅凭普通国民身份参与社会竞争,他们在此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不安全感和失落感。
国家实施均等化措施的本意,是希望归难侨逐渐融合于本地,不再需要凭借特殊的归难侨身份获取资源。但政策性地位均等化所产生的一些非预期后果(如归难侨生活贫困,基层出现不和谐声音等)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2年,时任国侨办主任李海峰在全国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华侨农场问题。国家试图重新给予华侨农场与归难侨以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支持”①Li Minghuan,Collective Symbols and Individual Options:Life on a State Farm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fter Decollectivization,How Chinese Migrants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3,p.105.,在观念上重新强调了归难侨的特殊身份,在实践层面以“侨”与“非侨”作为资源获得的划分依据。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整合认同的演变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整合认同的演变
在国家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归难侨的整合认同随之发生了演变。此时归难侨的整合认同首先体现在越南归难侨积极运用国家符号象征②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通过强调其国民身份,为其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性框架与依据。一方面,归难侨通过不断确认与表述其归属性国家认同,将自身地位与中国的高速发展联系在一起,以此获得自豪感和相对优越感,为其利益表达提供合法性框架:“我们国内好起来了,在外国人面前有信心了。当然感觉到自豪啦,我们国家强大了。”另一方面,归难侨积极寻求国家的政策保障,在赞同性国家认同框架内铸牢其资源获得的合法性基础:“现在是中国人了嘛,拿着中国身份证。像我们这样,中国对我们华侨很多政策都是很好的。我们理应享受到国家的政策。”
此外,整合认同还体现为,归难侨在国家认同框架内重新强调其作为归难侨与国际难民的身份归属与利益诉求,以弥补单一国民身份所无法满足的情感与利益需求。首先,归难侨通过群体内部共同体建设,强化其作为归难侨与国际难民的情感纽带,以此补偿由于市场经济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缺失。越南归难侨蔡先生说:“我们(越南)归难侨大家有什么事就走到一起,你帮我我帮你……我最欣慰的就是这点,吵架也有,但多数都很好。人情味,大家还有点人情味。”其次,归难侨还发展出一系列利益表达实践,不断督促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省级政府针对归难侨群体的倾斜性政策,以满足其实际需求③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应给予救济。”中央财政在华侨事业费中专门设立了归侨生活困难补助费。而自华侨农场下放地方管理以来,省级政府也高度重视相关工作,针对改制过程中归难侨出现的生活困难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为扶持华侨农场工作相应安排专项资金。。比如越南归难侨曾就国家危房改造政策向基层政府寻求经济利益,要求省市下拨的归难侨危房改造资金发给个人④《1949年至2008年农场(管理区)大事记》,内部资料。。2006 年,三百多名职工到机关大院旁要求解决职工住房改革等5 个问题⑤《南涌街地方志(2005—2011)》,内部资料。。归难侨徐先生回忆当时情境:“每个侨队都会有一个代表,我是*大队的代表来的。就是国家有政策针对我们这些归难侨的……所以我们就要反映情况。”越南归难侨潘先生说:“毕竟来说,中国接纳了这批难民,你就一定要对他们负责……”由上可知,越南归难侨试图通过整合认同的调整来获取情感支持与满足利益诉求,以此实现社会适应与向上流动。
与华侨农场体制改革前的情形不同的是,越南归难侨调整后的整合认同对基层治理造成一定压力,同时也易于面临被问题化的风险。街道干部说:“这个越南归侨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所以有这个压力。就是我们要做到让上级满意,对群众也要有个交代。”南涌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越南归侨觉得政府应该管他们。他们就是等靠要的。”本地人陈先生也认为:“这些人现在呢也比较懒,他们就老是觉得自己很特殊,是华侨嘛,就希望享受待遇,最好是不用干活也有很多钱拿那种……”当然,“问题化”也不完全是负面的。比如基层干部就指出归难侨是需要被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他们属于弱势人群,需要我们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化是由各方在实际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虽然归难侨依赖国家政策实现了整合认同的调整,但这种身份认同始终与普遍主义的治理逻辑存在张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群体的政治参与、社会适应与文化融入。
结 语
在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相关理论基础上,笔者尝试建立“整合认同”这一分析性概念,来理解越南归难侨多重身份认同相互支撑、高度胶着、深度粘合、共生共演的观念与实践过程。受国家政策变迁、社会经济转型与群体地位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归难侨群体的整合认同是呈现系统结构性、整体功能性调整变化的。辗转回国的越南归难侨在与国家力量、本地社会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发展出整合认同。随着国家发展目标与总体治理理念的变化,归难侨调整其整合认同。整合认同的动态演变,既是越南归难侨在政策机会结构与经济社会体制下的情境性反应,也是其参与社会竞争及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动性体现。一方面,享有政策性地位的越南归难侨积极运用国家符号象征,通过强调其特殊国民身份,为群体利益表达提供合法性框架与依据。另一方面,越南归难侨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与观念体系下,持续实践其作为归难侨与国际难民的身份归属与利益诉求。
在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的背景下,群体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迅速提升,这一方面给国族整合机制提出了新挑战,一方面也凸显了国族建设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起一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完整的、具有适应性和弹性的国族机制,才能为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提供有力支撑①参见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党和国家长期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参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本文的案例也表明,归难侨的多重身份认同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作用与支撑的。归难侨群体试图在其身份实践中不断整合多重身份认同,以试图满足群体的多元需求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发展而来的整合认同不仅是归难侨群体进行利益表达、参与社会竞争的基础,更是其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真实情感表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大背景下,归难侨的整合认同也将在不断融入过程中重新面临调整与变化:一方面,归难侨与本地社会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与交融;另一方面,他们将面临从享有特殊政策性地位的群体逐步转变为普通国民的挑战以及这个过程中所伴随的不适应乃至阵痛。而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整体化、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如何激发有关华侨农场与归难侨社区的治理创新活力,使归难侨群体自身的能动性及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取向,既是新时期侨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学术共同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聚焦各国难民儿童生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