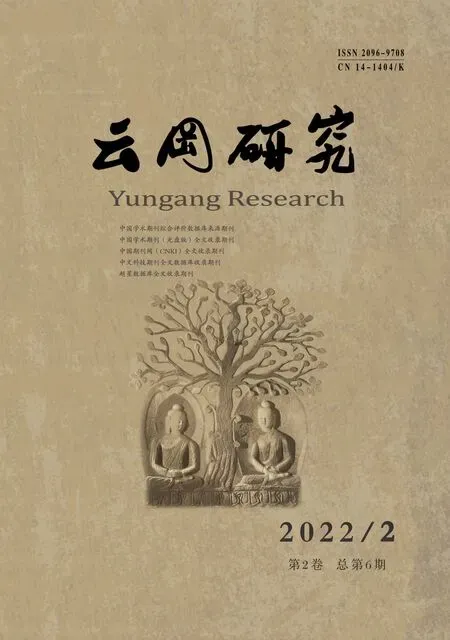北魏平城时期族际通婚研究
马永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个体社会成员愿意接受彼此的族群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的婚姻。古时的族际通婚包括顶层和亲、上层宗族贵族世家联姻与民间通婚三种形式。和亲是指中国古代不同种族、民族和政权的君王之间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政治联姻;宗族贵族世家联姻是指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上层宗族贵族世家等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联姻,其中多夹杂政治成分;民间通婚指不同民族、种族和政权的下层普通民众互通婚姻、结成姻亲。
古时大同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处,匈奴、林胡、狄、乌桓、鲜卑、柔然、突厥、沙陀、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在这里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繁衍生息。大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民族融合的重任,成为族际通婚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北魏时期,作为京师的平城(即大同)成为汉族与诸多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心,族际通婚成为常态,从而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为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和亲——族际通婚的官方宣言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君王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武力征伐、和亲、羁縻、结盟等不绝于史书。在武力征伐未果的情况下,和亲政策便备受君王青睐,因为它可以缓解两个对立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亲慕、友善的关系,有力于政权的长治久安。发生于大同的“白登之围”开创了和亲的先河。
(一)“白登之围”开先河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32万大军,御驾亲征据守同朔地区的韩王信叛乱,并试图征服日益势大的匈奴部族。然而“白登之围”给了刘邦当头棒喝,使其意识到汉初羸弱的国力根本无法对抗彪悍的游牧民族,遂采纳谋臣刘敬(即娄敬)的“和亲”建议:“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1](卷99《刘敬传》,P2719)不过因吕后舍不得亲生女儿远嫁他族受难,刘邦只好退而求其次,“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1](卷110《匈奴传》,P2895)虽然匈奴单于冒顿不太明白和亲的真实意图,但对汉王朝的示好欣然接受。自此,作为官方宣言的族际通婚——和亲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白登之围”引发的汉匈和亲开创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先河。[2](P57)此后70余年内,汉匈双方虽在边境偶有冲突摩擦,但并未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长期续存。这其中和亲的贡献不言而喻。而作为“白登之围”发生地的大同见证了和亲政策的出笼与施行,从此与和亲紧紧捆绑在一起,哪怕是王昭君出塞并未途经大同,但依旧有好事者演绎出琵琶老店的故事佳话来。
(二)北魏时期的和亲之路
北魏建国初期,北方政权林立,鲜卑拓跋部不仅无力通过武力来消灭其它政权以完成统一,且还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如何使北魏政权生存、发展、壮大,摆在了统治者面前。而和亲无疑是暂时首选,“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3](卷118《姚兴载记下》,P2999)和亲不仅可以为北魏政权寻找到临时盟友,避免四面受敌,且可以为其完成一统北方提供契机。事实上,早在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时期,便规定帝室十姓不得通婚。而拓跋力微本人以身作则,与曹魏进行了和亲。北魏统治者遂开启了和亲之路,先后与匈奴、前燕、后秦、北凉、柔然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和亲。
1.北魏与匈奴的和亲
当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的鲜卑拓跋部进入蒙古草原后,便与匈奴部族杂居于长城内外的广袤土地上。两个不同部族之间难免矛盾重重,作为外来势力的鲜卑拓跋部选择通过和亲来加强两族首领之间的联络,从而改善两族的关系,消除彼此的隔阂。北魏与匈奴的和亲最早可追溯到平皇帝七年(293年),平帝拓跋绰之女与匈奴宇文部大人普拨之子丘不懃和亲,“帝以女妻拨子丘不懃。”[4](卷1《序纪》,P5)昭 皇帝 五 年(298 年),匈 奴 宇文部大人逊昵延朝贡时,昭帝拓跋禄官“以长女妻 焉 ”。[4](卷1《序纪》,P6)鲜卑拓跋部与匈奴宇文部和亲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融合出在北魏、隋、唐历史中书写浓墨重笔的鲜卑宇文部,而这绝不是两次和亲所能完成的。
平文帝二年(318年),匈奴南单于后裔刘虎占据朔方,时常进犯鲜卑拓跋部,被平文帝拓跋郁律击溃,刘虎从弟刘路孤率领匈奴余部投降。为了笼络刘路孤,平文帝将女儿许与他为妻。昭成帝四年(341年),刘虎故去,其子务桓继位。为了得到鲜卑拓跋部的支持,务桓请求归顺。面对务桓的示好,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并未因刘虎的屡次进犯而不依不饶,其依旧利用和亲来化解隔阂,将女儿嫁与务桓。昭成帝二十三年(359年),务桓第三个儿子卫辰继位后,据守塞外朔方,控制疆域东西长达千余里,对鲜卑拓跋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拉拢卫辰,昭成帝将女儿嫁给了卫辰。
可以说,鲜卑拓跋部进入蒙古草原后,能够生根发芽、日益壮大,并与匈奴部族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融为一体,和亲功不可没。
2.北魏与前燕的和亲
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同族血脉使得双方很自然的相亲相近,和亲自是必不可少。东晋咸康三年(337年),慕容元真以辽西为基地建立了前燕政权。昭成帝二年(339年),昭成帝请求和亲,慕容元真将亲妹妹嫁给他,后者将其立为皇后。昭成帝四年(341年),幕容皇后不幸去世。同年12月,慕容元真派遣使臣前来朝贡,“并荐其宗女。”[4](卷1《序纪》,P12)昭成帝六年(343年),慕容元真再次遣使请求和亲,欲把女儿嫁给昭成帝。幕容元真对此次和亲非常重视,于第二年二月亲自将女儿送到边境。昭成帝则派重臣长孙秩到边境上迎接,以显诚意。慕容元真的女儿被迎到代都平城后,立为皇后,史称昭成皇后,备受昭成帝的宠爱,育有献明帝和秦明王二子,可谓尊宠至极。昭成帝七年(344年)秋七月,慕容元真派使臣携带聘礼向北魏请求和亲,昭成帝将烈帝的女儿嫁给了他。昭成帝十九年(356年)冬,慕容元真之子慕容俊请求和亲,昭成帝同意。昭成帝二十五年(362年)十一月,慕容俊之子慕容暐推荐宗室女给昭成帝以备后宫。
虽然在北魏与前燕和亲之路上,前燕处于弱势地位,但北魏统治者给予了对方足够的尊重,多人被立为皇后。北魏与前燕通过和亲,加强了双方的隶属关系。终前燕始终(337-370年),两国的和亲之路从未中断过。和亲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更重要的是解除了前燕的后顾之忧,从而能集中力量,南下灭掉后赵、冉魏,雄霸中原。[2](P63)
3.北魏与后秦的和亲
北魏登国元年(386年),羌族人姚苌建立后秦。登国八年(393年),姚苌病逝,其子姚兴继位。后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较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严重威胁着刚刚建国的北魏政权。为了笼络后秦,道武帝拓跋珪主动示好,于天兴五年(402年)以马千匹作为聘礼,向姚兴请求和亲。姚兴赞同,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道武帝要立他的女儿为北魏皇后。而道武帝却选择立同属鲜卑族的后燕慕容宝的幼女为皇后。姚兴恼羞成怒,不仅终止和亲,还兵戎相见。两国爆发了一场激烈战斗——柴壁之战,后秦军队惨败。柴壁之战固然是北魏与后秦两国欲消灭彼此完成统一所进行的军事角逐,但双方和亲的失败则成为了导火线。有鉴于此,北魏与后秦两国都开始审慎对待和亲。姚兴先后于永兴三年(411年)六月和永兴五年(413年)二月两次派遣使臣前往北魏请求和亲。遭到拒绝后,姚兴并未灰心,于永兴五年(413年)十一月癸酉再次“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即明元帝拓跋嗣)许之。”[4](卷3《太宗纪》,P54)不过此次和亲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一度搁置下来。神瑞元年(414年),姚兴重提和亲之事,并于第二年派尚书姚泰与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将西平公主送到魏都平城。鉴于上次和亲失败所引起的柴壁之战的惨痛教训,明元帝高度重视此次和亲,以皇后礼仪把西平公主迎进北魏皇宫。虽然西平公主因铸造金人失败而无法被立为皇后(北魏习俗,立皇后时要铸金人以获天佑,一旦铸不成,则说明此人没有皇后之福命),而是被立为夫人。但拓跋嗣仍“宠幸之,出入居处”,以皇后之礼待她。[2](P65)
北魏与后秦的和亲历程,虽有波折,但双方统治者都认识到了和亲“实亦永安之福”,在力倡和亲之时,都小心谨慎的修正之前的失误,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4.北魏与北凉的和亲
北魏天兴四年(401年),匈奴卢水胡沮渠部沮渠蒙逊起兵攻杀北凉国主段业,承袭北凉国主。由于北凉国小势弱,为了避免被其它政权吞并,沮渠蒙逊决定与北魏和亲,拟将女儿兴平公主嫁给太武帝拓跋焘。延和二年(433年),太武帝派太常李顺前往北凉都城姑臧迎接兴平公主。斯值沮渠蒙逊病逝,其子沮渠牧犍继位。沮渠牧犍坚持既定的和亲方针,派左丞宋繇将尚在悲痛之中的兴平公主送到平城。太武帝非常高兴,册封兴平公主为右昭仪,在后宫的地位极高。北魏与北凉的和亲,加强了双方的隶属关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联系,太武帝于太延三年(437年)将妹妹武威公主嫁与沮渠牧键。沮渠牧键受宠若惊,册封武威公主为皇后,原皇后李后移居酒泉。最初,沮渠牧键对武威公主宠爱有加,但很快移情别恋于其嫂子李氏。武威公主察觉后,怒责沮渠牧犍和李氏。李氏心存怨念,企图毒杀武威公主。事情败露后,太武帝大怒,于太延五年(439年)亲率大军讨伐北凉,沮渠牧犍投降,北凉亡国。
北魏与北凉的和亲,曾经收到了两国“永安之福”的效果。而北凉的灭亡,虽然其本质上是北魏要统一北方,但其导火线却是北凉破坏了两国和亲的苦果。
5.北魏与柔然的和亲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其最高统治部落为鲜卑别部的一支。5世纪初,社仑统领柔然,建立起一个由柔然、匈奴与高车等诸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强大政权,对北魏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社仑时期的柔然选择与后秦姚兴和亲结盟,共同对抗北魏。北魏神二年(429年),吴提继位。为了缓和北魏与柔然两国的关系,双方开始了和亲之路。延和三年(434年),吴提迎娶西海公主为妻,同时派遣兄长秃鹿傀为首庞大的送亲队伍护送妹妹到平城。拓跋焘将吴提的妹妹纳为夫人,后册封为左昭仪,仅比皇后低一等。
虽然这次和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快两国便围绕争夺西域爆发了战争。这严重影响到两国和亲政策的继续执行。例如柔然予成可汗曾于北魏延兴元年(471年)、太和元年(477年)两次向北魏提出和亲,均遭拒绝。
北魏和柔然两国边界犬牙交错,一些小冲突在所难免,只有通过和亲来建立民族间从上到下的通婚与信任,再通过和亲而带来的边界和平与频繁的商品交易、人际交流,才能实现民族融合,而得民族间的“永安之福”。[2](P69)可惜两国统治者或“每怀诡诈”,或“款约不著”,导致和亲之路步履维艰,未尝不是憾事。
此外,《魏书・皇后列传》所载神元皇帝到孝文帝20余位皇后中,就有匈奴、汉、鲜卑慕容、羌、匈奴铁弗、匈奴赫连、柔然等族,至于妃嫔,族类更杂,有汉、匈奴、柔然、吐谷浑、氐、蜀、羯、羌……当时北方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女性进入北魏帝室。[2](P170)这其中有多少来自和亲,我们不得而知,相信不在少数,尤其是这些异族皇后,应多是和亲的结果。可以说,北魏王朝真正把和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和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延续了上千年,为历代统治者所采纳。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和亲的评价褒贬不一,总体是褒大于贬。“贬”者认为和亲是屈辱妥协,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褒”者认为和亲是维护各民族友好关系的有效手段。如果从民族融合角度来说,绝大多数和亲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缓和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有力促进了多民族杂居的融合。由和亲带来的中原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及人口的迁移对人口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更使其成为中华民族融合的最佳途径。[2](P61)和亲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二、贵族门阀联姻——族际通婚的上层示范
在鲜卑拓跋部历代君王和亲的感召下,其统治集团上层宗室贵族亦不甘落后,频繁地与其他少数民族贵族、汉族门阀士族联姻,实现了顶层和亲、上层联姻的互动,起到了族际通婚的示范引领功效。
鲜卑拓跋部上层宗室贵族联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魏建国前,联姻对象主要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宗室贵族。拓跋力微制定了帝室十姓不通的“祖训”,这样在鲜卑拓跋部与周边少数民族君王和亲的基础上,其上层宗室贵族的联姻日益频繁,一些新的少数民族还由此产生,如铁弗匈奴、赫连匈奴等,而这些民族最后又都被鲜卑拓跋部征服,全部融合于北魏大家庭中。可以说,鲜卑拓跋部由弱变强,统一北方,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与其他部族和亲、联姻。
第二阶段是北魏建国到孝文帝改革前,联姻对象主要是其他少数民族宗族贵族与在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进程中建立卓越军功的世家大族。伴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北方其它政权皆灰飞烟灭,昔日的竞争对手成为北魏王朝的臣属。如何正确处理与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宗室贵族的关系,平息境内不同声音,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征服者的北魏统治者并未因对手沦为阶下囚便肆意打压,甚或斩草除根,而是以“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4](卷2《太祖纪》,P30)的兼容并包的民族平等理念,选择联姻将其吸纳到北魏统治集团中,借以笼络人心、减少敌对势力,扩大统治基础,从而更好地为北魏政权服务。至于那些立下悍马军功的世家大族更是要论功行赏,与北魏宗室联姻无疑是最大的赏赐。“北魏除了注重帝室与他族通婚的同时,对于下面的王公大臣,也是注重用通婚的手段来加以联结与融合的。”[2](P170)
第三阶段是孝文帝改革后,联姻对象以北方汉族门阀士族为主。魏晋之际,汉族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以宗族为纽带的官僚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累世为官、把持朝政,通过联姻、仕宦、严格等级来维护门阀制度。门阀士族高高在上,构成了强大的居于垄断地位的社会政治势力。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一度使门阀士族惶恐不安。幸而北魏统治者秉承“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的治国理念,重用清河崔氏、勃海高氏、陇西李氏、河东柳氏、范阳卢氏等门阀士族,将其中的才学之士纳入到统治集团中,如北方第一名门清河崔氏领袖崔浩。崔浩辅佐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帝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中居功至伟。以崔浩为桥梁,一些门阀士族开始参与北魏朝政。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己亥发生的“国史之狱”中,崔浩被诛杀,“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4](卷35《崔浩传》,P826)北方门阀士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他们与北魏统治者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前者意识到,后者并非真正信任他们,对他们只是利用而非重用。门阀士族开始游离于政权之外,以此抗议北魏统治者的暴政。而北魏统辖境内以汉人居多,门阀士族在汉人中的影响力是无法取代的,故北魏统治者欲维持政权长治久安,必须要借助汉族门阀士族。于是孝文帝开始将联姻的重心转向了门阀士族。“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4](卷21上《咸阳王禧传》,P534)孝文帝一次性为6个弟弟与门阀士族进行了联姻:咸阳王拓跋禧、河南王拓跋干、广陵王拓跋羽、颍川王拓跋雍、始平王拓跋勰、北海王拓跋详分别迎娶了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中散代郡穆明乐女、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对于门阀士族来说,若果他们不接受北魏统治者已然抛下的绣球,可能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灾。联姻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何乐而不为呢?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述:“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亦远胜于胡人,故胡人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之大族亦欲籍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使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5](P42)于是,一场以政治为目的的胡汉上层联姻便轰轰烈烈展开了。清河崔夤、崔瓒,赵郡李安世,陇西李彧、李挺,司马家族中的司马楚、司马朏、司马跃,琅玡王肃、王诵,范阳卢氏一族3人都曾迎娶过北魏公主。正是通过这种联姻,使北魏统治集团上层宗室贵族率先实现了多民族的融合。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统计出发生在平城的上层联姻有多少,但作为北魏都城所在地,平城权贵云集,应是联姻的绝对中心。
三、民间通婚——族际通婚的下层普及
上有所好,下必仿效。君王和亲、上层联姻引领着北魏社会族际通婚的潮流,推动了民间族际通婚向前发展。北魏时期的民间族际通婚主要建立在移民杂居和北魏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基础之上。
(一)移民杂居——民间族际通婚的关键所在
移民杂居自古便存在,这在大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拉近了汉胡人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同地区遂开始了大规模的民间族际通婚。北魏王朝建立在兼并其它政权的基础之上,这本身便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为了隔断原政权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联系,避免二者勾结再次威胁北魏政权,北魏统治者采取移民措施,将原住地民众迁往其它地区,多民族人民杂居一处,为实现大规模民间族际通婚创造了条件。登国元年(386年),北魏定都平城后,开启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登国六年(391年)—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政府移民多达58次,有具体数目的为41次,迁徙人口应在200万以上。[2](P175)其中史载确切时间移民京师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有天兴元年(398年)、天兴五年(402年)、天兴六年(403年)、泰常三年(418年)、太延五年(439年)、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皇兴三年(469年),移民人数近百万,尤以天兴元年(398年)移民人数为最,“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4](卷2《太祖纪》,P32)这使得平城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使平城成为诸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心。各民族共同生活,开始逐渐接受彼此的族群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族际通婚成为了北魏时期的社会生活常态。可以说移民杂居是民间族际通婚的关键所在。正是这种民间的、大规模的通婚行为所带来的族际间的交融,方使得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部族消融在这种族际通婚之中。[2](P40)可惜由于历史的失语,绝大多数民间族际通婚未被载入史书,实属憾事。
(二)有意识的政府行为——民间族际通婚的合法保障
为了有效推动民间族际通婚进一步展开,北魏王朝有意识地加大了政府行为,如外放宫女、将女性俘虏赐婚给劳苦功高的将士、诏许异族异姓通婚等,为民间族际通婚提供了合法保障。
1.外放宫女
据《魏书》记载,北魏定都平城期间,统治者曾五次外放宫女并赐婚给鳏民。其中明元帝1次、太武帝1次、孝文帝3次,如永兴三年(411年)“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余悉出以配鳏民。”[4](卷3《太宗纪》,P51)太和十三年(489年)“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4](卷7下《高祖纪下》,P165)宫女所嫁范围应为京师平城及京畿地区,而上述地区已然成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故“每一次外放宫女配以京师及北镇鳏贫的行动,都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民族通婚行为。”[2](P171)
2.赐婚将士
北魏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是与广大将士的英勇作战分不开的。为了笼络部下将士,北魏统治者便将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异族妇女、牛马羊等战利品赏赐给他们。这主要发生在道武帝和太武帝时期,其中道武帝建立北魏政权,太武帝基本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战事较为频繁。如天兴二年(399年)征伐高车时,道武帝将掳掠而来的人口、牛马羊等班赐给将士。始光四年(427年)年征伐赫连昌时,太武帝“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赍将士各有差。”[4](卷4上《世祖纪上》,P73)此外,太武帝还曾于延和三年(434年)、太延五年(439年)两次将掳掠来的妇女班赐给将士。事实上,将战争中掳掠而来的异族妇女、财物等战利品班赐给将士的现象在北魏王朝并不少见,毕竟北魏广大将士也是人,也需要成家立业、成就功名。尽管这种方式很野蛮,但大规模的族际之间的通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2](P171)
3.诏许异族异姓通婚
为了使异族异姓通婚合法化,孝文帝于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癸丑颁发《禁同姓为婚诏》,明令同姓之婚娶“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4](卷7上《高祖纪上》,P153)自此,一场以胡汉通婚为主的民间族际通婚在北魏境内全面展开。太和二十年(496年)七月丁亥,孝文帝下诏:“又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4](卷7下《高祖纪下》,P180)孝文帝鼓励民间奔会(相当于现在的婚庆会),错过婚嫁年龄的男女可以在仲春二月奔会上寻找合适的伴侣。这在历代统治者中尚属首例。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北魏统治者诏许异族异姓通婚,但却严禁不同阶层通婚。北魏和平四年(463年)十二月辛丑,文成帝拓跋濬诏曰:“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4](卷5《高宗纪》,P122)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年)重申该禁令,严禁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和普通百姓通婚,“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4](卷7上《高祖纪上》,P145)这使得北魏族际通婚打上了明显的阶级烙印。
综上,如果缺少北魏王朝有意识地政府行为,民间族际通婚势必会大打折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融合未必会如此彻底。
结语
族际通婚打破了血缘、地域、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的界限,将不同种族、民族的人通过婚姻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北魏统治者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尊己贱彼”的民族狭隘境界中,而是以“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的兼容并包的民族平等理念,通过顶层和亲、上层联姻、民间通婚三管齐下,使族际通婚成为了北魏时期的社会生活常态。而族际通婚是民族融合的最佳途径。通过族际通婚,改善了民族关系,缓和了民族矛盾,各民族人民很自然地相亲相近,有序地融合在一起。正是在族际通婚的基础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平城作为北魏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族宗室、权贵云集,普通民众则杂居其中,遂成为族际通婚的中心。平城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民族融合的历史重任,在北魏定都97年时间内,将北方数十个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平城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上功绩卓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无愧于中国民族融合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