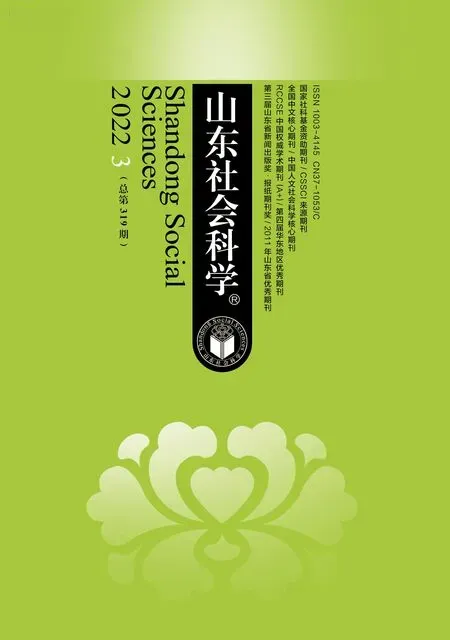永井荷风的洁癖与复仇
——《断肠亭日乘》中的日常抵抗及其限度
王升远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巨大(1917.9.16—1959.4.29)的七卷本鸿篇,永井荷风的日记《断肠亭日乘》(以下简称《日乘》)确是考察战时日本知识人精神史的重要文学、思想文本。但反过来看,作为问题意识的“战争”只能是观察、阐释该作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由是,当研究者以战争之名对文本进行切割(1)学术界有关《断肠亭日乘》的版本问题、学界研究之得失,以及永井荷风在文化立场、文明批评意义上的时局观察与评论,参见王升远:《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中的现代日本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时,作为论旨的“抵抗”虽得以凸显,但简单的“刺激-回应”模式又有难觅研究对象精神源流之弊,荷风的抵抗、反战也因此而成为突兀的个体问题、战时现象,高山仰止却又似乎“不足为训”。研究者、文学史家为“不屈文士”塑像的潜在指向与《日乘》本有的日常性和一贯性遂形成了难以协调和解释的龃龉,这便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日记这一潜在写作与政治威压下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关系、文学创作、文化活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对应性?作家的活动、言论及其内向化写作之间是自洽的,还是断裂的?抵抗是战时独有的观念性存在,还是贯穿其人生的基本生活姿态和价值取向?既未入狱、殒命,又不愿与强权合作并为之张目,作为战时为数甚稀的“沉默者”,荷风的抵抗如何可能,又何以能从严酷的战时思想、言论统制中全身而退,其抵抗又有着怎样的限度?作为知识人,荷风的个案是可复制的吗?从观念和方法的层面来说,对前述诸问题的讨论将更具超越战时、超越日本之普遍意义。
就研究视野而言,长期以来的荷风研究基本是在将其作为唯美派作家、文明批评(2)《大辞林》将不同于欧美之义的“文明批评”定义为:“揭示、评价世相、文化现象、意识倾向之意义与本质的批评。很多情况下,是以传统抑或外国为基准重审现代,通过专门的学问领域批评现代状况。”家和战时不合作者三个互不关联的向度下展开的,人们带着明确的理论预设、文学史标签从荷风文学中寻得自家观念的对应物。然而,《日乘》是一部永井荷风的生活、精神自传,更是一个知识人、文学家所有面向的复杂交错与综合,它天然地拒绝了后来者的切割、剪裁抑或节选。(3)《断肠亭日乘》此前未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全译本,仅在中译本文集《断肠亭记》中收入了选译的极少部分内容,以呈现荷风全貌之一斑。参见[日]永井荷风:《断肠亭记》,汪正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58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试图将《日乘》作为相对完整且有着其内在源流、脉络和逻辑的精神史文本,将战争时期仅作为荷风生涯的一个阶段,将战时抵抗作为其生平中长时段日常抵抗的一部分进行整合性、联动性的考察,据此在剧变的时代探寻某些“不变”的精神质素。较之于诸种特定语境下的战败日记、疏散日记等,荷风之沉默抵抗正因其日常性、长期性、策略性而独具异彩,解码这部荷风留给后来者的遗书,探究“极端语境下的个人”何以可能,无疑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到一个具体、生动的个体立场,在《日乘》的日常性中为文豪永井荷风降维,在时代语境、政治场域与文坛生态融通的视野中,发现其生活感觉、文艺观念、世界视野与其政治态度、战争认知、现实抉择之间复杂纠葛的内在联系,揭橥其日常抵抗的观念源流与实践限度,即是本文的关切所在。
一、吾道不孤:世界主义视域下“现代日本”的形神、敌友
1944年,日本已陷入战争的泥沼不可自拔,败象尽显。是年8月4日例行曝书时,荷风颇感神伤:“念及明治文化未几将亡,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心中只有无尽的绝望、失落和不舍。回望日本人之过往,日本文化唯有受到海外思想感化时方得发展。奈良朝佛教之盛、江户时代儒教之兴、明治时代导入西洋文化之灿皆可为证。海外思想感化衰落之际,日本国内则必成戎马倥偬之地。”(4)永井壮吉:『断腸亭日乗』(第5巻)、岩波書店1981年版、第471-472頁。永井壮吉乃荷风本名。下文引述荷风日记,均为此版本,不再另注,随文标注日记日期与卷数、页码。此前因制作毛笔的羊毛无法从中国进货,荷风甚至一度哀叹“日本文化灭亡之日不远矣”(1943.4.7,卷五:337)。在文化最终败给了武力、战火之时,他追念的乃是大正时期其所百般揶揄(5)昭和初年,荷风所批判的正是延续了明治遗风、大正文化惯性的激进西化、“和洋折衷”美学、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化中的选择性问题。从对歌剧自西徂东橘枳之变的嘲讽,到日人以剽窃西人为能事、开国六十年无一发明的齿冷,他基于生活实感、日常观察,对日本“外发的近代化”“仿制的现代性”及其造就的生活畸态百般揶揄。参见:1919.1.29(卷一:120);1925.10.12(卷一:388);1925.12.23(卷一:419);1926.11.20(卷二:80);1928.12.2(卷二:302);1946.4.28(卷六:136)。进而,现代日本人学艺有始无终、朝三暮四导致的本末倒置、形神乖离、见利忘义,无不在其批判射程之内。参见:1928.2.3(卷二:214);1929.9.7(卷二:358);1929.10.28(卷二:366);1930.4.4(卷二:396);1930.6.17(卷二:407);1939.8.31(卷四:405)。的明治日本曾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深知,开放乃有和平之日与斯文之盛,锁国致有兵燹之灾和思想之衰,这是其兼有东、西文化教养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所赋予他的国际视野,也是“过去的日本”文化之昌兴昭示的历史经验。较之于明治时期无主体性地吸纳西洋文明,开放性之丧失所导致的僵化、一元化则意味着更大的文明危机。
在关于“日本何以至此”的追问中,荷风发现“现代日本”之堕落与西方亦不无干系:在日、西的诸般相遇中,现代社会的粗鄙、暴戾乃“江户往昔与西洋当下的恶习偶然汇聚一处”(1925.12.17,卷一:414)的结果;而文艺界之堕落则是因从业者缺乏理解江户文学和西方骑士气质的能力(1929.1.31,卷二:320)。这是荷风长期以来兼有“西洋崇拜”和江户趣味双重偏好(6)在1904年4月26日致友人生田葵山的信中,荷风坦言自己既有时髦的“西洋崇拜”倾向,又有保守的江户趣味(参见『荷風全集』25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14頁)。当然,荷风的江户趣味中是否也有对旅法时期法国自19世纪中期以降日本趣味的逆输入,恐怕也是值得关注的视角。的观念对应物。遗憾的是,他发现“现代日本”并未从其先贤和中、欧诸国赓续美德良俗,反倒熏染了古今内外的诸多恶习。(7)尽管在文化层面对中国心向往之,但《日乘》中,中国并不是“恶习”意义上的缺席者,在论及军国主义暴政、“武断政治”时,荷风便常以秦始皇讽喻之。参见:1934.11.10(卷三:404);1940.8.7(卷五:56);1943.12.31(卷五:419);1944.1.25(卷五:429)。其中,典型的案例便是暗杀。1923年,在难波大助因狙击皇太子裕仁的“虎门事件”(8)“虎门事件”,指1923年12月27日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在麹町区虎门外狙击时任摄政王的皇太子裕仁(后成为昭和天皇)的暗杀事件。被执行死刑三日后,荷风记曰:“现代日本人生活,无论大事小情,无不模仿欧洲文明之皮相,大助的犯罪只是其一端。”(1924.11.16,卷一:344)1932年二三月间,前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团琢磨先后遭暗杀(即“血盟团事件”)。在得知两案凶手皆为水户人时,他认为,“水户人原本就嗜杀,自安政年间的樱田事变以来就不少见。凡事利弊相伴,时至昭和当下,水户人依旧嗜杀。总之,此乃水户儒学之余弊”(1932.3.5,卷三:90)。“血盟团事件”两月后又发生了“五一五事件”,《日乘》对此评论称:“近年来暗杀事件频发,不逊于明治维新前后。……有人说,此番军人之暴行乃是效仿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我国现代社会大小事件无不模仿西洋,像模仿意大利法西斯这种事情毫不足怪。也有人说,暗杀乃我国古来之特技,并非模仿。”(1932.5.15,卷三:132—133)时值1932年,甲午中日战争以降频仍的对外征伐让荷风忧心忡忡:“风闻日本陆军已将从满洲到蒙古的土地纳入囊中,威压俄国。但愿日本不要穷兵黩武,重蹈德意志帝国的覆辙”(1932.4.9,卷三:112—113)。1940年9月,德、意两国已从30年代荷风警惕、恐惧与嘲讽的恶友(9)参见:1936.11.27(卷四:112);1937,11.7(卷四:224);1939.5.10(卷四:377);1939.8.28(卷四:404);1940.4.30(卷五:32);1941.1.25(卷五:135);1943.3.31(卷五:336)。,成为现实中日本的盟友。闻知三国结盟之讯,他愤然记曰:“风闻日本与德、意两国缔结了盟约。(以下为栏外所补)爱国者们常言,日本有举世无双的日本精神,无须仿效外国。然此番却自愿卑躬屈膝,与侵略不仁之国缔结盟约,国家之耻莫此为甚。其原因虽不一而足,但我认为终究还是儒教衰灭的结果。”(1940.9.28,卷五:74)由此不难窥知,荷风反对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的道德基础乃是儒家“仁”的观念。1932年10月,阅读到报纸上关于“满洲外交问题”的报道时,他列举动物界诸般实例,论证“弱肉未必会被强食”(1932.10.3,卷三:169—170),据此批评日本的“满洲”政策。战败后回望过往,荷风自称,“我并非世上所说的爱国者,亦非英美崇拜者(10)荷风确非英美崇拜者,《日乘》中对其没有实感的英国所论甚少,倒时见其对美国的批评。较之于法国,无论是对留美时期部分美国学生不讲礼仪的回忆(1928.6.29,卷二:266),还是对美国新兴都市无雅致可言的评论(1932.9.11,卷三:163),都可见荷风对新兴强国美国的人情、世风并无太高评价。另外,尽管荷风在日记中不断呼吁美国以战争的形式给日本以最深刻的教训,但依然会批评美国禁止古巴使用本国语言唱歌(1941.2.4,卷五:139),愤慨于占领日本的“美夷”挑逗日本舞女等恃强凌弱的做派(1949.10.3,卷六:309),这与其人道主义精神、自由意志是始终如一的。事实上,荷风对美国文化的反感也是溢于言表的,详见下注。,只是不禁会有怜悯被欺者、抑强救弱之心”(1945.9.28,卷五:83)。前述诸引文明示了荷风对强权侵略的抗逆、站在弱者一方并为之鼓与呼的悲悯乃是出于儒家式的恻隐之心、仁爱思想和西洋式的人道主义观念。
如果说对德、意法西斯恃强凌弱之痛恶折射出的是这一观念的一面,那么对中、朝、法、荷、波等受侵略诸弱国的同情则是呈现出了另一面。从这个意义上,就应对荷风“反战”这一复杂的观念做进一步辨析。首先,较之于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力量强弱对比的考量,他对侵略战争的批判首先是在文化和道义层面展开的。荷风对法国的游学生活、人物风度、文艺情致的怀恋、倾倒和认同,以及对法国文学的偏嗜是人所共知的,在风雨如晦的极端年代,法国文学也曾使他获得了难得的精神慰藉。(11)荷风对法国生活、人物、文艺情致的怀恋和倾倒可参见:1919.9.24(卷一:142-143);1919.12.6(卷一:152);1922.2.13(卷一:224);1922.3.20(卷一:229);1926.12.20(卷二:89);1935.1.14(卷三:425);1943.4.17(卷五:340);1943.5.6(卷五:345);1944.8.25(卷五:480)等。关于荷风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的阅读史,日本学者已有充分的整理可资参阅,参见志保田務、赤瀬雅子:『大正期作家の読書遍歴に関する書誌的研究——荷風の読書遍歴書誌』(その一~七)、『総合研究所報』第12巻第3号~第14巻第3号(1987.3.31~1989.3.31)。其中尤须强调的是,荷风对法国文艺的偏爱是建立在与英国、美国、俄国文艺比较的基础上的。游学美、法期间,荷风发现:较之于托尔斯泰式的沉郁,法国悲剧的华丽更适合自己(致生田葵山,1904年4月26日);较之于英国文学的宗教性,法国文学的典雅更适合自己(致生田葵山,1905年4月13日);美国戏剧偶见名伶,而法国的卓越则是整体性的(致西村渚山,1908年4月17日;致西村惠次郎,1908年4月17日);美国的文艺皆是对欧洲的照搬或模仿,尽管在工业、电气等方面几乎是全球第一,但“一见到实物,则诗兴荡然无存,全无写作之念”(致西村惠次郎,1905年4月1日)。参见『荷風全集』(第25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15、18、31、125-126、96-97頁。由此可知,能否激发诗兴,是荷风异国观察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视角。此外,鹿岛茂的看法也可作为一种参考,他认为,“荷风对巴黎的憧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到了纽约的上流社会视线的影响并为之所同化,他们怀有巴黎憧憬,并以此轻视自己纽约的同伴。”参见川本三郎、鹿島茂:「『近代の誕生』、『荷風』の成立」、『ユリイカ』1969年3月号、第100-101頁。同样地,荷风对战时法国之命运亦拳拳在念,极为在意周围人士、日本媒体对欧洲战场尤其是德法战况的评论、报道倾向,为欧美反德军事力量的胜果感到振奋,尤其心盼法国获胜。(12)参见:1939.10.18(卷四:416);1940.5.16(卷五:34-35);1940.5.19(卷五:35);1940.6.19(卷五:43)。另外,荷风深知,“欧罗巴全面停战之日,日本的社会状态也自会转变”,也就是说,关注欧洲战局,实则也是在关切本国命运(1941.6.15,卷五:176-177)。此情就像在闻知德波开战后,他旋即“祈祷肖邦、显克微支的祖国拥有胜利之荣光”(1939.9.2,卷四:406)一样。事实上,战时对法国的遥念中内隐着他对自由国度、文艺圣地沦陷之痛惜,毕竟早在明治末期,对荷风的文学立场、政治抵抗构成观念支撑的正是左拉、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法国文学巨匠。(13)参见永井荷風:「フランス物語の発売禁止」(『読売新聞』1909年4月11日初出)、『荷風全集』(第26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89頁。而落实到实践层面,荷风在德、法之间的道义倾向展现在对自家文学外译的抉择上:
1941.11.19:国际文化振兴会一位名叫黑田清的人来传话说,德国人Oscar Beur(14)根据永井荷风日记中的记载以及在日时间推测,此人可能为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奥斯卡·贝尔(Oscar Benl),记录之误。贝尔是德国的日本学家。1933年,贝尔在慕尼黑和汉堡学习法律,1935年修习汉学。1937年至1940年,贝尔又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古典文学。返德后,贝尔于1941年至1945年在汉堡大学日本语言和文化系担任研究助理,并于1943年以《世阿弥的艺术理想》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至1945年,贝尔曾服兵役(包括担任国防军的翻译),1944年他受雇于德国驻东京大使馆。这一经历为其与荷风的相识提供了契机。想翻译拙作小说《面影》,希望得到我的授权。我不希望拙作被德国人读到,因此礼貌地回绝了。(卷五:233)
1941.11.26:这次是文艺会馆出面斡旋德国人翻译拙著《面影》一事,复信回绝。我的作品还是被德国人盯上了,真是可怕又可悲。(卷五:235)
1942.4.2:又有一位在东京的德国人希望把我的旧著《两个妻子》以及《新桥夜话》中的《美男》一篇译为德文。若是法国人将其译为法文,我会喜不自胜。真是身不由己。(卷五:263)
1944.6.12:今天的演奏会上,有人介绍了一位年轻的德国人与我相识,他自称研究日本文学,想把我的旧作《隅田川》译为德文。(卷五:451—452)
1944.8.19:菅原君来聊天,他给我看了法译《牡丹客》之评论(NRF1927年8月号的剪报)……[荷风引述了法国评论家马塞尔·阿兰对其作品之评论,以下为其内容节译]我读了这部短篇,想起了德彪西的一支曲子。以如此单纯的手法却能表现如此悲壮之美,盖可谓艺术上极度洗练之作矣。(卷五:477—479)
1947.6.10:德国人库尔特·迈斯纳来信说想翻译我的旧作《较量》和《两个妻子》,并在汉堡出版。他曾在昭和十七八年左右翻译过《新桥夜话》中的一篇《美男》,我便回信答应授权于他。(卷六:198—199)
上述诸引文均未见删改。由此不难看出:一、出于对纳粹德国的强烈憎恶,1941年荷风对其作品德译事宜一度敬谢不敏,但从其1947年6月的日记反推,1942年4月两部作品之德译最终还是得以实施,而“身不由己”之叹正暗示了其天人交战之际的晦暗心境和无奈屈从的现实抉择;二、《日乘》中,他明确记录了拒绝德译的回复,却并未明确记下自己的迎拒抉择,面对彼时现实与后世读者之心态曲折,颇值得玩味;三、相比之下,他更关注、乐见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尽管因时局之故,对德国会“身不由己”,但对法国的爱恋则是毫不犹豫的;四、战后,他对德国的憎恶和警惕因其战败始有缓解,对彼方的译介请求做出了慨允的姿态。鲜少涉猎德国文学的他,甚至在1946年开始通过英译和法译本接触彼邦文学(1946.11.8,卷六:159)。这就如同战后荷风对美国宪兵在日暴行的认知,唐纳德·金指出,“荷风憎恶的对象始终是宪兵,而不是美国人。”(15)ドナルド·キ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芸春秋2009年版、第116頁。能做出这般理性区分者,在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战时、战后初期日本并不多见。
当然,“世界视野”也是荷风个人阅读史的一个主要特征,其读书趣味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便是西人所著日本论,由前文所引志保田务、赤濑雅子的书志学稽考足见其涉猎之广,这为荷风对本国风物、文艺、学术、社会、政治的认知和判断补充了必要的域外视角,而其中自然不乏会心之见。例如,法国海军士官皮埃尔·洛蒂对日本风土、生活的描述与自己归国之初的观感所见略同(1932.4.24,卷三:115—116);英国公使夫人弗雷泽的《日本游记》对国会开设前壮士横行之痛批甚合其意(1935.10.27,卷三:505);法国人安德烈·贝莱索尔在《日本日夜记》中对不笑时的日本人贪婪、阴鸷和不安之印象也与自己不谋而合(1936.3.10,卷五:33)。这种嘤鸣求友的姿态,使得荷风在艰难时世中获得了自我确认的世界视野。以读攻毒、开放包容的姿态实则是他面向污浊、暴戾、闭塞时代的对抗性阅读抑或补偿性摄取,而这种姿态几乎贯穿了《日乘》之始终。我们可以从其1919年5月12日的日记中略窥其意:
受野间五造翁之邀,去帝国剧场听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早就想听中华戏曲,今夜偶赏之,其艺术品质远在吾邦现时戏剧之上,格局宏大,可谓极有大陆风度,甚为感动,何也?我对日本现代文化常深感厌恶,而今更难以压抑对支那及西欧文物之景仰。此感素已有之,面对异邦优秀艺术,必会生此感慨。然居于日本现代帝都尚能安享晚年,只因有不严肃的江户时代艺术之故。川柳、狂歌、春画、三弦,皆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值得其他民族一观。若要安稳无事地住在日本,须从这般艺术中寻得一丝慰藉。(卷一:129—130)
就像对自家文学世界地位的审视和省思(1935.1.14,卷三:425;1945.12.8,卷六:110)一样,荷风对“日本现代文化”的认知背后始终隐置着一个宏大的世界坐标,自家创作、各国文学与文化价值皆可在此获得恰切的认知和冷静的估价。在民族主义风潮席卷一切的时代,世界文学中的永井荷风、世界格局中的日本,这种超脱单边民族情感抑或敌我二元认知框架的世界主义文化视野、世界公民意识殊为可贵。可以说,荷风与“现代日本”的对峙,也是世界主义观念与日本军国主义风潮对峙的缩影。
视野关乎判断,而判断攸关责任。一般日本国民眼中在亚洲攻城略地、英勇无畏的皇军在荷风的世界主义视野透视下,就成了害人害己的“和寇”(1941.3.24,卷五:151;1943.2.3,卷五:318)和愚昧、冲动、狼奔豕突、一味破坏国际秩序的“老鼠”(1941.1.18,卷五:137;1944.5.30,卷五:450),一如其对进城“乡下人”的蔑称。事实上,对于日本打着正义的招牌侵略亚洲诸国之实质,荷风始终洞若观火,并“对如此傲慢无礼的民族以武力入寇邻国感到痛惜”(1941.6.20,卷五:179)。
慑于警宪力量,《日乘》中的诸多删改让今人难以准确把握荷风彼时的观察与见解。转折发生在1941年6月15日,读过喜多村筠庭的《筠庭杂录》后,他深为神泽杜口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精神所鼓舞:
读过之后,心中大惭。今年二月我把《杏花余香》一文投给了《中央公论》。世人读了此文,方知我多年来有记日记之习,亦不无欲窥知我对时局持何意见、每日记录何事者。我担心出事,一天深夜起来删除了日记中愤愤不平之辞,还会在外出之际,将日记藏到鞋柜中。今读《翁草》一文,甚感惭愧,今日以后,我将毫无忌惮地记录心中之所想,以为后世史家提供资料。
此番日支战争,始于日军暗杀张作霖、侵略满洲。日军以“膺惩暴支”为名,开始侵略支那领土。长期作战后俄而又换了名目,祭出了“圣战”这般无意义的辞令。日本政府乘欧战之后英军不振,企图在德、意的旗帜之下侵略南洋。然,此皆无知军人和残暴壮士之所愿,而非一般人民所乐见者。一般国民服从于政府命令,吃着米饭而不抱怨,那是恐惧的结果,是看到麻布联队叛乱之状而恐惧的结果。而今,他们打出忠孝的招牌讨好新政府,是因急于赚上一笔之故。日本人原本就没有理想,将追随强者安闲度日视为首要追求。对一般人民而言,这次的政治革新和戊辰革命别无二致。(卷五:176—177)
上述引文交代了删改日记之缘由,其间不难看出荷风曾有的畏惧,以及无畏的精神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名实背离的欺瞒行径以及人性和国家行为中的伪善深恶痛绝,如其所言,“我生来就有洁癖,不喜欢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1936.9.5,卷四:87)。对其叔父阪本钐之助在贵族院大讲仁义道德、实则私德败坏的批判,对日本政府成天高呼正义和人道的愤怒,对出版界挂羊头卖狗肉风气的齿冷,对政治家假借社会公益之名满足私欲的嘲讽,对日本假借和平之名、以国家名义作恶之实质的揭露,对战后美国人嘴上说着民政自由而一旦对自己不利便忙不迭掩盖的丑行,(16)参见:1926.1.4(卷二:7);1929.9.19(卷二:360);1932.10.3(卷三:169);1936.9.5(卷四:87);1943.7.5(卷五:361);1946.4.6(卷六:132-133)。他皆以真率之气直指虚伪之风,不唯日本是责,这与其对明治近代化批判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
其次,较之于法国,尽管长期耽读中国古典,荷风对近代以降尤其是同时代的中国、朝鲜着墨并不多。在《日乘》有限的记录中,无论是对朝鲜人要求民族自治的同情,还是对日本人虐杀中国人之批判,(17)参见:1918.5.4(卷一:91);1921.6.2(卷一:198-199);1939.1.28(卷四:356);1939.4.7(卷四:371);1941.2.4(卷五:138-139)。无不与荷风对弱小民族的仁爱之心、人道主义观念等平素主张始终如一。而在对日本侵略亚洲诸国的评论中,荷风反战的基本观念已不难窥见:
1939.9.25:归途的电车里碰到两个醉汉。女车长见之,马上拿来一个沙袋,把沙子撒在(呕吐物——引者)上面。沙袋貌似是其一直备在车里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见到这般乘客,也绝对看不到做着这般准备的车。(以下三行强剪切)每次看到这般丑态,我都对这个民族的海外发展高兴不起来。(以上为栏外补写)(卷四:411)
1940.4.18:这孩子(邻居奥地利人家孩子——引者注)近来与日本小学生交往,在我家门前扔球时,举止甚为恶劣。(此间强删除16行,以下为栏外补写)这一实例明确地告诉我们,接受日本式教育者皆野蛮粗暴。我对日本侵略支那、朝鲜感到不悦,就是担心这些恶劣影响殃及亚洲其他国家。(卷五:84)
1941.7.25:今晚听人说,日军已经侵入了法属印度和荷属印度……若传闻是真,日军之所为无异于是趁欧洲战乱打劫的强盗,乘人之危大逞私欲,全无仁爱之心。这种残忍无情的行为很快就会影响到日本国内每个人的性行,似乎是在暗中教唆人们可以去做强盗。(卷五:192)
1943.10.12:去年以来,随着军人政府的压迫日甚一日,终不堪精神之苦,以至于不得不寻求慰藉之道。耶稣教讲的是弱者面对强者压迫而取得的胜利。此教不逞兵力却让欧洲全土信服,这与现代日本人侵略支那大陆、南洋诸岛的行径大异其趣。(卷五:391)
1944.1.2:痛批时势的信件与贺年卡一道纷至沓来,皆是陌生人所寄。概括起来,其大意如下:……以此次文艺杂志统统遭禁推测,似是将学术文艺视同无用之物。视文学为无用之物,是在防止思想的变迁,阻碍文化之进步。现代日本无异于回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不知如此愚昧暴虐之举是否真能成功。若成功,则国家将走向衰亡。断然实施这般愚行的国家单以武力便能治理得了支那、印度和南洋诸民族吗?(卷五:424)
前已论及,以1941年6月15日为分水岭,荷风决定不再删改日记。由上述引文即可清晰地看到此前此后的变化痕迹,补写的部分虽难以复原最初文意,但循其文脉不难推断,应是对“现代日本人”国民性和社会风习的强烈批判。在他看来,民间的恶习、劣行与国家层面缺乏仁爱之心的强盗逻辑是相表里的;而让其叹服的唯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和宗教力量,而非基于物力、战力压迫关系的丛林法则。面对侵略战争,荷风对社会风习、世道人心、文艺审美、宗教信仰的关注,正出自文学家文明批判、社会批判、审美批判的视角,是一种以文化之力否定暴力的取径。
事实上,这种基于生活体验与实感的内向批评在战时并不多见。加藤周一曾指出,“在日本的知识分子身上,现实生活和思想是互相脱离的。因此,处在危机的情况下,思想便屈服于来自现实生活方面的要求。……这就是知识分子对战争进行合作这一事实的内部结构。”(18)[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杨铁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与之相对应,将生活、审美、思想贯通为一的荷风之历史意义便不难窥知了。但同时亦须注意,这里的生活并非单指艰难困顿的战时生活。唐纳德·金认为,“对永井荷风而言,这场战争只意味着军部让其生活变得不便,舍此无他。曾经一直作如是观的荷风,在自己的房屋化为灰烬时,方知战争为何物”,“因为战争,荷风像乞丐一般,对他人所给的哪怕一丁点食物都满心欢喜。他憎恨让事态恶化至此的那些人,因此得知了战败的消息,荷风要庆祝一番”。(19)ドナルド·キ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芸春秋2009年版、第115、119頁。同为“战中派”的唐纳德·金所强调的自然是荷风的战争实感。战争所带来的生活之不便虽是荷风在《日乘》中反复记录的(20)参见:1941.4.11(卷五:158);1941.5.23(卷五:171);1943.6.11(卷五:272);1943.7.30(卷五:369);1944.3.21(卷五:437);1944.11.3(卷五:500);1944.12.26(卷五:509)。在战时艰难的生活中,独居且对饮食考究的荷风常靠友人接济肉禽蛋奶等生活物资。,但若仅以此立论,显然低估、窄化了其战争认知的历史纵深和视野广度,及其批判和抵抗的长期性。
二、“规格外的爱国者”:极端时代的怕与爱、抵抗与妥协
不逐时流的乖僻、孤高,社交上的过度敏感、洁癖和执拗,加之对文坛、舆论界、出版界浊气日盛的绝望,除屈指可数的几位挚友之外,1914年后荷风与周边亲友长期处于疏离甚或紧张的状态。(21)除了前述与叔父阪本钐三郎的紧张关系,荷风还与其胞弟威三郎绝交,水火不容,并因母亲与威三郎同住,甚至在其母病笃弥留之际拒绝前往探视,又因威三郎在场而拒绝参加叔父葬礼。此外,他对家中其他亲戚也尽量避见。参见:1922.12.22(卷一:258);1936.12.16(卷四:117);1937.3.18(卷四:146); 1937.4.30(卷四:160-161);1944.3.14(卷五:436);1947.4.3(卷四:153)。尽管早在游学美国时期,这位文坛新人即已在致诸师友的书简中反复强调文坛生存中的政治手腕、权力因素的重要性,并为之感到心忧和焦虑,(22)「西村恵次郎宛」(1905年3月27日)、「生田葵山宛」(1905年4月13日)、『荷風全集』(第25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96-97、14頁。但归国后,丰厚的家资和不菲的稿费、版税确保了他衣食无忧、自立自尊的日常生活,而对权力的疏远、对清净文学创作生活的向往更使其与以菊池宽为代表的主流文艺界以及新闻界、出版界关系不洽。“可笑”“可悲”“断交”“绝交”等字眼频现于《日乘》之中,他企盼文艺的独立(1929.4.4,卷二:330),警惕商业主义和政治权力对文艺的不断侵蚀,抗拒权势者(23)除了自身拒绝菊池宽等文坛当权者的诱惑、收编外,另有两例。其一,荷风的精神偶像是其恩师森鸥外。1918年,他接到森鸥外来信,得知其要“进入宫内省,出任帝室博物馆馆长,其后将完全脱离文笔生涯,悲哀之情莫名难抑”(1918.1.24,卷一:85-86),而据《日乘》记录,森鸥外逝前的“临终口授”中希望自己的离世勿与宫内省、陆军扯上干系(1933.12.17,卷三:293)。其二,1941年10月18日还在日记中记录“日美开战的传言愈发多了起来”的荷风在翌日去参谒了栗本锄云之墓(1941.10.19,卷五:216)。幕末时代,栗本曾活跃在日法外交舞台上,成就卓著;明治政府成立后,誓忠于幕府的栗本拒绝了新政府的出仕邀请,过起了隐遁的生活。关于以上二人,荷风虽未做进一步评论展开,但从中不难看出其对权力的淡漠态度。的收编,甚至一度欲从文坛隐退。(24)参见:1919.6.29(卷一:134);1924.11.24(卷一:345);1925.6.15(卷一:371);1925.9.9(卷一:381);1925.9.23(卷一:383);1925.10.16(卷一:390);1925.10.24(卷一:391);1925.11.13(卷一:398);1926.8.11(卷二:54);1927.4.6(卷二:123);1927.8.12(卷二:149);1927.10.10(卷二:166-167);1928.1.22(卷二:210);1928.1.25(卷二:212、214);1928.9.7(卷二:286);1928.11.31(卷二:311-312);1929.1.27(卷二:319);1929.4.3(卷二:330);1929.5.22(卷二:342);1930.1.24(卷二:380-381);1933.11.17(卷三:276);1934.9.9(卷三:380-381);1934.10.2(卷三:385);1935.5.29(卷三:458);1936.12.14(卷四:116);1940.4.10(卷五:28);1943.12.7(卷五:412);1944.10.12(卷五:494-495)。当然,据其交代,从文坛隐退的直接原因乃受“二·二六事变”之影响。(1942.11.24,卷五:297)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丰厚的家资、孤高的做派、沉湎花柳巷的浪荡生活、对社会的“冷笑”(25)《日乘》1936年7月2日(卷四:73-74)中记录了《文艺春秋》刊文对他的酷评,批评其对社会报以冷笑、对社会缺乏正义感,社会应将其埋葬;当今社会不应再允许其仗着财产为所欲为云云。经核实,此文实为:『昭和人物月旦·永井荷風』、『文藝春秋』1929年4月号、第149-150頁。,加之文学创作中的情色题材,使荷风在赢得众多读者、收获巨大名声之同时,自身行止、道德也成了文坛、媒体甚至政客所瞩目的话题。《日乘》中一一记录了包括菊池宽、小山内薰等文坛朋侪对自己的酷评(26)参见:1928.7.6(卷二:269);1929.3.27(卷二:328); 1938.10.20(卷四:319-320)。——显然,他是介意的。
然而,不惮与文坛对立的荷风并非无畏。在1919年决计效仿江户戏作家的日记中,他已强调了“天下人心日渐凶恶,眼红富贵”(1919.4.6,卷一:125—126),显然早在是时,荷风已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层面的“恶意”。如前所述,“大逆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隐遁避世的处世姿态,而随着军部的抬头及其暴政的深广铺展,《日乘》中时见抽签卜命之记录,全面侵华战争后言论、思想统治的日益严酷更使其对笔祸的畏惧日甚一日,(27)参见:1938.9.6(卷四:307);1940.10.24(卷五:88);1941.1.27(卷五:137);1942.2.21(卷五:256)。避祸自保遂成为现实谋身之策。应注意的是,荷风的时势判断和现实因应多受文坛先辈的前车之鉴启发。1928年,他将政党腐败、大道不行的彼时比之于幕府末年,认为全身之计唯有效仿安井息轩、成岛柳北,深藏功名之心,遁世自娱(1928.4.10,卷二:242);1934年,他把军部暴政相形于幕府,尤恐重蹈寺门静轩、为永春水之覆辙(1934.11.6,卷三:403;1938.10.20,卷四:319—320);1935年,他悟到要保全自己,须有江户人一般洞明世事的通透与洒脱(1935.5.10,卷三:451)。尽管荷风早在1928年已然意识到“日后发表乘兴而作的闲情文字须当谨慎”(1928.7.11,卷二:273),生活中亦离群索居、远离公众视线,但30年代以降,因文艺和言论审查制度的不断强化、媒体和右翼团体对其创作和生活的关注、文坛同行因言获罪的震慑、特高警察的无孔不入、树敌甚多并开罪于菊池宽等文坛权势者种种,当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员、“专制政治威胁到操觚者的生活”(1940.10.30,卷五:89—90)时,他依然对自身安危忧惧不已(28)参见:1934.7.23(卷三:366);1934.10.22(卷三:393);1934.11.10(卷三:304);1936.3.27(卷四:37);1936.9.23(卷四:94);1939.8.3(卷四:397-398)。——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为此,在谨慎自诫之余,荷风甚至一度蛰伏于花柳巷(1940.7.1,卷五:45)。
此外,尽管荷风在1941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决定“今日以后,我将毫无忌惮地记录心中之所想”,但其后他实则并未“毫无忌惮”。唐纳德·金注意到,“荷风日记所记录的事情,很多都只不过是传闻”(29)ドナルド·キ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芸春秋2009年版、第116頁。,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日乘》中的风闻性记录在1941年6月15日后骤增乃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调整。细读此后的日记会发现,凡涉及对时局、敏感人物的批判性观点,《日乘》常援引街谈巷议抑或师友(隐去姓名)在信件和明信片中的论调等嘲弄戏讽。较之于此前“直言—删改—补写”之曲折,这种隐晦的春秋笔法显然是荷风内心深处难以明言的畏惧心理、自保意识以及为后世留下史料的证言意识对冲、折中的产物。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和伤害(如被壮士殴打),虽心有抵触,但意识到时势之变的荷风依然会像常人一样,买好国旗和礼服以备不时之需(1935.2.3,卷三:429—430);对于巡警和邻组的诗笺索求,虽不情愿,但大多遂其所请(1925.10.21,卷一:391;1944.7.18,卷五:468);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面对“大日本中央文化联盟”以“公爵岛津某”的名义发出的邀约,以及“旅顺要塞司令部”索求题字之约,虽屡屡悲鸣“焚笔之日不远矣”“吾名为军人所知,可怕、可恶至极”,但依然带着畏惧之心从其所邀;(30)参见:1937.11.3(卷四:223);1940.1.13(卷五:9),此二日日记皆有修改和补写,因发生在1941年6月15决定不再删改日记之前,据这天日记的自述以及前两篇日记的文脉,推断应是因事涉敏感人物和机构而做的处理和补写。对日本诗人协会、文学报国会等组织强迫加入的做法,虽牢骚满腹、愤懑不已,但亦默从其计(1941.3.22,卷五:149—150;1943.5.17,卷五:346);虽对军部要求重印自己被打上花柳小说标签的作品《较量》用以赠送出征的士兵感到滑稽、苦涩,但亦未拂其意(1944.9.20,卷五:487)。对于有着洁癖的荷风而言,这恐怕已是其承受极限。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可能对个人生活安危构成实际威胁甚至起决定作用者,他以相对圆融和顺的姿态,以不与权力正面对立、对抗的妥协态度,最大限度地换取了个人的现实安全与自由。同时,尽管《日乘》的论说虽不无面向后世读者表明心志、自我塑造的潜在意图,但在不曾积极投身时局、追名逐利的意义上,荷风已是战时日本文坛难得的异例。
同时必须指出,在考察战时日本文学家的观念与实践(无论是“协力”抑或抵抗)时,论者常局限于对研究对象“作为”层面的考察,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所不为/言”的沉默层。但在极端语境下,底线意识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它意味着个人面对善恶时的道德良知底线和实践限度。面对难以反抗的恶,缄默无为意味着拒绝成为其认同者、胁从者。面对军国主义暴政之恶,荷风也会拒绝,兹举三例。
其一,拒绝赴中国战线视察的邀请。1938年2月27日,《日乘》记曰:“中央公论社佐藤氏来,劝我去支那战线视察。”(卷四:254)众所周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曾召集各大媒体和出版机构“恳谈”,要求举国一致“协力”战争,特派员、“笔部队”遂应运而生,其中的主导者便是荷风甚为厌恶的菊池宽。揆诸现实,或汲汲于名利,或畏惧于权势,文坛赴前线视察、写作者一时间如过江之鲫。《日乘》中虽未言明其如何回复过访者之动员,但由后续日记不难推断此行最终并未成行。其二,拒绝将身后财产捐给日本文坛。由于对本国同行深恶痛绝,1936年荷风曾在日记中草拟的、类似遗书的文字中明确提出,希望死后将个人财产全部捐赠给法国的龚古尔基金会(1936.2.24;卷四:29);三年后又在日记中嘲讽了文坛设立的菊池宽奖等文学奖项,再次表明个人遗产处置将与日本文坛无关(1939.3.10,卷四:365)。尽管荷风逝后,这一心愿似乎并未真正落实,但彼时其拒绝同流合污的意志是决绝的。其三,在国家战时面临物资困局、不断有人宣扬将贵重之物上交/卖给军国主义政府之时,断然拒绝。在他看来,“与其轻易交到官员手里换点钱,莫如扔掉”,并最终将烟管上的金子扔进了浅草川(1939.7.1,卷四:390),因为他深知捐赠后也只能变成官员和军人肥私之资。(31)参见:1939.4.16(卷四:372);1940.8.31(卷五:64);1940.12.5(卷五:116);1944.9.7(卷五:482)。由上可知,荷风对时代政治、文坛主流态度冷淡,不愿与之合作,成为支持军国主义暴政的分母。在战争末期,他对自己的淡漠态度有一番颇值得注目的自解:“如今再对军部横暴心怀愤慨实乃是愚蠢至极,唯有置之不理。作为复仇之举,我们只能对日本国家采取冷淡漠然的态度。”(1945.5.5,卷六:30)
那么,荷风对国家的冷漠是否等同于“不爱国”呢?实际上时值战时,他与时代政治的一个重大的分歧正表现在对爱国的不同理解上。就像保阪正康所指出的那样,“让荷风尤感不安的是爱国者们之恶趣味和幼稚的口号”(32)ドナルド·キ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芸春秋2009年版、第20頁。。昭和以降,他便不断在《日乘》中批评民间假借“忠君爱国”之名徇私害国的种种行径,难以忍受有伤于艺术的爱国文化和宣传,忧惧有害邦国的国家主义狂热分子和宗教人士,并对菊池宽、三木武吉等政治投机文人竞选议员、掌控舆论之动向深感忧虑。(33)参见:1928.2.13(卷二:220);1928.6.26(卷二:266);1929.2.11(卷二:321-322);1935.7.25(卷三:472);1938.10.8(卷四:317);1940.11.25(卷五:104);1941.1.26(卷五:135-136);1941.9.10(卷五:207-208);1943.7.5(卷五:360)。在此对立面上,1929年11月30日,外交官佐分利贞男(34)佐分利贞男系日本外交家,与荷风曾是一桥寻常中学同级生,曾在中国、俄国、法国从事外交工作,后历任外务省参事官、大使馆参事官、通商局长、条约局长等职,于1929年11月29日自杀。关于他自杀原因的传闻很多,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他对日本对华外交感到绝望。自杀翌日,荷风记曰:“他多年来身担剧职,担负国家重任,遂不能全其天寿。念及于此,反观自己多病之躯,徒贪余命,瓦全之叹甚切。”(卷二:370—371)1943年8月11日又记曰:“××××××(35)东都书房版此处处理为“政治家某某”(参见永井壮吉:『永井荷風日記』、東都書房1959年版、第169页),而参考岩波新版《日乘》方知,此二人实指野依秀一、三木武吉(参见永井壮吉:『新版断腸亭日乗』、岩波書店2002年版、第389頁)。这篇日记出现在1941年6月15日荷风表示不再删改日记之后,然而岩波旧版《日乘》出现这般处理,证实了荷风顾及战后新形势,而对涉及人事问题的部分做了一定的处理,但这并不妨碍《日乘》中情与理的连贯表达。二人送来了为捐献飞机集资的记事笺。世人皆知他们都是有前科的不良之民,国家存亡的危机终为这些不良分子提供了博名逐利之便。而吾人却没有机会对此次战争产生纯粹的感激之情,真令人浩叹无际。”(卷五:370)而在1941年4月9日的日记中又有如下记录:“终日阅读帕莱的《万国史》。……美国人热爱美国的诚挚之情蔼然动人,在表达爱国之心的著述中,此可谓最佳之作。日本殆无此类出版物。”(卷五:158)由此不难看出一个疏离世事者的忧患之心。荷风愤懑于伪爱国、实害国的虚伪奸诈之行,他期盼蔼然、诚挚、纯粹的爱国之心,敬慕务实谋国之士。
如前所述,荷风对日本帝国侵略亚洲的批判转向了对本国颓败的世道人心进一步恶化之隐忧,在群情激越的昭和初期,这一堪称异端的忧国姿态实则根植于明治时代。在发表于1909年的《新归国者日记》中,他严厉批评、嘲讽了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者”:
与其做弁庆那般强国之民,毋宁出生在被打了脑袋也可以毫无顾忌哭出来的国度。我绝非在诽谤自己的生身之国,不过是以人心之常,敬慕美好的事物。如果说国民的义务便是将祖国万事都赞美为至高无上的存在,那么,那些善男信女们便是最佳爱国者。教育他们学习比较判断的知识,或许就变成了可怕而罪恶的教唆吧。(36)永井荷風:『新帰朝者日記』、『荷風全集』(第4巻)より、岩波書店1964年版、第195頁。
这里,荷风强调的是基于“人心之常”自然生发的情感和自由无拘的选择,并明确提出了将“祖国”作为非绝对化的存在予以比较判断的认知倾向。尽管荷风深知与“善男信女们”相抗的现实风险,但1919年他依然在《晴日木屐》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观:“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将永远守护乡土之美、致力于国语之纯化和洗练作为第一要务。”(37)永井荷風:「日和下駄·夕陽 附 富士眺望」(初出:『三田文学』1919年6月号)、『荷風全集』(第13巻)より、岩波書店1963年版、第387頁。这一以守护社会、乡土、民族语言与文艺之美为着眼点的呼吁,与极端时代那些以国家利益之名谋求私利的伪爱国论调泾渭分明。而后者泛化导致的激越氛围让其绝难在言论层面与之公然分庭抗礼,只得“龙蛇以蛰,以存身也”。
然而,在狭隘爱国主义浪潮中韬晦避世殊非易事。《日乘》1941年5月16日载,“听说佐藤春夫在某报上发表了一篇给我惹事的论文,没有比不明事理的乡下人和醉酒发狂者更麻烦的人了”(卷五:170)。遗憾的是,因是“听说”,荷风并未给出有关此文的具体信息。值得玩味的是,在荷风逝世翌年(1960)出版的《小说永井荷风传》中,作者佐藤春夫专就此事做了一个极长的“自注”:
我的确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那篇评论。在抗议一切都按照规格行事的世相之后,我举了一个例子,旨在说明文学家爱国未必要去讨好军部,像荷风这样热爱祖国的风土、致力于国语纯化者皆是规格外的爱国者。他没读过我的文章,而是听了平井(平井程一——引者注)进行了一定歪曲后的意思。荷风原本就是一个偏执狂,不会原谅年轻人对他的评论。尤其是虽说是规格外,但把他说成其最厌恶的爱国者惹怒了他。……但不管荷风高兴还是恼怒,我相信他就是热爱国土之美、旨在纯化和美化国语的规格外的爱国者。(38)佐藤春夫:『小説永井荷風伝』(新潮社、1960年5月初版)、『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35巻)より、臨川書店2001年版、第332頁。
大野茂男考察了荷风与佐藤春夫的交游史,发现二人之龃龉乃因《荷风读本》一书的版税纠纷而起(参见1936.6.7/6.9,卷四:69—70),又因后者战时的投机趋时行径渐行渐远。(39)大野茂男:『荷風日記研究』、笠間書院1976年版、第138-139頁。大野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文脉,但围绕爱国之分歧的思想根由仍未被准确剖析。以下,我们对这桩文学史迷案略作辨析。
事实上,佐藤春夫的回忆中存在着一个记忆的讹误。那篇讨论荷风爱国问题的文章绝无可能发表在《时事新报》上,因为该报已于1936年12月停刊。依其所述内容以及事发时间推断、核实,此文应为1940年10月发表于《报知新闻》的《两种爱国形态》。是文中,佐藤在“自注”申辩中陈情之意固有之,然而另外一番陷荷风于险境的话则被其有意地遮蔽了:
爱国精神无二,但其表现形式千差万别。……我们大致能看到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本国之优长为傲并醉心于其中者。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爱国者类型,通常的官员、军人、教育家等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者皆为此类。
与此相对,还有一种稍显乖僻的爱国形态。他们对本国的不平、不满,无疑皆出于至诚的爱国之心,这些不幸爱国者乍一看就像在鞭挞自己所爱之物一般,会被误认为是不爱国之人。
……
永井荷风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是新体制的人物,在任何意义上把他看作过去历史上的人物都是毫无问题的。我想,对荷风散人来说,就连在这里提及他的名字都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他是唯一能代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代的日本文学家,正因如此,也无疑是最难适应现代时势的文学家。他很有自知之明,颇得韬晦保身之术。……
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极端的复杂性,有一次就把自己的印象坦诚地和盘托出,问道:“先生为什么看起来又像爱国者,却又不像?”听了我的愚问,他非常直截了当地答道:“我极爱我国的一切人情、风俗、风土、民众,但对我国一切的知识都极度厌恶。”我知道,不仅是他这一席话,其作品中的不少细节和主题都可印证其言。(40)佐藤春夫:「二つの愛国型」、『報知新聞』1940年10月23-24日。
这番看似回护荷风之辞,实则将这位无声无息地蛰伏保身、希图被世人遗忘者(1940.9.26,卷五:73)有声有色地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将对政治始终保持着遥远的兴趣而不曾与其贴身肉搏的荷风推向了“通常的官员、军人、教育家”、日本“一切的知识”生产者之对立面,甚至以其创作坐实了这一倾向。在言论、思想统制日益严苛的政治语境下,这将为评论对象带来怎样的难堪与风险不难想见。荷风所谓“给我惹事”“不明事理”之怨盖出于此。然而,这仍是“事”层面的浅层认知。若结合《日乘》中关于佐藤的另一些记录,我们或许可以潜入问题的“理”层面。自1931年11月8日第一次提及佐藤之名后,数年之间二人往来不断,其现实往来也未因1936年的版税纠纷而断绝,1937年《日乘》便有四次面晤的记录,而自1938年起面晤始减:
1938.8.28:午后佐藤慵斋(即春夫——引者)君来聊天。他说要跟几个文士一道乘军舰去汉口。(卷四:304)
1939.1.7:(引述佐藤门人平井程一的信,其间提及东京市长倡导的“大都会艺术”)汇聚旗下的都是菊池、吉屋、佐藤、西条这些乡下汉子,令人喷饭。(卷四:353)
1941.3.22:(日本诗人协会来信强迫加入)看了会员人名,从蒲原、土井、野口这些老人,到佐藤春夫、西条八十等年轻人都名列其间。在协会“宗旨书”中,处处可见“肇国精神”“国语净化”诸般文字。……今天他们所谓的诗,无非是近代西洋韵文体的日译或其模仿之作,没有西洋近代诗歌,就不会有日本诗歌的诞生,其出现与肇国精神全无关系,反倒促使国语走向浊化。……说佐藤春夫的诗致力于国语净化真可谓滑稽透顶。……现在才开始谈什么国语整理、国语净化为时已晚。(卷五:149—150)
1941.5.16:听说佐藤春夫在某报上发表了一篇给我惹事的论文,没有比不明事理的乡下人和醉酒发狂者更麻烦的人了。(卷五:170)
1943.11.12:听说佐藤春夫身着右翼壮士般的衣服到人群中宣扬皇道文学。(卷五:404)
由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一、荷风对佐藤的反感与武汉会战以降后者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马前卒并为之鸣锣开道的丑行似有直接关系,自此以后几无面晤;二、1919年前后荷风爱国观中的核心问题——国语纯化倡议,时过境迁后在战时语境下被协力战争的诗人组织、曾经的友人佐藤春夫等有意无意地嫁接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文脉而做了不当理解。事实上,在荷风看来,军国主义宣传口号正是让国语走向浊化的元凶,(41)《日乘》对“精忠”“至诚”“义勇奉公”“武运长久”“大东亚”“共荣圈”“殉国精神”“日本精神”等军国主义精神动员和宣传的核心词汇之滥用一一嘲讽、指斥。参见:1934.5.31(卷三:350);1941.6.11(卷五:175);1941.7.15(卷五:187-188);1941.9.7(卷五:207);1943.7.5(卷五:361);1944.10.11(卷五:493)。而这场运动的鼓动者之一便是佐藤。他以荷风最为反感的方式塑造的爱国者形象,实乃建立在“不正确理解”的嫁接之基础上,恐怕这才是二人交恶的深层逻辑。
战争中后期,“规格外的爱国者”荷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末路已有所预期。在他看来,“今天军人政府之所为颇似秦始皇政治。先是扑灭国内的文学艺术,继而必定会断然关闭剧场、烧毁债券,剥夺私有财产的。如此,日本就会灭亡”(1931.12.31,卷五:419)。1944年10月12日的日记引述了“某位忧国者”之言称,“国家组织为上流和劳动阶级所占、中产阶级消亡之日,便是国运倾覆之时,日本前途黯淡”(卷五:494)。在荷风看来,这正是历史教训以及战时生活实感不断传递、强化的认知。游学美国期间,他对美国工业实力、物力水平及其世界影响力的实感与理解(42)在1905年致友人西村惠次郎的信中,荷风直言,在工业、电器诸方面,美国有很多超越欧洲甚至独步世界的产品。参见:「西村恵次郎宛」(1905年4月1日)、『荷風全集』(第25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97-98頁。,更是其判断的直接经验依据。然而,由于言论环境的急转直下,他只能在日记及信任的友人圈子里表达真意。据秋庭太郎考证:“这一天,报纸号外报道了日美开战的消息。(并非这一天之事)荷风在银座的咖啡店与杉野橘太郎闲谈时,突然大放厥词:‘与美国开战真是太愚蠢了,必败无疑!’让杉野非常担心。这都是杉野亲口说的。”(43)秋庭太郎:『考証 永井荷風』下、岩波書店2010年版、第188頁。杉野之言应可采信,荷风的悲观论调与日记中的表述是一致的。尽管在日美开战之初的日记中,其笔调平静异常,但战争末期的1945年3月6日日记中,他借助邻组配给葡萄酒之事直言:“这就像未搞清敌国状况而开战般愚蠢,可笑、可怜又可怕。”(卷六:17)当以乡土、国语之名爱护、守护的国家日渐沦落,最终变成一个斯文已丧、穷兵黩武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时,荷风的爱国、忧国之心终以这样一种倒错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三、“偏奇”人生:“近代的自我”、里仁为美与“为良心和后世写作”
明治时代是激进西化的时代,尽管永井荷风曾长期激烈批判明治近代化之形神不一,但那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相对开放、包容的时代。桶谷秀昭指出,时至大正时期,日本“近代文明”开始发生“变质”。所谓“变质”,“并不是说这时有什么变了,什么都没变、也无法改变的内发性缺失状态,正意味着变质”(44)桶谷秀昭:『「断腸亭日乗」覚書——文明の変質と感受性の運命』、『海』1974年4月特大号、第187頁。。就在明治风度日渐随风消散、日本社会的开放性逐渐丧失的大正中期,永井荷风开始了《断肠亭日乘》的写作。
在这部留给后世史家的资料中,他以“为时代作证”的自觉意识,对日本剧变的世道人心、时代政治,从审美、道德和社会的层面展开了持续的、一贯的批判,让我们据此得以管窥大正、昭和时期荷风的精神史,甚至以此文本为透镜,理解彼时“政治权力—社会结构—个人世界”之间、“日本—世界”之间复杂、交错的多元关系。社会人口结构剧变,世道人心颓废,军阀政治崛起,政党政治腐败,“现代日本”的全面堕落使文明批评家荷风愤懑不平;而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使他更为认同江户戏作家们的游戏心态及其抉择,最终也被迫选择了与之相同的姿态——背对日益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压抑介入激情,隐遁、缄默。(45)参见王升远:《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中的现代日本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可以说,《日乘》正是与可怖的时代潮流难以构成对话关系的荷风,以“为鞋柜写作”的姿态面向后来者喊话的文本。为此,战争末期,在美军轰炸东京的炮火中,荷风拎着装有日记的手提包不顾一切地仓皇逃出,唯愿以此心史“留与世人”(1944.12.3,卷五:504)。
在1917年3月致友人籾山庭后的书简中,荷风即已坦言:“我们彼此都生于父祖积善之家,每天无须靠稿费过活。聊为堪遗后世之作,也无愧于良心。”(46)「籾山庭後宛」(1917年3月)、『荷風全集』(第25巻)より、岩波書店1965年版、第59頁。由此可见,荷风这种遗世独立、对良心与历史负责的写作姿态,是在《日乘》起笔写作(1917.9)之初便已有的自觉;而其家资的丰裕也确保了其说“不”的自由。唯此,荷风才得以从商业利益的牵绊、文坛政治的掣肘、群情激愤的裹挟中超脱而出、离群索居,保持着独立而清醒的自我和强韧的主体性,以其不变因应世间万变。川本三郎在与鹿岛茂的对谈中指出:
无论是颓废、恋爱还是贫民窟,荷风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这是近代的一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荷风是有着彻底的“近代的自我”的作家。……一天将要结束之时,必定将自己的体验如同他人之事一般写成作品,日复一日,才能与之保持距离。……常有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是以发表作品的意识来写日记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日乘》——引者)是完全为了自律、为了防止陷入颓废、为了彻底的读者视角、为了确保自己的位置写作的日记。(47)川本三郎、鹿島茂:「『近代の誕生』、『荷風』の成立」、『ユリイカ』1969年3月号、第106-107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荷风将日本、“此时”甚至自我相对化的背后乃是彻底的“近代的自我”。
与大部分选择热情投身时代政治洪流、博名逐利者相比,荷风的冷静判断还得益于其开阔的世界主义文化视野和崇古趣味。礼失求诸外,乐坏访诸古。荷风游学美、法的经历和对域外文史的广泛涉猎使其得以在更广阔的认知视野中确认自己的本土观察立场,并能将“现代日本”的文艺格调、文明状况、国力水平乃至政治得失予以历史化和相对化;而对中国文化、江户政治的深刻理解又使他得以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浪潮中发现、辨析东亚与欧洲的遗毒与良训,这让他穿透激越的时代情绪和魅惑的宣传口号,看清了日本侵略亚洲诸国的不义本质,区分了日本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真正敌友。
另须注意,文学家荷风的日常抵抗与战时反战之坚定、一贯,与其将生活感觉、生命体验、审美趣味和人物评骘、社会观察、政治批判贯通一处的认知倾向密不可分,强调“人心之常”,看重形神如一。所谓“理一分殊”,在他那里,世间万象凡有伤于“美”、有悖于“仁”者即为自己、日本(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乃至人类之敌,无问亲疏。(48)正如唐纳德·金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荷风自家房屋被毁,但他并不恨美国人,他所恨的常是开启了这场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参见ドナルド·キン:『日本人の戦争:作家の日記を読む』、角地幸男訳、文芸春秋2009年版、第83頁。《论语·里仁》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现代日本”世道人心的颓败、军国主义的暴政皆因有悖于此而被荷风唾弃。
当然,江户趣味的诗性视野也是利弊两端的。“江户儿”荷风对明治以降军阀政治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的认知与警惕,与戊辰战争对东京都市文化、日本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有着潜在的历史关联,永井家的幕臣家世乃是荷风“方法以前的方法”(49)在接受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访谈时,鹤见俊辅先提出了其战争体验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的家庭出身。他指出,“这是与我的思想和行动‘方法以前的方法’相关的,说它是原点也好、是制约也好。”参见[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同时,关于旧幕臣群体的忠诚观及其对维新的认识,可参见:[日]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然而,他对明治以降日本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政党—军队—国民多边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却有着文人论政的暧昧和感性,作为“局中人”难以揭示出天皇制国体对近代自我之觉醒的致命羁绊。甚至毋宁说,对天皇这一政治实体做出宗教式“诗性幻想”的荷风式神秘主义倾向,正是日本近代悲剧的精神起源,这也是今人所当深思者。话虽如此,若以此求全责备、讨论其所谓“历史局限性”,无疑将落入“历史的辉格解释”(50)“历史的辉格解释”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指的是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本党利益出发,以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其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陷阱。实际上,文人论政的暧昧与感性并未妨碍荷风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和不合作的现实抉择,在变动性逐渐丧失、社会政治渐趋一元化的时代,超脱利益牵绊的“近代的自我”,带着世界主义视野和以史证今的眼光尝鼎一脔、洞明实质,并非难事。
上述一切皆关乎判断,而判断又关乎抉择、行动与责任。在战时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永井荷风并未对现实给出“有为”的批判,而是以无为、缄默的姿态拒绝主动与军国主义政治权力合作,以一种相对圆融的姿态艰难地捍卫了知识人的良知底线。曲折记事而不曲笔,蛰伏避祸而未折节。荷风终以其不逐时流、不屈强权的“偏奇”(51)汉语中“偏奇”意谓“特出而异于流俗”。1920年5月23日,荷风移居麻布新居(1920.5.23,卷一:170),屋号“偏奇”乃因该建筑之装饰使用了“ペンキ(油漆)”。以“偏奇”名室,足彰心志。,守得天明,成为一束照亮昭和前期历史暗夜的理性、智性与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