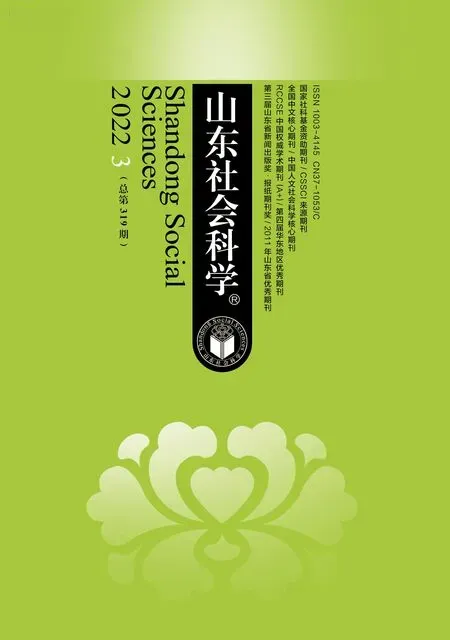法理论作为法律解释的基础
崔寒玉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
法理学有用吗?对于这一问题,在法律人中间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有些法律人对法理学持排斥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对于法律实践缺乏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也有不少法律人积极肯定法理学对于法律实践的价值。对待法理学的这种矛盾态度也延伸到了法律解释领域。关于法理学能为法律解释做什么,学者们的观点也大致可以分为“无关联性”“弱关联性”与“强关联性”三种。主张“无关联性”的人彻底否定法理学的价值,认为法理学对于法律解释非但无益,甚至可能有害。(1)[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主张“弱关联性”的人认为,法理学之于法律解释学,最多只有澄清概念的作用。(2)马驰:《作为概念理论的法理学及其实践意义》,《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而主张“强关联性”的人则认为,法理学之功用绝不止在于澄清概念,其对于思考“应该如何解释法律”这一实践难题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3)张文显教授就曾明确提出,“法律解释不仅必须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而且必须符合法理。”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一般认为,法理学包含“法理论”与“法伦理学”两个部分。其中,法理论探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也称法律的“性质”问题或“概念”问题;法伦理学探讨的则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将范围局限于法理论能够为法律解释做什么。
一、为什么是“强关联性”
如何解释法律,即法律解释方法论问题,是法律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法律人在实践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法理论能为法律解释做什么”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法理论与法律解释方法论这两种理论的关系问题。毕竟,所有实践都是“理论内置”的。(4)[美]罗纳德·德沃金:《理论的礼赞》,载《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86页。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法理论能为法律解释做的也就越多。而理解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需要从它们各自的问题意识与结构入手。
(一)法律解释方法论
法律解释方法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律规范从何处发现,或者说依据什么得到证立。法律(解释)论辩具有基本的形式,即法律规范一般是从宪法、法律、法规、案例、立法历史、习惯等事实中发现或得到证立的。在此,可以区分出两类事实:一是关于法律规范及其内容的事实,可以称之为“法律规范事实”或“法律内容事实”(5)Mark Greenberg, “How Facts Make Law”, Legal Theory, Vol.10, No.3,2004,p.157.;二是宪法、法律、法规、案例、立法历史、习惯等所组成的事实,法律人一般将之称为“法律素材”或“法律渊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事实在层面或者说位阶上并不相同:法律规范事实并非终极性事实,其存在依赖于在层次上更为基本的法律素材。
法律解释方法论的任务正是厘清这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即有哪些法律素材有资格作为发现法律规范事实的线索或证立法律规范事实的依据,以及法律素材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法律规范事实。从理论结构上看,法律解释方法论就是关于两类事实——法律规范事实与法律素材——之间决定—被决定关系的理论。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对于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偏重文义的解释理论主张权威法律文本的文义是构成法律规范事实的最主要的素材,立法目的则并不具备法律素材的资格;偏重立法目的的方法论不仅承认立法目的的法律素材地位,而且主张立法目的在对法律规范事实的影响力上高于权威法律文本的文义。
至此,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结构已经被勾勒出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对于任何法律解释方法论来说,如何证立其对于法律规范事实与法律素材之间关系的理解?或者换一种角度,当不同的解释方法论产生分歧时,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孰是孰非?显然,这样的争议并非诉诸经验性考证所能化解的。用德沃金的话说,这种争议是“理论性的”(6)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德沃金这一说法其实也暗合本文的主张,即法律解释方法论的证立问题需要法理论的介入才能解决。至于原因,同样要从法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结构谈起。
(二)法理论
法理论所探讨的问题通常可以简单归结为“法律是什么”。然而这一问题本身看上去很模糊,就像哲学家追问“人是什么”,让人乍听之下不知从何作答。因此,需要对该问题作出更为明确的界定。根据美国法理学家安德瑞·马默的观察,当代法理论关于“法律是什么”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法律效力的条件问题与法律规范性问题。(7)Andrei Marmor and Alexander Sarch, “The Nature of Law”,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9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9/entries/lawphil-nature/,2020年8月19日访问。其中,法律效力的条件问题探讨的是,赋予一项规范以法律效力的条件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条法律规范的效力条件都可能是多方面或多层次的。法理论并不试图识别出所有的效力条件。其所关注的效力条件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般性与终极性。首先,法理论并不关心在特定法律体系中、特定时代下使得某一规范具备法律效力的那些具体条件。这些具体条件可能是因地、因时制宜的,随时空的变化而有所移易。法理论关心的毋宁是那些超越时空的、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法律体系的条件,即法律效力的一般条件。其次,法理论作为法哲学的一部分,与其他哲学性思考一样,都是对研究对象的终极追问。法律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实践,决定某一法律规范效力的条件无疑是多层次的。法理论并不企求将这些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事无巨细地找寻出来,而是更关心在最根本层面有哪些事实、以何种方式赋予特定规范以法律效力,即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至于在中间层次有哪些事实决定法律规范事实,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经过提炼的法律效力的条件问题可以被表述为:使得任何形式的命题——“X(一些规范性内容)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对特定人群是法律”——为真或为假的一般性、终极性条件是什么?(8)这里参考了马默的表述,但马默只强调了一般性,而未指出终极性。参见[美]安德瑞·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围绕法律效力的条件问题,法理论家们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一派法理论家认为,法律效力的条件最终是由社会事实所构成的。这些社会事实包括人们的所思、所欲、所言、所为,等等。(9)[美]斯科特·夏皮罗:《合法性》,郑玉双、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在性质上,社会事实都属于描述性事实、经验性事实,而非价值事实。(10)Mark Greenberg, “How Facts Make Law”, Legal Theory, Vol.10, No.3,2004,p.157.这一派通常被称为法律实证主义。例如,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实证主义理论,即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就主张,使得某一规范具备法律效力的一般性、终极性条件是所谓的“承认规则”,也就是法官与其他法律官员们的“聚合性实践”这一社会事实。(11)[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嘉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0-100页。
另一派法理论家则认为,构成法律效力的条件并不囿于社会事实,还有价值事实。所谓的价值事实主要是指道德事实。例如,关于非道德性法律规则是否是法律规范的问题,后一派法理论家就认为,虽然社会事实看上去可以为其效力提供支持,但这些规则从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角度看都是无法接受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一派通常被称为自然法学。自然法学的法理论在当代最为人所熟知的代表是“拉德布鲁赫公式”: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12)通常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由“不能容忍公式”与“否认公式”两部分组成。此处引用的只是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后半部分,即“否认公式”。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1946年)》,舒国滢译,载雷磊编:《拉德布鲁赫公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总的来说,法理论家们关于法律效力条件问题的分歧集中体现为两方面:哪些种类的事实有资格决定法律规范的效力,以及这些事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决定法律规范的效力。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将法理论更具体地界定为:关于哪些事实以何种方式在最根本层面决定法律规范效力的构成性阐释。
(三)法律(解释)论辩中的“三阶事实”
前面的分析揭示出法律解释方法论与法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结构,这是为确定二者的关系所作的必要准备。不难发现,两种理论的共同特征是,所涉事实是分阶层的。而这恰是发现二者关系的重要线索。
总体而言,法律(解释)论辩的实践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它的“逐步深入”体现为论辩所依据的事实是分阶层的:随着论辩的展开,论辩所依据的事实将由“浅”入“深”、由“高阶”至“中阶”终至“初阶”。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阶层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理解这一过程。“三阶事实”中的“高阶事实”是诸如“在咖啡馆内禁止吸烟”“在上海必须分类投放垃圾”“在英国车辆须靠左侧通行”之类的法律规范事实,它们是关于法律规范的存在与内容的陈述,是确定法律赋予人们的权利及义务的最直接的依据,亦即法律推理三段论中的规范前提。“三阶事实”的“中阶事实”是诸如成文法的文义、立法史以及习惯等“法律素材”,它们是形成、判定法律规范事实的常规论据;法律(解释)论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集中并止于在这一层面展开。“三阶事实”中的“初阶事实”则是如“承认规则”或正义等法律效力的根本条件,它们决定了法律素材在法律(解释)论辩中的论据资格与强度,并经由法律素材间接决定了法律规范事实,是形成、判定法律规范事实的最终依据。除非是疑难案件,法律(解释)论辩通常并不会深入到这一层面,但它依然初始性地影响了其他两个阶层的事实,因此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可以说是法律(解释)论辩的隐性前提。简单来说,三个阶层事实之间由深至浅、由初阶至高阶呈“决定—被决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决定—被决定”的相互关系,使得法律(解释)论辩须透过这三个阶层的事实由浅至深、由高阶至初阶渐次展开:如果在法律规范事实层面存在分歧,就诉诸较深层面的法律素材;如果在法律素材层面存在分歧,就进一步下溯,直至最根本的法律效力之终极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三阶事实的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在法律(解释)论辩的实践中只会涉及这三个阶层的事实。如果将法律(解释)论辩中所涉及的每一阶层事实理解为论证链条上的一环,那么该论证链条在环节上是难以计数的。这里所谓的“难以计数”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三阶事实之间,可能存在其他更多层级的事实。例如,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与法律素材可能并非直接的“决定—被决定”关系,在这两层事实之间或许存在更多层级的中间事实,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需要经由这些中间事实间接决定法律素材。另一方面,在三阶事实之外,也会存在更多层级的事实。虽说在三阶事实的终端是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但“终极”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性表述。因为对于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议的,而争议的解决必然需要诉诸其他更为基本的事实。不难想象,法律论辩的论证链条可能会一直延伸下去。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阶层的相关事实一一识别出来。就本文的论证目标而言,只需明确一点:由“法律规范事实—法律素材—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所组成的三阶事实,对于法律(解释)论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且三阶事实相互之间存在“决定—被决定”的逻辑关系。
如果以上关于法律(解释)论辩中的“三阶事实”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后文简称“三阶事实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律解释方法论与法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法律解释方法论的任务是厘清法律规范事实与法律素材之间的关系,即哪些法律素材有资格作为发现与证立法律规范事实的依据,以及法律素材以何种方式构成法律规范事实。从“三阶事实论”的角度看,法律解释方法论的焦点是中阶事实,处理的是中阶事实与高阶事实的关系问题。而法理论探讨的则是哪些事实以何种方式在最根本层面决定法律规范事实的存在与内容。就“三阶事实”而论,法理论聚焦于初阶事实,处理的则是初阶事实与高阶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三阶事实”之间存在“决定—被决定”的关系,且初阶事实需要经由中阶事实才能决定高阶事实,因而任何研究中阶事实的理论都需要以研究初阶事实的理论作为前提和预设。因此,任何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建构与反思都需要以法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强关联性”。
“三阶事实论”不仅揭示出法律解释方法论与法理论的关系,而且侧面反映出二者在法学学科中的地位。任何一门高度发展的复杂学科在研究对象上都是多元化的。如果将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解为特定事实的话,那么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为事实的广泛性,更体现为事实的层级化。其中,研究初阶事实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基础理论、“元理论”或“本体论”。法理论正是法学中公认的基础理论。研究中阶事实的理论通常被称为“中层理论”,其典型代表为学科中的“认识论”“方法论”。法律解释方法论就可以被定位为法学中的中层理论。以高阶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被称为“高阶理论”,它是与实践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理论;精细化与体系化的高阶理论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各部门法教义学正属于法学中的高阶理论。由法理论至法律解释方法论再到法教义学,三种不同位阶的理论从纵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学学科体系。而法理论正位于这一学科体系的“塔基”,对法律解释方法论与法教义学都发挥了基础性影响。
(四)“强关联性”命题之限定
虽然本文通篇都在论证法理论之于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基础性作用,但也要警惕另一种极端倾向,即认为法律解释方法论是法理论的附庸,其建构与批判都依从于并且仅仅依从于法理论。根据“三阶事实论”,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初阶事实)决定法律素材(中阶事实),并经由法律素材间接决定法律规范事实(高阶事实)。从这个角度说,法理论的确是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基础与前提。但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并非是决定法律素材的唯一因素。在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之外,还有诸如解释者的能力以及系统性效应等制度性因素也会对法律素材产生影响。(13)[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162页。
假设根据某法理论,凡是立法者在主观上想要实施的、实现的规范,就是在法律上有效力的规范。在这里,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对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凡是能够作为立法者主观意图证据的材料,亦即所谓的“立法史”,都应当成为法律素材?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法律解释方法论在选取与运用法律素材时,还需要考虑各种立法史材料在实践中能否成为立法意图的可靠证据。一般来说,解释者作为个人,必然是有限理性的,在运用立法史的过程中难免会犯两类错误:“信息错误”和“评估错误”。(14)[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具体来说,立法史通常篇幅甚广,种类繁杂,而且部分材料可能并未公开或难以取得。解释者通常缺乏时间与精力对立法史形成一个整体性把握,容易以偏概全。不仅如此,解释者在了解立法史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诉讼当事人的策略性行为、司法前见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错误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当上述认知错误被传递到其他解释者那里时,错误非但难以纠正,还会进一步扩散。“因为法官决策的程序是逐案解决的程序,这种程序通常过于关注特殊的个案,从而阻碍了法官去考虑他们运用的解释方法所产生的系统性影响。”(15)[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正是基于以上制度性因素的考虑,作为立法意图证据的立法史在证明力上一直备受质疑,这也直接影响到立法史的法律素材资格及其在法律解释方法论中的地位。
立法史的例子说明,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初阶事实)与法律素材(中阶事实)之间虽然存在“决定—被决定”的关系,但这种“决定—被决定”的关系并非排他性的。确切地说,法律素材乃是由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与各种制度性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因此,法理论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塑造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唯一根据。在建构与评判法律解释方法论时,不仅要提供法理论上的依据,还要考虑到司法能力与系统性效应等制度性因素。这是对“强关联性”命题所作的必要限定。
二、“强关联性”命题之应用:以刑法解释方法论为例
前文从理论上对法理论与法律解释方法论之间“强关联性”命题作出了论证。证明这一命题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该命题所能引申出的理论与实践意涵,而这正是本文接下来两节的任务。在本节,笔者将通过一个实例为“强关联性”命题提供一个应用分析。笔者选取的是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刑法解释学界备受关注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依笔者之见,这场学术争论深度不足,有“口号之争”(16)陈坤:《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刑法解释学上的口号之争》,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316页。的嫌疑。这里所说的“深度不足”,尤为体现在法理论在这场争论当中是隐身的,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证立作用。
(一)形式解释论VS.实质解释论:争点与缘由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分歧是十分广泛的,有学者总结出多达8个方面。(17)劳东燕:《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论与实质论之争》,《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但若仅从法律解释方法论的角度看,双方的分歧集中体现在所青睐的解释方法以及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上。在各种解释方法当中,形式解释论者最为倚重文义解释,倾向于根据刑法条文的日常语义来划定构成要件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再采用目的解释等其他方法作为辅助,如根据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来判断是否应该作出刑事处罚。与此不同的是,实质解释论者更强调目的解释的至上性,为了达至刑法所欲保护的法益,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刑法条文的日常语义范围。简言之,在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排序中,形式解释论主张文义解释的优先性,而实质解释论则强调目的解释的优先性。
两派在解释方法上的主要分歧集中于那些在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在形式上缺乏明确规定的案件。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刑法解释方法论上的分歧,根源于双方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上的差异。(18)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刘艳红:《形式与实质刑法解释论的来源、功能与意义》,《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形式解释论坚持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认知,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以文义解释为核心、根据刑法条文的日常语义来划定构成要件范围的解释方法,就成为捍卫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逻辑必然。形式解释论者批评实质解释论以实质判断先于甚至取代关于法律有无规定的形式判断,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践踏。(19)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但实质解释论者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解,理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本身既有“形式的侧面”,也有“实质的侧面”。(20)张明楷:《罪刑法定原则的两个侧面对法治的启示》,《法学论坛》2004年第2期。实质解释论者援引日本的刑法学说,将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概括为6个方面:①成文法主义;②禁止事后法;③禁止类推解释;④禁止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⑤刑罚法规的明确性原则;⑥刑罚法规内容的适正原则。(21)张明楷:《罪刑法定原则的两个侧面对法治的启示》,《法学论坛》2004年第2期。其中,前4个方面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后2个方面则构成其实质侧面。在实质解释论者看来,像形式解释论那样单纯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其实是不充分的,而实质解释论不仅坚持了罪刑法定的形式,更坚持了罪刑法定的实质,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22)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73页。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实质解释论才反对那种单纯以刑法条文的字面意义为依归的解释方法,主张在可能文义的范围内,以目的解释方法为核心追求刑法法益的刑法解释论立场。因此,拆解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这场刑法解释方法论之争的关键,是正确理解与把握罪刑法定原则。
(二)论战的误区
不得不承认,论战双方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上都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论辩,并论证己方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认识才是准确的。例如,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理论是如何从意大利与日本以讹传讹引入国内的(23)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从思想根源的角度,挖掘出“社会危害性理论”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观念形成的隐性影响(24)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通过我国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均采用了实质解释论的立场这一实证研究结论,来论证实质解释论的功能与价值(25)苏彩霞:《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通过对于糟糕法治状况的历史省思,警示单纯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所可能导致的实践危害(26)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张明楷:《罪刑法定原则的两个侧面对法治的启示》,《法学论坛》2004年第2期。;等等。诚然,论战双方多元化的研究思路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人们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但客观上也导致论战呈模糊化与失焦的状态。论战的失焦集中体现为多数学者未能区分两个概念:“正当性”与“(法律上的)有效性”。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条被公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实在法中的直接表述。它同时意味着,作为规范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规范,而非仅仅是普通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证立的方式是论证其道德正当性,即在道德上是值得欲求的。法律规范的证立却须证明其有效性,即在现行法律体系的框架内是有法律效力的。例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一条道德规范,但在很多地方也兼具法律规范的属性。如果仅仅论证其正当性的话,你可以说:在公共场合吸烟会损害他人的健康,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在道德上显然是不正当的。但如果需要论证其有效性的话,说同样的话恐怕是不适宜的,或至少是不充分的。你需要证明在当地的法律制度中,“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一条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这就意味着你要诉诸法律效力的条件(其中可能包含终极条件),论证该规范是满足这些条件的:假使你认同哈特的法理论,你就应当论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是法律规范中明文规定的,而该法律规范是法律官员们所共同承认的。这正是“有效性”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所在。
反观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双方阵营都主张己方对于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理解才是正确的,但多数学者所提供的论据都是从“正当性”(27)部分学者使用的术语略有不同,如苏彩霞使用的是“适正性”,但从内容上看,他们都是从正当性角度出发提出论据并组织论证的。参见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角度出发,并未见有哪位学者有意识地从“有效性”的角度出发来组织论据并形成论证。如果罪刑法定原则仅仅是一条道德原则的话,这样论证或许是没问题的。但罪刑法定原则更主要的身份是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法律原则的内容与分量都依附于特定的法律体系。罪刑法定原则虽然为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所共同承认,但比较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既包括国内法体系也包括国际法体系),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的内容与适用的分量上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28)姜敏:《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维度和启示——兼与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比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不仅如此,特定法律体系所属社会的历时性变迁与发展,也会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影响。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是一场中国刑法学内部的论战,双方争论的是在当下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刑法解释方法论。因此,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讨论也应当被放置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其在中国刑法教义学体系中所应具有的内容与分量。如此看来,论战双方从正当性角度来论证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然误解并模糊了论战的焦点。只有在法律上具有效力的规范内容方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内容。因此,有效性问题才是论战双方在相互论辩时真正应该着力之处。换言之,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论证不应简单地论证其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而应论证其能满足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法理论是关于法律效力终极条件的探讨。因此,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应当深入到法理论层面进行较量。遗憾的是,无论是形式解释论者还是实质解释论者都没有随着论战的推进有意识地在法理论层面展开交锋。我们无从窥测双方在法理论层面所持有的具体立场,更难以设想他们会从法理论层面形成什么样的论证。
三、“强关联性”命题的意涵
“强关联性”命题对于思考法律解释问题,尤其是对法律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至少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明确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
(一)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是指,思考、研究与论辩法律解释方法论时,应当坦率而清楚地展示自己的法理论立场。
虽说法理论是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基础与前提,但在法律解释实践的绝大多数场合,解释者是感受不到法理论的作用的:解释者所需考虑的仅限于如何妥当地运用特定解释方法,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但是,当人们对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本身产生怀疑与争议时,法理论还能够或应当“隐身”吗?
从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可以看到,在我国刑法解释方法论的讨论中,法理论是缺位的,论战双方没有亮明各自的法理论立场。这并非个例,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宪法解释方法论研究上。在美国宪法解释学界,最为持久的争议发生在“原旨主义”与各种“反原旨主义”理论之间。与实质解释论者与形式解释论者相仿,原旨主义者与反原旨主义者在相互论辩时也都喜欢诉诸正当性论据而非有效性论据。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为原旨主义提供的辩护是,原旨主义是一种“较少的恶”,它能够通过建立一种历史标准防范法官以个人主观偏好任意施为。(29)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Vol.57, No.3,1989,pp.849-866.而斯卡利亚的同僚,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则攻击原旨主义非但不能限制司法主观性,反而会“让法院走入歧途,将法律与生活割裂开来”(30)[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伤害那些国会旨在扶助的人们”(31)[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而他所倡导的解释方法论则有助于法律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实现其所谓的“积极自由”(32)[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20页;[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斯卡利亚与布雷耶论战了二十余年,双方却不约而同地从未陈述各自的法理论立场,来自法理论的论证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虽然前文论证了法理论是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必要前提与基础,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在思考、研究与论辩法律解释方法论时应当亮明法理论的主张。毕竟根据“休谟法则”,“是什么”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应该做什么”。而“明确性原则”对于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都提出了“应然”的要求,显然是一个规范性主张。因此,本文依然需要对“明确性原则”提供特别证立。在笔者看来,证立理由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首先,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法理论具有论据整理功能,法理论的隐身会导致法律解释方法论证的散漫与失焦。无论是形式解释论者与实质解释论者,还是原旨主义者与反原旨主义者,他们在论战中都提出了多方面的论据。这的确拓展了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但是旁观者很难从他们的讨论中理出一个头绪,即他们是循着什么样的线索来找寻与组织论据的,论据与论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这说明论者本身对于论据的相关性与体系性缺乏审慎的思考。其集中表现为在论证中习惯于采用“霰弹枪”模式——随机罗列一堆彼此关联不甚密切的论据,并不企求论证在整体上为读者所接受,但求所列论据中至少其中之一能够“打动”“击中”读者即告成功。这其实是一种思考上的怠惰与投机,并不利于研究的实质性推进。
其次,从理论延展的角度看,法理论是连结法律解释方法论与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纽带与桥梁。虽然法律解释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法学问题,但并不能完全依靠法学内部的知识资源而彻底解决。与其他重大法学问题一样,对于法律解释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随着思考与论辩的深入,不仅会牵涉到越来越广泛的法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知识,也会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哲学思辨性。而这些法学外学科资源的引入并不是任意的,需要在法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有知识都是为“法律问题”来服务的,而非为“伦理问题”“经济问题”抑或其他问题来服务的。形象地说,法理论既是引入有价值外部知识的“导管”,也是排除非相关外部知识的“滤芯”。因此,从学术体系上看,法理论扮演了法律解释方法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间枢纽的角色。在研究中阐明法理论有助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朝纵深发展。
最后,从学术批评的角度看,法理论是对法律解释方法论进行“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必要前提。学术批评是理论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一般来说,对于某一理论的考察与批评会着眼于以下方面:①逻辑自洽性:在论证上前后一致,不违背逻辑定律;②资料的准确性与广泛性:所采用的论证材料有事实依据,且具备较高程度的普适性;③简洁性:用尽可能少的要素与尽可能简单的结构解决疑难问题或阐释复杂事实;④预设前提的可证伪性:论证所预设之前提并非先验或超验,而是在经验上不仅能够得到验证,而且可以证伪。其中,基于第④点展开的学术批评也被称为“思想的前提批判”。法理论作为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如果隐而不显,其他研究者在评判某一法律解释方法论时要么无法作出前提批判,要么只能通过揣测其所预设的法理论作出测度性评估。长此以往,无助于在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中形成健康的学术批评氛围与审慎的理论增长。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有意识地阐明自己的法理论立场应成为思考、研究与争辩法律解释方法论的一项基本要求。
(二)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是指,任何法律解释方法论,都必须与其所预设之法理论在逻辑上保持一致。
“一致性原则”出自逻辑学上的公理,也是基本的学术规范,因而不需要像明确性原则那样进行特别证立。但也不应因习以为常而掉以轻心,因为在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中,“一致性原则”常常在不经意间被违反。最常见到的情况是,很多法律解释方法论都声称以哈特的法理论为基础,但事实上哈特的法理论与任何法律解释方法论都是相抵触的。
作为当今最为法律人所熟知的一种法理论,哈特的法理论因其“光环效应”使得很多法律解释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作正确的法理论,并且直接预设为自己法律解释方法论的本体论基础。然而,马克·格林伯格指出,哈特的法理论并不能作为任何争议性法律解释理论的基础。(33)Mark Greenberg, “What Makes a Method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Correct? Legal Standards vs.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Vol.130, No.4,2017, pp.105-126.根据该法理论,法律效力的终极条件是所谓的“承认规则”;判断哪种法律解释理论是正确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看看在一国(或地区)内,法官与其他法律官员们在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选择上是否存在共识,或哪种解释方法论为大多数法官及其他法律官员所广泛接受。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一解释方法论与法律官员们的共识存在偏差,站在哈特法理论的立场上看,它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哪种法律解释方法论在特定法律体系下是没有争议的。无论是前文提到的中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还是美国宪法学界的原旨主义与反原旨主义之争,都并非个例,而是“争议性”——这一法律解释实践本质属性——的现实呈现。某一解释方法论可能在特定法律体系的特定时期被特别提倡或推崇,但在法官与其他法律官员当中也远未达到共识的地步。更何况学术界还在不断“供给”新的解释方法论,这在事实上不仅未能促进共识,反而加剧了分歧。毫不夸张地说,法律解释方法论上的争议弥漫于法律实践的各个角落。因此,任何解释方法论都无法主张它为“承认规则”所排他性地接纳,其与哈特的法理论必然是相龃龉的。那么,任何学者声称其法律解释方法论建基于哈特的法理论之上,都违反了“一致性原则”,是不真诚、自相矛盾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违反“一致性原则”的一种常见情形,我们也不难设想其他可能情形。例如,在法理论上预设了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立场,却主张(客观的)目的解释、(内在的)体系解释等必然依赖价值判断的方法论。再如,在法理论上预设了拉德布鲁赫式的自然法立场,却主张文义解释至上的方法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故不赘述。
四、结语
不得不承认,在部门法学者与法律实务人士那里,法理学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也是近年来学者们频频撰文为法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辩护的原因所在。本文也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本文探讨的是法理学中的法理论能为法律人的日常实践——法律解释——做什么。通过法律论辩的“三阶事实论”,本文论证了法理论是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前提与基础。虽然法理论本身艰深难懂,且存在高度的争议性,这在客观上造成法律人不敢或不愿触碰法理论,但它与法律解释方法论之间的“强关联性”意味着,在思考、研究与探讨法律解释问题时,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法理论预设,并确保解释方法论与法理论在体系上是前后融贯的。这对于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有序与有效推进是必不可少的。一言以蔽之,法理论是法律解释的“入场券”与“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