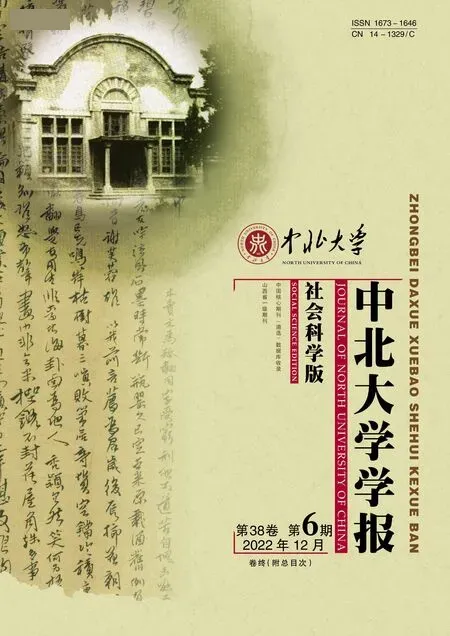论王昌龄对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悖离与新创*
吴昌林,刘泓希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0 引 言
传统诗教自古就重视诗歌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交际功能,唐人更是在离别宴饮之际频繁地赋诗饯行,产生了大量的离别诗。于是,盛唐离别诗在六朝离别诗的基础上,达到了鼎盛,从诗歌群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诗歌门类。这首先表现在一定数量的作品上:清人沈德潜选编《唐诗别裁集》的1 900多首中有300余首离别诗,《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离别诗有5 000余首。元人辛文房云:“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于众中推一人擅场者”[1]658,凡参与饯别之人,无论送者与留者,都需作诗以表惜别或祝福。除了数量突飞猛进之外,离别诗能被视为一种诗歌主题(或类别)被确立,更是因为“自先秦萌芽开始……(离别诗)终于在盛唐时期走向艺术上的成熟”[2]2,形成了自身稳定的程式结构。
离别诗在反复的社交应酬中形成一个无关离愁别绪的创作场景,而参与者就需要寻找一种可供临时发挥的、稳定输出的诗歌程式,以确保无论诗才高低、与远行者认识与否,都能按照程式顺利写出礼节应酬性的离别诗,即以作诗的形式完成交际场合的寒喧。前代诗人的不同尝试最终在盛唐结出硕果——王维以其稳定的送别诗程式、质量兼备的送别诗作与文坛盟主的地位,确立了一套可供模拟的程式传统——“以五言律诗作为标准格式,对行者即将遇到的沿途风景进行‘沿路叙景’的描写”[3]6。
在以王维诗作为代表的作品群逐渐固定离别诗创作传统的同时,王昌龄一反主流,在诗歌体式、叙景程式、意象营造三方面上,形成了个性化的离别诗程式化创作。此前对于王昌龄离别诗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审美意象、迁谪心理、七绝诗体、整体风格等研究方向,而研究王昌龄离别诗创作程式的则较为罕见,因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探讨,比较其与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异同,确定王昌龄诗作对离别诗史的发展意义。
1 在诗歌体式上,悖离主流律诗的应酬性,以古诗绝句抒写真情
诗体特征看似只是诗人的创作个性,因为无论是分析诗歌主旨,还是考察具体的创作场合,离别诗都以“内容是否抒发离别之情为判断标准”。王昌龄也有“七绝圣手”的美誉,偏好创作绝句似乎是不必深究的问题。抛开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笔者仅从作品形式考察其对盛唐离别诗创作传统的悖离,以资于研究不同诗体在离别诗创作中适用的情况与作用。
离别诗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划分出来,其成熟标志除了明确表达离别之情外,也体现在形式的成熟程度上,即诗体、诗题、程式等形式上的标准。主题并非抽象地存在于作品内部,作为内容的主题与作为形式的诗体是不可分割的,“形式不但具有审美价值,它本身也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意味’,同时又是积淀着内容的形式,忽略了形式,片面强调内容,往往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整体”[3]315。基于以上理由,有必要考察盛唐离别诗在诗歌体式上的情况,以诗题中是否使用“送、别、饯、留、祖”等字为判断依据统计,详见表1。

表 1 盛唐代表诗人的离别诗诗体使用情况
同为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为人饯行时所作的离别诗中,有39首采用律体,而绝句仅有9首;隐居深山、一生未能出仕的孟浩然,其离别诗中有34首律诗,5首绝句。高适、岑参的离别诗也都有过半是律诗,绝句的占比仅为10%左右,同样是数量悬殊。所以说,盛唐时期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以律诗写离别”的创作风气,不过李白纯以其“飘逸不群”的气质作诗,并不在比较范围内。王昌龄目前可考的55首离别诗,全是长篇五言古诗与短篇五、七言绝句,没有写作过一首律诗,或者说没有律诗流传下来。
“诗体是通过其表现规模以及该种诗体特有的样式意义”[4]231来决定作品之性质的。律诗和古诗是不受限于篇幅的,在叙事功能上有着先天优势,较长的篇幅能够从容地铺陈对方的社会成就,褒美对方的懿德佳行;而绝句在篇幅有限的制约之下,抒发离别之情时必须更加精炼地选择表达内容,追求一种言简意赅、意味隽永的抒情性效果,难以胜任社交应酬的需要。既然绝句缺乏应酬性是显而易见的,那王昌龄的长篇五言古诗中是否存在应酬性?试以《留别伊阙张少府郭都尉》[5]43分析:
迁客就一醉,主人空金罍。江湖青山底,欲去仍徘徊。郭侯未相识,策马伊川来。把手相劝勉,不应老尘埃。孟阳蓬山旧,仙观留清才。日晚劝趣别,风长云逐开。幸随板舆远,负谴何忧哉。唯有仗忠信,音书报云雷。
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王昌龄由汜水尉左迁岭南时,于伊水岸边留别旧日同僚张少府以及初识的郭都尉。从主客双方来看,送别者是张少府、郭都尉,留别者是被贬谪的王昌龄,这应是一篇官场应酬之作。但在结构上,王昌龄对送别者郭、张二人各作四句以留别:“郭侯未相识”四句,言郭都尉与昌龄素不相识,却能不辞辛苦,专门为之送别,并引郭的安慰之语“不应老尘埃”;“孟阳蓬山旧”四句,意为张孟阳是长安中枢秘书省旧识,其人有清才,王昌龄以张的鼓励之言“风长云逐开”入诗。又“幸随板舆远,负谴何忧哉”两句,言王昌龄虽遭谪降,但幸而老母随行,可奉养以尽孝道。但王昌龄时年四十岁,王母也早已过“知天命之年”,母子二人南迁烟瘴之地,何其艰难。“唯有仗忠信,音书报云雷”明言清白之身遭宵小诬陷,陡见气势。这篇五言古诗虽明言官场离别,实则抒写的是诗人的愤慨之情和勉励友人之意。
前文已述诗人常因应酬而作诗,那么在不同离别场合下触发写作的离别诗,势必会展现出不同风貌,可将离别社交场合简分为“集体送别”与“私人送别”。“集体送别”中的集体常是以达官显贵为核心的官僚贵族群体,或以名士为中心的文学团体。在此场合中,诗人代表集体送别远行者,或者诗人留别集体,内容多有对双方社会成就和道德修养的美誉和期许,如高适的“光阴蓟子训,才术褚先生”(《赠别褚山人》)、王维的“薄赋归天府,轻徭赖使臣”(《送元中丞转运江淮》)等,尽管客套话与离别事件并无直接联系,但诗人们也都乐于美言几句。私人送别是亲友之间的互诉衷怀,彼此通过诗歌得到情感的确证,送人赴任则鼓励建功立业,送人隐居山林则向往自然悠游,送人贬谪落第则安慰东山再起,如王维的“宛洛有风尘,君行多苦辛”(《送丘为往唐州》)、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二首·其一》)等。
由此可见,形式上的诗体对于诗歌内容是存在间接影响的,媒介因素则是离别场合的正式与否、离别双方关系的亲疏,即诗体影响内容上所体现出应酬性的多少。如此再看《留别伊阙张少府郭都尉》,张少府、郭都尉虽以官名出现,却毫无官场送别诗中的奉承因素,直接将对方言语引入诗中,本来有冒犯之嫌,但这里更多展现的是王昌龄对友人远道前来送别的一片感激之情,毫无保留地向他们倾诉怀才不遇的委屈和高远旷达的志向,类似篇幅较长且充满朴素真情的离别佳作,还有《送韦十二兵曹》《东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等诗作。
2 在叙景程式上,悖离“沿路叙景”的隔离功能,形成“临水意境”
离别诗在盛唐时期发展出成熟稳定的程式,除了要归功于律诗体式的定型外,更重要的是在创作思路上模式化,将送别诗中有关离别后的景色描写(简称“别后之景”)固定为叙景程式——“沿路叙景”,从而在离别诗的大类中再次区分出送别诗和留别诗两个小类。所谓“沿路叙景”是指以想象的方式叙写行人在离别之后沿途遇见的以及目的地的风景。诗人借助“沿路叙景”在送别诗中明确区分双方,诗人是此处的留者,对方是将到彼处的行者,那么把远行者置于由此地前往目的地中,隔离送别双方,算是最合适的表现程式了。
“沿路叙景”还需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叙写的风景应与离别场所在地理空间相隔较远;其次,叙写的景物能够明显地区别于离别场所的风景,描写的风景与离别现场的距离越远,或者与离别场所的实际风景越是不同,效果越佳。以王维《送梓州李使君》[6]96为例,说明”沿路叙景”的原理: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
此诗是王维送李某赴任梓州刺史所作,是典型的盛唐官方送别诗。首、颔二联写蜀道异于关中长安的山林景色,颈、尾二联以“汉女纳橦布”(税贡)、“巴人讼芋田”(民讼)、“文翁教土民”(教化)三个蜀地典故,铺陈李某远行途中即将见识的景象,劝勉鼓励行者为官在任时要以先贤为榜样,完成了社交上的应酬。如此一来,一方面在身份立场上区分出了送者和行者,将双方分别放置于空间中的两端;另一方面,将行者的形象从现实的离别场景(长安)中脱离出去,放置到远行的旅途中或遥远的他处(蜀地)。换言之,在诗歌写作时,可以通过展现行程中或目的地的地名和典故等,有效地达到“隔离”效果。
送别诗要求的“隔离”功能并非写作本意,更多是礼节应酬性招致的。上述已将离别场合简分为集体送别与私人送别两类,而具备“隔离”功能的多是集体送别:私人送别时,送者与行者常是交情甚深的友人或血脉相连的宗亲,双方情感默契,送者回忆交游经历、幻想再次重聚,行者也能够产生共鸣;但在集体送别时,送者是代表集体意志作诗,甚至与行者交情淡薄,再一味地表白离情、鼓励劝勉,难免些许虚伪。也就是说:“只有当作者与送别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密切的一体关系或心理上的契合时,作者才能够‘踏入对方的领地’”[3]126,而“沿路叙景”客观中立地铺陈别后的风土人情,正好避免冒失地触及行者的境况遭遇。
蒋寅认为,唐人的送别诗“涉及的内容可归并为八个基本要素:1.送别时地;2.惜别情状;3.别后相思;4.前途景物;5.行人此行事由及目的地;6.节令风物;7.设想行人抵达目的地的情形;8.赞扬行人家世功业”[7]。而(4)到(7)都可归入“沿路叙景”,以此考察王昌龄的送别诗中出现的“沿路叙景”因素,不过八首而已:“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送人归江夏》),“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卢溪别人》),“蓟门秋月隐黄云,期向金陵醉江树”(《送朱越》),“潮从秣陵上,月映石头新”(《送乔林》),“楚国橙橘暗,吴门烟雨愁”(《送李擢游江东》),“吴掾留觞楚郡心,洞庭秋雨海门阴”(《送姚司法归吴》),“遥送扁舟安陆郡,天边何处穆陵关”(《送薛大赴安陆》),“岭上梅花侵雪暗,归时还拂桂花香”(《送高三之桂林》)。所用的地名与典故都与离别场所相隔甚远,满足沿路叙景的条件,但叙景的效果却消解“沿路叙景”本应具备的“隔离”功能,把送者与被送者之间的感情紧密联系,以王昌龄的《送姚司法归吴》[5]172为例:
吴掾留觞楚郡心,洞庭秋雨海门阴。
但令意远扁舟送,不道沧江百丈深。
此诗应是诗人于岳阳送姚某赴吴时所写,从诗题看,属于官方送别。“吴掾”以酒留别王昌龄,乘舟缓缓消失在洞庭湖,王昌龄遥望连绵秋雨,想到姚某前往的“海门”恐怕也是天气阴沉。如此共通的心理与相似的天气便将两地联结,遥远的距离,不仅未能分隔双方,还使诗人的惜别之情更为强烈,将双方的情感紧紧相连。
当王昌龄悖离了“沿路叙景”传统的“隔绝”功能后,势必要摸索一个供自己模拟的程式,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只有在王昌龄的离别诗中才能感受到、于其他盛唐诗人作品中少见的“临水意境”。这种意境不仅有别于王昌龄在边塞诗中所表现的激昂壮烈,也有别于其他盛唐诗人离别诗的清新俊逸,而是营造出凄凉寂寥的氛围,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送魏二》中有如此的“别后叙景”:孤独的行人乘着一叶扁舟,泛波于江上,雨云连绵,遮断送者与行者相望的视线,相隔千里的人们只能凭借一轮时隐时现的月亮,在梦乡中与友人欢饮,始终萦绕着萧瑟凄凉之感。
“临水意境”并非简单的景色描写,而是构成王昌龄送别诗程式的诸要素:“江/河~扁舟~云雨~月/梦”。在这水边景色中,“行者登船”是线索,即使在现实离别场所中并不存在,王昌龄也会借助对未来情况的想象来补充,以使其描绘的“送别场景”结构能够完整。如《送刘十五之郡》中写到“平明江雾寒,客马江上发”,尽管这是一场马背上的离别,缺少了意象要素“船”,诗人还是特意以对未来情况的想象补充了“扁舟”这一意象:清晓的江面上,寒雾笼罩,友人执着缰绳,骑马来到江边。“扁舟事洛阳,窅窅含楚月”则写道,一叶扁舟即将载他直赴洛阳,诗人抬眼,又望见朦朦楚月若隐若现。又如《送人归江夏》[5]113:
寒江绿水楚云深,莫道离居迁远心。
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
“扁舟”与“双帆”、“江雾”与“楚云”、“楚月”与“孤月”这种反复描写的景色贯穿于王昌龄的离别诗,不同诗作的句子几乎可以替换。不仅是绝句,篇幅较长的古体诗也具备同样的写景特征,以《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至白马寺宿》[5]46为例:
鞍马上东门,徘徊入孤舟。贤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薄宦忘机括,醉来即淹留。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廓,夏夜如凉秋。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
“徘徊入孤舟”“即棹千里流”写诗人即将从洛水乘船南下,与众贤豪友人难舍难分,但船公催促开棹。待到末尾两句“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则又是想象到达目的地后,在梦中从江宁重返故地,和友人们再度相聚。诗中的场景与其绝句中极其相似,都是江河之上,弥漫着一片水汽微烟,亦或阴雨绵绵,游子乘着一叶孤舟,在现实中随着一轮明月而去,在梦境中随一轮明月而返。诗人把在洛水岸边离别的现在乃至未来,从头到尾都框定到河边,通过对未来情况的想象,圆满地补充了“临水意境”中缺少的“梦”意象。
联系此诗的写作背景,是王昌龄初次贬谪岭南后,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北归,又迁至江南东道的江宁县丞,途中与河南府诸公、诗友綦毋潜、李颀于洛阳东郊白马寺留别所作,换言之,王昌龄已经领略过楚山湘水的南方风景了。当面对一场发生在北方河洛平原上的离别,他回避了现实中、离别场所的景色,而选择描写脱离现实的水乡风景,去呈现他的“临水意境”,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诗人确实在艺术构思前,就将“临水意境”作为诗歌程式在意识形态中保留下来了,不过具体的形成过程则因目前王昌龄生平资料仍较匮乏,难以详细论述,有待进一步研究。
3 在意境营造上,以“月”意象统摄其他意象,超越时空联结双方情感
“月”意象的联结属性由来已久,在早期的闺怨诗中尤为常见。如曹植《七哀诗》有“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何逊《闺怨》有“晓河没高栋,斜月半空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游子与思妇仰望高悬中庭的明月,皎洁的月光洒遍人间,游子与思妇则凭借这轮明月,跨越时空而短暂地联结。若把游子视为远行者,思妇视为送行者或留者,那么以“月”寄情的手法被离别诗所吸纳,自是顺理成章的。
在王昌龄的离别诗中,江河、扁舟、云雨、梦境、月夜这些事前就已经预设好的写景材料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其中尤以“月”意象最为独特。据不完全统计,在王昌龄的55首离别诗中,有36首出现了“月”意象,可以说王昌龄对于描写月夜是情有独钟,这也是因为“月”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月”意象并非排列在众多景物中的普通意象,而是处于统摄全诗的位置,其他的意象都是围绕月色来营造意境的,而且其他意象多是离别场所中此时此地的景色,“月夜之景”则是唯一被固定的“别后之景”,以“月”的唯一性联结双方情感。
“月夜之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若隐若现的凄冷之“月”,潮湿的雨雾中月光也显得朦胧不定,引得离人愁苦不已,如“怨别秦楚深,江中秋云起”(《送李邕之秦》)、“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送魏二》);另一类则是明净之“月”,如“何处遥望君,江边明月楼”(《送胡大》)、“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送窦七》)。一轮明月高悬中天,陪伴着孤独的离人与无际的江河去对峙。两类“月”意象恰好在不同方面反映了“月”意象是如何统摄其他意象排列、架设行者和送者之间联结情感的桥梁的。
当王昌龄试图描写在若隐若现的凄冷之“月”时,或云雾缭绕,或雨雪纷纷,往往夜色朦胧,缺少光线照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像晴朗的白天一样详细、准确地描写出离别场所的景色,是非常耗费时间精力的,并不适合在短促的离别之际进行。所以,“月夜之景”的描写不能完全依赖于视觉,需要的是敏锐的触觉、味觉感官和奇妙的通感艺术,正如王昌龄写“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春怨》),就是以百花的香气衬托西宫春夜的寂静;杜甫写“水宿鸟相呼”(《倦夜》)以动衬静,描写栖息水间的鸟儿惊起,鸣声霎时间划破夜的寂静。假若不依赖于触觉和听觉,那么就只能描写高楼、灯火、白帆等在黑夜中可被视觉感知的景物,而其他的森罗万象则虚化成一片广漠的背景,仅留下黑暗的轮廓,如“天长杳无隔,月影在寒水”(《送李十五》),诗人仰望寂寥的天空,杳无鸿雁的音讯,诗人好像寒水中的月影,企望随着空中那轮好似友人在问候他的冷月。在频繁描写的“月夜之景”中,周边的其他景色只是附带描写;换言之,王昌龄描写的明月,只显示明月本身而不受其他事物的限制,而这一点在明净之“月”上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如“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送窦七》)、“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送郭司仓》),都是描写友人乘坐的扁舟在月光下不堪惜别,徘徊不发,而其他的意象如鄂渚、轻帆将会随友人远去,春潮般的思念,也只有通过月光的照射才得以向友人寄去。
盛唐离别诗在描写景物时,逐渐将“别后之景”限定于“沿路叙景”,前述“沿路叙景”是叙写的典故记载的沿途与目的地的景色以及离别后将会遇见的风景,诗人为了加强“沿路叙景”隔绝的效果,在描写风景时必须突出与离别现场明显不同的特质。王昌龄的“月夜之景”与当时一般离别诗中的“沿路叙景”明显不同。因为“沿路叙景”的隔绝功能还需满足另一条件,即设定的风景必须与离别场所相隔遥远,王昌龄的“月夜之景”,不是诗人想象中升上故乡山岭松枝的明月,而是一轮没有任何修饰的永恒之月,不仅属于行者,更属于送者,王昌龄的形象常常出现在这月色中,而盛唐主流的离别诗歌中只有行人孤独的身影。
在王昌龄的别后世界中,“月夜之景”并非实质上离别现场的实时景色,而是离别之后的假想性情景,是诗人在虚构的未来时空中使之成为现实的意象,又在叙景程式中作为抽象的核心去统摄其他具体的意象。王昌龄所追求的,是脱离具体形象、抽象概念化的,不受时空制约、永恒悬挂于中天的明月,正如《送柴御史》中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夜空中高悬起一轮光照九州的明月,明亮得让人忘掉一切多余的联想,鲜明地烘托出望月的离人彼此间思念的身姿,使得遥远的时空变得咫尺可见,漫长的离别成为倏忽间的往来,千里之外的亲友仿佛就在身旁。此时,王昌龄离别诗中抒情诗人的形象就达到最为丰满完整的程度。
4 结 语
盛唐离别诗的创作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多数诗人选择以律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诗体,叙写离别后的风土人情,这样既能满足社交应酬必须交代的内容,既不至于无话可说,也不至于喧宾夺主。王昌龄对主流的悖离,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他半生沉浮,多次贬谪蛮荒后,懒于官场应酬,对待所剩不多的朋友,直抒一片冰心,同时出于诗人的自觉,避免诗歌创作与他人雷同,努力表现出独属自身的创作风格。因此,读王昌龄之离别诗,虽然可以察觉到其程式所在,却仍能为其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情所感动,不觉俗套;同时因其悖离,具有了对离别诗类别发展的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