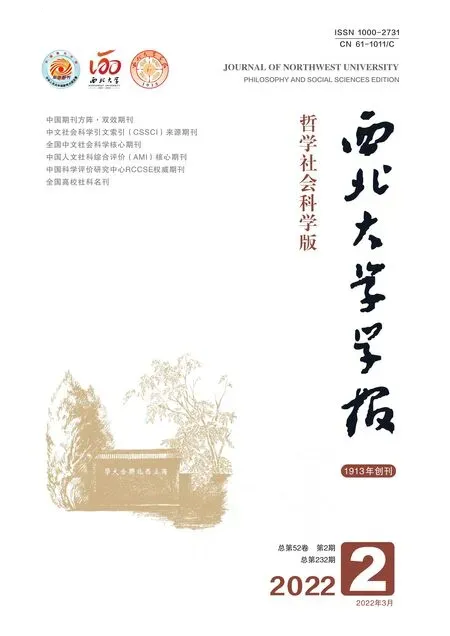从“尚阀阅”到“贵人物”
——唐宋官宦世家婚姻价值取向的比较
姜 宇,王善军
(西北大学 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宋人沈括在论及“士人以氏族相高”的社会习俗时曾云:“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1]233沈括在讲宗族等级社会的形成和影响时,明确提及士族、庶族婚姻习俗所表现出的等级内婚的价值观念。的确,两性婚姻关系的缔结,从来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因涉及家庭、宗族,往往不同社会阶层的婚姻各有特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阶层,其婚姻也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唐宋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尽管仍有许多相同的因素,但就主体价值而言,则表现出从崇尚阀阅到崇尚人物的时代转变(1)关于唐五代婚姻价值观念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涉及。李志生认为“关中旧士族高门的通婚观念也随时代进行着变化,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载《北大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金滢坤认为,唐代前期世人选婿注重门第,开元天宝以后,婚聘观念逐渐以门第、科名并重(《论唐五代科举对婚姻观念的影响》,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00页)。杜文玉认为“‘婚姻不问阀阅’应始自五代十国时期”(《“婚姻不问阀阅”应始自五代十国时期:对学术界“宋代说”的纠正》,载《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131页)。作为社会关系变迁明显且较为复杂的两宋时期,宋人婚姻的价值取向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张邦炜认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6页)。方建新提出宋代婚姻论财(《宋代婚姻论财》,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78页)。姚兆余专门研究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认为一是崇尚门第,二是“以才择婿”(《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52页)。上述研究成果,尽管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婚姻价值取向,但具体到某些特定群体,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社会群体婚姻价值取向的研究,尚有待加强。。
一、尚阀阅: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
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家族,亦即旧士族与新士族。唐代官宦世家婚姻崇尚阀阅,并非仅表现为士族阶层的等级内婚,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旧门间互通婚姻
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等级内婚制,入唐后流风遗俗继续存在。旧士族“犹相矜尚,自为婚姻”[2]2769。由于旧士族特别是其代表——崔、卢、李、郑、王五姓士族的郡望多在太行山以东,因而被时人称为山东士族。唐人柳芳所说的“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3]5679,很大程度上是指旧士族为维持其传统的社会地位而崇尚群体内婚。
旧士族群体以婚姻维持社会声望,矜尚群体内婚,但社会发展形势已使其婚姻难以完全限定在群体内。若不得已而与其他社会群体通婚,则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时人将这类财物谓之“陪门财”;这类婚姻谓之“卖婚”。非但嫁女如此,娶妇亦是如此。“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昏。”[3]3841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所谓“四望族”(即姑臧大房李氏、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组成的婚姻群体。他们“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4]1432-1433。即使是时居三品以上的高官之家,如果想与衰代旧门为亲,也要多输钱帛,才有可能被接受。
旧士族自恃身份并借婚姻敛财的做法,逐渐引起当朝统治者的不满。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基于“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的社会认知,下诏指出当时乖谬的社会现象是:“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为改变这一社会现状,他明确要求官府“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唐太宗在诏书中措辞严厉,批评旧士族失衣冠之绪、乖德义之风,甚至直接斥责此类婚媾为“有如贩鬻”。显庆四年(659),高宗在诏书中还曾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玄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5]1810-1811此后,唐政府还不断重申这类规定。
尽管李唐统治者此举有意打压传统士族、抬高新贵,却也揭示了旧士族呈现出寥落和式微的趋势。然朝廷举措并不能立竿见影,旧士族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他们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而坚持不与婚姻群体之外的宗族平等议婚。这种旧门间互通婚姻的风气,甚至延续到五代宋初。清河大房崔休之后人,尽管在仕宦方面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沦为平民,但在婚配对象方面,却仍然只与卢、李、郑数家通婚。直至宋初,所娶之妇“犹皆卢、李二姓,故世高其门风”[6]1432。可见,旧士族虽呈渐衰之象,但其互通婚姻的习俗仍影响深远。
(二)新贵攀附旧门
唐朝建立后依靠功业、能力或机遇而跻身统治阶级上层的官员,尽管在其所获得的各种特权庇护下,宗族势力得以提升和发展,成功实现了世代仕宦的梦想,但他们在婚姻方面却明显具有攀附旧士族的倾向。旧士族之能够仍然自矜门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贵们的热衷攀附。为了攀附成功,不少新士族甚至自贬其家门,甘心受屈于姻娅。
唐朝初年,新贵攀附旧门蔚成风气。官至宰相的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的宗族,皆联姻于旧士族。此后,这种现象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如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玄宗朝宰相张说,好求山东婚姻;睿宗朝宰相李日知诸子,皆结婚名族。一些没能成功与旧士族联姻的官僚,也明显表露出了艳羡或嫉恨的心态。高宗朝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平生有三恨,“不得娶五姓女”[7]28为其中之一。李义府亦官至宰相,向旧族为子求婚而不得,因而衔恨奏请:禁止陇西李等七家相与为婚。
(三)新贵间互通婚姻
新士族阶层一方面攀附旧士族,一方面又对旧士族以群体内婚自矜而愤愤不平。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新士族间的相互通婚更为常见。这实际上也是群体内婚,也是崇尚门阀,只不过崇尚的是新门阀而已。唐人柳芳所说的“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3]5679,即包含着崇尚新门阀的因素。
唐朝最高统治者为了强化权力,打击山东士族的门阀观念,积极提倡新贵间互通婚姻。针对旧士族“不贵我官爵”的婚姻价值取向,贞观六年(633),唐太宗诏令《氏族志》对新社会等级的认定标准时,曾对人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8]165他还令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显然,这是以身作则,带头实施崇尚新门阀的观念[9]。
新贵间互通婚姻自然可形成崇尚新门阀的风气,但新贵意识中的旧门阀观念却未必就能完全消除。王梵志诗云:“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10]416这应是看重旧士族崇尚礼法的传统习俗。唐文宗欲以二公主下嫁士族,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3]5205-5206这是以皇族之贵而与旧士族争高下,显示出对旧士族社会声望的无奈认可。
当然,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并不局限于崇尚阀阅,也有注重人物、注重财富等各种情况。但就其主流取向而言,崇尚阀阅在有唐一代特别是前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高宗等统治者以皇族之尊打压旧门士族,积极引导新贵间通婚,引领婚姻价值取向由传统门阀向官品、人才等转向,推动“官宦”“忠孝”“道义”“学艺”等成为“天下士大夫”的判断标准,尽管已使社会风气逐渐变化,但也说明传统的门阀观念改变之艰难。可以说,对于官宦世家群体而言,尽管崇尚阀阅的婚姻价值取向已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冲击,但终唐之世尚未形成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取向。
二、贵人物:宋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
中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受新兴势力冲击,门阀势力更加式微。门阀宗族制下“士庶天隔”的门第等级观念,至宋代已基本消失。明代史学家胡应麟指出:“五代以还,不崇门阀。”[11]394“婚姻不问阀阅”[12]1成为由唐及宋婚姻价值取向变化的显著特征。但所谓的“不问阀阅”,并非完全不讲门第,只是不再将阀阅作为首要条件而已。同时,宋人逐渐接受了更为重要的婚姻条件,那便是贵人物,甚至“贵人物相当”。袁采曾告诫世人:“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13]50重视“人物”是一种综合考量方式,不仅包括个人才能,还包括个人资财、家世及家法影响下的个人品行。
(一)人物的才能
在宋代官宦世家的选婿过程中,个人才干已受到相当重视。徐度总结高级官僚的择婿情况说:“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己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14]123由于宋代科举出身受到特别重视,因而新榜进士成为富贵之家选婿的理想对象。姚兆余认为“以才择婿”是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之一[15]。其实,南宋亦然。绍兴二十四年(1154),张孝祥廷试第一,唱第后,出自于官宦世家真定曹氏的曹泳,便急不可耐地在殿廷上向其请婚。下面这段史料,更说明官宦世家于榜下择婿几至于饥不择食:
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有一新先辈,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逊。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16]284
(二)人物的修养
人物的修养主要表现在对礼法的重视。司马光撰写书仪,要求议婚先看对方“家法何如”[17]24。东平吕氏,“时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荐女请昏者不可为数”[18]437。安陆李氏家族,“婚嫁皆择门户,问家法,不问富也”[19]1666。苏轼在为子迈求婚的帖子中,称“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20]1371。他盛赞女方之家法,而对其他方面却可置而不论。这均说明在议亲时对家法影响下人物修养的重视。元祐五年(1090),范祖禹为宋哲宗纳后之事上疏太皇太后说:“闺门之德,不可著见,必是世族,观其祖考,察其家风,参以庶事,亦可知也。”[21]10825可见,即使是皇家择偶,也应将家族的礼法传统当作观察对方的重要指标。在宋代六礼多废、货财相交的社会环境下,官宦世家对人物修养的重视格外引人注目。
(三)人物的资财
宋人赵彦卫曾云:“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22]51既然是“王公之女”,就算“贫乏”,又能贫乏到哪里去呢?富室之能够与其通婚,当然是因为她们特别是她们的家庭看中了富室的资财。而在娶妇的过程中,更不乏看中女方嫁资的情况。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薛惟吉遗孀柴氏,正是因为她拥有巨额财产。司马光在《书仪》中说:“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有鉴于此,他要求人们“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可也”[17]33。但是,官宦世家议婚更多地表现出了“贪鄙者”的嘴脸,而不及于财者则属于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所以宋人才有“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23]618的说法。
(四)人物的家世
尽管宋代已不可能出现门阀制度下的门第婚,但官宦世家对门当户对仍然相当重视。时人彭汝砺曾说:“今士大夫之族议亲,非以德望,则犹以门阀。”[24]327南宋初年大将张俊,所选诸婿为韩世忠第二子韩彦朴、刘光世第三子刘尧勋、杨存中第三子杨亻與,均出自门当户对的将门之家。在一些世代交往的宗族间,人物的家世更多地表现为重视世婚。苏轼曾总结当时的社会状况说:“里闬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以世姻。”[20]1371袁采亦说:“人之议亲,多要因亲及亲,以示不相忘,此最风俗好处。”[13]51社会现实中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陈、吴,皆水南著姓,世姻也。”[25]5992“胡序少宾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宾于夫人实内外兄弟。”[26]291可见,官宦世家之间世代通婚已相当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衡量人物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相互重合的。但其最主要的取向,则在于婚配对象本人的才干与修养。为官宦世家所选中的才干之婿,其家族背景虽有不少属于同等门户,但亦有相当一部分出身相对贫寒。官宦世家姻亲中亦有官位很低甚至并无官位的富室之家,这则是婚姻重视资财的结果。
三、唐宋婚姻价值取向转变的原因
唐宋婚姻价值取向的转向,虽然甚为明显,但无疑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主要是因为影响其变动的诸因素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各种特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消长,使官僚阶层的群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各相关社会群体的地位也随之升降
自唐中叶以后,门阀士族的各种特权逐渐丧失殆尽。尽管依靠家法、门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门阀士族“犹自云士大夫”,但对“世代衰微”的社会现实却无能为力,有些甚至已经“全无冠盖”。政治特权的逐渐丧失,又使其丧失了各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权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由富而贫。如此一来,门阀士族也就只能“身未免于贫贱”了。显然,这样的社会群体已逐渐失去对新兴官僚宗族的吸引力,很难再成为他们议婚时崇尚的对象。
与此同时,新贵宗族通过对现实政治权力的获取,逐渐形成一些当世及世代传承的特权。政治上通过门荫、征辟或科举使子弟不断进入仕途;经济上可以依官位占田,特别是占有永业田,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经商等手段不断扩大势力或维持已有的经济地位。除了现实势力的不断扩大,当权者亦借助传统习俗提升新贵宗族的社会影响。唐太宗时修《氏族志》,崇重“今朝冠冕”;武则天时改为《姓氏录》,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现实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使新贵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从而逐渐消解传统婚姻价值取向中的门阀观念。“五代之际,干戈纷扰,高门旧族,无复孑遗,门第婚姻,已非所尚。”[27]136及至宋代,完全依靠特权而维持宗族地位的情况已十分稀见;官宦世家地位的维持,主要依靠宗族精英人物的功业和能力。随着宋代科举取士数量的增加,科举士人阶层获取的社会权益不断扩大,士人的群体意识不断加强,婚姻选择时更注重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宗族建设。胡瑗曾云:“嫁女须胜吾家者,娶妇须不若吾家者。”人问其故,他的理由是:“嫁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事舅姑必执妇道。”[28]385可见,这是完全以维护宗族人伦秩序为目的的做法。
(二)对官宦世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姻亲网络已逐渐发生了变化
官宦世家通过婚姻结成姻亲关系网络,有利于宗族政治势力的扩大。具有姻亲关系的官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自觉地就会受到人情影响。但这种人脉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成方式。唐前期的旧士族群体,由于继承先前等级婚姻的余荫,已形成比较固定且相对封闭的姻亲圈。旧士族继续相互通婚,有利于维护这一姻亲圈;新士族攀附旧士族,可以借力于已有的姻亲圈;新士族间相互通婚,则可以建立新的富有现实政治能量的姻亲圈。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凡三娶皆山东旧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族属姻家。这种崇尚阀阅的婚姻取向,显然蕴含着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及至宋代,由于官宦世家更易受到社会流动的冲击,因而积极利用已有势力,不断联姻于具有政治前途的人物,才能得益于姻亲关系网络。常州胡氏,“自武平使枢密,宗愈继执政,宗回、宗师、宗炎、奕修皆两制。宗质四子同时作监司,家赀又富,东南号富贵胡家。相传祖茔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壻”。诸婿中有7人“皆为显官,余无不出常调”[29]163。所谓“祖茔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壻”,显然只是个传说。诸婿仕途一帆风顺,无疑与“富贵胡家”的提携和庇护有密切关系。反过来,诸婿政治能量的得以发挥,又对胡氏及各联姻宗族带来各种好处,得以相互奥援。
官宦世家姻亲间通过经济上互助,有利于孤寡贫弱家庭渡过困难阶段。尽管官宦世家具有优越的生存条件,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相对经济困难。那些孤寡贫弱的家庭,往往需要姻亲的帮助。唐前期有些旧士族面对经济上的不断衰弱,通过“卖婚”寻求补偿。这对其经济地位的维持,显然是有益的。但唐后期出现贫女难嫁的现象,说明人们看重贵贱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贫富观念的冲击。正如白居易所吟:“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30]30两宋时期,商品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贫富更不稳定,婚嫁也更加看重人物的资财。在出现家道变故时,姻亲之家往往会相互帮助。理学开山人物、营道人周敦颐幼孤,依靠舅家的抚养教育,才得以成人成才。江阴人赵越,同情其妹贫不能自存,甚至连其夫与子一起养于家。浦城章氏的章钅监之母盛氏,字养早孤的侄子盛如杞将近20年,直至其进士及第。似此类事例,均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三)社会流动性的变化,使个人能力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
自九品中正制废罢、庄园农奴制衰落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科举制为士人提供了依靠经学知识和文学才能向上流动的机会,募兵制也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了依靠军功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社会现实,逐渐使官宦世家在议婚时越来越看重个人才能。唐朝进士在放榜后,于曲江亭大宴,是时往往为官宦世家择婿提供了机会。“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31]17此类情况延续至宋朝,更为兴盛。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32]659苏轼亦有诗云:“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33]222宋代的官宦世家,其起家人物依靠个人才能带来宗族长远利益者不乏其例。安州宋氏的宋庠、宋祁兄弟,在考中进士之前曾于上元佳节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真定韩氏和徐州李氏的起家人物韩亿与李若谷皆出身贫寒,一同赴京师参加科考期间,每次拜访宾客,便更替扮成一主一仆。以巨富而知名的成纪张氏,起家人物张俊在16岁时曾应募为弓箭手。可见,宋代的许多官宦世家是从中小地主或农民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崇尚人物才干逐渐成为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不足为奇的。
四、结 语
官宦世家婚姻对象的选择,主要是由其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官宦世家在婚姻方面的价值取向,往往能引导其他社会群体。因而,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官宦世家择婚的价值取向在某些方面并无明显特殊之处,只是在价值认可程度上更为突出而已,而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则可能为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及。
唐宋时期,尽管官宦世家单一价值取向的婚姻不是没有,但更多的婚姻往往是多重价值取向综合考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单一价值取向,还是多重价值取向的综合考量,其社会主流取向则明显表现出从“尚阀阅”到“贵人物”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唐代旧士族曾在前朝取得众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特权,尽管入唐后政治特权日益缩小,但经济势力的衰败则相对缓慢,而文化优势的丧失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唐代的新士族不断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并通过施政行为逐渐形成对该群体有利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从而成为上层社会中的核心群体。宋代的官宦世家,虽然也有一些唐代士族的后裔[34]通过宗族衰败后的重新起家而兴盛于新王朝,但更多的是新兴宗族,因适应社会需要而能够世代仕宦,社会地位得以相对长久地维持。唐宋官宦世家群体的变迁,尽管使其主流的婚姻价值取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核心的取向仍然是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可以说是转变中的不变因素。
———崇尚“大”的短暂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