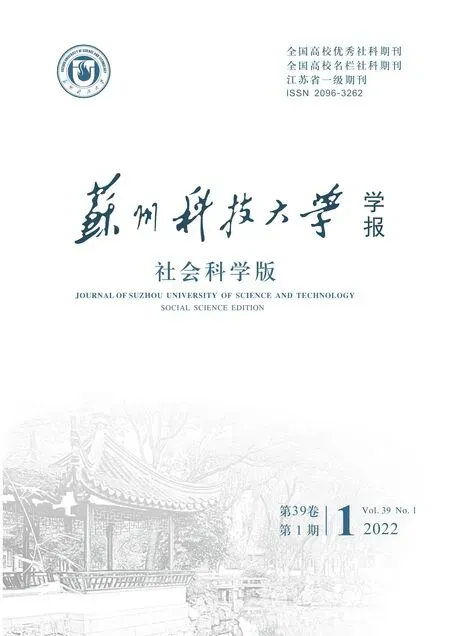《琼创造历史》与澳大利亚新历史小说热潮*
黄 洁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20世纪下半叶,历史小说在文学领域经历了一场广泛的复兴。历史小说的对话性、公共性和潜在的再生产能力,决定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许多边缘群体如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新解放政体公民等,开始公开发声,质疑历史本身的权威性。在澳大利亚,20世纪后期涌现的一大批历史小说虚构书写真实人物,以达到挑战更正统的民族主义版本的“过去”的目的。通过该实践,历史的“去神秘化过程”得以展开。[1]
以历史书写奠定澳大利亚乃至英联邦主流作家地位的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的《琼创造历史》(JoanMakesHistory, 1988,以下简称《琼》),展现了当代女作家对本国历史的崭新解读。该作品试图重新定义“澳洲殖民二百周年庆”(Australian’s Bicentenary,下文简称“二百周年庆”)所标记的白人在澳洲的“殖民功绩”,不仅强调女性于重大历史时刻的“在场”地位,而且认定女性是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主人公。在澳国内,该小说的热度不及作家同时期的“沃格尔文学奖”(Vogel Literary Award)获奖作品《莉莲的故事》(Lilian’sStory, 1985);我国文学评论界对她的这两部早期作品的态度也大致相同。然而,21世纪的读者应该看出《琼》作为女性新历史小说更具典型意义。除了再现澳现代史上首次全国性庆典的文化影响力[2],读者还可从中探知以下重大问题的答案:澳大利亚新历史小说热潮孕育于怎样的国际国内语境?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兴盛及退潮如何影响女作家的历史书写?该小说在内容和样式上如何呼应“二百周年庆”时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使其在整个社会面临被撕裂的危机时刻免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议?笔者试从这三个方面对小说展开分析与阐释。
一、国际国内语境
针对20世纪后期历史题材小说纷纷获得重要奖项的现象,批评家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在《剑桥现代英国小说指南(1950—2000)》(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ModernBritishFiction, 1950-2000)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英国小说出现明显的历史小说转向,这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粗砾的工人阶层现实主义”形成对照。[3]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现代英国小说》(TheModernBritishNovel)中也认为,20世纪后期英国小说家一再重访历史上的危机时刻与危机场景,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事实上演变为“历史的回归”[4]。迈克尔·麦基恩(Michael McKeon)在《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TheOriginsoftheEnglishNovel, 1600-1740)中致力于探寻该热潮的源头,认为英国有历史小说的传统,“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爵士的作品深刻影响了该国的小说创作,新历史主义思潮在欧美的盛行也催生了大量的新历史主义小说。[5]尽管历史小说在英国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后期兴起的“历史小说热”却不是英国所独有的。(1)从1980年以来获“布克奖”的历史小说作家身份便可看出这一点:14位作家中,6位来自英国,4位来自澳大利亚,2位来自加拿大,1位来自牙买加,1位来自新西兰。
加拿大学者麦尔达·丹尼特(Milda Danyte)在分析这一世界范围的热潮时指出,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安塔纳斯·西雷卡(Antanas Sileika)等人创作的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以往的模式,而是“后后现代历史小说”。这些新型历史小说“不像19世纪的作品那样盛赞民族神话或民族英雄,又不像后现代作品那样戏仿过去。相反,它赋予非官方记忆以优先权,并在广泛的意义上赞美通俗文化”[6]。换言之,在传统的历史小说或后现代历史小说中,关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即使以反讽的方式展现,也都支配着人物;而在“后后现代历史小说”中,主人公在大众文化内部找到了另一套价值体系。
澳大利亚语境下的“新历史小说”概念最先由批评家彼得·皮尔斯(Peter Pierce)于1992年提出。在《捕食过去:一些近期新历史小说的语境》(“Preying on the Past: Contexts of Some Recent Neo-Historical Fiction”)一文中,皮尔斯将彼得·凯里(Peter Carey)、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e)、罗德尼·霍尔(Rodney Hall)、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等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表现出与以往历史小说显著差异的作品称作“新历史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小说来书写历史的方式得到重新审视。20世纪中期最具影响力的澳历史小说家埃莉诺·达克(Eleanor Dark)的作品集,展现的是对历史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上的尊重,而凯里、德鲁等人更多表现出对现实的兴趣,他们质疑以往的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准则,并对其展开无情的剖析和披露。[7]批评家苏珊·勒维尔(Susan Lever)则指出,站在21世纪初回顾,运用主观性较强的历史小说修正澳大利亚历史,似乎是20世纪后期的一个“集体方案”。[8]她梳理了这批历史小说的创作情况,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主流男性作家的作品上,包括霍尔的“严迪利三部曲”(Yandilli Trilogy, 1988-1993),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andLucinda, 1988)、《凯利帮真史》(TrueHistoryoftheKellyGang, 2000),德鲁的《我们的阳光》(OurSunshine, 1991)、《溺水者》(TheDrowner, 1996),马洛夫的《忆起巴比伦》(RememberingBabylon, 1993)、《科洛溪边的谈话》(TheConversationsatCurlowCreek, 1997),利亚姆·戴维森(Liam Davison)的《白女人》(TheWhiteWoman, 1994)等。对女作家作品,勒维尔只重点提及格伦维尔的《琼》。事实上,同时期其他女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严肃历史小说,如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的《善意杯》(AKindnessCup, 1974)、《雨影的多重效果》(TheMultipleEffectsofRainshadow, 1996),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 Anderson)的《司令官》(TheCommandant, 1975),吉恩·贝德福德(Jean Bedford)的《凯特妹妹》(SisterKate, 1982)、《恰似一颗悸动的心》(IfwithaBeatingHeart, 1993),芭芭拉·汉拉恩(Barbara Hanrahan)的《切尔西女孩》(AChelseaGirl, 1988)、《晚安,月亮先生》(GoodNight,Mr.Moon, 1992),等等。
澳本土学者大多格外关注小说家对历史小说社会功能的运用。凯琳·高尔兹华斯(Kerryn Goldsworthy)认为,澳小说家一次次回归历史小说,是在寻求关于民族建构、另一种历史书写、为殖民罪恶赎罪或者对他们自己的时代进行评论的方式。[9]戴尔斯·伯德(Delys Bird)将20世纪后期澳历史小说的复兴视为“作家们转向历史,去寻求向混乱的当今注入某种秩序和召唤集体记忆的方式”[10]。对女作家而言,回归历史小说显得尤为迫切。澳当代女性写作所处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民族主义神话的持续影响力、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土著的土地和财产剥夺问题、“二战”后从英国以外的欧洲和亚洲移民造成的冲击等,其结果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地位愈加牢固。女作家们始终致力于颠覆该版本的历史,她们不信任统一的、同质性的历史话语,许多当代女作家均与某种独特的“地方声音”(local voice)相认同,如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与西澳,奥尔加·马斯特斯(Olga Masters)与科巴戈,海伦·加纳(Helen Garner)与卡尔顿。[11]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她们描摹或远或近的历史,或多或少地展开叙述实验以探索纷繁复杂的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个体写作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澳大利亚女性新历史小说还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英语国家涌现的一批以普通女性为关注焦点的历史小说遥相呼应,其中包括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 1987)、A.S.拜厄特(A.S.Byatt)的《占有:一段罗曼史》(Possession:ARomance, 1990)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别名格蕾丝》(AliasGrace, 1996)。这些女作家集中关注被包括正史在内的官方话语所压制或掩盖的女性的真实生活,“历史小说为妇女和女性角色提供了一个‘收回主权’的手段,这一叙述上的授权使妇女得以成功恢复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12]。在创作手法上,这些女作家“质疑一个一元的、线性的历史。她们通过重写经典文本,通过多重的或分裂的叙述者、碎片式的或自相矛盾的叙述以及对线性编年表的瓦解,强调了历史知识的主观的、支离破碎的本性”[13]。
二、女性新历史小说与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
无论在欧美还是在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主力军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将目光投向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女性从属地位的溯源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20世纪早期对历史话语权和女性地位二者关系的分析在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那里得到重申。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赋予“她历史”(her-story)以重要性。“她历史”意味着对不为人所知或并无确切记载的女性生活的挖掘,使原本没有历史地位的普通妇女成为历史考察的主角。“她历史”策略对历史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对一些文献的重新评估,如日记、书信等,以往被认为太过主观,无法被纳入历史话语,后来却以传记、回忆录等作为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收集关于历史上的妇女的相关证据,它驳斥了坚持妇女‘没有历史或在历史上没有重要地位’的一批人的论调。”[14]在英美等国,拜厄特、莫里森等女作家对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倾注了极大热情,创作出一系列迥异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小故事”。在《关于历史和故事:论文选》(OnHistoriesandStories:selectedessays)中,拜厄特指出历史是线性的和前进的,又是环状的和复调的,比起宏大的历史书写,她主张复兴“小故事”的创作。她还认为,女性被排除在男性的历史叙事之外这一现实是女权主义者在后殖民小说中重写历史的源动力。[15]170澳大利亚的情况正印证了拜厄特的分析:“当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创作出不同版本的历史的同时,女作家也正在发表‘另类故事’。通过小说这一媒介,她们得以在历史再现的问题上进行磋商和试验。”[16]
澳大利亚女性作家群体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并非孤军奋战,而是与历史研究诸领域女性学者的基础性工作同向而行。20世纪70年代中期,澳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历史学领域起步,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的《该死的娼妓与上帝的警察》(DamnedWhoresandGod’sPolice)作为奠基之作,是典型的“女性形象”批评,聚焦根源于殖民历史的两大刻板型女性形象。萨默斯指出,奉行性别主义的早期澳大利亚社会拒绝承认女性的文化潜能和经济地位,从而导致她们不能建构自身独立身份,在个人生活中也无法做出自由选择。评判女性邪恶还是善良,就看其是否遵从资产阶级家庭所规定的妻子/母亲的角色。[17]。
《琼》既反映了女权主义任务中“挖掘被正史湮没的女性”部分,又展现了追寻女性自身的写作传统、通过重新定义历史来争夺在民族叙事中的话语权部分。格伦维尔在谈到女作家遭受长期冷遇以及女性内部形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时指出:简·奥斯汀(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伍尔夫等标志性女作家是陷入男作家汪洋的伟大而孤独的灯塔。男作家会使人们产生谱系感,而标志性女作家的存在却很突兀,这是因为其基座——众多二流女作家在彼时被轻视,在此时陷入沉寂。时至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创造了女性共同体的氛围,使格伦维尔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的同时,对自己能够写出不同于以往女性作品的小说拥有足够的自信:“我读了《女太监》(TheFemaleEunuch, 1970),并被它彻底改变了。萨默斯的《该死的娼妓与上帝的警察》实际上播下了《琼》的种子。”[18]
通过刻画不同肤色、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12位“琼”,小说呈现了200年的澳洲女性生活图景。除了当代的东欧移民之女琼·雷德曼(Joan Redman),出现在各历史时刻的“她”分别是1770年随丈夫航海的妻子、1788年的女流放犯、1795年的土著少女、1839年的自由移民、1851年的金矿区洗衣妇、殖民扩张时期的女佣、1855年的总督夫人、种族隔离前夜的混血女子、1878年的摄影师女助手、19世纪末的丛林妇女和1901年的镇长夫人。将这些历史上的“琼”的人生与“前景”中的当代女性的境遇相比照,更能凸显她们看似相同却又各不相同的命运。每一位“琼”都是一个全新的个体,都要求讲述她独一无二的故事,但所有这些女性的命运又共同构成一个独特的女性传统。历史上的“琼”们的故事和雷德曼这位个人反叛以“失败”告终的当代反英雄式人物的故事互相呼应,两股支流在小说末尾汇成一股合流:参加联邦成立仪式的镇长夫人无法融入上层人物的行动,她顿悟后决定告诉孙女不会在史书上出现的“另类故事”;而琼·雷德曼已是一位心满意足的祖母,她相信自己“创造了历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转入后高潮阶段,女性写作的主要内容转为反思激进,检讨前期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历为基准的价值观和倾向,并积极展开语言与形式实验。相应地,格伦维尔的女权主义历史观在《琼》中也经历了从激进到缓和的戏剧性变化。历史上的“琼”在小说开头企图代替男性创造历史,后来则与男性并肩创造历史,或致力于纠正男性创造的历史中的可疑观念。“格伦维尔的信条是妇女不应该试图步男人的后尘,创造出他们那样的历史,而是应当要么使历史编撰‘去阳刚化’,要么试图在她们自己的领域——家庭中创造历史。”[19]312因此,与前一阶段的澳女性历史小说不同,《琼》“要缓和得多,可能这指向一个即将发生的变化,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好战的女权主义或女性研究向90年代更为放松的社会性别研究转变”[19]310。《琼》不仅标志着格伦维尔个人创作倾向的转变,还标志着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写作的总体转向。
三、危机时刻的女性历史书写
《琼》创作于澳大利亚人深刻反思自己的民族历史、试图重新定义民族身份的“二百周年庆”时期。该时期活跃的各方势力,无论是以工党为代表的左派,以自由党和国家党为代表的右派,还是其他中间势力,都纷纷参与角逐。土著团体、移民团体、妇女组织等原本被边缘化的群体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发表各自的观点,争取自身的权益。持续不断的左右派论战、土著的游行示威、移民对曾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抗议、女性对自身地位的不满等不同声音尖锐碰撞,使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犹如沸腾的汤锅。表面上看,“二百周年庆”似乎是现代国家面临被撕裂的危机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各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阶段。该时期澳大利亚人思想空前活跃,创造的文化成果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应时之作,《琼》可谓各方势力参与角逐的一个话语场。其中既有对殖民史的黑暗面进行披露和批判的一面,又有对传统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进行肯定和重申的一面。在核心家庭的问题上,既可把作家对核心家庭重要性的强调视为她反思激进女权的结果,又可将其看作她对民族大讨论中的保守派呼声的回应。
围绕如何阐释澳大利亚的历史,尤其是欧洲人在澳洲大陆的早期殖民史,当代澳文化界长期存在一个被称作“历史战争”的重要文化现象。格伦维尔的《神秘的河流》(TheSecretRiver, 2005)(2)《神秘的河流》曾获得包含“英联邦作家奖”、“克里斯蒂娜·斯戴德小说奖”、“布克奖”短名单提名、“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短名单提名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并在超过20个国家被翻译出版。就知名度和影响力而言,《神秘的河流》无疑是格伦维尔目前最成功的作品。自出版之日起就成为“历史战争”的一个新焦点,来自历史学阵营和文学阵营的意见不同,一度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这与17年前脱胎于“多事之秋”、同样探索殖民历史问题的《琼》被普遍接受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将两部作品做一番比较便可看出,她在《琼》中对保守派价值观的回应、在土著问题上积极探索的姿态和公开承认作品中的历史性错误等做法,恰恰为其免除了后期历史书写引发的争议。
琼·雷德曼起先不满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既定命运,她选择逃离缺乏有效沟通的家庭生活和让人窒息的干旱内陆环境。但她发现,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根本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而在现实中伪装成男性的生活又违背了她的本心,于是她认识到,家庭这一领域才是她真正可以创造历史的场所。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选择回归家庭。但这一回归并不意味着倒退,因为她的丈夫邓肯在妻子逃离家庭后开始反思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当琼出于自身意愿返回家庭后,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理想状态。
在《神秘的河流》中,格伦维尔选择放弃再现土著的主体意识。她认为自己无法进入土著达拉戈人的意识,因此留下一个“空洞”来提醒读者其存在将更有说服力。批评家爱丽丝·希利(Alice Healy)认为,该做法是一个“忧郁的脚注”,它提醒公众,对澳大利亚殖民史进行反思的“历史战争”恰恰将土著排除在外。[20]而在《琼》中,格伦维尔没有回避对土著主体意识的再现。两个以土著女性为主人公的章节——澳洲土著与英国探险家初次接触的场景、热衷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探险的混血女子与新科技成果火车相遇的场景,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这两位土著女性与其他场景中的白人女性无疑处于同等的叙述地位,她们的声音清晰且坚定,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女性自我意识。
在《琼》的序言里,格伦维尔提醒读者不要指望在小说中看到历史现实主义。文中暗示,所有的历史场景都是20世纪的琼·雷德曼想象的结果,该结构安排使作家不必在历史的真实性上耗费太多精力。小说开篇描绘宇宙的浩瀚、斗转星移的变化、地壳的运动、物种的形成和进化。在此背景下,琼·雷德曼宣布:“我,琼,曾是所有这些生命……我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还是曾存在和呼吸过的任何一个普通女人:在历史的任何一次事件中都曾有一个琼在做饭、洗衣、拖地,虽然迄今为止任何一本书中都没有提到她。”[21]5《琼》的结尾处,当年老的琼回首过往人生时,她并不懊悔自己没有做出常人眼中的不朽功绩;相反,她认为自己作为妻子、母亲和祖母所做的点滴小事,都有资格被载入史册。通过解构“大历史”和“小故事”的二元对立,小说消解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基于意识形态的人为划分。
《琼》强调女性的“在场”地位。当库克船长发现新大陆时,她在场;当“第一舰队”在植物湾登陆时,她在场;当移民在丛林拓荒时,她在场;当贫民被“神圣的饥饿”驱使而在澳洲东部掘金时,她在场;当内德·凯利将要开创一则崭新的民族神话时,她在场……出现在不同时期的“琼”,要么对历史事件进行“兜底式”评点,要么直接以自己的方式干预或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些不同的叙述声音和视角打破了主要叙述者“惟我独尊”的叙述模式。通过将这些叙述者的身份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或人物相联系,作家还达到了瓦解正史的单一性和正统历史叙事的权威性的目的。
格伦维尔响应“二百周年庆官方机构”(Bicentennial Authority)关于“凝聚共识、着眼未来”的号召,有意识地回应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的各方呼声。这种贴合时代精神的开放态度接近折中主义,但并不等于说《琼》是一部毫无锋芒的“中庸之作”。小说最具革新意味的部分在于女作家致力于使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传统“去阳刚化”。通过再现19世纪末大萧条下普通丛林女性的命运,她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民族主义的文学文化传统。“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深受灾难性大萧条的折磨。当时,人们认为介入市场的自然运作的行为不明智,结果造成很多人慢慢饿死。萧条的景象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在同一时期,独特的澳大利亚艺术开始繁荣,在其中,我,琼,找到了一个永恒位置。”[21]227“永恒位置”指画家弗雷德里克·麦卡宾(Frederick McCubbin)的名画《漂泊不定》(OntheWallabyTrack, 1896)。格伦维尔挖掘了殖民时期的丛林女性可能经历的磨难和艰辛,并尝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琼”机缘巧合下成为画家的灵感缪斯,她在流浪途中与另一位丛林妇女的相识相知、相互扶持更是对公认的澳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伙伴情谊”(mateship)的补充和修正。“伙伴情谊”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是适应开拓荒凉辽阔的澳洲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那个提倡工会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的产物”[22]。“伙伴情谊”是19世纪90年代的时代精神,与澳大利亚的男性气质乃至民族身份有着密切关联,更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热情讴歌的重要内容。
在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等男性作家主导的民族主义文学传统中,“伙伴情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但正如女性在其中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描绘丛林女性之间深厚情谊的部分同样是一块明显的空白。《琼》对“伙伴情谊”引以为基础的两性关系的牢固地基提出了质疑。在这位丛林妇女“琼”的故事中,格伦维尔试图通过再现普通丛林女性之间毫无保留、倾其所有帮助落难同胞的“姐妹情谊”,来揭示并填补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留下的空白。由于“二百周年庆”时期最突出的论争焦点是土著问题,而非妇女问题,所以作家以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参与不同利益群体角逐的话语场的行动并未引起争议,反而顺利地融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学术界反思民族主义文学文化传统的大潮。
四、结 语
出于“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和未被记录的人的历史的政治欲望”[15]12,以格伦维尔为代表的当代澳女作家侧重在其作品中以较大篇幅去挖掘和探索自己熟悉的题材——女性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并以私人化的话语去“柔化”历史所代表的公共话语。格伦维尔在《琼》中不仅关注男性民族主义历史中女性“缺场”的问题,还关注女性历史应该怎样撰写的问题。她将“二百周年庆”时期复杂的民族意识铺陈于纸面,以小说这一虚构形式书写另类真实:早期白人殖民者对土著的掠夺和迫害,民族主义历史编撰者对女性、土著等边缘群体的压制,被启蒙运动式线性的历史书写所忽视的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劳动妇女)的日常劳作的价值等。《琼》还反映了作家女权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琼”起初试图创造出区别于男性版本的女性历史,后来则致力于改变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看法。
作为对“历史正典”展开反思和颠覆性改写的“伪经故事”,《琼》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还反映了女作家独特的文化诉求。格伦维尔无意宣扬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而是以一种诙谐的戏说风格来淡化它可能具有的争议。正因为如此,苏珊·谢里丹(Susan Sheridan)称其为“不恭敬的喜剧”[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