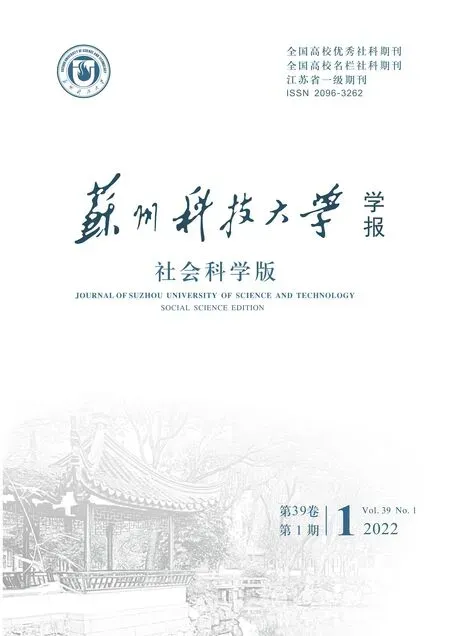19世纪美国的妇女俱乐部及其社会参与*
——以城市环境卫生改革为视角
李 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美国妇女俱乐部(Women’s Clubs)肇始于19世纪中期,是以女性的名义联合起来的为实现某种共同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它既包含以自我教育为目标的文学俱乐部,也包括以社会改革为己任的改革型俱乐部。其目标不仅在于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教育其成员,而且旨在塑造公共舆论及保障良好的生活水准。[1]妇女俱乐部是19世纪美国社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其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及社会各个领域。作为妇女俱乐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城市环境卫生改革是其对工业文明综合征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其试图通过改善城市环境以提升公民健康的道德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改革成为女性提高其公共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研究美国妇女组织的著述颇丰,但对妇女俱乐部的专题研究不多。笔者拟从19世纪美国女性的传统角色入手,剖析妇女俱乐部诞生与发展的背景,并以城市环境卫生改革为例,考察俱乐部引领女性参与社会改革的过程,揭示妇女俱乐部对于19世纪美国女性社会地位转变的推动作用以及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一、美国妇女俱乐部诞生的背景
妇女俱乐部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断变革的产物,也是美国女性突破传统角色、争取自身权利的结果。虽然独立战争的胜利涤荡了北美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但并未从根本上给北美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带来革命性变化。独立后的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习惯[2],这注定了女性的权利斗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两分领域”(separate sphere)是十八九世纪衡量美国两性关系的标尺。它认为,男性应从事商业、政治等竞争激烈的公共领域活动;而女性温顺、热爱和平的特性决定了她们的责任就是管理好家庭,努力成为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它被19世纪的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由此产生的“真女性信条”(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成为衡量女性品德的重要标准。“真女性信条”规定,女性要虔诚(piety)、纯洁(purity)、顺从(submissiveness)及守家(domesticity)。[3]多数女性欣然接受该信条,并将其视作自我检验和被丈夫及传统社会检验的标准。
“真女性信条”对美国女性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将女性束缚于家庭的围墙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智性发展。另一方面,它赋予女性的家庭责任不仅使其家庭管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也给予了她们特别的社会责任,即“共和国母亲”(Republican Mother)的身份和天然的文明开化者的角色。当19世纪美国的公共道德缺失之时,“真女性信条”将女性的家庭责任拓展到公共领域,使其利用独特的身份管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从这一点看,它赋予了女性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4]
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政治民主化进程加速、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勃兴、社会分工发生变化、思想和文化繁荣、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加等。社会的大发展使女性开始重新审视“真女性信条”下自身的生存状态,期望打破传统角色的束缚。18世纪90年代妇女慈善组织的诞生,便是女性试图通过联合的方式实现社会参与、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标志着美国女性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些慈善组织主要通过护理、教育、帮助贫困者、孤儿和妇女等工作提供社会救助,涉足社会多个领域。成立于巴尔的摩、纽约及费城等地的妇女人道主义协会(Female Humane Association)除了为贫困妇女和儿童提供衣物、食物等,还开办了慈善学校,传授缝纫、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基本知识;在波士顿,成立于1812年的妇女慈善组织——片段协会(the Fragment Society)致力于帮助失业者、孤儿、寡妇、孕妇等,共资助了1.02万个家庭,分发了3.9万件衣物,资助金额达2.23万美元。[5]这些社会活动激发了美国女性的母性情怀,体现了她们走出家庭的渴望和纠正社会问题的道德责任感。
19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和内战进一步深化了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她们渴望获得平等权利的呼声更加强烈。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的支持下,1833—1838年,超过100个妇女反奴隶制协会在美国东北部城镇相继成立。作为反奴隶制的重要参与者,女性通过撰写小册子和演讲等方式奔走疾呼,在唤起国民意识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内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的组织化。成千上万的妇女联合起来,组建了联邦卫生委员会(the Union’s Sanitary Commission),通过募捐的方式向联邦军提供食物、衣服、医疗物资和医疗服务。废奴运动和内战使女性获得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她们进行公开演讲,组织各类会议,同政治家和民众进行互动,目标更加明确,政治意识开始觉醒。
上述因素推动了19世纪美国女性争取权利运动的展开。1848年,一群女性废奴主义者在伦敦参加废奴大会时因性别被拒绝入场,这直接激发了她们要求获得平等权利的想法。她们组织召开了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为争取平等的教育权、职业权、法律权及政治权利而战,美国女权运动由此诞生。同时,妇女权利斗争也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6]在这场斗争中,一部分激进的女性发起了选举权运动,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大部分女性虽没有勇气进行激烈的斗争,但又不甘屈服于“真女性信条”。这些女性在激进的选举权斗争和传统的女性角色之间,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改革,即利用其道德卫士的力量,组建形式各异的组织,妇女俱乐部由此诞生。
二、被组织起来的女性:美国妇女俱乐部的兴起与发展
美国妇女俱乐部的诞生是女性渴望摆脱“真女性信条”、走向社会领域的产物。它经历了从文学俱乐部向改革型俱乐部的转变。俱乐部女性试图利用其独特的家庭角色影响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一)以“家庭女权主义”为基础的文学俱乐部的出现
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发现,美国人遵循一种“联合原则”(principle of association):他们成立了各类组织,服务于宗教、慈善及其他社会改革。[7]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由美国妇女创建的各类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s or Societies),便是这样一种自发性社团。女性通过学习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家政等知识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素养。
文学俱乐部的指导思想是“家庭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家庭女权主义”一词由历史学家丹尼尔·斯科特·史密斯(Daniel Scott Smith)提出,是指19世纪的美国女性力图在家庭中赢得自主权、争取管理权的思想。[8]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俱乐部女性将自我教育作为主要目标,通过读书和交流,拓宽视野,加强对家庭的管理和对社会的认知。当她们被社会问题吸引并开始讨论公共事务时,自我提高的活动便同社会改革和国民福祉结合起来。这类组织也成为妇女俱乐部的雏形。如1852年在密歇根州成立的妇女图书协会(Ladies Library Society)和1859年在印第安纳州成立的密涅瓦协会(Minerva Society),都旨在使女性获得知识的同时,了解家庭以外的世界,最终为妇女权利而斗争。这两个团体的成员成为内战后俱乐部运动的重要领导人。[9]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开拓性的妇女俱乐部是妇女联谊会(Sorosis)。它由一位女权主义记者简·坎宁安·克罗利(Jane Cunningham Croly)创建。当克罗利和其他几位女性因性别而不被允许参加在纽约市为查尔斯·狄更斯举办的欢送晚宴时,克罗利决意建立一个专属女性的组织,专门处理自身事务,代表自身的利益。[10]151868年3月的第一个周一,五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在克罗利纽约的家中召开会议,成立了妇女联谊会,妇女俱乐部的想法正式实现。
建立伊始,妇女联谊会仅有12名成员,大多是职业女性。当时,尚未有人听过“妇女俱乐部”,或任何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世俗组织。因此,妇女俱乐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妇女联谊会以自我教育为主要目标,但其成立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它本身所蕴含的女权主义思想,因而遭到男性的质疑、抨击甚至羞辱。尽管如此,她们仍顶住压力,不仅向女性传播独立和民主的思想,还努力组织丰富的活动,希望得到肯定和支持。最初,联谊会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和音乐四个委员会,将阅读、讨论和自我教育作为主要内容。随着联谊会的发展,它逐渐将自我教育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成立了科学、慈善、卫生、时事等常务委员会,致力于女工、环境卫生、公共教育等与社区相关的问题。
妇女联谊会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激励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成百上千类似文学俱乐部的涌现,引发了一场由女性领导的俱乐部运动。这场运动横扫全国,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美国妇女的“文艺复兴”[11]。以妇女联谊会为首的文学俱乐部对于女性个人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将拥有共同利益与目标的女性联合在一起,教授她们大量知识的同时,成为她们谈论自由与民主、培育独立意识的重要场所。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学俱乐部悄然发生变化。女性开始抨击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引发的社会堕落和不公,并逐渐转向社会服务与改革,其影响力得到更为广泛的提升。
(二)城市管家理念指导下的改革型妇女俱乐部的发展
“城市管家理念”(municipal housekeeping)指女性将其特殊的道德品质和家庭管理技能运用于家庭以外的活动的理念。[12]相对于“家庭女权主义”,城市管家理念不仅提倡女性的独立,而且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改革型妇女俱乐部的指导思想。随着内战后工业化的推进和人口的剧增,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文学俱乐部的女性立志利用道德卫士的责任拯救美国社会,“城市管家理念”由此诞生,并推动文学俱乐部向改革型俱乐部转变。该理念既有利于维护女性的传统角色,又能帮助她们顺利地成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守护者。
在城市管家理念的指导下,妇女俱乐部经历了全面的变革。它们开始设立更宏大的社会改革目标,加入由政治家、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等组成的社会运动。为了提高效率,妇女俱乐部逐渐制度化、组织化,建立了明确的指导方针、行动纲领和项目,参与各地、各州及全国性事务管理;有的还建立了宣传机构,影响力不仅深入社会基层,还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与此同时,妇女俱乐部成立了分工细致的部门,其内容从文学、艺术研究发展为一般性研究和社会改革,部门俱乐部(the Department Club)由此形成。部门俱乐部由负责具体事务或计划的各部门组成,专门应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及城市问题的凸显,另一种俱乐部形式——市政俱乐部(the Civic Club)诞生。第一个市政俱乐部——费城市政俱乐部(the Civic Club of Philadelphia)出现于1893年,主要解决城市问题,旨在提升公共精神及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10]76
妇女俱乐部发展进入高潮的标志是全国妇女俱乐部总联盟(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简称“总联盟”)的诞生。在妇女联谊会的推动下,总联盟于1890年正式成立,其目的是“促进全世界范围内妇女俱乐部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并为彼此提供裨益”[10]98。总联盟由各地方妇女俱乐部以及各州的妇女俱乐部联盟共同组成。1896年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举行的年会显示,总联盟共有495个直属的成员俱乐部及20多个附属的州级妇女俱乐部联盟,而州级俱乐部联盟的成员俱乐部数量达800个。[13]到1906年,总联盟的成员俱乐部数量已达到5000个。除此之外,总联盟还吸引了各类妇女协会、改革组织、健康保护协会、妇女教育与工业联盟及海外妇女组织的加盟,扩大了工作范畴和影响。
总联盟除了保留之前自我教育的目标,还积极推行社会改革,试图在各个社区推动文明化的进程。总联盟主要通过各委员会开展工作,包括艺术、教育、家政学、资源保护、市政服务、童工、立法等。在总联盟的指导下,妇女俱乐部的工作更加系统化,改革力度和范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扩展。在女性的努力下,社区修建了各类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诊所、公立大学、职业介绍所、安置所、城市游戏场等;各州俱乐部联盟还成立了艺术、文学、教育委员会,市政和乡村改进委员会,工业环境委员会,举办有关慈善、垃圾处理、家政学、监狱改革等的茶会、朗诵会和讲座。这些活动为公众创造了更优良的生活环境。
至此,妇女俱乐部完成了以单一的自我教育为目标向教育与社会改革并重的转变,俱乐部真正成为19世纪美国女性影响政治和社会的媒介。通过发起形式各异的改革活动,俱乐部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了独特的社会价值观[14],用道德卫士的特殊角色重建社会公正。在此过程中,她们将家庭管理才能应用于公共领域,其政治技能、公共演讲、组织能力等均得到了锻炼,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尊敬,为其平等权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
三、妇女俱乐部的城市环境卫生改革实践及其社会参与
随着19世纪美国工业城市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多,城市环境迅速恶化,成为各类疾病的温床,严重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和生命,腐蚀着美国人的道德。俱乐部女性发挥城市管家的作用,以社会公正与民众福祉为名,通过宣传教育、调查研究、揭露批判、游说进言及与男性合作等方式,发起了一场通过环境卫生改革以重建健康生存空间的运动。在城市环境卫生改革过程中,俱乐部女性通常先发现问题,再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应对措施,最后发起试验性工作。在实施具体工作时,她们通过教育市民及游说政府,推动相关法律的通过。
19世纪,致力于城市环境卫生改革的妇女俱乐部遍布全美,譬如著名女性领袖简·亚当斯(Jane Addams)领导下的以赫尔之家(Hull House)为首的各大安置所(social settlements)、卫生保护联盟(the Sanitary Protective League)、街道清理协助协会(the Street Cleaning Aid Society)、城市秩序联盟(the Municipal Order League)、波士顿妇女市政联盟(the Women’s Municipal League of Boston)、芝加哥妇女城市俱乐部(the Women’s City Club of Chicago)等。如果说男性关注商业发展、政治运作和城市规划,那么女性则用其独特的道德情怀拯救了城市环境。在俱乐部女性的通力合作下,美国城市环境卫生改革如火如荼地推进。
俱乐部女性发起了一系列高调的城市清洁行动。她们宣传清洁理念,揭露危害城市环境的行为;设立了多个实践项目,游说市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并颁布法令,以推动更加健康和舒适的城市环境的创建。这些女性也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加利福尼亚州妇女俱乐部联盟提议各地区在街道和学校放置垃圾桶,集中收集铁皮罐;组织少年市政联盟,让孩子们分担维护城市卫生的责任;鼓励孩子们植树种花,庆祝植树节和鸟类保护日;督促市政部门为学校和社区提供卫生的饮用水,同时敦促旨在保障妇女儿童卫生和健康的立法的通过。[15]纽约市的15名女性对城市街道上未得到及时清理的垃圾深感愤懑,她们于1884年成立了首个以卫生改革为目的的妇女健康保护协会(the Ladies’ Health Protective Association),发起了一场清扫街道垃圾、改善居民住房状况、清理屠宰场及改善学校卫生状况的运动。底特律妇女俱乐部联盟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敦促市政官员修建公共浴池。在克莱拉·阿瑟(Clara Arthur)的领导下,联盟代表其2000名成员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迫使市政府最终于1906年拨款2万美元,修建了底特律首个公共浴池,并于1908年正式投入使用。[16]
在环境卫生改革中,以社区改良运动(the 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中各大安置所的工作最为突出。社区改良工作者认为,贫困的根源并非个人的堕落,而是引起贫困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为了改善贫民窟中移民的生活品质,社区改良工作者们与大城市贫民居住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状况,通过教育、文化传播和设立恰当项目的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亚当斯对移民的生存状态深表担忧,她曾写道:“街道异常肮脏,学校数量严重不足,卫生立法得不到有效执行,街道光线昏暗,小道和巷子里的路崎岖不平,马厩臭气熏天……许多房子没有自来水,除了后院的水龙头。”[17]98-100对于这些情况,社区改良工作者希望利用中产阶级文化同化移民,帮助他们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融入美国的城市生活。[18]
首先,社区改良工作者们通过教育劝导的方式,让移民意识到肮脏的环境对于身心健康的威胁。她们多次同移民对话,让附近的女性移民明白恰当处理垃圾的重要性,告诫她们自家的卫生和周围环境同等重要,同时警告她们乱丢垃圾会导致孩子染病,甚至死亡。[17]281,283她们向女性移民提供卫生保健和儿童护理知识,将卫生理念深入移民家庭;为附近居民提供文学、艺术、历史、缝纫、烹饪等方面的指导;开办关于厨艺、清洁和儿童护理等方面的课程及免费图书馆和成人教育课堂,成为建立家庭秩序的城市社区的典范。
其次,社区改良工作者为贫民们提供相关的教育和娱乐活动,以提升移民的生活质量和道德品质。她们修建了游戏场,提供日常服务和各种娱乐活动;设立幼儿园、假期学校、诊所、浴室等;还为人们提供乡村短途旅行和湖边派对,让年轻人远离毒害他们的酒吧,鼓励他们走向自然,帮助他们提升健康意识的同时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1892年,赫尔之家修建了一个小型游戏场,面积是四分之三英亩,它向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开放。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荡秋千、玩沙堆、搭房子和玩滑梯等,稍大的男孩可以玩手球和室内棒球。1893年,它又修建了一个体育馆来代替室内游戏场,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为以后更加宏大的公共娱乐设施的修建提供了范本[19],也为城市公园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灵感和经验。
紧随赫尔之家,其他安置所也参与到环境卫生改革中。例如,纽约市亨利街(the Henry Street)的领袖莉莲·沃尔德深切体会到穷人的困境:疾病、贫困,缺乏教育和娱乐方式。为了给儿童提供必要的保护,她推动成立了联邦儿童局。[20]她还在安置所后院修建游戏场,上午用作幼儿园,下午供稍大的孩子们玩耍,晚上为年轻人提供跳舞和聚会的场地。又如,西北大学安置所(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ettlement)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游戏场;费城的学院安置所(College Settlement)即当时的斯塔尔中心,也积极监督游戏场的修建。[21]
最后,社区改良工作者们通过调查研究和游说进言的方式践行环境卫生理念,敦促市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亚当斯曾召集赫尔之家的女性们对芝加哥市的垃圾收集体系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研,调查它与死亡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10年夏,赫尔之家的妇女俱乐部成员聚集一堂,对所在选区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由12名成员负责同居民们建立联系,调查街巷中的卫生问题。在这些女性的努力下,赫尔之家将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提交给卫生部门,相关报告的数量达到1037份。亚当斯本人曾参加芝加哥市垃圾收集的竞标,虽然被否决,但她被任命为本选区的垃圾督察员,监督垃圾的收集和处理工作。她每日六点起床,不仅对装满垃圾的四轮马车进行监督,还和垃圾承包商协商,说服他们增加垃圾车的数量;同时还对那些随意处置垃圾的人提出控诉。[17]284,286在亚当斯的领导下,赫尔之家设置了六个小型焚化炉,专门用来焚烧垃圾,并多次向市政厅汇报本选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市民健康和生活产生的影响,得到了市长的大力支持。
妇女俱乐部作为城市环境卫生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推动了市民卫生意识的觉醒和城市环境卫生的改观,疾病与死亡数量最终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相关研究表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清洁用水项目就使得美国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下降75%。相应地,人均寿命得到显著提高。马萨诸塞州人均寿命由1850年的38.3岁提高到46.1岁。[22]这些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女性的士气。在此基础上,女性转而投入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致力于纯净水供应、食物监管、反煤烟和噪音、城市公共空间开辟、儿童福利、监狱改革、工厂环境改革等问题,推动美国城市向更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工业城市是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形态,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出现严重威胁着美国人的健康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俱乐部妇女承担起城市管家的职责,通过环境卫生改革创建整洁的城市环境和公正的社会秩序。这些活动是19世纪美国女性参与社会改革的缩影,体现出其进行社会参与、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理想与实践,成为当时试图建立城市秩序和工业秩序的重要标志。[23]
四、结 论
美国自建国以来,女性仅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在家庭中存在,公共领域几乎没有她们的身影。而妇女组织的出现打破了女子无能的魔咒,使她们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妇女俱乐部是19世纪美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大发展、精神觉醒和社会大调整的产物。它服务于社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对国家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妇女俱乐部使19世纪的美国女性获得了新的社会定位,培养了女性更优秀的品质。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她们都变得更加强大。在私人领域,她们作为道德卫士的角色得到了加强,成为更优秀的家庭管理者。在公共领域,俱乐部为女性提供了更多机会,为她们的生活赋予了社会意义和目标。[24]通过参与诸如环境卫生改革等社会活动,俱乐部妇女的演讲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及游说能力得到了提高,其影响渗透到社会基层和上层建筑领域。正如历史学家卡伦·梅森(Karen Mason)说的那样,赫尔之家的女性改革者们利用城市管家理念为自身打造了一种“以母性为基础”的政治角色。[25]俱乐部推动了一代优秀的女性社会科学家、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的诞生,并使女性问题上升到联邦层面。虽然19世纪的妇女俱乐部并不公开支持选举权运动,但到了20世纪初,许多妇女俱乐部已经成为选举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原因在于,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女性提出的很多提议被忽视,这使她们逐渐意识到获得政治权利的必要性。妇女俱乐部对选举权的支持,扩大了选举权运动的范围,推动了妇女政治权利的获得。
通过参与社会改革,俱乐部女性为修正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无法心安理得地忍受商业利益驱使下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存在[26],渴望通过改革建立社会公正。在城市管家理念的指引下,俱乐部女性通过多项改革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在家庭、学校、政府和人类关系中树立了信念。如社区改良为移民适应美国生活方式、改善移民生活环境提供了各种便利,它所修建的各类设施也被竞相效仿,推动了全国社区改良运动的开展。女性在改革过程中所采用的诸多措施效果良好,获得了政府机构的认可和借鉴;多个项目最终被转移到政府手中,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这一点符合大部分女性进行改革的初衷,即通过改革唤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最终由政府制定政策和相关议程来解决问题。
妇女俱乐部无论是对女性权利的获得还是对美国社会的改革都功不可没,同时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在改革过程中,俱乐部女性时刻强调女性特征,常常用道德、审美、教育等女性化语言和方式进行改革,导致她们的改革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和较大的保守性。因此,她们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进入立法程序时,常因“缺乏科学依据”“过于感性”而被否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其次,受性别、阶级、种族等的制约,一些女性具有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偏见以及种族偏见。她们认为,下层女性缺乏道德和女性气质,文明程度不高,她们的加入会降低俱乐部的工作效率;以总联盟为首的白人妇女俱乐部反对吸纳有色人种女性,担心俱乐部的工作会因种族问题而受到阻挠。这些都是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下必然的矛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