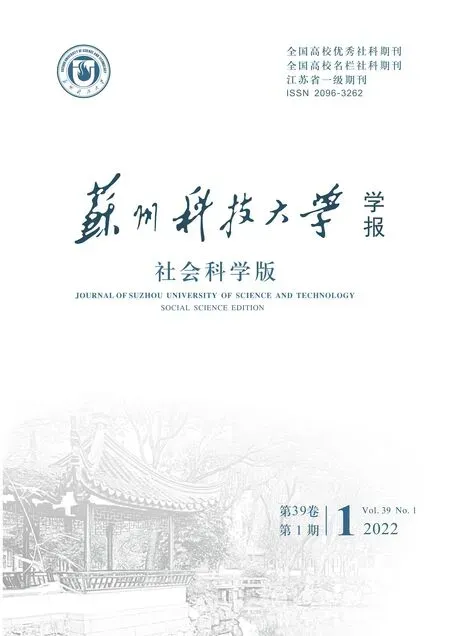媒介可供性视角下江南文化的融媒体传播*
陈小燕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已成共识。“在文化层面上,江南文化是长三角的最大公约数”,“长三角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文化的动因十分重要”。[1]当代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江南文化传播的方式,表现为江南文化地理空间界域的突破、文化活动体验从“在场”到“虚拟”的转变。数字空间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并存,人媒融合空间共同影响着人们对江南文化的感知和消费。江南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为新媒体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灵感。2021年7月10日上映的纪录片《天工苏作》,对苏州传统工艺中的灯彩、核雕、宋锦、明式家具、苏式船点、苏绣、香山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等9项“非遗”进行影像呈现,不但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还意外地拉动了城市旅游的后劲——“电影不上购物链接,却有超强带货功能”[2]。在万物皆媒、万众皆媒的新语境下,江南文化跟上新媒体的步伐刻不容缓。由于“技术理性和社会多样性的矛盾,虚拟传播无边界和物理区域上管理归属的矛盾加剧”,“虽然媒体融合已从内容和人才融合阶段步入资源和产业整合阶段,但尚未摆脱路径分歧、融合浅表等问题”[3]。在江南文化的传播融合研究中,媒介效能的激活方面一直难以突破。“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今日文化之繁荣景象。”[4]34如何从媒介技术自身出发挖掘新时代江南文化的传播潜能,扩大数字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创造出符合个体情感需求和审美判断的新型文化形态?笔者将以媒介可供性理论来讨论江南文化实现融媒介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移动化与社交化:江南文化传播的场景新变
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模式是一个颠覆性过程。随着体验性媒介消费的崛起,网络用户的互动参与推动了社会话语结构的转变。“重振‘江南的文运’,必须形成新的文化造血机制,不能把人杰地灵的江南只作为一个具有精致物质生活的所在。”[5]通过媒介来传承文化的传播效果问题,需要考虑到文化和社会被互联网技术洗礼后的新媒介时代环境。
(一)时代的主旋律:从社交化、移动化的新媒介技术出发思考文化问题
“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6]我们所处的Web2.0时代表现为移动性、互动性的媒介时代,时空和语境的变化都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验。
时代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交化。社交媒体将人与人互动的方式标准化,使用经过重新定义且基本标准化的社交互动模型,组装更大的社会实体。这意味着人类复杂的情感在社交媒体中变得简单且几乎没有差异。社交媒体在交流方面的强大力量在于两个因素:一是个人方面,个体与他者基于“缘”的交流发生扩散,不再局限于血缘、亲缘、地缘,而是扩展到“趣缘”,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交流所产生的愉悦和亲近感与现实社会别无二致,同时超越了传统媒介渠道难以实现的扩大化交往;二是产生级数效应,在社交媒体上,专业的文化信息、业余的文化内容以及未经审核的文化形态混合在一起。
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移动化。在移动时代,拥有并使用移动设备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子邮件、微信、QQ、微博等应用程序使人们能够摆脱社区的限制。延森谈到“移动性”的三个方面:空间的移动性指空间的位置变化,时间的移动性指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与环境的灵活交流方式,语境的移动性体现的是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变化程度。[7]112-113现代的数字媒介将移动性发挥到极致,可以同步处理多个跨越时空的任务。这种时间、空间和语境的移动性进一步模糊了体验式存在和缺席之间的区别。
新时代的移动媒介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传播者展开包括图像、文本及声音在内的交流,离身传播和远程操作成为可能。“流动社会的兴起重塑了‘自我—它’的日常活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以及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8]个性化的流动性通常将个人生活牵连到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网络中。总之,从社交化、移动化的时代旋律出发,把握新媒介的传播特质,思考江南文化的传播问题,有助于“生成新的区域文化意识以及为面向未来的行动奠定文化意识和情感认同基础”[9],推动江南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二)数字化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可供性的潜能挖掘
新媒介从技术表现上看是数字化的。数字化是指把文字、图像和声音的传播转变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与模拟技术为基础的早期电子传播相比,它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灵活性。数字技术包括5G网络、虚拟现实、全息影像、增强现实等。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形态,不仅复制了先前所有交流媒介的特征,而且将它们整合于一个软硬件兼具的物理平台上。
新媒介是数字的,更是文化的。“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10]新媒介凭借其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能力进一步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在流动空间和永恒时间中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数字化工具和呈现形式固然重要,然而作品的永久流传却依然要靠其文化内涵。”[4]31数字新媒介作品中使用全息投影、3D街景、特效声音等栩栩如生地还原场景不太难,但要创造一个引发公众产生深刻审美的共情角色就不容易了。
数字技术为江南文化的传播转型赋予了新的可能性。“技术是当代文化展示的核心。”[11]这种文化数字化的转型呼唤着挖掘更多更新的文化传播可能性。从媒介可供性的角度来看,“传播可供性不仅仅是功能的简单捆绑,也不是技术的更新换代,而是通过新技术创造更丰富的功能,在更高维度上服务于传播实践”[12]。江南文化传播的数字媒介挖掘,需要延长文化内容制作的生产链,探索更为灵活的文化节目生产顺序,以及扩大实际产出的多媒体文化产品。“数字能够对优秀文化进行再创造,以新创意和新设计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现代生活、当代审美、当代价值观,开发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和表现形态。”[4]28比如水乡周庄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展示沈万三的传奇一生,讲述一代望族的风雨变迁往事,一帧帧影像画面灵动自然,3D技术活灵活现,虚拟技术与现实场景融合巧妙,历史人物跃然于眼前,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总之,技术可供性理论带给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个观念,就是“以生态性(ecological)而非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思路去看待技术的角色,并在技术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分析、重新‘配置’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13]。这为江南文化的传播锚定了一个发展的方向:江南文化的融媒介传播从文化传播网络(Culture Communication Network)的各要素(物、技术、内容、人等)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德勒兹式的“根茎方法”(Rhizomatic Approach)重新组织文化传播的概念体系并思考融媒介的新角色。因此,高效的江南文化融媒传播,需要把握技术与文化的互动环节中的各种关系,探寻媒介技术为江南文化赋能的诸种可能性。
二、媒体技术可供性:江南文化创新传播的着眼处
“可供性”(affordance)是指技术令某种社会行为成为可能的属性。这一概念最早由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Gibson)提出:“一个具体环境的可供性,就是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14]吉布森将“互补性”视为可供性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自然环境中的可供性是由其他动物提供的,人类的可供性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但人类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远远大于自然环境,因为人类在受到物理条件和生物条件约束时,会使用技术体系来塑造第二自然,如照明为工作环境增加安全舒适感,电力为印刷报刊和互联网络奠定动力基础。当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CMC)出现后,受众对媒介效用的主观感知发生改变。从吉布森的概念出发来思考现代社会的媒介可供性,即文化是由技术环境提供的。学者潘忠党从新媒体与旧媒介区分的角度进一步明晰了可供性,认为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移动可供性三个方面比较来看,可供性水平越高的媒体,就越是新媒体。[15]这为评估新的媒介技术、形态和结构的发展潜力指明了方向。这意味着,媒介可供性强调的是媒介技术环境为江南文化提供了什么,以及文化是如何改造并影响媒介的。
(一)文化内容生产的可供性:视频转向、自动化与多主体生产
首先,视频转向带来了新的文化内容呈现,扩展了文化内容生产的可供性。纯文本传播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从原来的广播(Broad-casting)发展到数据传播(Datacasting)和比特传播(Bitcasting)。图像处理智能技术使得图片、视频传播显著增加,随着智能手机功能提升、网路带宽增加,“视觉传播系统具备了从图片向视频转向的条件”[16]。文字、图片、视频、虚拟现实以及增强现实等多元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形态。“短视频背后的技术性媒介生态系统因素、多元的社会群体的丰富表达需求以及部分既有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机制相互嵌入,形成一种物质与技术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共同参与短视频的文化生产实践。”[17]因此,以抖音与快手为主导的短视频数字文化蔚然成风。建筑数字场景化也被运用到游戏媒介中。以巴黎圣母院为例,2019年的大火将矗立了8个世纪之久的尖顶烧毁殆尽,世人为之扼腕叹息。此时有一款发行于2014年的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却火爆起来,原来这款游戏中有开发人员用两年多的时间精确复原的巴黎圣母院建筑,网友们纷纷涌入游戏瞻仰历史文化遗迹。这一文明遗产依靠数字技术成功保留,说明超级数字场景的视频化建构创造了意外的社会价值。
其次,自动化带来了内容生产的机械生产模式,扩大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未来内容生产的参与主体不仅仅是人,机器也成为信息的采集者,可以完成内容的智能化加工。算法介入社会运作机制,每个信息接收者都在这个智能网络中生存。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文化传播中,掌握着智能机器和传播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将成为关键的技术主导角色。机器根据个人的行为轨迹记录数据,算法和机器将成为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个人不由自主地处于这种由机器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当智能机器信息采集日益普遍时,人与物的信息交互成为常态,物所监测到的信息通过物-人信息系统直接到达用户。因此,专业媒体的信息中介性意义被削弱。
最后,多元主体参与内容创作,拓宽了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在线文化生产的低门槛开辟了令人惊叹的可能性。”[18]新媒介最显著的特征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个体被激励到参与内容的生成,数字化媒介在信息生产方面有了双重的逻辑,既是专业内容的生产者,又是受众/用户的积极参与者。新媒介扩展了传播的模式,从过去的雅典式集会、哈贝马斯的公共对话机制,到当下Web2.0时代的在线集体智慧,用户从过去被动的内容接收者变成积极的内容生成者,他们不仅有大量的机会贡献自己的内容,还能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互联网从“出版的媒介”变成“交流的媒介”。
(二)社交可供性:连接效应与圈层化社区的情感认同
首先,关系连接带来的聚变效应,丰富了社交的可供性。社交媒体中的社交(social),实质在于关系的连接与扩张。“社会网络可以表现出一种智慧,它可以让个体更有智慧,或者成为对个体智慧的补充。……社会网络可以捕捉和容纳人人相传的、不同时间的信息(信任规范、互惠传统、口述历史或者在线维基等),还可以通过计算将成千上万的决策汇总。”[19]用户借助网络形成关系连接,达到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聚变效果。面对数字移动媒介对多元类型连接的创造,“观众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不但将自身从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模式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新的‘行动者—网络’,而且也在数字技术生态下获得了一种传统环境无法赋予他们的新型自由”[20]。社交媒体的逻辑就是挖掘用户的力量,将用户变为参与者与贡献者。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使“永久在线,永久连接”[21]成为人类日常社交生活的常态。
其次,圈层化社群产生的情感认同,放大了社交的可供性。技术将大众的群居属性延伸至虚拟空间,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社交媒体的连接可供性进一步扩大了公众之间的连接,从而为公众的情感共振提供了情境。此类公众被齐齐·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称为“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指通过情感表达而动员起来的网络化公众组织形态,“因网络技术转化而来,表现出人、技术、实践互动的新空间和从这种互动中想象出来的共同体”。[22]网络平台通过提供热搜、热榜、事件标签将公众情绪进一步聚拢和放大,具有相同兴趣或相同价值观的节点更容易形成圈层传播。在新媒体传播网络中,日益形成“‘大广场’与‘小客厅’的概念。‘大广场’指的是网络公共空间,‘小客厅’就是圈层交流空间”,“‘小客厅’越来越占据着用户的个人时间与信息获取通道,同时用户之间在‘小客厅’中的关系连接频率远远高于在‘大广场’中”[23]。在网络社会,用户从社会交往和仪式性消费中获得知识和体验,“围绕某一文化形式的社交活动,能够为个体存在意义、自我定位提供确切的证据”[24]。网络中的个体一旦青睐某类题材或文化,就容易产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诉求,于是基于兴趣和情感驱动的社群产生,个体封闭式的阅读变成群体的议题讨论,催生了情感交互和知识共享的现象。比如在苏州取景拍摄的电视剧《月里青山淡如画》,主创人员掌握了公众情感的流量密码,迎合年轻人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相结合的审美品位,为该剧贴上“文物修复”“国潮”标签,采用汉服元素,这些国风元素在B站、抖音等平台“是热搜的常客”[25],激活了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协商互动。
(三)移动可供性:场景化、进行时式与人媒合一
首先,信息消费的多场景提高了移动的可供性。与电脑时代的网络传播相比,移动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强化。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被称为“场景五力”,“五种原力正在改变你作为消费者、患者、观众或者在线旅行者的体验”[26]。社交媒体基于各种不同的场景进行设计的越来越多,不仅要理解特定场景中的用户,还要提供与其需求相适配的内容或服务。人们与文化的互动可以在多个终端实现,江南文化不再是一种必须与剧院、书场、博物馆等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文化,而是拥有了无穷的可能性。电视节目开始利用AR(增加现实)技术来增强真实感,充分发挥融合媒介技术,扩大观众的收视体验。如覆盖全球三亿观众的央视中秋晚会,2014年将江南地区的首场晚会放在苏州,主题为“苏州月·中华情”。该节目深挖地域元素和吴文化特色,将“虎丘曲会”“石湖串月”“钟无艳祭月”等连接起来,将明清时苏州居民中秋夜游虎丘、祭拜皓月以及千人石听歌等文化习俗完美呈现,呼应了古诗“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邵长蘅《冶游》);将钟无艳幼年时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为皇后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用符号巧妙地重建历史真实,用历史典故叙事,甚至赋予观众更多参与的体验感。格调鲜明的江南文化风韵通过影像光影抵达海内外观众的心中,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扩大了传播效果。
其次,进行时式的信息消费扩展了移动的可供性。“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数字文明,是一种以全息文化为终极形态的文明,它是一种谋求与我们的生活高度逼真、高度同步的文化存在。这种文明转型是一种动态过程。”[27]全息影像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功能让表演者以各种虚拟方式出现,观众在虚拟和现实共同交织的时空中体验丰富的情感。在社交媒体Web2.0时代,文化消费的模式不仅仅是在用户脑海中建构一个虚幻、想象的世界,还要同步激发一个可以感知、体验的真实感受。比如日本茑屋书店出售的烹饪类书籍,用VR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厨房场景,在教学课件中让读者同步听到烹饪时的声音,甚至可以触摸厨具的温度,这样的融媒介文化产品提升了读者的代入感和体验感,读者更容易产生共情共振。杭州G20峰会上,张艺谋导演的晚会《最忆是杭州》运用全息投影的手段展示诗情画意的江南文化,如《采茶舞曲》、《难忘茉莉花》、取材于梁祝故事的《美丽的爱情传说》等节目,虚拟现实技术加上西湖实景,更生动地呈现典雅的江南文化韵味。
最后,人媒合一的多媒体体验增强了移动的可供性。“任何一种过去只能通过单一媒介提供的服务,例如广播、报纸、电话,现在都可以有多种媒介来提供。由此,过去在媒介与它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的一对一的关系正在被侵蚀。”[28]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就是各个媒介之间界限被不断打破、功能逐渐多元、参与者日益方便的结果。“慢直播+VR”等技术用于视频节目,真实的现场通过摄像头或无人机展示全景,为用户提供了现场触达的临场感;同时,用户手中便捷的视频应用软件方便了他们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与其他空间的观看者一同交流,增加了用户选择和参与慢直播的权力。比如2019年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次日,苏州新媒体“看苏州”在苏州博物馆开启了“慢直播”,让不能到达现场缅怀的全世界华人寄托哀思,众多网友在直播中一边感悟苏州博物馆园林文化的魅力,一边写下对贝老的追思。
三、阐释框架、联结与舞台:媒介作为江南文化数字传播的新角色
媒介不应被视为文化与社会机制相互分离的存在,而应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结构性条件。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传播者—使用媒介—传递信息—抵达受众”这个线性序列,而是扩大至社会文化领域间多种变化的互动关系之中。“从历史的角度看,媒介融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7]17江南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从传统文化产业迈向现代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江南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意味着原本就存在一个产业,在数字技术出现后,我们利用数字技术来增长文化产业的产出,提升文化传播的效率。“随着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不断革新,媒体融合创新的目标与进路日益清晰”,就是“融合创新的传媒形态、传媒角色、传媒功能、传媒生产流通等一系列战略安排与生存发展的问题”[29]。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我们可以从阐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联结(nexus)功能和公共事务的舞台(arena)角色等维度理解文化进程与社会机制互动关系中的变化。
(一)媒介作为理解江南文化的阐释框架
作为阐释框架的媒介是指媒介提供对“事物状态”(the way things are)的呈现和解读,并借此建构身份认同感和社群意识。于江南文化的数字转型而言,这里的“事物状态”即“江南文化状态”(the Jiangnan Culture is),新媒介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关于江南文化分享的领域并持续呈现和阐释江南文化的内涵。新媒介通过对江南文化的多平台、多主体的持续呈现,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文化经验分享的领域。很多对于江南美丽动人的想象,来自外来者和流寓者,“他们的文学书写,经常反客为主,凝聚成缤纷多彩的江南文化符号,加深了人们对于江南文化的认知”[30]。在这个领域,用户彼此建构身份社群意识,并生成身份认同感。比如历时三年打造的纪录片《天工苏作》充分挖掘各种新媒介技术和叙事创新的手段,运用现代数字媒介技术将苏作的精巧绝美展现出来,有的观众看完就“想要去买缂丝扇子,想把灯彩工艺运用在新家的装修上”[31]。影片受众通过对江南文化的意蕴解读获得强烈的情感认同,并将这种文化体验延续到日常生活消费之中。
(二)媒介作为文化机构之间的联结
网络化社会的媒体是信息交换的中介机构,是社会关系连接和资源重组的重要力量。媒介扮演着文化机构内部和文化机构之间关系的联结平台。“由于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及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社会、文化、媒介和政治不再是独立的子系统,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32]在技术衍替的发展过程中,媒介与其他机构的差异逐渐增大,它既作为信源为受众提供对社会的看法,又存在于特定的文化机构之中。因此,“媒介既是特定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家庭、政治等)的基本结构之一,又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扮演着其他文化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纽带角色”,并“为公共讨论构建了一个共同的舞台”[7]5。江南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是由网络用户、机构媒体、文艺工作者等多个主体力量互动完成的。比如“非遗薪火计划”是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微信平台和中国传媒大学等多个机构合作推动而成,并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微信号,用拍摄短视频加直播的方式,充分利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开发“非遗”项目。多媒介平台的使用,既传递了手工艺的文化价值,又发掘了“非遗”的市场价值。
(三)媒介作为用户沉浸的文化事务舞台
媒介构建了一个文化公共领域,各种文化制度和文化机构在这个领域追求并保护其自身利益,建立各自的合法性。数字媒介通过制造连接方式来调动对文化遗产的集体保护,新媒介去中心化和去地域化的特质使得公共事务的讨论更具广泛性。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我们已经从第一媒介时代进入第二媒介时代。“以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单向性播放模式占主导的时代,是第一媒介时代;集媒介的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为一体的双向性、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为主导的时代,可称为第二媒介时代。”[33]新媒介在文化和社会关键议题的动员力量日渐加剧,“读者、观众等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成为积极主动的用户。融合媒体必须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吸引用户参与,鼓励UGC产品生产,共同创造价值。突破社会、个人、文化、经济等各种边界和壁垒,形成各种新的融合可能性”[34]。媒介犹如黏合剂,将社会中独立的个体连接成社会整体。比如腾讯公益联合ELLE时尚杂志和天天P图公司,共同发起“非遗代言人H5”项目,用户只要进入H5,就可以观看真人实景的“非遗”视频,还可以选择民族服饰,利用视频换脸技术生成具有个人风格的“非遗代言人”封面。此举大大激发了用户的“非遗”保护认同感和责任感。媒介功能升级的过程,往往是我们已熟悉的许多元素或界面的整合,如互联网整合了音视频与文字,带来了高纬度的传播形态,移动媒体整合了传播资源和场景信息,使得个人能够实现物理和数字社会领域的联结。
四、结 语
从发现和留住受众来说,媒介融合的技术可供性提供了一个好的策略,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获得高质量的内容需求和圈层社群文化消费的新体验。江南文化的融媒体传播过程是一个媒介可供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新时代的沉浸传播生态系统为江南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持,它将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文化形态融为一体,使得文化内容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新媒介效能的激活并非传播渠道的简单叠加,而是技术属性与用户所处的时代环境在互动之下产生的加成作用。媒介的融合不会消除规模的等级,而是产生重构规模的效应。我们要不断检视数字媒介所创造的新连接形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吸纳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探索“技术-文化”的江南文化融媒研究理论体系。我们要以沉浸媒介思维方式挖掘更多的媒介可供性,实现江南文化融媒介发展的整体性提升。江南文化的融媒介纵深发展,需要谨慎考虑技术和内容二元驱动之后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问题,需要抵御个体化连接后可能存在的网络个人主义和文化“三俗”的问题,需要厘清“用户参与文化”与“用户视角狭隘”的矛盾问题;既充分利用参与的广泛性,又让广大用户之间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纠错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江南文化的融媒介传播才能从技术先进性上扩大数字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向大众提供更符合个体需求和审美判断的优质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