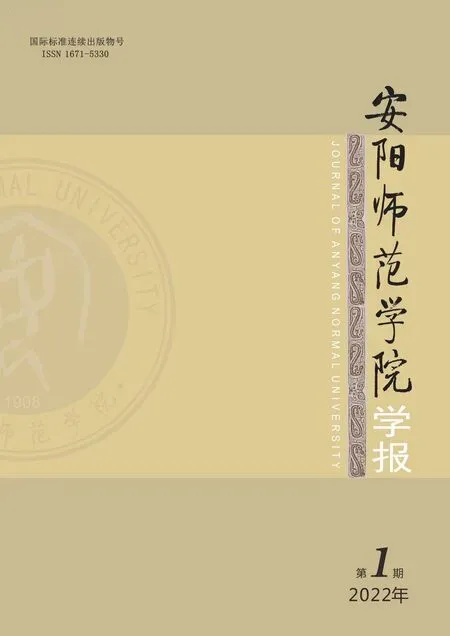多重语境下的21世纪女性写作新质概览
刘 琳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实事”,刘勰早已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揭示了时代变迁之于文学发展的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女性文学也概不能外。21世纪已悄然逼近第21个年头,女性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喧嚣的烟霭中拂尘前行,在日益分化的多重语境中恣意生长,亦渐渐绽出另一些夺目的光芒。
继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以物质消费为中心的时代新语境,重构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以商业利益为主导原则的消费文化渗入社会各个领域,携市场与资本之手改造着当下生活,已然成为醒目的时代表征和文化内核。服装、化妆品、美容美体等以女性为目标受众的商品及服务,将消费文化、时尚文化与性别文化挂钩。这种看似以女性为中心的消费指向,实则亦是一剂麻痹和弱化女性自我性别构基的致幻剂,并悄然浸入女性写作的内里。于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作家的写作面向俱得以晃动。“身体”“欲望”写作曾在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并被赋予承载着言说和释放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重任,但其随即也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成为博取眼球的噱头,沦为被看和被消费的对象,失却了原初的性别建构意义。部分女作家亦在有意或无意中向市场靠斜,备受争议和批判。进而,“身体”“欲望”在新世纪文学中几乎成了连女作家都不愿直视的贬义词,性别问题也似乎逐渐地不再是21世纪女性写作首要考虑的问题,甚至不再能构成女性写作的切入点和叙事主体。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变革、阶层的分化也带来了经济、民生、人文、自然环境等诸项纷扰,民众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欢愉与阵痛必然有着更为真切和复杂的感受。于是,文学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及作家身为知识分子的敏感与良知,俱引导着已然放下性别战备状态的女性写作者褪去激进和自赏,开始关注大地、回归现实,底层、乡村、职场成为新的写作主题,“非虚构”引人注目。而精英文化视阈下的理论批评也时刻警醒女性写作者必须紧守时代之门,体察世事变迁下的众生百态,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和身心情状。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长期被掩埋于“历史地表”之下的记忆太过于刻骨铭心,另一方面亦因为女性写作者身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感对于“启蒙”(尤其是对女性的启蒙)这一文学传统的自觉把守意识的督促。于是,21世纪的女性写作也不乏坚守性别建构和致力于拓宽领域的写作者和作品。同时,书写与传播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为21世纪的女性写作提供了更广阔和自由的空间,给文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新质。
由是,与20世纪90年代固守于自己的房间,在“性别”的对抗、“身体”和“欲望”的展现、“历史”的追索中探询“主体”的女性写作不同,21世纪女性文学在驳杂的语境下调整姿态调转目光,直面多重语境夹裹下的时代现场,呈现出新的写作动向。
一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以“自己的房间”来隐喻女性需在充斥男性话语的世界里开辟出一个独属于女性的话语场域,以尽情展现和张扬被历史隐没的女性意识及生命体验。20世纪90年代,部分女性写作者纷纷固守于“房屋”之内,展开以身体为壁垒的女性私密体验,意图挣断禁锢欲望的锁链,然而,如前所述,“个人化写作”筑就的私人空间逐渐变得暧昧和狭窄,“身体”和“欲望”在消费语境中被裹上了商业外衣,沦为“被看”的恶俗消遣而备受质疑。
21世纪,女性作家开始将写作从私人空间拉向公共空间,从“身体”和“欲望”的帷幕里抬头,将视角伸向坚实而宽广的大地。林白曾是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始作俑者与典型代表,然而进入21世纪,她却陡然调转笔触,将“一个人的私语”拓展为与整个中国乡村大地的对话,接连推出了《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两个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万物花开》以一个脑子里长着瘤子的农村男孩“大头”的独特视角展开叙述,其叙事人称与叙事性别的变化已具转型意味;同时,以一个叫“王榨”的乡村为场域展开叙述,文本中充斥着现代乡村原生态的场景、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图集和生命体验,贫穷、奇异、怪诞而又富有勃勃生命力的讲述方式,喷薄的笔调和宽阔的视野,完全没有了林白过去的幽暗与狭窄。《妇女闲聊录》仍以“王榨”为背景,其视阈更趋宽广也更具烟火气息。新时期文学中淳朴封闭的农村在现代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肆虐中所遭遇的道德解体的危机,村民对性、贞操与婚姻观念的开放或淡漠,众多农村妇女的隐痛,令人堪忧的农村儿童教育以及外出打工者在大都市底层里的挣扎,众生百态的农村浮世绘取代了房间里的自视自语。林白曾说:“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1](P278)从只关注“女人”到关注“人”,走出房间走向社会,21世纪以来的林白以其久为世人称道的敏感和细腻感受,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对底层大众带来的冲击和震荡,是一位女性作家对更坚实也更阔远的精神建构和情怀拓展的奋力追求。
如果说林白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是对刻板的性别姿态和对题材领域的调整,那么更多女性作家的转变则体现在,从曾经的过于单向度地关注女性内心世界、重刻画而轻叙事的倾向,转向更关注女性真实具体的外部生活世界并注重叙事的饱满性与完整性。毕竟,21世纪的多元语境给女性带来的内心激荡或创伤,需要在外部生活处境的剧烈变化中把握,而不能仅限于、停留于逼仄的心理学推导和僵硬的话语演绎。一向以文笔细腻、描写女性幽微内心为写作特色的王安忆,也在21世纪推出了一批关注底层、贴近现实的作品。《桃之夭夭》以一个波澜不惊的故事来展现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所折射出的细碎、烦琐而又灼灼其华,在对现实琐碎的描摹中,上海依然是《长恨歌》里的小市民世界,却不再是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心理的映衬,也不再肩负大时代里曾经被人遗忘的女性历史的重任,而是女性和她们所处的社会共同铸就的血肉之身,是生活本身。《上种红菱下种藕》更是展示了江浙农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所发生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动荡转变。《保姆们》《遍地枭雄》《骄傲的皮匠》则有着一种兼容并包的生命视野。除此,迟子建、盛可以、孙慧芬、魏微、须一瓜等,都在21世纪后的作品中将笔触探向更本真和宽广的生活场景。因而,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曾因陷入幽闭与私语的叙事局限而被质疑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那么21世纪女性写作所呈现出的上述“出走”则为女性文学的未来找到了突围的可能。
21世纪以来的多重语境的出现,也意味着女性境遇的趋于多元。这种变化也必然带来女性对性别身份的重新确认和价值观的重建,于是另有一批女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探讨女性直面不同社会境遇时的自我独立生存问题上,这当中,“职场”及其相关的叙事主题成为21世纪女性写作一个新的亮点。2017年,一部讲述都市青年女性白领故事的电视剧《欢乐颂》红遍大江南北,并于2018年上半年迅速推出第二部,反响依然强烈,《欢乐颂》小说原作者阿耐也因此备受关注。除了《欢乐颂》这部电视剧,阿耐还写了一系列以“职场”为题材的作品,讲述女性在混流复杂的商业职场中奋斗打拼的辛酸历程。《余生》里,女主角于扬是商界女强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力图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而不择手段,在残酷的商业游戏中逐渐迷失自我,付出惨重的身心代价;《回家》描述了白领阶层女性在经历了商业市场的勾心斗角后对家庭的重新思索与理解;《不得往生》则写了一个女性创业者的奋斗故事。阿耐本身就是一位女性职场者,所以她的写作自觉融入了女性在面临情感、家庭、事业、自我主体失衡时的身份认同和性别体认:“我们的物质生活进步清晰可见,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偏离崇高、尊严、真实,日益被物质侵蚀;为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1)转引自黄薇:《现代女性的自我救赎,需要情感和智力同步进行》,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689190100d49i.html。其写作亦正是建基于此。计文君的《琢光》,也写了现代女性在职场的拼杀里展现出的人性明暗、自我的坚守与退却。工作上冷酷犀利的艾薇,一旦面对患了产后抑郁症的亲侄女林晓筱,立刻变得软弱慌乱;一贯冷静理性的心理精神学专家司望舒,却要借助虚无的禅佛来修补被童年家庭阴影划破的内心;为了工作上的爬升,乌迪、酱紫、余菲菲等女性都各有各的可憎,也各有各自身为女性而独有的可怜和无奈。计文君以“琢光”为题,隐喻现代女性若想在家庭里获得真正的自由、人格的完整和事业上的价值认同,犹如隔空雕光,异常艰难;职场里的女性,虽外表精致练达,内心却荒芜残破。除此,还有范小青的《女同志》、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等,都勘探到女性在职场里生存的艰难。“虽然我们社会的环境看上去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轻松,但女性自由和解放的规模和程度却远远不及曾经自由的年代,比如五四时期。”[2](P52-67)21世纪的女性写作者们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关注并反思着职场女性的成长与哀痛。
除却“职场”写作,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现实图景,“非虚构”这种新的叙事范式也应时而来。自2010年2月《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不久之后又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大批非虚构作品陆续被刊登出来。其中女性作家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更是引起了极大关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郑晓琼的《女工记》、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羊道”系列、陈丹燕的“上海”系列等。如果说林白的“访谈录”式作品还只是作家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审视一个外在于她的世界,那么,“非虚构”作品中的女性写作者则是设身处地去体验、去融入这个世界。梁鸿是以故乡儿女和大学教师的双重身份参与到事实的采集当中;乔叶更是拆迁事件的亲历者,亲眼看见姐姐家拆迁的全过程甚至参与出谋划策,极尽真实地呈现这个时代里烟尘弥漫的“拆迁”语境;郑小琼本身就是女工;王小妮是“上课记”中的大学老师;李娟做过裁缝、卖过小百货、在新疆生活、有过与牧民一起转场的不凡经历;陈丹燕则长期浸泡于上海都市生活之中,熟知它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
这些作品都说明,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女性作家们的视野更趋阔朗深刻,她们较大程度地脱离了自我镜像而关注日常生活,驻足坚实大地,触摸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底层人群,关注她们所身处的外部世界并建构起女性眼中的现实图景。她们的视阈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社会)空间拓展,这种拓展为女性写作的未来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公共叙事的参与,对“自我”和“大我”的融合点以及对个人与社会的衔接点的重新寻求,使得21世纪女性写作的精神气质有了新的向度,新的拓展,甚至有了新的提升。
二
由于女性在历史中显见的长期身份缺失,突显“性别身份”一直以来是女性写作中都极为关注和刻意凸显的主题,这甚至导致了一些今天看来较为极端的文化命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张洁、 张辛欣等作家,因其对“性别身份”的刻意强调,以致其某些作品被视为典型的“仇男文学”读本,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们的写作也几乎都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标识感,以将男性/女性置于二元对抗的战场中来彰显女性的性别意识并以此作为性别对抗和建构的策略,并以“私人化”“身体”和女性家族史写作的方式践行之。但弊端和争议也随之而来:“无论是纯粹的‘女性家庭’, 还是走向女性的自我幽闭, 都是一种脱离两性和谐共生之自然状态的自我幻灭, 一切反抗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决绝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虚弱和疲惫。”[3](P155-156)21世纪后,女作家们虽仍执着于对两性关系的关注,但如上所述,由于纷繁复杂的新语境及对世纪前的创作反思,女性写作者逐渐放松了性别对峙状态,作家们纷纷走出女性本位的排他性写作堡垒,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了性别的拘囿,对两性关系做出新的审视。
这种性别审视态度的转变首先以“超性别意识”的写作方式体现出来。“超性别意识”最初由陈染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陈染写道:“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 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地完整。”[4](P105-107)此后,虽然学界对“超性别意识”的概念和内涵论争不断,但仍有部分女性作家在21世纪推出了反思后的践行之作,“ 对文学作为‘人学’的内涵和意义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回应”[5](P38-45)。
迟子建是其中公认的“超性别意识”写作特征较为明显的女性作家之一。不同于其他女作家惯于以细腻手法刻画女性隐秘的心理历程和生命际遇的相对狭小且固定的视角,迟子建的视野较为开阔和多元,其作品取材不拘于女性世界,而是显露出独特而又阔达的自然和社会视野。她的小说里经常出现故乡东北的白山黑水、走兽飞禽、时令节俗、民风民情,如《酒鬼的鱼鹰》里能辨别人性善恶的鱼鹰,《越过云层的晴朗》中隐忍又忠诚的狗,《清水洗尘》里淳朴的故土风物习俗、朴素却透着至爱深情的家庭生活,绵柔克制的文字里透出浓烈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关系的人道关怀。关于两性关系,迟子建曾直言:“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他们紧相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6](P85)因而迟子建鲜少以强势的女性主体姿态来构建文本,而是极力营造两性之间和谐共生的画面,《清水洗尘》里母亲因邻居蛇寡妇而生起地对父亲的嗔怪、焦虑最终都化解在父亲的温存和宽厚之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在描写两性之间深厚温情的关系之时也透着普世的人性情怀。总之,其作品总是以疏淡又不乏温情的笔墨勾勒出俗世男女流连于普通家庭生活时的诗性和谐关系。
铁凝也曾提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入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7](P33-39)。2006年出版的《笨花》中,铁凝一改以往作品几乎只关注女性命运、专注个人情感世界的风格,转而挥笔描绘出一幅跨越了“民国”初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近50年的历史画卷,但作者并无意展示这段历史的波澜恢宏,也无意掘探男性与女性在历史中的性别等级,而是将大量笔墨涂抹在这段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群普通中国人(有男人也有女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上,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描摹人的心境和生存状态。而且,作家没有着意强调女性视野,也没有为了刻意突出女性形象而弱化或丑化男性形象,《笨花》里的男性不再是《麦秸垛》《玫瑰门》《大浴女》《永远有多远》里孱弱虚化的形象,而是鲜活、饱满和丰富的。同时,男性与女性之间二元对立的状态亦不复见。
王安忆也在《女作家的自我》中指出,女作家如果过分强调“自我”,就容易掉进“自我”的陷阱,自赏自恋[8](P414-421)。在王安忆看来,超性别写作并不是“无性别”写作或是放弃女性意识,而是要跳脱性别的局限。在2005年出版的《遍地枭雄》里,王安忆虽亦采取了早期作品《叔叔的故事》里的以男性作为叙事焦点的方式,但人物形象和性别姿态已大相径庭。如果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对自私、虚伪的“叔叔”形象的塑造来完成对男性神话的解构,并以此推进某种女性主义式的批判性言说,从而有着显见的女性立场,那么到了《遍地枭雄》里,女性则被拒绝出场,男性不仅是叙事的主角,且被冠以“枭雄”的美名。但女性人物在文本中的缺失并不代表作家对性别反思的缺失,这样的故事情节设定——“韩燕来”们只能在幻想的世界里随心所欲地游弋,一旦回到现实社会,就只能以悲剧收场——已然表明作者的性别态度。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脱离女性而存在的,现实社会不容男性独属,男女共生才是现实之本。王安忆以这种貌似极端化的写法“揭示和论证了完全脱离女性、脱离社会的男性独立价值的不可能性,简而言之,也就是‘男性英雄论’在当今社会的彻底覆灭”[9](P103-107)。如此,王安忆以“虚妄”来反证“虚妄”,实现了其“超越性别局限”的写作理念,只是相较于迟子建的朴直,王安忆的表达更趋隐晦。
戴来的写作也喜欢聚焦于男性,这一点与王安忆《遍地枭雄》的性别关系反思策略相似。但不同的是,戴来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并不拒绝女性的出场,而是把男女两性都投掷于叙事进程当中,让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碰撞交叉,演绎性别之维的复杂。戴来一贯远离宏大历史的描述,她似乎更偏好将男性置身世俗生活的烟火中,在庸常又烦琐的婚姻、工作里展露男性人物的品性情状,“不是要展现男性的强悍与力量,恰恰相反,走入他们的内心展现他们外表下的脆弱与无奈才是戴来此种书写的诉求 。”[10](P75-78)在戴来这种置换性别的写作里,现代男性真实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困乏被由内而外地透视出来,男性不再是被历史传统预设的强势主体,其看似岿然不动的坚强与从容在“爬满了虱子”的生活里其实不堪一击。戴来笔下有一大批这样陷入生存困境的男主形象。《给我手纸》里婚姻尴尬、生活疲惫的岑晟,《红烧肉》里懦弱无能又暴躁易怒的可怜男人,《没法说》中限于臆想和猜忌而导致心灵扭曲的父亲,等等。同时,戴来也以男性视角或中性立场刻画置身其中的女性人物的可敬或可憎,写女性同男性在世俗生活里的纠缠、斗争、和解或彼此冷漠。从某种角度来说,戴来的写作可谓是对女性写作未知领域的一次探索,因为,以女性之躯的写作来“代男性发言”,这样一种“设身处地”的性别叙事看似另类,实则更像是对传统男性写作里“代女性发言”的一种戏仿,令读者的阅读体验分外新颖和有质感。在这种被置换的性别体验中,女性读者能透视到男性的心理世界,而男性读者也能体会到异性作者的共鸣,从这个角度上讲,是对以往“女性主义”独角戏式写作的平衡与调和,有助于推动女性写作与异性关系的建立;同时,对开拓女性写作视阈也不无裨益。
除此,还有方方、魏微、盛可以等女性作家也在她们的作品中显露了对于性别关系的对话态度。正是这样的性别关怀,使得21世纪的女性写作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个体自我”。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女性”身份渐显暧昧,而“作家”身份则趋于鲜明。
总而言之,21世纪的女性写作在性别姿态上有一种策略性的渐趋低调,个别作家的性别立场甚至是暧昧模糊的,她们放下宣言和战斗,转而关注两性最具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在看似平淡实则暗潮涌动的婚姻关系中审视两性各自的弱点、迷惘、无奈和精神苦痛,揭示两性之间既相互矛盾又彼此依赖的微妙关系,并交织着对伦理道德的探询;部分女作家甚至刻意以男性视角和口吻切入叙事,以“设身处地”的性别转换叙述方式,在错位的情感对峙中寻求两性的和谐并表达普世的人性关怀。当然,也有部分作品显见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关注,但是方式更趋理性和客观。或许这也是女性意识表达的一种新的叙事策略。既是写作技巧上的创新策略,也是内容上的转型策略。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对“历史”的态度是审视性的,执着于“指认历史的男权性质,指认由男权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历史’对于女性的舍弃、遮蔽、贬义和扼杀”[11](P200),极力以对既往历史的解构和对母亲谱系的建构为策略来弥补女性在历史书写中的不在场与溃败感。而多元文化语境激合下的21世纪女性写作除了将性别视阈指向看似更温和的性别对话和更宽广的社会现实,也在有意无意中淡化了与历史的“恩怨”,将“历史”化解在现实或日常叙事的平和、节制和波澜不兴之中。
上文提及的铁凝的《笨花》,是21世纪指涉历史主题的女性写作中尤为突出的一部。全书涵盖了20世纪前50年的历史时间,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历史写作之区别在于:其一,如前所述,《笨花》不以女性人物为主角,也并不采用女性的特定视角展开叙述;其二,与90年代的女性历史写作惯于以碎片化的历史事件来撑起时间上的线性叙事并以此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不同,《笨花》对于历史的书写虽也充满了大量的类似碎片的日常化生活,但铁凝并无意解构历史,她曾说,《笨花》“在宏大叙事和家常日子之间找到一种叙述的缝隙,并展现了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12](P36-38)。而她所谓的“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书中一再突显的“笨花精神”,即一种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和精确细节的“日常精神”,如文中大量出现的笨花村的民风民俗、四季农事、人情世情,甚至笨花村在兵荒马乱大时代背景下显示出的血缘宗族观、宗教观、阶级观、民族观、革命观,都以日常性来体现这种精神[13](P80-89)。同时,《笨花》将日常生活置于叙事的本体性位置,以此推动叙事的铺展,也与以往的多数女性写作行为中极力拒斥日常书写,并将历史理性的必然性与合法性作为叙事本体的宏大历史写作拉开了距离。
如果说铁凝是以“日常性”来完成对历史意识的淡化,那么王安忆的《天香》则是重新建构了一个文化视阈(而非性别视阈)里的历史。《天香》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虚构演绎出申氏家族由盛转衰的故事,由此编织出晚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折射出世事盛衰、历史更迭的因由。其中申氏家族几代女性的命运波转是这本书的连轴,明末上海的世情以及大家族里的生活日常和细节是肌理,作者将这些闺阁女性的生命际遇置于“社会”“家庭”的变迁之中,也置于衣食住行的琐碎日常中,但与《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不同,《天香》里的女性并没有在历史的浮沉里随波逐流,而是以绣艺延缓着家族的没落,最终“天香园绣”发扬光大,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实现了女性对历史的对抗和重构。作者努力还原一个尘封的时代,写制度、写衣食住行、写造园、写服章、写技艺、写“天香园绣”历经“闺阁—艺术—民间”的发展轨迹,以细小而实在的器物面对漫长宏大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在“变”与“不变”的微妙辩证中完成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溯源,从而也呈现了一种新颖的历史打开方式——虽然这是以“上海”为符号的。
林白继《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后,又推出了长篇《致一九七五》,小说题目已然明示了它的“历史性”视角。“历史”以回忆展开,但这种回忆是从容的,加入了大量的生活细节和现实图景,使得关于“历史”的描写充满了蓬勃的生机。林白一扫曾经幽暗冷冽的叙事声音,用平和的日常化叙述替代以往吼叫似的叙述,只撷取生命的片段,静静拂去历史角落里的尘埃,笔调轻盈而有光泽,于是“历史”就在这种“轻盈”当中,褪去过往女性历史书写里的沉重晦暗,作者也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技法完成了对历史的追溯反思和对现实的抚摸。
正如《天香》中高雅精致的“天香园绣”最终从闺阁流散到民间,融入世俗生活,21世纪的女性写作者们也纷纷从遥远暗淡的历史中收起笔尖,回归日常。面对那些只在过往岁月中留下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女性与历史的“恩怨”,女性写作者们更关注的是女性作为一个常态的“人”,而非狭隘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对历史的反思、对生活的参与和体验,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将触角伸向男性容易忽视和轻视的生活细节,视笔尖为“现实的显微镜”,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日常化的重构。她们的写作旨归正慢慢由对女性历史的挖掘演义变为对现实的关注,将个人置于“社会”“家庭”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反思历史,审视现实。
如果说20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关键词是“身体”“欲望”“性别”和“历史”,那么到了充满多重语境的21世纪,上述关键词已被悄悄置换或刻意淡化。21世纪女性写作既有对20世纪女性书写传统的继承发扬,呼应着当下中国新语境的同时也绽露出许多新特征,在更阔大的现实大地中显示出阔朗明媚,退却、坚守、前进与转向并行。但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缺憾。刻意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规避、过分淡化性别意识,尤其是对女性意识的压缩或变形,如果掌握不好“度”,很有可能让女性写作从商业消费的深渊滑入女性主体缺失的深渊,甚至有陷入对男权传统的回归和趋同的危险;对宏大历史的拒绝,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写作深度和主题厚度。“今天的女性作家在写作上的难度遭逢空前挑战,这种挑战是难以一言蔽之的,它既包括来自女性文学传统自身的内部挑战,也包括来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传统的全面挑战,同时,艺术与思想上的双重挑战更令写作难度犹如倒悬之苦。”[3]但是,新世纪的多元语境为女性文学开辟出了一片漫长而又广阔的时空,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写作者尚有足够的时间和领地为自己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