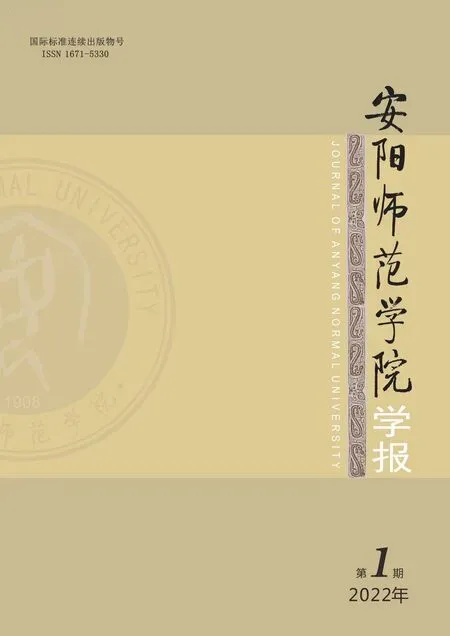《周易程氏传》中的理学旨要探微
崔 波,邵 宇
(1.郑州大学 《周易》与古代文献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1;2.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经学哲学化”(1)向世陵教授在《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一书中直接以“经学哲学”这一说法来研究经学的变革和理学的兴起;蔡方鹿教授在《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也以“经学哲学”说明宋初经学上的创新;邓庆平学者在《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一书中运用“经学哲学”的概念对朱子门人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李记芬学者在《刘敞“复静”论研究》一文中以“经学哲学”表达北宋初经学义理化这一思潮变化。安井小太郎在其书《经学史》中明确指出宋代经学的一个特征就是经书解释的哲学化和形上化。由此可见,“经学哲学”已经成为研究宋学的重要应用范畴。指的是经学诠释的哲学化、义理化,它是汉学转向宋学或经学转向理学的重要思想特征。北宋理学家们以“疑经变古”的方式一改汉唐“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注疏原则,直接回归到先秦儒家原典之中,侧重于探讨和阐发其中的义理成分。在诸多儒家经典之中,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自然是理学家们必然关注的对象。因此,理学视域中的易学注解版本较多,无论是张载、周敦颐还是二程都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公认程颐之《周易程氏传》义理解读最为透彻。程颐曾经这么解释易学:“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今人须看了易,方始看得系辞。”[1](P164)这实际上道出了他注解、诠释《周易》的特色所在。朱伯崑先生对此称赞道:“从易学史上看,流传下来的义理学派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前有王弼《周易注》,后有《周易程氏传》。”[2](P195)程颐正是在易学与理学的交融视域中诠释义理发扬儒学。通过对程颐之《周易程氏传》的考究,我们可以看到程颐是在严格的儒学立场上对易传进行注解,此书不仅弥补了王弼的未注之辞,同时也清算了汉本易学之中的道家成分,终结了这种注疏的研究范式,更是作为宋代易学哲学研究的奠基之一,树立了理学易学交融阐发的模板,对后世易学的义理提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易学与理学交融视域中的《周易程氏传》
高怀民先生曾在《宋元明易学史·自序》中说:“周、张、二程学养固然好,但其主要学思指向在于理学,不在易学,非纯然易学家。”[3]他在这里是以邵雍为纯易学家的标杆来定位周、张、二程的易学。基于这种对比,再结合《周易程氏传》的成书过程及评价,其论述确实十分合理。
根据《伊川先生年谱》记载,《周易程氏传》成书于元符二年(1099年,此年程颐66岁),但直至崇宁五年(1106年,此年程颐73岁)程颐才将其书公开讲学,开始传授于弟子尹焞、张绎二人[1](P345)。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外在政治环境问题,崇宁二年(1103年),程氏之学因被范致虚等人诬称为“邪说诐惑乱众听”,而被当时的河南府追究,“尽逐学徒,复禁当籍。”[4](P590)所以程氏之学不得其传。随着崇宁五年(1106年)程颐再次致仕,政治环境略有变化,程氏之学可暂时得传。另一方面是程颐对易传注解的高标准要求。在程颐自己看来,尽管易传成书已久,但是其中旨要还需不断考究。授学之时程颐说过“自量精力为衰,尚觊有少进耳”[1](P345)。这并非是说《周易程氏传》还存着缺陷与不足,而是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凝聚了其毕生的学问主旨与精神所在。所以尹焞在先生祭文中无不钦佩地写道:“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以。”[1](P345)综合考虑到程颐的一生学问研究,他作为理学大宗,更注重挖掘儒学经典之中的原始义理与精神,因此,孔子之《易传》必然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而进行的注解。所以,《周易程氏传》必然是基于儒学的立场,特别是“理学”这一当时新儒学理论形态的立场。同时结合程颐的生平时间来看,易传成书于其晚年之时,对于这样的理学大宗而言,此时正是其理论思想、人世体究、总结反思最为深刻之时。因此,《周易程氏传》可称之为其毕生精力之成果,此著作之中的义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程颐理学的高峰。因此,将《周易程氏传》定位为一本具有丰富儒学义理的易学著作,毫不为过。
也正是因为其书具有这种性质,所以清代编著的《四库全书》将其列入《经部》“易类”,而非《子部》“术数类”[5](P6)。按照四库馆臣在《总目》归类问题上所遵循的原则:“不以方士之说混羲、文、周孔之大训”,绝不可“牵异学以乱圣经”[6],以目录的归类来实现官方儒学思想上的清理,程氏易传隶属官家儒学之列。一般而言,《四库全书》中关于“易学类”文献的分类有“易学两栖”的说法,其延续的是孔子关于易学之“卜筮”与“德义”的区分标准,《经部》“易类”注重公理,而《子部》“术数类”注重术数[7]。对于《经部》而言,其功能和地位在于“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5](P1)。由此可以看到,《经部》实际上是一个纲领性的存在,其所揭示的是天下之共同所遵从的普遍性的“公理”。它强调“公理”作为人性修养、辨明是非、史诗经验的衡量标准:“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5](P769)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道统上的自觉”[7]。那么对于归于此类的《周易程氏传》而言,也必然符合以上原则。在有关《易传四卷》(也即《周易程氏传》)的总目论述中这样说道:“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5](P6)结合上文高老先生的说法以及邵子之数存于《子部》“术数类”的分类,我们可以说程颐之《周易程氏传》实则是一部儒家理学典籍。
总之,上文分别从程颐易传成书的历程以及《四库全书》的分类方面来证明程颐之《周易程氏传》是基于易学与儒学的交融视域,以宋代儒学立场去注解、解读易传,进而阐发出儒学的义理成分。用我们现在的视角去看,这种义理成分其实就是我们所知悉的理学哲学内容。仔细研读《周易程氏传》的文本内容,我们便可清晰地发现程颐对易学诠释的哲学化、义理化。正如胡安国之《奏状》中所总结的:“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1](P349)
二、 “因理以明象”与“因象以明理”
《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一》中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襳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5](P1)这一段话交代出易学的流变过程。第一,易学文献的核心旨要在于“明道”;第二,胡瑗、程子之易学不同于其他人之易学的地方在于“阐明儒理”,这是易学的一大变化。而如何“阐明儒理”则离不开程颐对儒家义理、卦辞爻辞、卦象之间关系的处理。
接续上文所言,胡安国认为程氏易学“因理以明象”的概述,通俗来讲,即通过天理、物理、人理等来诠释卦象。这里事关的是“理”与“象”的关系。在程颐看来,“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8](P325)在“理”与“象”之间,“理”是本体,处于第一性,而“象”是第二性。因此,在“因理以明象”的背后实际上还蕴含着“因象以明理”这一层意思。程颐说:“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8](P325)这就是说,作为本体之“理”,由于其纯粹无形的本质属性无法直接为人所知,只能通过“象”这一载体表现出来。这也是程颐在《易传序》中所说的“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1](P689)。因此,“象”之中也就蕴含着“理”,通过对“象”的深层次考究能够把握“理”的存在。以上只是从抽象的层面对“理”“象”的关系进行的简要诠释,下面就程颐易传中的“理”“象”关系进行考察。
首先,程颐在“理本体”的哲学框架中秉承着“随时取义”的原则对“象”进行诠释。程颐在对《否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的注解中说:“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1](P760)在《离卦》之“彖传”中“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的注解中,程颐再次强调了“学者知时义而不失轻重,则可以言《易》矣”[1](P850)。在他看来,“随时取义”是诠释“理—象”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这种既坚守原则又保持灵活的处理,才能做到取“象”用“象”而不被“象”所困。人们可以由辞观象,由象识理。如果抓住了理义,也就意味着可以实现对象数的正确把握。因此,得其义而忘其象与王弼所强调的“得意忘象”颇有相近之处。与王弼在“扫除象数”之时对“老庄”引入不同的是,程颐则是基于儒学的立场进行诠释。
其次,程颐将易学之理同物之理与圣人之道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回归到孔子释易归儒的传统之中,做到“随时取义以从道”,《乾卦》和《坤卦》集中体现了这一旨要。在《乾卦》的诠释中,程颐在注解“初九,潜龙勿用”时说:“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便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初九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阳气方萌。圣人侧微,如龙之潜隐,未可自用,当晦养以俟时。”[1](P695)意思是说,无形的“乾”之“理”不能自己表达出来,只能通过“龙”之“象”来彰显。而之所以将“乾”与“龙”进行配比,原因在于“龙”的变化属性,其灵动变化而不易把握,正相符合“乾”之义理,阳气之消长,同时也是圣人进退之道。以初九之位置,圣人处于低位,此时当是退隐之状,正和“龙”在腾飞之前的潜伏隐藏是一个状态,因此这个时候当是韬光养晦、积聚力量之时。通过将圣人之道”与“龙”的融合起来相互解释,不仅阐明了卦象,同时也贯彻落实了义理精神。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程颐关注的并非只是抽象的经文之义与纯粹的天道,而是存在于周边世界的人事、社会与政治。诸如此种注解模式遍见于《乾卦》各个爻辞之中。从卦辞注解中的“上古圣人”到初九注解中的“圣人侧微”,再到九二之中的“舜之田渔”,九三之中“舜之玄德升闻”,九四“舜之历试”,九五“圣人既得天位”,上九“圣人知进退”,分别代表着圣人在不同时期的处世之道。换言之,程颐是以“舜”这一位古圣王的不同处境来象征《乾卦》之变化。爻辞注解中关于“舜”的说法散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与《尚书·尧典》之中。详细而讲,九二爻“舜之田渔”讲的是舜无论是在历山田间耕作还是在雷泽打鱼,在他的影响下,四周人民皆是相互嵌和,民风淳朴。正是因为其所具备的这种中正之气和高尚品德,才会奠基起之后的机遇与尧的赏识。尽管此时依旧远在田郊,身份卑微,但是其品行已达圣人之才,所以说“利见大人”。九三爻“舜之玄德升闻”,是讲此时舜的德行已经被尧所知晓,与以往相比处于接近尧的上位,这个时候很容易被人嫉妒诬陷,对于君子而言,这个时候理应保持内心的康健,小心谨慎地做好自己,所以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爻以“舜之历试”之时来说明,按照程颐的说法,是指舜此时已经接受了尧的考验,开始总理百事。但这时舜正处于上与下的关键地位,这种位置难以把握,但舜依旧将事情处置得井井有条。对于九四爻而言,处于上卦之下,下卦之上,阳爻居阴位,不当而不正,因此十分危险,借以舜的事迹则是劝告君子要向舜一样敢于前进,顺势而为,秉道前行,进而“无咎”。九五爻“圣人既得天位”是指此时舜已经承接尧位,处于帝王尊位,广纳人才,以德治国。对于九五爻这一中正之位而言,与九二爻相应,所以讲“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爻以“圣人知进退”而劝告,以尧的晚年与舜的做法为例示警,物极必反,所以讲“亢龙,有悔”,君子处于最高之位要知进退之道。通过对《乾卦》六爻的详细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程颐以舜的一生来诠释“人君”与“天道”,告诫君王要效法“天道”,行德性之治,这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也”。结合宋儒对“圣人之道”的体悟以及他们对心性论、工夫论的建构,由此我们知道,程颐在此讲的也即“修齐治平”的问题,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程颐在诠释易传之时所遵循的逻辑理路:首先剖析象辞,然后引申至儒家义理之学,进而归置于圣人之道。在这里“道”这一原则贯穿于程颐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解读之中。
程颐在《坤卦》中亦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诠释阴阳之道,其中最为核心的当属君臣之道。在对卦辞“先迷,后得,主利”的注解中说:“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1](P706)所谓“迷”则在于阴先阳后,所谓“得”则在于阳先阴后。意思就是说阴要等待阳的倡导再进行应和,这才是阴阳常道。在程颐看来,这种阴阳之道和君臣之道具有一致性。君臣分为阴阳,为臣之道当是顺应君王之号令,操劳于事务是为臣的职责。在“六三爻”的《象辞》“含章可贞,以时发也”的注解中对为臣之道进行了详细讲解,程颐说:“夫子惧人之守文而不达义也,又从而明之:言为臣处下之道,不当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含而不为,不尽忠者也。”[1](P709)程颐借孔夫子语强调,之所以会有象辞,是因为担心人们只会固守字面意思而不能深刻领悟内在深层的义理,而象辞的作用就在于进一步揭示出象之理。为臣之道当是涵养美德于内身,不应当过分宣扬功劳善德,这样才是恒常之道。但这并非意味着为臣之道尽是守成不出之道,而是要依据时机顺势有所作为,含藏而无所作为则是不忠之人。仅从以上两处对“为臣之道”的诠释便可看到程颐内心的坚守。不同于乾卦中对“君道”的推崇,坤卦则是对“臣道”的寄托,这实际也是北宋士大夫“得君行道”理想的体现。
因此,无论是“因理以明象”还是“因象以明理”,程颐都是借“理”与“象”之间本末关系来演示“天道”与“人事”,而在具体的“象”的理解上,则要遵守“随时取义以从道”的原则。从逻辑上肯定“理”的本源性,“理”是“象”产生的“所以然”,这其实就是程颐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即“理本体”的哲学思想。在他看来,天下只有一个“理”,这个“理”首先就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道”,“象”则属于形而下之“器”的范围,是“理”所形成的可以被人之感官所认知的具体形象或器物。换言之,“象”实际上构成了“理”与“气”、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贯通环节。同时,这个“理”还是“儒家伦理道德之理”,是“圣人之道”,是为君者、为人者都必须遵守并效法的“理”,只有遵循此“理”才能避祸趋吉,成就圣人伟业。总之,在程颐这里,“理”在自然层面就是万物运行的必然法则,于人间社会,就是儒家圣人之道,二者又同是一个“理”。这就不仅为“象”的产生以及自然和社会的运行寻找到本体依据,同时也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宇宙本体的哲学高度[9]。
三、“体用一源”与“理一分殊”
从上文关于“理”与“象”关系的考察中可知,二者之间的相融关系,用理学的范畴来讲,这就是“体用一源”,也即胡安国所讲的“知体用之一原”。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P689)这里的“源”就是他所强调的“理本体”为体,“体”就是指万物自身的“所以然”,是“理本体”在现实事物上的贯彻和落实,这些“所以然”不仅指“理本体”,还指具体的物之“理”;而“用”则是指这些具体的物之“理”在外所形成的“当然”,这些“所以然”和“当然”归根到底都是“理本体”在不同处境、物象之中的展现方式。对此,朱熹的解释就比较充分,他说:“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晦庵集》卷三十《答汪尚书》)。又说:“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而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10](P9)朱子这种“理在物先”的解读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在他看来,“理”的状态是一种纯粹空然之状,属于第一性,但实际上已经蕴涵了“万象”之样,也就是“即事即物”之样。而一旦事物之象得以落实,亦同时具备“理”之体,体用之间是相互圆融的,所以称之为“无间”,这也正是朱熹之“无形而有理”的哲学本体论思想。
但是程颐关于“体用”这一理学范畴的应用与解读又是遵循着“随时取义”的原则,解易之时并非机械地局限于某一个概念的教条应用,如在《易序》中,程颐就曾说道:“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1](P690)从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卦辞代表着整个卦的性质和走向,对于爻辞而言,是一个基本的、整体的存在,爻辞则是对卦辞的具体展现,可以说卦为体,而爻为用。但无论是卦还是爻,“皆所以顺性命之道,尽变化之道也”[1](P690)。由此可见,“体用”范畴的应用尽管不一,但落脚点最终都在一个“理”字。正如程颐针对“《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注解的那样:“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1](P690)这实际上就是程颐“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易学之中的应用。
以《咸卦》为例。程颐在注解九四爻“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时说道:“夫贞一则所感无不通,若往来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则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动,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类则从其思也,以有系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岂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系辞》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夫子因咸极论感通之道。夫以思虑之私心感物,所感狭矣。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其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故贞其意,则穷天下无不感通者焉,故曰‘天下何思何虑’。”[1](P858)
按照程颐对《咸卦》整体卦意的把握,此卦上下皆能相互感应,其主题是阴阳、男女交感。从“天道”层面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从“人事”层面看,“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1](P273)。而要想实现“天道”与“人道”的顺利感应,就需要做到虚怀若谷。从卦爻整体结构来看,九四爻处于上卦之下,下卦之上,依据卦象而言,即正处于股背之交,相当于人之“心脏”所在。因此,九四爻实际上属于《咸卦》之主爻,但由于其不居“二、五”中正之位,所以有失偏失正之嫌。从六爻应位来看,九四爻与初六相应,阴阳相感,但由于初六处于“咸其拇”的状态,其志在外,所以对九四之感未能回应。那么,对于九四而言,必然是辗转反思,心神不宁,即“憧憧往来”。“朋从而思”之中的“朋”指的就是初六。只有九四坚守“贞吉”,即坚守正道,耐心感应,初六才会被九四之诚心所感化,进而顺应接受九四之爱慕之心,终成佳音。由此可知,程颐是从至虚本体的角度,或者说是从“理本体”的角度去考虑,因此他在这里所讲的“理”都不能简单地从“天下的道理”这种普通层面去理解,“贞一”在这里其实就是“理”的一种表述方式。从程颐对《周易·系辞》中“同归而殊途”的解读就可以看到他将这个同一的归点划归为“理”。在他看来,天下只有这么一个本体意义上的体,其虚中无我,纯粹中正。虽然它的用途以及所呈现出来的物样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是“理”的落实和表现。因此,没有必要执着于物样,只要把握了这个“理”,则天下万事无所不通,因此也就不会被思虑所困。基于这样“理本体”哲学框架,程颐批判了“以思虑之私心感物”的做法,但是他并没有反对这种“以心感物”的方式。实际上程颐在其他地方就这一方式进行了着重考虑,尽管主要是针对“气”,但百变而不离其宗。他说:“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无即无,无古今前后。至如梦寐皆无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于形声之类,则是气也。物生则气聚,死则散而归尽。”[1](P56)
他在另外一处则是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诠释:“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烘炉。遂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其造化者,自是生气。至如海水潮,日出则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则潮水生也,非却是将已涸之水为潮,此是气之终始。开阖便是易,‘一阖一辟谓之变’。”[1](P163)
程颐以“理”为本,认为气化聚散,事物形象随着气聚而生,气散而灭,而决定这一切变化的则是“理”,因此,心能感通的不是物象而是一个“理”。他进一步强调“理”决定气的变化是一个单向的运动,他以“潮水生落”来说明气一旦消亡就不可再生,也就不会回归到原始之“理”。尽管这一论证颇显吃力,但其核心旨要倒是表达得比较明确。在《萃卦》的注解中,程颐更是进一步说明:“观萃之理,可以见天地万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动静终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观其所以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P931)聚散只是变化之现象,只要把握了“所以聚”,即物象或气之聚散的根据,就能够推天道至人事。
但这并非是断绝“理”“气”之间的融合关系,程颐以“开阖便是易,‘一阖一辟谓之变’”作为总结。依据《周易·系辞》的说法“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11](P543)。“阖”是关闭门户,象征着阴之坤;“辟”是打开门户,象征阳之乾。阴阳之变化正如同门户一开一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开,这正是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所谓“通”就是阴阳往来不穷的相互变化,催生了天地万物。而这些外在的显现就是“象”,具体的形状则叫作“器”,而可供人们通用的规律称之为“法”,这其实也就是“道”在不同领域的运行规律。而这些规律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称之为“神”,这就是“显微无间”的最高状态。
四、小结
通过以上对《周易程氏传》中程颐注解的考察,我们就不再是基于抽象意义上去谈论《周易程氏传》的学派性质,而是可以确证其不仅是一部易学著作,更是在宋代易学与理学交融中所形成的一部理学著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程颐是在严格的儒学立场上对易传进行注解,基于“理本体”的视域中去考察易传之义理。他运用儒学最新的理论形态——理学思想就易传之中的问题进行新的解读与阐发,不仅承继改造了以往研学中的诸多哲学命题和范畴,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有理性特色的范畴和命题。具体而言,他利用理学的范畴对传统易经进行新意解读,如“理气”“天命”“体用”等,从而建构起理学模式中的易经体系。这些范畴并非程颐之独特发现,多数于先秦之时就已存在,但程颐借助旧词赋予了新的哲学义理,进而使易学在它这里具有明确的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意义等。同时这也证明了程颐易学解读的“道统”地位,即是对先秦儒学精神的回归,而不是仅限于字词上的咀嚼。而孔氏《易传》在程颐之理学这一最新儒学形态下也实现了新的发展,彰显出新的活力。就其理学内容而言,他基于“理本体”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理”与“象”的问题,将一般意义上的“天下之道理”上升到具有哲学本体性的“理”意义,详细地区分了形而上下以及“象”的中间地位,提出“因理以明象”与“因象以明理”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被程颐进一步归为“体用一源”,这其实也正是程颐之“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易学之中的应用。这些内容都彰显出程颐对易学诠释的哲学化、义理化。对于把握《周易程氏传》的学派性质以及宋代儒学、易学形态的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易学阐释分期断代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