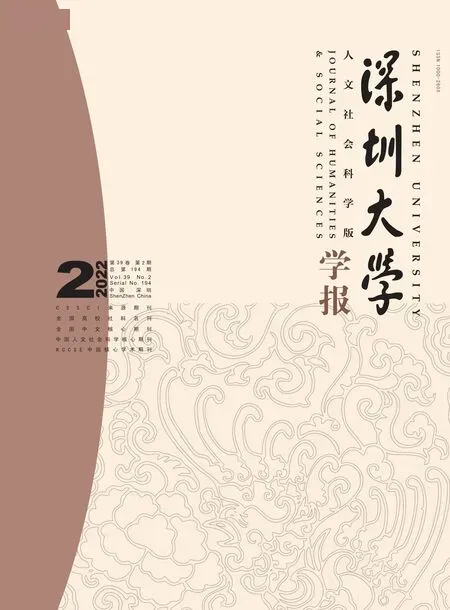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
陈玉强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国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1](P1)为首,中国文学以“韵者,美之极”[2](P372)为审美理想。 可以说,“韵”是建构中国美学传神写意体系的核心范畴。“韵”的内涵建构具有由自然到人文、从形下向形上发展的特点,在魏晋六朝时期形成了两种认识趋向:一是通过对自然界声音节奏的感知及对音乐的审美体验,形成“音和为韵”的形下阐释;二是通过对人物气度的观察及对绘画作品的鉴赏,形成“舍声言韵”的形上探索。 二者对南朝文学的声韵学说及绘画的气韵学说有着深刻影响,也奠定了唐宋以来探讨“韵”之内涵的基本模式。 “韵”作为通称共名被使用时,其多层次蕴涵纠葛在一起,存在一定的含混性。 以往对“韵”范畴的研究存在以求同思维探求范畴统一性本质的趋势,诸如认为基于声韵之韵的和谐义是气韵之韵的本质,忽视二者语境及哲源的差异,强为之解,导致“韵”范畴语义的历史性及语用的差异性反被遮蔽。
本文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是基于对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学理考量,旨在统一性之外探求差异性,以呈现“韵”的复杂面貌。 文艺美学对“韵”多层涵义的参与性建构及选择性使用既存在意界融合,也存在审美分野,且后者要早于前者。 就笔者的观察而言,“韵”最初并未在文学与绘画二者之中形成审美共识。 从“韵”在谢赫《古画品录》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呈现的内涵来看,南朝画论与文论中存在“舍声言韵”与“即声言韵”的审美分野,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需要从发生学及观念史的视野,对“韵”字的起源、内涵建构、哲学渊源及审美演化进行研究。
一、“韵”字的起源及“音和”义的建构
“韵”字出现于何时? 以往主要有先秦说、汉代说、建安说、魏晋说、晋宋说5 种说法。 以下举其要者,试加辨析,以阐明“韵”字产生的时代语境与其初义建构的关系。
“韵”字出现于先秦说,以清代陈澧为代表,今人亦有以青铜器铭文声援此说者。 陈澧《东塾集》卷四《跋音论》举《尹文子》“韵商而舍徵”一语,认为“此韵字之见于先秦古书者”[3]。 但是今本《尹文子》疑为南北朝时期的伪作,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指出:“今所传《尹文子》分二篇。 言名法之理颇精,而文亦平近。 疑亦是南北朝人所为,故《群书治要》已载之也”[4]。 对《尹文子》的真伪问题,学界或有争议;搁置争议,从此书所引“韵”的含义入手,我们亦可提出质疑。 陈澧所引《尹文子·大道上》“韵商而舍徵”,即喜好商声,舍弃徵声。 “韵”与“舍”相对,有喜好之意。 据邵宏考证,韵字用作动词,应在东汉蔡邕之后[5]。 故而陈澧之说不可轻信。
近年有学者以先秦青铜器铭文证明“韵”字起源于先秦,其说先引用清代阮元《文韵说》:“王复斋《楚公钟》篆文内实有‘韵’字。 从音从匀”[6]。 又引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商钟四》及卷六《曾侯钟》篆文的释文,以两器上皆有从音从匀的“韵”字,“可证阮元说不诬”[7]。 但是上述青铜器铭文的释文并不可靠,阮元后来也改变了他的看法。
阮元所谓“王复斋《楚公钟》”指南宋王厚之(号复斋)《钟鼎款识》收录的《曾侯钟》,以其铭文记载楚王之事,故别称《楚公钟》;此铭文引自比他稍早的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曾侯钟》。 铭文中有一句被薛尚功、王厚之释为“楚王韵章作曾侯乙宗彝”[8](P105-106),其中“韵”字实是误释。 “韵章”指楚王姓名,但楚王以“熊”为姓,而非以“韵”为姓,此为常识。 阮元在《钟鼎款识》跋语中指出此铭文“章上一字不可识。 钱献之以为古能字通熊,此字为能字之省变”[9]。 可见,阮元修正了他在《文韵说》中的说法,认为此“韵”字并不可识,并引钱献之的说法认为是“能”字的省变。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酓章镈,其上的铭文与上述《曾侯钟》铭文一致,说明有相同铭文的钟不止一件[10](P92)。 楚王酓章铭文上涉及楚王姓名的一句,郭沫若据字形隶定为“楚王酓章”,遂成学界共识。 罗运环 《楚王酓章铭文疏证》 指出:“酓,宋人隶定为‘韵’,与原字形不合。 ……郭沫若隶定为酓,说:‘酓假为熊,近出《楚王鼎》幽王熊悍作酓忓,正为互证。 ’今按:酓,从酉今声,在上古属于侵部影纽,熊为蒸部匣纽,二字音近,故可通用。在楚人姓氏中,传世文献均写作熊,出土文献多写作酓”[10](P92)。 此可为定论。 同理,薛尚功《商钟四》释文“望能全之格韵”[8](P9)之“韵”字,其字形既然与《曾侯钟》误释的“韵”字形一致,也就不能视之为“韵”字。 因此,以青铜器铭文证明“韵”字出现于先秦,不能成立。
“韵”字出现于汉代,今人多持此说,又分为西汉说与东汉说。 持西汉说者,以《全汉文》收录西汉京房《律术对》、班婕妤《捣素赋》中的“韵”字为证据;持东汉说者,以《全后汉文》收录东汉张衡《鸿赋》、蔡邕《琴赋》中的“韵”字为证据。 但是上述证据皆存疑。 清代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汉代文献用“韵”字者,多非汉代之旧。《全汉文》收录西汉京房《律术对》有“听乐韵”“韵清影长”“韵浊影短”[11](P741)等句,注明出自“《御览》十六引京房传”。 检索《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太平御览》卷十六,上述3 处“韵”皆作“均”,《后汉书·律历志》所引亦作“均”,可知《全汉文》这几处“韵”字不可信。 《全汉文》收录西汉班婕妤《捣素赋》有“勋陋制之无韵”[11](P372)一句,宋刊本《古文苑》所引虽同,但《文选》李善注谢惠连《雪赋》,已疑《捣素赋》非班婕妤之文[12](P592)。《全后汉文》引东汉张衡《鸿赋》有“远心高韵”一句,宋刊本《太平御览》所引亦同;但武英殿本《隋书》引作“远心高致”,则此处“韵”字亦存疑。 《全后汉文》收录东汉蔡邕《琴赋》“雅韵复扬”[11](P1707),“韵”字恐也经后人窜改,《文选》李善注陆机《文赋》引《琴赋》作“雅音复扬”[12](P768)可证。 故而上述证明“韵”字始于汉代的文献皆存疑。 所谓严可均所据或另有版本者, 亦无实据,难以采信。
“韵”字出现于晋宋说,以明末清初顾炎武、清代卢文弨为代表。 顾炎武《音论》卷上“古曰音今曰韵”条指出:“今考自汉魏以上之书并无言‘韵’者,知此字必起于晋宋以下也”[13](P23)。 清代卢文弨也指出:“韵之为言,始自晋宋以来”[14]。 但是此说已被清代阎若璩批驳,他在《尚书古文疏证》中指出:
余谓《文心雕龙》:“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晋书·律历志》“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 ”二书虽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韵”字。 知此字之兴,盖于汉建安中。 不待张华论“韵”何况士衡? 故止可曰古无“韵”字,不得如顾氏云起晋宋以下也[15]。
阎若璩认为“韵”字出现于“汉建安中”。 建安(196-220)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其时政权已被曹操把持,汉朝已名存实亡。 阎若璩的建安说与上述汉代说有所不同,但也仅有《文心雕龙》《晋书》论曹操重视音韵的间接证据,未提供直接文献依据。 “韵”字出现于魏晋说,以清代徐鼐为代表,他在《读书杂释》中说:“经籍无‘韵’字,汉碑亦无‘韵’字,盖起于魏晋之间”[16](P209)。 这一说法绍述顾炎武、阎若璩之说而有所综合,但依然不准确。
现代学者徐复观认为“韵”字起于汉魏之间,近于阎若璩之说,且认为曹植《白鹤赋》“聆雅琴之清韵”为“韵”字之始[17](P100)。 但在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中,曹植此句作“聆雅琴之清均”,用的是“均”字而非“韵”字,虽然“均”字是古“韵”字,但此处不宜作为用“韵”字之始。
根据现有文献,关于“韵”字起源的诸种说法,以阎若璩之说相对合理。 实际上,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三国魏李登《声类》指出:“音和,韵也”[18]。 这是现存文献对“韵”字的早期释义。其后韵书、辞书多采李登之说。 “韵”的释义出现在三国曹魏时期,这与当时探讨声韵的时代风气有关系。 东汉许慎《说文》采用部首分类,精于辨析字形,但其注字音采用“音某”“读若”的直音法,略显含混。 三国魏李登《声类》以声韵相协为部,三国魏孙炎《尔雅音义》以反切注音,在字音研究上取得新突破。
“韵”的初义“音和”正是在曹魏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中建构起来的,与音乐有直接的关联。晋人认为“韵”字的古字是“均”字,从“均”到“韵”,正突出了音乐性因素。 西晋学者晋灼注释《子虚赋》有“文章假借,可以协韵,均与韵同”[12](P869)的说法。 唐初李善注《文选》,对成公绥《啸赋》“音均不恒,曲无定制”句,他注引晋灼之说,并指出:“均,古韵字也”[12](P869)。 据徐鼐《读书杂释》考证,晋灼最早指出“韵”与“均”同[16](P210)。北宋初年,徐铉等人校注《说文解字》补入“韵”字,释曰:“韵,和也。 从音,员声。 裴光远云:古与均同。 未知其审”[19]。 徐铉引用晚唐裴光远之说,却不知其说出于晋灼。 晚唐杨收论乐指出:“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言韵也。 古无韵字,犹言一韵声也”[20]。 可见,“韵”从“均”取义实与音乐有关。
“均”的诸种含义中有两义当为“韵”取义的来源。 其一,“均”指校正乐器音律的器具。 《国语·周语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韦昭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 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21]。 “均”作为测声音共鸣的均音之木,其调声以同声相应为准则,韵的“音和”义从此而来。 《晋书·律历志》“音韵”与“声均”两词并举,可见“韵”从“均”取义的痕迹,其中记载:
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武王。 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22]。
杜夔精识音韵,认为柴玉所铸的钟声均不对,于是数毁改作,引起柴玉的不满,告到曹操那里,最后由曹操测试判定杜夔所定声均为优。 这一记载正是将声均之“均”与音韵之“韵”相联系。 徐鼐指出:“均本均音之木,长七尺、长八尺,其制不可知;然其为调和五音之用,无可疑也。 魏晋以后始亡其器,然其义犹存,故借为调和声音之训。 《广雅》曰:‘韵,和也。 ’是其义也”[16](P210)。 此说甚当。
其二,均即钧,是陶工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正字通》:“均,造瓦之具旋转者”[23]。 《管子·七法》:“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 ”房玄龄注:“均,陶者之轮也”[24]。 声、音、韵有联系也有区别,所谓“单出为声,成文为音,音员为韵”[25]。“音员为韵”之员,即“圆”“周”。 《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句,毛亨《传》曰:“员,均。 ”孔疑达《正义》疏曰:“员者,周匝之言,故为均也”[26]。 可知“音员为韵”借转轮之回旋往复喻指声音的周还谐和,此就同声相应之效果而言。 故而戴侗《六书故》说:“韵,音响相谐也。 声相应为韵。 ……凡诗必有韵,今之字书以音相协为部,曰韵书”[27]。 韵就是同声相应而产生的周还谐和之音。
不论是字形上“音员为韵”,还是字义上“音和为韵”,都反映出“韵”在造字之初与音乐相关。 声律之“韵”也是从音乐之“音”发展而来的。 顾炎武《音论》指出:“《诗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笺》云:‘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 ’按此所谓音,即今之所谓韵也,然而古人不言韵。 ……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颙、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13](P23-24)。 就音乐而言,乐曲是不同音部或声部的声音的和谐共存;就声律而言,声律的形成是由同一音部的声音共振形成。 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指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28](P1128),认为不同的声音相谐是“和”,而相同的声音相应则是“韵”。 刘勰此说正是“韵”脱离音乐范畴转变为声律范畴的标志。不论是异音相从,还是同声相应,本质上仍是声音和谐的反映,实质上并没有突破韵之“音和”义。
二、形神之辨与“韵”之新义的形成
形神之辨是魏晋玄学探讨的重大命题,其旨归是以精神重于形体,故嵇康《养生论》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29]。 魏初刘劭《人物志》品评人物重视由外形考察人的精神,“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30]。 从形而观神是人物品鉴的基本原则,对艺术的形神观念影响颇大。 魏晋时期,政治混乱而思想自由,嵇康、阮籍等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精神解放,这必然要求文艺传写精神。 就绘画而言,东晋顾恺之(字长康)主张绘画“以形写神”[31](P111)“传神写照”[32](P849)。 传说顾恺之的人物画一旦点睛,人物便能开口说话,这当然不可信,但反映出他的绘画极为传神。 顾恺之的传神理论正是魏晋玄学重神轻形思想在绘画领域的体现。 “‘以形写神’,系顾氏总结晋代以前人物画形神之相互关系,与传神之总的。 即是我国人物画欣赏批评之标准。 唐宋以后,并转而为整个绘画衡量之大则”[33]。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风气之下,晋人“舍声言韵”而将“韵”与人的精神气度相联系。 北宋范温《潜溪诗眼》指出:“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2](P373)。 这种变化是伴随人物品评风气而兴起。 “韵”指向人物的气度、性情时,不仅以和谐优雅为美,也以放达怪诞为美。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 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 ”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32](P885)。
“大韵”指特出的气度及情趣。 罗友乞食而不羞愧,这种行为在晋人眼中并不认为可耻而是旷达的表现。 陶渊明写过一首《乞食》诗,实是旷达的自嘲,他晚年虽穷,但还未到去乞讨的地步。 他把蹭饭说成乞食,是一种放旷之举。 陶渊明咏贫更多地是为了表达安贫乐道的志向。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32](P863),指的不是优雅而是放旷。 阮浑之父阮籍正是以放旷闻名,他逢母丧而散发箕踞,白眼向人;醉卧当垆沽酒的邻家美妇之侧,而不自嫌;兵家女未嫁而死,不识其父兄却往哭之,尽哀而还;尝作《大人先生传》,喻君子为裤裆中的虱子,震惊千古。
放旷、怪诞是不和谐的。 “韵”超越声音范畴之后出现了新义,指称的重点不是人物的形体而是其精神,实际有形外之美的含义。 放旷、怪诞只是外形不和谐,精神层面则是个性高扬、心灵自由的表现。
在魏晋玄学影响下,重神轻形渐成时代的主流审美倾向。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指出人物品评:“论情味则谓风操,风格,风韵。 此谓为精神之征”[34]。王珣评司马曜“亹亹太宗,希夷其韵”[11](P3134),指虚寂玄妙的境界,因为“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35],希夷之韵不可闻见,实指形外之美。 “韵之一字,其在晋人,盖由其本训屡变而为风度、思理、性情诸歧义,时或用以偏目放旷之风度与性情,所谓愈离其宗者也。 然考验所及,则义虽歧出,而皆以指抽象之精神,不以指具体之容止,是则其大齐矣”[36]。 是为确论。
三、谢赫《古画品录》“韵”论的哲源及内涵
南朝谢赫将“韵”从人物品评引入艺术批评,他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是以“气韵生动”为首。 “气韵”的哲学来源学界存有争议。 一般认为谢赫所谓“气韵”是上承魏晋人物品评而来,受到玄学影响。 但也有学者认为玄学在南朝已走向衰落,“‘气韵’根本没有可能在玄学的名下作为本体论的观念提出”;“气韵”之“气”的哲学基础是汉代的元气说,气韵源于气运,后者是元气周而复始的循旋运动,即自然之气韵,“谢赫的气韵则是艺术家笔下的创造,画面与宇宙万物同其节奏,是气之节奏和谐的显现,以自然之气韵为本”[37]。 此说虽有新意,但也有牵强之处。
首先,玄学在南朝与佛教思想融合,依然有着潜在影响力。 谢赫认为绘画有气韵之作是“取之象外”的结果,是象外之精灵,即象外之神,他不是从玄学本体论有无之辨而是从玄学形神之辨的角度来谈气韵。 “象外”是曹魏玄学家荀粲在言意之辨中提出的玄学范畴,他认为大道存在于言象之外,是“象外之意”。 东晋以来释僧肇、释僧卫等佛教徒化用玄学术语,以“象化之谈”指称佛理[38]。 从根本上来看,谢赫“取之象外”的主张主要是受到玄学影响。
其次,气韵也并非是基于元气论而作为气之节奏和谐的显现。 谢赫讲“气韵”已经是在晋人“舍声言韵”之后,他突破了韵的“音和”义,讲的实际是基于玄学的传神问题。 “韵”由人物品评移入绘画批评,由指称人物的风气韵度转向所绘艺术形象的风气韵度,其含义有延续性,都重视形外之美。 因此要把握“气韵”的内涵,应当回到魏晋人物品评中去寻找其来源。 《世说新语》评价阮浑“风气韵度似父”[32](P863),这个“风气韵度”指的就是“气韵”。 谢赫将人物品评中的“风气韵度”简化为“气韵”,用于说明艺术形象的风气韵度。 谢赫《古画品录》评卫协的绘画“颇得壮气”,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作“妙有气韵”[31](P95),可见“气韵”与“壮气”意思相同,指向的不是和谐之美,而是传神之美。 因而所谓“气韵生动”是指艺术形象呈现出活泼泼的生命力,简而言之就是传神。
谢赫“六法”首标“气韵生动”,是把传神作为绘画的第一要法。 这可以从谢赫对前代画家的点评中得到映证。 谢赫将卫协的绘画列入第一品,因为卫协兼善六法,“虽不该备形妙, 颇得壮气”[1](P8),他的绘画不以形似取胜,而重在展现艺术对象充沛的生命力,达到神似的境界,所以称得上是“凌跨群雄,旷代绝笔”[1](P8)。 谢赫评张墨、荀勗的绘画:“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 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1](P8)。 张墨、荀勗的绘画深有气韵,具有神似之妙,故列入第一品。 谢赫批评“拘以体物”的形似之作,因其不精粹;而“取之象外”的作品极妙参神,以传神为务,方为微妙。 谢赫评顾骏之的绘画:“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1](P9)。 “神韵气力”意近于气韵,顾骏之的画有精微谨细的形似,但气韵不足,不够传神,所以列在第二品。 谢赫评丁光的绘画:“虽擅名蝉雀,而笔迹轻羸,非不精谨,乏于生气”[1](P22)。 丁光以画蝉雀著名,虽然形似精谨,但乏于生气,不能传神,故列入第六品。 从上述诸例来看,气韵显然是对形似的超越。 张彦远评价谢赫所谓“气韵生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31](P24)。 这正是从气韵与形似对举的角度而言的。
谢赫继承顾恺之“传神写照”的思想而发展出以“气韵生动”指称传神。 徐复观分析谢赫“六法”与顾恺之“传神写照”的承继关系,指出:
除了“经营位置”,如后所述,乃系作品与画布的关系,及“传移模写”,乃系习作的方法以外;自“二骨法用笔”至“四随类傅彩”,皆是顾恺之的所谓“写照”的分解性叙述;而“气韵生动”,乃是顾恺之的所谓“传神”的更明确的叙述[17](P95)。
当然,谢赫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之间可能存在断裂,他自己的画作被认为尚停留在形似层面。姚最《续画品录》评谢赫绘画“点刷研精,意在切似”“至于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39],姚最以“切似”与“气韵”对举,可谓得谢赫气韵说的精髓。
谢赫所谓“韵”,就作品形态而言,受玄学形神之辨的影响,指艺术形象生动传神的风气韵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审美意蕴层面,谢赫是否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而将“韵”指向余音余味呢? 这是值得探讨的。 谢赫虽然提出绘画“取之象外”为有“气韵”,但他讲的“象外”是指象外之精灵,指的是所绘人物的精神,这其中并没有余音余味的含义。韵之余音余味义是北宋时期文人的新开拓,此点详见后文的阐释。 总而言之,谢赫不是在平淡与绚烂的对立统一中探讨气韵的余音余味义,而是将气韵指向形神之辨语境下的传神。 对此,元代杨维祯《图绘宝鉴序》认为“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40],其阐释得极为准确。
四、刘勰《文心雕龙》“韵”论的哲源及内涵
刘勰《文心雕龙》列有《声律》篇,专门探讨文学声韵问题,该书其他篇章也不乏论“韵”的观点。 刘勰论“韵”是基于儒家的“中和”学说。 从宏观上来看,《文心雕龙》反映的主要是刘勰的儒家思想;从微观上来看,对于声韵问题,刘勰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折之中和”(《章句》),如转韵要在缓与急之间折中;他界定“异音相从”的“和”及“同声相应”的“韵”,也都呼应着儒家倡导的和谐之美。 刘勰指出:“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 音以律文,其可忽哉!”(《声律》)他以儒家礼仪中佩玉和步的和谐节奏,强调和谐的声韵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儒家“中和”学说指导下得出的结论。
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 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的范围。 以下先列《文心雕龙》原文,再试作分析。
(1)“泉石激韵,和若球锽。 ”(《原道》)
(2)“孝武爱文,《柏梁》列韵。 ”(《明诗》)
(3)“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 ”(《明诗》)
(4)“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裝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 ”(《诠赋》)
(5)“彦伯梗概,情韵不匮。 ”(《诠赋》)
(6)“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 ”(《颂赞》)
(7)“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诔碑》)
(8)“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講。 ”(《哀吊》)
(9)“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 ”(《哀吊》)
(10)“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封禅》)
(11)“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 ”(《体性》)
(12)“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 ”(《声律》)
(13)“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 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声律》)
(14)“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 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 ”(《声律》)
(15)“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 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章句》)
(16)“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丽辞》)
(17)“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总术》)
(18)“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 ”(《总术》)
(19)“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 ”(《时序》)
(20)“喈喈逐黄鸟之声,莭莭学草虫之韵。”(《物色》)
(21)“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 ”(《才略》)
上述文献中,刘勰所言之“韵”有3 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韵”指自然界的声韵。 “泉石激韵”(《原道》)与“草虫之韵”(《物色》)即是其例。
第二种含义,“韵”指文学的声韵。 例如“《柏梁》列韵”(《明诗》)、“联句共韵”(《明诗》)、“盘桓乎数韵之辞”(《颂赞》)、“辞韵沈膇”(《哀吊》)、“华过韵缓”(《哀吊》)、“辑韵成颂”(《封禅》)、“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总术》)、“穷初终之韵”(《总术》)以及《声律》篇中“叠韵离句而必睽”、“风力穷于和韵”、“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作韵甚易”、“诗人综韵”、“讹韵实繁”、“张华论韵”、“切韵之动”,《章句》篇中“改韵从调”、“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嫌于积韵”、“观彼制韵”、“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含义明确,均是就文学声韵而言。
这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有4 处。 一是“彦伯梗概,情韵不匮”(《诠赋》),“情韵”作何解呢?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指出:
《世说·文学》篇:“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 时王繤在坐云:‘恨少一字,得写字足韵当佳。 ’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 注:“《晋阳秋》曰:宏尝与王繤、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续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云,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 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 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 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即所谓“情韵不匮”也[28](P303-304)。
以上可见刘勰评袁宏《北征赋》“情韵不匮”是就袁宏续写此赋以足其韵而言,因此不匮之情韵并非“情之韵”而是“情与韵”,这个“韵”依然是声韵之韵。
二是“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体性》)以及“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韵流”“流韵”作何解?潘岳行为轻薄而才思机敏,“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辞锋显露(‘锋发’),音韵流畅(‘韵流’)”[28](P1030)。 可见“韵流”之“韵”指的就是声韵。 对于“流韵绮靡”之“韵”,学界有争议,或以情韵释之,或以风韵释之,或以韵味释之,或以声韵释之。 实际上,“韵流”“流韵”同义,均指称声韵的流畅。
三是“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诔碑》),“韵长”作何解?对“韵长”之“韵”,学界亦有争议,有释为篇幅者,有释为情韵者,有释为韵语者。若要辨析其义,应考察柳下惠妻为其夫所作的诔文。该诔文载于《列女传》卷二,其文曰: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 屈柔从俗,不强察兮。 蒙耻救民,德弥大兮。 虽遇三黜,终不蔽兮。 恺悌君子,永能厉兮。 嗟乎惜哉,乃下世兮。 庶几遐年,今遂逝兮。 呜呼哀哉,神魂泄兮。 夫子之谥,宜为惠兮[41]。
柳下惠妻所作的诔文当然情意深长,刘勰评其“辞哀”已示此义,以“韵长”反复揭示此义似无必要。 观此赋开篇以“不伐兮”“不竭兮”“无害兮”3 个兮字,一唱三叹,取其同声相应之义,具有延长音节的效果,兼以衬托哀情。 此处“韵长”当与《体性》“锋发而韵流”之韵流的含义相近,指的是声韵绵长。
四是“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逸韵”作何解?刘勰以偶意对丽句,以逸韵对深采,可见逸韵是就辞韵而言,因而“此逸韵指高雅的音韵”[42]。
第三种含义,“韵”代指有韵的作品。 “结言短韵”(《诠赋》)、“季鹰辨切于短韵”(《才略》)中的短韵,均是以用韵的数量来计量作品的长短,故短韵指称短篇。
由上可知,《文心雕龙》中的“韵”论依然是“即声言韵”,尽管学界对其中个别“韵”字的诠释存在异议,但《文心雕龙》整体上并没有像谢赫在画论中那样“舍声言韵”,也未探讨“韵”的形上内涵。 更进而言之,南朝文论家以“韵”论文学者颇多,但“舍声言韵”者极为罕见。 “韵”在钟嵘《诗品》中凡五见,也均为声韵之韵。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文章“放言落纸,气韵天成”[43],已用“气韵”二字,看似与谢赫同调,实则不然,其说并未脱离声韵而言,其中至少包含声韵之天成。
五、《古画品录》与《文心雕龙》“韵”论分野之原因
“韵”在南朝画论与文论中存在“舍声”与“即声”的分野,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
第一,绘画与文学作为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区别,导致它们对于“舍声”与“即声”有着不同取向。 绘画以传神写照为宗旨,本就无法表现流动的声音,也就无法“即声言韵”。 画论家借用人物品评“舍声言韵”的成果,在艺术领域进一步开拓“韵”的形上内涵。 谢赫《古画品录》中的“韵”论带有明显的超形取神的倾向,与两晋人物品评中“韵”的形外之美的含义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从人物品评之“韵”发展到画论之“韵”,这一线索是相当明晰的。文学是时间艺术,不仅能描述声音之美,其本身在产生之初就是与乐、舞共生,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故而文论家探索文学的声音之美是必然的趋势。
第二,讨论声韵是魏晋以来形成的新风尚,“即声言韵”是南朝文论家们的主动追求。 三国魏李登《声类》、孙炎《尔雅音义》、西晋吕静《韵集》的推出,使魏晋时期形成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 南朝文论家又有新发展,齐周颙作《四声切韵》,梁沈约撰《四声谱》,发明“四声论”并用于永明体诗歌创作,由此形成南朝文人探索文学音乐性的热潮。 讲究调协声韵的骈体文及永明体诗歌的兴盛构成了南朝文学重视形式美的基本面相,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韵”论正是对这一声韵研讨风尚的呼应。
第三,虽然“韵”在晋人那里通过“舍声”发展出了新义,谢赫此前在画论领域也使用了这一新义,但是刘勰对词语新义心存抵触,他固守“韵”的本义。 在《文心雕龙·指瑕》中,刘勰批评“赏”作为欣赏的新生义,而固守“赏”作为赏赐的本义;对于“韵”,他也坚持使用其“音和”的本义。 刘勰未在理论上跟进“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
整体来看,南朝文学“韵”论受儒家思想影响,“即言”而胶滞于形下。 这与南朝绘画“韵”论受魏晋玄学影响“舍言”而走向形上之途完全不同。 魏晋玄学在思想境界及行为方式上对魏晋士人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其落实到文学上,以玄言诗的面貌呈现时,就受到南朝文论家的激烈批评,导致玄言诗背负了淡乎寡味、率多浮浅的骂名。 诗至东晋郭璞,一变玄言平淡之体,刘勰以其诗“艳逸”而称之足冠中兴,钟嵘则以其诗“彪炳可玩”而许为中兴第一。 这些“艳逸”“彪炳”的赞语足以反映南朝文论家的审美趣味。
余论
南朝之后,唐代文学在诗境及诗艺上有进一步开拓,时人多以“风韵”“逸韵”论诗,可见“韵”作为人物品评术语向文论的迁移,然只言片语,失之零散,不成系统。 唐代司空图讲“韵外之致”[44],虽然指向了余音余味,但是“韵”本身并不指余音余味,否则就不会有“韵外”的说法。 中国文论对“韵”之形上性的探讨在北宋才有实质性突破。 北宋李廌认为:“如朱弦之有余音、太羹之有遗味者,韵也”[45]。李廌将“韵”的美学蕴涵指向了有余音余味的平淡美。 北宋后期范温《潜溪诗眼》指出:“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 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2](P373)。 是为确论。 所谓“近代先达”指的就是李廌等人。 范温进而提出“有余意之谓韵”[2](P373),“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2](P372),以“韵”会通艺论与文论,建构出“韵者,美之极”[2](P372)的审美理想,从而实现了文学与艺术之“韵”的意界融合。
上文对“韵”内涵建构的历史性考察以及对“韵”之审美分野现象的探讨,旨在揭示“韵”范畴的复杂面貌。 中国美学范畴的涵义常常变化不居,或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或因语境而异,或因文艺门类而异,古人对范畴又往往用而不释,这就造成对它的阐释困境。 有人认为翻过文字、文献、语境三座大山,就能求得对范畴的会通性理解。 但是,这种翻山而出的结论未必可靠,因为“会通”的执念已成为研究的前设,那么但凡遇到不通之处,难免强通、横通,范畴的真义反被遮蔽。 就“韵”范畴而言,学界对它的研究可谓多矣,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也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诸如过于相信“韵”跨越时空的统一性内涵,对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以及“韵”在画论与文论中的审美分野缺乏认知,这必然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 虽然“韵”范畴作为字词存在时,它的基本释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进入哲学及文艺美学领域,其含义亦有一定的沿袭性,但是不能由此忽视“韵”范畴语义的历史性及语用的差异性。 美学范畴研究的难点一定程度上来说,不在于探求范畴内涵之同,而在于追问其内涵之异。 唯有从范畴文献出发,溯其源流,剖其肌理,避开统一性的思维陷阱,方能在学理上对范畴研究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