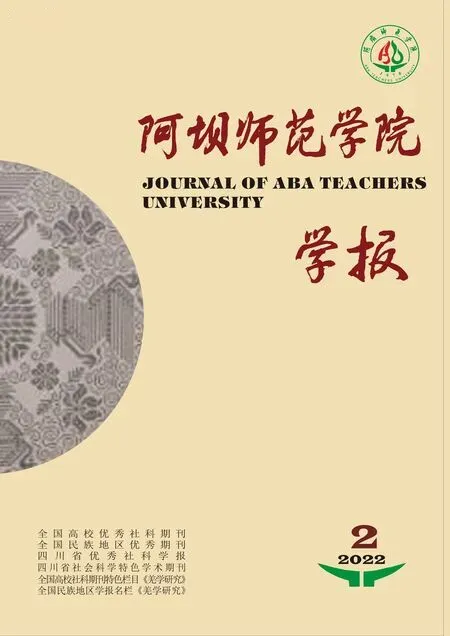“羌戏”的基本类型及特征论要
李祥林
“羌戏”是对羌族戏剧的简称。目前,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是“羌戏”的分布地带。关于“羌戏”的存在及身份等问题,学界多年来有所忽视(1)当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分册、《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等皆无涉及“羌戏”的信息。有鉴于此,上个世纪90 年代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同仁编纂《四川傩戏志》即意在补其不足,收入了“释比戏”等,该书于2004 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笔者为此撰写过系列论文并有主持结项的“羌戏”研究专题(2)参见李祥林的相关论文:释比·羌戏·文化遗产[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8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舞台艺术.2010,(1);羌族戏剧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保护[A]//冯骥才.羌区何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建言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川西北尔玛人祭神驱邪的民间仪式戏剧[J].民族艺术研究.2012,(5); 羌族民间仪式戏剧的活态存在——来自理县蒲溪尔玛人村寨的田野报告[A]//刘祯.祭祀与戏剧集——中国傩戏学研究会30年论文选.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等等。这方面研究,有李祥林主持并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结项时间为2021 年3 月。,可供读者参考。有剧本搜集整理,也有活态演出,加上学界有心人士的研究成果,是完全可以回答“有无羌戏”的问题。那么,“羌戏”有哪些类型? “羌戏”又有什么特征? 结合川西北羌族地区实际,针对羌族戏剧存在现状,从宏观角度对之可作如下把握: “羌戏”主要有释比戏和花灯戏两大类型,“羌戏”的存在及演出以民间性和仪式性为两大基本特征。本文就这些问题作扼要论述。
国内首部《羌族文学史》初版于1994 年,再版于2009 年,其中涉及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虽不见有关羌族戏剧文学的篇章,但在介绍当代羌族小说家时提及,“1998 年,叶星光整理编写出第一部羌族神话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3)李明.羌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380.。木姐珠神话涉及尔玛人的先祖崇拜,该剧源于羌族神话传说,脚本是20 世纪80 年代搜集整理的。木姐珠是天神木比塔的三女儿,也是川西北羌民世代尊奉的女祖,“羌人唱古歌,常常提到三公主;今天我来唱,起头先唱木姐珠”(4)《中国歌谣集成·四川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四川卷[M].北京:中国ISBN 中心,2004:1013.。2010 年6 月,“首届羌族文学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会上,遇见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叶星光,我们彼此以书相赠。笔者询问当年搜集整理《木姐珠剪纸救百兽》的情况,他说这是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期深入理县偏远山寨所得,该“羌戏”曾在汶、理等地流传,但今人已知之甚少。这位羌族作家是理县薛城人,他在前述《羌戏考》中介绍过此剧并以该剧最后一场作为文末附录,其小说《神山·神树·神林》中也曾提及该神话剧的某些情节。2013 年3 月中旬,去理县蒲溪沟顶端的休溪羌寨参加当地的“夬儒节”,我俩再次相遇,“这次他告诉我,《木姐珠剪纸救百兽》就是当年在蒲溪乡奎寨搜集的,他们家在该寨子有亲戚。那时,他从寨子老人口中录了音,回家整理出来后给一位搞戏剧的朋友看,后者说‘这不就是羌戏么’……”(5)李祥林.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M].成都:巴蜀书社,2014:175.这出“羌戏”的全本,后来在于一、罗永康等合著的《羌族释比文化探秘》(2003 年)、集群体之力编纂的《羌族释比经典》(2008 年)中均有见,后者明确将其列入“释比戏篇”,有羌语注音和汉文译意。在理县蒲溪,说到“羌戏”不能不提到今天仍由村寨民众用羌语活态演出的《刮蒲日》。笔者曾多次在高山羌寨观看这出活态搬演在民间的“寨子戏”,并且撰写了专文《夬儒节上看羌戏》(文中有笔者根据现场演出本校订后的剧本),收入拙著《城镇村寨和民俗符号——羌文化走访笔记》(2014 年)中。见于高山羌寨的这出戏,有朋友告诉笔者,其恢复曾多得已故释比王定湘指点,此外,还有参与该剧演出者讲述自己“跟村里老释比王久清学习释比戏”的经历,说过去寨子里搬演此戏意在“教化”,也就是“惩恶扬善”,通常是在春节或夬儒节期间演出;1958 年受时局影响“就没得人演了”,1991 年有日本调查者来了解夬儒节活动,村里恢复此戏,释比王久清“那个时候好在他还在,组织了一次”,而如村民所言,“我们演释比戏就是他口头给我们传授的”(6)《传承者说——羌族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编写组.传承者说——羌族文化传承人口述史:上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179—180.讲述者饶富民是《刮浦日》中会首扮演者,1951 年出生,理县蒲溪乡蒲溪村人,羌族。蒲溪村在当地人口中习惯称“大蒲溪”。王九清是大蒲溪人,他精通上、中、下三坛经,是知名度甚高的释比; 其子王定湘(或写作“王定相”“王定襄”)生于1927 年,从小随父亲学做法事,也是释比,他对释比戏《刮浦日》的恢复也出力甚多。。2015 年韩国知名的EBS(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前往蒲溪拍摄之;2018 年3 月,笔者应邀赴韩国讲学,在延世大学以“川西北羌族文化研究”为题做讲座时也曾介绍这出“羌戏”。2018 年11 月,在成都与阿坝区域文化交流之藏羌戏曲进高校展演活动中,由村民演出的该戏还亮相在西南民族大学的舞台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兴起,对“羌戏”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受到地方上重视,如被列入理县第三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释比戏传承人,就有韩富保、饶富民、韩水云、杨树林、王相全、杨德林、韩双保、王友顺8 人。既有戏又有人,“羌戏”活态存在着。
“羌戏”以释比戏为主,笔者对此屡有文章论述,在所承担的“羌戏”研究课题中又有更详细探讨,兹不赘言;除此以外,也包括在地化或曰“羌族化”的花灯戏(7)载歌载舞的花灯戏属于民间小戏范畴,2017 年启动并将历时八年完成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是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其中有与“神话”“史诗”“故事”“说唱”等并立的作为大类的“小戏”,大类之下,又将小戏具体划分为9 类,其中有与“秧歌戏”“采茶戏”“道情戏”等并列的“花灯戏”。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四川卷》编纂工作已正式启动,我们将羌族地区的花灯戏明确列为搜集、采录对象。。目前,有的文章或书籍是把“羌戏”视为一个剧种而以之为羌族释比戏的代称,如《四川傩戏志》称释比戏“习称羌戏”便是这样。释比戏是植根于本民族土壤的戏剧,以之为羌族民间戏剧的代表这没问题;至于是否将“羌戏”作为剧种概念而仅仅用于指释比戏,这问题有待更深入探讨。从现有文献看,迄今更多见的是对“羌戏”概念的使用没有停留在此。比如,有介绍羌区文化资源的文章云: “羌戏。羌戏是羌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民族戏剧。羌戏的内容反映民族史事、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良好愿望和美好追求。现在著名的剧目有《斗旱魃》《木姐剪纸救百兽》《众母舅求雨》等。有书面剧本的不多,绝大多数为代代口传。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措施,对羌戏进行抢救、挖掘、整理,并使其有了新的发展。此外,羌族还有释比公戏、武士戏、花灯戏、马马杰、打围鼓等。”(8)四川省社科院旅游研究课题组.激活羌族文化 推进四川羌区文化旅游发展[J].西羌文化.2007,(1).这段文字并非出自戏剧研究者之手,是参照多种资料后形成的综合性文字,因此表述上不那么严密,如“释比公戏”当是“释比戏”之误、“马马杰”应为“马马灯”;至于“打围鼓”主要是跟传入羌族地区的川剧有关,说它是羌区存在的民艺之一可以,直接将其归为羌族戏剧行列则不合适。不管怎么说,此处对“羌戏”的述介是广义的。前述《羌戏考》一文,提及的剧目既有《龚男子招亲》又有《木姐珠剪纸救百兽》,前者是汶川雁门的花灯戏而后者被《羌族释比经典》明确列入“释比戏篇”。作为“民族知识丛书”之一的《羌族》在肯定“羌戏这古老的剧种早已在民间流行”的同时,也指出: “羌戏的剧目,目前已保留不多。据近人调查,有神秘而古老的‘端公戏’,有金戈铁马、英勇悲壮的‘武士戏’,也有喜庆欢快的‘花灯戏’。演唱时还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体系。”(9)周锡银,刘志荣.羌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118 -119.此处所言“端公戏”,实指“释比戏”,因“端公”在此是对羌族释比的汉语俗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参加某次全省戏剧研讨会,遇见羌族友人罗永康,我们谈起羌戏,兴致甚高。会后,时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创作室主任的他给笔者寄来了文章《开发民族戏剧丰富巴蜀戏剧舞台》,其中述及羌族戏剧的剧目时写道:“从现在搜集到‘释比戏’‘花灯戏’的剧目中除了大量反映羌族神灵、英雄、历史的故事如《木吉珠斗安珠》《木吉珠剪纸救百兽》外,还有不少从汉地移植的剧目,如《关公保皇娘》《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钟馗嫁妹》等等。”(10)“罗永康(1940— ),男,羌族。四川茂县人。副研究馆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阿坝州文化局创作室主任、《阿坝文苑》《阿坝文化报》常务副主编。四川省傩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四川省傩戏志编委会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参加‘四川省傩戏志’的编撰工作,主写《嘉绒藏戏》和羌族《释比戏》部分。”(参见:《羌族词典》编委会.羌族词典[M].成都:巴蜀书社,2004:507),2000 年3 月,“编辑部召开《四川傩戏志》初稿讨论会。主编严福昌,副主编于一、余光寿、唐滨、秦德宣,编辑部副主任李祥林、张松琴及各地代表戴德源、姚光普、罗永康等参加会议”。这里,也是并举释比戏和花灯戏来叙述“羌戏”的。2019 年11 月,笔者应邀到汶川绵虒给阿坝州举办的羌族口传史诗传习班做非遗保护讲座,羌族友人余永清以新著《秘境羌人谷》相赠,他在书中亦回忆家乡龙溪往日过春节,从正月初五到十五,“阿尔村巴夺寨的村民们都要组织耍狮子和唱花灯戏”,舞狮唱戏队伍会挨家挨户拜年,“到主家门口起唱花灯戏”,从户外到室内舞起狮子,主家要准备糖果、酒席和“喜封钱”犒劳之(11)余永清,董耀华.秘境羌人谷[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140 -141.2019 年12 月14 日,永清通过微信以照片发来他抄录在笔记本上的《十二杯酒歌》,其中唱道:“一杯酒正月正,我问情郎几时生;情郎生在元宵会,元宵会上闹花灯。”他告诉笔者:“这是我十多年前(从)龙溪乡马房寨杨开明老人那儿收集的,在春节时耍狮出灯唱的‘十二杯酒歌’,今天才从一本笔记中翻了出来。”。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有别于土生土长的释比戏,花灯戏是从汉区传来而逐渐“羌族化”后成为尔玛村寨的民间戏剧的(12)类似例子在多民族的中国并不鲜见。比如,傩文化在中华大地尤其是中原地区由来古老,也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种种带有地方民族色彩的“在地化”种类。近年来笔者屡去贵州道真,得以观看当地的“仡佬族傩戏”,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不因为它在来源、剧目、表演等方面跟汉区多有关联而去掉了“仡佬族”这族群定位的冠名。又如,岷江上游松潘县是回、藏、羌、汉多民族共居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根据调查所得的客观事实,在“全省民族民间舞蹈调查表”之阿坝州部分也不含糊地标示有“[回族]花灯”(参见: 吴晓邦.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M].北京:中国ISBN 中心,1993:30.)指明此在地化的花灯艺术的族群属性。有鉴于此,对于在地化的羌区花灯戏,也务必要客观地加以认识和把握。。目前,从市州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13)2006 年9 月,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布的首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戏曲类项目有二:一是羌族灯戏,一是释比戏,均由茂县申报。,既有“羌族释比戏”也有“羌族花灯戏”,二者都是“羌戏”家族的成员。
“羌戏”的民间性。有别于剧场上舞台的高雅、精英、主流的或曰文人的、官方的、学院派式的纯艺术,无论羌族释比戏还是羌族花灯戏都存活在川西北尔玛村寨的民俗土壤中,是跟尔玛人的民俗生活密切关联的民众艺术,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羌戏”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属于非官方、非文人化、非学院派式的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民俗学领域从来都为民间戏曲留有一席之地。”(14)李祥林.中国戏曲的多维审视和当代思考[M].成都:巴蜀书社,2020:243.按照民俗学定义,“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就其根本言,“民间艺术是各种民俗活动的形象载体,其本身便是复杂纷纭的民俗事象”(1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27.。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的民间文学也把“民间小戏”纳入其中,如当下正在推进的国家重点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便是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民间文学理论等分类的(16)贾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全面启动[EB/OL].[2018 - 01 - 31]. http: //www. cflac. org. cn/wlyw/201801/t20180131_395021.html.。在此动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并预计实施八年的调查、编辑和出版工作中,笔者也应邀担任“民间小戏”专家组成员(17)刘洁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民间小戏”专家组成立[EB/OL].[2018 -06 -20].https: //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 NewsID=17805.。关于民间小戏的形成和发展,有书籍作了三方面归纳:在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民间巫觋、祭祀活动也直接影响着民间小戏的发展(18)李慧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279 -282.。拙文《从民间文学看民间小戏》,也论及小戏的“口头性”“民众性”和“族群性”(19)李祥林.从民间文学看民间小戏[J].文艺报,2019,(6).。“在华夏,以‘二小’(小生、小旦或小旦、小丑)或‘三小’(小生、小旦、小丑)见长的民间戏曲覆盖面广,遍及全国90%以上的乡村城镇,它们扎根民众生活,与各地的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和文化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深厚的地方传统。”(20)李祥林.中国戏曲的多维审视和当代思考[M].成都:巴蜀书社,2010:243.学界又有“民俗艺术”的说法,既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态,又指民间艺术中能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就其存在和功能言,“‘民俗艺术’往往作为民俗传统的象征符号和民俗生活化的原生艺术,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社会交际、衣食住行、消遣娱乐等方面广泛应用”(21)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诸如此类论述,有助于我们立足田野、深入实际去认识和把握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川西北“羌戏”。在笔者看来,对于“羌戏”之民间性的把握,可以从观演主体、剧目内容、表演场景、演出功用等方面切入。在尔玛人村寨中,释比作为释比戏的表演主体,他不仅不是专业艺术剧团或经过专业艺术训练的专业演员,甚至他作为民间宗教人士也不是专职的; 戴上法帽、跳起皮鼓、唱起经文他是神圣的法师,走出仪式场景、脱下法师服装、回到日常生活他是农民。对于生活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地带的羌民来说,对雨水的祈求是半牧半耕的他们生活中的大事。汶川等地民间流传的仪式剧《斗旱魃》即跟当地人的求雨活动有关,演出前,由释比挑选一人扮作旱魃,藏匿于山林中; 戏开始,释比主持祈雨仪式,告诉大家天旱是因旱魃作祟,于是在他指引下,村寨男女老少鸣锣执棍,上山捉拿旱魃。在此,村民就是演员,演员就是村民,谁能区分彼此? 至于理县蒲溪“夬儒节”上演出《刮浦日》,其本身便是当地村寨在节日期间“宣讲‘惩恶扬善’的乡规民约”的传统习俗,所谓“每逢重要的节日或集会,总是能够看到数百人聚集在祭祀场地观看‘释比戏’上演的盛景”(22)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羌族“释比戏”》,理县蒲溪文化中心服务站制作,2013 年1 月。。归根结底,羌族戏剧生长并存活在尔玛人社会土壤中,跟其传统思想、族群伦理、民俗信仰、村寨教育、民众娱乐等有密切联系。此外,作为地处汉藏之间的民族,羌人跟周边民族尤其是汉族有悠久密切的交往,其民间演剧文化中又凝聚、体现出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的积极因素,是我们借以了解多民族中华文化的生动个案。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尊重研究对象,笔者研究“羌戏”并非将其从生活中抽取出来进行所谓纯戏剧学或纯艺术学考察(尽管这不应忽视),而是立足人类学立场,将其作为羌人的族群生活与民俗事象加以审视,也就是结合羌人的生活、传统、习俗,将“羌戏”作为族群文化遗产和地方民俗艺术进行不脱离其生活场域的整体研究。
“羌戏”的仪式性。作为民间戏剧,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跟民间信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仪式和戏剧,有人类学家指出: “仪式可以被看做表演,它包括观众和演员两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仪式亦可谓是一种表演或戏剧,“一个表演究竟是归属于仪式,还是归属于戏剧,有赖于(按照谢克纳的说法)它的背景和功能。在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一端是‘功效’(能够产生转变的效果),另一端是‘娱乐’。假如一个表演的目的在于功效,那么它就是仪式。假如它的目的在于娱乐,那么它就是戏剧……”(23)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3、182.顾名思义,“释比戏”是以“释比”命名的,释比是羌族民间宗教人士,也是释比戏表演和组织的核心人物。“释比熟知本民族社会历史与神话传说、主持祭山请神祀祖的重大仪式、进行逐祟禳灾治病的民俗活动,‘祈神佑羌’的他们实质上是羌族文化极重要的掌握者和传承者,从他们口中所传递的精神文化信息对羌人族群有重大影响,他们在羌民社会中占有不可取代地位并享有崇高威望,人们生产生活中每逢大事都要请他们主持唱经做法事。”作为口述传统,释比用羌语演唱的经文按照神事、人事、鬼事分为上、中、下三坛,达数十部之多(如祭祀歌、喜庆歌、劳动歌、丧事歌等等),其内容莫不跟羌人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等密切相关。释比戏作为跟仪式活动密切相关的民间戏剧,即由此衍化而来。“在原始宗教层面上,释比是仪式主持者;在民间艺术层面上,释比是戏剧表演者”。此外,“就其性质和功能看,有的剧目从神话传说演化而来,在释比主持相关仪式中或仪式后演出,娱神的同时有更明显的娱人色彩,如《羌戈大战》《木姐珠与斗安珠》等; 有的剧目即是祀神驱鬼仪式本身,在此傩仪和演戏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汶川一带流传的《斗旱魃》”,而“这种不乏狂欢色彩的群体行为,在仪式层面即是弗雷泽于《金枝》中多有讲述的‘公众驱邪’,从中可以看到戏剧性扮演与宗教性仪式的合二为一,也可以看到村寨百姓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重合,这种奇妙的双重性正是民间演剧特点所在”(24)关于释比及释比戏,可参阅李祥林《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文化研究》第八章“释比名实及生存现状”,第十一章“释比诵经与仪式戏剧”,李祥林.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搬演在高山羌寨集体祭祀仪式上的“羌戏”《刮浦日》,同样是在教化村民和祛除邪祟中呈现其功用的。归根结底,由释比担纲的释比戏属于民间仪式戏剧,撇开仪式性无从谈论释比戏。至于羌族花灯戏,其作为民俗艺术除了有愉悦大众的审美功能,还有替村寨替人家祛邪求吉的仪式功能,“花灯演出时间,通常是在农历正月初一出灯,至二月初收灯,即主要在正月里唱灯跳灯,求吉祥逐邪祟,人神共乐”(25)李祥林.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唱灯跳灯及其多元观照[J].民族艺术研究,2010,(6).。在北川,许家湾花灯戏便是“平时娱乐性为主,正月祭祀全寨每家扫瘟疫为主”(26)本方案编写组.绵阳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实施方案[Z].2010:17.,用羌族民间艺人的话来说,“我们这个保平安,保证家家清净,户户平安……添寿添福,百病消除,起到哪保到哪”(27)《传承者说——羌族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编写组.传承者说——羌族文化传承人口述史:上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171.;又据羌地马马灯艺人讲,“马马灯是大致起源于清光绪年间,当地土司在此建有戏台……后来地方闹瘟死了很多人,算命先生说灯要继续耍起来才行,这样马马灯就开始成为了此地扫瘟神活动”(28)梁佳佳.新春活动之白什马马灯[EB/OL].[2017 -02 -15]. http: //www. sohu. com/a/126348988_534763. 讲述人李玉平,男,84 岁,北川羌族自治县白什羌族藏族乡鱼背村村民。。在此,羌族民间灯艺表演同时是祈福禳灾活动,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讲的“消灾仪式”。
文化人类学关注“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根据学界定义,其“指文化中非书面的故事、信仰和习俗”,而“口头艺术是包括叙事、戏剧、诗歌、咒语、谚语、谜语和文字游戏”(29)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49.,有宽泛的涵盖面。对于有语言无文字的尔玛人来说(30)羌族是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如汉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其羌语读音用汉字标注就是“阿、倪、星、止、尾、主、喜、铠、顾”;又如在羌语中,成都读音为“夷读”,衙门读音为“卦皆”,手艺人读音为“离日米”,雁门(乡)读音为“普子格”(民国《汶川县志·风俗·附语言》),等等。如今学界又采用国际音标为羌语注音,如《羌族释比经典》即采用此法。作为族群名称,见于甲骨文的“羌”实际上是来自汉语的他称,羌族自称的汉字标音是“尔玛”,又写作“日麦”等。,存活在民间并传承于口头的“羌戏”(无论羌族释比戏还是羌族花灯戏)正是他们共同创造、世代传承并集体享用的“口头传统”。既然如此,对于“羌戏”的考察和研究,那种单一的、狭义的、正统的、纯艺术的乃至刻板化的“戏剧”观念是不够用的,因为其涉及艺术、习俗、信仰、教化以及民间心理、乡土传统、地方知识等多方面,需要我们在艺术学研究、民俗学考察、人类学透视等多学科整合视野中加以融会贯通地把握。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羌戏,与其说是艺术学意义上的文艺样式,毋宁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羌族民俗生活及民俗事象本身,它存活在尔玛人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中,伴随着民俗信仰,寄寓着民俗心理,适用于民俗场景,体现出民俗功用。对之的研究,无论着眼历史还是现实,尤其需要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眼光、理念及方法。大致说来,“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立足羌族的民俗生活,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羌戏”这不可多得的民族文化遗产做整体性考察、梳理和研究,包括: 川西北羌族戏剧及存在现实调研、作为民俗生活的羌地民间演剧考察、作为民俗艺术的“羌戏”形态梳理和辨析、从经文说唱到戏剧文学的演进透视、民间技艺展示与民俗表演形态解析、民艺视野中服装道具及文化内涵考察,以及羌族村寨的口头遗产及活态呈现、族群互动中的多元文化和相邻艺术,等等。其价值和意义在于: 其一,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看,作为整体考察民间“羌戏”这份口头遗产和民俗艺术,对于把握古老的羌族文化和研究多民族中国的族群互动及文化交融有某种补充意义;其二,从文化学及戏剧学看,作为从民俗生活角度研究民间“羌戏”遗产的个案,对于考察中国本土戏剧的民间发生及存在、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三,着眼地方和现实,对于当今中国西部藏羌彝走廊上羌族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文化发展建设有可供借鉴处。
大而言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中国有形态丰富的戏剧文化遗产。作为本土戏剧的组成部分,汉以外民族的戏剧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中华戏剧文化有独特价值。小而言之,研究“羌戏”,既是尊重羌区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也是为了羌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归根结底,不管是作为民俗艺术还是作为村寨艺术乃至其他,羌族戏剧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羌族戏剧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决定了它是我们研究中华戏剧共同体所不可缺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