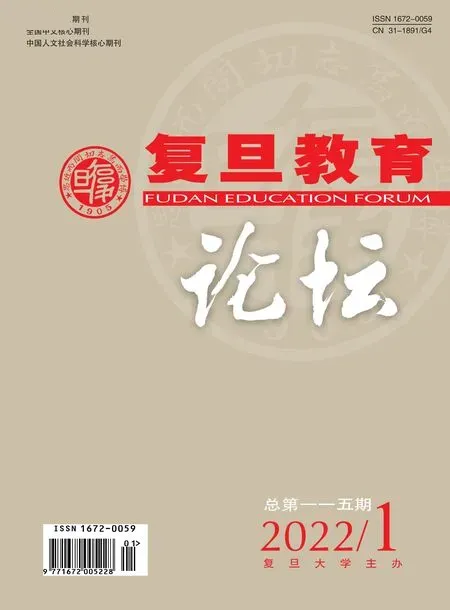家与世代:培养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陆 一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个新兴的高教研究议题,通常认为这类大学生实现了学历的突破,具备了向上流动的初步条件,但他们又在大学里属于弱势群体,存在一些显性或隐性的困境。
在上几代人都拥有了大众高等教育的美国,仅存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相对劣势更加凸显。学生调查是美国高教研究的重点领域,有大量研究依托大数据统计预测学业成就,发现存在各式各样的优势或弱势群体,揭示教育场域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其中首先被关注到的是性别、种族、经济条件、生活地域等直观的个人背景变量。随着相关成果的饱和,将父母都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未获得高教学历的大学生界定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这类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沿。比起父母拥有高学历的同学,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意味着文化资本亏缺,是大学里的少数,他们还承担着阶层跃升的压力,较不容易取得成功。如果他们终究不能借助大学教育克服出身不利,对个人而言无法实现人生抱负,对社会和教育体制而言,会使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落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有着共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不过,当我们仔细地回顾自己的生活经验,观察身边大学生的真实状态,上述思路似乎还缺点什么。这些实证模型设定都是个体本位的,家庭只是个人拥有的一种自然禀赋,父母长辈提供的教养被化约成个人享有的“文化资本”。正如家庭经济条件一样,如果子女对此命运的馈赠并不负有什么义务,那么不均等的天赋就会产生结构性不公平。最后子女所取得的学业成绩和人生成就也同样被个人化地计算。欧美的青年上了大学成人之后与家庭联系变得松散,父母的教养至此终止。
中国的亲子关系则包涵丰富的人伦属性和社会义务。经典有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会不分阶层、不论学历地支持子女上大学。子女上了大学之后,父母也不会突然离场。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出了大学生,就会被寄望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中国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体会到更多亲情与恩情的纽带,光荣与负担的纠葛,还有“报”与“孝”的文化本能与社会期待。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正加速促进学生对现代价值观念的领受,大学生更习惯于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和工具理性的得失计算。可见,中国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文化处境比欧美复杂得多。
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显示,通过良好的学业实现向上流动,既是所有现代社会的理想追求,也是很难逾越现实难题。在个人奋斗和国家教育体制之间,还有家庭。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巨大难题恰如“愚公移山”的志愿,如果一代人难以实现,就甘愿投入世代的努力。“个体的成功有时候并不只是靠个人,而是通过一代代人积累而达成梦想。在这样的梦想背后,是‘家’所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生存结构。”不同于两希文明,中国传统特别强调个人在家族世代中的作为,依靠家庭繁衍和子子孙孙的信念传承,人得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保持昂扬的生命力。相反,典故中的“智叟”则看似具有启蒙式的精明机智,实际上却虚无孱弱。
诚然,现代中国人还没能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剧烈思想变革与传统情感本能之间找到最适度的“家”的位置,例如父母对子女学业竞争力过度苛求、在高等教育阶段持续干预,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在研究中不假思索地采取个人主义的假设,任凭模型设计遮蔽经验,削足适履。我们之所以重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这一选题,不仅因为它关注教育中的弱势,更因为它将现代的个人与家庭在教育目标中连为一体,启示我们在认识现代家庭的基础上讨论现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