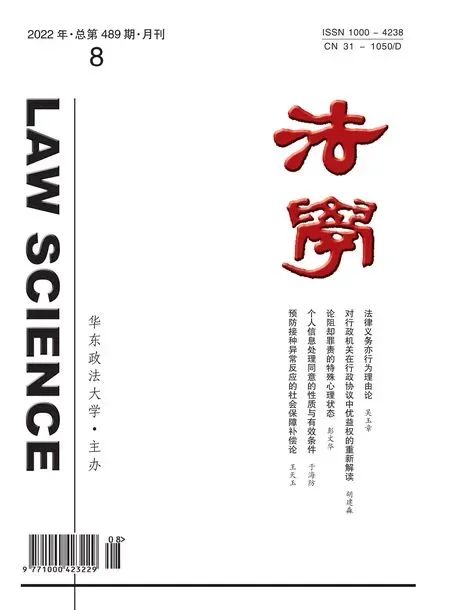借款法上“利息透明”原则之释义与运用
●王吉中
在银行借贷合同中,合同约定的名义利率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呈现借款利息的真实负担。具有相同本金、借期和名义利率的两份借款合同,如果其中一份是年末还本付息,另一份是每月偿还等额本息,则后一份分期借款的真实负担显然更高。〔1〕举例而言,本金50000元、名义年利率9%的一年期还本付息的借款,与本金50000元、名义年利率9%、借期一年但每月偿还等额本息(每月偿还4541.67元,其中利息和本金每月固定不变,分别为375元和4166.67元)的借款,前者的实际年利率为9%,后者的实际年利率约为16.22%。但由于两份借款合同表面上载有相同的名义利率,借款人难免产生“利息幻觉”,认为两笔借款具有相同的利息负担。欲消除此种“利息幻觉”,只能在借款合同中引入一个在金融数学计算上具有“复利”结构的实际利率。但与比较法〔2〕自1975年4月25日欧共体决议(AblEG Nr. C 92)以来,欧洲立法者便屡屡要求各国立法准确计算并披露消费借贷的实际利率。英国《消费借贷法》第60条第1款b项规定,贷款人应使借款人注意到“借款总体费用的数额或数率”。瑞士《消费借贷法》第9条第2款b项、奥地利《消费借贷法》第6条第1款第7项均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披露贷款的“实际利息”。而自2008年4月23日欧盟《消费借贷合同指令》(Richtlinie 2008/48/EG)颁布后,欧盟以及已“脱欧”的英国对消费借贷中的实际利率计算方法和实际利率披露规则已基本达成一致。上通行数十年的立法体例不同,我国相关实证法一直未为贷款人明文引入披露实际利率的义务,司法者亦对利率计算问题不甚敏感,常在判决书中公开使用名义利率计算方法。〔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27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4343号民事判决书。而以营利为目的的贷款人显然也没有主动披露实际利率的动力,这使得大量借款人仍然蒙受“利息幻觉”的困扰。
转机出现在2021年。在上海金融法院同年1月4日审结的“适用《民法典》首案”〔4〕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终103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一审判决情况,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1394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以借贷双方缔结的《贷款合同》和《还款计划表》仅载明名义利率、未披露实际利率为由,判决贷款人向借款人返还多收的利息88万余元。在这则判决中,透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第26条第1款以及《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法院间接地引入了比较法上通行的“利息透明”原则,即贷款人在借款合同中必须向借款人准确地披露借款实际利率。〔5〕Vgl. Reifner/Feldhusen, Handbuch Kreditrecht, 2. Aufl., 2018, S. 352.
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也采取行动回应司法实践。2021年3月12日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要求“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营销和缔约时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2022年3月1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诱导的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不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的行为。然而,中国人民银行在前述公告中指出,“年化利率”既可以“复利”亦即实际利率标准计算,也可以“单利”也即名义利率标准计算。可见,我国目前尚未引入拘束贷款人的“利息透明”原则。这也使得当前有的法院认为贷款机构有义务披露实际利率,〔6〕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2509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4民初37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终12137号民事裁定书。有的则仍然认为其披露名义利率即为已足。〔7〕参见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1)豫0311民初7997号民事判决书。但从长远看,为使借贷市场健康发展,应有必要将司法中的“利息透明”原则上升为法律的拘束性规定。
一、“利息透明”原则的法律基础
“利息透明”原则设定了贷款人向借款人准确披露借款实际利率的义务。关于这一义务的法律基础,可在两个层面予以探讨,一为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形式上的制定法依据,二为法定的计算基础。
(一)正当性与制定法依据
要求贷款人准确披露实际利率是正当的。通过对实际利率的披露,不同还款方式下的借款合同将展现出真正可以相互比较的利息负担,借款人因而能明确自身的真实借款负担,并与市场上其他银行的借款产品进行比较,〔8〕Vgl. Soergel/Hefermehl, 2014, § 138 Rn. 91; MünKomm/Grundmann, 2019, § 246 Rn. 55.这就有助于促进市场透明和竞争,〔9〕Vgl. MünKomm/Grundmann, 2019, § 246 Rn. 55; BeckonlineBGB/Coen, 2021, § 246 Rn. 25.亦有助于利率管制规则(我国《民法典》第680条第1款)的正常运转,确保实现债务人免于“过度负债”(Überverschuldung)〔10〕Vgl. Reifner, Verantwortung bei Kreditvergabe oder im Kredit - Zum Konzept des Entwurfes der Konsumentenkreditrichtlinie,VuR 2006, 121, 125.的规范意旨。因为在揭示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后,真实利息负担不同的借款合同不会因为名义利率相同而被作同等对待,真实利息负担相同但名义利率不同的借款合同亦不会被作不同等对待,这就确保了利率管制的准确性,大大限缩了牟取高利的空间,宪法上“平等原则”的要求同时亦因此得到满足。〔11〕Vgl. Reifner, Zinsberechnung im Recht, AcP 214 (2014), 695, 714 f.
从形式层面看,我国现行法上并无披露实际利率之义务的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仅倡导贷款机构以实际利率标准披露“年化利率”。但参考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的裁判依据可以认为,如涉及与消费者缔结的消费借贷合同,则可以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商家向金融消费者告知金融服务的“价款”“费用”的义务)〔1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规定:“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作为此种披露义务的法律基础;而在格式合同中,相关法律基础似为《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关于提示说明义务之规定。
(二)法定计算基础
在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中,被估算出的案涉借款合同之实际年利率约为20%,但不清楚其计算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尽管有人可能认为,所谓实际利率披露义务的内容实质仅具金融数学性质,可经由“一般生活经验”的管道将其注入司法裁判过程,无须为其设定专门的法律原则。但为维护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与法的安定性原则,法律必须主动介入,透过一种“经济—规范的思考方式”〔13〕Vgl. BeckonlineBGB/Coen, 2021, § 246 Rn. 23; Staudinger/Omlor, 2021, § 246 Rn. 22; Reifner/Feldhusen, Handbuch Kreditrecht, 2. Aufl., 2018, § 19 Rn. 17.,对实际利率的“复利”式计算设定某种限制性框架。
如某借款合同约定的名义年利率为10%,但每半年结算一次(结算利率为5%),那么单位1的资本在半年中就增长了1.05倍,其在一年中的增长便是1.05乘以1.05也即增长了1.1025倍,这实际上相当于一年10.25%的利息。而如果名义年利率10%保持不变,但每月结算一次(结算利率即为10%/12),则以相同方式得出实际年利率为10.47%。如果在同样条件下每日结算一次(结算利率即为10%/365),则得出实际年利率为10.51%。依照同理进行推演,当名义年利率10%以及其他所有条件保持不变时,对资本增长进行结算的最小单位似乎可以无限分割至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结算单位分割得越细,则得出的实际利率就越大。但这种“连续复利”其实最终在数学规律上仍然会受到自然对数的底e(2.71828……,亦称“欧拉数”)的限制,〔14〕参见邓纲、连牧川、张瑞玺:《复利的理性》,载《金融法苑》2015年第1期,第202-203页。当结算单位无限小时,依前述方法得出的实际年利率将无限趋近于10.517%。〔15〕Vgl. BeckonlineBGB/Coen, 2021, § 246 Rn. 61.5 f.
根据前述数学规律可知,在名义利率相同时,不同的利息结算间隔(1年、1月、1日)会导致计算结果出现明显差别。法律必须对此介入,明确利息结算间隔的法定最小单位和换算单位。〔16〕Vgl. Staudinger/Omlor, 2021, § 246 Rn. 46.比较法上多将结算间隔的最小单位限定为“日”,但对换算单位“周”“月”“年”等则多有不同规定。如在德国与英国,为转化欧盟《消费借贷合同指令》附件中的实际利率计算方法,德国《价格陈述法令》第6条之附件与英国《消费借贷(借款总体费用)规定》〔17〕英国《消费借贷(借款总体费用)规定》可参见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10/1011/made,2022年7月5日访问。之附件都规定,利息结算间隔的法定最小单位为“日”;同时,其针对换算单位规定,1年等于365日(闰年为366日)、52周或12个标准月;而如果仅考虑标准月,则每个标准月为30.41666日,不再考虑闰年的差别。
此外,为使利率比较成为可能,前述欧盟法、德国法与英国法均规定仅应计算与披露“实际年利率”。因为某贷款“实际月利率1%”并不必然在数学上意味着“实际年利率12%”。〔18〕Vgl. Seckelmann, „Zins“und „Zinssatz“im Sinne der Sache, BB 1998, 57, 59.
前述法定计算基础既无法从《民法典》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中推导出来,亦不可能以“一般生活经验”为依据,只能以专门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虽在其附件中确立了实际年利率的计算公式,但与瑞士《消费借贷法》附件1〔19〕瑞士《消费借贷法》附件1仅将利息结算单位抽象确定为“年”(Jahren)和“年的份额” (Jahrensbruchteilen)。该法文本可参见https://www.fedlex.admin.ch/eli/cc/2002/593/de,2022年7月6日访问。类似,并未明确利息结算间隔的法定单位。而且从中国人民银行上述公告来看,其所展示的利率计算公式本身似乎并没有拘束力。〔20〕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附件的起始表述是“计算贷款年化利率较为公允的方法是……”,似指该附件仅仅提供参考性公式。这不符合法的安定性要求。故在应然意义上,我国仍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基础建设。不过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相关职能部门一方面可在以条文形式细化实际利率的法定计算规则之后,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发一款功能强大、操作便捷、参数统一的实际利率计算器〔21〕目前许多网站、手机APP提供的实际利率计算器往往在基本参数上存在差异(比如,有的将一年确定为365日,有的仅将一年确定为360日),输入相同的借款条件可能会得出略有不同的计算结果。供公众使用,另一方面仍须加强公开宣传,努力提升社会公众对实际利率的了解和认知。〔22〕Vgl. Seckelmann, „Zins“und „Zinssatz“im Sinne der Sache, BB 1998, 57, 65.
二、“利息透明”原则的体系定位与适用范围
(一)体系定位
“利息透明”原则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披露实际利率,但这是否意味着同时创设了一种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容许贷款人依实际利率主张利息债权?“利息透明”原则意义上的“复利”是否是复利规定的适用对象?此外,“利息透明”原则与合意制度又具有何种关系?这些均涉及“利息透明”原则的体系定位问题。对此,首先需揭示实际利率计算的基本过程。
以本金10000元、名义年利率10%、借期1年且年末还本付息的借款合同为例,如果以实际利率计算借款利息,那么利息就不再是以10000×10%的公式(名义利率)一次性算出。此时,比如说应先假设实际月利率为i,然后进行如下计算:本金自第一天发放给借款人后经过1个月,会产生10000×i的增长;当月月底,借款人持有的金钱总价值就是10000 + 10000×i;再经过1个月,这笔金钱又产生了10000×i +(10000×i)×i的增长,当月月底,借款人手中金钱的总价值就变成了10000 + 10000×i×2 +(10000×i)×i;在如此指数型增长12个月后,借款人手中金钱的总价值应等于其年末还本付息的总额。
前述计算过程展现了实际利率的“复利”结构,但该结构本身原则上仅具经济学〔23〕对利息“复利”结构的探讨涉及大量经济学文献,本文不赘。在此仅提及最经典者,亦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年)基于经济哲学的分析。其认为,在估计财货(如地窖里的酒、母牛)的价值时,还应当考虑财货的“预期将来效用”。参见[奥]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何崑曾、高德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0页。因此,借款利息其实是借款资本自身在“未来”的增值,是资本的现值与同一资本未来价值的差额。参见[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1页。庞氏之思想为今日以“净现值法”从金融数学上还原利息的“复利”结构预备了理论基础。与数学上的认识意义,并没有在每月月末结算利息时直接使利息债务到期。〔24〕Vgl. Staudinger/Omlor, 2021, § 246 Rn. 45.利息债务何时到期,以当事人的约定与法律规定为准。依《民法典》第674、670条,只要不违反预扣利息禁令,当事人仍可约定利息债务的到期时点;如无约定,则法律推定利息债务在一年年末或借款合同终止时到期。这说明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框架内,实际利率之计算与利息债权之主张无关,二者实属平行过程。〔25〕Vgl. BGH NJW-RR 1988, 363 (364); Reifner, Zinsberechnung im Recht, AcP 214 (2014), 695, 710, 730.因此,“利息透明”原则并不具有请求权基础之意义。借款利息债权的请求权基础唯独为《民法典》第674条。
实际利率计算方法中的“复利”亦非复利规定中的“复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法释〔2020〕6号修改)第27条规定,借贷双方可以在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后,将不超过合同成立时利率上限的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而后期借款届满后的应付本息之和不得超过前期借款本金乘以其成立时的利率上限以及总体借期时长的总数。虽然该规定的事实构成即“将到期应付而未付的利息计入本金再计算利息”也被称为“复利”〔26〕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92页。,但此种“复利”在结构上由“到期未付利息的本金化”与“重新计息约定”组成,二者都是到期可请求和执行的债务负担行为。这显然与实际利率计算方法中的“复利”不同。后一“复利”中的“利息”仅具数学意义,并非到期可请求和执行的债务负担行为。
另外,由于实际利率计算方法呈现的利息“复利”结构原则上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即仅在于反映利息债务对借款人形成的经济影响,故“利息透明”原则亦与合意制度无关。合同要素通常仅仅是指标的物的种类、数量、质量等,〔27〕Vgl. Staudinger/Bork, 2010, § 145 Rn. 17.并不需要反映标的对当事人的经济影响。对借款合同来说,合意制度仅要求利息的绝对数额“可确定”,〔28〕Vgl. Canaris, Der Zinsbegriあ und seine rechtliche Bedeutung, NJW 1978, 1891; Heermann, Handbuch des Schuldrechts - Geld und Geldgeschäfte, 2003, § 4 Rn. 19.甚至都不要求反映“利率”这种“资本的百分比”的表现形式本身。〔29〕Vgl. PWW/Schmidt-Kessel, 2016, § 246 Rn. 5.因此,只需存在可以算出利息债务绝对值的名义利率或利息,那么就足以满足合意制度的要求。可见,“利息透明”原则并不隶属于法律行为之一般制度,而是构成借款法上的一个专有原则。
不过,如果要严格贯彻实际利率的计算方法,那么该计算方法在返还清算情形中仍将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简言之,基于利息债务对主债务的从属性,随着有效用益借款本金时间之经过,贷款人对约定利息的“保有因”也依据这种数学方法在数额上不断扩大。在确定利息债务的到期时点时,当事人和立法(《民法典》第674条)绝大多数不会参考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实际利率计算方法,而是依据简单、线性的名义利率计算方法相对“恣意”〔30〕Vgl. Reifner, Zinsberechnung im Recht, AcP 214 (2014), 695, 711.地予以确定。故在实务中,利息保有因的发生时点与利息债务的到期时点相互错开,实为常态。〔31〕Vgl. BGH NJW-RR 1988, 363 (364).据此,如果借款人背离借款合同原定的还款方式和计划,向贷款人提前还本或付息,而借款合同嗣后又因故提前终止,那么就应当根据实际利率计算方法准确地计算出利息的实际保有因,以确定贷款人需要还给借款人利息的确切金额。
由于利息“保有因”之确定须借助于实际利率计算方法,因而现代学说已然摒弃中世纪“金钱不育”(sterility of money)〔32〕亚里士多德认为,收取利息相当于让金钱扮演“父亲”以生出子嗣,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2页;Reinhard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0-171.的教条,通过法定的数学规则人为构建了利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33〕Vgl. Reifner/Feldhusen, Handbuch Kreditrecht, 2. Aufl., 2018, § 19 Rn. 3.这深化了对借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我国《民法典》第321条第2款)的理解,也即所谓“法定”既包含法律行为(即当事人约定),亦包含法律规定(即实际利率的法定计算基础)。〔3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二)适用范围
实际利率在德国法上被称为借款的“真实价格”。〔35〕Vgl. Tiあe, Die Zulässigkeit von Bearbeitungsgebühren bei Verbraucherdarlehen, VuR 2012, 127, 130.英国《消费借贷法》第60条则将其称为“借款总体费用的数率”(the rate of the total charge for credit)。据此,在根据“利息透明”原则披露实际利率时,理应在披露的实际利率中计入本金以外所有足以反映贷款成本的借款人支付项目。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将其称为“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而从德国《价格陈述法令》第6条、英国《消费借贷(借款总体费用)规定》第2条以及瑞士《消费借贷法》第9条第2款c项来看,在计算实际利率时也应考虑两类项目,一为典型意义上的利息,二为手续费、中介费等“一次性费用”。利息与费用固然存在差异,〔36〕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当事人约定借款合同提前终止时贷款人无须返还某笔费用,则该笔费用并非利息,而是一次性费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484号民事判决书。但在“利息透明”原则下却应一视同仁。因为“实际利率”是一种人为构建的“致力于透明性的计算数值”,与法律意义上作为债务标的的“利息”并不完全对应。〔37〕Vgl. Staudinger/Blaschczok, 1997, § 246 Rn. 39, 41; BGH NJW 2014, 2420 (2423).
此外,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仅涉及一份使用了利息格式条款的消费借贷合同。法院据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有关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中找到了实际利率披露义务的规范依据。但是,在我国现行法中,实际利率披露义务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借款合同?此种义务是否还有其他规范基础?
有人可能认为,仅仅应当对金融借款适用“利息透明”原则,明确贷款人的实际利率披露义务。我国的一些机构、学者正是如此解读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的裁判主旨的。〔38〕例如,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2019-2020年度“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中纳入了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并认为“贷款机构”有义务明确披露贷款实际利率。参见https://t.ynet.cn/baijia/30510442.html,2022年7月6日访问。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同样仅倡导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披露实际利率,对民间借贷的贷款人则持“鼓励”态度。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借款贷款人是持牌金融机构,有能力计算借款交易的实际利率。实际上,银行内部在会计核算时,也经常会以“年化利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简称APR)与“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IRR)这两个标准衡量银行的贷款业务收益,而后者对应的正是本文讨论的实际利率。〔39〕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也用“内部收益率”(IRR)指称本文意义上的实际利率。相反,如果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由于出借人往往欠缺金融数学知识,难以要求其计算并公布实际利率。此种观点的论证重心无疑在于贷款人的“计算能力”。但在民法上如为贷款人确立实际利率披露义务,必须以某种具体的法律评价作为支撑。仅以贷款人有无特殊计算能力确立其有无披露实际利率义务,欠缺充分的正当性。
实际利率的计算确实十分复杂,往往只能通过计算机计算。实际利率计算亦具有反直觉性,如德国司法界人士所言,其计算过程是一种“对人类大脑而言更可以说是陌生的超线性思考”,〔40〕Vgl. BGH NJW 1995, 2286 (2287).因为它的增长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像树上长出枝条、枝条上再长出枝条的过程,〔41〕Vgl. Reifner, Zinsberechnung im Recht, AcP 214 (2014), 695, 704.或如卡纳里斯(Canaris)所言,呈现为“阶梯性增长”。〔42〕Vgl. Canaris, Die Auswirkungen der Sittenwidrigkeit von Ratenkreditverträgen auf Folgekreditverträge, WM 1986, 1453,1458.在实务中,许多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没有经过金融数学训练,无法仅凭名义利率洞悉借款合同的真实负担。故传统观点合理地认为,之所以要引入“利息透明”原则,核心目的仅在于避免优势贷款人剥削无经验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借款人。〔43〕Vgl. Reifner, Zinsfiktion und AGB-Gesetz, NJW 1989, 952, 959.易言之,“利息透明”原则的核心主旨仍在于保护缔约人的“事实上之决定自由”〔44〕所谓“事实上之决定自由”,关注的是行为人在“法律上之决定自由”的界限(如行为能力)以外,其自主决定的意思是否受到了实际的妨害。Vgl. Canaris, Wandlung des Schuldvertragsrecht: Tendenzen zu seiner „Materialisierung“, AcP 200 (2000), 273, 277.,其适用前提与缔约过失损害赔偿的要求相近,〔45〕Vgl. Reifner, Zinsfiktion und AGB-Gesetz, NJW 1989, 952, 959.是一种保护借款人的规定。
因此,仅在借贷双方存在有利于贷款人的明显力量落差时,“利息透明”原则方有介入之必要。在我国民间借贷司法实务中,就有法院在弱势借款人为维持生活而仓促借取大额贷款的情形中确定了贷款人的实际利率披露义务。〔46〕参见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20)粤1424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书。而如果借贷双方力量均衡,比如说财力相当的商人之间的借款,那么引入“利息透明”原则的必要性便不复存在。〔47〕Vgl. Casper/Möllers, Zulässigkeit von Bearbeitungsentgelten bei gewerblichen Darlehensverträgen, WM 2015, 1689, 1695.故此,如果其他类型借款合同中的借贷双方存在有利于贷款人的明显力量落差,那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和《民法典》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之外,基于类似的相对人或借款人保护之思想,还可以借由缔约过失(《民法典》第500条)的管道引入“利息透明”原则,为优势贷款人设定一个向弱势借款人披露借款实际利率的先合同义务。〔48〕遗憾的是,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并未注意到《民法典》第500条。
既然“利息透明”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规范贷款人的缔约行为保护借款人的法律原则,那么该原则为何不能直接渗入合意制度之中?渗入的结果无非是借贷双方必须对某个实际利率达成合意方能设立利息债务。这在理论上貌似合理,在实践中却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如果借款人对贷款人预定的利率提出异议,希望以另一个利率确定借款利息债务,那么其就必须自行提供一个实际利率。但是,为了明确自己在依据此种方法计算时所负担的利率具体数额,借款人需要先进行极具技术性的计算作业,这对处在弱势地位的借款人而言不免过于苛刻。对借款人而言,最为便利的交易模式通常是其仅须借助最为简单的名义利率方法对利息数额予以明确和磋商,但其可以基于对借款关系的信赖,〔49〕借款关系具有信赖、协作的性质。Vgl. Reifner, Das Geld-Band 3: Recht des Geldes, 2017, S. 156.要求贷款人相应地计算和披露借款资金的真实价格亦即实际利率。如果以维护意思自治为名,要求借款人在提出新要约时须自行给出实际利率,则交易便利难免会成为被牺牲的代价。为使交易便捷、流畅,适度维持传统合意制度与不法缔约行为防免规则(缔约过失责任)的张力格局是必要的。〔50〕参见孙维飞:《〈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179页。
三、违反“利息透明”原则的法律后果
如果贷款人未披露或未准确披露实际利率,则“利息透明”原则将透过何种管道引发何种法律后果便成为最重要的实务问题。从逻辑上看,此时应当先明确利息债务是否已经成立,然后再判断贷款人是否准确披露了实际利率。正如前述,从合意制度来看,利息债务之成立仅须在绝对数额上“可确定”。这通常仅仅要求存在足以计算出利息债务绝对值的名义利率。而下文将予讨论的也是当事人仅以名义利率确立利息债务且利息债务总额自始即可确定这种常见实务情形。
(一)“利息约定不明”规则
首先需要简单探讨《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的“利息约定不明”规则。我国司法实务对该规则形成了以下两个案例群。其一,如果存在利息约定的意思,名义利率虽约定不明但仍可确定,那么此时就不构成“利息约定不明”。实务中的典型情形有以下三种:(1)能确证存在利息清偿的事实,并可根据该事实计算出名义利率;〔51〕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一终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书。(2)事先扣除利息,并可根据该事实计算出名义利率;〔52〕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2770号民事裁定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终490号民事判决书。(3)约定“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利率四倍计算”。〔53〕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云高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其二,如果利息约定意思无疑,但名义利率无法确定,那么就构成“利息约定不明”。实务中的典型情形有以下四种:(1)借贷双方在诉讼中均认可约定利息,唯对利息计算标准/名义利率有争议,且双方主张均难以佐证;〔54〕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2)约定了“按月给付利息”等内容,但未约定具体的名义利率标准;〔55〕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黑高商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民终2616号民事判决书。(3)尽管约定了利息的数值、比率,但计算方式无法确定;〔56〕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63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及关联规定适用指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43页。(4)约定事先扣息,但扣除份额不明,无法计算出具体的名义利率。〔57〕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申3355号民事裁定书。
归总来看,《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利息约定不明”的实质是“名义利率约定不明”。〔58〕参见刘勇:《〈民法典〉第680条评注(借款利息规制)》,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184-185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务指导与疑难解答》,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我国司法实务从未在此规定中纳入实际利率的披露要求。根据《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在自然人借款合同中,如果名义利率无法确定,那么视为未约定任何利息债务;而在其他借款合同中,如果名义利率无法确定,则法院通过补充性解释确定合同的名义利率。
需要注意的是,在满足《民法典》第680条第3款之适用条件时,“利息透明”原则即无用武之地。因为此时应由法院确定利率,并不存在该原则所欲防范的贷款人剥削风险。
(二)利息格式条款
如果贷款人未在其提供的名义利率格式条款或者具有隐瞒借款利息实际负担效果的利息计算条款中披露实际利率,那么这在格式条款法上将产生何种后果?
1. 确定名义利率数额的条款
对格式条款的审查包括两个步骤,即订入审查与内容审查。但是,并非所有涉及给付或对待给付的格式条款都须接受内容审查。一般认为,直接确定给付或对待给付之数额的“价格主约定”并不接受内容审查,仅须接受订入审查;需要额外接受内容审查的,是对给付允诺予以限制、变更、修正或排除的所谓“从属约定”。〔59〕Vgl. Erman/Roloあ, 2017, § 307 Rn. 42 f. 亦可参见贺栩栩:《〈合同法〉第40条后段(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第180-181页。就区别对待二者而言,我国法与德国法上的理由略同。我国的有力学说从不同类型格式条款在缔约“合意度”上的典型差异出发,认为当事人在典型情况中已经对“价格主约定”达成了充分合意,但对“从属约定”达成合意的程度则有所不足,因此,只有后者才需要接受内容审查。〔60〕参见解亘:《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0-114页。德国学者则以条款相对人在缔约时的“注意力”差别确定应受内容审查的条款范围,并认为在缔约时格式条款相对人有限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价格主约定”上,故“价格主约定”并不会带来条款使用人单方滥用合同形塑自由的典型危险,无须接受内容审查。前述危险毋宁说仅存在于“从属约定”场合,因为这种约定在缔约时并非相对人关注的重点。〔61〕Vgl. BGH NJW 1989, 222 (223); Taupitz, Unwirksamkeit der sog. nachträglichen Tilgungsverrechnung bei Annuitäten-Darlehen- BGH NJW 1989, 530, und NJW 1989, 222, JuS 1989, 520, 524; Bunte, Anmerkung, JR 1989, 375, 376.另外,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数额原属私法自治范畴,除违法、悖俗界限(我国《民法典》第153条)之外,法律上通常也并不存在审查标准。〔62〕Vgl.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1. Aufl., 2013, § 18 Rn. 374; Erman/Roloあ, 2017, § 307 Rn. 38; BGH NJW 1997, 2752.
如果一个利息格式条款仅仅确定了名义利率,亦即仅仅确定了借款合同中一种主给付的数额,那么其显然构成“价格主约定”,并非内容审查的适格标的,仅能成为订入审查的对象。〔63〕Vgl. Niebling, Die Inhaltskontrolle von Preisen und Leistungen nach dem AGBG, WM 1992, 845, 850.此时仅须考察借款人能否注意、了解名义利率的数值,这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都不难得出肯定结论。因此,即使该条款未载明实际利率,其在格式条款法上通常亦无疑虑可言。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也没有对载明名义年利率11.88%的《贷款合同》提出合法性质疑。
2. 利息计算条款的司法评价
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在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层面具体考察了《还款计划表》。该《还款计划表》实为一种确定利息计算具体过程的格式条款。尽管该条款在利息数额的某种计算上与《贷款合同》载明的名义年利率11.88%相互印证,但因计算方法特殊,该条款令借款人对真实利息负担(实际年利率约为20%)产生了错误感知。法院认为,贷款人没有披露《还款计划表》在利息计算上对借款人产生的不利影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1款、《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规定的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还款计划表》未被订入借款合同。而后,法院通过合同解释,将《贷款合同》载明的“平均年利率11.88%”解释为一个按月结算的名义年利率,在案涉借款合同确立的分期支付规则的基础上,以借款人在每月月初能够实际支配的借款本金为基数,对借款利息的数额进行了重新计算,最后判决贷款人返还多收的利息88万余元。〔64〕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终1034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金融法院的这则判决,无论在案情上还是在裁判结果上,皆与德国上世纪80年代有关“清偿结算与利息计算条款”(Tilgungsverrechnungs- und Zinsberechnungsklauseln)的司法实务情况相近似。在形式上,清偿结算条款与利息计算条款是两个条款。二者在借款合同原定的名义利率以外,还额外确定了以下内容。清偿结算条款规定,借款人要进行“年内清偿”(unterjährige Tilgung),也就是说每月、每季度或每半年按计划支付本金,但相应支付的清偿效果却并不立即发生,而是推迟至当年年末才发生。利息计算条款则规定,名义利率的计算基数是上年年末时的本金数额,也就是说包含了已经被清偿的本金部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8年11月24日的一则判决中认为,清偿结算条款规定的年内分期支付、年末统一发生清偿效果的规则对客户来说是清楚、明确的,故此种条款是有效的。〔65〕Vgl. Hunecke, Zinsberechnungs- und Tilgungsverrechnungsklauseln im Lichte der BGH-Urteile vom 24. November 1988, WM 1989, 553, 555.但利息计算条款却对借款人隐瞒了其在与清偿结算条款互动时所隐蔽产生的更高实际年利率,违反了“透明性强制”(Transparenzgebot)规则,应视为无效。〔66〕Vgl. BGH NJW 1989, 222 (224 f.).要消除这种不透明性,贷款人不仅必须在形式上将利息计算条款“附加”在清偿结算条款中,而且必须通过披露实际利率等方法,让两个条款“实质性咬合”在一起,以使客户能够明了两个条款背后隐藏了一个未明说的后果,即借款人仍须对已被清偿的债务支付利息,其承担的实际利率更高。〔67〕Vgl. BGH NJW 1990, 2383 (2384); BGH NJW 1992, 1108 (1109); BGH NJW 1995, 2286 (2287).在判定利息计算条款无效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借款人实际使用的资本为计算基数,根据合同名义利率重新计算利息数额,并提示借款人可依不当得利法请求贷款人返还多收的利息。〔68〕Vgl. BGH NJW 1989, 222 (225).
如果利息格式条款利用某种特殊的利息计算方法隐瞒了真实的借款利息负担,又没有同时披露实际利率,自然违反了“利息透明”原则,应予否定评价。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与德国前述判决在大体上都是合理的,但在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层面尚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3. 利息计算条款的审查路径
首先,以计算方法隐瞒借款利息实际负担的格式条款,究竟应归于“价格主约定”仅接受订入审查,还是应归于“从属约定”而主要被置于内容审查阶段加以规制?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虽未加详细说理,但实质上选择了前一种进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则明确选择了后一种进路。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进路后来引发了巨大争论。核心争议在于,其设立了一种所谓“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Unangemessenheit durch Intransparenz)的内容审查标准,这似乎模糊了订入审查与内容审查的界限。〔69〕Vgl. Staudinger/Omlor, 2021, § 246 Rn. 85.尽管出现大量反对声音,〔70〕Vgl. Bruchner, Zinsberechnungsmethode bei Annuitätendarlehen im Lichte der BGH-Urteile vom 24. November 1988, WM 1988, 1873, 1875; Wagner-Wieduwilt, Das „Transparenzgebot“als Angemessenheitsvoraussetzung im Sinne des § 9 AGBG, WM 1989, 37, 40.但支持将“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设置为内容审查之独立标准的观点〔71〕Vgl. Köndgen, Grund und Grenzen des Transparenzgebots im AGB-Recht, NJW 1989, 943, 950.仍然占据了上风。在2002年德国债法改革时,《德国民法典》第307条第1款第2句新增了“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内容审查标准的有关规定。笔者认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见解,亦即具有隐瞒借款利息实际负担效果的利息计算条款应归于“从属约定”。此种条款通常已经订入合同,只是需要接受内容审查。
德国法学家卡纳里斯认为,对利息数额与计算方式的约定不能被人为割裂为“价格主约定”与“从属约定”,否则明显违背当事人的真意。〔72〕Vgl. Canaris, Zinsberechnungs- und Tilgungsverrechnungsklauseln beim Annuitätendarlehen, NJW 1987, 609, 614.但此论并不准确。〔73〕Vgl. Niebling, Die Inhaltskontrolle von Zinsberechnungsklauseln, ZIP 1987, 1433, 1435.具有隐瞒效果的利息计算条款并不是将统一价格作分别约定,而是通过一种隐蔽的操作,致使其他合同文本和材料中已经载明的利率不复准确甚或具有欺骗性。比如在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中,《还款计划表》致使《贷款合同》载明的名义年利率11.88%具有欺骗性,但《还款计划表》本身是一份载有96期分期款的还款计划,借款人在缔约时显然不太可能详细阅读这份还款计划。故此,不应认为具有隐瞒实际利息负担效果的利息计算条款构成“价格主约定”,而应认为其构成“从属约定”。
但这类“从属约定”通常确已订入合同。格式条款订入合同,除双方须有合意之外,依《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尚须满足两个前提,一为条款使用人在缔约时向相对人明示援引格式条款,二为相对人得以据此注意、理解格式条款的内容。前一个前提不难满足,后一个前提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相对人“注意”或“理解”的标准。从学说上看,这一标准较低,相对人得知条款内容即可,无须验证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法律状态。〔74〕Vgl. Bieder, Der Schutz vor täuschungsgeeigneten Formularverträgen, AcP 216 (2016), 911, 949; Linden, AGB-rechtliches Transparenzgebot bei Zinsanpassungsklauseln, WM 2008, 195, 196 f.因为使用人对大规模使用重复文本也具有一种“理性化”利益,如果在订入审查阶段就启动严苛的妥当性审查,无异于对使用人课加类如立法者立法的标准。〔75〕Vgl. Hellner, Quo vadis AGB-Recht?, FS-Steindorあ 1990, S. 585.因此,应当将格式条款的审查置于一个时间序列中,并在每个阶段各有侧重。为了顾及使用人使用格式文本的“理性化”利益,在订入审查阶段可以放宽审查标准;但为避免相对人因缔约之初的信息不对称而遭受不利,应当在内容审查阶段严加审查,尽力避免其因未仔细审读格式条款而遭受危险。〔76〕Vgl. Leyens/Schäfer, Inhaltskontrolle allgemeiner Geschäftsbedingungen, AcP 210 (2010), 771, 798 f.
在将隐瞒利息实际负担的利息计算条款视为“从属约定”之后,应当在内容审查的框架内,检视其是否对借款人造成了“不妥当的不利对待”或“不合理的利益减损”。〔77〕参见贺栩栩:《〈合同法〉第40条后段(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第183页。具体而言,则是判断利息计算条款是否“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其核心审查基准是判断隐瞒性的利息计算条款是否具有严重阻碍借款人意思决定之自由的分量。〔78〕Vgl. Taupitz, Unwirksamkeit der sog. nachträglichen Tilgungsverrechnung bei Annuitäten-Darlehen - BGH NJW 1989, 530,und NJW 1989, 222, JuS 1989, 520, 526.如果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差额显著,而此种条款又完全没有披露实际利率,自然可予肯定回答。
4. 偏低披露实际利率的情形
如果贷款人在利息计算条款中披露了实际利率,只是该实际利率低于真实的实际利率,又应作何评价?在这一情形,如果借款人已然得知利息计算条款载明的实际利率(尽管是错误的),这就已然满足订入审查的要求了。至于借款人被“欺骗”了,并不知道自己得知的实际利率与真实的实际利率有所不同,则如前述,当在内容审查阶段加以解决。此时须判断偏低披露实际利率的格式条款是否足以阻碍借款人意思决定之自由。如果借款人得知的实际利率与真实的实际利率仅有微小差额,似乎还无法认为借款人的意思决定自由严重受阻,以至于面临贷款人单方滥用磋商优势的危险,亦即此种微小差额尚不足以证成利息计算条款无效。
综上所述,与上海金融法院的见解不同,笔者认为在格式条款法中,“利息透明”原则的真正栖身之地并非订入审查规范,而是“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这一内容审查标准。这一内容审查标准的制定法依据可被认为是《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提及的“公平”原则。《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并未划清订入审查与内容审查的界限,第497条亦仅是粗略列举格式条款经内容审查无效的个别情形,现行法似乎欠缺格式条款内容审查标准的一般性依据。但学界有力观点认为,可将《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视为一个不完全法条,该款提及的“公平”实为需要法官予以具体化的内容审查一般标准。〔79〕参见贺栩栩:《〈合同法〉第40条后段(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第182页。
(三)消费借贷合同
在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中,法院尽管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与第26条第1款,最终却仍然仅在格式条款法的框架内进行裁判,这一做法是否合理?
1. 比较法上的规制经验
对消费借贷中的“利息不透明”问题,英国、瑞士、德国等均采专门规制策略。瑞士《消费借贷法》第15条第1款与《德国民法典》第494条第1款均规定,如果消费借贷的贷款人根本未披露实际利率,则消费借贷合同无效。但与瑞士《消费借贷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合同无效后借款人无须返还任何利息、费用不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494条第2款第2句,如果借款人已经受领或使用了借款,那么消费借贷合同将因被“治愈”(Heilung)而有效,只是此时借款合同的名义利率将直接以《德国民法典》第246条规定的法定年利率4%确定。因为尽管应当制裁未披露借款合同必要信息的贷款人,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受领或使用借款,那么又要对贷款人的利益予以“适当妥协”。〔80〕Vgl. MünKomm/Schürnbrand/Weber, 2019, § 494 Rn. 1.
不过瑞士《消费借贷法》第15条并未明确是否应将错误披露与完全未披露实际利率的行为作同等评价。对此,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原先持肯定见解,〔81〕Vgl. BGE Urteil 4C_58/2006 vom 13.06.2006.但近期立场似有松动。〔82〕2020年的一则判决对此虽然未给出结论,但承认“错误披露实际利率是否一直都导致合同无效”确实是一个问题。Vgl.BGE Urteil 5A_998/2019 vom 02.10.2020.德国法则明文区分前述两种情况分别作了规制,考虑更为周全。依《德国民法典》第494条第3款之规定,如果实际利息被披露得过低,则名义利率须减去真实实际利率与错误披露的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如名义年利率为9%,实际年利率为16.22%,但披露的实际年利率仅为10%,那么名义年利率9%就要减去16.22%与10%之间的差额6.22%,得数为2.78%。借款人最终仅须支付依该名义年利率2.78%计算出来的利息。按照这个规则,在极端情况中名义利率甚至可能被减至为负数。〔83〕Vgl. Erman/Nietsch, 2020, § 494 Rn. 19.这一规则的目的是让贷款人受其错误陈述之拘束。〔84〕Vgl. BeckOnline/Knops, 2021, § 494 Rn. 32.原则上,完全没有披露实际利率将导致借款合同全部无效,错误过低披露实际利率则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整体效力,只是导致利息债务缩减。〔85〕Vgl. MünKomm/Schürnbrand/Weber, 2019, § 494 Rn. 2, 12, 31.不过与错误过低披露实际利率的情形不同,对实际利率的错误偏高陈述是无害的。因为后者并未在实质上增加借款人的负担,法律没有必要对这种没有产生实质后果的错误披露行为施加制裁。〔86〕Vgl. MünKomm/Schürnbrand/Weber, 2019, § 494 Rn. 32.
另外,在消费借贷领域内,如果存在与实际利率披露相关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瑞士《消费借贷法》第15条、《德国民法典》第494条),那么基于此种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保留”〔87〕我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具有“规范目的保留”,也就是说,已经对特定情事设定了排他性的规范目的和规制方法,一旦该规定适用,具有相同适用范围的其他规定就不再适用。Vgl. MünKomm/Armbrüster, 2012, § 138 Rn. 4.可以推知,在消费借贷合同使用了利息计算格式条款但并未同时披露或未如实披露实际利率的情形中,应优先适用相关强制性规定,不再进行格式条款法上的内容审查。〔88〕参见贺栩栩:《〈合同法〉第40条后段(格式条款效力审查)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第181页。
2. 基于悖俗的法律续造
我国并无专门的《消费借贷法》。在消费借贷司法实务中,其他消费者保护规定也往往未能享受特别法的优先适用地位,而是常常沦为法院裁判说理的辅助依据。比如在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中,法院虽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和第26条第1款明确了商家对金融消费者的实际利率披露义务,却并未由此推导出具有特别法性质的裁判准则,而是仍然回到了格式条款法的审查框架。然而,仅依格式条款法评价消费借贷合同的做法可能并不合乎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在格式条款被判定无效后,合同其余部分原则上仍然有效。〔89〕同上注,第190页。此外,法院在判定利息计算条款无效后,又依据借款人在整个借期内实际用益资本的资金数额和用益时间,重新以合同原定的名义利率计算借款利息。在此过程中,法官势必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这对司法效率产生了不必要的妨碍,也对该案提炼出的裁判规则的普及意义产生了消极影响。
针对消费借贷的情形,能否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评价性依据,在我国现行法中导入一种优先于格式条款法适用的、有关实际利率披露的法效果规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似可胜任,因其一般性地确立了商家在缔约时向消费者披露金融服务价格的义务。然而,这一规定虽为《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但其何以直接撼动合同效力,在解释上未免陷入困难。那么可否基于《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的公序良俗条款,藉由法律续造构建出一种法效果规范?参考以往的相关案例,续造线索近乎渺茫,但或可以某种“主观不法+客观不法”的演绎框架〔90〕以此种演绎方法对“公序良俗”予以具体化的做法,vgl. Bamberger/Wendtland, 2012, § 138 Rn. 19 あ.; Brox/Walt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3. Aufl., 2009, § 14 Rn. 330; BGH NJW 2010, 363.尝试续造。
在消费借贷合同中,如果贷款人未披露或错误偏低披露实际利率,则显然已经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之规定,可视为主观不法。〔91〕但在贷款人未披露实际利率时,通常难以肯定贷款人有欺诈故意,难以落入欺诈制度的规制范围。Vgl. Bruchner,Zinsberechnungsmethode bei Annuitätendarlehen im Lichte der BGH-Urteile vom 24. November 1988, WM 1988, 1873, 1876.而未披露或错误偏低披露实际利率之行为,可能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借款人负担超出其偿付能力的债务,〔92〕隐瞒真实利息负担的消费借贷合同在德国被称为“现代的债务监狱”,在韩国被称为“掠夺性贷款”。Vgl. Emmerich, Die Verzugsschadensproblematik bei Ratenkrediten, FS-Giger 1989, S. 189, 191 f. 另参见吴睿离:《韩国新〈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载朱慈蕴、汤欣主编:《清华金融法律评论》(第6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57页。亦产生了客观上的不法危害。
前述主观不法与客观不法相结合时,可能足以证成消费借贷合同的效力瑕疵,主要理由如下。《民法典》第151条的显失公平规则可视为第153条第2款公序良俗条款的特别规定,〔93〕参见贺剑:《〈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显失公平制度)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166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211页。而依《民法典》第151条,显失公平行为仅可撤销,与《民法典》第149、150条规定的欺诈、胁迫行为保持一致,这说明显失公平行为的客观不法要素在法律评价上并未超越其主观不法要素的损害相对人性质,显失公平规则仍为单纯的意思决定自由之保护规定。〔94〕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4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页;尹田:《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行为的性质及其立法安排》,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1-12页。由此可推知如果一种法律行为兼具主观不法与客观不法特征,则可能构成悖俗行为,但如果主客观不法因素都仅损及相对人利益,则悖俗行为的法效果受《民法典》第151条之影响,应被限制为可撤销。消费借贷合同的贷款人未准确披露实际利率时,兼具主观不法与客观不法,与显失公平行为在不法结构上具有类似性,此时应当基于动态体系论之思想,〔95〕Vgl. MünKomm/Armbrüster, 2012, § 138 Rn. 29.研判未准确披露实际利率行为的整体不法性是否接近或达到显失公平规则的评价权重,亦即是否严重危及相对人的意思决定自由。在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存在明显差额,且贷款人根本未披露或明显偏低披露实际利率时,可认为达到了危及借款人意思决定自由的程度,此时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51条及第153条第2款,容许借款人撤销借款合同。问题是借款人依前述推论撤销借款合同时,应以何种合同范围作为撤销对象,对此应区分以下不同情况而论。
首先,如果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显著,而贷款人完全未披露实际利率,那么认为消费者对整个消费借贷合同的意思决定自由都受到妨碍,可以撤销整个消费借贷合同,当属无疑。其只须依据不当得利法向贷款人返还实际用益资本的利息用益。
其次,如果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显著,且贷款人又明显偏低地披露实际利率,则借款人之意思决定自由遭受妨碍亦无可疑。唯此时如何影响消费借贷合同之效力尚待阐明。《德国民法典》第494条第3款的策略是不影响借款合同整体效力,仅在约定名义利率的基础上减去真实实际利率与虚假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这一规则可资参考。一方面,不影响借款合同整体效力的做法应予赞同。偏低披露实际利率可能是披露或计算过程中的疏失或草率所致,如因此即可颠覆交易,未免对贷款人施加了不合比例的制裁,同时纵容背信借款人的投机行为,亦即在较晚之后才表示撤销合同,并仅须依据不当得利法返还以更低利率计算之利息。另一方面,在偏低披露实际利率时,应认为消费者仅对利息债务之约定产生了意思决定自由上的瑕疵,但瑕疵的具体范围理当限制在真实实际利率与虚假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上。因此,消费者仅能撤销以这个差额为基数乘以本金和借期得出的债务。
最后,如果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甚微,或虽然二者差距显著,但错误偏低披露的实际利率与真实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甚微,则应认为借款人的意思决定自由未受妨碍,并否认其撤销权。不过,在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显著的情形中,如果贷款人披露的实际利率极其过分地低于真实利率,则在评价上几与完全未披露无异,此时应例外容许借款人撤销整个借款合同。〔96〕有德国学者亦指出,如果披露的实际利率出现了“重大不正确”的情况,则可视为与完全未披露等同。Vgl. BeckOnline/Knops, 2021, § 494 Rn. 16.1.
(四)缔约过失责任
但是,前述方法仅限于消费借贷情形,而且在论理上未免过于迂回。是否存在更便捷的、能够适用于所有存在有利于贷款人之明显力量落差情形的解决方案?对此,或可参考《民法典》第500条的缔约过失规则。如前所述,“利息透明”原则与该规则有共通之处,即都以保护交易相对人之“事实上的决定自由”为旨归。而在存在有利于贷款人的明显力量落差的借款合同中,如果贷款人未准确披露实际利率,则借款人能否善尽“事实上的决定自由”原本就殊为可疑。此时不当披露实际利率的行为本身就可直接视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不过,为触发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还以借款人受有损害(事实上的决定自由遭受严重妨碍)为前提。
1. 完全未披露实际利率
如果贷款人完全没有披露实际利率,那么这就已然违反了先合同义务。但仅在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显著之时,借款人才受有损害,〔97〕在数学规律上,整年借款(比如借期一年且年末还本付息的借款)的名义年利率与实际年利率的数值是相同的。在这种合同中不披露实际利率恐怕不太可能会对借款人造成不利影响。亦即其无法察觉借款的真实价格,进而获得了一个在获知真实情况时根本就不想要的借款产品,遭受了可谓“一整个不利合同之订立”的损害。〔98〕参见孙维飞:《〈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190页。故此,借款人可以请求贷款人“恢复原状”(《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第5项),也即回复至贷款人准确披露实际利率时的状态;而一旦贷款人准确披露,借款人便不会与贷款人缔约。〔99〕同上注,第186-187页。因而,此时“恢复原状”的结果便实质等同于使借款合同溯及无效。贷款人丧失合同利息请求权,须依不当得利法将借款人支付的所有利息都返还给借款人。当然,此时的贷款人也可以依据不当得利法,根据市场利率(如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请求借款人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不当得利。
2. 偏低披露实际利率
如果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差额显著,贷款人虽然披露了实际利率但披露得明显偏低,那么贷款人仍然违反了其先合同义务,借款人事实上的决定自由也仍然遭受了妨碍,此时亦可触发贷款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不过,借款人此时仅可主张“部分解消”借款合同。因其此时遭受之损害通常仅为“部分不利合同之订立”,亦即因贷款人之虚假陈述而多负担了利息债务,因此,在依《民法典》第500条主张损害赔偿时,借款人可以通过主张“恢复原状”,在实质上使这部分的利息债务溯及无效。而在计算这部分损害时,也自然应以真实实际利率与虚假实际利率的差额为准。当然,如果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差额显著,而贷款人却极其过分地偏低披露实际利率,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被认为与完全未披露无异。此时应例外容许借款人对整个借款合同的解消主张。
对比来看,在贷款人违反“利息透明”原则时,依据《民法典》第500条的缔约过失制度,容许借款人“解消”借款合同之全部或一部,当属现行法下最为明晰的解释论方案。这一简单规则不仅使借款人有动力诉请制裁贷款人,而且也大大节省了法官的利息计算工作。
四、结语
本文力图揭示“利息透明”这一在我国久被忽视的借款法重要原则,成文契机归功于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首案”,这是一则具有开创意义和标志意义的判决。其引入的“利息透明”原则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准确披露借款实际利率,最直接的意义是促成一个信息透明的借贷市场,借款人的利益将因此受到充分保障。要求贷款人准确披露实际利率也是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体数十年来的通行做法,因此贷款人将不再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取暴利,高利贷的容身之地将大为减少。从我国现行法下的解释论来看,“利息透明”原则在格式条款法中栖身于“因不透明而致不妥当”这一内容审查标准,其法律基础是《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提及的“公平”原则。而在消费借贷以及借贷双方存在有利于贷款人的明显力量落差的其他借款合同中,“利息透明”原则最具实践意义的法律基础应是《民法典》第500条的缔约过失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