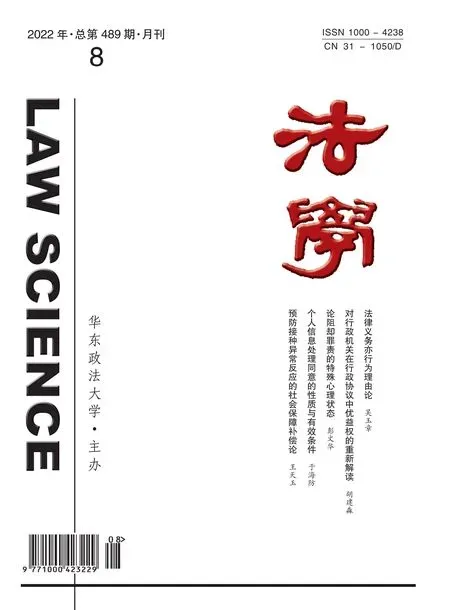论阻却罪责的特殊心理状态
●彭文华
一、视角与问题
在定罪量刑时,传统刑法理论往往关注行为和责任,显得过于绝对。事实上,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审视行为和责任,有时更有助于理性地看问题。以正当防卫为例,有学者从侵害人的视角出发,认为侵害人法益值得保护性的下降程度影响防卫权边界的划定,并与防卫限度的判断密切相关。〔1〕参见陈璇:《侵害人视角下的正当防卫论》,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0-138页。这种从侵害人立场出发,对正当防卫具体要件认定展开体系化解释的方法,拓展了正当防卫研究的视野,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同样,基于维护防卫人权利和强化法益保护的需要,从受害者(遭受不法侵害的防卫人等)视角对正当防卫的具体条件进行解释,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正当防卫的研究。特别是对遭受特殊侵害的行为人而言,从其作为特殊受害者的立场进行审视,能为客观评价行为性质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行为人受到特殊侵害,受特殊心理及其应激行为驱使,其反击行为在性质上可能与普通危害行为有所不同。基于理性与道德情感需要,对行为的评价不该忽视行为人的特殊心理及其应激反应。然而,司法实践似乎完全置此于不顾。以受虐妇女杀夫案为例,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检索127例判决书发现,受虐妻子杀夫案的共同特点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家暴,最后因杀死丈夫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刑,刑期从有期徒刑2年6个月(包括缓刑)至无期徒刑不等。甚至,在妻子反击而未造成轻伤以上结果的场合,也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刑。〔2〕例如,在柳某故意杀人案中,柳某与李某登记结婚系夫妻,柳某长期遭受李某打骂,并多次报警处理。2015年6月9日14时许,柳某因离婚事宜与李某发生口角,在遭到李某恐吓、殴打后,趁其不备用榔头打击被害人,致李某多处受伤,但均未构成轻伤以上。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柳某有期徒刑2年。参见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1刑初169号刑事判决书。尽管法院通常对妻子杀人给予从轻处罚,但基本上是从被害人过错的角度来评价的,并未考虑行为人受特殊心理状态及应激反应所驱动这一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杀夫的受虐妇女,判例常以“情急之下”“无法忍受”“不满”揭示当事人行为时之心理状态。丈夫之暴力虐待被认定为被害人过错,妻子长期受虐下的特殊心理及应激反应对行为定性的影响,则完全被司法忽略。事实上,在我国裁判文书中,特殊心理状态及应激反应对行为定性的影响,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在司法实践中,无论丈夫如何暴力虐待妻子,妻子的反击行为都被当作一般侵害加以对待。只要妻子欲杀丈夫,无论造成何种危害结果,都将以故意杀人罪论处。问题在于,对于刑法规范适用而言,只有更好地平衡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刑罚效果的最佳化。〔3〕参见彭文华、傅亮:《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1期,第32页。就特殊心理状态对罪责的阻却而言,需要在不法侵害人与受特殊心理状态支配的防卫人之诉求和权益间加以恰当平衡,才能够更为理性地对行为进行定性的价值判断。本文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经验,以特殊行为人(包括防卫人等)的视角,对其特殊心理及应激行为对行为定性的影响,拟从法理与规范的立场加以深入分析和评价,以期客观看待其在定罪量刑中的体系性地位。
二、特殊心理状态:阻却不法与责任
对在特殊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如何定性,两大法系国家有不同认识和理解。对行为人的特殊心理状态,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在不法层面讨论其性质及其对定性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则通常在责任层面对之进行评价。
(一)阻却不法的特殊心理状态
英美法系国家对犯罪有两种正面辩护:正当辩护和宽恕辩护。前者包括自卫、紧急避险等,后者表明被告行为有错却存在可原谅的其他原因。〔4〕See Abigail Finkelman, Kill Or Be Killed: Why New York’s Justification Defense Is Not Enough for the Reasonable Battered Woman, and How to Fix It, 25 Cardozo J. Equal Rts. & Soc. Just. 267 (2019), p. 283.典型宽恕理由是受虐妇女综合症。“受虐妇女综合症”一词最早见于1977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资助的研究中,〔5〕See Lenore E. A. Walker,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 49.而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乃美国心理学院教授丽诺尔·沃克在其所著《被殴妇女》一书中提出的。沃克立足于大量临床研究提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旨在为遭受持续身体和心理虐待的妇女使用武力反击提供帮助,借此支持自卫主张并为难以理解的行为之合理化寻求依据。〔6〕Se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11 Geo. J. Gender & L. 59 (2010), p. 60.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妇女不能以‘理性人’的方式确定对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恐惧,自卫判断必须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7〕Gayle Strommen, Criminal Law - Battered Women and Self-Defense, 63 Temp. L. Rev. 375(1990), p. 375.起初,受虐妇女综合症用来解释某些受丈夫、伴侣或情人虐待的妇女的行为(包括潜在的暴力行为)。〔8〕See Xinge He, Emma Johnson, Lauren Katz, Blake Pescatore, Alexandra Rogers & Eva Schlitz, Domestic Violence, 21 Geo. J.Gender & L. 253 (2020), p. 274.因为受虐妇女生活在亲密合作伙伴(通常是男人)施加的身体、性或心理虐待中,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根据该理论,对受虐妻子不能以“理性人”的方式看待,其杀夫存在宽恕理由。受虐妇女综合症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受虐妇女为什么没有离开亲密伴侣,为什么不寻求其他帮助,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危险,为什么对家庭暴力会困惑不已,为什么难以控制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为什么会诉诸暴力,等等。〔9〕针对受虐妇女综合症,沃克提出了所谓经科学检验的七个标准。它们是:“(1)创伤事件的侵入性回忆;(2)过度觉醒和高度焦虑;(3)通常表现为抑郁、分裂、最小化、压抑和否认的回避行为和情绪麻木;(4)情绪和认知上的消极改变;(5)殴打者的权力和控制措施导致人际关系破裂;(6)身体形象扭曲和/或身体或物理上的抱怨;(7)性问题。”Lenore E. A. Walker,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 50.这些标准主要为了说明受虐妇女被迫反击的原因和心理。
受虐妇女独特的心理、行为反应,在法律上主要涉及杀害施暴者能否成立自卫。在美国,起初将受虐妇女杀夫与普通妇女杀人等同,不认可其成立自卫。〔10〕在1980年的莫里森诉布拉德利案(Morrison v. Bradley)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她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请求法院认定其成立自卫。法院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这样做将改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证据规则。See Nancy Ogle, Murder, Self-defense, and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in Kansas State v. Stewart, 243 Kan. 639, 763 P. 2d 572 (1988), 28 Washburn L. J. 400(1989), p. 402.后来,受虐妇女综合症逐渐获得司法实践认可。〔11〕在1988年发生的州诉斯图尔特案(State v. Stewart)中,妻子佩吉拒不认罪,声称射杀丈夫是为了自卫,她出示了她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证据,陪审团接受了自卫的理由,宣布佩吉无罪。See State v. Stewart, 243 Kan. 639, 763 P. 2d 572, 574-75 (1988).Quoted in Nancy Ogle, Murder, Self-defense, and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in Kansas State v. Stewart, 243 Kan. 639, 763 P. 2d 572(1988), 28 Washburn L. J. 400 (1989), p. 400.作为一个与科学有特殊关系的课题,美国各州法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此外,加拿大、英格兰等也在法律或司法实践中赋予受虐妇女综合症应有地位。例如,1988年加拿大在一起著名案例(R. v. Lavallée)中接受“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辩护”理由,并考虑在刑法中赋予其地位。〔12〕See Lee Stuesser, The Defence of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in Canada, 19 Man. L. J. 195(1990), p. 195.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接受因受虐妇女综合症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自卫,阻却违法性。“被殴妇女综合症或被殴妻子综合症已经被确认,并被压倒性地接受,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子类。”〔13〕Alexandria Patterson Tipton, PTSD Is a Limited Defense in Federal Court: Defendants with PTSD Generally Fail in Asserting the Affirmative Insanity Defense, and the Diminished Capacity Failure of Proof Defense Is Only Applicable in Limited Instances, 8 LINCOLN MEM’l U. L. Rev. 82 (2021), p. 87.
受虐妇女综合症并非没有受到质疑,但从来没有相似理论像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这样,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和支持。例如,父母疏远综合症就是一种极具争议的心理障碍,但迄今为止并未获得人们的支持。“父母中的一方操纵孩子诋毁和真正害怕另一方,不能成为正当理由。尽管父母疏远综合症在心理学话语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它还没有得到任何主要科学组织的认可……”〔14〕Alyssa G. Rao, Rejecting Unjustified Rejection: Why Family Courts Should Exclude Parental Alienation Experts, 62 B. C. L.Rev. 1759 (2021), p. 1760.又如,因不良关系导致的暴力虐待,也容易与受虐妇女综合症混淆。这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在暴力事件的不良关系模式中,受害者有行之有效的安全选择权利,可以相对顺利、安全地打电话给警察,获得保护令或脱离施暴者等,因而被害者受虐可以被认为没有行使她的安全选项,从而导致暴力的持续。而受虐待妇女综合症模式之所以能为受害者开脱,是因为她几乎没有选择权,乃至于因受虐待而出现精神健康问题。〔15〕See Heather Douglas, Stella Tarrant & Julia Tolmie, Social Entrapment Evidence: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Self-Defence Cases Involv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44 U. N. S. W. L. J. 326 (2021), p. 327.从司法实践来看,受虐妇女综合症常见于在婚姻关系中长期遭受家暴的妻子,男性因无有效实践数据支撑,一般认为不能形成这种心理及行为反应。
(二)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虽无受虐妇女综合症规定,但对特殊心理状态阻却犯罪却有规定。如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防卫人由于惶恐、害怕、惊吓而防卫过当的,不负刑事责任。”瑞士刑法第33条之2规定:“正当防卫人由于可原谅的惶惑或者惊惶失措而防卫过当的,不处罚。”韩国刑法第21条之(三)规定:“前项情形下,如其过当行为系在夜间或者其他不安的情况下,由于恐怖、惊愕、兴奋或者慌张而引起的,不予处罚。”另外,《日本盗犯防止法》第1条第2款规定:“虽然并没有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贞操的现在的危险,但由于行为人因恐怖、惊愕、兴奋或狼狈,而当场杀伤犯人的,不处罚。”〔16〕[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第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页。
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的特殊心理状态,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是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受到不法侵害的防卫人或者准防卫人(现场经历危险的人),后者的主体是受虐妇女;二是行为对象不同,前者的行为对象是率先发动不法侵害的人,或者“他人住所或他人看守的宅第、建筑物或者船舶”的侵入者,后者的行为对象是与行为人有密切关系的伙伴,通常是男性;三是产生前提不同,前者产生之前提,仅以行为人受到不法侵害或者住所、看守的宅第、建筑物及船舶遭受侵入为限,后者则为行为人长期遭受被害者暴力虐待;四是行为人与受害者的关系不同,前者之产生对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无具体要求,后者之产生以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特定的亲密关系为前提。
对于在特殊心理状态下,防卫人因防卫过当造成侵害,或者住所、看守的宅第、建筑物及船舶中人杀伤犯人,因何不处罚,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普遍认为乃阻却责任。在德国,学界通常主张,“被侵害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逾越了许可的紧急防卫界限的,其行为违法,但可依照《刑法典》第33条免除责任。”〔17〕[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对于韩国刑法第21条之(三)的规定,韩国学者认为,“超过必要性时,不成立正当防卫而成立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并不被正当化,而且根据情况成为责任减免或者免责事由。”〔18〕[韩]金日秀、徐辅鹤:《韩国刑法总论》,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日本学者也认为,《日本盗犯防止法》第1条第1款规定不处罚不是由于排除违法性,而是因为不具有责任。〔19〕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从学界表述可知,对特殊心理状态支配下的侵害行为之不处罚原因,有免除责任与无责任之别,两者有所不同。无责任乃指无谴责或者非难可能性的情形,缺乏故意、过失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其典型形态。免除责任则指无须谴责或者非难的特殊情形,包括责任内容未达到可罚性的情形。“立法者放弃提起责任非难,因为立法者认为,行为的不法内容、责任内容尚未达到可罚性的界限。”〔20〕[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60页。无论是免除责任与不具有责任,在性质上均属于阻却责任。
在德国,对刑法第33条规定的紧急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体系性定位,司法裁判一度持摇摆不定态度。起初,该情形被认定为一种排除刑罚的基础,法院确立了超过紧急防卫限度的违法性,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司法判例中才作为免责的根据。〔2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页。这表明对于紧急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性质,人们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不仅如此,引发争议的还有特殊心理状态本身。如前所述,德国刑法只是规定防卫人之惶恐等特殊心理状态,瑞士刑法则要求是可原谅的惶惑等特殊心理状态,韩国刑法限定为夜间或者其他不安情况下之特殊心理状态,而《日本盗犯防止法》则规定为侵入住宅等产生危险而滋生的特殊心理状态。就此而言,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并不如受虐妇女综合症那样相对清晰、明确。
(三)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状态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人的侵害行为受一定的心理支配。侵害心理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其形成具有复杂性,是由复杂、动态的心理结构决定的。本文所谓的特殊心理状态,乃因行为人遭遇长期或者特殊不法侵害或者危险等而产生,有别于常态侵害心理状态及精神错乱。
常态侵害心理通常表现为一般性的反社会或逆社会消极人格,基于狭隘、低级的情感需要,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绪易受刺激并波动等特征,不能正确调节自身与外界的矛盾冲突,以至于造成心理状态失衡,充其量只是一种性格缺陷。诸如成瘾者、纵火犯、商店扒手强迫症或患有孟乔森综合症等,尽管会体现出性格倾向,但都只是一种性格特征。〔22〕See Steven Goode, It’s Time to Put Character Back into the Character-Evidence Rule, 104 MARQ. L. Rev. 709 (2021), p. 750.性格缺陷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激情性心理状态。“‘激情’是一种迅猛爆发、激动而短暂的情绪状态,如狂喜、暴怒和绝望等。处于‘激情’的人理智大为减弱,认识和控制能力降低,容易导致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行为和严重后果,‘激情犯罪’是突然发生,但事后往往后悔不已。”〔23〕夏勇:《解读中外“激情犯罪”》,载《法学》2011年第5期,第127-128页。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状态要么指行为人遭遇长期暴力虐待产生的特定心理状态,要么指行为人遭受即时的特殊不法侵害或者危险等而产生的特殊心理状态,其范畴较之激情性心理状态要小,且行为人事后并不会后悔。另外,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只存在于特殊人群中,与常态侵害心理通常存在于普通人群中有所不同。
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状态也不同于精神错乱。例如,受虐妇女综合症虽为特殊的心理、行为反应,容易让人与暂时性精神错乱联系起来。但是,它并非精神错乱。首先,它不符合精神病的医学标准,因为绝大多数妇女杀死施暴者是危情下的应急反应,很难与精神错乱联系起来。其次,以精神错乱作为辩护理由,会给受虐女性开脱罪责提供机会,如杀害施暴者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让人无法接受。再次,若受虐女性被认定为精神错乱,会给其带来消极后果。“如果被虐待的女性用暂时的精神错乱作为辩护,她就被贴上了精神病标签,可能会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24〕Barbara A. Venesy, State v. Stewart: Self-Defense and Battered Women: Reasonable Perception of Danger or License to Kill, 23 Akron L. Rev. 89 (1989), p. 91-92.最后,精神病人不存在自卫问题,因为她无须对自己的任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受虐妇女并非如此。总之,“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证据现在可以接受,法院不再将受虐妇女综合症视为被告的一种精神缺陷。”〔25〕Eleanor Leontine Guidry Kitto, A Criminal Law Reform in Louisiana and Its Profound Impact on Battered Women Charged with Murder, 21 Loy. J. Pub. Int. L. 107 (2019), p. 133-134.同样,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特殊心理状态,显然与精神错乱等无责任能力之责任阻却事由不同。否则,刑法就没有必要就特殊心理支配下的防卫过当行为等,专门作出免除责任或者不处罚的规定。
三、特殊心理状态阻却犯罪的理论根据与成立条件
在英美法系国家,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宽恕理由被认可,与其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密不可分。对于阻却不法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范畴,尽管理论与实务中存在分歧,但相对而言有其明确的成立条件。而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则欠缺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成立条件也存在分歧,这也是其在理论与实务中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
(一)特殊心理状态阻却犯罪的理论依据
1.受虐妇女综合症阻却犯罪的理论依据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心理学依据和法学依据。心理学依据为受虐妇女具有受虐妇女综合症提供理论支撑,法学依据为具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女性的侵害行为正当化提供理论支撑。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心理学依据,主要是暴力循环理论与习得性无助理论。暴力循环理论是一种缓解紧张的理论,旨在解释为什么一名女性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忍受特定关系中的虐待。它由与反复发生的暴力循环相关联的三个不同阶段组成:“(1)紧张的建立伴随着不断上升的危险感,(2)严重的暴力事件,(3)爱的忏悔。”〔26〕Lenore E. A. Walker,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 94.第一阶段以轻微虐待为特征,并因此在双方之间建立紧张关系;第二阶段是野蛮暴力无法控制地爆发,打破紧张关系;第三阶段是殴打者的平静、表达歉意和请求原谅。当然,随着暴力虐待的持续,第三阶段可能会变得可有可无。“习得性无助”理论由马丁·塞利格曼博士提出,旨在从理论上解释暴力循环是如何让受害者陷入虐待关系中,乃至铤而走险的。沃克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受虐妇女不离开施虐者。沃克认为,陷入暴力循环的受害妇女会相信她们无法摆脱暴力,将停止努力避免虐待,并屈服于这种受虐模式。〔27〕See Kaley Gordon, Finding Favor: A Call for Compassionate Discretion in Cases of Battered Mothers Who Fail to Protect, 13 DREXEL L. Rev. 747 (2021), p. 771.但是,随着暴力无休无止地循环发生,受虐妇女会产生恐惧、焦虑、抑郁等情绪,这种情绪随着向公权力投诉无望的负面体验而不断强化。最终,“她们达到了恐惧、焦虑、抑郁的最高点,然后当她们接近愤怒、厌恶、敌意的顶峰时,她们变得不那么恐惧和抑郁了。”〔28〕Lenore E. A. Walker,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p. 78.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通常会采取强烈的反击措施来改变现状,以摆脱反复受虐产生的无助感,于是她们决意伤害施虐者。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法学依据,主要是通过重塑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为非对抗状态下受虐妻子杀夫的正当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受虐妇女综合症多为长期受虐妻子产生的特殊心理状态,并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杀害丈夫。以是否存在对抗性为标准,可将受虐妻子杀夫分为非对抗性杀夫和对抗性杀夫。在对抗性杀夫场合,妻子的反击应当说符合正当防卫条件。在非对抗性杀夫案中,由于施暴者无现时暴力行为,或者说不法侵害尚未发生,如何看待其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非对抗性杀夫案中受虐妻子杀夫成立自卫,需要符合紧迫性原则。关于紧迫性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紧迫意为“危急”(imminent),乃“即将发生”;二是认为紧迫意为“立刻”(immediate),乃“即时发生”。有学者认为,需要区分两者以恰当理解自卫的紧迫性。〔29〕See Whitley R. P. Kaufman, Self-Defense, Imminence, and the Battered Woman, 10 New Crim. L. Rev. 342 (2007), p. 344.也有学者认为,“即将发生”与“即时发生”并无严格界限。〔30〕See Paul H. Robinson, Criminal Law Defens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82 Colum. L. Rev. 199(1982), p. 217.理由在于:自卫的基本要素是诉诸武力的必要性,“即时”没有独立意义,只是必然性的“代理”。“即时”仅仅是衡量必要性的一种方式。之所以需要即时,是因为担心没有即时就无法保证必须采取防御行动来避免伤害,因而在没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可能没有必要。〔31〕See Whitley R. P. Kaufman, Self-Defense, Imminence, and the Battered Woman, 10 New Crim. L. Rev. 342 (2007), p. 344.换句话说,如果“即将发生”的不法侵害具有必然性,同样具有防卫的紧迫性。在英美国家的理论界与实务界,多数人对两者不加区分。〔32〕将“即将发生”作为紧迫性应有含义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如果认为紧迫性只包含“即时发生”,那么只有当丈夫开始实施暴力行为时,妻子才能自卫,等于变相剥夺了处于弱势方的妻子的防卫权,纵容“法向不法让步”;其次,从语义上看,“即时发生”既包括正在发生,也包括随时可能发生,为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侵害,允许妻子以“即将发生”的暴力为据对丈夫使用武力,是合乎情理的。
2.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阻却责任的理论依据
在大陆法系国家,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阻却责任的理论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如在德国,对于刑法第33条规定的不受处罚的防卫过当,学界通常认为因遭受侵犯而产生的情绪,属于不可期待的情形,让行为看起来能够免责。〔33〕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德]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239页。日本学者也认为,“因恐惧、惊愕、激奋狼狈而杀伤盗贼等的,不予处罚(《有关防治以及处分盗窃等的法律》第1条第2款)。这些都是基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者期待可能性的降低。”〔34〕[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但是,如果概括地将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确定为责任阻却事由,在缺乏相对明确、具体的条件限制的情形下,会不恰当地扩张责任阻却事由的范围,并给认定带来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在德国,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3条讨论的罪责,行为人的动机亦可起决定作用,进而比照适用第33条。〔35〕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在日本,针对《日本盗犯防止法》第1条第2款,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把相当于误想防卫或者误想过剩防卫的行为广泛地规定为责任阻却事由。”〔36〕[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责任阻却事由之如此扩张显然是不恰当的,引发争议在所必然。例如,对于误想防卫过当之阻却责任,德国的主流观点就持否定态度。“主流观点拒绝将第33条适用到误想防卫过当的案件中。理由是:第33条和第32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第33条就要求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紧急防卫情形。同样地,如果行为人的紧急防卫已经不成立,那么,就不得再对其免除责任。”〔37〕[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责任阻却事由不恰当扩张,还会模糊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界限。“盗犯等防止法的这一规定将根据刑法第36条本应属于防卫过当行为的一部分纳入正当防卫中,具有这样的意义;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使得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变得更不明确了。”〔38〕[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页。此外,责任阻却事由不恰当扩张还会带来其他问题。例如,对于反击家暴的伤害行为,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杀害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避险行为只能成立责任阻却事由,那就意味着该行为依然属于一种不法侵害。于是,施暴者或者第三人就可以针对避险人采取正当防卫,甚至可以行使直接致其死亡的特殊防卫权。这样的结论恐怕难以为人们所接受。”〔39〕陈璇:《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26页。这样的诘难可谓一针见血。
将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确定为责任阻却事由,还会给责任阻却事由的认定带来随意性。客观地说,造成个体处于惶恐、惊吓等心理状态,并不限于人的侵害行为,猛兽袭击、灾祸、事故等同样会造成惶恐、惊吓等心理状态,因而是极具包容性的。如果将所有遭遇不安情况而产生的特定心理状态均包括在内,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为,遭遇不法侵害时能否造成特殊心理状态及造成何种情状的特殊心理状态会因人而异,在缺乏必要条件限制的情况下一概以责任阻却事由论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惶惑、害怕或者惊恐——就像其他所有的情绪冲动一样,仅仅在罕见的边缘性情况下,才会排除确定符合规范的意志的能力,除此之外,从这个立场出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在超越紧急防卫时,它们才会导致不受刑罚处罚。”〔40〕[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页。
(二)特殊心理状态阻却犯罪之成立条件
1.阻却不法之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成立条件
美国各州判例对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宽恕理由的条件做法不一,存在较大分歧。于是,有学者提出最低限度原则(Minimum Principle)。“如果自卫规则允许在紧急危险情况下对这一原则作出例外,那么这种例外最好保持在绝对最低限度。”〔41〕Whitley R. P. Kaufman, Self-Defense, Imminence, and the Battered Woman, 10 New Crim. L. Rev. 342 (2007), p. 369.从美国司法实务来看,受虐妇女综合症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是典型且公认可成为宽恕理由的情形。从英美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来看,作为宽恕理由的最低限度受虐妇女综合症一般要符合以下条件。
(1)前提条件:存在持续性或长期性的暴力虐待
受虐妇女的习得性无助是经受持续或者长期暴力伤害,在反复求助无果的情形下逐渐形成的。例如,在美国的州诉柯利案〔42〕基本案情:卡蒂娜与丈夫雷纳尔多·柯利结婚近十年,长期遭丈夫暴力虐待。案发时妻子卡蒂娜与丈夫分居,当时她和母亲住在一起,丈夫同孩子住一起。一天卡蒂娜打电话问孩子们情况,得知有丈夫的两个朋友来访,遂决定回家。到家后她要求两位客人离开,招致丈夫向她扔了个汽水罐并进行威胁。卡蒂娜遂从床垫下取枪返回楼下,在丈夫穿鞋准备出门时开枪杀害了丈夫。See Brittany A. Carnes, State v. Curley: Modernizing Battered Woman’s Syndrome in Louisiana, 65 Loy. L. Rev. 223 (2019), p. 225-226.(State v. Curley)中,法院再次强调受虐者遭受长期虐待的重要性。“辩护律师没有对受害人长期虐待的情况进行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调查,仅仅因为他认为她所遭受的创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43〕Brittany A. Carnes, State v. Curley: Modernizing Battered Woman’s Syndrome in Louisiana, 65 Loy. L. Rev. 223 (2019), p.242.其中,辩护律师没有就丈夫长期虐待举证,是导致该案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将遭受持续性或者长期性暴力虐待作为受虐妇女综合症形成的前提条件,已基本获得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可。另外,持续性或者长期性暴力虐待之要求表明,若妻子遭受丈夫辱骂而非暴力虐待,无论辱骂时间多长、程度多么剧烈,其杀夫均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2)实质条件:遭受紧迫性暴力威胁
受虐妇女使用致命武力时,受到两个条件约束:一是遭受迫在眉睫的威胁;二是暴力威胁具有严重性。“当一个人面临遭受巨大伤害或死亡的选择,对造成巨大伤害或死亡的人使用致命武力,才是合理的。”〔44〕Abigail Finkelman, Kill Or Be Killed: Why New York’s Justification Defense Is Not Enough for the Reasonable Battered Woman, and How to Fix It, 25 Cardozo J. Equal Rts. & Soc. Just. 267 (2019), p. 291.为什么不要求受虐妇女脱离家庭躲避受虐呢?根据城堡主义,受虐妇女没有离开家庭的义务,这种不撤退规则得到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认可。〔45〕Ibid.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受虐妇女在家可以肆意而为。家庭也是施暴者生活的地方,若受虐妇女可以随意对丈夫发动攻击,也是不符合城堡主义的。正因如此,新城堡主义没有允许女性在家中随时使用致命武力自卫而不撤退,这在美国许多州的法律中也有体现。新城堡主义实质上明确了无义务撤退规则的行为规范,要求受虐妇女在紧迫时使用致命武力,即受虐妇女“必须先受到攻击,然后才会使用武力”。〔46〕Jeannie Suk, The True Woman: Scenes from the Law of Self-Defense, 31 Harv. J. L. & Gender 237 (2008), p. 268.
(3)限制条件:不适用于能合理脱离施暴者控制的受虐者
面对暴力虐待,如果受虐者具有脱离的合理机会,就难以形成“习得性无助”,也不会出现暴力循环,受虐妇女综合症将无从谈起。美国法院肯定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几项共同要素中,就包括“被告没有逃离或者阻挠伤害威胁的合理机会”。〔47〕Kelly Grace Monacella, Supporting a Defense of Duress: The Admissibility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70 Temp. L. Rev.699 (1997), p. 725.在上述柯利案的审判中,妻子卡蒂娜·柯利提出了对枪击事件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即其是在丈夫没有暴力虐待的情况下意外开枪,同时她又以丈夫长期虐待作为辩护理由。这种互相矛盾的辩护被控方驳回,成为败诉的重要原因。〔48〕See Brittany A. Carnes, State v. Curley: Modernizing Battered Woman’s Syndrome in Louisiana, 65 Loy. L. Rev. 223 (2019),p.244.那么,卡蒂娜为什么辩称意外开枪呢?原因在于她已经合理脱离丈夫控制,因为两人当时处于分居状态,卡蒂娜因故回家并在特定情境下杀死丈夫,谓之“意外”在情理之中。可见,已经合理脱离丈夫控制,才是造成卡蒂娜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的关键所在。据此,若妻子能够合理脱离,如丈夫提出离婚而妻子不愿意,致丈夫长期暴力虐待,妻子杀死丈夫时,不能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由主张成立正当防卫。
(4)主体与对象条件:受虐妻子与施暴丈夫
沃克提出受虐妇女综合症,起初关注的是受虐妻子,后来被扩展至家庭成员甚至所有人,便有了各种不同称谓,但在内涵和本质上并无实质差异。不过,适用主体的随意扩张,导致了多样化的后果,并引发众多争议。允许妻子之外的女性成为主体,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适用对象宽泛化,进而造成主体与对象无原则扩张,甚至有人提出男性也可成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男性成为主体,不但与受虐妇女综合症中的“受虐妇女”存在形式冲突,也缺乏事实与数据支撑,其科学性、合理性存疑。同时,如果不对主体与对象加以任何限制,是违背沃克创设该理论之初衷的,并会使之失去现实意义。从英美各国司法实践来看,将适用主体和对象限定为共同生活的妻子和丈夫基本上获得认可。
2.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成立条件
如上所述,尽管受虐妇女综合症成立范畴存在争议,但其最低限度形态阻却违法是得到公认的。然而,对于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之成立条件与范畴,大陆法系国家尚无定论,且通常将之作为特殊的责任阻却事由来对待。“对于该款的适用范围虽然存在争议,但被认为是根据欠缺期待可能性这种理由,而作为特别的责任阻却事由来规定的。”〔49〕[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这也使得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成立范畴更为多元化。
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来看,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成立条件,除需要存在紧急之不法侵害或者特定危险(主要指侵入住宅等产生的危险)外,几乎没有其他条件限制。但是,由于不加任何限制会导致其范畴过宽,极易与普通激情性心理状态混淆,故不少国家刑法通常会对特殊心理状态产生的境遇或者类型加以限缩。如韩国刑法规定的“在夜间或者其他不安的情况下”属于境遇限制,瑞士刑法规定的“可原谅的惶惑或者惊惶失措”属于类型限制,而日本法律将“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贞操的现在的危险”排除在外,无疑是另一种限制。德国刑法虽然未作特别限制,但理论上认为需要加以严格限定。“在说明第33条时,有各种心理性推论,这些推论使得对超过限度的行为人不受刑事惩罚的做法,必须追溯到‘强烈减弱的控制意志’或者‘心理上例外的情况’中去。”〔50〕[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页。多样化的标准必然导致多元化成立条件与差异化范畴,极大地削弱了特殊心理状态阻却犯罪的合理性。
由上可知,较之英美法系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成立条件相对简单、概括,这是导致其范畴不当扩张的主要原因,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相关规定在理论与实务中倍受争议的根源所在。因为,简单、概括的成立条件,会导致不同类型、情态的心理状态相混淆,影响人们的判断与评价。在大多数案件中,行为人受到攻击多少都会伴随着惊恐或者惶惑等攻击性冲动,若在此冲动下紧急防卫超过限度被允许,将导致权利滥用,违背立法本意。“因为被禁止的攻击性动力,需要根据一般预防的理由,通过一种刑罚威胁加以压制;否则,这种导致武力自卫权的报复,就不再能够制止住了,这一定会导致法和平的严重动摇。”〔51〕同上注,第660页。因此,如何进一步限定紧急防卫特殊心理状态之范畴就变得十分必要。
四、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状态的拓展与限缩
从两大法系国家判例均认可的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出发,以最低限度的受虐妇女综合症为基础,对受虐妇女综合症本土化时的拓展与限制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加以适当限缩,以迎合司法实践的需要,是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拓展与限制
理论上,最低限度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是可以拓展的。其拓展难以通过改变前提条件、实质条件和限制条件来达成,因为这可能会动摇阻却违法之立场,唯有立足于主体和对象条件才有可能。另外,英美法系国家无成文法之特征决定了作为自卫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缺乏一致性的规范标准,而成文刑法通常会对正当防卫及其成立条件等规定明确的标准。于是,来自自身(主体和对象)和规范两个不同角度的张弛,构成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横向(面的)维度与纵向(体的)维度。
1.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拓展
以最低限度原则为基础,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拓展主要是主体和对象的扩张。如果妻子之外的其他女性也有可能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那么将受虐妇女综合症扩张至妻子之外的女性无疑是可行的。同时,从临床经验和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医学根据和案例支撑,男性原则上不能成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
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限定为女性,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女性有着完全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且长期以来得到一定的科学数据和临床实践支撑,并被广泛认同。同时,将受虐妇女综合症限定于女性,也得到了英美国家司法实践普遍认可。“法院对受虐妇女综合症证词的广泛承认,承认受虐妇女的经历超越了特定妇女的经历。因此,作为评估她行为合理性的背景资料——案件的情况——关于受虐待妇女经历的证词应该被接受。”〔52〕Erica Beecher-Monas, Domestic Violence: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Equality in the Law of Evidence, 47 LOY. L. Rev. 81(2001), p. 127.其二,较之女性,男性被暴力虐待要少得多。既然如此,基于必要性、效果及司法成本等考虑,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向来针对一种现象而非个别情况,故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限定为女性符合法理与情理。“考虑到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远高于女性对男性的暴力,任何自卫法的进化都需要通过阻止无因的男性暴力和鼓励响应性的女性暴力来解决这种不平衡。”〔53〕Mary Anne Franks, Real Men Advance, Real Women Retreat: Stand Your Ground, Battered Women’s Syndrome, and Violence as Male Privilege, 68 U. Miami L. Rev. 1099 (2014), p. 1127.也许,受虐妇女综合症并非绝对为女性所有,但消除性别界限很可能是多年以后的事。〔54〕See Jacquie Andreano, The Disproportionate Eあect of Mutual Restraining Orders on Same-Sex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108 CALIF. L. Rev. 1047 (2020), p. 1051.当前,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主体限定为女性是较为妥当的。
当然,即使拓展主体范围,也必须限定于较受虐妻子更容易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女性,不能肆意加以扩张。这类女性通常要受两个条件约束。一是其与暴力施虐者关系密切,这是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基础。只有亲密关系中的伴侣造成的长期、深深的创伤,才会令受虐妇女产生精神后遗症,包括创伤后应激综合症。〔55〕See Magdalena Roxana Necula, The Eあect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8 Logos Universality Mentality Educ. Novelty Sect.:L.73 (2020), p. 80.二是具有较之正常女性更为不利的身心状况。身心健康较正常女性更差的女性,会更容易形成无助与过敏性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从而更可能产生受虐妇女综合症。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符合这样条件的女性,主要包括因故被监护、看护的女性等。在我国,社会转型、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养老和护理模式等的改变,造就了大量因年老、患病、残疾等需要监护、看护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她们与监护者、看护者关系极为密切,其地位,对监护者、看护者等的依附及摆脱受虐的能力等,与家庭中的受虐妻子极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长期遭受暴力虐待的被监护、看护的女性,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更容易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
需要注意的是,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拓展适用时,女性与暴力虐待者之间不应存在血缘性亲缘关系。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虽然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但血缘性亲缘关系与夫妻关系明显不同;其次,在婚姻家庭中,除夫妻间外打骂多发生于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且多因家庭琐事或者教育方式等引发,粗暴的教育方式、不和谐相处的承受者与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在心理、行为反应上会决然不同;再次,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直系血亲、近亲之间的杀戮行为难以为社会容许,故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间,以受虐综合症作为杀人的正当化理由,缺乏社会伦理道德基础;最后,从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来看,认可女性与施虐者存在血缘性亲缘关系并形成受虐妇女综合症,并未获得共识。
2.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规范限制
在我国,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违法阻却事由,需要受刑法对正当防卫规定的约束。根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故形式上应当将非对抗性反击行为排除在正当防卫之外。不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正当防卫时间等作了扩张性解释,即强调紧迫性在正当防卫时间认定上的功能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吸收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合理内核。例如,《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这里的“现实、紧迫危险”,显然不同于传统刑法理论认定正当防卫时间时所要求的“正在进行”,因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现实侵害而非现实危险。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现实、紧迫危险”是客观事实而非防卫人主观认识。另外,何种“危险”不影响对正当防卫时间的理解,但对防卫限度会有影响。例如,如果防卫的后果是剥夺生命,那么所要求的必须是“现实、紧迫的危险”,必须具有一定的严重性。
《指导意见》第6条有关正当防卫时间的某些规定,亦有不同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之处,总体上看属于限制性规定。《指导意见》规定,“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该规定与上述“紧迫性”要求之规定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不法侵害的紧迫性。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现实、紧迫危险”不要求有先行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则必然要求存在先行不法侵害,否则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无从谈起。两者之所以相辅相成,是因为“现实、紧迫危险”是不法侵害客观现实化的危险状态,需要不法侵害行为人有一定的行为表现,尽管不是不法侵害本身,但至少与不法侵害关联,如用刀杀人的找刀、掏刀行为等。而不法侵害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则不需要实施用刀杀人的买刀、找刀行为等关联行为,即使不法侵害完全停止,如不法侵害人暂时休息,也可以认定为不法侵害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可见,“不法侵害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拓展了不法侵害的“现实、紧迫危险”。
《指导意见》规定的暂时性要求,虽然对刑法所规定的“正在进行”作了扩张解释,但较之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要更严苛。“暂时”本意指“短时间的”,〔5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31页。虽然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度,但从语义上看应当指相对短暂的、随时可发生的,其与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所要求的“即将”截然不同。根据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不能将“即将发生”简单地理解成时间上的“暂时性”,其有效性与不法侵害的持续性直接相关。如果不法侵害具有持续的可能性或者条件,即使时间上相对较长而不具有暂时性,也可以理解成“即将”。正因如此,“即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较大的包容性,美国学者罗宾逊甚至主张十天之内发生亦可认定为即将发生。〔57〕See Paul H. Robinson, Criminal Law Defens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82 Colum. L. Rev. 199(1982), p. 217.显然,《指导意见》规定的“暂时”不可能包括数天或者十数天这样长的时间,具体指多长时间有待司法解释明确。总之,较之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指导意见》关于“暂时”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正当防卫的成立范畴。
(二)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范畴之限缩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对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较为笼统、概括,如何加以限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罗克辛所谓的“强烈减弱的控制意志”或者“心理上例外的情况”,是对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加以极端限缩的体现,并未发挥其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功能。在限制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的适用条件上,英美法系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1.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范畴限缩的基础与方向
德国最高法院刑事判例认可诸如长期遭受暴力虐待等而进行的紧急防卫,即使超过限度也可以根据德国刑法第33条之规定不予处罚。“当一种长期以来被预感到的和所害怕的事件,在发生时从精神上击倒行为人时,这名行为人也能够惶惑、害怕或者惊恐地做出反应。另外,这种超过限度的情况所具有的可预见性和可避免性,并不一定排除诉诸第33条;因为这个行为人没有义务来避开这种能够产生情绪冲动的攻击。”〔58〕[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59页。其中的“长期以来被预感到的和所害怕的事件”,与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所要求的受虐妇女遭受长期暴力虐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无疑为限缩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范畴奠定了基础。
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适用受虐妇女综合症引发争议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被胁迫经历也会产生焦虑障碍,按理可成为宽恕理由。但是,反对者却担心妇女受胁迫范畴过于广泛,容易导致被滥用。“法院一直不愿意将受虐妇女综合症延伸到对胁迫的辩护中,因为该理论可以为那些与施暴者一起对无辜的人犯罪的受虐妇女开脱。”〔59〕Alafair S. Burke, Rational Actors, Self-Defense, and Duress: Making Sense, Not Syndromes, out of the Battered Woman, 81 N. C.L. Rev. 211 (2002), p. 211.又如,女性趁施虐者睡觉等施加伤害,能否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由主张宽恕亦存在分歧。“最棘手的自卫问题出现在非对抗性杀戮的案例中——女性在挨打之前或之后进行回击,或者最具争议的是,在施虐者睡着的时候进行回击。”〔60〕Kit Kinports, So Much Activity, So Little Change: A Reply to the Critics of Battered Women’s Self-Defense, 23 St. Louis U.Pub. L. Rev. 155 (2004), p. 156.此外,在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判断标准等方面,判例也有不同意见。上述争议无疑给受虐妇女综合症及自卫认定造成一定困惑。“由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原因,检察官们还受到了一系列错误信息的困扰。”〔61〕Amber Simmons, Why Are We So Mad? The Truth behind “Angry” Black Women and Their Legal Invisibility as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36 HARV. B. L. LAW J. 47 (2020), p. 69.不过,受英美法系国家不成文法特点及理论体系等影响,造成上述问题是值得理解的,毕竟没有其他合适途径可供选择。
成文法系国家则不然。对于最低限度的受虐妇女综合症之外的其他特殊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即使不能通过违法性判断其性质,也可以在有责性的范畴内加以解决。就最低限度之外的受虐妇女综合症而言,很多时候确实不符合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时间条件,乃至于难以在定性时通过判断是否具有违法性寻求解答。此时,如果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受虐妇女综合症认定为违法阻却事由,容易导致正当防卫的不当扩张与紧急权的滥用,背离刑法的立法目的。正因存在规范限制,因而对成文法系国家而言,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本土化不能限于违法阻却事由层面上的探究。例如,反击者因长期遭受暴力虐待产生创伤性应激障碍,有着特殊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若不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就不能阻却违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击行为不正当。在违法阻却事由之外,仍存在排除犯罪性的路径。
从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的情况来看,在不能认定为阻却违法的情形下,认定为阻却责任而排除犯罪性,或者认定为责任减轻事由,是具有可行性的。只不过,我们不能像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那样,对阻却责任的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规定得过于宽泛,而是需要加以一定限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不同于一般的情绪障碍和精神错乱,而是一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属于焦虑障碍,是由于“暴露在极端创伤性应激源中”而导致的,包括经历或目睹死亡威胁或对自己或他人的严重伤害。〔62〕Se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p. 424.这意味着情绪受到压迫、被胁迫的经历,或者经历死亡威胁等严重伤害是产生焦虑障碍的根本原因。因此,某种特殊心理状态成立责任阻却事由,其前提必须是在被压迫、被胁迫的特殊经历下产生的,或者经历死亡威胁等严重伤害后产生的。相应地,普通不法侵害导致的惶恐、惊吓等心理状态,不能成为阻却责任的事由。
2.阻却责任的紧急防卫特殊心理状态范畴之具体限缩
由于最低限度的受虐妇女综合症之认定条件相对明确、具体,成立自卫并作为宽恕理由也基本成为定论,故而对那些存在争议的特殊心理状态,在不宜认定为违法阻却事由的情形下,若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可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在确定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范畴时,需要区分其与阻却违法的最低限度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界限。从后者的适用条件来看,它们之间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前提条件是有因性,即存在持续性或长期性的暴力伤害,这对认定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同样重要。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也不是无故的,而是有因的。〔63〕这里的“有因”,是指除遭受不法侵害本身之外的其他原因,否则就不能称为有因。因为任何人遭受不法侵害,心理状态多少都会与正常状态有异,不能成为缺乏期待可能性的理由。德日等国法律规定之所以随意、不确定,在于未区分有因与无因之特殊心理状态及不同类型的特殊心理状态。如德国、瑞士刑法规定就采取无因论。无因论会导致不法侵害、紧急危险导致的特殊心理状态也被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会架空违法阻却事由,引发评价上的混乱。与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因”不同,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因”不一定是暴力伤害,即使是威胁或者要挟也是可以的。同时,即使是暴力伤害也不要求具有持续性或长期性。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有过遭受暴力侵害的经历等,足以导致难以期待行为人不实施伤害行为的,都可以阻却责任。
阻却违法的受虐妇女综合症须以存在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为实质条件,且通常采取客观标准,对于采取主观标准是否成立自卫则存在较大争议。之所以存在这种区别,原因在于两者的评价依据不同。客观标准有赖于事实性测试,主观标准以评价性测试为据。“事实性测试要求陪审团考虑被告是否突然和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评价性测试要求陪审团参照理性人或普通人的标准来考虑被告是否应该失去自制力。”〔64〕Graham Virgo, Provocation Restrained, 64 Cambridge L. J. 532 (2005), p. 532.客观标准是针对事实之测试,较为客观、明确;比较而言,主观标准强调防卫人主观认识的合理性,本身较为模糊、笼统,自然会引起争议。另外,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主观上认为存在不法侵害或者威胁,事实上并不存在,属于假想防卫,理论上通常认为不能阻却违法。因此,当不存在客观的暴力虐待事实或者威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存在且符合理性人或普通人标准,虽然不阻却违法性,但在不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伤害行为的情形下,可以阻却责任。
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果行为人能准确预测暴力事件,通常可以认定为自卫并成为宽恕理由。“除非理性的人受到了长期的虐待,因此能够准确地预测暴力事件,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一个人睡觉时攻击他。”〔65〕Amanda Clough, Battered Women: Loss of Control and Lost Opportunities, 3 J. Int’l & Comp. L. 279 (2016), p. 282.例如,丈夫每次酗酒回家都会对妻子实施严重的暴力虐待,当妻子发现丈夫酗酒回家时将其杀死,可以成立自卫。理由在于:对于妻子而言,丈夫酗酒回家必然会实施严重的暴力虐待,故只要丈夫酗酒回家时,妻子预测其会实施严重的暴力虐待无疑是准确的,故伤害丈夫可成为宽恕理由。不过,这种情况由于不存在不法侵害,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前提条件。如果对妻子实施伤害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可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而不处罚。〔66〕在邓玉娇案中,法院认定邓玉娇成立防卫过当,并以她存在自首情节和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为由,依法判决免予刑事处罚。对此,有学者从防卫人的立场出发,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参见何萍:《论特殊防卫中的犯罪侵害——兼评邓玉娇故意伤害案》,载《法学》2009年第8期,第159页。笔者认为,邓玉娇遭邓贵大等人强求异性陪浴,甚至百般纠缠不让离开房间,在无法脱身且继续遭邓贵大等人猥亵、纠缠的情形下,期待邓玉娇不实施伤害行为不具有可能性,故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不处罚较为合理。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限制条件是,不适用于能合理脱离施暴者控制的受虐者,这是以受虐者与施虐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为前提的。在成立责任阻却事由的场合,由于不需要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且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特殊心理状态是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根据的,因而对能否合理脱离施暴者控制需要另当别论。如果行为人无故遭受不法侵害者刻意、任性的暴力干扰、纠缠,且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摆脱施暴者的暴力干扰、纠缠,就不能期待他不对不法侵害者进行伤害,此时可以阻却责任而不处罚。例如,甲见乙便会遭乙戏弄或者暴力殴打,为避免与乙碰面而有意规避,但乙故意制造机会令甲无法正常回避,若甲因无法正常回避而见乙并实施伤害,就可被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而不处罚。
从主体和对象条件来看,如果不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要求,在对其不实施伤害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形下,均可认定其为责任阻却事由。这意味着,受虐妻子,受监护、看护的女性之外的其他女性及男性,均可成为阻却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的主体。当然,如果是受虐妻子,受监护、看护的女性,在其他条件不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要求的情形下,其不实施伤害行为不具有可期待性,理当阻却责任。
五、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
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人提出对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等特殊心理状态,在减轻责任事由的框架下进行辩护更合适。“受虐待的妇女故意杀人将不得不依靠减少责任来辩护。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更适当的辩护,因为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妇女并不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而且往往不会被激怒而杀人。”〔67〕Graham Virgo, Provocation Restrained, 64 Cambridge L. J. 532(2005), p. 534.在最低限度原则的范围内,认定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宽恕理由阻却违法,将最低限度的其他特殊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作为减轻责任的辩护理由,是英美法系国家相对通行的做法。比较而言,对于受虐妻子在独特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反击行为,我国司法实践的定性相对单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准确认定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需要“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这里的“防卫因素”显然属于量刑情节。受虐妻子的独特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当属于防卫因素,根据《意见》规定乃量刑情节,其性质与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存在本质不同。对此,有学者指出,“处理此类案件局限于量刑情节的考察并不妥当,并且司法机关在否定正当化事由之适用后又承认行为具有防卫因素也显得矛盾。”〔68〕隗佳:《责任阻却性紧急避险的厘清与适用——以受虐妇女杀夫案为视角》,载《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131页。《意见》一概将受虐妻子的特殊心理状态规定为量刑情节,对受虐妻子杀夫的定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判例一边倒地将受虐妻子杀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与《意见》规定不无关系。这样的规定,根本没有从受虐妻子的角度审视其杀夫的正当化问题,容易令人误认为“当女性拿着枪或刀应对这些威胁时,她们被视为使用了过度武力来保护自己”〔69〕Michael R. Slaughter, Th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and Self-Defense, 1 Women’s L. J. 78 (1997), p. 79.。我国司法实践将受虐妻子杀夫一律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单一的定性恰恰忽视了从受虐妻子的角度看问题,不利于保护防卫人权利,既不符合刑法规定,也有违法益保护原则。
那么,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包括哪些具体情形呢?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之外的特殊心理状态,均可成为责任减轻事由。以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为据,结合上述分析与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减轻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遭受长期不法侵害,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趁不法侵害人不备实施伤害行为的;主观上认为存在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并实施伤害行为,但其主观认识缺乏合理性的;在缺乏准确预测遭受暴力威胁的情形下,主观想象可能遭受暴力威胁或者侵害,趁不法侵害人睡觉、不备时,实施伤害行为的;在遭受暴力侵害后,趁不法侵害人睡觉、不备等实施伤害行为的;能够正常摆脱不法侵害人暴力威胁,如不法侵害人要求离婚却拒不离婚,或者正常回避不法侵害人便可避免冲突,拒不回避而伤害不法侵害人的;长期或持续遭受不法侵害人要挟等,再次遭受要挟而实施伤害行为的,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与被害人过错有所不同。被害人过错也会导致行为人产生特定心理状态,其在广义上应当包括受虐妇女综合症等一切特定心理状态。狭义的被害人过错属于量刑情节,并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由于量刑的类型和程度存在差异,不同的被害人过错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量刑,因而被害人过错原则上无须受相关条件限制。因此,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较之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要宽泛。本文所谓的特殊心理状态为外因性的,即被害人曾对行为人有过错行为,如暴力虐待或者威胁、要挟等。这种既往过错会影响行为人并令其产生特定心理状态。当被害人再次实施不法侵害时,行为人在特定心理状态下实施伤害行为,若不阻却违法或者责任,应当作为从宽处罚事由。被害人过错则不限于此。一方面,即使被害人过错是外因性的,如被害人对行为人曾有过暴力虐待等行为,若行为人主动挑起纷争而伤害被害人,也难以磨灭被害人曾有过的暴力虐待等过错,但此种情形不能认为具有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与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不同的是,被害人过错可以是原生性的,即未曾对行为人有过错行为,只要被害人实施不法侵害或者挑衅等不当行为,能让人产生不满情绪或心理,对行为人而言就意味着被害人存在过错,但此时特殊心理状态及其行为反应则无从谈起。总之,减轻责任的特殊心理状态受特定条件限制,应属于特殊的被害人过错。
六、结语
作为最强有力的部门法,刑法不但要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为基本机能,更要将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置于核心地位。〔70〕参见彭文华、傅亮:《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刑法学新理念》,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1期,第16页。就正当防卫成立而言,从不同的安全立场出发,可能会有不同见解。我国司法实践将丈夫施虐及对妻子的影响作为量刑情节,相对强调不法侵害人的安全。英美法系国家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将特殊心理状态规定为责任阻却事由,则更侧重防卫人的安全保护。从刑法理性的角度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通过严格限制适用条件,将受虐妇女综合症酌情运用于正当防卫制度中,较好地解决了受虐妇女伤害施暴者的正当化问题。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虽对紧急防卫之特殊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的性质作了规定,但总体来看较为笼统、概括,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比较而言,我国司法实践对受虐妻子的特殊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仅以量刑情节论,让人感觉略有重侵害人权益保障而轻防卫人安全诉求之嫌。
在理论上,需要注意对阻却犯罪的特殊心理状态的误读、曲解。有学者反对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认为这样做“忽视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正当防卫制度上存在的差异。因为要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引入正当防卫之中,必须考虑受虐妇女主观上对于不法侵害的认知,这恰好吻合了加拿大刑法规定。”〔71〕王俊:《反抗家庭暴力中的紧急权认定》,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第121页。另有学者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属于免责事由。“确立‘被虐妇女综合症’的作用在于降低‘紧迫性’的判断标准,使之由‘理性的一般人’转变为‘具体的行为人(精神病人)’,因而仅仅是一种免责事由,而非正当化事由……”〔72〕潘星丞:《正当防卫中的“紧迫性”判断——激活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教义学思考》,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第33页。还有学者对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自卫理由持怀疑态度,认为将施暴者杀伤的行为有成立正当化紧急避险的余地。〔73〕参见陈璇:《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17页。通过文中分析,可知这些观点均存在一定问题。以加拿大刑法规定为反对理由不可取,因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缘起于美国。而且,受虐妇女杀夫成立自卫,要求主观上对不法侵害有认知,在普通正当防卫认定中也同样需要。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一律认定为责任阻却事由,则明显以偏概全。认为受虐者杀伤施暴者成立紧急避险亦失之偏颇,且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紧急避险不能针对危险来源(如制造危险者)。
——从《刑法》第13条之“但书规定”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