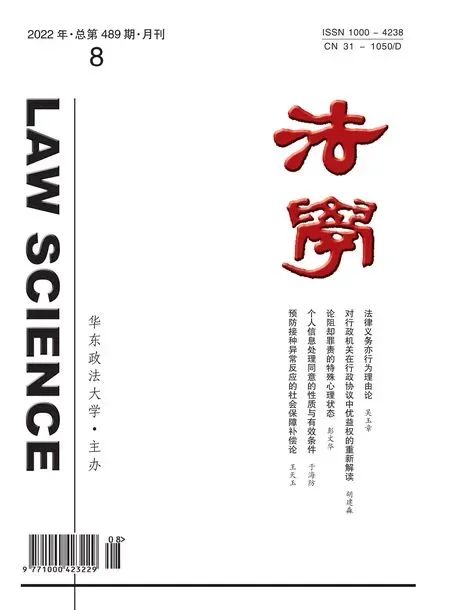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社会保障补偿论
●王天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们普遍将希望寄托于疫苗,期盼依靠以往战胜天花、霍乱等传染病之经验,借助疫苗实现群体免疫。着眼于全球化的公共卫生势态,疫苗是最有力的传染病防治措施之一。此次疫情使得预防接种提升到了新的量级,可能成为周期性的防疫手段。在此背景下,关切及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以规范方式接种合格疫苗造成受种者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的极端情形。〔1〕我国《疫苗管理法》第52条第1款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界定是“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以此为基础,该法以“反+正”的列举方式限定了预防接种的异常反应范围:反面列举是该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排除疫苗异常反应的情形,第一类是可能的过错情形,包括疫苗质量问题、接种单位违规操作、受种者及其监护人未如实提供健康信息,第二类是特定的无过错情形,包括接种一般反应、偶合发病、心因性反应。正面列举是该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了应给予补偿的异常反应情形,包括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世间无完美的疫苗,有效的疫苗亦存在发生异常反应的风险,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严重损害人体。〔2〕世界卫生组织将合格疫苗发生异常反应的比率划分为:非常常见≥10%、常见≥1%并<10%,症状如发热、皮疹等免疫反应;不常见≥0.1%并<1%、罕见≥0.01%并<0.1%、非常罕见<0.01%,症状如严重过敏反应,通常需要临床处置。See WHO,Vaccine Safety Basics, 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tech_support/Part-1.pdf?ua=1, p.22,last visit on Feb. 20, 2022.该异常反应比率须根据具体疫苗种类进行监控。例如,我国在2009年末至2010年初防控甲型H1N1流感期间,流感疫苗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万分之一,严重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约为百万分之一。参见《2009年11月份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卫通〔2009〕 21号)、《2010年1月份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卫通〔2010〕4号)、《2010年2月份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情况》(卫通〔2010〕5号)。世界卫生组织主张快速有效地应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否则会削弱公众对疫苗的信心,最终对免疫覆盖和患病率产生显著影响。〔3〕See WHO, Global Vaccine Safety, 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initiative/detection/AEFI/en/, last visit on Feb. 20, 2022.为此,主要国家均建立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制度,〔4〕有研究团队于2019年完成了对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的调查,确定其中有25个国家或地区施行了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See Mungwira RG, Guillard C, Saldaña A, et al., Global Landscape Analysis of No-Fault Compensation Programmes for Vaccine Injuries: A Review and Survey of Implementing Countries, 5 Plos One 15 (202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3334, last visit on Feb. 20, 2022.作为抵御疫苗损害风险的安全网。〔5〕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安全全球咨询委员会(GACVS)将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视为维系防疫计划的重要措施,能够为疫苗损害的补偿提供明确的标准和渠道,提升补偿的充足性和公正性。See WHO,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mes,https://www.who.int/vaccine_safety/committee/topics/pharmacovigilance/Dec_2018_VICPs/en/, last visit on Feb. 20, 2022.我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始于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34号,以下简称《条例》)。鉴于几次影响重大的疫苗事件,〔6〕我国此前多次暴发疫情安全事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案例包括2006年山东和河北的糖丸事件、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2014年深圳泰康乙肝疫苗事件。相对于疫苗事件造成的人身伤亡,公众因此产生的恐慌心理影响更为普遍,如在乙肝疫苗事件中,“对疫苗不良反应的恐惧被非理性地放大了,这有可能对乙肝防治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参见黄永明:《乙肝疫苗:被放大的恐惧》,http://www.infzm.com/content/97403,2022年2月14日访问。学界对该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检讨,但仍有一些学理和实践问题有待解决。
一、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学界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补偿责任的性质、补偿责任与民事过错责任的衔接、补偿标准和程序、制度走向等,总体上分歧大于共识。在立法层面,从国务院2016年修订《条例》(国务院令第668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下简称《疫苗管理法》),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若干改进,客观上回应了一些学界反思。但即便如此,此项制度在体系构建和学理阐释上并未完全成型。
(一)《疫苗管理法》新规对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的重塑尚未完成
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采取的是“顶层设计+地方落实”的结构。《疫苗管理法》出台前的“顶层设计”是国务院《条例》,各省级政府制定补偿办法予以落实。由于2005年《条例》第46条仅规定了应补偿的异常反应情形、一次性补偿原则及第一、二类疫苗损害的补偿主体,〔7〕《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2005)第46条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国家鼓励建立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受种者予以补偿的机制。遗留了较大的立法空间,未给予地方补偿办法充分的约束和指导,导致各地具体补偿标准和程序差别过大,个别规定与补偿的宗旨不符。有学者研究了除新疆外的30个省级地方补偿办法,发现补偿金额和给付时间的地方化问题突出,如上海、湖南、海南等地规定了医疗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死亡补偿金等分项计算补偿金额,但总额受限;北京、江西、广西等地规定了分项计算而总额不受限;吉林、河北、江苏等地规定了死亡和严重残疾不分项计算;浙江、重庆、云南等地规定了全部不分项计算,仅设总额标准。〔8〕参见冯珏:《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互动——以我国疫苗接种损害救济体系建设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63-1464页。补偿给付时间亦不统一,“有的省份甚至为了自身工作的便利,限定接受补偿申请的时间”,如湖南、河南。〔9〕同上注,第1465页。《湖南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第17条规定,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季度最后一周前将本辖区申请补偿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并加盖公章后,与第16条规定的材料一起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河南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第25条规定,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分别于每年5月底、11月底前,将本辖区申请补偿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材料审核、汇总并加盖公章后,与第24条规定的材料一起,分两批集中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2019年《疫苗管理法》针对前述问题取消了“一次性补偿”的规定,代之以“及时、便民、合理原则”,并将“补偿范围、标准、程序”的立法层级提升到行政法规层面,〔10〕参见《疫苗管理法》第56条之规定。相当于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补偿权配置,把补偿立法的核心内容收归中央,收紧了地方立法的空间。尽管此项新规转化为具体条文和执行措施尚待时日,但无疑将重塑各地现行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自上而下的体系建构仍处于进行时。
(二)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制度的衔接问题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是无过错补偿,《疫苗管理法》和《条例》均规定“相关各方均无过错”。因疫苗质量问题或接种不规范等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不属于异常反应,受种者应通过民事责任体系获得救济。由此形成了基于“过错”划分的民事责任体系与国家无过错补偿制度之“二元并列”结构。
有学者从“过错+因果关系”的角度审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补偿制度“以‘无过错’作为反面实质性要件,会不当扩大除外责任的适用范围”,带来三方面的影响。首先,经审批合格上市的疫苗难以证明存在过错;其次,受种者的与有过失被无过错补偿制度所排除;最后,如果接种单位的过错与受种者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会被国家补偿制度排除。〔11〕参见冯珏:《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互动——以我国疫苗接种损害救济体系建设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49-1455页。这种判断是基于《条例》对无过错责任极为严格的限定,但《疫苗管理法》在“无过错”原则的前提下对两个体系的因果关系边界作出了调整,在第56条第1款增加了“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规定,扩大了补偿适用的范围,使受种者在“难以证明生产者过错”及“接种者过错与损害结果无关”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补偿,从客观上限缩了“不当扩大的除外责任”。〔12〕在《疫苗管理法》出台前,已有部分地方引入了“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补偿标准,如《重庆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原则上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理”,《贵州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第12条规定“补偿相应金额的20%”。亦有部分法院根据“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支持补偿诉求。如在“赵某1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高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受种者接种狂犬疫苗后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经诊断为病毒性脑膜脑炎,急性散播性脑脊髓炎,消化道出血,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能排除与狂犬病疫苗接种有关”。法院认定该案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导致受种者损害的案件,由于当地补偿办法并未规定“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情形,所以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判定生产者按照50%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本案属于第二类疫苗致害案件,接种操作无过错,且涉案疫苗为合格产品。如果按照严格的因果关系,那么“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既不支持无过错补偿,也难以证明生产者存在过错,受种者可能落入两种救济方式未能衔接的制度夹缝。法院依据鉴定结论实现了因果关系推定,虽然仅支持了部分补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救济。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3806号民事判决书。
《疫苗管理法》将“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基层实践提升为顶层设计,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制度的衔接关系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无过错补偿制度的边界将因“盖然因果关系”而扩张,吸收“无因果关系的接种者过错”和“潜在的生产者过错”,统一遵循无过错标准予以补偿,由此填补了《条例》下因“除外责任扩大”导致的两个体系的衔接空档。但是,因果关系的边界调整不能彻底解决体系衔接问题,较为突出的就是两个体系给付标准的落差。虽然《疫苗管理法》已明确“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补偿标准与确定性异常反应相一致,但现实问题是无过错补偿标准在整体上比民事赔偿责任的标准低很多。在一起案例中,民事赔偿给付136万元,无过错补偿制度给付25万元。〔13〕参见冯珏:《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互动——以我国疫苗接种损害救济体系建设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61页。如果两个体系的救济能力相差如此悬殊,二者势必难以仅通过因果关系的扩张而实现有效衔接。受种者一方基于经济理性会背离无过错补偿制度,可能将“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明生产者(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存在过错的证据,从而将案件推向医疗事故纠纷,导致再次陷入证明过错的窠臼,消减制度进步的成果。〔14〕补偿金额的不充分与地域悬殊必将极大地抑制补偿计划救济功能的发挥,使国家设立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价值立场和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受种者也会更倾向于从民事责任体系中获得救济。同上注,第1477页。
(三)无过错补偿的责任性质和改革取向存在较大学理分歧
有学者主张,预防接种是国家强制行为,国家直接补偿是社会保障。〔15〕参见刘洪华:《我国疫苗伤害救济的路径选择和制度构想》,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140页。有学者提出,社会补偿虽为社会保障之一种,但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重要区别,社会补偿权的实质是实现平等权,“目标是恢复作为消极权利的原权利”。〔16〕娄宇:《论社会补偿权》,载《法学》2021年第2期,第99页。也有学者认为,补偿不是社会保障性质,而是国家或政府对合法行为所致损害的行政救济,“因社会影响重大,政府作为实施者对异常损害予以合理补偿。生产者基于其受益对风险损害予以合理补偿。”〔17〕刘士国:《突发事件的损失救助、补偿和赔偿研究》,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第72-73页。在补偿责任的学理阐释上,有学者认为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属于“公益牺牲补偿”,依据德国法上的“公益牺牲补偿请求权”(Aufopferungsanspruch),专门针对人民非财产性权利受损的情形,并且区别于“衡平补偿”(Billigkeitsausgleich)或曰“社会补偿”(soziale Entschädigung)。〔18〕参见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31页。另有学者提出,强制预防接种补偿是“公法上的危险责任”(dieöあentlich-rechtliche Gefärdungshaftung),“能避免公益牺牲补偿说的空洞”。〔19〕伏创宇:《强制预防接种补偿责任的性质与构成》,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47页。
鉴于制度尚未定型,学界形成了两种相异的改革取向:主流意见是强化补偿功能,但在实施方案上存有分歧。部分学者提出“基于损害结果的国家责任”,主张从过错责任转向结果责任,即只要发生了疫苗异常反应就予以补偿,不考虑是否存在过错。〔20〕不论原因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只要作为行政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损害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那么国家或公共团体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参见张新宇:《预防接种致害国家责任体系的完善》,载《法学》2019年第8期,第100页。这一思路契合了社会保障的定位,有学者主张“社会补偿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给付”,社会补偿的主体是政府或其授权组织机构。〔21〕参见林嘉、张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补偿制度的构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9页。另有学者提出“补偿的基金制改革”,参考美国疫苗损害补偿计划(VICP),借由基金将补偿责任从国家责任体系中拆分出来,通过疫苗特别税来强化补偿的财务基础,以实现降低门槛、提高待遇的目标。〔22〕参见冯珏:《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互动——以我国疫苗接种损害救济体系建设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77页;刘洪华:《我国疫苗伤害救济的路径选择和制度构想》,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142页。此外,相对较少的意见是强调行政补偿责任的补充功能,“有必要在制度上鼓励‘先民事、后行政’以及‘先行政赔偿、后行政补偿’的救济方式。”〔23〕伏创宇:《强制预防接种补偿责任的性质与构成》,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55页。
(四)财政补偿转向保险补偿的试点及其局限性
在学界讨论强化政府对疫苗损害的社会保障或行政救济的同时,实务层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政府补偿责任保险化倾向,即政府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将原本由财政负担的疫苗损害补偿责任转变为保险公司承担的理赔责任。早在2014年,卫计委牵头的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4〕19号)就提出“鼓励和推进地方通过商业保险解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问题”。自2016年起,卫计委在地方开展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试点,同时国务院在《条例》第46条修订中明确了“国家鼓励建立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受种者予以补偿的机制”。各地试点的核心均是将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由“财政补偿”转变为“保险补偿”。江苏试点只针对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依据《关于改革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的通知》(苏卫疾控〔2016〕2号),省级财政通过政府采购,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疫苗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在发生异常反应后,受种者持鉴定结论等材料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保险公司按现行补偿标准予以一次性补偿。广东试点将保险分为基础保险和补充保险,其中基础保险对应第一、二类疫苗补偿的政府责任和企业责任,《广东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实施方案》(粤卫规〔2018〕3号)规定“基础保险为政府统一购买及疫苗企业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此外,补充保险是“受种方、接种单位等根据需要,自愿、自费选择购买的商业保险”,以便提高补偿额度。
政府对第一类疫苗的补偿责任保险化的主要优点是补偿程序不再受政府财政制度的限制,受种人可更为便捷地获得补偿。但就目前试点经验而言,“财政补偿”转向“保险补偿”带来的改进效果基本是操作层面的,且主要是针对政府补偿的操作,既没有解决无过错补偿与民事赔偿的给付标准落差,也未能将第二类疫苗损害补偿的企业责任社会化。在国家医保局2020年10月发布的《疫苗责任强制保险管理办法》中,疫苗责任被限定为疫苗质量问题导致的赔偿责任,明确排除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此外,基于商业保险的运行机制,保险化后的补偿方式依旧是“一次性给付”,几乎不可能形成“长期给付”,〔24〕世界范围内以商业保险补偿疫苗异常反应的国家仅有芬兰和瑞典,补偿方式均为一次性给付,并且补偿依据是民事侵权责任法。See Mungwira RG, Guillard C, Saldaña A, et al. Global Landscape Analysis of No-Fault Compensation Programmes for Vaccine Injuries: A Review and Survey of Implementing Countries, 5 Plos One 15 (2020), p.6-8,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3334, last visit on Feb. 19, 2022.这与《疫苗管理法》新确立的补偿原则存在冲突。可见,当前的保险试点只是在原有补偿机制上打补丁,虽有裨益,但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法理基础
为什么应当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予以补偿?各国补偿理论建构的背景都是非国家责任,其中德国、日本采取了受种者自担风险的立场,美国采取了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德国自1807年巴伐利亚州推行天花疫苗强制接种(obligatorische Impfung)开始,到1874年制定的《预防接种法》(Impfgesetz)确立了“接种义务”(Impfpflicht),均未规定疫苗损害的补偿,直至1961年的《联邦传染病防治法》(BSeuchG)才建立了疫苗接种损害补偿制度。〔25〕Vgl. Peter Schiwy, Impfung und Aufopferungsentschädigung, 1.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74, S. 10 あ.日本1875年《种豆医规则》引入了强制接种义务,在1946~1947年发生的近百起疫苗损害事故中,厚生省排除了接种过失和疫苗质量问题,认定损害的原因为“特异体质”,即个人体质所导致,与疫苗接种没有因果关系,不能给予行政救济。1948年制定的《预防接种法》延续了强制接种义务与特异体质论,未规定损害救济制度,直到1976年修订《预防接种法》,才正式建立了疫苗接种损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26〕参见杜仪方:《日本预防接种行政与国家责任之变迁》,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23-29页。美国虽然在联邦层面没有疫苗强制接种的立法,但是马萨诸塞州自1855年起即要求儿童必须接种天花疫苗才能入学,〔27〕See Hodge JG, Gostin LO, School Vaccination Requirements: Historical, So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90 Kentucky Law Journal 851 (2002).到1980年几乎所有州都要求儿童入学、入托前需接种相关疫苗,〔28〕See Lois A. Weithorn, Dorit Rubinstein Reiss, Legal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Parental Compliance with Childhood Immunization Recommendations, 14 Human Vaccines & Immunotherapeutics1611 (2018).而美国《国家儿童疫苗损害法》是1986年才出台的,在此之前的疫苗接种损害只能通过民事侵权诉讼,国家未提供其他救济途径。〔29〕See Hensen R. Inoculated Against Recove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5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63 (2007).由此可见,各国对疫苗接种损害的事实认定基本无差别,但发展出不同的理论以阐释补偿的合理性,进而构建不同的制度形态。
(一)特别牺牲法理及其源流
德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解释基于“特别牺牲法理”。作为公益牺牲(Aufopferung)的扩大解释,特别牺牲(Sonderopfer)意指“构成特别负担的公益牺牲”。在我国,学界对德国公益牺牲理论的阐释不尽周延,尤其表现在公益牺牲与特别牺牲的关系上。如有观点认为,征收征用补偿系针对财产权损失,而其他权利的损失补偿依据公益牺牲补偿请求权,二者的基础都是特别牺牲。〔30〕参见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第31页。实际上,德国公益牺牲理论的起点是国家针对财产权的征收征用行为,其后经扩大解释产生了特别牺牲,并逐步拓展到人身权损害领域。
早在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第74、75条就规定了当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冲突时,个人应当容忍由此造成的侵害,但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损失。个人合法利益因国家实施的公益性、非过错行政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就构成“公益牺牲”。〔31〕Vgl. W. Schmidt, Die Aufopferung vermögenswerter Rechte, NJW 1999, S. 2847.这一法律原则被学界阐释为“容忍及补偿”(dulde und liquidiere),〔32〕Vgl. Joachim Lege, System des deutschen Staatshaftungsrechts, Juristische Arbeitsblätter, 2016, S. 85 f.有效地支持了政府基于修建基础设施等公益理由征收土地的行为,据此形成的通说认为公益牺牲补偿仅适用于财产损害,1831年的内阁通令(allgemeine Kabinettsordre)明确将补偿对象限定为私有财产。〔33〕Vgl. Peter Schiwy, Impfung und Aufopferungsentschädigung, 1.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74, S. 29.帝国法院亦在判例法中支持了这一立场。〔34〕Vgl. RGZ 72, 85 (88); 103, 426; 122, 301; 144, 325 (333).此后,第74、75条被《魏玛宪法》第153条和《德国基本法》第14条所承继,后两者均规定了征收征用财产权的公益牺牲补偿权。然而,除了政府直接实施的征收征用行为外,还有公权行为对个人财产利益间接造成的损害,典型例证是政府修路使公众无法进入路边店铺而造成的店铺营业损失。德国学理将政府行为直接侵害称为“法律行为”(Rechtsakte)造成的“狭义的公益牺牲”,将政府行为间接侵害称为“事实行为”(Realakte)造成的“财产权特别负担”,该负担超出了财产权社会义务(Sozialbindung)的一般限度,却因不是法律行为直接损害而使财产权人无法获得补偿。为了填补这一法律空白,德国学理形成了“广义的公益牺牲”或称“公益牺牲理念”(Aufopferungsgedanke)。特别牺牲正是在该理念下孕育而生,或者说是公益牺牲扩大化的产物。〔35〕Vgl. Fritz Ossenbühl, Matthias Cornils, 6. Aufl. Staatshaftungsrecht, C. H. Beck, 2013, S. 270 f.
特别牺牲法理进入法律体系是基于德国联邦法院的判例法。在1952年的“难民安置案”中,政府暂时征用闲置土地和房屋用以安置难民,法院认为该行为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但是连带侵害了周边房屋所有人的财产权利,已超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构成特别牺牲。〔36〕Vgl. BGH, 10.06.1952 - GSZ 2/52.正式将特别牺牲法理适用于疫苗接种人身损害的是1953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起“疫苗损害索赔案”。此案原告称1930年在其一岁时,根据1874年《预防接种法》接种了天花疫苗。此次接种引发原告脑炎,使其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导致永久性体弱。故此,他主张获得全面的补偿。德国上诉法院认为,公益牺牲只适用于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情形,疫苗受种者不构成公益牺牲意义上的受害者。然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之所以强调征收征用行为导致的公益牺牲,是因为公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侵犯一般是针对财产权。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基本法》意图否认其他公权力干预情况下的政府补偿义务。《普鲁士普通邦法》第74、75条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惯例法,其中蕴含的补偿法理应结合《德国基本法》第2条关于“人之生命与身体基本权利”来理解,故应突破帝国时期内阁通令和判例法对补偿对象施加的限制,个人因接种疫苗造成的健康损害同样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被迫作出的一种特别牺牲”,应根据“平等原则”予以补偿。〔37〕Vgl. BGH, 19.02.1953 - III ZR 208/51.此案的意义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打破了补偿责任的限制条件,从以往仅针对征收征用财产损失的“公益牺牲”发展出针对人之生命和健康损害的“特别牺牲”,弥补了国家无过错行为导致人身损害的救济空白。该案中提出的“特别牺牲”与平等原则的关系在1957年的“梅毒强制治疗案”中得到了深化,〔38〕该案原告因患有梅毒,被依法接受强制治疗。医院合规使用“新胂凡纳明”进行治疗,却致其瘫痪。原告主张依据“特别牺牲”法理获得补偿。法院认为,政府追求社会利益的过程中采用强制手段,对个人生命、健康、身体造成的损害超出了法律所预设的个人承担限度,该损害相对于其他人是“不平等的”,是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特别负担”,政府应基于衡平原则予以补偿。Vgl. BGH,26.09.1957 - III ZR 190/56.通过此案,法院明确了平等原则在特别牺牲概念构成中的定位。
综上可知,“疫苗损害索赔案”提及了平等原则,但未强调平等原则对特别牺牲的界定意义。而基于“梅毒强制治疗案”,平等原则成了判断某一“牺牲”特别与否的内在要件,亦成为确定补偿标准的基本依据。
(二)疫苗损害特别牺牲的构成要件
1.公权行为是损害之起因
从狭义的公益牺牲到特别牺牲,公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直接相关发展到间接相关。就疫苗接种而言,德国早期规定的是“强制接种”(obligatorische Impfung),个人违反接种义务将被处以罚款,此后强制性减弱为“接种义务”(Impfpflicht),“未接种天花疫苗而感染者,且危及他人时应受到处罚”。〔39〕Peter Schiwy, Impfung und Aufopferungsentschädigung, 1.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74, S. 29.在此情况下,公权行为的强制性是具体的,直接构成了疫苗接种损害的起因,个人不存在选择的可能。然而,德国自1983年取消水痘疫苗接种义务后,已无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德国学理将公权行为的强制性抽象为“国家策动”(staatlicher Veranlassung)的概念,即国家对其策动的行为负有担保义务,“那些因为法律规范或机关推荐之预防注射,从而遭受超过正常注射反应之损害者,也将受到补偿,这同样从国家策动所生责任而得以合理化。”〔40〕[德]艾伯哈特·艾亨霍夫:《德国社会法》,李玉君等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9-310页。
据此,公权行为作为疫苗接种损害的起因,已不要求以接种义务为前提,法律或相关机关推荐疫苗的行为构成国家策动,由此形成“个人对政府权威的信赖”。〔41〕BSG, 20.07.2005 - B 9a/9 VJ 2/04 R.疫苗接种损害发生在此条件下,公权策动行为构成特别牺牲的起因。
2. 非财产性权利遭受损害
为了尽可能地涵盖疫苗接种可能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情形,特别牺牲的客体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2款界定为“非财产性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完整性及行动自由。德国学者认为,上述非财产性权利是先于法律秩序而存在的人之基本权利,难以如财产权一样进行概念分割,也无必要在法律上进行细分。因疫苗接种造成的损害补偿,不是《德国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损害的法律效果,而是非财产价值的私权领域,属于特殊的公益牺牲请求权。〔42〕Vgl. Hartmut Maurer, Christian Waldhoあ,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 C. H. Beck, 2017, § 28 Rn. 2.就疫苗接种造成的异常反应而言,限于科学认知不宜用列举方法,应以“非财产性权利”的表述进行领域划定,以保持法律对疫苗异常反应的弹性,不遗漏可能发生的人身损害情形。据此,特别牺牲客体的非财产性扩张了补偿的范围,尤其是吸纳了服务性的照顾补偿。
3. 损害之发生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
从公益牺牲到特别牺牲的概念演进中,一脉相承的是牺牲的公益性,即减损个人利益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说以个人损失换取的成果由社会共同体共享。应当区分的是,针对财产权利的公益牺牲存在明确的公权行为侵害性,如政府征收征用私人财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而针对非财产权利的特别牺牲一般不存在公权行为的侵害性,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均在已有科学条件下验证了安全性,政府为了促进公共卫生须尽最大可能避免发生人身损害。在疾病治疗和疫苗接种中,个人是直接受益者,那么该如何判断其损害是否增进了公共利益?德国在仍规定接种义务或特定疾病强制治疗时,将法律强制等同于公共利益,正如“梅毒强制治疗案”所显示的,治疗虽有利于患者个人,但其接受强制治疗的法定义务是将公共利益强加于她。〔43〕Vgl. Fritz Ossenbühl, Matthias Cornils, 6. Aufl. Staatshaftungsrecht, C. H. Beck, 2013, S. 135.而随着此类强制义务被取消,公共利益识别的主要标准与公权行为相结合,是否存在“国家策动”成为考察重点,内在逻辑是国家策动在最低限度上也会对个人形成精神强制,该强制必然是出于公共利益之目的,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公权行为的起因要件上,公权行为与公共利益成了一个要件的两种说法。
4. 该损害的严重性违背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旨在解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情形下个人的容忍限度,并在损害发生后衍生出补偿的衡平功能。在狭义的公益牺牲概念下,平等原则对应的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是个人须容忍的限度。而对于疫苗接种损害,社会成员平等地负有容忍义务,须承担常见、轻微的一般接种反应,如皮疹、短时发热等。法律基于平等原则设定了个人承担损害限度的预期,超出此限度的严重损害体现了牺牲的特殊性,实质是国家代表社会共同体要求受害者承担了超出一般人所容忍的损害,此损害是受害者不能预期、不愿承担、无力承担的,造成了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在“疫苗损害索赔案”中,德国上诉法院主张,疫苗损害应理解为受害者为了追求更高价值的目标而有意识地接受不利条件,不能予以补偿。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此观点引用了《德国基本法》第3条的平等原则,指出对于特定受害者而言,疫苗损害是一种强制性的、超出一般人的特殊社会义务,拒绝补偿无异于再次违反平等原则,相当于要求受害者再次为社会共同体作出牺牲。〔44〕Vgl. BGH, 26.09.1957 - III ZR 190/56.
在新冠肺炎疫苗面世后,德国Paul-Ehrlich-Institut (PEI)作为联邦疫苗管理机构已批准了四款疫苗并向公众推荐接种,〔45〕Vgl. Paul-Ehrlich-Institut, https://www.pei.de/DE/newsroom/dossier/coronavirus/coronavirus-node.html;jsessionid=434F96746 AAD96CE0874FA8F1AAA61DF.intranet222. (abgerufen am 20. Februar 2022).由此构成了“国家策动”的预防接种。德国联邦卫生部已经表明,疫苗接种是自愿的,接种异常反应适用社会补偿的相关法律(sozialen Entschädigungsrechts)。〔46〕Vgl.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https://www.zusammengegencorona.de/impfen/logistik-und-recht/rechtliche-fragen/.(abgerufen am 20. Februar 2022).
(三)非特别牺牲的国家结果责任及其形态
相对于特别牺牲法理精密的逻辑演进,日本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疫苗接种异常反应本质的阐释,转向更为实用的补偿效果,形成了“非特别牺牲的结果责任”。就损害结果的责任承担方式而言,日本是公共财政对疫苗造成的个体损害结果承担补偿责任,美国是法定专项基金承担补偿责任。
1. 日本建构特别牺牲法理失败而转向国家承担的结果责任
日本曾尝试按照德国特别牺牲法理的推进路径,在实体法尚未作出规定时通过判例法确立国家对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责任,但未能成功。这一路径的起点是日本法关于国家补偿责任的规定,《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将国家补偿的对象限定为因公用目的造成的私有财产损害,不包括生命、健康等非财产性权利。此项规定与《德国基本法》第14条基本相同,是公益牺牲补偿的依据。
在标志性的“疫苗接种事故集体诉讼案”中,日本法院几乎是仿照德国法院的论证逻辑,尝试在判例法中对公益牺牲作出扩大解释,以便将国家补偿责任延伸至非财产权损害领域。日本地方政府根据1948年《预防接种法》进行强制或推荐疫苗接种,包括百日咳、脑炎、脊髓灰质炎等疫苗。但疫苗接种导致多起受种者死亡或伤残事件,62位原告于1973年向政府发起集体诉讼,要求政府承担责任。〔47〕参见杜仪方:《日本预防接种行政与国家责任之变迁》,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29页。东京地方法院借助此案全面论述了特别牺牲法理,并试图通过对《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的类推适用,确立疫苗接种损害的国家补偿责任。此案判决的表述几乎是照搬了德国1953年的“疫苗损害索赔案”。首先,国家为公共利益实施强制行为,其中政府推荐疫苗亦具有心理强制的效果。其次,儿童及其父母承担了超出一般接种反应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为公共利益作出的特别牺牲,应由全体人民共同负担。最后,从宪法相关条文的目的来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财产牺牲可获得补偿,而生命或身体牺牲不能获得补偿。因此,应类推适用第29条第3款,对疫苗接种造成的生命和身体损害予以补偿。〔48〕東京地裁1984年5月18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527号165頁参照。二审中,东京高等法院没有支持这一见解,否定了疫苗损害的特别牺牲法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国家结果责任,其要点包括《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所针对的财产权与生命身体有根本区别,不能类推适用;人的生命身体不能成为牺牲的对象,既然存在疫苗造成人身损害的可能性,国家推行强制疫苗接种就是违宪的;因强制接种违宪,所有疫苗损害事件均归因于政府行为违法,发生的是国家赔偿责任,而不是补偿责任。〔49〕東京高裁1992年12月18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807号78頁。
以此判决为契机,日本学界对强制接种的法理展开了讨论,最终促成了《预防接种法》的修改,取消了疫苗接种的义务性要求,转向个人自愿接种。〔50〕参见杜仪方:《日本预防接种行政与国家责任之变迁》,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30-31页。国家对免费提供的“常规接种”(定期の予防接種)和“临时接种”(臨時の予防接種)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无须考虑接种过程是否存在过错,仅以人身损害结果为依据。〔51〕参见杜仪方:《“恶魔抽签”的赔偿与补偿——日本预防接种损害中的国家责任》,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161页。日本学者认为,预防接种的国家诱因行为不宜作合法或非法的评价。〔52〕尾崎孝良「無過失補償等を巡る判例動向に関する調査研」日医総研5号(2005年)93 頁参照。
由此看出德国特别牺牲法理与日本国家结果责任的根本区别,即公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德国强调“提供给付之国家并未使牺牲者受到损害,其给付义务毋宁系基于,其促成损害的产生”。〔53〕[德]艾伯哈特·艾亨霍夫:《德国社会法》,李玉君等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9页。而日本认为国家直接造成了受种者损害,因此无论公权行为是否合法,只要发生了损害结果,国家均应承担责任,至于该责任是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并不重要。在此差异下,日本政府批准新冠肺炎疫苗后,厚生劳动省已经明确,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所致健康损害的,根据《预防接种法》予以补偿,救济标准按照常规接种项目中主要针对儿童的A类疫苗执行。〔54〕厚生労働省·副反応による健康被害が起きた場合の補償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https://www.cov19-vaccine.mhlw.go.jp/qa/0003.html, 2022年2月20日訪問。
2. 美国补偿模式的法理基础
美国补偿模式的法理基础是通过基金制分配疫苗损害风险与补偿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常规疫苗损害的“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National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VICP);二是针对紧急状况的“对策损害补偿计划”(Countermeasures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CICP),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即属于此类。
(1)补偿基金的设置是疫苗常规风险与紧急风险并行
“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是美国根据1986年《国家儿童疫苗损害法》设立的,以信托基金形式运营,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向免疫计划内的疫苗征收每剂75美分的消费税。〔55〕See Richard F. Edlich, Dana M Olson, et al., Update on the National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33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00 (2007).该制度的起因是民事诉讼造成的社会成本过高。20世纪80年代,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导致的儿童死亡事件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多起民事诉讼。疫苗生产者为了参与诉讼和维持责任保险付出了高额成本,如在“Johnson v. American Cyanamid案”中,陪审团判决生产者给付一千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八百万是惩罚性赔偿。〔56〕See Johnson v. American Cyanamid, 239 Kan. 279 (1986).一家疫苗生产者在1984年停产后,其他生产者也威胁停产,造成了公众对疫苗短缺、免疫缺失和疾病暴发的恐慌。〔57〕See Anna L. Jacobs, Liability and Maternal Immunization: In utero Injury Claims in the VICP, 207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63 (2012).在此背景下,美国出台了疫苗损害补偿计划,以确保疫苗供应足够、疫苗成本稳定,并为疫苗受害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补偿途径。〔58〕See Katherine M. Cook, Geoあrey Evans, The National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127 (Supplement 1) Pediatrics 75(2011).
“对策损害补偿计划”是美国根据2005年《公共准备与应急防备法》(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设立的,针对严重传染疾病或安全威胁情况下,因使用疫苗、药物或相关设备造成的人身损害,列举情况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神经毒剂等,新冠病毒于2020年2月被纳入其中。〔59〕See HHS, Countermeasures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CICP) , https://www.hrsa.gov/cicp/, last visit on Feb.18, 2022.此类病毒的疫苗尚不成熟,无法达到常规疫苗的风险控制程度,不在“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的疫苗目录中。为此,美国在常规疫苗补偿计划之外新设了此项补偿计划,旨在填补原有补偿制度之空白。
(2)补偿模式的特点是实体与程序相结合
“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作为常规机制强调司法功能。该计划之下,受害者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提出申请,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为被告,由司法部律师代理。申请者不服联邦索赔法院判决的,可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直到联邦最高法院。〔60〕See 42 U.S.A. § 300aa-10.“疫苗损害列表”(Vaccine Injury Table)起到的作用是替代双方的举证责任,以便简化程序。补偿基金的来源是生产者集体缴纳的疫苗消费税,本质为疫苗风险特别税,纳税形成的补偿基金由美国财政部管理,一旦确认疫苗损害结果,即由基金予以补偿。
“对策损害补偿计划”作为应急机制强调行政功能。申请人向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提出请求,该部门作出决定后,申请人可提出一次行政复议,但无权向法院起诉。〔61〕See 42 U.S.C. §§ 247d-6d, 247d-6e.该计划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的紧急拨款,从属于“既有对策过程基金”(Covered Countermeasure Process Fund, CCP Fund),是将应对紧急情况的人身损害确定为国家结果责任,由公共财政承担。
(3)补偿模式的核心是国家责任与生产者共同体责任相结合
“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使得原有“受种者—生产者”的民事诉讼救济转变为“受种者—基金—生产者”的无过错补偿,“受种者—基金”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国家责任,“基金—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国家将疫苗风险强制分配给生产者。生产者兼具疫苗产品获利者与疫苗风险承担者双重身份,须以其受益作为疫苗损害的补偿来源,公共财政不承担此项开支。表面上看,美国补偿基金是财政部管理下的国家责任,但从资金性质来看,则是生产者集体缴纳的补偿预备金。生产者集体基于法律规定构成“共同体”,即“疫苗供应共同体”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责任共同体”,通过基金制塑造生产者之间互相担保的关系,使全行业共同承担疫苗风险。
“对策损害补偿计划”因针对风险不明的紧急情况,超出了生产者共同体能够承担的限度。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保持生产者的研发积极性,应急疫苗损害补偿完全归于国家责任,但适用条件限定为法律列举之特定情况。从实效上看,截至2022年2月1日,“对策损害补偿计划”共收到6540件主张新冠肺炎治疗或疫苗造成的伤害及死亡申请,该计划尚未对任一申请予以补偿。〔62〕See HRSA, Countermeasures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CICP) Data, https://www.hrsa.gov/cicp/cicp-data, last visit on Feb.15, 2022.
(四)我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法理建构
我国根据疫苗分类采取了财政补偿与生产者补偿的“双入口”结构。《疫苗管理法》将《条例》中“第一类疫苗与第二类疫苗”的分类改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63〕《疫苗管理法》通过“免疫规划制度”提升了《条例》的疫苗管理级别。虽然免疫规划疫苗与第一类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与第二类疫苗在概念内涵上没有重要区别,但是《疫苗管理法》将第一类疫苗的省级采购提升为免疫规划疫苗的国家集中招标采购,将第二类疫苗的县级采购提升为省级采购。反映在规范层面的主要变化是《疫苗管理法》明确了居民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义务。〔64〕《疫苗管理法》第6条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此外,《条例》第33条规定了“省级卫生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传染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建议信息”,可理解为“政府建议策动下的居民自行接种”。但是,《疫苗管理法》删去了“政府建议”的规定,消除了“强制接种”与“自愿接种”之间“建议接种”这一灰色地带,将公共防疫责任完全归为政府。政府负责评估传染病风险,若存在公共卫生风险,则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免费提供疫苗,否则由居民自愿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
可见,在此疫苗分类的基础上,我国疫苗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逻辑可表示为:免疫规划疫苗—强制接种—异常反应—政府无过错补偿,非免疫规划疫苗—自愿接种—异常反应—生产者无过错补偿。鉴于我国卫生主管部门已明确新冠疫苗为自愿接种,那么该疫苗在现阶段仍是非免疫规划疫苗。国家疾病控制部门发布的《新冠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监测处置要点》表明,“对属于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相关规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给予补偿。”〔65〕《新冠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监测处置要点》,https://www.sccdc.cn/manage/Public/Edit/uploadfile/20210406/20210406095540980.pdf, 2022年2月18日访问。应理解为适用生产者无过错补偿。
免疫规划疫苗因强制接种无疑构成特别牺牲,属于国家责任范畴,问题是非免疫规划疫苗被排除在国家责任之外是否正当?从疫苗损害补偿法理的发展脉络来看,国家责任的扩张是为了因应疫苗的不可预测风险。在德国,取消强制接种后,政府建议范围内的疫苗损害均为特别牺牲,不考虑损害起因,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66〕Vgl. Stefan Bales, Hans-GeorgSchnitzler Baumann, Norbert Schnitzler, Infektionsschutzgesetz, 3 Aufl. Kohlhammer, 2015, § 1 Rn. 5.在日本,国家结果责任的内核是将特别牺牲起因的公权行为抽象到极致,要求政府对一切疫苗损害负责,从而将国家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的二分框架合二为一。在美国,“国家疫苗损害补偿计划”叠加“对策损害补偿计划”的疫苗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疫苗,〔67〕See Vaccine Injury Table, https://www.hrsa.gov/sites/default/files/vaccinecompensation/vaccineinjurytable.pdf, last visit on Feb.18, 2022.虽然两个基金的筹资渠道不同,但是均表现为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所以,预防接种是强制还是自愿、是免费还是自费不应作为限定国家责任的依据。因疫苗本身的特殊性,国家对全社会可能发生的全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承担结果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卫生信用机制。况且我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范围参考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疫苗,〔68〕参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范围参考目录及说明(2020年版)》,https://www.cma.org.cn/art/2021/1/6/art_58_36966.html,2022年2月20日访问。其医学作用与美国“疫苗损害列表”相当,但法律作用却未能与补偿机制相衔接。鉴于此,我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法理应阐释为国家对核准上市的疫苗引发的异常反应承担结果责任,包括免疫规划、非免疫规划及进口疫苗,核准上市行为构成国家责任的起因,异常反应鉴定结论是损害结果的证据,国家据此予以补偿。依此法理,当前我国基于疫苗分类的“双入口”结构应改造为“单入口”的统一补偿模式。
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的制度模式
《疫苗管理法》第56条确立的“及时、便民、合理原则”应当表达为怎样的制度安排?考虑到财政补偿的保险化试点,以及《疫苗管理法》对“一次性补偿”的摒弃,补偿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现有补偿制度进行改造,尤其是能否引入基金制,能否将两类疫苗异常反应纳入同一补偿体系。
(一)社会补偿体系下的疫苗接种损害补偿
1. 从行政补偿到社会补偿的认识演进
我国学理通常认为,免疫规划疫苗的无过错补偿是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由财政经费安排支出,属于行政补偿。这一认识没有错误,但仍可深化。就行政的属性而言,在传统干预行政之外形成的“给付行政”旨在实现“提供给人民给付、服务或给予其他利益的行政作用”。〔69〕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德国学者福斯多夫(Ernst Forsthoあ)最早提出的“给付行政”概念的核心是“用公共行政的力量和方式为相对人提供生存照顾”,〔70〕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此观念之下形成的行政补偿是“基于公益上的‘负担平衡’(Lastenausgleich)的原则以及对于基本权利的尊重,在行政机关因‘合法’执行公权力而形成人民之特别牺牲时,所给予被害人公平之补偿。”〔71〕钟秉正:《社会法与基本权保障》,元照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48页。可见,行政补偿强调公权力合法行使与损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社会补偿是在行政补偿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连带,“社会补偿原理建立在‘共同体责任’的基础上,也是对受特别损害者之损害予以衡平”,〔72〕台湾地区社会法与社会政策学会主编:《社会法》,元照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2页。并且该特别损害“不必然与行政权行使有直接因果关系”。〔73〕Helmar Bley, Ralf Kreikebohm, Andreas Marschner, Sozialrecht, 9. Aufl. Luchterhand, 2007, Rz. 911 あ.参照《德国社会法典》第一编第5条来理解,社会补偿的目标为“人身损害之衡平”,“基于国家整体对于特别牺牲之补偿或基于照顾法上的原则而生之其他理由,人民就其所遭受之健康损害,对于健康治疗之必要措施,以及对于适当之经济照顾拥有请求权。”〔74〕[德]艾伯哈特·艾亨霍夫:《德国社会法》,李玉君等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7-308页。可见,社会补偿是从行政补偿中发展而来针对人身损害的特别补偿机制,或者说是加入了社会化因素的人身损害行政补偿,最终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2.社会补偿的财务基础
(1)基于公共财政的社会补偿
作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社会补偿一般是“透过社会整体来分担个人损失,在财源上系透过税收,并由政府编列预算之方式加以支应”。〔75〕郝凤鸣主编:《社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E1页。据此形成的社会补偿的财务基础是公共财政,典型者如日本,所有疫苗损害均归入药害救济制度(医薬品副作用被害救済制度),由独立行政法人“药品和医疗器械局”(医薬品医療機器総合機構,PMAD)予以补偿,〔76〕参照独立行政法人·医薬品医療機器総合機構:《医薬品副作用被害救済制度の給付対象》,https://www.pmda.go.jp/reliefservices/adr-suあerers/0011.html,2022年2月20日訪問。这一机构为财政拨款单位,属于公共财政给付的国家结果责任。
(2)基金制的专项社会补偿
国家补偿责任与基金制并不相互排斥,基金制也是一种实现国家责任的财务安排。从美国基金制来看,其与德、日的最大区别在于通过基金制实现了责任形式与责任实质的分离,即形式上是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实质上可根据损害类型转移至生产者共同体,“在社会补偿中,通过集体的责任来承担损害,而不将损害承担与肇事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连接。”〔77〕[德]乌尔里希·贝克尔:《社会法:体系化、定位与制度化》,王艺非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4页。基金制使单个生产者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转变为共同体承担的补偿责任,或者说在共同体内实现了疫苗风险分担。
3. 基金制的优势
(1)打破补偿路径的条块分割,便于落实统一的国家责任
从各省现行的免疫规划疫苗补偿办法看,公共财政的给付效率并不高,且存在根据行政工作周期来设定补偿给付时间的做法,十分不利于实现及时、便民的目标。若根据国家责任的补偿法理,将非免疫规划疫苗补偿纳入公共财政,势必会增加行政部门的工作量与程序,进一步降低给付效率。相形之下,基金制能超越疫苗分类,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范围参考目录”要求所有疫苗生产者缴费。独立运行的专项补偿基金不在公共财政体系内,能够根据自身特点确定给付程序和周期。受种者寻求救济无须考虑疫苗类型,只需向补偿基金提出补偿申请即可。这样既可涵盖财政补偿保险化的益处,又能解决现行制度的其他问题。
(2)实现统一标准补偿给付
德、日以公共财政为基础运行社会补偿制度的社会背景是国土面积相对较小、财政体系完备,便于各地落实统一的补偿标准。但美国与我国均国土面积广阔、各地差异性大,存在央地公共财政配置与衔接问题,若设定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会造成各地公共财政的负担差异。我国现行免疫规划疫苗补偿以公共财政为基础,实质上并不是全民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而是省域居民组成区域“社会共同体”,省级政府作为区域“社会共同体”的“代理人”向受种者承担补偿责任,因此各省在补偿金额的计算上以本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标准,这必然导致各地补偿标准的差异化。要解决此问题,最优的方法就是建立涵盖全国的专项补偿基金,形成超越地域的统一补偿标准。
(3)督促生产者提升品质、控制风险
作为特殊的公共产品,疫苗虽然因既有技术水平不能完全排除致害风险,但是不意味每一个生产者在每一支疫苗上都尽到了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鉴于疫苗研发和生产的专业性,对于疫苗品质和风险的管理不能仅依靠政府规制,还要强化行业自律和生产者互相监督,财政补偿或保险补偿都难以对生产者产生倒逼作用。基金制则能够通过生产者共同体内的互保机制,将补偿责任的压力直接传递给整个疫苗行业。若疫苗补偿基金开支增加则提高全体生产者的缴费额度,实质是高风险生产者提高全行业的经营成本,由此迫使行业提升自律水平,形成生产者之间的监督效应,直至驱逐高风险生产者。
(二)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项目
补偿项目关乎补偿制度与民事责任体系的衔接,也直接决定着补偿的社会效果。只有补偿项目较之民事责任更为周延和妥当,才能将《疫苗管理法》引入“不能排除因果关系”后形成的补偿制度与民事责任体系重叠的部分受种者吸引到补偿制度中,防止出现新的衔接问题。
1.金钱补偿还是照顾补偿
多数国家采取金钱补偿,较为特殊的是德国,以照顾补偿为主。根据德国《传染病预防法》(IfSG)第60条第1款,疫苗接种损害可申请《联邦照顾法》(BVG)所规定的照顾(Versorgung),基于法规范的转介,疫苗接种损害的社会补偿进入了国家照顾给付的领域。《联邦照顾法》第10~24条规定的补偿项目包括医疗服务、残疾康复,《传染病预防法》还针对低龄受种者提供特别教育治疗等。〔78〕Vgl. Stefan Bales, Hans-GeorgSchnitzler Baumann, Norbert Schnitzler, Infektionsschutzgesetz, 3 Aufl. Kohlhammer, 2015, § 62 Rn. 1-2.在以照顾补偿为原则的前提下,《联邦照顾法》亦提供一定的金钱补偿,但补偿的对象不是接种损害,而是受种者因身体机能受损导致“工作能力减损”,因此产生的经济上的不利益应通过定期给付的年金予以衡平。〔79〕Vgl. § 63 IfSG Konkurrenz von Ansprüchen, Anwendung der Vorschriften nach dem Bundesversorgungsgesetz, Übergangsregelungen zum Erstattungsverfahren an die Krankenkassen, https://www.sozialgesetzbuch-sgb.de/ifsg/63.html, 2022年2月20日访问。可见,照顾补偿能够最大限度地扶助受种者恢复到“社会共同体”的一般状态,显著优于金钱补偿。德国之所以能够以照顾补偿为原则,是基于完备的公共医疗保障和长期照护体系,加之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对军人和遗属的照顾观念,〔80〕德国的国家照顾制度可溯及至17世纪王室对伤残军人和遗属的照顾。相关讨论可参见[德]艾伯哈特·艾亨霍夫:《德国社会法》,李玉君等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8页。这是其他国家难以移植的。日本和美国都采取金钱补偿模式,包含医疗费用支出,但不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我国亦无国家照顾体系,惯例上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只是金钱补偿,因此金钱补偿成为补偿项目的重点。
2.金钱补偿的项目及给付方式
补偿项目的要点在于是仅针对疫苗接种造成的人身损害本身,还是顾及受种者因损害而需要的持续性支持?给付方式的要点是一次性给付,还是年金给付〔81〕年金是与一次性给付相对应的金钱给付方式,一般按月定期给付确定金额,“本质上是对工资或收入的替代”。参见郑尚元主编:《社会保障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日本补偿模式的特点是以年金方式提供持续性给付。其《预防接种法》第16条根据疫苗针对的疾病将补偿项目分为两类,A类疾病疫苗是儿童接种的,包括白喉、百日咳、脑炎、儿童肺炎等。B类基本疫苗主要是流感,适用于成人。两类疫苗损害的补偿项目都包括医疗费用、医疗津贴、残疾儿童抚养年金、残疾年金、丧葬费,区别在于A类疫苗导致儿童死亡的,金钱补偿为一次性死亡抚恤金(死亡一時金),B类疫苗导致成人死亡的,遗属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死亡抚恤金或是以年金方式领取。〔82〕参照《予防接種法》,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23AC0000000068#101,2022年2月20日訪問。相比之下,美国补偿模式的特点是针对疫苗损害本身提供一次性金钱给付。美国补偿基金根据受种者死亡和伤残进行分类,均为一次性给付,只是补偿项目不同。受种者死亡的补偿为最高25万美元的抚恤金、收入损失、合理的律师费。受种者伤残的补偿为医疗费、看护费、康复费及相关费用,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开支,不设金额上限。〔83〕See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 Booklet, https://www.hrsa.gov/sites/default/files/hrsa/vaccine-compensation/resources/about-vaccine-injury-compensation-program-booklet.pdf, last visit on Feb. 20, 2022.我国《条例》确立的补偿模式也是针对疫苗损害本身的一次性金钱给付。由于《条例》未规定补偿计算项目,而在第45条规定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鉴定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就使各省补偿办法大都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四级医疗事故分级来确定补偿标准,例如受种者损害的一级甲等是死亡,一级乙等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广东、海南等地补偿办法列出的计算项目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交通费、死亡补偿金,并且明确规定不补偿后续治疗费用。这一规定可能导致补偿金不足以支付后续治疗费用而产生新的争议,不仅无法实现补偿平等原则,还会使受种者及其家庭陷入长期困境,相当于造成了二次牺牲。〔84〕在“山东省交通医院案”中,受种者损害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领取了10余万元的补偿金,但后续治疗费远超10万元,遂又起诉要求接种单位赔偿2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仅酌情判令接种单位补偿1万元。参见冯珏:《民事责任体系与无过错补偿计划的互动——以我国疫苗接种损害救济体系建设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62页。
3.精神补偿是否可行
疫苗接种所致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无疑会对接种者和家人产生极大的精神痛苦,但各国补偿制度均未规定精神补偿。在司法层面,我国对此的做法并不统一,有的法院支持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并酌情确定了金额,〔85〕参见“吴某甲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否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86〕参见“王某与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565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依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种立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6民终285号民事判决书。我国台湾地区也有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代表性案例。〔87〕参见“陈威鸿流感疫苗异常反应案”,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2017年判字第355号判决。德国司法的主流观点认为,因疫苗异常反应导致的精神痛苦是抽象性损害,与补偿所针对的生命和身体的完整性不同,须证明已导致忧郁症等精神疾病,方可在个案中作为特殊情形予以补偿。就一般精神痛苦而言,应以可归责的加害者为前提,加害者因主观过错及危险责任,有义务“抚平”受害者的精神损害。所以,无过错补偿不适用于精神损害。〔88〕Vgl. BGH, 13.02.1956 - III ZR 175/54.笔者认为,既然特别牺牲之客体为非财产性权利损害,理当包含精神损害。预防接种是针对健康人实施的,并且主要是儿童,个人和家庭对于发生严重人身损害的可预见性、心理准备要显著低于常规药害,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巨大而现实的,与生命和身体的完整性紧密相关,不能仅因精神痛苦无法用物理方式衡量就归结为抽象性损害,从而否定其补偿需求。并且,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针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项目已列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计算标准,而照此设计的疫苗损害补偿制度却排除了精神损害,无异于忽视了受种者及其家庭的精神痛苦,显然有失公允。既然疫苗接种异常反应能够分级量化,精神损害亦可据此予以分级补偿,使受种者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均获得抚慰,只有如此,才能更凸显人文关怀。
4.补助性质的金钱给付
补助并非针对人身损害本身,而是在异常反应救济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费用,如手续费、鉴定费。我国现行制度的立场是申请者垫付,如果确认疫苗异常反应,那么按补偿制度报销,反之则由申请者承担。例如,原卫生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卫生部令第60号)第18条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预缴,鉴定结论确认异常反应的,由财政或生产者承担,不属于异常反应的由申请者承担。各地补偿办法以同样的思路规定了其他相关费用,此类规定虽然没有逻辑错误,但是仍有进步的空间。
基于社会补偿制度的理念,异常反应的善后处理不仅与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心密切相关,还牵涉社会公众的团结性和认同感。在疫苗整体安全水平高的背景下,疑似异常反应是低概率事件,鉴定等相关费用总量有限。如果将社会对受种者损害分担的时点从“确认异常反应”提前到“发生疑似异常反应”,在补偿之外可增加补助性质的金钱给付,涵盖鉴定等相关费用,那么既能分担受种者及其家庭的开支,又能体现社会的温暖。
(三)我国疫苗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的完善要点
首先,建立统一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不区分免疫规划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并以基金制作为财务基础。基于国家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承担结果责任之法理,疫苗损害补偿应以受种者权益保障为中心,并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受种者—国家”关系中,受种者无须考虑疫苗类型,仅因异常反应的损害结果向国家请求社会补偿。现行免疫规划和非免疫规划的补偿“双入口”应合并为“单入口”,以社会保障体系之公法人作为办理机构,以此完成形式上国家结果责任的制度构建。在补偿的财务基础上,应将所有疫苗损害补偿从公共财政中剥离,设立专项异常反应补偿基金,由全体疫苗生产者按上市疫苗制剂数量缴费,并规定缴费额度与异常反应发生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浮动费率值。
其次,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从卫生行政部门划归社会保障部门,由社保经办机构管理补偿基金。卫生行政部门对异常反应补偿的管理是与公共财政联系在一起的,在采纳基金制后,此项补偿应明确为社会保障性质,应将相应的补偿职权转移至社会保障部门。按照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在此框架下,可在中央社保行政部门下设立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运营及拨款。各地社保经办机构作为办理社会补偿的公法人,接受受种者的补偿请求并给付补偿金,社保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最后,实现补偿项目的类型化与给付方式的年金化。建议采取三级分类补偿:第一级是死亡和伤残,死亡的补偿包括抢救阶段的医疗费、丧葬费、确定金额的死亡抚恤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二级是伤残等级,应从当前基本按照医疗事故分级的办法升级为独立的疫苗损害分级,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范围参考目录》与补偿计算项目衔接。第三级是成人与儿童。一方面儿童是疫苗接种的主要群体,另一方面成人与儿童的社会义务存在显著差别,对成人的补偿须兼顾其抚养和赡养对象的生活来源,对儿童则应考虑特殊教育的支出。
补偿给付方式应以年金为原则,此为长期稳定支持人身损害后续费用的最佳方式,也是民事责任体系所不具有的保障功能。年金作为工资或收入的替代,可防止一次性补偿的不当使用,亦可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以维持保障对象的生活水平。成人死亡的应由其遗属选择一次性领取全部补偿金抑或以年金方式领取,儿童死亡的不存在收入替代需要,应一次性领取。成人伤残的应给付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年金,根据伤残程度、家庭义务等综合计算。儿童伤残的应给付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残疾儿童抚养年金,根据伤残程度、康复教育等综合计算,此外,还有必要在补偿项目之外增设补助事项,涵盖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鉴定、尸检等费用,由基金在补偿过程中支付。
四、结语
疫情既是社会成员面对的生命健康重大危险,也是促使社会成员更为紧密团结的契机。疫苗接种使个人充分意识到其能在社会连带关系中获得庇护,同时又有义务参与社会群体免疫建设,容忍一般的接种反应。在严格的疫苗审批及管理之下,虽然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发生概率极低,但是任一异常的反应后果都是个人为社会共同体承受了特别牺牲,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在现有科学水平下获得疫苗保护,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公共卫生安全。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法理与制度均较为复杂,但这不应成为受种者获得补偿的障碍。良法善治的目标应是避免受种者面对复杂的救济程序,不使其遭受巨大不幸后又陷入维权困境。基于国家责任的社会补偿应是受种人得到“确认或不能排除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结论后,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补偿手续,以年金等形式获得身心痛苦的补偿和持续性的生活保障。受种者无须忧虑未来生计无着,更不用考虑补偿经费来源,不致发生救济过程中的二次牺牲。良好的社会补偿制度既能够加强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亦有利于提升社会共同体之凝聚力,团结抵御其他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