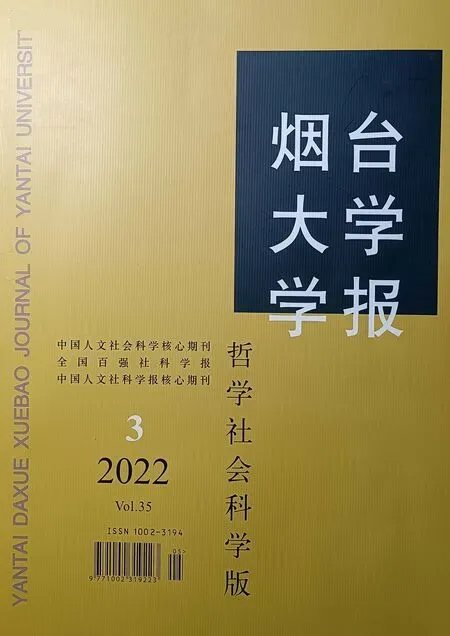昭君文化符号生成原因考
王前程(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西汉女子王昭君出塞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和亲事件。从历代史籍记载看,昭君出塞很难说比解忧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和亲女性的经历更加曲折生动,其在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纽带作用也很难说更加显著。然而,昭君出塞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令人关注、最享有盛名的一次民族和亲,两千多年来围绕昭君出塞产生了2000多首(篇、部)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戏剧、说唱、民谣、传说故事、音乐、绘画、影视等文艺作品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等,从而使王昭君成为一个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千百年无数女性和亲事件中,为什么唯独昭君出塞在历代文人和民众中会产生如此高的关注度?为什么唯独王昭君能够成为最具代表性、最富影响力的民族和亲文化符号?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何在?兹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一、平民女子的家国情怀是昭君文化符号生成的基础
远在王昭君之前的先秦时代,家族之间、诸侯国之间、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就产生过政治联姻性质的和亲活动,“和亲”一词亦常见于先秦典籍,但民族之间名副其实的和亲则始于西汉初期。汉初六年(前201),刘邦亲率大军出击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精骑围困于平城七天七夜,险遭不测,史称“平城之围”或“白登之围”。为了消除匈奴铁骑对于汉朝的威胁和骚扰,刘邦委曲求全,采纳了刘敬的和亲之策,即将公主嫁给单于,使汉与匈奴成为翁婿关系。当时因吕后哭阻公主远嫁,便以宗亲女儿假冒公主远嫁大漠。此后西汉一百六十多年间,大多数时候皆延续和亲政策,见载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的女性和亲活动达十数次,只是这些和亲女子的名字湮没无闻。
西汉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遣送王昭君出塞和亲。《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均记录了昭君和亲事件,如《汉书·元帝纪》曰:“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1)《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册,第297页。《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亦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2)《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0册,第2941页。
由史载可见王昭君是良家子出身,其后宫身份为待诏。所谓“良家子”,按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李将军列传》引三国学者如淳之言曰:“非医、巫、商贾、百工也。”(3)《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9册,第2867页。说明昭君为出身清白的普通人家的子女,如农家子弟、士人子弟、军人世家子弟等。所谓“待诏”,按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元帝纪》引汉末学者应劭之言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4)《汉书》卷九《元帝纪》,第1册,第297页。可见,昭君是等待皇帝诏令觐见的后宫女子。历代封建王朝后宫女子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妻妾,都有被宠幸而富贵的机会,然而后宫女子成百上千,等级森严,西汉后宫嫔妃分昭仪、婕妤等十四个等级,待诏远在十四等之下,大多数掖庭待诏一辈子都难以等到皇帝诏命,其心境难免凄凉,魏晋文人说昭君“积悲怨”是大体符合实际情形的。这充分说明王昭君在出塞之前出身平民家庭,在西汉后宫中亦是毫无地位的普通宫女。汉初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是以汉公主“妻单于”。西汉和亲女子虽然真公主不多,但大多是“诈称公主”的宗室女、宗人女、外戚女,即和亲女子均有较高贵的出身地位,出宫和亲之前皆赐以“公主”名号。而王昭君则是唯一一个名载史册的平民出身的普通宫女,身份清白而卑微正是昭君作为和亲女子的独特之处。
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享受尊荣富贵的皇亲国戚为朝廷分忧或承担某种政治任务是理所当然的职责。远嫁乌孙国王的细君公主不习惯乌孙国子孙妻其后母的习俗,上书朝廷要求返回汉朝,武帝则直接诏令其履行责任和义务:“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5)《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12册,第3904页。作为一位并未享受荣华富贵生活的平民女子,王昭君永别故乡亲人,勇敢地履行了原本由贵族女子履行的和亲职责,出色地完成了和睦汉匈两大民族的使命,成为震动西汉朝野的和亲大使。如果没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可贵的大局观念,王昭君在民族关系史上是难以做出特殊贡献的。今天从原始史籍中找不到昭君表现家国情怀和全局观念的片言只语,但有一个基本史实可以说明问题,即昭君的子女亲属无不是民族和亲的积极支持者。根据诸多学者的推算,昭君大约死于汉哀帝建平年间(公元前6年至前2年),在匈奴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来汉匈民族一直和睦相处,相亲友好。而昭君死后情况如何呢?《汉书·匈奴传》载:“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越舆而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云、当遂劝咸和亲。天凤五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6)《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26-3827页。这段文字粗略记述了昭君死后二十余年中昭君亲人从事汉匈和亲的活动情况,足见王昭君不忘言传身教,在后代中播撒民族和平友好的种子,其浓烈的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感深刻地影响了其子女亲属。尽管王莽时代执行了歧视性的民族政策,极大地伤害了匈奴民族的自尊心,但昭君子女亲属为修复被王莽破坏的汉匈关系,常常不辞辛劳奔走于长城内外,许多亲人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个出身卑微的汉家女子,不远万里奔赴大漠,出色地完成了汉王朝交托的民族和亲使命,无论是从国家政治层面上还是从世俗情理上论,都是极为令人感叹的大事件,因而自然会成为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历代文人在反复歌咏和描述中常常强调昭君是来自乡野、出身卑微的奇女子,亦充分说明了这一社会审美心理。如薛道衡《昭君辞》:“我本良家子,充选入椒庭”,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白居易《过昭君村》:“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马致远《汉宫秋》:“祖父以来务农为业,闾阎百姓”,郭天锡《明妃曲》:“君不见王昭君,家住子规啼处村”……无不对昭君这位出生村野的奇女子表达了热切的关注和由衷的赞叹。而这位奇女子的奇不单单表现在令人惊艳的美貌上,更表现在令人惊叹的心灵美上。无论是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还是戏曲家的舞台艺术,王昭君常以忧国忧民、甘愿舍弃个人幸福的爱国者形象出现。如郑舜卿《昭君曲》:“但愿夕烽常不惊甘泉,妾身胜在君王边”,许棐《明妃》:“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马致远《汉宫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青史留名”,卢昭《题昭君出塞图》:“此去妾心终许国,不劳辛苦汉三军”等,无不高度赞扬了昭君爱国爱民、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直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胡适还以“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为题,为王昭君作传记,热情洋溢地讴歌了“王昭君的爱国苦心”。(7)胡适:《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19页。毫无疑问,历代文人和广大民众对于昭君奇女子身份的高度关注,对于昭君深厚家国情怀的激情礼赞,都有力地推动了昭君和亲故事的传播,促进了昭君文化符号的生成和发展。
二、远嫁匈奴的艰辛使昭君出塞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两大元素。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各民族创造了农耕文化,生活于草原戈壁沙漠地带的边疆游牧民族则创造了游牧文化,两大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冲突、碰撞、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古代极富影响力的游牧民族是匈奴、羌、吐蕃、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游牧民族无疑是匈奴。
勇敢尚武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溶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但在早期激烈碰撞和频繁交往中,匈奴等游牧民族给华夏民族的印象多半是负面消极的。首先,认为他们生活环境恶劣,饮食习惯粗陋。西汉桓宽《盐铁论》云:“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8)桓宽:《盐铁论》卷七《备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43页。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9)《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879页。在汉人眼中,匈奴之国风沙漫漫,气候酷寒,绝非人类宜居之地;他们整天与牛羊马驴为伍,衣旃裘,住穹庐,生吃畜肉、贱视老弱的现象十分普遍,与汉人蒸煮五谷、优先老弱的习俗大异。其次,认为他们文化风俗极其野蛮落后,其心性行为如同禽兽,这也是最根本最负面的思想认识。远在周秦时代,中原民族就将北方游牧民族视为野蛮族类。《国语·周语》云:“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1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8页。《左传·闵公元年》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6页。到了汉代,人们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偏见更是有增无减。《史记·韩长孺列传》载韩安国之言曰:“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自上古不属为人。”(12)《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第9册,第2861页。《汉书·匈奴传》记大臣季布对吕后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1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11册,第3755页。又记武帝时期的使者讥刺匈奴“收继婚”习俗说:“常妻后母,禽兽行也。”(1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11册,第3780页。可见,汉人对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消极看法极为突出,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这类消极看法,但它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思想认识。作为一个卑微的汉家弱女子,昭君远离家国父母,身赴天寒地冻、风沙摧面之境,衣毡裹皮,食肉饮酪,同“怀禽兽之心”的部族为伍,还要面对有悖汉人伦理的“妻后母”的难堪,这本身就意味着莫大的艰辛、痛苦与牺牲。学者崔明德曾说:“从汉匈和亲到唐懿宗第二女安化公主嫁给南诏王隆舜(883年)共1003年中的112次和亲,没有一位和亲公主是含笑颜出塞或入塞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泪水、哀叹和悲伤。……就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态而言,只能是悲伤、泪水,绝不是含笑颜出塞。”(15)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页。诚然,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印象相当负面的匈奴部族,王昭君出塞和亲时很难说心情畅快。
然而,悲伤的泪水并不代表着畏惧与屈服,王昭君不仅永别了父母亲人,远赴风沙寒凉之地履行了和亲职责,而且还生儿育女生活了三十年,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仅仅依仗心中的家国情怀,恐怕很难长期支撑下去。我们不妨将昭君和亲与汉唐时期几位著名公主和亲做个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到昭君身上非凡的勇毅精神。
同众多和亲公主相比,昭君的孤弱感和凄苦感更甚于她们(少数乱世和亲公主惨遭杀害另当别论)。一是昭君无法像公主们那样受到特殊关照。在历代著名和亲女子中,昭君之前有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昭君之后有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她们出塞之前皆有公主封号,身份显贵,出塞之时都受到皇家特殊关爱。细君公主出塞时,汉武帝为她准备了极其丰厚的妆奁,配备的属官、宦官、乐工和侍者竟达数百人。解忧公主接替细君公主和亲乌孙,其出塞时的待遇史籍无载,但应与细君公主相当。文成公主由江夏王李道宗亲自持节护送入藏,沿途受到盛大欢迎,入藏后松赞干布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迎亲仪式。金城公主入藏时仪式更为隆重,吐蕃派遣一千多名迎亲使者,唐中宗亲自为其送行,还令随从大臣们“赋诗饯别”。而昭君出塞时虽然也受到汉元帝重视,但从《汉书》两处记载“赐单于”的诏令来看,昭君远嫁带有以特殊礼物恩赐单于、安抚匈奴的性质,其待遇不可能同公主们比肩。二是昭君出塞后的游牧生活远比公主们艰苦辛劳。匈奴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6)《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879页。即常常过着迁徙流动的生活,惯宿穹庐,不以建造固定居所为业。可见昭君远嫁大漠后常随部族迁徙不定,对于一个汉家弱女子而言,其颠沛艰辛可想而知。乌孙和吐蕃虽亦属游牧民族,但他们不像匈奴部族那样乐于迁徙,而是过着以城堡聚居为主的生活。《汉书·西域传》载:细君公主至乌孙国,还能“自治宫室居……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17)《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12册,第3903页。《新唐书·吐蕃传上》载:弄赞(松赞干布)亲迎文成公主归国都(今西藏拉萨),“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1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9册,第6074页。金城公主“至吐蕃,自筑城以居。……请河西九曲为公主汤沐”。(1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第19册,第6081页。足见细君等和亲公主过着深居宫室的安逸生活,还能常常得到朝廷的馈赠和慰藉,这是迁徙无常的王昭君难以想象的。不单如此,公主们一旦不如意或年老体衰,便可直接上书皇帝,要求回归故土,解忧公主还得到朝廷特别恩准:“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时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20)《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12册,第3908页。如此优厚的待遇也是王昭君不能比拟的。许多学者根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21)《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10册,第2941页。的记载,便认为昭君有着公主一般的特殊地位。其实,《后汉书》有关昭君的记载多杂糅野史杂记,难为信据。汉朝和亲匈奴非始于昭君,匈奴妻后母之俗早已闻于昭君出塞之前,知晓匈奴习俗的昭君自然做好了适应匈奴婚俗、终生生活于大漠的心理准备,不大可能向皇帝上书求归,非公主的卑微出身也不大可能具有这样的特殊权益。故而,与昭君时代相近的史学家班固便无昭君上书求归的只字片语,范晔所言不过是由《汉书·西域传》细君公主事推衍而来。
由此可知,远嫁匈奴的昭君付出了更多的牺牲与担当,她面临的艰难困苦要比若干和亲公主大得多,其内心深处的孤弱感也要强烈得多。但她成为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惊人传奇,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汉匈和亲过程中,无数和亲女性默默无闻,连姓名都消失在历史之中,唯有昭君出塞成为民族和亲的典范而名垂青史。正因为如此,昭君和亲引起了世人最广泛的情感共鸣,历代文人常以“昭君悲”“昭君怨”“昭君思”为主题,反复咏唱和极力渲染昭君内心的孤单凄怆,而且这种悲怨主题历久不衰,逐渐赋予了昭君出塞悲剧基调的象征符号意义。这类文学作品如西晋石崇《王明君辞》:“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唐人白居易《王昭君》:“满面胡沙满面风,眉销殊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宋人司马光《和介甫明妃曲》:“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元人刘因《明妃曲》:“飞鸿不解琵琶语,只带离愁归故乡”;明人黄幼藻《题明妃出塞图》:“天外边风掩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清人曹雪芹《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民国文人起予《题昭君出塞图》:“天山风急,摧残媚色。紫台月冷,照见啼痕。环佩凄然,丹青痕煞”;等等。今多有学者批评古代文人题咏昭君之作存在着严重的失真之弊,如洁芒《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云:“把原来高高兴兴、欢欢喜喜两族和亲的喜事给描写成了悲悲惨惨、哭哭啼啼的历史悲剧,王昭君也成了一个被同情被怜悯的牺牲者的角色。”(22)巴特尔编:《昭君论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马冀《论王昭君悲剧形象的成因》云:“尽管昭君的一生并非悲剧的一生,然而,在旧时代绝大多数文学艺术作品中,她却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23)巴特尔编:《昭君论文选》,第112页。这类批评当然有其道理,将昭君出塞视为民族和亲悲剧也确实未必合乎史实,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不难感受到“昭君悲怨”主题的价值所在。第一,对历史上曾经经受孤苦、为国家付出巨大牺牲的巾帼英雄寄寓无限悲悯之情,深刻体现了人类永恒的善性,而这种善良人性情感的共鸣正是昭君故事传扬天下的重要因素。第二,极力渲染昭君远嫁的艰辛困苦,又何尝不是对于昭君坚强意志、坚毅性格和吃苦耐劳精神的礼赞!这种悲叹式的礼赞时刻提醒着后人永远缅怀英雄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而正是千百年来反复的咏唱和提醒使得昭君出塞成为吃苦耐劳和勇敢坚毅等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
三、追求和平的共同意愿使昭君和亲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
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涵的“和合”思想以及彰显的“和平、和睦、和谐”等文化内涵,对于解决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作用。(24)崔明德:《论和亲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尽管汉代两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都存在着个人偏见,班固更是一个“和亲无益”论者,但他们仍然针对复杂的汉匈民族问题作了非常理性的评述,尤其是班固对西汉后期昭君出塞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十分客观的记录。从班固等史学家的客观记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昭君出塞是多民族从冲突对抗走向和平团结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座光辉夺目的丰碑,从而成为各族人民心中永久的历史记忆。
(一)战争灾祸引起执政者深刻反思形成民族和亲共识
自西汉立国至武帝继位初期,虽然常有匈奴入寇边境劫掠财物的行为,但由于汉王朝实行和亲策略,汉匈民族关系总体融洽,双方和平相处。《史记·匈奴列传》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5)《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904页。然而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发生了破坏民族和平关系的马邑事件,西汉边吏以大量财物和牲畜引诱匈奴单于亲率十万骑入塞劫掠,而武帝则暗中在马邑四周埋伏精兵三十万,准备围歼单于,单于得知消息后迅速逃离。“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26)《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905页。马邑事件固然与匈奴单于贪婪有关,但主因在于汉武帝自恃国力强大,想以战争方式彻底解决汉匈矛盾。此后汉匈统治者皆逞强好胜、穷兵黩武,民族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七十余年,双方损失惨重。《史记·匈奴列传》载元狩四年(前123)卫青、霍去病率部围剿匈奴:“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27)《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911页。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更可悲的是汉匈战争导致多民族卷入冲突,各方相互攻伐,士卒死亡无数,部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不堪。《汉书·匈奴传》曰:“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28)《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11册,第3781页。又载西汉与乌孙联合击匈奴,导致“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29)《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11册,第3786-3787页。而西汉王朝亦陷入经济凋敝的深渊。《汉书·食货志》记述了武帝时期经济由盛转衰的变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30)《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4册,第1135-1137页。西汉经济由盛转衰,除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是对外穷兵黩武,尤其是汉匈之间“兵连而不解”。
长期而惨烈的战争导致国穷民贫、怨声载道,使得汉匈执政者们开始认真反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功过是非。《汉书·食货志》载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31)《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4册,第1138页。《汉书·西域传》载武帝下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自责连年用兵扰劳天下,导致大量军士死亡离散、民怨沸腾,“悲痛常在朕心”。(32)《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12册,第3912-3913页。
尽管汉武帝晚年尚未充分认识到推行民族和亲政策的正确性,但他深刻反思了以战争手段解决民族矛盾的严重失误,也促使他将国家战略重心转移至发展经济上。而一向崇尚武力、骄纵好战的匈奴执政者在战争严重损耗、士众怨声四起之下也开始深刻反思行为过失:“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稀,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3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11册,第3783页。尽管汉匈执政者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尽一致,但顺应民意摈弃战争、实行民族和亲政策逐渐成为双方共识。昭君出塞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自然产生的,和亲既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也是各民族大众追求民族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之结果。
(二)昭君出塞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础上的民族联姻
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危害性和广大民众要求民族和平共处的强烈意愿,促使汉匈执政者逐渐清醒理智和务实,民族之间的和亲活动便应运而生,而昭君出塞和亲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础之上的民族联姻,受到历代民众的特别关注。
其一,汉匈平等相待,消除民族歧视色彩。西汉早期女性和亲是在匈奴强大军事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匈奴单于常以“天之骄子”自居,以征服者姿态处理汉匈关系,对汉朝傲慢无礼;汉朝则将和亲活动美其名曰“羁縻”,即对匈奴采取笼络手段以约束他们对于边境的侵扰。因而,尽管那些和亲女性贵为公主或翁主,却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们大多是羁縻政策的牺牲品,很难在民族关系中发挥应有作用,故其姓名、事迹在史籍中湮没无闻。昭君出塞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汉朝强盛而匈奴衰弱,呼韩邪单于主动遣使请求和亲,不仅质子于汉,还多次亲往甘泉宫朝见汉帝,以示与汉朝和解之诚心。强大的汉朝也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以强凌弱。汉宣帝接受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建议,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4)《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798页。表现了开明政治家们过人的政治智慧。昭君远嫁匈奴正是汉匈政治家们为改善民族关系、妥善解决民族问题而采取的有力举措,全然没有早期和亲活动中的民族歧视色彩。正如林干、马骥先生所言:“(昭君出塞)与汉初的和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匈强汉弱消极妥协的产物,而是两族和平友好向前发展的标志;也没有屈辱的色彩,而是民族团结和睦相处进一步加强的诗篇。”(35)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其二,建立互信基础,双方高度重视和亲活动。“互信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要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坦诚相见,民族关系就和谐,就会沿着友好轨道良性发展、持续发展。相反,只要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猜疑,民族关系就会恶化。”(36)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页。从《汉书》详尽记载看,汉宣帝、汉元帝、萧望之、呼韩邪、左伊秩訾等汉匈政治家无不努力消除汉匈之间的猜疑、欺诈,采取诸多有力措施构建民族互信基础,推动民族关系发展。一是结束民族对抗,尽力避免战争。《萧望之传》记载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发生内乱,西汉群臣主张乘机灭之,而萧望之则坚决反对用兵,认为自古君子不伐丧,他说:“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向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37)《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11册,第3279-3280页。《匈奴传》记载,在左伊秩訾等大臣的积极支持下,呼韩邪单于力排众议,在边境上与汉将订立“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盟约。(38)《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01页。二是在经济上相互扶持,在军事上相互救助。《匈奴传》载呼韩邪上书言部族民众“困乏”,汉朝则先后“转边谷”五六万斛及若干衣服锦帛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呼韩邪则向汉朝保证“有寇,发兵相助”,“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39)《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00-3803页。三是开诚布公,摈弃欺瞒。早期汉匈和亲旧约是以公主嫁单于,但实际情况是公主不愿远嫁,汉朝常常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和亲(不排除以普通亲属女子冒充公主的可能性),而昭君和亲则名正言顺地将“掖庭待诏”的身份写进诏令里,向匈奴单于示以诚信。《汉书》载呼韩邪单于请求汉朝“罢边备塞吏卒”,被汉元帝拒绝,元帝特遣车骑将军许嘉向呼韩邪解释:“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呼韩邪单于释然道:“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40)《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05页。双方开诚布公,大大增强了民族之间的互信。
正是由于汉匈民族互信增强,促进民族交流交融的和亲活动便得到了双方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呼韩邪单于上书“愿婿汉氏以自亲”,亲自向汉朝请求民族联姻,改变了从前将和亲女子视为战利品的民族歧视观念,不仅极为尊重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阏氏相当于汉之妃子),而且冠以“宁胡”。《汉书·匈奴传》引颜师古注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41)《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07页。汉王朝同样以高规格待遇送别昭君出塞,元帝亲自主持“临辞大会”,特改年号为“竟宁”。《汉书·元帝纪》引应劭注曰:“呼韩邪单于愿保塞,边境得以安宁,故以冠元也。”(42)《汉书》卷九《元帝纪》,第1册,第297页。可见,汉匈执政者都深刻认识到民族和平相处永远都优于民族之间兵戎相见,因而无不将昭君出塞视为吉祥的民族联姻而载入正史,也使得昭君出塞成为各族民众高度认同与共享的和平吉祥符号。
(三)昭君出塞是古代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实行民族和亲政策,在政治上起到消除战争、安定边境的作用,在文化上有利于民族交流交融,在经济上更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班固《汉书·匈奴传》赞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43)《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32-3833页。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亦曰:“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44)《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10册,第2953页。尽管史学家班固和范晔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民族偏见,但他们无不肯定了民族和亲政策给各民族经济带来的巨大裨益。事实上,汉宣帝对匈奴部族采取恩威并举之手段,的确大大改善了汉匈关系,为北方各民族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汉宣帝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非常理性地处理民族问题,实行平等互利、和睦相处的民族政策,为真正改善多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等延续这一民族政策,尤其是汉元帝遣王昭君出塞和亲,为进一步加强汉匈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笔者不大赞同过分夸大王昭君个人的历史作用,但应该承认昭君出塞创造了民族和亲史上的标志性成果。昭君作为一个普通宫女(历史上不乏以普通宫女冒充公主之事例,但这些普通宫女并未发挥特殊作用)甘愿承担大汉帝国交托的重任,在匈奴生儿育女生活了三十余年,与匈奴部族融为一体,不仅以其非凡的牺牲精神有力地维护了汉匈民族共同努力创下的和平大好局面,也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繁荣发展。《汉书·匈奴传》载曰:“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45)《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26页。又载乌珠留单于(呼韩邪之子,呼韩邪之后第四任单于)上书汉哀帝云:“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46)《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11册,第3817页。足见汉匈和亲以来不仅汉朝北部边境地区经济繁荣,而且匈奴等游牧民族也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盛壮”的大好局面,当汉朝中郎将韩况所部在塞外缺粮乏食时,乌珠留单于还为韩况所部提供了粮草。这充分说明了昭君和亲进一步改善了民族间的和平环境,大大促进了北方多民族的友好团结。对于昭君出塞的历史贡献,历代文人多有赞叹和肯定,如唐人张仲素《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崔涂《过昭君故宅》:“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宋人陈造《明妃曲》:“胡雏酌酒单于舞,铭肺千年汉朝主。传闻上谷与萧关,自顷耕桑皆乐土”;元人吴师道《昭君出塞图》:“平城围后几和亲,不断边烽与战尘。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等等。这些文学作品无不将昭君视为民族的大功臣,高度赞扬了其远嫁和亲所起到的安边息战、利国利民的典范作用,表彰其在促进胡汉民族团结、经济共同发展上的杰出贡献。
王昭君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汉和亲女性,而是世人心中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一个多民族共享的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各族人民和知识界无不将昭君出塞视为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许多学者甚至称赞昭君为民族关系史上的“民族友好使者”,乃至昭君葬地“青冢”亦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正如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所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47)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1年2月13日。毫无疑问,昭君文化符号的形成有其复杂因素,但各民族广大民众努力追求民族友好、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才是昭君出塞名扬天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