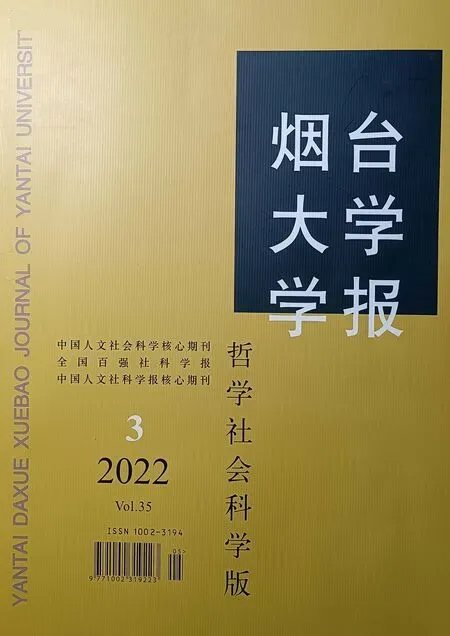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
马晓丽,杨亚蓉(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的联姻,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1)崔明德:《论和亲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目前,学界已对和亲的概念、内涵及历代和亲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和亲相关的古代墓葬不断出土,为和亲及和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本文拟对与和亲相关的古代墓葬作一初步梳理,以展现其承载的和亲文化,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一、出土的和亲相关的古代墓葬
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大批古代墓葬被出土,其中柔然茹茹公主墓、吐谷浑王室墓群、阿史那忠墓葬、西藏王室墓葬、辽朝兴平公主墓、清代公主墓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出土的体现和亲文化的遗迹与遗物,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公元420年,柔然社仑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建立起可汗王庭。柔然强盛之时所辖地域,东到朝鲜故地之西,南邻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北到今贝加尔湖一带。柔然与北魏及之后的东魏、西魏之间都有过和亲,共计六次。天赐三年(406),闾大肥娶华阴公主,公主死后,复尚濩泽公主。(2)《魏书》卷三十《闾大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册,第729页。濩泽公主与闾大肥成亲的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据专家推测,大致在始光四年(427)底与神二年(429)四月之间。(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西魏大统四年(538),西魏文帝迎娶突厥可汗阿那瓌长女,并立为皇后,史称悼皇后。大统六年(540),悼皇后因“产讫而崩,年十六,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4)《北史》卷十三《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册,第507页。悼皇后离世以后,东魏高欢趁机挑拨西魏与柔然的关系,又向柔然表明自己是正统,于是“阿那瓌乃召大臣与议之,便归诚于东魏”。(5)《北史》卷九十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5页。武定三年(545),阿那瓌次女出嫁高欢。武定五年(547),高欢离世,依照柔然婚俗,柔然公主又嫁给高澄。兴和四年(542),高湛娶了阿那瓌的孙女邻和公主。
1984年,在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了陶俑若干、陶镇墓兽、陶牲畜、陶模型器、陶器、石灯、金器、铜饰、铁器、青釉仰覆莲带盖瓷罐、珍珠以及一方“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公妻茹茹公主闾氏铭”的墓志。(6)朱全升、汤池:《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突厥活动于六至八世纪,是以阿史那氏为核心,吸收漠北、西域庞杂的铁勒、粟特因子构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7)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页。突厥崛起后快速发展,至木杆可汗时代,实现了漠北、西域的政治上的统一。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等政权争先与突厥和亲。隋时突厥分为东西二部,隋、唐均与突厥多次和亲。在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和亲公主中,嫁给北周武帝的突厥木杆可汗女儿的墓已经发掘。据《周书》《北史》和《隋书》等记载,突厥木杆可汗的女儿阿史那氏于北周天和三年(568)嫁给北周武帝宇文邕,史书称其为阿史那皇后。周宣帝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大象元年(579)二月,改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二月,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周静帝即位后,尊其为太皇太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阿史那皇后去世,年仅32岁。隋文帝诏令有司“备礼册,祔葬于孝陵”。(8)《周书》卷九《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第1册,第144页。
1993—199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阳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经过对陕西省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的一座被盗古墓的调查,确定其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与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9)张建林、孙铁山、刘呆运:《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由于墓室破坏严重,难以确定原随葬器物的数量。现存墓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金器、铜器以及“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墓志。此前,收缴的“周武德皇后志铭”和“天元皇太后玺”,也都很有价值。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宗室之女定襄县主嫁与突厥始毕可汗的孙子阿史那忠。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将阿史那忠提升为右卫大将军。唐高宗即位后,封阿史那忠为薛国公、右骁卫大将军。上元初(760年),阿史那忠死于长安,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10)《新唐书》卷一百十《阿史那社尔传附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册,第4116页。1972年,在陕西省礼泉县烟霞公社西周村出土了阿史那忠墓,(11)王玉清、苟若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墓室经历过严重破坏,已无法确定原有陪葬器物的数量。现存墓中出土了陶俑、壁画、阿史那忠墓志、镇墓石等。
吐谷浑原属鲜卑慕容氏分离出来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开始向西迁徙,从阴山南下经陇山抵达今甘肃临夏西北,后又向南向西发展,到吐谷浑孙叶延时始建政权,以吐谷浑作为国号和部族名,最终定都于青海湖以西的伏俟城。吐谷浑与柔然、西魏、隋、唐都有和亲关系。唐太宗时期,唐将宗室之女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首领诺曷钵。永徽三年(652),弘化公主回到长安,为其子求亲,唐高宗将金城县主许配给弘化公主的长子苏度摸末。“久之,摸末死,(弘化公)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12)《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第20册,第6227页。此外,根据“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的记载,慕容曦光与武则天的后代也有联姻关系。
1971年,武威市青嘴喇嘛湾出土了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13)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墓葬群中出土了9方墓志,分别是大周故西平公主、青海国王慕容忠、金城县主、代王慕容明、辅政王慕容宣彻、政乐王慕容宣昌、燕王慕容曦光、夫人李氏、夫人武氏。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因素,墓葬遭受过破坏。1980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5座保存较好的墓葬进行清理。五号墓为弘化公主墓,墓中出土了彩绘木俑、彩绘木器残件、漆器残件、丝织物残片。(14)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第191-192页。六号墓是武氏墓,在墓中出土了彩绘木雕女侍俑两件、木俑与马俑残件、象牙雕刻的棋子、骨器、石器、漆器和一件牛角梳等。还出土了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把阮咸琵琶。(15)宁笃学:《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七号墓是李氏墓,墓中出土了彩绘木俑、木器残件、五件灰陶碗。(16)党寿山:《武威县南山青嘴嘛喇湾又发现慕容氏墓志》,《文物》1965年第9期。
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位于青藏高原,早在旧石器时代,那里就有先民活动的踪迹。松赞干布继任吐蕃赞普之位后,内清理叛乱,外统一各部,完成了对西藏的统一。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1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册,第5221页。唐朝开始没有答应。后来吐蕃出兵攻打吐谷浑和唐朝的松州,以出兵要挟,要与唐和亲,但吐蕃军队很快就被唐军所败。经此较量,唐太宗同意与吐蕃和亲。贞观十五年(641),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入蕃和亲。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四十年之久,在维系唐与吐蕃友好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文成公主之后,长安五年(705),吐蕃赞普的祖母派大臣到唐朝贡,为孙子请婚,唐中宗答应金城公主出嫁。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嫁给赞普赤德祖赞(弃隶蹜赞)。
藏王墓群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琼结县境内,是吐蕃王朝规模最大的墓葬群。山南地区文物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资料,利用地理定位技术对藏王墓群的数量及墓主身份进行考察,确认了一号墓是松赞干布的陵墓,确认了五号墓为赤德祖赞墓。(18)强巴次仁、卓玛:《关于藏王墓数目及墓主身份的重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由此判断,文成公主墓极有可能在一号墓的附近。
在藏王陵对面的青瓦达孜遗址,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和藏族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葬在青瓦达孜,人们把青瓦达孜遗址称为金城公主墓。(19)霍巍:《关于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光明日报》2021年5月15日,第10版。青瓦达孜遗址依据建筑类型和建筑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三期。第一期建筑中的夯土堆,其建筑类型、材料及技术等方面均与遗址上其他建筑不同,且覆盖于土石建筑之下,应早于其他建筑遗迹,推测其为吐蕃时期的遗迹。据传说,夯土堆为金城公主墓,但从夯土层的位置、地层关系、吐蕃王氏墓地分布等角度分析,夯土堆很大程度上是城堡或者宫殿建筑遗存。2012年到2014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系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琼结藏王墓、青瓦达孜遗址等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调查与试掘工作,认为青瓦达孜遗址已经与后期的建筑融为一体,其早期的全貌很难寻觅和复原。(20)霍巍:《青瓦达孜遗址考古侧记》,《中国藏学》2017年第2期。
辽与西夏共有三次和亲。(21)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316页。第一次是辽圣宗以义成公主出嫁西夏李继迁。统和七年(989),“戊戌,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22)《辽史》卷十二《圣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册,第134页。第二次是兴平公主出嫁李元昊。辽兴宗即位,“以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23)《辽史》卷十八《兴宗纪一》,第1册,第213页。第三次和亲是成安公主出嫁西夏首领李乾顺。天祚即位后,乾统五年(1105)“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国王李乾顺”。(24)《辽史》卷二十七《天袏帝纪一》,第1册,第321页。1971年,宁夏驻军某部在民间传说的“昊王墓”附近发现了刻有文字的残碑碎片,后经钟侃带领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进行考古发掘,确定了7号陵主为西夏仁宗皇帝,同时确定182号陪葬墓主的身份。这里大多数墓葬破坏严重,只有101号墓保存较好,墓中出土了一尊铜牛屈身肢葬式鎏金铜牛和一件圆雕石马。李元昊时期辽与西夏交恶,兴平公主被迫害致死。青牛、白马为契丹人的标志和祖先神相,在兴平公主墓中放入跪拜的铜牛和石马,说明李元昊具有以此厌胜契丹的意图。一般人没有陪葬王陵的资格,因此101号墓主人为被迫害致死的兴平公主。(25)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代兴平公主墓葬考》,《西夏学》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兴平公主墓葬考》,《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
满蒙联姻成为清朝国政,有清一代,和亲人数达595人。其中出嫁蒙古的公主、格格共计432人,迎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26)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3页。从清朝相关制度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清朝出嫁外藩公主的安葬之地,前后有截然不同的变化。清朝初期,公主死后都葬于额驸所辖旗地,从清太祖到清太宗一百余年间,先后嫁到昭乌达盟的七位公主死后都安葬于藩地。(27)武亚芹:《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从乾隆朝中期一直到清末,出嫁外藩公主死于京师,都在京师郊外安葬,不得移葬外藩。在清朝下嫁藩部的公主中,已知墓葬在蒙古的有公主墓9座,共有14位公主入葬;(28)韩佺:《清代皇族女性墓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嫁到蒙古葬在京师的公主有10位,主要集中在康熙朝之后。清朝出嫁外藩公主安葬之地的变化,反映了清政府与蒙古王公之间的关系以及清朝对蒙古政策的变化。由于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下来,蒙古王公贵族在巩固清朝政权方面的作用有所变化,清朝皇帝对蒙古额驸的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出嫁藩部的公主不再葬于藩部。目前已经发掘的清代公主墓主要有固伦雍穆长公主墓、荣宪公主墓及吉林省清代公主墓。
固伦雍穆长公主于崇德六年(1641)正月出嫁弼尔塔哈尔,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去世。根据文献记载,清朝早期亡故的公主大都安葬在外藩“额驸”的封地,固伦雍穆长公主就是如此。1977年,哲里木盟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位于通辽市扎鲁特旗黄花山镇前德门嘎查(村)西南三公里的固伦雍穆长公主墓进行了清理。雍穆长公主墓为火葬墓,墓中出土了银制骨灰盒,装有麋子、珍珠、玛瑙和玉石的瓷瓶和一方刻有满、汉双语的墓志。(29)张柏忠:《清固伦雍穆长公主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闫洪森:《清代满蒙姻盟的见证——扎鲁特旗固伦雍穆长公主墓》,《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11期。
荣宪公主于康熙三十年(1691)六月嫁给乌尔衮,雍正六年(1728)四月去世,雍正七年八月与驸马合葬于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白音尔灯乡十家子村东北巴彦陶拜山南麓。墓地20世纪60年代被挖掘破坏,1966年考古工作人员对荣宪公主墓进行了清理,出土随葬品主要有服饰和首饰两大类。其中服饰包括两件苏绣旗袍、一件珍珠团龙袍服,首饰包括金簪、金镯、金戒指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方墓志。(30)项春松:《内蒙古白音尔灯清代荣宪公主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七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武亚芹:《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张伟娇:《清代固伦荣宪公主墓随葬品述略》,《北京文博文丛》2019年第4辑。
1982年,吉林省文物队与白城地区文管会、通榆县文化局在通榆县兴隆山乡同发屯清理了一座受到严重破坏的清代公主墓,学术界认为可能是固伦纯禧公主、和硕淑慎公主和固伦和敬公主的某一位公主墓。(31)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白城地区文管会、通榆县文化局(张英执笔):《吉林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文物》1984年第11期。墓葬群中有两个墓,其中在一号墓中出土了金银饰品、铜钱、铜盅、铜烛台、各种玉器、珍珠、象牙筷和服饰。二号墓随葬品较一号墓少一些,随葬品主要是以金银饰品为主。
二、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的和亲相关的古代墓葬
王昭君从被选入宫到远嫁匈奴,沿途涉及我国湖北、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王昭君在中国和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墓地呈现出分布广、数量多的特点。昭君墓在我国有十几处之多。(32)王绍东、汤国娜:《历代文献记载中的昭君墓及相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四处昭君墓,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八拜昭君墓、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朱堡昭君墓、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33)《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单于府》载:“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台、王昭君墓”;孙利中:《青冢村》,《中国·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1-171页。、鄂尔多斯市的伊盟达拉特旗昭君墓(34)郑隆:《伊盟达拉特旗的“昭君坟”》,《包头文物资料》第1辑,1984年,第97页。。但经考证,八拜昭君墓和朱堡昭君墓是汉代的燧烽遗址,并非墓葬遗址。(35)刘英魁、王加关主编:《三晋史话·朔州》,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第51页。山东有两处昭君墓,分别是山东菏泽东明县的昭君墓(36)乾隆《东明县志》载:“青冢在县北十八里,柿子园迤南,冢上各有青草,故名俗传为昭君墓。”参见储元升纂修:《东明县志》卷1,《中国方志丛书》第5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14页。和单县的昭君墓(37)嘉靖《山东通志》载:“青冢在单县南八里,相传为王昭君墓。”参见陆釴等纂修:《山东通志》卷二十二《古迹》,明嘉靖十二年刻本。。河北保定也有两处昭君墓,分别是高碑店昭君墓(38)民国《新城县志》卷二十三《识余》:“青冢,汉明妃墓,吾乡紫泉有大小青冢之村,不知始于何时”,见民国《新城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5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951页。和定兴昭君墓(39)光绪《定兴县志》卷十四《古迹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367-368页。。陕西省有神木昭君墓(40)雍正《神木县志》:“青冢,塞草皆白色,惟此冢独青”,参见雍正《神木县志》卷三《古迹·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8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32页。,河南省有许昌昭君墓(41)嘉靖《襄城县志》载:“昭君墓在县西北”;嘉靖《许州志》:“青冢,在襄西北十五里,旧传为昭君墓”。参见嘉靖《襄城县志》卷一《地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24页;嘉靖《许州志》卷八《杂述》,《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影印本,第480页。,山西省有朔州昭君墓(42)郑凤岐:《昭君坟茔今安在》,《山西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A03版;齐宏亮:《昭君墓应在朔州青钟村》,《朔州日报》2013年8月24日。。
北魏金陵是迁都洛阳之前的北魏皇陵所在,具体的位置,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三处说”(43)古鸿飞:《北魏金陵初探》,《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和“两处说”(44)松下宪一、王庆宪:《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但目前“一处说”处于主要地位。左云五路山、右玉马头山及其与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交界一带都有可能为北魏金陵所在。(45)杨天源:《北魏金陵的考古学调查》,《美成在久》2021年第5期。北魏与后秦、柔然之间进行过和亲,依据北魏陵寝制度,承担政治使命的和亲女子,离世以后均葬于云中金陵。
北魏与后秦之间有两次和亲。第一次和亲北魏拓跋珪没有履行约定,立后秦姚兴之女为皇后,引发战争。义熙三年(407),双方重归于好,北魏主动要求和亲,义熙四年,北魏与后秦再次和亲,北魏以皇后之礼迎娶西平公主。泰常五年(420),西平公主离世,谥号昭哀皇后,葬于云中金陵。北魏与柔然也进行过多次通婚。延和三年(434),柔然吴提可汗娶北魏西海公主;之后,拓跋焘娶吴提之妹,先将其封为夫人,后又加封为左昭仪。左昭仪离世后,安葬于云中金陵。
回纥灭东突厥以后,建立回纥汗国,成为漠北草原上的霸主。唐与回纥之间的和亲共有7次。宁国公主和太和公主最后回到长安,其余的公主都留在回纥。王延德写到:“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46)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5页。经学者考证,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是契丹设立的镇州可敦城,唐朝的和亲公主离世后,埋葬在生前所居住地附近。(47)白玉冬:《“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清朝满蒙联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陵寝制度经历了草创、完善和衰落三个时期。“(入关之前为)草创时期,顺治朝到嘉庆朝为完善时期,包括孝陵、景陵、泰陵、裕陵、昌陵及后妃陵寝。从道光朝到宣统朝为衰落时期,有慕陵、定陵、惠陵、崇陵及其后妃陵寝。”(48)徐广源:《论清代陵寝制度在乾隆朝的完备及其原因》,《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393-402页。乾隆朝是清代陵寝制度最完备的时期。
努尔哈赤时期,满蒙之间至少进行了14次联姻。(49)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14页。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纳科尔沁部贝勒孔果尔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被尊为寿康太妃,康熙四年(1665)去世,(50)《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0册,第8900页。葬于盛京福陵贵妃陵园。
在皇太极的后宫中,共有“后妃15人,有7人来自蒙古,在这7人中又有3人来自蒙古科尔沁部,姓博尔济吉特氏,而且是姑侄两辈”。(51)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21页。皇太极娶科尔沁莽古思贝勒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即孝端文皇后。顺治六年(1661),孝端文皇后离世,合葬昭陵。天命十年(1625),皇太极娶博尔济吉特氏,封为庄妃。其子福临继位后,被尊为太后。康熙二十六年(1688),孝庄离世。按照常理,孝庄去世后应合葬昭陵,但孝庄却向康熙表明其意愿:“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莹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52)朱诚如、孟宪刚主编:《清朝通史》大事记分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康熙应允了孝庄,并为其选择合适的陵址。只是当时东陵已建好,风水墙并无合适位置,故将孝庄葬于大红门东侧。因在昭陵西侧,称昭西陵。“昭西陵与昭陵相距太远,不像孝东陵依靠孝陵,所以因此在昭西陵前建神首碑一统,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孝庄后的谥号。在有清一代,首开皇后陵建神道碑亭之例。”(53)徐广源:《“下嫁”皇太后与她的昭西陵》,《中国档案报》2001年8月31日,第5版。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娶武克善妹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崇德元年(1636),封其为关雎宫宸妃,崇德六年,宸妃去世。据史书记载:“妃有宠于太宗,生子,为大赦。子二岁而殇,未命名。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上仍悲痛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54)《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册,第8904页。1982年,沈阳故宫博物馆根据自称是蒙古科尔沁寨桑后人名叫“博尔济吉特氏珍”关于宸妃墓地的信件,成立了由铁玉钦、邹兰欣、王爱军三人组成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宸妃墓葬调查组”,以皇太极出猎路线和对宸妃的祭奠为线索,最终确认宸妃墓在沈阳市大东区辽沈环境卫生管理所院内。(55)铁玉钦:《清关雎宫宸妃墓地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
到了顺治时期的14位主要的嫔妃,蒙古族后妃占6人,共册封3位皇后,2位来自蒙古科尔沁部。除了孝惠章皇后葬于孝东陵之外,废后、淑惠妃、恭靖妃、端顺妃等均葬本朝妃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太后(孝惠章皇后)去世,建立新陵,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初七入葬后,称“孝惠章皇后陵”。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礼部题:“古来有帝后不合葬而自称陵者,俱就方位定名”,(56)胡杨:《历代帝陵全档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第273页。得到了康熙的批准,自此称孝东陵。以后各皇后陵均按此种方法,即以本朝帝陵的方位来命名。康熙以后的后妃大都出身于旗籍,出身蒙古族的女子减少。少有的来自蒙古族的嫔妃,离世之后均葬入本朝妃陵。
在蒙古族女子嫁入清朝的同时,清朝的公主也大量嫁到蒙古,执行联姻政策,共有23位公主和9位王室女子出嫁蒙古。在各个时期,与蒙古和亲有所侧重:“太祖、太宗时期侧重与漠南蒙古特别是科尔沁部的联姻;顺治初年至乾隆中后期,联姻由漠南蒙古扩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乾隆后期至清末,联姻政策上只局限于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满蒙联姻开始走向松懈。”(57)王静芳:《清代满蒙联姻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增刊。清朝这些出嫁外藩的公主,死后葬在两个地方,在清朝初期葬于额驸所辖旗地,到嘉庆朝“则都葬于京师郊外”。(58)武亚芹:《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下嫁敖汉部的公主墓葬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附近。太祖第三女莽古济天聪九年(1635)出嫁吴尔古代,后改嫁琐诺木杜陵,因以罪受诛,玉牒不列,也不知死后葬身何处。(59)刘冰、顾亚丽:《草原姻盟下嫁赤峰的清公主》,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44页。皇太极长女固伦端敏公主,于天聪八年出嫁班弟,顺治十一年(1654)去世,葬于今内蒙古敖汉旗双庙乡喀喇勿苏村河西二十家子。(60)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赤峰人物·总古代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崇德四年(1639)正月,靖端长公主出嫁奇塔特,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去世,葬于蒙古藩部。端靖长公主陵位于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瓦房屯,当地人称为“妈妈公主陵”,陵前刻有“温都伊特格勒图”字样,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陵墓被拆毁。(61)《科尔沁左翼中旗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32页。
顺治五年(1648)二月,清太宗第五女淑慧长公主出嫁色布腾。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病故于北京,遗体迎回旗地安葬,初葬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汉山塞音宝拉格,后迁葬于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新立村,最后葬于公牛山北(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巴彦和硕山)。(62)董坤玉:《清代公主园寝调查》,《文物》2011年第3期。淑慧长公主生前捐资建桥一座,名“公主桥”,勒碑纪念。(63)田志和:《碑林的震撼》,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和硕敦恪公主出嫁多尔济。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来京薨逝,兹值归葬、请遣官护送”,(64)李澍田主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3),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16页。墓葬在今之内蒙古通辽、呼伦贝尔一带。
清圣祖弟恭亲王常宁长女,初封和硕纯禧公主。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出嫁班第。雍正元年(1723),进封固伦纯禧公主。乾隆六年(1741)十二月离世,葬于今吉林省通榆县同发屯,(65)董坤玉:《清代公主园寝调查》,《文物》2011年第3期。当时称为“小公主陵”,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白冠”。(66)郝维彬:《科尔沁历史考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顺治二年(1645)四月,固伦端贞公主出嫁巴雅斯护朗,初封昌乐长公主,复改永安长公主。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去世,墓地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67)郝维彬:《科尔沁历史考古》,第197页。该墓曾被盗过,陪葬品流散,只保留有固伦永安公主墓志,存于科右中旗。
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硕温恪公主出嫁翁牛特右旗多罗杜棱郡王苍津,康熙四十八年去世。温恪公主陵坐落在今赤峰市郊区松山区大庙镇公主岭村,最初是出嫁此处的公主府,后“改府为陵”。(68)杨海山:《内蒙古赤峰市郊公主陵辨疑》,《紫禁城》1996年第4期。
清圣祖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出嫁敦多布多尔济,雍正十三年(1735)去世,葬于今蒙古共和国和林格尔省额尔德尼庙。(69)董坤玉:《清代公主园寝调查》,《文物》2011年第3期。
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嘉庆帝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出嫁科尔沁部索特纳木多尔济,嘉庆十六年三月离世,葬于北京王佐村。嘉庆帝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出嫁土默特部玛尼巴达喇,死后也葬于北京王佐村。庄敬公主葬在王佐村东面,庄静公主葬在西面。(70)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66页。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道光帝第四女寿安固伦公主出嫁奈曼部台吉德穆楚克扎布,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三去世,墓在朝阳区洼里乡。(71)胡玉远主编:《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三、古代墓葬所承载的和亲文化
和亲文化是和亲双方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72)崔明德:《论和亲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从出土墓葬的随葬品、文献记载及专家学者田野调查情况来看,古代墓葬所承载的和亲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分布范围广
和亲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由于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分布范围很广,决定着和亲文化较广的分布范围。古代墓葬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有承载和亲文化的墓葬。在东北地区的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陵村,有出嫁齐默特多尔济的和硕端柔公主陵墓,在吉林省通榆县同发屯,有出嫁班第的固伦纯禧公主陵墓。(73)董坤玉:《清代公主园寝调查》,《文物》2011年第3期。在华北地区,河北、山西、内蒙古都有昭君墓,内蒙古通辽、赤峰等地有多处出嫁蒙古族公主的陵墓,河北磁县有茹茹公主墓,北京市有多处满蒙联姻的公主墓。在华东地区的山东省有两处昭君墓。在华中地区的河南省也有昭君墓。在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咸阳市有阿史那氏与北周武帝合葬的孝陵,陕西省礼泉县有阿史那忠墓等;甘肃省武威市有弘化公主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有兴平公主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有细君公主墓。在西南地区的西藏自治区有山南琼结县的藏王墓群和尚未确定具体位置的文成公主墓、金城公主墓。
(二)多元聚合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思想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了汉族思想文化,另一方面汉族思想文化也影响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74)崔明德:《高欢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目前已经出土的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和亲文化的多元聚合性。从比较丰富的随葬品可以看出,和亲把不同类型的文化联结起来,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纽带。
东魏茹茹公主墓中出土了萨满巫师俑、陶骆驼、身旁挂着猎获物的驴,充分体现了柔然的游牧性质。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灶等体现农业社会娱乐与生活的器物,(75)朱全升、汤池:《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反映了东魏的生活习俗。这与高欢“融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于一身”“具有胡汉两种身份”非常吻合。(76)崔明德:《高欢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阿史那忠墓中出土的墓镇石基本符合阴阳五行和民间墓神的传统丧葬习俗,体现了唐代初期人们希望利用在墓中放置各种灵神来辟邪、祈求生者和死者安宁的信仰。(77)周苗:《唐阿史那忠镇墓石试释》,《文博》2010年第1期。墓室壁画中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装饰以及乘舆、仪仗出行、列戟、阙楼等体现了唐文化的特征。在壁画中有身着圆领窄肩红袍、头梳螺髻、足穿长筒黑靴的昆仑奴;有上身均穿糷衫、戴圆毛帽、足穿长筒乌靴的御手,是典型的胡人形象;墓道壁画中前面还有骆驼形象,反映的是典型的异域文化图景。阿史那忠的墓葬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出这一时期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唐代帝陵依山为陵,陵前放石俑,明显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是唐“突厥化”的表现之一。(78)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欧亚学刊》2001年增刊。阿史那忠墓室的壁画中反映出突厥文化与唐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时代特征。
甘肃省武威市吐谷浑墓中出土的马、骆驼、家禽等器物,反映了吐谷浑民族“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以肉酪为粮”(7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第16册,第5297页。的生活习惯。墓葬中木质的雕刻马镫、金平脱文马鞍、铜马镫、马颈皮带等器物,生动展现了吐谷浑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同时,在弘化公主墓中出土了丝织物残片,金城县主的墓中出土的瑟、曲颈琵琶,在武氏墓中发现了表现唐朝风貌的棋子、阮咸琵琶、乐器、白瓷樽,都体现了唐朝文化的风貌。吐谷浑所辖之地,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弘化公主墓中所出土的丝织品为当时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体现。
吐蕃和亲具有多元化特点,藏王陵墓所体现的和亲文化也具有多元聚合性。据专家考察,藏王陵墓的封土形态“跟唐陵的封土形态非常接近”,陵墓的周围还有与唐陵一样的陵园垣墙,“陵园内还有石碑和石狮,也体现出和唐陵相仿的制度特点”。(80)霍巍:《关于文成公主的历史记忆》,《光明日报》2021年5月15日,第10版。
荣宪公主墓、吉林兴隆山清代公主墓出土的文物可分为衣服和首饰两大类,体现了满、汉、蒙三种文化的交融。出土的首饰和服饰上有梅、兰、菊、松、竹等装饰,蝙蝠等象征多子多福的纹饰也出现在随葬品之中,体现当时满族人对汉文化的吸收。满族人耳饰为一耳三钳,荣宪公主墓中出土了花丝龙衔珍珠金耳坠三副。兴隆山清代公主墓中还出土了以莲花和卍图案做装饰的饰品,莲花、卍字符为佛教文化中常用的图案。“民族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由选择机制所促成的文化的横向联系是有条件的,必须以不影响、不中断文化的纵向联系为前提。便决定了对异文化元素的接受和吸收是部分的接受,有改造的吸收。”(81)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满汉文化在交融演进中,汉族文化占主导。(82)滕绍箴:《试论满汉文化认同的几个问题》,《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这是外嫁公主墓中汉族文化因素占据主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清朝和亲公主陵的多种文字墓志、碑刻,也能体现和亲文化的多元聚合性。在内蒙古地区的固伦永安公主、淑慧长公主、和硕温恪公主、荣宪公主、和硕端静公主的碑刻,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的碑刻。如现存吉林省博物馆的“固伦永安公主圹志文”、保存于赤峰市博物馆的“淑慧长固伦公主圹志文”、现存于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公主陵村的“和硕温恪公主圹志文”半截碑刻、现今下落不明的“固伦荣宪公主碑文”、收藏于赤峰市喀喇沁旗清代蒙古王府博物馆的“和硕端静公主圹志文”,都是“满、蒙、汉三体合璧”。(83)乌日嘎:《内蒙古地区清代多体碑刻文献统计与分类》,《满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开放包容性
和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墓葬的随葬品中,多种文化的身影无处不在,体现了和亲文化的开放包容性。
北周孝陵中出土了“玻璃”。相关专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样品表面进行微损分析,确认北周武帝孝陵中出土的玻璃是植物灰型的玻璃。(84)成倩、张建林:《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玻璃珠的科学分析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结合墓葬的时间,墓葬中出土的这种植物灰型玻璃珠很可能是萨珊王朝所产。北周武帝孝陵中出土的铜带具,也带有鲜明的异域色彩。带扣的左侧是一呲牙舞爪的人形怪兽,右侧为蹲踞的狮子,圜眼小耳;条带銙上的雕纹片二片分别嵌于两侧,纹饰大同小异,两相对称,这种相向的人形怪兽和蹲狮的形象,称为“醉拂菻”。鞢带饰有五尖忍冬纹装饰,这种图案的腰带称为“狮蛮带”或“师蛮带”。醉拂菻和狮蛮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东魏茹茹公主墓的壁画中出现了偶首、偶蹄鸟翼雀尾的有翼兽的形象。有翼兽一直以来有外来说和本土说之争。由于有翼兽形象与祆教中的森穆夫形象有着相似性,故有学者认为有翼兽就是祆教中的森穆夫形象,森穆夫形象的流变,反映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85)赵洋:《中古丝路文化的传与承——以墓葬所见有翼神兽为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羽化”“升仙”的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有翼兽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东魏茹茹公主墓中出土的鸟翼雀尾的有翼兽形象,是在中外文化共同影响的产物。
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了两枚拜占庭金币,一枚是阿纳斯塔一世时期的金币,另一枚则是查士丁一世时期的金币。在我国的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同样也出土了相同时期的金币。5世纪后半期,柔然的财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将珍玩、金、玉石、文绣等都视作珍宝。(86)林英:《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中国钱币》2009年第4期。金币首先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次金币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茹茹公主墓中的金币,损耗较少,用于商品交换的可能性较低,更多的是体现茹茹公主的身份与地位。
北周武帝孝陵墓中出土的玻璃以及狮蛮带、醉拂菻等形象,东魏茹茹公主有翼兽的形象、拜占庭帝国的货币,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图景展现了出来。墓葬中这些器物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墓主人对异文化趋于认同,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
(四)传承与创新性
和亲文化源远流长,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只停留在古代,随着古代墓葬的出土和发现,一批以古代墓葬为基础而建立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以及以和亲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节庆等活动,赋予了和亲文化新的内涵。
汉与乌孙和亲的目的是“切断匈奴右臂”,先后有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入乌孙。2005年,考古学家经过反复考证,确认位于夏特大峡谷口的乌孙古墓群中其中之一便是细君公主墓,(87)宋伯航:《谒细君公主墓》,《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2期。故在此立碑纪念。江苏省以细君公主故事为主线,在伊宁援建了汉家公主纪念馆,在展现和亲公主风采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亲公主成了维系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纽带,王昭君更是成了一种精神和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象征。(88)王绍东、汤国娜:《历代文献记载中的昭君墓及相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内蒙古、山西、湖北、陕西等地开展的关于王昭君的各类活动,不仅有效地传承了和亲文化,而且还有一定的创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君墓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和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1981年,建立昭君墓文物保护管理所,2006年更名为昭君博物院。该院依托王昭君墓发展成为集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社会教育于一体的“一院多馆”格局的遗址性博物院。昭君博物院既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内蒙古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称号,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评为“内蒙古十大人文景观”和“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带动了呼和浩特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省区有以“公主陵”“公主坟”命名的地方,这些地名的由来,与清朝和亲公主有一定的关系。乾隆帝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乾隆十二年(1747)出嫁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五十七年卒于四川军中,后葬于京师。其墓地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镇西北门村的一块平川地上,后将公主的遗物送往公主岭市黑山咀子合棺下葬,公主岭市黑山咀村北的公主陵,是和敬公主的衣冠墓。(89)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吉林省志》卷43《文物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7页。固伦和敬公主衣冠冢是今公主岭市由来之一。北京的王佐村由于庄敬公主和庄静公主两位公主墓的原因,被称为公主坟村;和硕端静公主去世后,择地修建了公主陵,随嫁而来的侍从世代定居于此,守护公主陵,该地因此称为“十家”,又称为“十家公主陵”。端柔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后旗齐默特多尔济,乾隆十九年病故,死后建陵,将陵墓处原村名“下金台”改为“公主陵”。(90)冯永谦、温丽和:《法库县文物志》,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这些以“公主陵”命名的地名,努力挖掘和亲文化资源,发展当地的旅游、民俗等文化产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