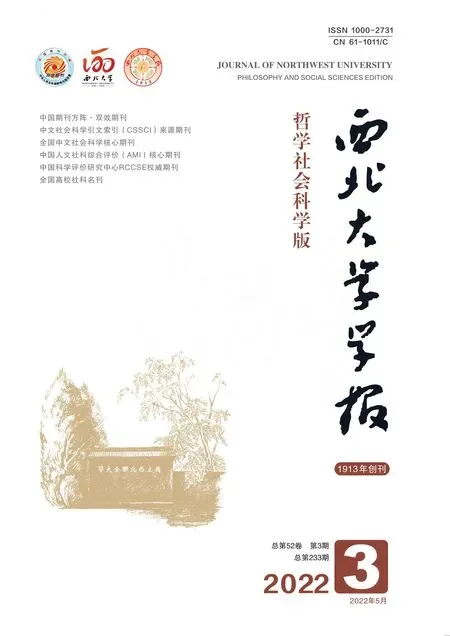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
——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黄汉平,李 智,刘汉波
(1.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指意丰富且充满解读空间的概念:它是地理意义上区别于城市、中心和主流的实体空间,是丈量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媒介,也是有别于现代社会的差序格局[1]35-46。现代性是一种表征繁多的现代文明属性,它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与宗教分离的世俗化,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资本积累、消费基础和商品生产的相互关联,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固有社会等级和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个人化世俗文化和工具化物质文化的崛起。现代性介入传统乡土社会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文化与技术的交锋、道德与资本的斡旋……种种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触碰的遭遇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林,张炜的胶东半岛,阎连科的耙耧山脉等,都演绎着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萦绕不散的寡民意识和迟来的现代文明在特定乡土空间内的相互作用。“人类一面生活在已形成的文化模式里,一面仍然不停地在以他们自己个别的方式提供新的模型和梦想”[2]67,作家通过选择塑造“乡土乌托邦”来重返历史现场、反诘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表达自身参与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态度。同时,如何对“乡土乌托邦”进行变形与解构,也反映出作家在不断反思、在文明演进、文化冲突、道德断层、知识重构等社会裂变中的自我定位问题。其中,张炜和阎连科在进行各自的乡土叙事时,选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张炜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并在回望道德乌托邦的过程中朝着现代文明蹒跚前行;阎连科则撕开乡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过敏反应”后溃烂的皮肤,肢解乌托邦,在无法遏制的躁动中表达对这场哗变的反思。二者就乡土社会遭遇现代性之后的出路问题给出了两种“极端”的回答。
一、张炜:“乡土乌托邦”的边界省思者
张炜小说中的乡村面对现代性的叩击并非抱持着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决绝姿态,而是通过不断地吐纳与现代性达成一种辩证共生关系。为了塑造乡土社会的道德主体,或者说道德乌托邦,张炜首先在乡土文明与现代性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边界。边界以内是张炜建立在作家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对乡土社会乌托邦式的纯粹想象: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里的自然崇拜,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里的生存意识,相对稳定的伦理结构内的道德法则……边界以外是现代纷繁世界的种种喧嚣:善与恶的冲突、新与旧的纠结、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边界并不是固定的、僵死的,而是流动的,具有过滤功能的。现代性的诸多因素中,不破坏道德乌托邦结构的部分被吸纳入边界以内,而一切导致伦理意识坍塌的因素都被拒斥到边界之外。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种种构成因素也在边界的过滤范围内,坚守原始淳朴的真善美固然重要,在现代性驱使下暴露出与人性和文明相悖的部分同样被允许反叛。
在《九月寓言》诗意的图景中,小村就是张炜构建的“乡土乌托邦”的具象:夜幕下的年轻人自由地奔跑、呼号、跳跃,展现了自由生命的盎然之姿;人们在野地里劳作、收获,享受着土地富足的给予。然后,强大的现代工业力量强势介入,矿区的开发令整齐的菜畦和秀丽的瓜田沉陷于地下,平原上现出斑驳的洼地,最终小村在一次矿井冒顶事故中坍塌,像荒野隐入暗夜般消失殆尽。小村中的几代“鱼延鲅”们寄居于此,忍受着当地人的蔑视和排斥、在饥饿感处处笼罩的焦虑中千方百计地寻找生存下去的方法,一再遭遇命运残酷的捉弄。小说中人物的“越界”之路充满隐喻,每当有人试图从这片近乎封闭的野地上突围,都会遭受更大的苦楚:金祥去南山后面找鏊子的路上历尽了千辛万苦,最后耗尽了全部的心力,虽然重回小村,但整个人已经垮了;妇人们想去干净的澡堂里洗去在土地里摸爬的污泥,得到的是男人们严厉的家暴;三兰子向往工区的现代生活,被语言学家骗到堕胎受罪,最后不堪婆婆的虐待服毒自尽。被作者寄予厚望纯净山野似乎也没有那么坚不可摧,稍有现代异质因素的入侵就在自身内部乱了方寸。渐渐地,在一些本应充满成熟红薯香气的九月里,人们开始互相猜忌羞辱打斗残杀,仿佛即使没有矿区的存在也会走向不可逆转的衰亡。其实小说一开始就道出了结局,“鱼延鲅”中唯一的幸存者肥对废墟的凝视是“孤独的现代人——绝望的个体在城市里无所皈依回到乡土找回精神家园的象征场景”[3]。如果说乡土历史的演进无法阻挡现代性的大举进攻,那么作家如此叙述的意义就在于传达一种站在“乡土乌托邦”边界之上的道德抉择:先进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现代人生存要素为代价的,现代人应如何面对随着物质生存环境一起毁灭的传统文化消失之后的精神困境。
早在《古船》里,作者就写到现代性带来的技术跃进刷新了洼狸镇的产业格局、物质构造甚至精神面貌。边界之内,是现代技术焕发的新活力;边界之外,是欲望和权力的侵袭。机械普及和技术革新的同时,沉睡的欲望也被工业文明的嘈杂之声唤醒,在资本垄断、权力觊觎的过程中,赵多多等人嘴脸之丑陋、灵魂之肮脏也展露无遗。在《家族》中曲府和宁家的后人在革命狂潮里引申出两种价值立场:一种是恪守道德和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理的立场,一种是不断追逐财富、确认身份和权力的立场。这就是张炜边界意识的隐喻。
在《独药师》中,张炜也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边界意识。小说以辛亥革命时的胶东半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在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不断推敲养生义理的家族传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戒律与欲望、保守与革命的抉择之间踟蹰前行的故事。与其说它是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民间寓言,不如说它是传统的乡土文明触碰现代性后的浮世绘。胶东半岛的季府历史悠久,代代传人都以独药师著称。一向尊师重道、恪守传统的季昨非,在面对西方文明和现代技术的时候,表现得既固执又自卑。“季府则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是半岛上苍黑沉重的存在,像一头衰老的大象。这头大象卧在那儿痛苦地喘息着,但就是不死。”[4]29这正是乡土社会与现代性发生碰撞之时季昨非的直观感受。传统书塾与洋学堂,季府药局与西医院,一开始在季昨非那里并不是本土与外来的区别,而是是与非、正与邪的对立。然而随着季昨非经历的增长,他逐渐改变了对西医院的既有认知:在用种种传统办法治疗牙痛都无效后,他屈尊去了“魔鬼的地盘”麒麟医院求医;在革命党的人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请来了麒麟医院的医生对伤者进行急救。在种种冲突之后,季昨非终于在文明的震荡中,步履蹒跚地越过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性滑移着的边界,踏上了道德乌托邦的净土。他由一个冒进、偏执甚至略显无能的公子哥儿,转变为一位在历史脊梁上辨别出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的老爷,修炼成一位懂得如何跟欲望打交道的独药师。
不难看出,张炜总在传统与现代、劳动与技术、道德与权力的推拉碰撞中透露出他对现代性的忧思。他曾说过:“我心痛的城市,正像我心痛的乡村。我不厌恶城市,正像我从来不曾厌恶乡村一样……离开城市,也会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我爱城市,所以我才要告别它。正像我爱乡村,我却告别了它一样。”[5]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以马克思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书名,探讨了现代性的体验。在他看来,现代性一开始是一种由技术带来的模糊的现代生活体验,随后人们得到(或渴望得到)现代公众的角色介入现代生活,最终在经验的不断扩展中产生了现代性带来的感受能力[6]15。张炜小说中的乡土社会,几乎都经历了马歇尔·伯曼探讨的现代性演化阶段。在张炜眼中,现代性并不是万劫不复的诱变元凶,他既认可其启发民智的理性和改善生活的技术,又为其带来的工具理性、剩余欲望和权力意志感到懊恼不安。与其说张炜是一名过度理想化的“原始主义者”[7]13-21,不如说他是一个目睹了现代性两副面孔之后、忧心忡忡的沉思者。
二、阎连科:用荒诞笔法解构“乡土共同体”
不管是《家族》《古船》《九月寓言》还是《独药师》,都可以看出张炜的立场:现代性会带来推动文明前进的技术、制度,也会催生误导人性的物质化、工具化社会景观,对道德乌托邦的回溯与反思或许可以抵御现代性席卷过后随之而至的精神灾难。面对传统乡土社会遭遇现代性的事实,阎连科在小说中传达出与张炜截然不同的立场:封闭乡土社会中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法则,恰是现代性介入后滋生异化的土壤;人们对乌托邦的狂热追求,恰好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理性的坍塌。
阎连科笔下原始状态的耙耧山脉是一个社会关系封闭的共同体(1)对于“共同体”,齐格蒙特·鲍曼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南希的《解构的共通体》都专门论述过。虽然诸家切入的角度和探讨的重点不同,但一些共识性判断依然可被归纳出来: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其中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它作为整体的乡土,有着严格而持久的一套权力系统、道德话语和伦理法则。人们一开始都怀揣着明显、热切而强烈的共同意志,围绕着同一个权力核心、遵循着同一套伦理法则去追求同一个既定的目标。社会学家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在《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分析过共同体式的中国乡土社会。他认为在这种社会里,人们与外界接触困难、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因此社会表面上呈现出稳定、平衡状态的中国乡土社会是“内向力量的历史统治”[8]25-38。现代性的介入,终结了共同体式中国乡土的稳定、平衡,个人主义的滋长、不同利益的分割、各种资本的输入、多元文化的渗透、过剩欲望的溢出,这些因素都为共同体成员打破内在限制、获得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提供了条件。当现代性所指涉的欲望(个人主义)、技术(工具理性)、市场(资本输送)等灌注到中国的乡土社会之后,共同体成员急切地追求身份认同。于是怒放的生命与扭曲的欲望、美好的愿景与癫狂的热望、单纯的行为与复杂的谋变密不可分地黏连在了一起,共同体成员陷入癫狂,原本稳定、平衡的中国乡土也因之产生了哗变。这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现代性的隐忧》中专门分析过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携同现代性之名肢解自由、造成秩序混乱现象的情形十分相似[9]1-14。在《日光流年》中人们为了挣脱四十岁堵喉而亡的诅咒,在村长司马蓝的带领下开凿灵渠,一系列怪异的仪式现象由此浮现。其中既有活寻墓穴、戴孝、结阴亲等“重死轻生”式的仪式,也有以权力或钱财为中心的下跪、卖身、结婚、卖皮等“生生抛弃”的仪式[10]。《丁庄梦》里,传统劳作已经无法实现人们对财富积累的渴望,“三层高的青瓦房”在村庄里制造出一种身份差异,人们想方设法通过财富积累消除这种差别,因此便出现了卖血产业链,上演了一幕幕以肉身作为原始资本追逐财富的惨剧。在《受活》中,资本不再停留在肉身层面,它瞄准了权力:一个充斥着残疾人的村庄狂热地计划着引进列宁遗体,试图以此来弥补缺失的身份认同。而到了《炸裂志》那里,人们为了确认城市人的身份,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以及更多的权力,不惜颠覆原来的所有秩序,最终陷入癫狂。
阎连科的反乌托邦叙事,实质上就是演绎乡村共同体瓦解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悖谬性的荒诞:正是人们对乌托邦秩序的狂热追逐,最终导致了乡土共同体的失序。《坚硬如水》中,阎连科将这种叙事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高爱军和夏红梅为践行先进思想、使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倾力奉献,然而原本平静地生活在传统乡村宗法制度下的程岗镇村民,却对外来思想保持警惕。高爱军与夏红梅的努力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曾经富庶的土地收成锐减,人与人之间不再坦诚相待,高爱军与夏红梅也在乡土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渐异化。他们为了扳倒王镇长和赵秀玉,潜入王家峪欺骗淳朴的乡民伪造罪证,将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王、赵二人送进了监狱。赵秀玉在狱中自杀,被高、夏二人欺骗的李林队长被乡民活活打死。现代性因素冲击着乡土共同体,在给乡村道德秩序以致命打击的同时,也造成了可怕的、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后果。高爱军和夏红梅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让现代社会法则取代传统道德,然而人们却在貌似现代的观念冲击下失序地狂欢,使得高、夏二人的现代“乌托邦”理想最终幻灭。在作品的尾声,高爱军和夏红梅在错误的判断下杀人炸寺,毁灭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传统的乡土秩序被彻底颠覆,然而现代“乌托邦”的理想却也未能实现,一切都归入了历史的虚无。
三、殊途同归的创作困局:简化言说和自我复制
学者邓晓芒在评论张炜的《九月寓言》时曾说道:“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便是寻根,寻回失落的童年,寻回远古的回忆,寻回数千年无变化的‘原生态’,寻回人们既有的‘本心’。”[11]的确,在现代文明以各种方式围追堵截的逼仄压迫下,传统乡土社会中历经了千年沉淀的生存伦理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对于本身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进程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们来说,一再回溯记忆中的乡村并在作品中不断以各种形式重现,是其寻找精神家园的自觉反射。“这代作家中的最优秀分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有自己稳定的后方,有着与脐带相连的审美乌托邦。”[12]。面对现代性介入乡土社会的种种话题,张炜和阎连科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重建乌托邦与解构乌托邦。虽然张炜在不同的历史维度对传统与现代、修持与欲望等问题进行思考,阎连科在不同的小说里进行别出心裁的文体尝试,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出现了简化言说和自我复制的创作困局。
张炜重塑道德乌托邦的边界意识表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中。在他早期的小说《秋天的愤怒》中,玉德爷爷便是一个充满隐喻意义的形象,“玉德”的意思是“纯洁美好的道德”,玉德爷爷是一个既能衡量进退得失又能准确把握新旧交替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形象,他始终屹立在誓要与传统黑恶政治势力作斗争的李芒与通过权力不择手段地运作资本的村支书萧万昌之间。《我的老椿树》中,“老椿树”在文本中的定位跟“玉德爷爷”相似,是超越天人、物我、人人之上的至高道德形象。《外省书》的里史珂,在亲历了目的时代的喧嚣和物欲世界的恣肆后,重返充满民间“地气”的故土,这里的“故土”折射出的也是一种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最和谐的道德想象。直至《独药师》,张炜依然鲜明地建立着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欲求的分野,师傅邱琪芝的形象便是某种“至高的道德形象”,既能在革命与保守之间取舍得当,又能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禁欲与纵容之间来去自如。在这个意义上,远在乡野的农民玉德爷爷跟贵为宗师的邱琪芝是一样的,具象化的“老椿树”与抽象化的“土地”“故土”“大地”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至高的道德”,是“最重要的理想”,是张炜所要表述的道德乌托邦。张炜在诸多作品中,都不自觉地将叙事本身视为阐释道德判断的契机,这种叙事模式一次次自我复制。重复出现在张炜不同作品里的“至高的道德”,固然寄予了作者内向单纯的道德诉求,但在面对礼俗秩序与市场法则、城乡二元与文化断层、乡土性与全球化等当今乡土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时,仅以这种带着逻各斯意味的绝对判断来衡量人性在剧变环境中的抉择,来验证关于制度、技术与传统的可能性,来构建支撑文化断层后乡土重建的终极法则,那么,这种简化操作与自我复制就流露出了一种狭隘、贫瘠的可怕性,它们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作家自身难以觉察、难以突破的写作困境。
阎连科瓦解乌托邦的热望,往往通过荒诞的叙事描摹一种传统封闭乡土不能逃脱的悖谬局面来呈现,但实质上他也是在重复地将乡土视为一个表意的素材,一个可循环使用的文化资源,以此为媒介来阐释他的立场。在2014年再版的《巫婆的红筷子》开篇,阎连科与梁鸿六次谈到写作的重复性或差异性(2)参见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谈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第56页,第57页, 第58页,第94页,第96页。,这说明他们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阎连科乡土叙事的自我复制困境:不断重复着对某种人物命运的荒诞性书写,不断展现对道德共同体和乌托邦追求的排斥立场。
纵观阎连科的创作,我们可以将其笔下那种重复出现的叙事称为 “得-失”模式:即耙耧山脉的村民都为了建立某种乌托邦(挣脱土地的束缚、摆脱农民的身份属性、建立最富裕的超级大都市、摆脱生命诅咒等),自然或不自然地放大个人欲求;他们追逐金钱、权力、想要得到城市人的身份认同,从而试图靠近乌托邦的假想;但最终代表着德性或善的“神”被驱逐出原有的乡土关系,人、土地和“神”(3)这里的“神”,并非指某种村社信仰中的神物崇拜,而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德性”或“善”等人类普遍价值判断。参见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122页。的三角关系被破坏,耙耧村民的现代性进程也便为荒诞所同构。简而言之,“得-失”模式是“为了得到而失去”或“因为得到而失去”的荒诞境况。《丁庄梦》中的村民为了像“血头”那样盖三层青瓦房而以卖血为荣,最终,一个又一个生命被利益牵引着走向了可怕的死亡之境;《黑猪毛白猪毛》中的村民把替领导坐牢作为靠近权力核心的筹码,而最终却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受活》中先天残疾的村民试图以各自的绝活——展览痛楚——来获得金钱及身份认同,最终却还是不得不黯然神伤地回归土地;《日光流年》中的村民试图用卖皮与卖身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最终却无法抵挡自然的残酷命运;在《日熄》中,贩卖尸油的情节也与《丁庄梦》里的卖血情节如出一辙。
张炜要确立“道德乌托邦”的至高合法性,为此,他建立了传统与现代、律令与欲望、意志与肉体的对立,演绎了一场场“现代性的后果”。阎连科则要展示乌托邦的毁灭过程,以此来揭示乡土根深蒂固的苦难、愚昧和无奈。他们都将复杂而广义的现代社会简化为一套单向度的模式,将中外、古今、城乡等场域内的冲突与融合简化为一项有迹可循的直线指令,将剧变与断层中的世相简化为“典型人物”所代表的标签。
四、矛盾与惶惑:知识分子作家的叙事立场
当作家成为观念的阐释者而不是审美的表达者,当审美诉求成为意识形态的抽象笼络而不是生命体验的具体抒发,当叙事本身成为一场场需要通过自我复制来强化观念的精神输出而不是对美学意义上内容实体的表达,这种连作家本人都不一定察觉的简化行为背后潜藏的,不只是状态的起落、才华的兴衰、灵感的盈亏、诚意的足缺等浅层次问题,在深层次里,还潜藏着拥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在现代社会中所遭遇的矛盾性问题。不管是参与过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张炜,还是在诸多场合对中国的文化、公共现象和社会热点发表过个人见解的阎连科,他们都接近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及的“专业人士”型知识分子[13]76-91。这类知识分子既需要在专业场域内做出独立的判断,又需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评价中;因为要担当社会责任,他们就必须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场域、进行普遍社会关怀;为了使这种关怀更具影响力,他们又必须从自己所批判的领域中获得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于是,个人立场、超然批判与公共角色、媚悦世俗就成为跷跷板的两端,知识分子必须要在其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文中曾敏锐地指出过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属于一个自足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让自己在知识界具有某种权威[14]275-290。
张炜小说中出现的“道德乌托邦”,其实是将实体的乡土、大地、自然等抽象为一种“人文精神”。这种形而上的“人文精神”是在与物质、欲望、肉体等形而下元素的对立中确立起合法性的,这就是上文所述的“边界意识”。在张炜的判断中,物质的泛滥、欲望的溢出、肉体的消费、资本的僭越、市场的介入和权力的失控恰好是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合谋的产物(现代性背后所指涉的诸多因素,张炜表现出最大宽容度的大概只有技术)。张炜不自觉地依靠着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排斥态度来获得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的背后,呼应的可以是未能适应市场经济节奏的人对过往生活模式的眷恋,可以是人们情绪上的单纯怀旧,也可以是某种平衡社会情绪的力量。文化资本冲破了审美本身的自律,引导了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隐蔽运作,实现了审美诉求从自我表达到“知识-权力”的隐蔽转换——通过文化资本扩大文本影响,增强个人立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度。
“反乌托邦”的阎连科与“建立道德乌托邦”的张炜一样,都在叙事中拿捏着自己的文化资本。如果说张炜的文化资本是排斥现代文明的乡土道德想象,那么阎连科的文化资本就是“感官/身体盛宴”,其“得-失”的叙事模式就成了镶嵌身体书写的前提。阎连科在书写耙耧山脉的时候,通过大量极端化的身体书写来探讨乡土的苦难,表现出阎连科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的深切关注。卖皮、卖血、卖身、痛楚表演等,无不表现出阎连科对农民的关切。但另一方面,极端化身体的书写又恰恰与当下物质性突出的消费文化语境形成了呼应,他对乌托邦狂热的批评和对农村问题的关切,无意识地偏移成了大众“感官盛宴”的消费品。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曾谈到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形象:“大量存在的视觉形象主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千真万确,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取决于培养永不满足的对形象消费的需求。为了刺激社会层面的消费业绩,众多的形象被生产出来。”[15]285在这个意义上,炫技式的身体书写以及挑战极限的器官买卖,形成了一种讨好读者的感官冲击,这使得阎连科的小说在表述农民问题的时候“非常有市场”,然而这种追求感官冲击的写作却阻碍了作者对文化、历史和人类自身的深入探索。萨义德曾对“专业人士”型知识分子做出批评,他认为“专业制度”或“专业态度”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威胁,“专业人士型”知识分子在确认其专业地位、传播其观念的时候,只有逾越公认的范式,才能促销自己、使自己更具市场性,因此,他们不敢做客观中立的知识分子[13]。
五、结 语
张炜的胶东半岛和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从语言背景、风俗习惯到生存境况和历史脉络,都有着各自的内在生态。然而不管是张炜笔下的对立,还是阎连科书写的荒诞,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乡土社会遭遇现代性后、乡村秩序重建之时所面对的文化矛盾问题,即乡土文化的断裂问题。他们都在描写这样一种局面:即“乡村文化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乡村自治空间等乡土文化的基本元素,在转型与现代化改造中被切断、被挤压和被挤占,而维护乡村文化整体性的衔接机制却并未建立起来,即‘先破而不立’的局面”[16]241。在描写的过程中,张、阎二人将个人经验和历史理解整理到这些以空间为媒介的记忆隐喻内,模拟还原出乡土与现代性对撞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演变历程。
然而面对乡土社会遭遇现代性后 “破而未立”的断层局面,无论是单纯地主导“精神还乡”、简单地呼唤“道德乐园”,还是歇斯底里地宣判“封闭有罪”、周而复始地放大“人性盲区”,都容易使小说作家陷入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僵化创作模式。作家不自觉地在这种模式中提炼文化资本,叙事艺术由此镶嵌进某种固定形式、丧失了广阔的艺术表现力;本应多元而深入的写作,也因此在客观上沦为了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这种隐蔽的僵化创作模式应该引起作家的省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