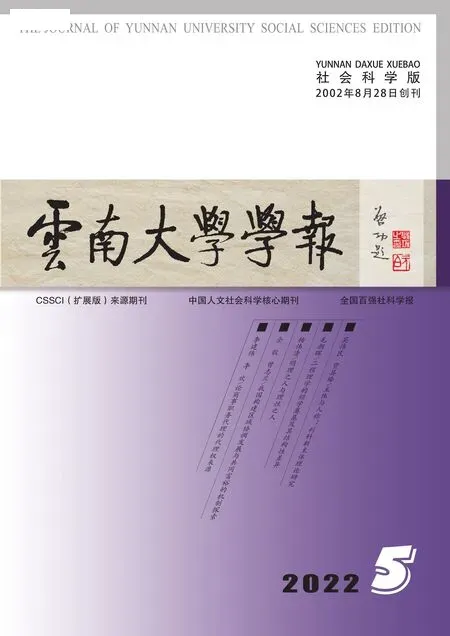论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与反驳
孙冠臣
[东北大学,沈阳 110819]
现代性开端之思所思之物是“我思”,笛卡尔与斯宾诺莎作为开端性的哲学家,确立了实体成为主体的道路。海德格尔认为,实体最终在德国观念论那里被把握为自我、主体、一般主体,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完成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争”是德国观念论兴起的序曲,甚至可以说,笛卡尔精神实体“自我”的确立以及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与反驳在18、19世纪的思想文化发展中集结为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开启了德国观念论的主体性哲学。斯宾诺莎作为现代性开端之思的哲学家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和重视,他与笛卡尔的思想关联研究也一直是哲学界聚讼纷纭的论题。本文选取三组概念:(1)身—心二元论与“神即自然”泛神论,(2)真理与人类理智,(3)理性的力量与情感——评估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的关系,通过分析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与反驳彰显他对现代性开端性之思的贡献。
一、“身—心”二元论与 “神即自然”泛神论
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实体”的理解和设定上。笛卡尔的实体概念有三种用法:(1)“显而易见,任何性质或特质都隶属于某个东西,而凡存在性质或特质的地方,必然存在有它们所依赖的东西或实体。”(1)Decartes R.,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with explanatory notes,by Alentine Rodger Miller and Reese P. Mill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2,p.23.当我们看到一些属性存在,我们就可以推断说,这些属性所依托的实体也必然存在。这是将实体定义为事物性质、特质、属性的载体和基底。(2)“每一个实体都有一个主要的属性,思想是心灵的属性,广延是物体的属性。……广延就构成了物体实体的本性,思想就成为能思的实体的本性。”(2)Ibid.笛卡尔区分了两个实体:一是能思想的实体——心灵;一是有广延的实体——物质。这两个实体是不可通约的:心灵能思想,但没有广延;物质有广延,但不能思想,构成身—心二元论。(3)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都不是自足和源初实体,是被造的实体,真正自足、无限和源初的实体只有一个,即神。“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自己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东西。”(3)Decartes R.,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with explanatory notes,by Alentine Rodger Miller and Reese P.
斯宾诺莎的实体只有一个,是一元论。他说:“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4)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在神的无限理智中没有一个实体不形式地存在于自然中。”(5)斯宾诺莎:《简论神、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关于自然,一切的东西全部地肯定属于它,并因此自然包含无限的属性,其中每一个属性在它自类之中完善。而这,和人们关于神的定义整个地相合。”(6)斯宾诺莎:《简论神、人及其心灵健康》,第27页。实体是自因,是神,亦即自然。与笛卡尔的神不同,笛卡尔的神是无限完满的存在,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与中世纪神学的神并无多少差别;而斯宾诺莎的神不是彼岸世界的创造者、人格神,而是内因意义上的自因,是自然本身。因此,斯宾诺莎也被斥为无神论者。对斯宾诺莎而言,物质和精神不是两大次一级的实体,而是实体的两大样式,实体是一,物质和样式则是多,多是一的外在表现。思维与广延是神这个唯一实体的两个样式,亦即神的无限属性,表达着神的无限和永恒的本质。
笛卡尔不是无神论者,他的身—心二元论以神为终极根据,不仅知识的真理性需要神来保障,而且自然万物的存在也需要神的存在来保证。而斯宾诺莎主张泛神论,为无神论奠定了基础:(1)斯宾诺莎的神不是人格神,不是创世神,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自然万物的外因,而是自然的内因,是最高理智。(2)斯宾诺莎把思想或精神安置在自然运动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必然性法则。在《形而上学思想》(CogitataMetaphyisca)中,斯宾诺莎正式接管了笛卡尔的神,尽管神依然被思考为宇宙的本原,但是神是作为永恒和无限的理智存在,神的实存、理智、本质、力量是同一的。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不是神的意志,而是其理智。神作为最高的理智这一观念就与神作为超越的意志这一传统观念区别开来。斯宾诺莎将关注的重点从神的意志转移到人的心灵上。他说:“哲学家并不研究神凭借它的万能能够做什么,而是根据神给予事物的各种规律去判断事物的本性……因此,我们在谈到灵魂时,并不研究神能够做什么,而只研究从自然规律中能够得出什么。”(7)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附录《形而上学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49页。斯宾诺莎说:“人的心灵是神的无限理智之一部分。”(8)斯宾诺莎:《伦理学》,第53页。心灵最高的善是关于神的知识,心灵最高的德性是认识神/自然。因此,斯宾诺莎以思想和必然性来反对意志和自由。在这个新方向上为人类的理智论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思想必定能够发现宇宙的秘密,否则,就没有科学,因此,不是神,而是必然性学说处于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笛卡尔的不彻底性和摇摆相对,斯宾诺莎哲学彻底贯彻了理性原则。
正如《伦理学》英文版评注者波洛克所言,斯宾诺莎并不是单纯阻断了笛卡尔的神学沉思,寻求将哲学建立在一个独立的根基之上,而毋宁是意图表明,一旦理性被允许自由地起作用,神学的沉思本身必定至少将其自身从人神同形同性论中清理出来,逐渐走向科学的观点。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在第三、第四以及第六章集中批判了笛卡尔神的观念,他提出了一个大胆且清晰的观点,如果我们打破自然之理性的假设,那么我们就打破了神的观念。尽管斯宾诺莎对神实存的讨论也与笛卡尔一样依赖心灵的实存,但它不是个体意志之心灵,限制为意识的不完满性;而是作为普遍理智的心灵,在思想的每一个过程中证实和发现它自身。笛卡尔仅仅论证了思想的有效性来自神的实存;与之相反,斯宾诺莎则论证了神的实存来自思想的有效性。甚至他在《神学政治论》中讨论的“神迹”概念都应要么理解为自然秩序的中断,要么理解为不能被自然原因所解释的一种事件。这种立场在教徒眼里隐含着巨大的危险:一方面它表明人的心灵是唯一可能达至真理和神的道路;另一方面它还导致一个无神论后果,即讨论自然的超越和神意志作品的不可理解性,不是拯救神之观念,而是在破坏它的意义。在斯宾诺莎看来,当人们不能找到一个理性的解释时,只会寻求神观念的庇护,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当人们拥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时,他们才可以说领会了神之观念的内在的充足性。
对笛卡尔来说,神作为“自因”(Causa Sui),是从“有效原因”(efficient cause),亦即从神圆满性的本质而言,他在反驳荷兰神学家卡特鲁斯时证明,既然神在其实存中保存他自身,他因此可以被称为他自身的有效原因,或“自因”。需要指出的是,笛卡尔总是在意志范畴下讨论神,实存与圆满只是能够让任何实体保存它自身力量的两个方面。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人可以说由自己而存在,因为他的持续保存总是依赖于外在的力量。可见,原因意味着生产和保存的力量。斯宾诺莎反驳说,“自因”概念不是从生产和保存的力量而言,而是从认识层面上说的,神作为圆满的存在的圆满性不是指其力量无限,而是指其自我完成。神与自然,通过由其自身存在且由其自身被认识。他是他自己知识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他自己的知识。“所以圆满和不圆满其实只是思想的样式,也就是说,只是我们习于将同种的或同类的个体事物,彼此加以比较,而形成的概念。”(9)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68页。圆满还是不圆满只是人们的成见,而不是基于对自然事物的真知。按照其一贯立场,那个永恒无限的本质就是神或自然,自然的运动并不依照目的,它的动作都是基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必然性。由此他主张,圆满性就是实在性。也就是说,圆满性指的是任何事物本质,是就那物按照一定的方式而存在和动作而言,而不管那物在时间中存在的久暂。而且,神的意志在这里也不再是生产、创造的原因,而是被其改造为与他的理智、他的本质相同一,意志来自于他的必然性。没有神、“自因”,无物可以存在和被设想,这不是因为神是绝对的力量,而是因为神是绝对理性。
基于笛卡尔对神的两个论证,笛卡尔哲学往往被看作是可以与新教合流,可以成为信仰的捍卫者,而斯宾诺莎则被视为有害于虔诚信仰的洪水猛兽,很多神学家也总是从笛卡尔主义出发驳斥斯宾诺莎。因此,就现代性的开端而言,斯宾诺莎显然比笛卡尔更重要。
二、真理与人类理智
笛卡尔哲学之所以被尊为近代哲学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他所创建的方法。其最大功绩是取消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并将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的整个观念精简为机械因果推理,如此一来,最终原因或目的性就从宇宙中消失了。为此,笛卡尔提出了一种与亚里士多德重在说明和分类的逻辑方法不同的新逻辑方法。新逻辑方法主张的因果推理链条(chain of reasoning)是由清晰可辨、各个独立的要素构成,成功构建一条推理链条涉及三个问题:即真理的标准、如何从一个清晰分明的观念运动到另一个清晰分明观念以及真理的根据。
(1)关于真理的标准,笛卡尔说:“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0)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页。清晰性和分明性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笛卡尔将其描述为神给予人的一种“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这种光可以用来区分真理与错误。(2)关于从一个清晰分明的观念运动到另一个清晰分明的观念的本性,不仅涉及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也涉及个体心灵与其他心灵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心灵观念的运动发生机制,那么结果就只能坚持个体真理,而否认存在普遍真理,从而陷入相对论和怀疑论。笛卡尔只能求助于神的观念。(3)关于真理的根据,笛卡尔的论证分两个步骤:第一步,证明神存在。作为有限的精神实体,我自身不可能产生清晰分明的观念,而事实上我拥有清晰分明的观念,这些观念只能是神给予的,所以神存在。第二步,神作为圆满的存在,不是骗子,不会欺骗我们,所以我们的清晰分明的观念是真实的。永恒的真实、几何学真理、物的本质,诸如此类,都直接产生于神这个第一根据,它们的持续存在依赖于神意志的保存活动。但神的意志超出了人类有限精神的理解范围,笛卡尔转而又求助于人的意志。他坚信,思想为了认知,必须拥有一个“意志,或下决定的自由”,意志自由本质上要求知识和德性。
斯宾诺莎主张“一切与神相关联的观念都是真观念。因为一切在神之内的观念总是与它们的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它们都是真观念”。(11)斯宾诺莎:《伦理学》,第73页。这种证明的大前提是:“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因此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就是那唯一的同一的实体,不过时而通过这个属性,时而通过那个属性去了解罢了。同样,广延的一个样式和这个样式的观念亦是同一的东西,不过由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罢了。”(12)斯宾诺莎:《伦理学》,第48-49页。小前提有两个:一是“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不外是一个现实存在着的个别事物的观念。”(13)斯宾诺莎:《伦理学》,第53页。二是“人的心灵是神的无限理智的一部分,……神是人的心灵的本性,神构成人的心灵的本质”(14)斯宾诺莎:《伦理学》,第54-55页。。可见,斯宾诺莎关于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真理自身,也就是说真理是它自己的标准。他之所以拒斥笛卡尔凡事诉之于神的论证,主要是因为:(1)笛卡尔提供的关于神实存以及真诚性的论证并不是一个正确合理的论证;(2)笛卡尔对怀疑论挑战的应对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斯宾诺莎的亲密朋友梅耶尔医生在为《笛卡尔哲学原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的两点分歧:第一,“意志并不是和理智不同的,它远没有笛卡尔赋予它的那种自由。”(15)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第7页。第二,“笛卡尔所奠定的科学基础和他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哲学并不足以弄清和解决形而上学中出现的所有困难。为了把我们的理性提高到认识的顶峰还必须有其他的基础。”(16)斯宾诺莎:《伦理学》,第8页。在《笛卡尔哲学原理》与《理智改进论》中,斯宾诺莎重复设计了他对笛卡尔循环论证的辩护性批评。一旦怀疑主义所立足的有一个欺骗的神之假设被移除掉,那么,怀疑论的根基就不存在了。不过,斯宾诺莎坚信笛卡尔方法是克服怀疑主义的有效方法,但他之所以依然提出批评,是因为他认为有更加直接和更好的方法应对怀疑主义。因此,他虽然论证了笛卡尔方法可以成功,而且不会陷入恶性循环,但他依然放弃了这种获得确定性的方法。
尽管从表面上看,斯宾诺莎重复了阿诺尔德在第二组反驳中提出的循环论证指责,但我们看到,斯宾诺莎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循环论证问题,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它源于对笛卡尔普遍怀疑逻辑结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斯宾诺莎反驳的核心是笛卡尔并不认为神的存在是已知的,而是从不确定的前提中衍生出来的。而且他认为,如果不需要从前提进行推论,就能够直接知道结论的真实性,循环论证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为了阐明这种区别,我们需要重构第二组反驳的结构:
Ⅰ.我们清晰分明地认识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只是因为神存在。
Ⅱ.我们能够确定神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拥有这种清晰分明的认识。
Ⅲ.因此,在确定神存在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清楚分明地认识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
斯宾诺莎与阿诺尔德的区别在于他没有设定这样一个隐含着的大前提,即所有清楚分明的命题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理性地肯定或否定),而是认为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根据在于一种无知: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只要我们无知于我们的起源。他指出,当笛卡尔发现神的圆满性时,他之所以从事怀疑的理由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原因将被破坏掉是无知的。据此,他所坚持的大前提是:我们既不能理性地肯定也不能否定我们是一个欺骗神的造物,这使得我们在对我们显而易见的东西上犯了错误。因此,我们既不能理性地肯定,也不能否定所有显而易见的命题都是真实的。斯宾诺莎认为,既然我们对我们的创造神的无知导致了我们不能理性地确定清楚分明的命题是否为真,因此他主张,只要我们理解了神的本质,就可以避免笛卡尔的循环论证。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欺骗神的造物,我们能够清晰分明地认识到我们的创造者不是一个骗子,因此,对数学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东西的怀疑就可以消除了。
问题的关键是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区分了真理与确定性,他提出了从普遍怀疑到“我思”,然后从“我思”到神的著名论证,然后才得出结论说:“我刚才当作规则提出的那个命题:‘凡是我们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实的’,其所以确实可靠,也只是由于神是或存在,神是一个完满的存在,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17)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页。我们注意到,这也是他为什么必须要证明确定性如何能够允诺真理的原因,同时这个论证也暗示了一种“道德规范”(morale par provision),对实践德性而言,充足的知识并不是严格必需的,按照笛卡尔的“道德规范”,德性实践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意志的坚定性,而不是我们判断的充分性。斯宾诺莎拒斥了真理与正确性的区分以及笛卡尔方法论的怀疑论,坚持理性的确定性,他说:“确定性不是别的,只是客观本质本身,换言之,我们认识形式本质的方式即是确定性本身,因此更可以明白见到,要达到真理的确定性,除了我们具有真观念外,更无须别的标记。”(18)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3页。斯宾诺莎主张,知识是实现至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真正的幸福、至善与对神的爱是共属一体的,万物的生灭变化皆遵循自然永恒的秩序及固有法则,至善就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斯宾诺莎寻求一种治疗和纯化知性的方法,以便知性能够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笛卡尔的认识论从自我的普遍怀疑出发,坚持“我思”是知识的确定性之根据,又以至上完满的神为真理的最终根据。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归根结底是自我保障的,因此,认知中的错误不在神,而在于我们误用了神赋予的自由意志。笛卡尔以神不可能欺骗我们为前提,构建了知识错谬的论证:
Ⅰ.神的至上完满性证明他绝对不能欺骗我们。
Ⅱ.自我(认知主体)从神那里接受过来一种判断能力;神不会让我们在正当使用它的时候总是弄错。
Ⅲ.因此,错误的根据不在于神的存在,而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
笛卡尔说:“意志较理智的范围大,这就是我们错误的来源。”(19)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8页。人类理智总是有限的,而意志是无限的。他认为,在思维中,意志是本质和决定性的要素,意志对人而言,就像对神而言一样,都是首要的事实。显然,笛卡尔的论证,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神正论,与奥古斯丁合流,将认识上出现的错谬与实践上的恶等同起来,皆来自于人滥用了神赋予的自由意志。
斯宾诺莎主张错误是由想象力造成的一种偏见,也就是说,错误来自于我们的观念缺乏清晰性和完整性,即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充分的观念不能完全把握它们的对象。他认为,笛卡尔在寻找错谬的原因时割裂了意志与理智,意志并不是和理智不同的东西,它远没有笛卡尔赋予它的那种自由。他说:“在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灵之有这个意愿或那个意愿乃是被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同样为别的原因所决定,如此递进,以至无穷。”(20)斯宾诺莎:《伦理学》,第86页。而且,在他看来,为了获得确定性,除了我们拥有的真观念之外,并不需要去寻找真理的标记(清晰分明),为了知道,我无须知道我知道。对确定性的寻求,我们不需要真理的标记意味着没有必要去验证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斯宾诺莎的方法是依靠人类理智直接去发现真正清晰分明的东西。他主张,只要我们的理智沿着不同于笛卡尔所发现和经历的道路去研究真理和认识事物,所有这些东西,以及更高超更精致的东西,不仅都能清楚明白地为我们所理解,而且甚至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加以说明。他由此认为笛卡尔所奠定的科学基础和他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哲学并不足以弄清和解决形而上学中出现的所有困难问题。从笛卡尔的天赋理性出发,人的理性是不可能认识神的;而从斯宾诺莎的经验理性出发,人通过在理性的指导下过上完全德性的生活,通过对神的理智的爱,是可以认识神的。可见,斯宾诺莎主张意志与理智的等同跟否认笛卡尔真理与确定性的区分一样,都是为他的道德理智论服务。
三、理性的力量与情感
笛卡尔率先将理性从希腊人的德性生活中独立出来,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将逻各斯从本体论转换为认识论。理性被规定为认识主体(心灵)先天的认识能力,与其他人类认识能力(感性、情感)相区分。笛卡尔认为,人类理性只是有限实体的认识能力,尚需要由无限的神来保证其确定性(天赋观念)。斯宾诺莎认为,理性并不是先天赋予的,人并非天生就有理性。在人们通过良好的教养,终于获得德性的生活之前,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光阴已经流逝了。在这些流逝的岁月中人们更多的是单独依靠欲望来生活并保存自身。这不仅否认了理性的先天性,而且也否认了人们一出生就有认识万物的能力。相对于“通过感官片段地、混淆地和不依理智的秩序而呈现给我们的个体事物的观念”而形成的泛泛经验得来的知识(21)斯宾诺莎:《伦理学》,第78-79页。,从理性而来的知识是一种概念能力,斯宾诺莎说:“从对于事物的特质(propria)具有共同概念和正确观念而得来的观念。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我将称为理性或第二种知识。”(22)斯宾诺莎:《伦理学》,第79页。但这种概念能力是推论性的,缺乏直接性,不如直观的知识(scientia intuitiva)直白。单凭直观就能看出本质的知识被斯宾诺莎称为直观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形式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23)斯宾诺莎:《伦理学》,第79页。
从理性到情感,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的分歧越来越大。对笛卡尔的情感理论,斯宾诺莎给予了详尽的驳斥。在《伦理学》第三部分的序言中,他宣布将以考察神和心灵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征服情感的力量,也将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他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他说:“就我所知,还没有人曾经规定了人的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如何可以克制情感。诚然,我深知道,那鼎鼎大名的笛卡尔,虽然他也以为人心有绝对力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却曾经设法从人的情感的第一原因去解释人的情感,并且同时指出人心能够获得绝对力量来控制情感的途径。不过至少据我看来,他这些做法,除了表示他的伟大的机智外,并不足以表示别的,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说明。”(24)斯宾诺莎:《伦理学》,第95-96页。在斯宾诺莎看来,既然人是自然序列中的一环,那么人的情感也必然遵守自然的规律。他说:“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25)斯宾诺莎:《伦理学》,第97页。能够克制情感是理性的胜利,也是自由的表现,与之相反,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则是人的奴役状态。“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26)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66页。
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对情感的讨论都坚持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强调情感产生的身体机制,两位哲学家都以线、面、体不同维度寻求构建一种关于情感的几何学。但是,斯宾诺莎的解决方案在情感的原因之本性和心灵控制情感的力量之本性的讨论上全面超越了笛卡尔。笛卡尔认为,情感在一般意义上是心灵的知觉,因此有两个原因:心灵和身体。在1643年5月21日给伊丽莎白的信中,笛卡尔说,情感既不会单独取决于心灵,也不会单独取决于肉体,而是取决于心灵和肉体的结合。那些将心灵作为它们原因的知觉是我们的意志力、想象力或思想。当心灵不能阻止它自己在某个时刻去知觉它意欲某物时,这种意欲是情感。“尽管从我们心灵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意愿某物的行动,可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心灵中的一个意识其意愿事物的情感。”(27)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页。既然意愿的知觉和意愿它自身是一回事,那么,将其思考为心灵的一个行动就是可能的。“由于这个知觉和这个意志活动事实上只是同一个事物,并且它们又总是由那些最高贵的人来命名的,由此,人们就不太习惯于称它们为情感,而只是称它们为一种行动。”(28)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15页。因此,“行动和情感总是一个东西,是依据两个不同的相关主体给出的两个不同的名称。”(29)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3页。行动与情感是同一种变化的不同名称:情感作为变化是从经验它的主体立场出发,即从被感动和触动的接受者立场上而言的;行动作为变化则是从使它发生的主体立场出发,即使运动和使触动的发动者立场而言的。
只有那些由身体引起的知觉,排除大部分与神经有关的那些,剩下的与动物精气有关的部分,在最确切和最特定的意义上,才被笛卡尔称为激情。激情把身体的行动作为它们的原因。准确地说,心灵的激情由本能驱动,由大脑过滤溶于血液中的细微颗粒在封闭的血管循环系统中极快地运动以及机械地持续运动。斯宾诺莎无法理解笛卡尔将情感的原因归于松果体,将情感的直接原因看作是本能的运动;更不能理解单凭意志的力量控制松果体来论证心灵能够绝对地控制情感。他根据情感产生的原因区分了两种情感(affects):行动和激情(passions)。行动是那些充分的、完整的、只由我们的本性来解释原因的情感;激情则是不充分,或部分的、也就是不能只凭我们的本性来解释,也应该考虑外部原因的情感。他说:“身体不能决定心灵,使它思想,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使它动或静,更不能决定它使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如果有任何别的东西的话。”(30)斯宾诺莎:《伦理学》,第99页。因此,激情不是取决于身体,而是取决于不充分的观念,行动则产生于充分的观念。由于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不能仅凭它自身而不通过其他部分被设想。一个人并不总是仅凭其本性而行动,也会遵从于外部原因行动,而外部原因并不必然地契合他的本性。
笛卡尔认为,心灵,根据它的自由意志以及无限的决断力,对它自己的行动拥有绝对的和直接的掌控力,但它并不能直接地掌控它的激情。激情是身体的一个行动,只要运动在心脏、血液、精神中没有停止,激情就会起作用。心灵能够很容易克服微弱的情感波动,比如,通过分一下神,或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来克服一段轻微的噪音或一个轻微的疼痛,但它不能克服强烈的情感。“在这种激动还是很活跃的时候,意志能做的最大事情是不去赞成激动的效果,并尽力控制一些它能适应的身体运动。例如,如果生气使得我们的手举了起来,试图击打别人的时候,意志一般可以使我们有所克制,如果害怕驱动我们的下肢准备逃跑,意志则可以让我们停下来,等等。”(31)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30-31页。
斯宾诺莎认可笛卡尔关于良好教养的心灵能够获得对它的情感的控制力,但这种控制力不是来自自由意志,而毋宁是来自理性的力量,即理性对情感发生机制的全面认知。他指出,这种控制力不是心灵凌驾于身体之上的控制力,而是心灵对其自身的控制力。解释情感以及心灵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力量的关键在于关于心灵力量的严格的知识,在于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说:“对于身体的任何感触,我们没有不能形成某种清楚明晰的观念的。”(命题四)“由此可以推知,没有一个情感,我们对它不能形成一个清楚明晰的概念。”(32)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41页。由此才能区分起于不正确的观念的被动的情感,和依理性的命令而生活的德行。所以,他主张“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去寻求克制情感的药剂,除了力求对于情感加以正确理解外,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药剂了,因为……人的心灵除了具有思想的力量和构成正确观念的力量以外,没有别的力量”。(33)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42页。斯宾诺莎诉之于人类理性的理解力来克服情感,坚持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一个被动的情感只要当我们对它形成清楚明晰的观念时,便立即停止其为一个被动的情感。”(命题三)(34)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40页。命题三与命题四共同表明,一个理智的人虽然不会对情感免疫,但可以使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制止。可见,理智力量才是控制情感的关键,认识到情感的原因和决定治疗并不是两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被回溯为一个问题,即获得关于心灵力量的准确知识以对抗人的本能意愿。在他看来,笛卡尔并没有认识到心灵的能力,其关于情感的原因以及提出的治疗方案的一切错误都根源于此。概而言之,斯宾诺莎对笛卡尔提出了四点责难:(1)批评笛卡尔将情感归于心灵与肉体统一的构想。(2)批评笛卡尔对心灵力量与身体运动之间相互作用的虚构。(3)批评笛卡尔关于松果体的虚构。(4)批评笛卡尔关于自由意志和绝对力量的虚构。人并非完全受制于被动的情感,只要人能够在理解原因的基础上主动地去完成该原因导向的行为结果,他就是自由的。斯宾诺莎说:“唯有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人们的本性才会必然地永远地相符合。”(35)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94页。违背本性的情感是恶的,而符合本性的情感是善的,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对情感的理解愈多,我们就愈能控制情感,一旦心灵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就再也不会受情感的奴役。因此,只有通过获取正确的观念(对原因的认识)、通过理性的认知和理解必然性,才能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安宁。
小 结
斯宾诺莎在给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的信(约 1661 年 9 月)中,将笛卡尔(和培根)的错误总结为三点:“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两人对于一切事物的第一原因和根源的认识迷途太远了;其次,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的心灵的真正本性;第三,他们从未找到错误的真正原因。”(36)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7页。就现代理性主义传统而言,笛卡尔主义只有经过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与反驳的洗礼之后才能起作用。斯宾诺莎在现代性开端之思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得到彰显:(1)泛神论取代二元论,通过实体与样式的区分初步回答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2)建立了一种“道德理智论”传统,将对自由意志的拒斥与对自然必然性的贯彻结合起来,人类只能在对自然必然性的认知中找到幸福,唯一可能的道德行为在于尽可能地理解人类的本性和情感,“道德理智论”主张,充足的知识对于纠正情感的混乱以及带来美德和幸福是必要和充分的;(3)斯宾诺莎将真理与确定性等同起来,废黜了笛卡尔方法的两个关键特征——怀疑与“我思”。对笛卡尔来说,我们有真实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是天赋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疑它,更要证明它是真实的。而斯宾诺莎直接否定了天赋观念论,他确立的哲学方法论主要任务是寻求改进和提升我们理智的方法,引导理智辨析真实(确定的)观念与不充分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所寻求的方法只能是一种反身观念,即关于什么是真实观念的观念。斯宾诺莎对笛卡尔的批评与反驳告诉我们,真正将笛卡尔主义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贯彻到底的哲学是斯宾诺莎主义,谢林曾在给黑格尔的信中说,我现在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斯宾诺莎所确立的理性至上原则始终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以及德国观念论绝对理性是以自身为中介的自我认识中隐秘地起着作用。斯宾诺莎主义在德国观念论中的隐秘作用将成为下篇的主题。